声明: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.org,kanripo.org, db.itkc.or.kr 和 zh.wikisource.org
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x 页
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
封事○上书
封事○上书
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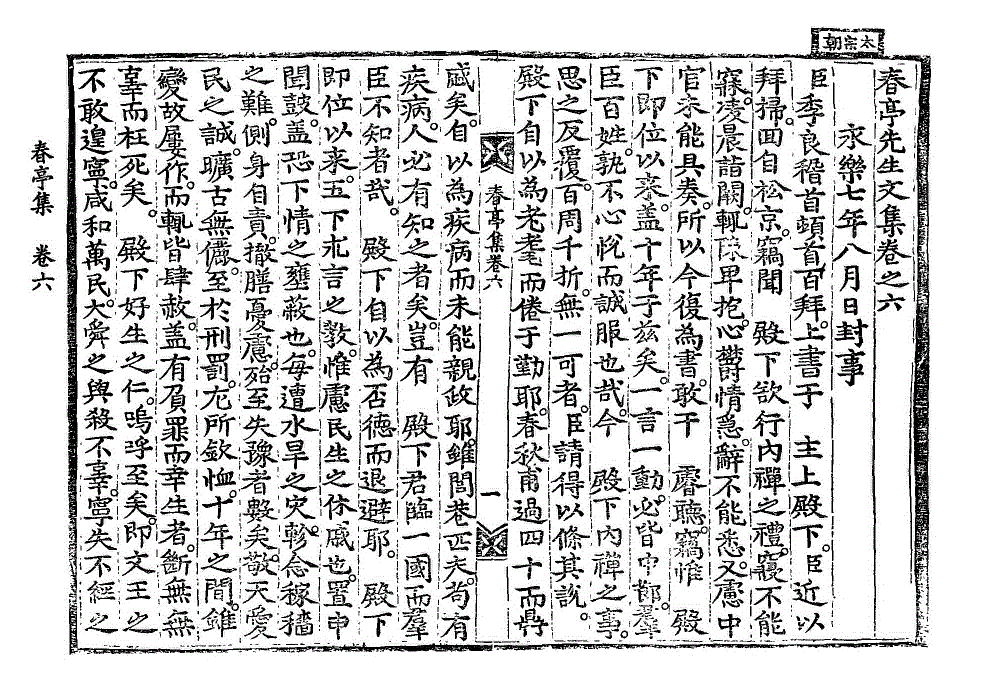 주-D001永乐七年八月日封事
주-D001永乐七年八月日封事臣季良稽首顿首百拜。上书于 主上殿下。臣近以拜扫。回自松京。窃闻 殿下欲行内禅之礼。寝不能寐。凌晨诣阙。辄陈卑抱。心郁情急。辞不能悉。又虑中官未能具奏。所以今复为书。敢干 睿听。窃惟 殿下即位以来。盖十年于玆矣。一言一动。必皆中节。群臣百姓。孰不心悦而诚服也哉。今 殿下内禅之事。思之反覆。百周千折。无一可者。臣请得以条其说。 殿下自以为老耄而倦于勤耶。春秋甫过四十而鼎盛矣。自以为疾病而未能亲政耶。虽闾巷匹夫。苟有疾病。人必有知之者矣。岂有 殿下君临一国而群臣不知者哉。 殿下自以为否德而退避耶。 殿下即位以来。五下求言之教。惟虑民生之休戚也。置申闻鼓。盖恐下情之壅蔽也。每遭水旱之灾。轸念稼穑之难。侧身自责。撤膳忧虑。殆至失豫者数矣。敬天爱民之诚。旷古无俪。至于刑罚。尤所钦恤。十年之间。虽变故屡作。而辄皆肆赦。盖有负罪而幸生者。断无无辜而枉死矣。 殿下好生之仁。呜呼至矣。即文王之不敢遑宁。咸和万民。大舜之与杀不辜。宁失不经之
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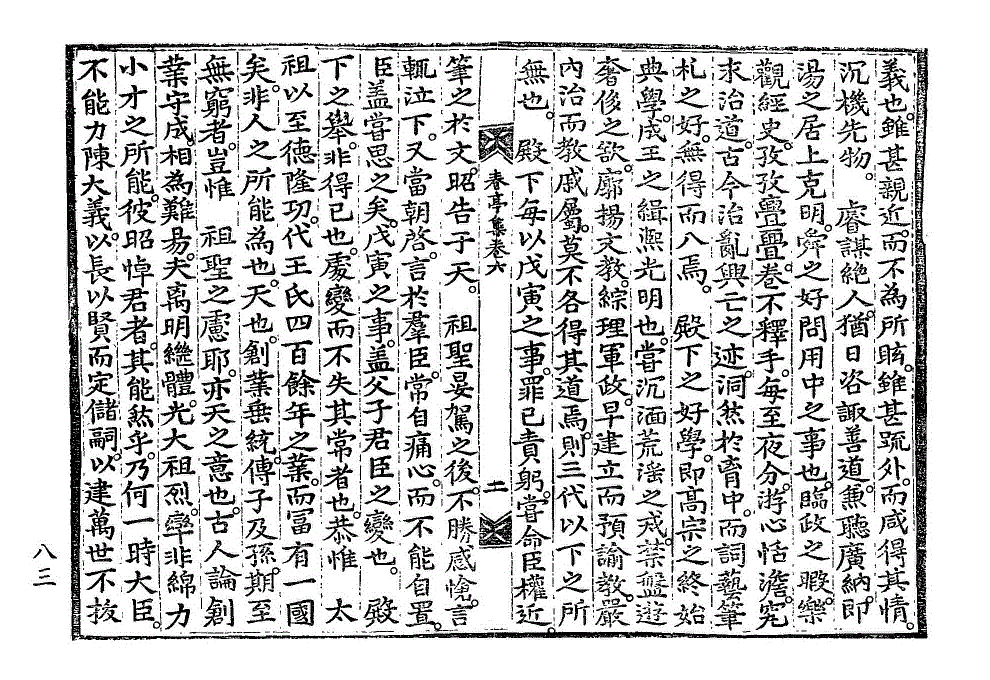 义也。虽甚亲近。而不为所眩。虽甚疏外。而咸得其情。沉机先物。 睿谋绝人。犹日咨诹善道。兼听广纳。即汤之居上克明。舜之好问用中之事也。临政之暇。乐观经史。孜孜亹亹。卷不释手。每至夜分。游心恬澹。究求治道。古今治乱兴亡之迹。洞然于胸中。而词艺笔札之好。无得而入焉。 殿下之好学。即高宗之终始典学。成王之缉熙光明也。尝沉湎荒淫之戒。禁盘游奢侈之欲。廓扬文教。综理军政。早建立而预谕教。严内治而教戚属。莫不各得其道焉。则三代以下之所无也。 殿下每以戊寅之事。罪已责躬。尝命臣权近。笔之于文。昭告于天。 祖圣晏驾之后。不胜感怆。言辄泣下。又当朝启。言于群臣。常自痛心。而不能自置。臣盖尝思之矣。戊寅之事。盖父子君臣之变也。 殿下之举。非得已也。处变而不失其常者也。恭惟 太祖以至德隆功。代王氏四百馀年之业。而富有一国矣。非人之所能为也。天也。创业垂统。传子及孙。期至无穷者。岂惟 祖圣之虑耶。亦天之意也。古人论创业守成。相为难易。夫离明继体。光大祖烈。率非绵力小才之所能。彼昭悼君者。其能然乎。乃何一时大臣。不能力陈大义。以长以贤而定储嗣。以建万世不拔
义也。虽甚亲近。而不为所眩。虽甚疏外。而咸得其情。沉机先物。 睿谋绝人。犹日咨诹善道。兼听广纳。即汤之居上克明。舜之好问用中之事也。临政之暇。乐观经史。孜孜亹亹。卷不释手。每至夜分。游心恬澹。究求治道。古今治乱兴亡之迹。洞然于胸中。而词艺笔札之好。无得而入焉。 殿下之好学。即高宗之终始典学。成王之缉熙光明也。尝沉湎荒淫之戒。禁盘游奢侈之欲。廓扬文教。综理军政。早建立而预谕教。严内治而教戚属。莫不各得其道焉。则三代以下之所无也。 殿下每以戊寅之事。罪已责躬。尝命臣权近。笔之于文。昭告于天。 祖圣晏驾之后。不胜感怆。言辄泣下。又当朝启。言于群臣。常自痛心。而不能自置。臣盖尝思之矣。戊寅之事。盖父子君臣之变也。 殿下之举。非得已也。处变而不失其常者也。恭惟 太祖以至德隆功。代王氏四百馀年之业。而富有一国矣。非人之所能为也。天也。创业垂统。传子及孙。期至无穷者。岂惟 祖圣之虑耶。亦天之意也。古人论创业守成。相为难易。夫离明继体。光大祖烈。率非绵力小才之所能。彼昭悼君者。其能然乎。乃何一时大臣。不能力陈大义。以长以贤而定储嗣。以建万世不拔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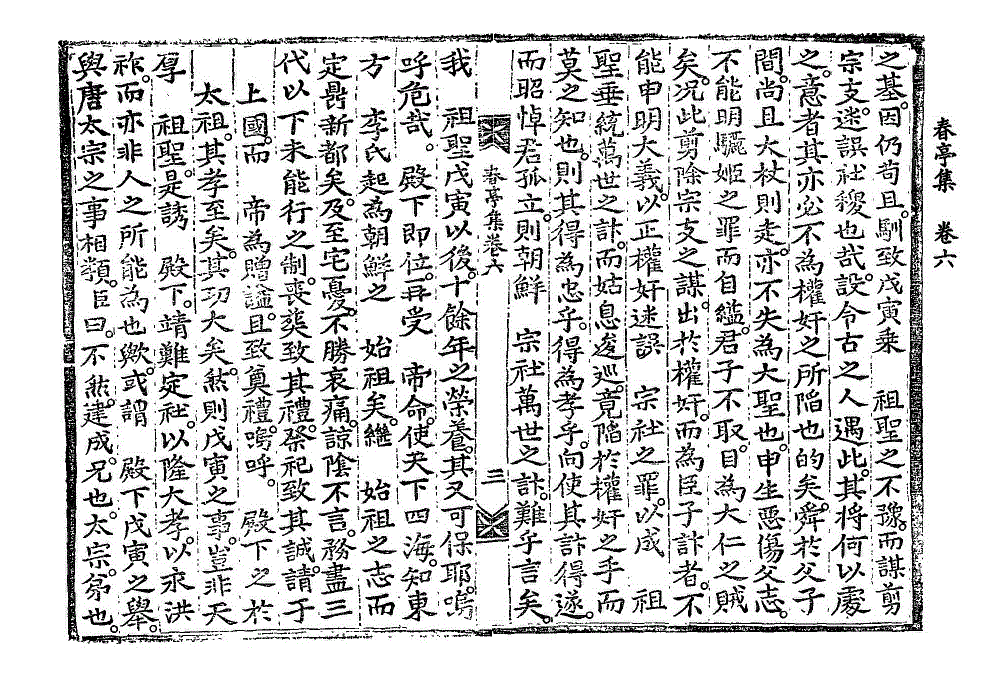 之基。因仍苟且。驯致戊寅乘 祖圣之不豫。而谋剪宗支。迷误社稷也哉。设令古之人遇此。其将何以处之。意者其亦必不为权奸之所陷也的矣。舜于父子间。尚且大杖则走。亦不失为大圣也。申生恶伤父志。不能明骊姬之罪而自缢。君子不取。目为大仁之贼矣。况此剪除宗支之谋。出于权奸。而为臣子计者。不能申明大义。以正权奸迷误 宗社之罪。以成 祖圣垂统万世之计。而姑息逡巡。竟陷于权奸之手而莫之知也。则其得为忠乎。得为孝乎。向使其计得遂。而昭悼君孤立。则朝鲜 宗社万世之计。难乎言矣。我 祖圣戊寅以后。十馀年之荣养。其又可保耶。呜呼危哉。 殿下即位。再受 帝命。使天下四海。知东方 李氏起为朝鲜之 始祖矣。继 始祖之志而定鼎新都矣。及至宅忧。不胜哀痛。谅阴不言。务尽三代以下未能行之制。丧葬致其礼。祭祀致其诚。请于 上国。而 帝为赠谥。且致奠礼。呜呼。 殿下之于 太祖。其孝至矣。其功大矣。然则戊寅之事。岂非天厚 祖圣。是诱 殿下。靖难定社。以隆大孝。以永洪祚。而亦非人之所能为也欤。或谓 殿下戊寅之举。与唐太宗之事相类。臣曰。不然。建成。兄也。太宗。弟也。
之基。因仍苟且。驯致戊寅乘 祖圣之不豫。而谋剪宗支。迷误社稷也哉。设令古之人遇此。其将何以处之。意者其亦必不为权奸之所陷也的矣。舜于父子间。尚且大杖则走。亦不失为大圣也。申生恶伤父志。不能明骊姬之罪而自缢。君子不取。目为大仁之贼矣。况此剪除宗支之谋。出于权奸。而为臣子计者。不能申明大义。以正权奸迷误 宗社之罪。以成 祖圣垂统万世之计。而姑息逡巡。竟陷于权奸之手而莫之知也。则其得为忠乎。得为孝乎。向使其计得遂。而昭悼君孤立。则朝鲜 宗社万世之计。难乎言矣。我 祖圣戊寅以后。十馀年之荣养。其又可保耶。呜呼危哉。 殿下即位。再受 帝命。使天下四海。知东方 李氏起为朝鲜之 始祖矣。继 始祖之志而定鼎新都矣。及至宅忧。不胜哀痛。谅阴不言。务尽三代以下未能行之制。丧葬致其礼。祭祀致其诚。请于 上国。而 帝为赠谥。且致奠礼。呜呼。 殿下之于 太祖。其孝至矣。其功大矣。然则戊寅之事。岂非天厚 祖圣。是诱 殿下。靖难定社。以隆大孝。以永洪祚。而亦非人之所能为也欤。或谓 殿下戊寅之举。与唐太宗之事相类。臣曰。不然。建成。兄也。太宗。弟也。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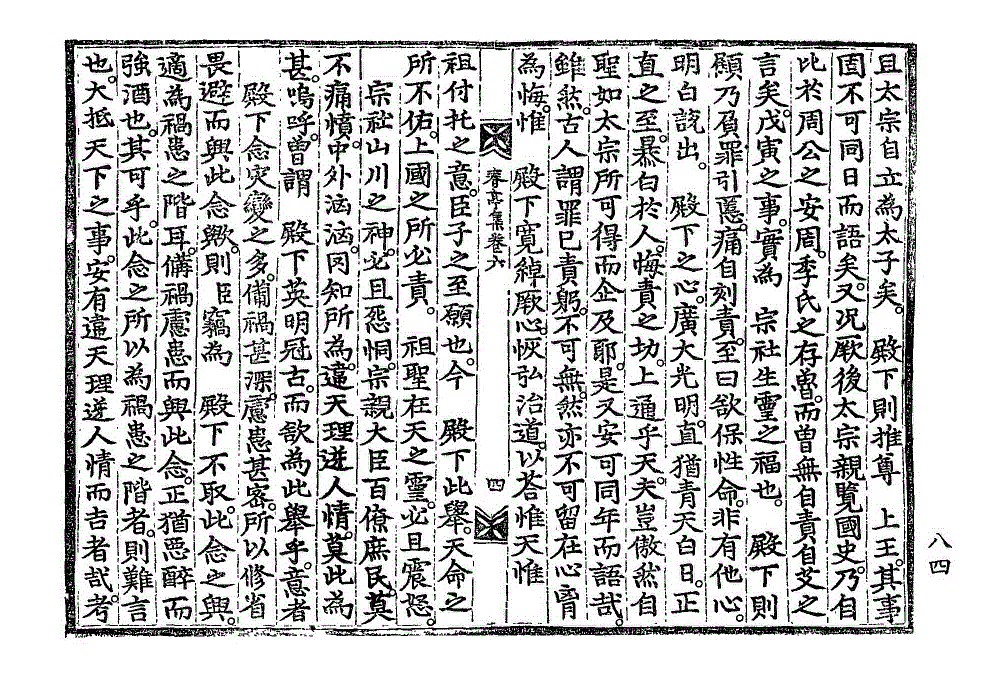 且太宗自立为太子矣。 殿下则推尊 上王。其事固不可同日而语矣。又况厥后太宗亲览国史。乃自比于周公之安周。季氏之存鲁。而曾无自责自艾之言矣。戊寅之事。实为 宗社生灵之福也。 殿下则顾乃负罪引慝。痛自刻责。至曰欲保性命。非有他心。明白说出。 殿下之心。广大光明。直犹青天白日。正直之至。暴白于人。悔责之切。上通乎天。夫岂傲然自圣如太宗所可得而企及耶。是又安可同年而语哉。虽然。古人谓罪己责躬。不可无。然亦不可留在心胸为悔。惟 殿下宽绰厥心。恢弘治道。以答惟天惟 祖付托之意。臣子之至愿也。今 殿下此举。天命之所不佑。上国之所必责。 祖圣在天之灵。必且震怒。 宗社山川之神。必且怨恫。宗亲大臣百僚庶民。莫不痛愤。中外汹汹。罔知所为。违天理逆人情。莫此为甚。呜呼。曾谓 殿下英明冠古。而欲为此举乎。意者 殿下念灾变之多。备祸甚深。虑患甚密。所以修省畏避而兴此念欤。则臣窃为 殿下不取。此念之兴。适为祸患之阶耳。备祸虑患而兴此念。正犹恶醉而强酒也。其可乎。此念之所以为祸患之阶者。则难言也。大抵天下之事。安有违天理逆人情而吉者哉。考
且太宗自立为太子矣。 殿下则推尊 上王。其事固不可同日而语矣。又况厥后太宗亲览国史。乃自比于周公之安周。季氏之存鲁。而曾无自责自艾之言矣。戊寅之事。实为 宗社生灵之福也。 殿下则顾乃负罪引慝。痛自刻责。至曰欲保性命。非有他心。明白说出。 殿下之心。广大光明。直犹青天白日。正直之至。暴白于人。悔责之切。上通乎天。夫岂傲然自圣如太宗所可得而企及耶。是又安可同年而语哉。虽然。古人谓罪己责躬。不可无。然亦不可留在心胸为悔。惟 殿下宽绰厥心。恢弘治道。以答惟天惟 祖付托之意。臣子之至愿也。今 殿下此举。天命之所不佑。上国之所必责。 祖圣在天之灵。必且震怒。 宗社山川之神。必且怨恫。宗亲大臣百僚庶民。莫不痛愤。中外汹汹。罔知所为。违天理逆人情。莫此为甚。呜呼。曾谓 殿下英明冠古。而欲为此举乎。意者 殿下念灾变之多。备祸甚深。虑患甚密。所以修省畏避而兴此念欤。则臣窃为 殿下不取。此念之兴。适为祸患之阶耳。备祸虑患而兴此念。正犹恶醉而强酒也。其可乎。此念之所以为祸患之阶者。则难言也。大抵天下之事。安有违天理逆人情而吉者哉。考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5H 页
 之历代。验之前朝。可以监矣。书之召诰。有曰今天其命吉凶。命历年。知今我初服。臣断然以为国家治乱安危之机。在此一举也。臣于平日读书。至论先王享国或七十年或六十年或五十年四十年。未尝不以有望于 殿下。岂期 殿下享国甫及十年。而遽为退避之计。不念惟天惟 祖付托之重。百僚万姓哀痛之切耶。抑 殿下此举。非徒不可。亦必不能为。何者。凡国家之事。必君臣合谋。而后能有所济。小事尚然。况于以国家相传乎。使在朝群臣。苟皆无知而不忠也。则 殿下此举。容或可成。如稍有知而且忠也。则必皆从义而不从君矣。 殿下此举。谁与而成之。若乃纵威肆虐。不畏神怒。不顾民怨。愤然必为此。则夏桀,商受,秦始,隋炀之所行矣。而谓 殿下为之乎。 殿下惧天灾地怪之层见叠出。则延访群臣。日闻直言。脩明政事。以对上天仁爱 殿下谴告之意。使虽有其灾而无其应。可也。忧祸乱之萌。则当益收揽权纲。明炳几微。而图难于其易。为大于其细。衍义所载。甚详至悉。朝观夕览。时复思绎。可也。虑疾病之生。则平心易气。颐养太和。约情节欲。保定正性。诸方所著。其说多端。万机之暇。采择服行。可也。疾病之生。祸
之历代。验之前朝。可以监矣。书之召诰。有曰今天其命吉凶。命历年。知今我初服。臣断然以为国家治乱安危之机。在此一举也。臣于平日读书。至论先王享国或七十年或六十年或五十年四十年。未尝不以有望于 殿下。岂期 殿下享国甫及十年。而遽为退避之计。不念惟天惟 祖付托之重。百僚万姓哀痛之切耶。抑 殿下此举。非徒不可。亦必不能为。何者。凡国家之事。必君臣合谋。而后能有所济。小事尚然。况于以国家相传乎。使在朝群臣。苟皆无知而不忠也。则 殿下此举。容或可成。如稍有知而且忠也。则必皆从义而不从君矣。 殿下此举。谁与而成之。若乃纵威肆虐。不畏神怒。不顾民怨。愤然必为此。则夏桀,商受,秦始,隋炀之所行矣。而谓 殿下为之乎。 殿下惧天灾地怪之层见叠出。则延访群臣。日闻直言。脩明政事。以对上天仁爱 殿下谴告之意。使虽有其灾而无其应。可也。忧祸乱之萌。则当益收揽权纲。明炳几微。而图难于其易。为大于其细。衍义所载。甚详至悉。朝观夕览。时复思绎。可也。虑疾病之生。则平心易气。颐养太和。约情节欲。保定正性。诸方所著。其说多端。万机之暇。采择服行。可也。疾病之生。祸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5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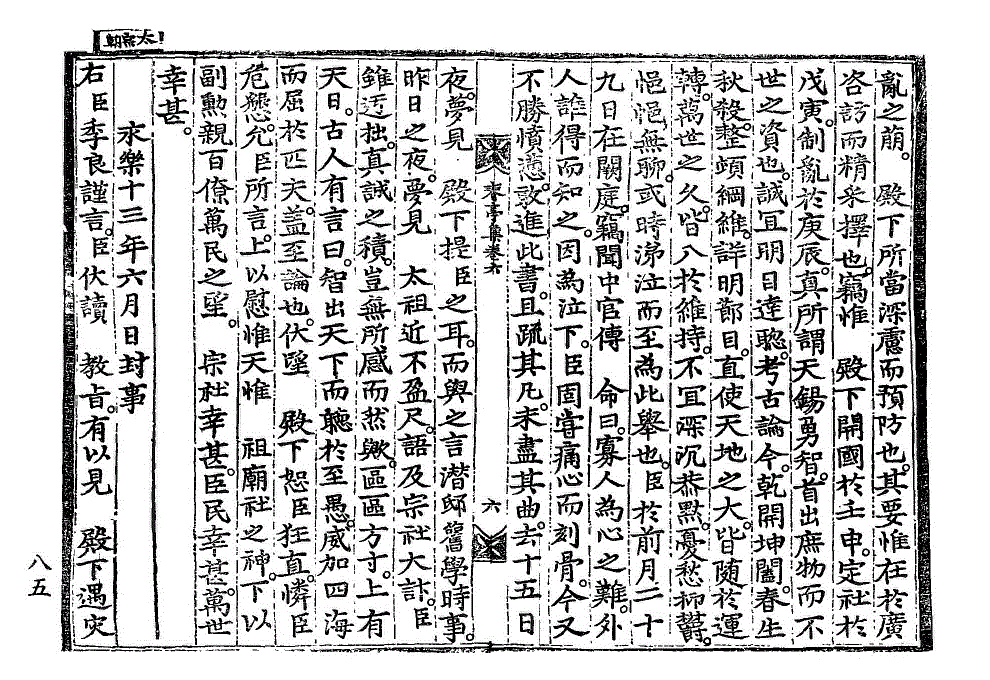 乱之萌。 殿下所当深虑而预防也。其要惟在于广咨访而精采择也。窃惟 殿下开国于壬申。定社于戊寅。制乱于庚辰。真所谓天锡勇智。首出庶物而不世之资也。诚宜明目达聪。考古论今。乾开坤阖。春生秋杀。整顿纲维。详明节目。直使天地之大。皆随于运转。万世之久。皆入于维持。不宜深沉恭默。忧愁抑郁。悒悒无聊。或时涕泣而至为此举也。臣于前月二十九日在阙庭。窃闻中官传 命曰。寡人为心之难。外人谁得而知之。因为泣下。臣固尝痛心而刻骨。今又不胜愤懑。敢敦进此书。且疏其凡。未尽其曲。去十五日夜。梦见 殿下提臣之耳。而与之言潜邸旧学时事。昨日之夜。梦见 太祖近不盈尺。语及宗社大计。臣虽迂拙。真诚之积。岂无所感而然欤。区区方寸。上有天日。古人有言曰。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。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。盖至论也。伏望 殿下恕臣狂直。怜臣危恳。允臣所言。上以慰惟天惟 祖庙社之神。下以副勋亲百僚万民之望。 宗社幸甚。臣民幸甚。万世幸甚。
乱之萌。 殿下所当深虑而预防也。其要惟在于广咨访而精采择也。窃惟 殿下开国于壬申。定社于戊寅。制乱于庚辰。真所谓天锡勇智。首出庶物而不世之资也。诚宜明目达聪。考古论今。乾开坤阖。春生秋杀。整顿纲维。详明节目。直使天地之大。皆随于运转。万世之久。皆入于维持。不宜深沉恭默。忧愁抑郁。悒悒无聊。或时涕泣而至为此举也。臣于前月二十九日在阙庭。窃闻中官传 命曰。寡人为心之难。外人谁得而知之。因为泣下。臣固尝痛心而刻骨。今又不胜愤懑。敢敦进此书。且疏其凡。未尽其曲。去十五日夜。梦见 殿下提臣之耳。而与之言潜邸旧学时事。昨日之夜。梦见 太祖近不盈尺。语及宗社大计。臣虽迂拙。真诚之积。岂无所感而然欤。区区方寸。上有天日。古人有言曰。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。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。盖至论也。伏望 殿下恕臣狂直。怜臣危恳。允臣所言。上以慰惟天惟 祖庙社之神。下以副勋亲百僚万民之望。 宗社幸甚。臣民幸甚。万世幸甚。주-D001永乐十三年六月日封事
右臣季良谨言。臣伏读 教旨。有以见 殿下遇灾
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6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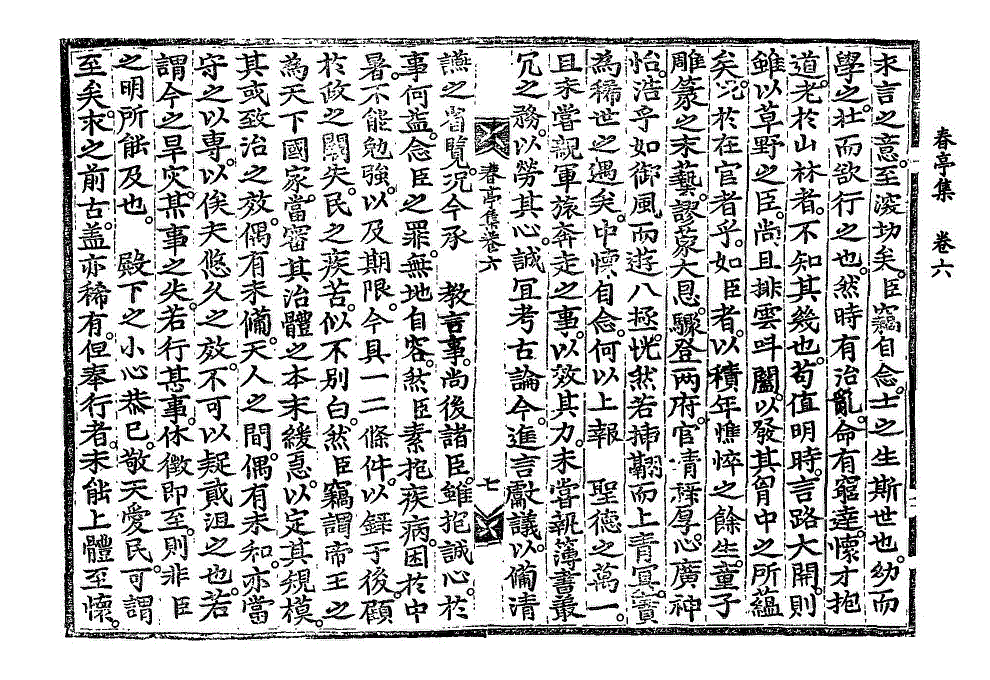 求言之意。至深切矣。臣窃自念。士之生斯世也。幼而学之。壮而欲行之也。然时有治乱。命有穷达。怀才抱道。老于山林者。不知其几也。苟值明时。言路大开。则虽以草野之臣。尚且排云叫阖。以发其胸中之所蕴矣。况于在官者乎。如臣者。以积年憔悴之馀生。童子雕篆之末艺。谬蒙大恩。骤登两府。官清禄厚。心广神怡。浩乎如御风而游八极。恍然若插翮而上青冥。实为稀世之遇矣。中怀自念。何以上报 圣德之万一。且未尝亲军旅奔走之事。以效其力。未尝执簿书丛冗之务。以劳其心。诚宜考古论今。进言献议。以备清宴之省览。况今承 教言事。尚后诸臣。虽抱诚心。于事何益。念臣之罪。无地自容。然臣素抱疾病。困于中暑。不能勉强。以及期限。今具一二条件。以录于后。顾于政之阙失。民之疾苦。似不别白。然臣窃谓帝王之为天下国家。当审其治体之本末缓急。以定其规模。其或致治之效。偶有未备。天人之间。偶有未和。亦当守之以专。以俟夫悠久之效。不可以疑贰沮之也。若谓今之旱灾。某事之失。若行甚事。休徵即至。则非臣之明所能及也。 殿下之小心恭己。敬天爱民。可谓至矣。求之前古。盖亦稀有。但奉行者。未能上体至怀。
求言之意。至深切矣。臣窃自念。士之生斯世也。幼而学之。壮而欲行之也。然时有治乱。命有穷达。怀才抱道。老于山林者。不知其几也。苟值明时。言路大开。则虽以草野之臣。尚且排云叫阖。以发其胸中之所蕴矣。况于在官者乎。如臣者。以积年憔悴之馀生。童子雕篆之末艺。谬蒙大恩。骤登两府。官清禄厚。心广神怡。浩乎如御风而游八极。恍然若插翮而上青冥。实为稀世之遇矣。中怀自念。何以上报 圣德之万一。且未尝亲军旅奔走之事。以效其力。未尝执簿书丛冗之务。以劳其心。诚宜考古论今。进言献议。以备清宴之省览。况今承 教言事。尚后诸臣。虽抱诚心。于事何益。念臣之罪。无地自容。然臣素抱疾病。困于中暑。不能勉强。以及期限。今具一二条件。以录于后。顾于政之阙失。民之疾苦。似不别白。然臣窃谓帝王之为天下国家。当审其治体之本末缓急。以定其规模。其或致治之效。偶有未备。天人之间。偶有未和。亦当守之以专。以俟夫悠久之效。不可以疑贰沮之也。若谓今之旱灾。某事之失。若行甚事。休徵即至。则非臣之明所能及也。 殿下之小心恭己。敬天爱民。可谓至矣。求之前古。盖亦稀有。但奉行者。未能上体至怀。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6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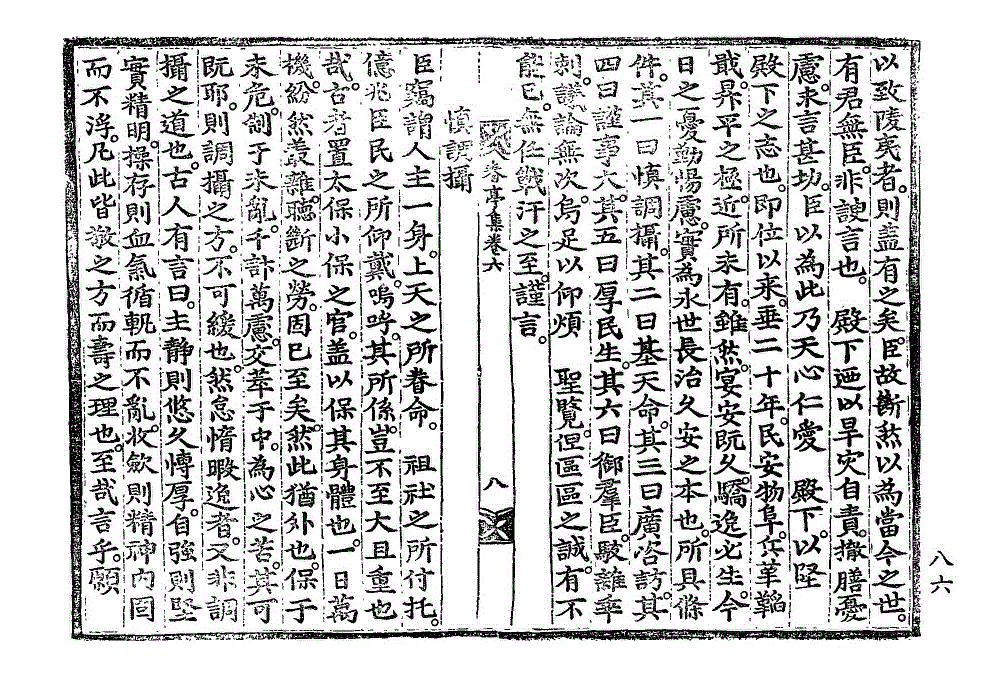 以致陵夷者。则盖有之矣。臣故断然以为当今之世。有君无臣。非谀言也。 殿下乃以旱灾自责。撤膳忧虑。求言甚切。臣以为此乃天心仁爱 殿下。以坚 殿下之志也。即位以来。垂二十年。民安物阜。兵革韬戢。升平之极。近所未有。虽然。宴安既久。骄逸必生。今日之忧勤惕虑。实为永世长治久安之本也。所具条件。其一曰慎调摄。其二曰基天命。其三曰广咨访。其四曰谨事大。其五曰厚民生。其六曰御群臣。驳杂乖剌。议论无次。乌足以仰烦 圣览。但区区之诚。有不能已。无任战汗之至。谨言。
以致陵夷者。则盖有之矣。臣故断然以为当今之世。有君无臣。非谀言也。 殿下乃以旱灾自责。撤膳忧虑。求言甚切。臣以为此乃天心仁爱 殿下。以坚 殿下之志也。即位以来。垂二十年。民安物阜。兵革韬戢。升平之极。近所未有。虽然。宴安既久。骄逸必生。今日之忧勤惕虑。实为永世长治久安之本也。所具条件。其一曰慎调摄。其二曰基天命。其三曰广咨访。其四曰谨事大。其五曰厚民生。其六曰御群臣。驳杂乖剌。议论无次。乌足以仰烦 圣览。但区区之诚。有不能已。无任战汗之至。谨言。慎调摄
臣窃谓人主一身。上天之所眷命。 祖社之所付托。亿兆臣民之所仰戴。呜呼。其所系。岂不至大且重也哉。古者置太保小保之官。盖以保其身体也。一日万机。纷然丛杂。听断之劳。固已至矣。然此犹外也。保于未危。制于未乱。千计万虑。交萃于中。为心之苦。其可既耶。则调摄之方。不可缓也。然怠惰暇逸者。又非调摄之道也。古人有言曰。主静则悠久博厚。自强则坚实精明。操存则血气循轨而不乱。收敛则精神内固而不浮。凡此皆敬之方而寿之理也。至哉言乎。愿
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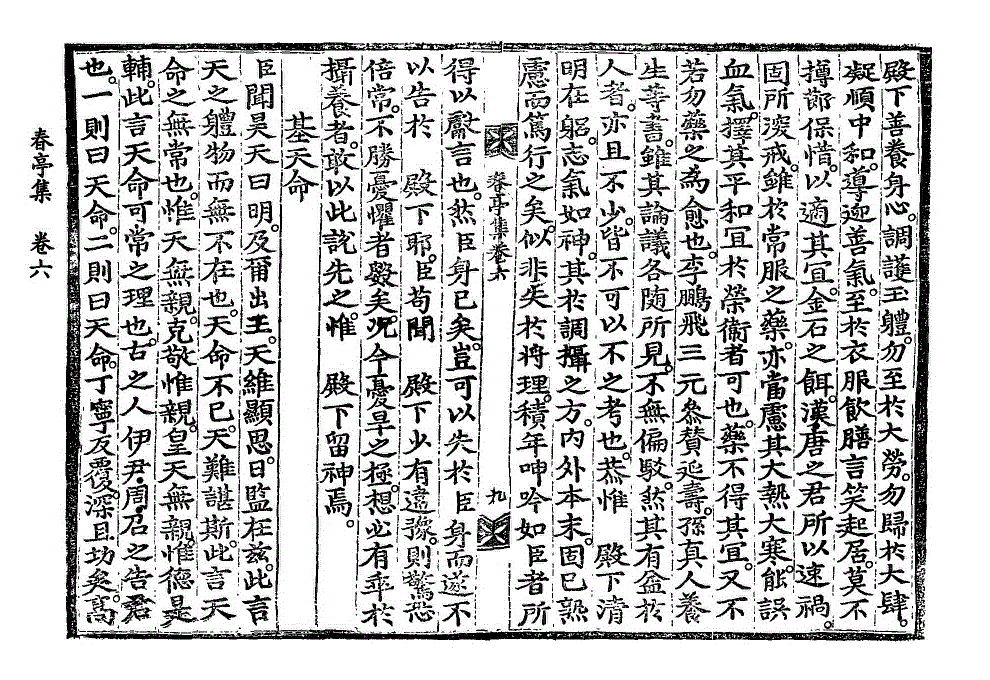 殿下善养身心。调护玉体。勿至于大劳。勿归于大肆。凝顺中和。导迎善气。至于衣服饮膳言笑起居。莫不撙节保惜。以适其宜。金石之饵。汉,唐之君所以速祸。固所深戒。虽于常服之药。亦当虑其大热大寒。能误血气。择其平和宜于荣卫者可也。药不得其宜。又不若勿药之为愈也。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。孙真人养生等书。虽其论议各随所见。不无偏驳。然其有益于人者。亦且不少。皆不可以不之考也。恭惟 殿下清明在躬。志气如神。其于调摄之方。内外本末。固已熟虑而笃行之矣。似非失于将理。积年呻吟如臣者所得以献言也。然臣身已矣。岂可以失于臣身而遂不以告于 殿下耶。臣苟闻 殿下少有违豫。则惊恐倍常。不胜忧惧者数矣。况今忧旱之极。想必有乖于摄养者。敢以此说先之。惟 殿下留神焉。
殿下善养身心。调护玉体。勿至于大劳。勿归于大肆。凝顺中和。导迎善气。至于衣服饮膳言笑起居。莫不撙节保惜。以适其宜。金石之饵。汉,唐之君所以速祸。固所深戒。虽于常服之药。亦当虑其大热大寒。能误血气。择其平和宜于荣卫者可也。药不得其宜。又不若勿药之为愈也。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。孙真人养生等书。虽其论议各随所见。不无偏驳。然其有益于人者。亦且不少。皆不可以不之考也。恭惟 殿下清明在躬。志气如神。其于调摄之方。内外本末。固已熟虑而笃行之矣。似非失于将理。积年呻吟如臣者所得以献言也。然臣身已矣。岂可以失于臣身而遂不以告于 殿下耶。臣苟闻 殿下少有违豫。则惊恐倍常。不胜忧惧者数矣。况今忧旱之极。想必有乖于摄养者。敢以此说先之。惟 殿下留神焉。基天命
臣闻昊天曰明。及尔出王。天维显思。日监在玆。此言天之体物而无不在也。天命不已。天难谌斯。此言天命之无常也。惟天无亲。克敬惟亲。皇天无亲。惟德是辅。此言天命可常之理也。古之人伊尹,周,召之告君也。一则曰天命。二则曰天命。丁宁反覆。深且切矣。高
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7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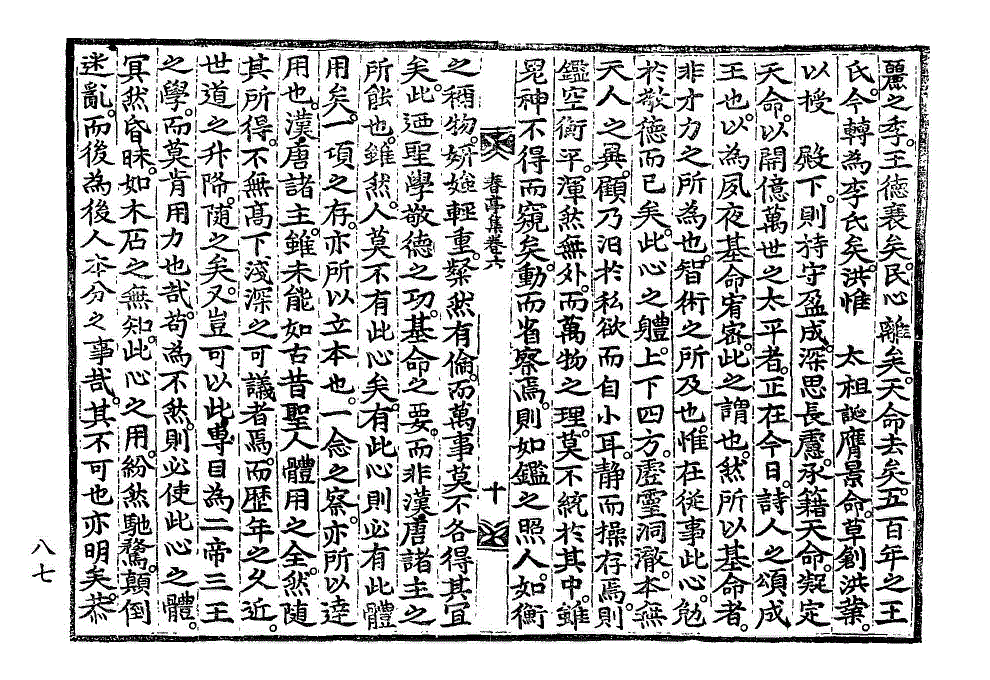 丽之季。王德衰矣。民心离矣。天命去矣。五百年之王氏。今转为李氏矣。洪惟 太祖诞膺景命。草创洪业。以授 殿下。则持守盈成。深思长虑。承籍天命。凝定天命。以开亿万世之太平者。正在今日。诗人之颂成王也。以为夙夜基命宥密。此之谓也。然所以基命者。非才力之所为也。智术之所及也。惟在从事此心。勉于敬德而已矣。此心之体。上下四方。虚灵洞澈。本无天人之异。顾乃汩于私欲而自小耳。静而操存焉。则鉴空衡平。浑然无外。而万物之理。莫不统于其中。虽鬼神不得而窥矣。动而省察焉。则如鉴之照人。如衡之称物。妍媸轻重。粲然有伦。而万事莫不各得其宜矣。此乃圣学敬德之功。基命之要。而非汉,唐诸主之所能也。虽然。人莫不有此心矣。有此心则必有此体用矣。一顷之存。亦所以立本也。一念之察。亦所以达用也。汉,唐诸主。虽未能如古昔圣人体用之全。然随其所得。不无高下浅深之可议者焉。而历年之久近。世道之升降。随之矣。又岂可以此专目为二帝三王之学。而莫肯用力也哉。苟为不然。则必使此心之体。冥然昏昧。如木石之无知。此心之用。纷然驰骛。颠倒迷乱。而后为后人本分之事哉。其不可也亦明矣。恭
丽之季。王德衰矣。民心离矣。天命去矣。五百年之王氏。今转为李氏矣。洪惟 太祖诞膺景命。草创洪业。以授 殿下。则持守盈成。深思长虑。承籍天命。凝定天命。以开亿万世之太平者。正在今日。诗人之颂成王也。以为夙夜基命宥密。此之谓也。然所以基命者。非才力之所为也。智术之所及也。惟在从事此心。勉于敬德而已矣。此心之体。上下四方。虚灵洞澈。本无天人之异。顾乃汩于私欲而自小耳。静而操存焉。则鉴空衡平。浑然无外。而万物之理。莫不统于其中。虽鬼神不得而窥矣。动而省察焉。则如鉴之照人。如衡之称物。妍媸轻重。粲然有伦。而万事莫不各得其宜矣。此乃圣学敬德之功。基命之要。而非汉,唐诸主之所能也。虽然。人莫不有此心矣。有此心则必有此体用矣。一顷之存。亦所以立本也。一念之察。亦所以达用也。汉,唐诸主。虽未能如古昔圣人体用之全。然随其所得。不无高下浅深之可议者焉。而历年之久近。世道之升降。随之矣。又岂可以此专目为二帝三王之学。而莫肯用力也哉。苟为不然。则必使此心之体。冥然昏昧。如木石之无知。此心之用。纷然驰骛。颠倒迷乱。而后为后人本分之事哉。其不可也亦明矣。恭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8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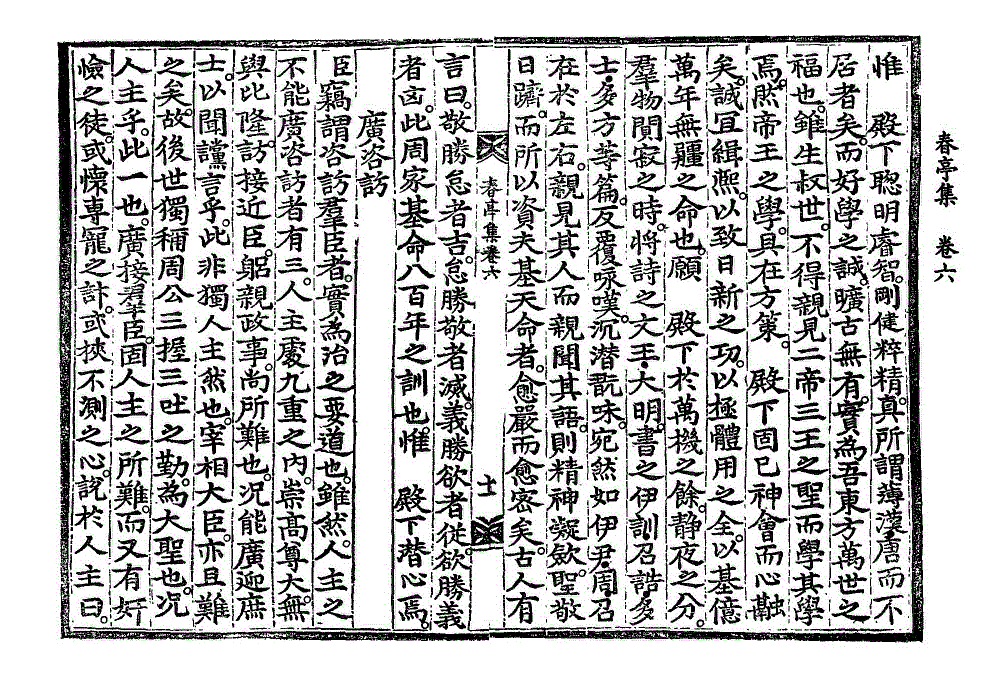 惟 殿下聪明睿智。刚健粹精。真所谓薄汉,唐而不居者矣。而好学之诚。旷古无有。实为吾东方万世之福也。虽生叔世。不得亲见二帝三王之圣而学其学焉。然帝王之学。具在方策。 殿下固已神会而心融矣。诚宜缉熙。以致日新之功。以极体用之全。以基亿万年无疆之命也。愿 殿下于万机之馀。静夜之分。群物阒寂之时。将诗之文王,大明。书之伊训,召诰,多士,多方等篇。反覆咏叹。沉潜玩味。宛然如伊尹,周,召在于左右。亲见其人而亲闻其语。则精神凝敛。圣敬日跻。而所以资夫基天命者。愈严而愈密矣。古人有言曰。敬胜怠者吉。怠胜敬者灭。义胜欲者从。欲胜义者凶。此周家基命八百年之训也。惟 殿下潜心焉。
惟 殿下聪明睿智。刚健粹精。真所谓薄汉,唐而不居者矣。而好学之诚。旷古无有。实为吾东方万世之福也。虽生叔世。不得亲见二帝三王之圣而学其学焉。然帝王之学。具在方策。 殿下固已神会而心融矣。诚宜缉熙。以致日新之功。以极体用之全。以基亿万年无疆之命也。愿 殿下于万机之馀。静夜之分。群物阒寂之时。将诗之文王,大明。书之伊训,召诰,多士,多方等篇。反覆咏叹。沉潜玩味。宛然如伊尹,周,召在于左右。亲见其人而亲闻其语。则精神凝敛。圣敬日跻。而所以资夫基天命者。愈严而愈密矣。古人有言曰。敬胜怠者吉。怠胜敬者灭。义胜欲者从。欲胜义者凶。此周家基命八百年之训也。惟 殿下潜心焉。广咨访
臣窃谓咨访群臣者。实为治之要道也。虽然。人主之不能广咨访者有三。人主处九重之内。崇高尊大。无与比隆。访接近臣。躬亲政事。尚所难也。况能广迎庶士。以闻谠言乎。此非独人主然也。宰相大臣。亦且难之矣。故后世独称周公三握三吐之勤。为大圣也。况人主乎。此一也。广接群臣。固人主之所难。而又有奸憸之徒。或怀专宠之计。或挟不测之心。说于人主曰。
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8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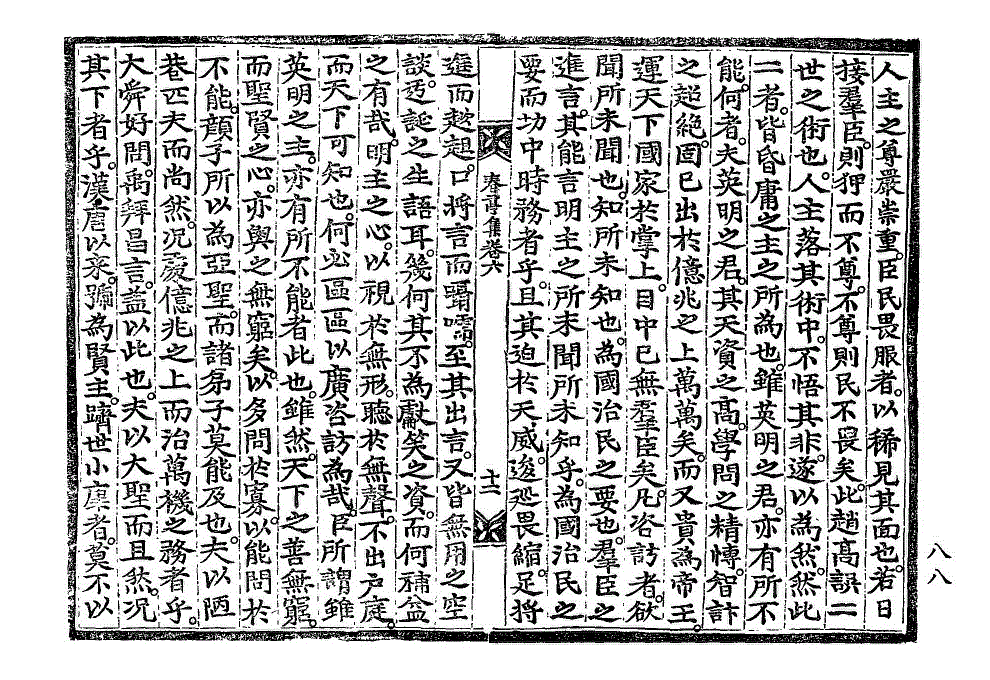 人主之尊严崇重。臣民畏服者。以稀见其面也。若日接群臣。则狎而不尊。不尊则民不畏矣。此赵高误二世之术也。人主落其术中。不悟其非。遂以为然。然此二者。皆昏庸之主之所为也。虽英明之君。亦有所不能。何者。夫英明之君。其天资之高。学问之精博。智计之超绝。固已出于亿兆之上万万矣。而又贵为帝王。运天下国家于掌上。目中已无群臣矣。凡咨访者。欲闻所未闻也。知所未知也。为国治民之要也。群臣之进言。其能言明主之所未闻所未知乎。为国治民之要而切中时务者乎。且其迫于天威。逡巡畏缩。足将进而趑趄。口将言而嗫嚅。至其出言。又皆无用之空谈。迂诞之生语耳。几何其不为献笑之资。而何补益之有哉。明主之心。以视于无形。听于无声。不出户庭。而天下可知也。何必区区以广咨访为哉。臣所谓虽英明之主。亦有所不能者此也。虽然。天下之善无穷。而圣贤之心。亦与之无穷矣。以多问于寡。以能问于不能。颜子所以为亚圣。而诸弟子莫能及也。夫以陋巷匹夫而尚然。况处亿兆之上而治万机之务者乎。大舜好问。禹拜昌言。盖以此也。夫以大圣而且然。况其下者乎。汉,唐以来。号为贤主。跻世小康者。莫不以
人主之尊严崇重。臣民畏服者。以稀见其面也。若日接群臣。则狎而不尊。不尊则民不畏矣。此赵高误二世之术也。人主落其术中。不悟其非。遂以为然。然此二者。皆昏庸之主之所为也。虽英明之君。亦有所不能。何者。夫英明之君。其天资之高。学问之精博。智计之超绝。固已出于亿兆之上万万矣。而又贵为帝王。运天下国家于掌上。目中已无群臣矣。凡咨访者。欲闻所未闻也。知所未知也。为国治民之要也。群臣之进言。其能言明主之所未闻所未知乎。为国治民之要而切中时务者乎。且其迫于天威。逡巡畏缩。足将进而趑趄。口将言而嗫嚅。至其出言。又皆无用之空谈。迂诞之生语耳。几何其不为献笑之资。而何补益之有哉。明主之心。以视于无形。听于无声。不出户庭。而天下可知也。何必区区以广咨访为哉。臣所谓虽英明之主。亦有所不能者此也。虽然。天下之善无穷。而圣贤之心。亦与之无穷矣。以多问于寡。以能问于不能。颜子所以为亚圣。而诸弟子莫能及也。夫以陋巷匹夫而尚然。况处亿兆之上而治万机之务者乎。大舜好问。禹拜昌言。盖以此也。夫以大圣而且然。况其下者乎。汉,唐以来。号为贤主。跻世小康者。莫不以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9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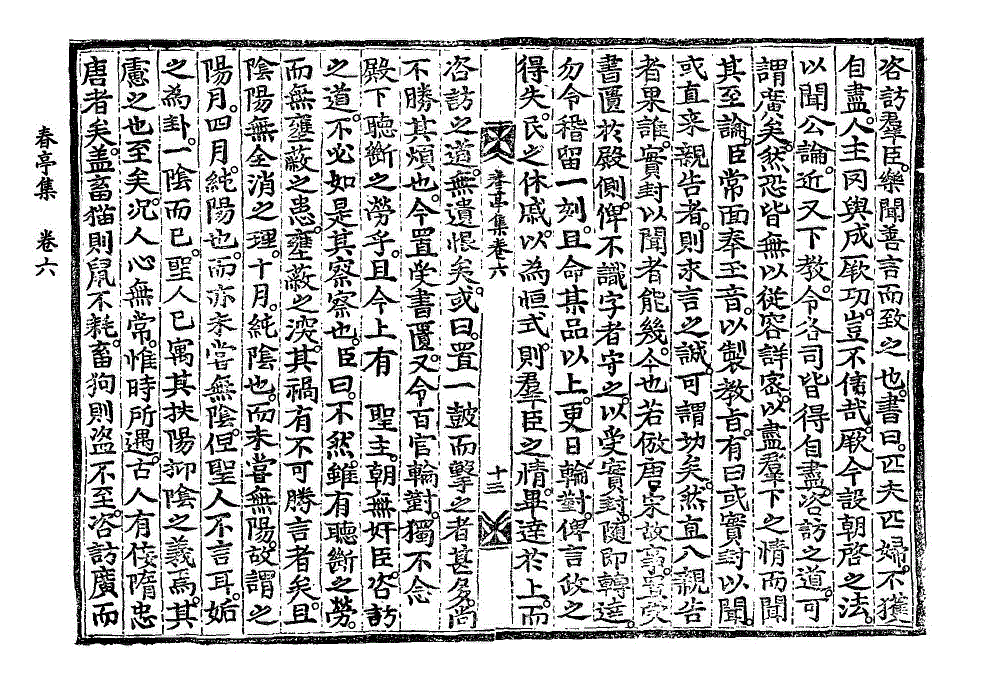 咨访群臣。乐闻善言而致之也。书曰。匹夫匹妇。不获自尽。人主罔与成厥功。岂不信哉。厥今设朝启之法。以闻公论。近又下教。令各司皆得自尽。咨访之道。可谓广矣。然恐皆无以从容详密。以尽群下之情而闻其至论。臣常面奉玉音。以制教旨。有曰或实封以闻。或直来亲告者。则求言之诚。可谓切矣。然直入亲告者果谁。实封以闻者能几。今也若仿唐,宋故事。置受书匮于殿侧。俾不识字者守之。以受实封。随即转达。勿令稽留一刻。且命某品以上。更日轮对。俾言政之得失。民之休戚。以为恒式。则群臣之情。毕达于上。而咨访之道。无遗恨矣。或曰。置一鼓而击之者甚多。尚不胜其烦也。今置受书匮。又令百官轮对。独不念 殿下听断之劳乎。且今上有 圣主。朝无奸臣。咨访之道。不必如是其察察也。臣曰。不然。虽有听断之劳。而无壅蔽之患。壅蔽之深。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。且阴阳无全消之理。十月。纯阴也。而未尝无阳。故谓之阳月。四月。纯阳也。而亦未尝无阴。但圣人不言耳。姤之为卦。一阴而已。圣人已寓其扶阳抑阴之义焉。其虑之也至矣。况人心无常。惟时所遇。古人有佞隋忠唐者矣。盖畜猫则鼠不耗。畜狗则盗不至。咨访广而
咨访群臣。乐闻善言而致之也。书曰。匹夫匹妇。不获自尽。人主罔与成厥功。岂不信哉。厥今设朝启之法。以闻公论。近又下教。令各司皆得自尽。咨访之道。可谓广矣。然恐皆无以从容详密。以尽群下之情而闻其至论。臣常面奉玉音。以制教旨。有曰或实封以闻。或直来亲告者。则求言之诚。可谓切矣。然直入亲告者果谁。实封以闻者能几。今也若仿唐,宋故事。置受书匮于殿侧。俾不识字者守之。以受实封。随即转达。勿令稽留一刻。且命某品以上。更日轮对。俾言政之得失。民之休戚。以为恒式。则群臣之情。毕达于上。而咨访之道。无遗恨矣。或曰。置一鼓而击之者甚多。尚不胜其烦也。今置受书匮。又令百官轮对。独不念 殿下听断之劳乎。且今上有 圣主。朝无奸臣。咨访之道。不必如是其察察也。臣曰。不然。虽有听断之劳。而无壅蔽之患。壅蔽之深。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。且阴阳无全消之理。十月。纯阴也。而未尝无阳。故谓之阳月。四月。纯阳也。而亦未尝无阴。但圣人不言耳。姤之为卦。一阴而已。圣人已寓其扶阳抑阴之义焉。其虑之也至矣。况人心无常。惟时所遇。古人有佞隋忠唐者矣。盖畜猫则鼠不耗。畜狗则盗不至。咨访广而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8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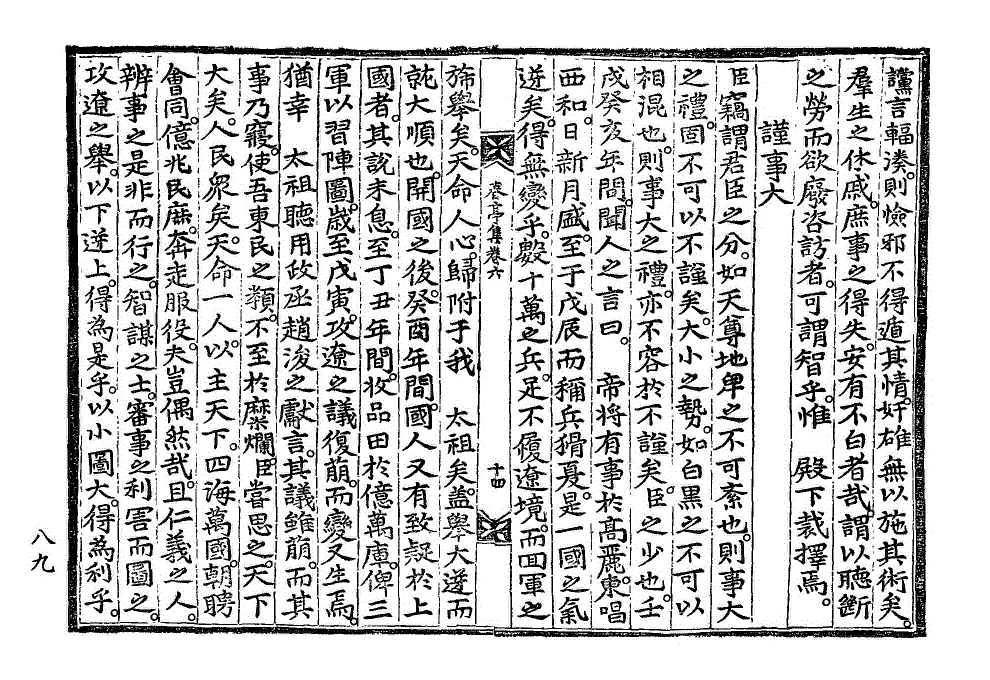 谠言辐凑。则憸邪不得遁其情。奸雄无以施其术矣。群生之休戚。庶事之得失。安有不白者哉。谓以听断之劳而欲废咨访者。可谓智乎。惟 殿下裁择焉。
谠言辐凑。则憸邪不得遁其情。奸雄无以施其术矣。群生之休戚。庶事之得失。安有不白者哉。谓以听断之劳而欲废咨访者。可谓智乎。惟 殿下裁择焉。谨事大
臣窃谓君臣之分。如天尊地卑之不可紊也。则事大之礼。固不可以不谨矣。大小之势。如白黑之不可以相混也。则事大之礼。亦不容于不谨矣。臣之少也。壬戌癸亥年间。闻人之言曰。 帝将有事于高丽。东唱西和。日新月盛。至于戊辰而称兵猾夏。是一国之气逆矣。得无变乎。数十万之兵。足不履辽境。而回军之旆举矣。天命人心。归附于我 太祖矣。盖举大逆而就大顺也。开国之后。癸酉年间。国人又有致疑于上国者。其说未息。至丁丑年间。收品田于亿万库。俾三军以习阵图。岁至戊寅。攻辽之议复萌。而变又生焉。犹幸 太祖听用政丞赵浚之献言。其议虽萌。而其事乃寝。使吾东民之类。不至于糜烂。臣尝思之。天下大矣。人民众矣。天命一人。以主天下。四海万国。朝聘会同。亿兆民庶。奔走服役。夫岂偶然哉。且仁义之人。辨事之是非而行之。智谋之士。审事之利害而图之。攻辽之举。以下逆上。得为是乎。以小图大。得为利乎。
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90H 页
 古人有言曰。施诸己而不愿。亦勿施于人。所恶于下。毋以事上。彼骊兴之主。必恶其臣之不恭。亦必不愿其臣之不忠矣。曾不自反。乃以事上而施于人。呜呼。其亦不思而已矣。臣又思之。臣等所以蒙 殿下之德者有二。何者。若中国板荡。四海糜沸。群雄角逐。穷寇残兵。逼我西鄙。则徵兵运粟。连年浃岁。相继于道路。其中变故。不可胜言。臣等虽欲安居饱食。其可得耶。此一也。 帝虽削除群雄。混一四海。若不谅东人臣事之诚。赫然震怒。欲加之罪。兴师动众。则虽鸡犬亦有不得而宁者矣。况臣等乎。今臣等所以饥食渴饮。冬裘夏葛。高枕晏眠。歌咏太平者。可不知其所自耶。谓帝力何有于我者。其亦不思之甚也。是宜夙兴夜寝。稽颡祝寿之不暇。何有于他志。古人有言曰。形于言。人得而知之。萌于心。鬼神已得而知之。盖至言也。是则逆上之言。非徒不可出诸其口。亦不可萌之于中矣。攻辽之举。逆之甚者也。发于事。则戊辰之大变作焉。形于言则戊寅之小变生焉。天之类应。厥惟显哉。臣又思之。夫有事于我国。 帝必无是心也。若劝之征者。则必有之矣。然劝之勿征者。亦必有之矣。劝之征者则必曰。蕞尔小国。介在山河。其俗轻矫。尝
古人有言曰。施诸己而不愿。亦勿施于人。所恶于下。毋以事上。彼骊兴之主。必恶其臣之不恭。亦必不愿其臣之不忠矣。曾不自反。乃以事上而施于人。呜呼。其亦不思而已矣。臣又思之。臣等所以蒙 殿下之德者有二。何者。若中国板荡。四海糜沸。群雄角逐。穷寇残兵。逼我西鄙。则徵兵运粟。连年浃岁。相继于道路。其中变故。不可胜言。臣等虽欲安居饱食。其可得耶。此一也。 帝虽削除群雄。混一四海。若不谅东人臣事之诚。赫然震怒。欲加之罪。兴师动众。则虽鸡犬亦有不得而宁者矣。况臣等乎。今臣等所以饥食渴饮。冬裘夏葛。高枕晏眠。歌咏太平者。可不知其所自耶。谓帝力何有于我者。其亦不思之甚也。是宜夙兴夜寝。稽颡祝寿之不暇。何有于他志。古人有言曰。形于言。人得而知之。萌于心。鬼神已得而知之。盖至言也。是则逆上之言。非徒不可出诸其口。亦不可萌之于中矣。攻辽之举。逆之甚者也。发于事。则戊辰之大变作焉。形于言则戊寅之小变生焉。天之类应。厥惟显哉。臣又思之。夫有事于我国。 帝必无是心也。若劝之征者。则必有之矣。然劝之勿征者。亦必有之矣。劝之征者则必曰。蕞尔小国。介在山河。其俗轻矫。尝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9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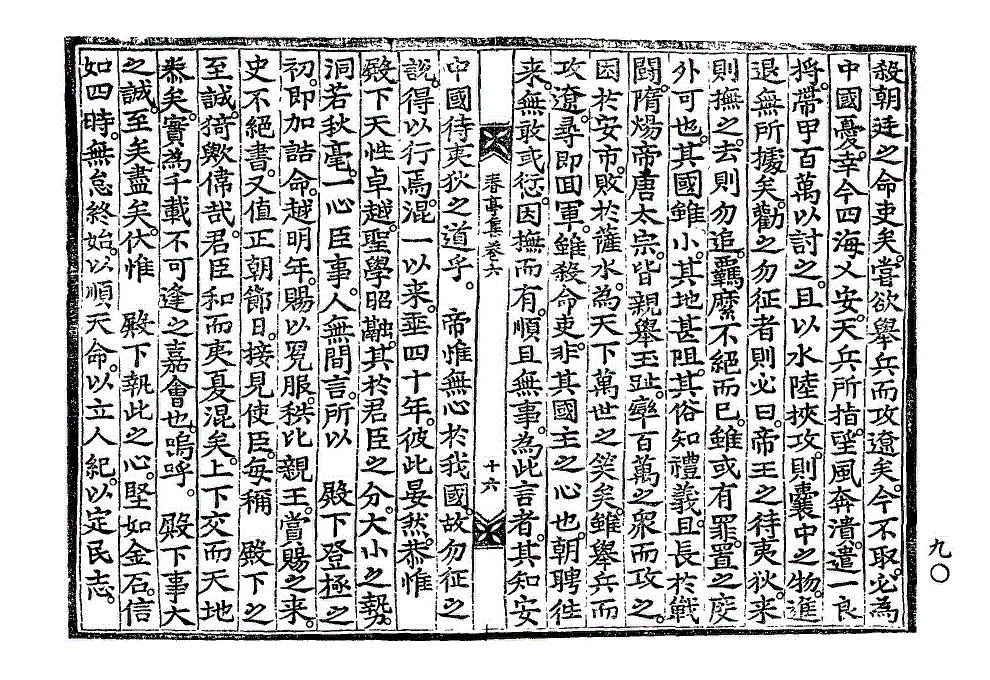 杀朝廷之命吏矣。尝欲举兵而攻辽矣。今不取。必为中国忧。幸今四海乂安。天兵所指。望风奔溃。遣一良将。带甲百万以讨之。且以水陆挟攻。则囊中之物。进退无所据矣。劝之勿征者则必曰。帝王之待夷狄。来则抚之。去则勿追。羁縻不绝而已。虽或有罪。置之度外可也。其国虽小。其地甚阻。其俗知礼义。且长于战斗。隋炀帝,唐太宗。皆亲举玉趾。率百万之众而攻之。困于安市。败于萨水。为天下万世之笑矣。虽举兵而攻辽。寻即回军。虽杀命吏。非其国主之心也。朝聘往来。无敢或愆。因抚而有。顺且无事。为此言者。其知安中国待夷狄之道乎。 帝惟无心于我国。故勿征之说。得以行焉。混一以来。垂四十年。彼此晏然。恭惟 殿下天性卓越。圣学昭融。其于君臣之分。大小之势。洞若秋毫。一心臣事。人无间言。所以 殿下登极之初。即加诰命。越明年。赐以冕服。秩比亲王。赏赐之来。史不绝书。又值正朝节日。接见使臣。每称 殿下之至诚。猗欤伟哉。君臣和而夷夏混矣。上下交而天地泰矣。实为千载不可逢之嘉会也。呜呼。 殿下事大之诚。至矣尽矣。伏惟 殿下执此之心。坚如金石。信如四时。无怠终始。以顺天命。以立人纪。以定民志。
杀朝廷之命吏矣。尝欲举兵而攻辽矣。今不取。必为中国忧。幸今四海乂安。天兵所指。望风奔溃。遣一良将。带甲百万以讨之。且以水陆挟攻。则囊中之物。进退无所据矣。劝之勿征者则必曰。帝王之待夷狄。来则抚之。去则勿追。羁縻不绝而已。虽或有罪。置之度外可也。其国虽小。其地甚阻。其俗知礼义。且长于战斗。隋炀帝,唐太宗。皆亲举玉趾。率百万之众而攻之。困于安市。败于萨水。为天下万世之笑矣。虽举兵而攻辽。寻即回军。虽杀命吏。非其国主之心也。朝聘往来。无敢或愆。因抚而有。顺且无事。为此言者。其知安中国待夷狄之道乎。 帝惟无心于我国。故勿征之说。得以行焉。混一以来。垂四十年。彼此晏然。恭惟 殿下天性卓越。圣学昭融。其于君臣之分。大小之势。洞若秋毫。一心臣事。人无间言。所以 殿下登极之初。即加诰命。越明年。赐以冕服。秩比亲王。赏赐之来。史不绝书。又值正朝节日。接见使臣。每称 殿下之至诚。猗欤伟哉。君臣和而夷夏混矣。上下交而天地泰矣。实为千载不可逢之嘉会也。呜呼。 殿下事大之诚。至矣尽矣。伏惟 殿下执此之心。坚如金石。信如四时。无怠终始。以顺天命。以立人纪。以定民志。 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9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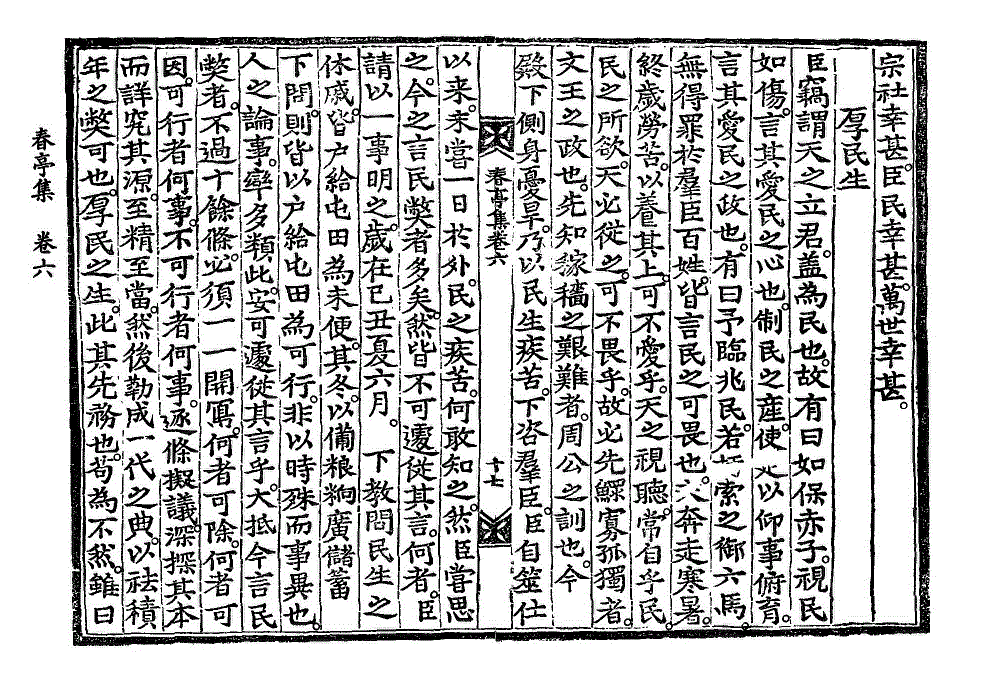 宗社幸甚。臣民幸甚。万世幸甚。
宗社幸甚。臣民幸甚。万世幸甚。厚民生
臣窃谓天之立君。盖为民也。故有曰如保赤子。视民如伤。言其爱民之心也。制民之产。使足以仰事俯育。言其爱民之政也。有曰予临兆民。若朽索之御六马。无得罪于群臣百姓。皆言民之可畏也。夫奔走寒暑。终岁劳苦。以养其上。可不爱乎。天之视听。常自乎民。民之所欲。天必从之。可不畏乎。故必先鳏寡孤独者。文王之政也。先知稼穑之艰难者。周公之训也。今 殿下侧身忧旱。乃以民生疾苦。下咨群臣。臣自筮仕以来。未尝一日于外。民之疾苦。何敢知之。然臣尝思之。今之言民弊者多矣。然皆不可遽从其言。何者。臣请以一事明之。岁在己丑夏六月。 下教问民生之休戚。皆户给屯田为未便。其冬。以备粮𥹝广储蓄 下问。则皆以户给屯田为可行。非以时殊而事异也。人之论事。率多类此。安可遽从其言乎。大抵今言民弊者。不过十馀条。必须一一开写。何者可除。何者可因。可行者何事。不可行者何事。逐条拟议。深探其本而详究其源。至精至当。然后勒成一代之典。以祛积年之弊可也。厚民之生。此其先务也。苟为不然。虽曰
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91L 页
 革弊。亦未免于朝令而夕改。已罢而寻复矣。恭惟 殿下天性仁厚。即位以来。宵衣旰食。惟以民生之休戚为念。崇俭节用。不违农时。养民以惠。筑堤堰以备旱潦。置义仓以济凶荒。爱民之心至矣。爱民之政举矣。苟值水旱。撤膳惕虑。或至失豫。其惧天灾恤民隐之诚。汉,唐以下之所无也。愿 殿下益以厚民生为心。念玆在玆。凡可以厚民生者。靡不行之。民生厚矣。邦本固矣。年代之久长。天命之保佑。亦不外焉。伏惟 殿下宜尽心焉。
革弊。亦未免于朝令而夕改。已罢而寻复矣。恭惟 殿下天性仁厚。即位以来。宵衣旰食。惟以民生之休戚为念。崇俭节用。不违农时。养民以惠。筑堤堰以备旱潦。置义仓以济凶荒。爱民之心至矣。爱民之政举矣。苟值水旱。撤膳惕虑。或至失豫。其惧天灾恤民隐之诚。汉,唐以下之所无也。愿 殿下益以厚民生为心。念玆在玆。凡可以厚民生者。靡不行之。民生厚矣。邦本固矣。年代之久长。天命之保佑。亦不外焉。伏惟 殿下宜尽心焉。御群臣
臣闻人主之职。在论一相而止耳。庶官万事。莫不各得其宜焉。此人君之所以勤于求贤。逸于得人。而坐享长治久安之利也。虽然。此可行于古。而不可行于今者也。何者。三代之民。直道而行者也。周公之相成王。忠圣之臣也。尚不免有流言之变。天下汹汹。王室几摇。降及后世。其可行乎。臣窃谓权者。天下之所畏也。利者。天下之所求也。权利之柄。不可一日而移于下矣。人主。至寡也。群臣。至众也。以至众而服役乎至寡者。盖以权利之在乎上也。而移之可乎。古人有言曰。可爱非君。民生于三。事之如一。臣自十三四时。已
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92H 页
 能诵说。然不知其味也。至年三十。始得其意。又七八年。乃大晓悟。深服古人之先觉也。尝思之。臣子之忠于君父者。甚顺甚易而且安也。反是者。甚逆甚难而且危也。然或为彼而不为此者。其有由矣。盖权利之柄。或移于贵臣。或移于左右。彼天下之人。惟利是求。惟权是畏者。其常也。窃人主之柄者。诱之以重利。威之以权势。势不得不归焉。其能识君臣之大义。不怵于威。不诱于利。挺然独立者罕矣。虽间有之。又必百计中伤。或短于上而逐之。苟不得焉。必嗾台谏之为鹰犬爪牙者。见逼多端。使之伤心畏罪。自求引退。此阴中独立者之至术也。于是。忠臣志士。无容足之地矣。则父诏子。兄教弟。朋友相劝。靡然趋之。然后肆焉。奸憸情状。历代一辙。人主孤立于万人之上。虽曰至明以照奸。然或得于前而失于后。或明于此而暗于彼。鲜有不落其术中者矣。臣每观胡氏之传春秋。朱子之作纲目。真德秀之衍大学。皆以人君存心寡欲敬天勤民为本。而尤眷眷于奸憸之情状。三致焉。欲万世人主之警省觉悟。以保长治久安之业于无穷也。其忠大矣。惜乎。当世之君。竟不能用。而徒使后人抚卷而太息也。夫今之时。非古之时也。今之人。非古
能诵说。然不知其味也。至年三十。始得其意。又七八年。乃大晓悟。深服古人之先觉也。尝思之。臣子之忠于君父者。甚顺甚易而且安也。反是者。甚逆甚难而且危也。然或为彼而不为此者。其有由矣。盖权利之柄。或移于贵臣。或移于左右。彼天下之人。惟利是求。惟权是畏者。其常也。窃人主之柄者。诱之以重利。威之以权势。势不得不归焉。其能识君臣之大义。不怵于威。不诱于利。挺然独立者罕矣。虽间有之。又必百计中伤。或短于上而逐之。苟不得焉。必嗾台谏之为鹰犬爪牙者。见逼多端。使之伤心畏罪。自求引退。此阴中独立者之至术也。于是。忠臣志士。无容足之地矣。则父诏子。兄教弟。朋友相劝。靡然趋之。然后肆焉。奸憸情状。历代一辙。人主孤立于万人之上。虽曰至明以照奸。然或得于前而失于后。或明于此而暗于彼。鲜有不落其术中者矣。臣每观胡氏之传春秋。朱子之作纲目。真德秀之衍大学。皆以人君存心寡欲敬天勤民为本。而尤眷眷于奸憸之情状。三致焉。欲万世人主之警省觉悟。以保长治久安之业于无穷也。其忠大矣。惜乎。当世之君。竟不能用。而徒使后人抚卷而太息也。夫今之时。非古之时也。今之人。非古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92L 页
 之人也。虽然。天理之在人心。万古如一日。虽以高丽衰季之极。而见危授命。有如侍中郑梦周者矣。才得七品之官。而终身不贰。有如吉再者矣。况于圣明之时乎。虽闾巷之夫。同心出塞。有患难相死之理。况于君臣之间乎。苟人主诚得御臣之道与术。孰肯舍其甚顺。而从其甚逆。去其甚易且安。而就其甚难且危者乎。何谓御臣之道。爱与公而已矣。爱则人心顺。公则人心服。既顺且服。于御臣乎何有。杜天下之私恩。破天下之私计。收天下之权而自执之。敛天下之利而亲用之。此则御臣之术也。苟权利之所在。虽于贵臣左右而群趋之。况于人主乎。使在朝臣子。苟得一命之荣矣。皆曰。吾君之德也。衣于斯。食于斯。寝于斯。皆吾君之德也。人人之心。辐凑于上矣。加以俯就咨访。如臣所谓虽其空谈生语。有不足听。亦且优容。使人人之言。毕达于上。则奸憸之徒。非徒不能肆志。反无容足之地矣。故人主御臣。莫大于照奸。而尤莫大于使不能为奸也。古人又有御相臣易。御将臣难之语。而相臣有重臣权臣之异。重臣不可一日而无也。权臣不可一日而有也。将臣有贤将才将之异。御贤将以诚。御才将以智。其大要皆不外于臣之所论御
之人也。虽然。天理之在人心。万古如一日。虽以高丽衰季之极。而见危授命。有如侍中郑梦周者矣。才得七品之官。而终身不贰。有如吉再者矣。况于圣明之时乎。虽闾巷之夫。同心出塞。有患难相死之理。况于君臣之间乎。苟人主诚得御臣之道与术。孰肯舍其甚顺。而从其甚逆。去其甚易且安。而就其甚难且危者乎。何谓御臣之道。爱与公而已矣。爱则人心顺。公则人心服。既顺且服。于御臣乎何有。杜天下之私恩。破天下之私计。收天下之权而自执之。敛天下之利而亲用之。此则御臣之术也。苟权利之所在。虽于贵臣左右而群趋之。况于人主乎。使在朝臣子。苟得一命之荣矣。皆曰。吾君之德也。衣于斯。食于斯。寝于斯。皆吾君之德也。人人之心。辐凑于上矣。加以俯就咨访。如臣所谓虽其空谈生语。有不足听。亦且优容。使人人之言。毕达于上。则奸憸之徒。非徒不能肆志。反无容足之地矣。故人主御臣。莫大于照奸。而尤莫大于使不能为奸也。古人又有御相臣易。御将臣难之语。而相臣有重臣权臣之异。重臣不可一日而无也。权臣不可一日而有也。将臣有贤将才将之异。御贤将以诚。御才将以智。其大要皆不外于臣之所论御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9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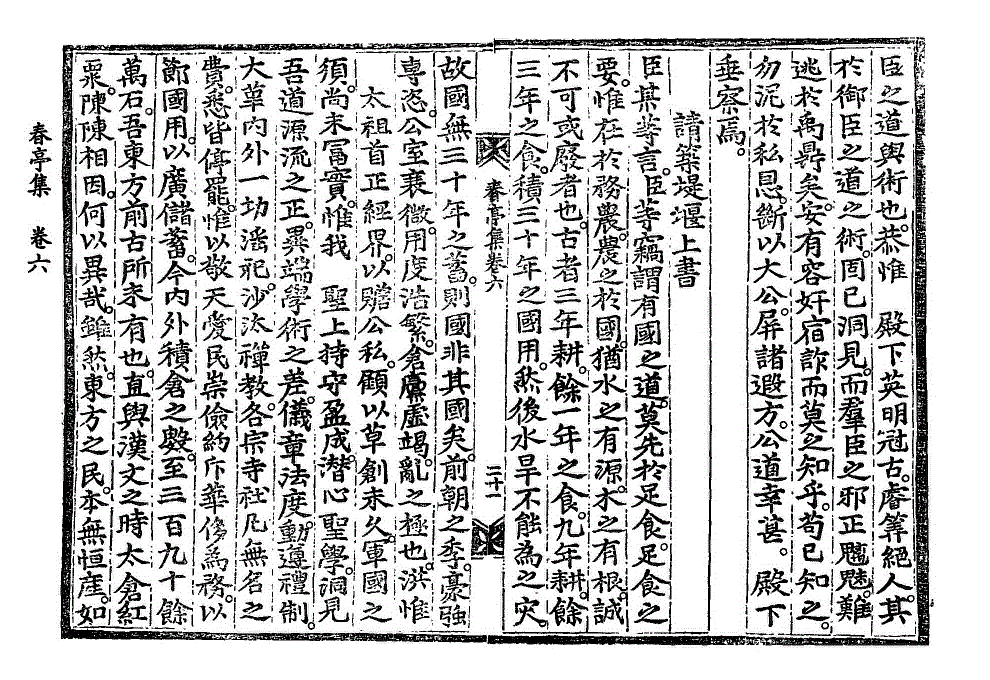 臣之道与术也。恭惟 殿下英明冠古。睿算绝人。其于御臣之道之术。固已洞见。而群臣之邪正魑魅。难逃于禹鼎矣。安有容奸宿诈而莫之知乎。苟已知之。勿泥于私恩。断以大公。屏诸遐方。公道幸甚。 殿下垂察焉。
臣之道与术也。恭惟 殿下英明冠古。睿算绝人。其于御臣之道之术。固已洞见。而群臣之邪正魑魅。难逃于禹鼎矣。安有容奸宿诈而莫之知乎。苟已知之。勿泥于私恩。断以大公。屏诸遐方。公道幸甚。 殿下垂察焉。请筑堤堰上书
臣某等言。臣等窃谓有国之道。莫先于足食。足食之要。惟在于务农。农之于国。犹水之有源。木之有根。诚不可或废者也。古者三年耕。馀一年之食。九年耕。馀三年之食。积三十年之国用。然后水旱不能为之灾。故国无三十年之蓄。则国非其国矣。前朝之季。豪强专恣。公室衰微。用度浩繁。仓廪虚竭。乱之极也。洪惟 太祖首正经界。以赡公私。顾以草创未久。军国之须。尚未富实。惟我 圣上持守盈成。潜心圣学。洞见吾道源流之正。异端学术之差。仪章法度。动遵礼制。大革内外一切淫祀。沙汰禅教。各宗寺社凡无名之费。悉皆停罢。惟以敬天爱民崇俭约斥华侈为务。以节国用。以广储蓄。今内外积仓之数。至三百九十馀万石。吾东方前古所未有也。直与汉文之时太仓红粟。陈陈相因。何以异哉。虽然。东方之民。本无恒产。如
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9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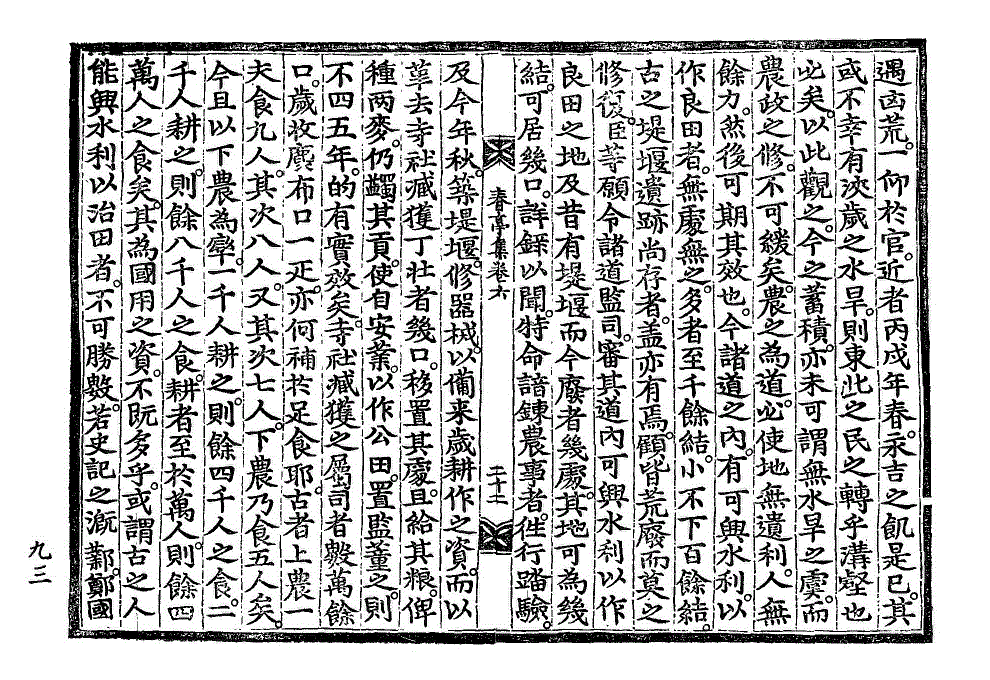 遇凶荒。一仰于官。近者丙戌年春。永吉之饥是已。其或不幸有浃岁之水旱。则东北之民之转乎沟壑也必矣。以此观之。今之蓄积。亦未可谓无水旱之虞。而农政之修。不可缓矣。农之为道。必使地无遗利。人无馀力。然后可期其效也。今诸道之内。有可兴水利。以作良田者。无处无之。多者至千馀结。小不下百馀结。古之堤堰遗迹尚存者。盖亦有焉。顾皆荒废而莫之修复。臣等愿令诸道监司。审其道内可兴水利以作良田之地及昔有堤堰而今废者几处。其地可为几结。可居几口。详录以闻。特命谙鍊农事者。往行踏验。及今年秋。筑堤堰。修器械。以备来岁耕作之资。而以革去寺社臧获丁壮者几口。移置其处。且给其粮。俾种两麦。仍蠲其贡。使自安业。以作公田。置监蕫之。则不四五年。的有实效矣。寺社臧获之属司者数万馀口。岁收粗布口一疋。亦何补于足食耶。古者上农一夫食九人。其次八人。又其次七人。下农乃食五人矣。今且以下农为率。一千人耕之。则馀四千人之食。二千人耕之。则馀八千人之食。耕者至于万人。则馀四万人之食矣。其为国用之资。不既多乎。或谓古之人能兴水利以治田者。不可胜数。若史记之溉邺。郑国
遇凶荒。一仰于官。近者丙戌年春。永吉之饥是已。其或不幸有浃岁之水旱。则东北之民之转乎沟壑也必矣。以此观之。今之蓄积。亦未可谓无水旱之虞。而农政之修。不可缓矣。农之为道。必使地无遗利。人无馀力。然后可期其效也。今诸道之内。有可兴水利。以作良田者。无处无之。多者至千馀结。小不下百馀结。古之堤堰遗迹尚存者。盖亦有焉。顾皆荒废而莫之修复。臣等愿令诸道监司。审其道内可兴水利以作良田之地及昔有堤堰而今废者几处。其地可为几结。可居几口。详录以闻。特命谙鍊农事者。往行踏验。及今年秋。筑堤堰。修器械。以备来岁耕作之资。而以革去寺社臧获丁壮者几口。移置其处。且给其粮。俾种两麦。仍蠲其贡。使自安业。以作公田。置监蕫之。则不四五年。的有实效矣。寺社臧获之属司者数万馀口。岁收粗布口一疋。亦何补于足食耶。古者上农一夫食九人。其次八人。又其次七人。下农乃食五人矣。今且以下农为率。一千人耕之。则馀四千人之食。二千人耕之。则馀八千人之食。耕者至于万人。则馀四万人之食矣。其为国用之资。不既多乎。或谓古之人能兴水利以治田者。不可胜数。若史记之溉邺。郑国春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9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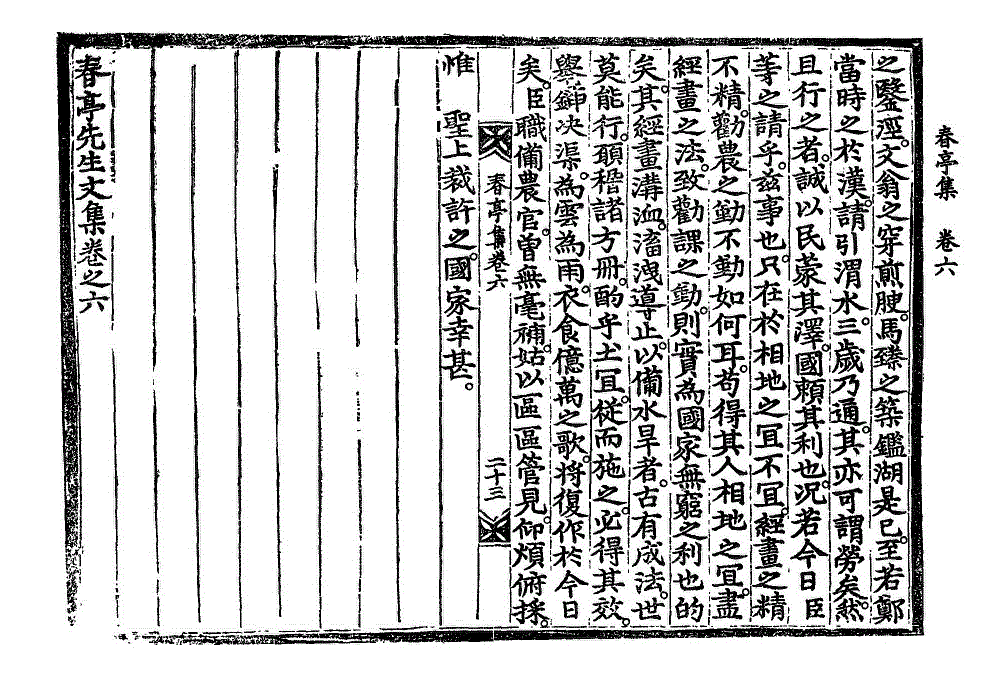 之凿泾。文翁之穿煎腴。马臻之筑鉴湖是已。至若郑当时之于汉。请引渭水。三岁乃通。其亦可谓劳矣。然且行之者。诚以民蒙其泽。国赖其利也。况若今日臣等之请乎。玆事也。只在于相地之宜不宜。经画之精不精。劝农之勤不勤如何耳。苟得其人相地之宜。尽经画之法。致劝课之勤。则实为国家无穷之利也的矣。其经画沟洫。滀泄导止。以备水旱者。古有成法。世莫能行。愿稽诸方册。酌乎土宜。从而施之。必得其效。举锸决渠。为云为雨。衣食亿万之歌。将复作于今日矣。臣职备农官。曾无毫补。姑以区区管见。仰烦俯采。惟 圣上裁许之。国家幸甚。
之凿泾。文翁之穿煎腴。马臻之筑鉴湖是已。至若郑当时之于汉。请引渭水。三岁乃通。其亦可谓劳矣。然且行之者。诚以民蒙其泽。国赖其利也。况若今日臣等之请乎。玆事也。只在于相地之宜不宜。经画之精不精。劝农之勤不勤如何耳。苟得其人相地之宜。尽经画之法。致劝课之勤。则实为国家无穷之利也的矣。其经画沟洫。滀泄导止。以备水旱者。古有成法。世莫能行。愿稽诸方册。酌乎土宜。从而施之。必得其效。举锸决渠。为云为雨。衣食亿万之歌。将复作于今日矣。臣职备农官。曾无毫补。姑以区区管见。仰烦俯采。惟 圣上裁许之。国家幸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