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明: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.org,kanripo.org, db.itkc.or.kr 和 zh.wikisource.org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x 页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
书
书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3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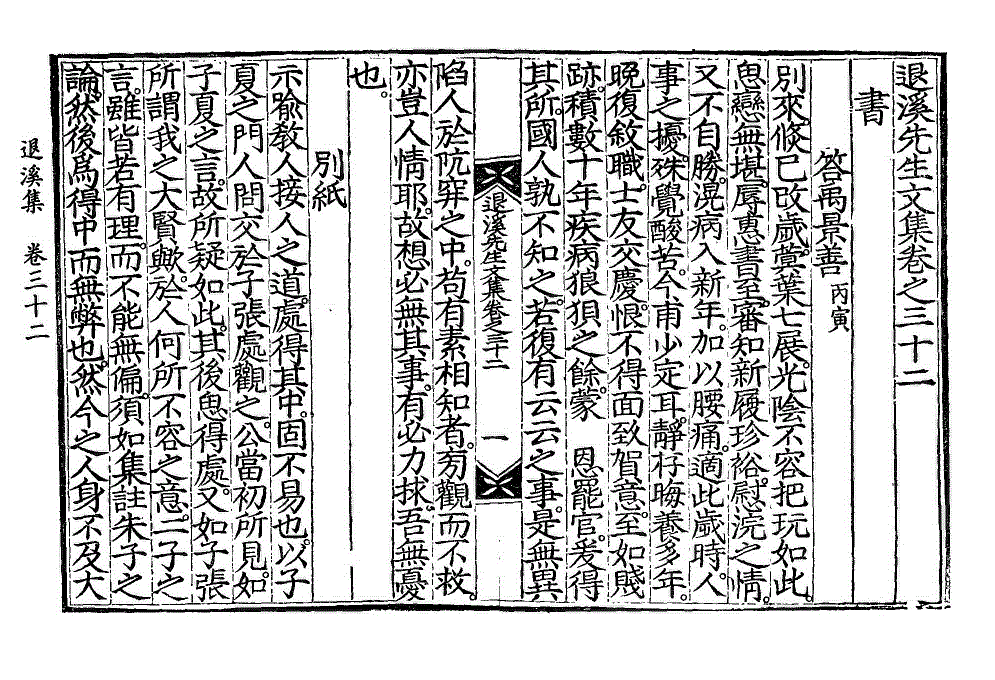 答禹景善(丙寅)
答禹景善(丙寅)别来。倏已改岁。蓂叶七展。光阴不容把玩如此。思恋无堪。辱惠书至。审知新履珍裕。慰浣之情。又不自胜。滉病入新年。加以腰痛。适此岁时。人事之扰。殊觉酸苦。今甫少定耳。静存晦养多年。晚复叙职。士友交庆。恨不得面致贺意。至如贱迹。积数十年疾病狼狈之馀。蒙 恩罢官。爰得其所。国人孰不知之。若复有云云之事。是无异陷人于坑阱之中。苟有素相知者。旁观而不救。亦岂人情耶。故想必无其事。有必力救。吾无忧也。
别纸
示喻教人接人之道。处得其中。固不易也。以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处观之。公当初所见。如子夏之言。故所疑如此。其后思得处。又如子张所谓我之大贤欤。于人何所不容之意。二子之言。虽皆若有理。而不能无偏。须如集注朱子之论。然后为得中而无弊也。然今之人身不及大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37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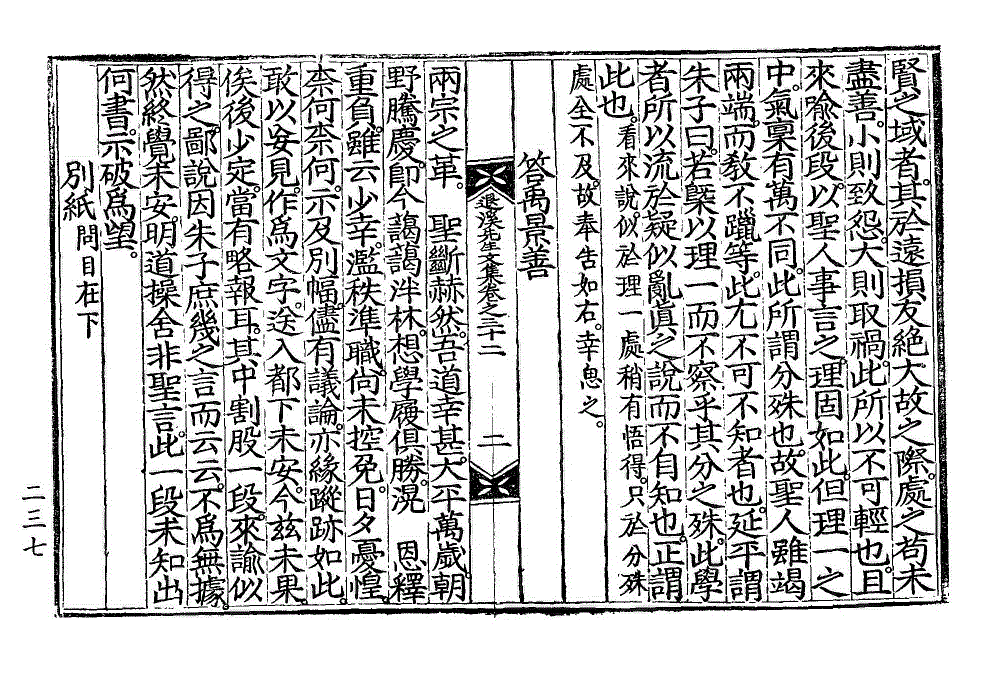 贤之域者。其于远损友绝大故之际。处之苟未尽善。小则致怨。大则取祸。此所以不可轻也。且来喻后段。以圣人事言之。理固如此。但理一之中。气禀有万不同。此所谓分殊也。故圣人虽竭两端。而教不躐等。此尤不可不知者也。延平谓朱子曰。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。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。正谓此也。(看来说。似于理一处稍有悟得。只于分殊处全不及。故奉告如右。幸思之。)
贤之域者。其于远损友绝大故之际。处之苟未尽善。小则致怨。大则取祸。此所以不可轻也。且来喻后段。以圣人事言之。理固如此。但理一之中。气禀有万不同。此所谓分殊也。故圣人虽竭两端。而教不躐等。此尤不可不知者也。延平谓朱子曰。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。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。正谓此也。(看来说。似于理一处稍有悟得。只于分殊处全不及。故奉告如右。幸思之。)答禹景善
两宗之革。 圣断赫然。吾道幸甚。大平万岁。朝野腾庆。即今蔼蔼泮林。想学履俱胜。滉 恩释重负。虽云少幸。滥秩准职。尚未控免。日夕忧惶。柰何柰何。示及别幅。尽有议论。亦缘踪迹如此。敢以妄见。作为文字。送入都下未安。今玆未果。俟后少定。当有略报耳。其中割股一段。来谕似得之。鄙说因朱子庶几之言而云云。不为无据。然终觉未安。明道操舍非圣言。此一段未知出何书。示破为望。
别纸(问目在下)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38H 页
 问目内。费隐一段最紧。姑略言此恐不可以气与器言也。本章注朱子说。因问者并举形而下者。故先有形而下者甚广之云。其实只为其下将说其形而上者实行乎其间。无物不具。无处不有。设此一句于前面。为之田地尔。正与释天命之谓性处。先言以阴阳五行。化生万物。气以成形。而后乃说理亦赋以下云云之意同。盖理不能独行。故将说理处。先说气。其意非以气为理。而衮作一片说也。若见先说阴阳五行。而谓天命之性兼气说。见先说形而下。而谓费为气为器。是全失朱子本意。请更详之。以禀祭酒丈前。何如。其词。(陶山曲)只为他人虑耳。公必无是。不须见还。启蒙翼传。送来则为幸。然真逸手之云。公亦以彼为信然耶。静存与祭酒丈。皆以为何如耶。朱子尝云。义理未安。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。亦须有商量。况此定非圣贤之言耶。朱子若果有此号。何故都无他见称处。且所谓真逸手有何义理事实耶。千不是万不是。定是自诳诳人之说耳。慎勿轻信。
问目内。费隐一段最紧。姑略言此恐不可以气与器言也。本章注朱子说。因问者并举形而下者。故先有形而下者甚广之云。其实只为其下将说其形而上者实行乎其间。无物不具。无处不有。设此一句于前面。为之田地尔。正与释天命之谓性处。先言以阴阳五行。化生万物。气以成形。而后乃说理亦赋以下云云之意同。盖理不能独行。故将说理处。先说气。其意非以气为理。而衮作一片说也。若见先说阴阳五行。而谓天命之性兼气说。见先说形而下。而谓费为气为器。是全失朱子本意。请更详之。以禀祭酒丈前。何如。其词。(陶山曲)只为他人虑耳。公必无是。不须见还。启蒙翼传。送来则为幸。然真逸手之云。公亦以彼为信然耶。静存与祭酒丈。皆以为何如耶。朱子尝云。义理未安。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。亦须有商量。况此定非圣贤之言耶。朱子若果有此号。何故都无他见称处。且所谓真逸手有何义理事实耶。千不是万不是。定是自诳诳人之说耳。慎勿轻信。答禹景善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38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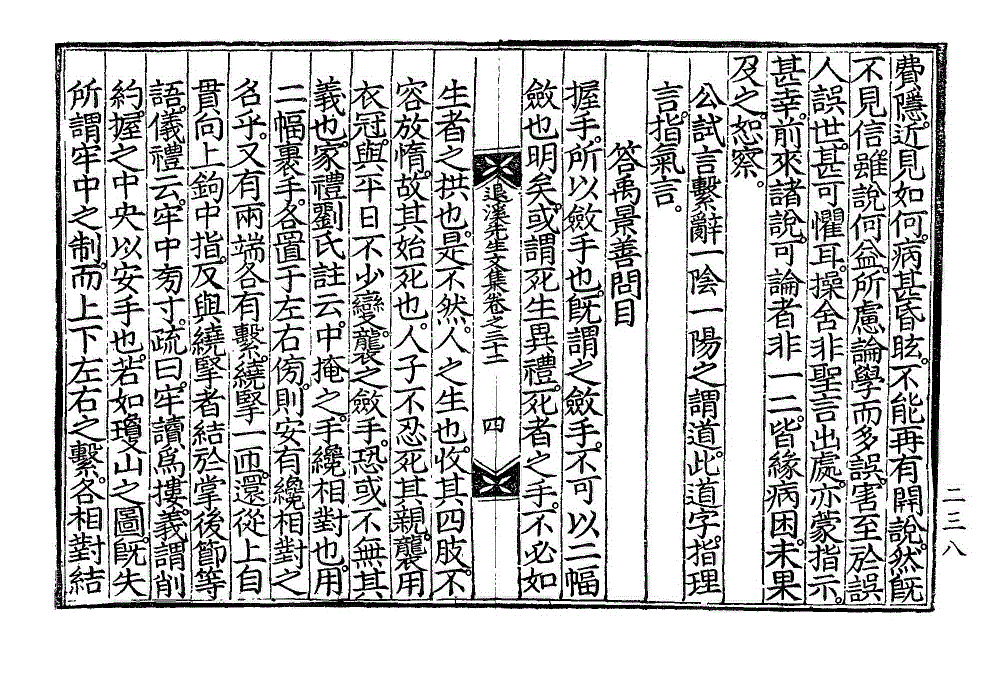 费隐。近见如何。病甚昏眩。不能再有开说。然既不见信。虽说何益。所虑论学而多误。害至于误人误世。甚可惧耳。操舍非圣言出处。亦蒙指示。甚幸。前来诸说。可论者非一二。皆缘病困。未果及之。恕察。
费隐。近见如何。病甚昏眩。不能再有开说。然既不见信。虽说何益。所虑论学而多误。害至于误人误世。甚可惧耳。操舍非圣言出处。亦蒙指示。甚幸。前来诸说。可论者非一二。皆缘病困。未果及之。恕察。公试言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。此道字。指理言。指气言。
答禹景善问目
握手。所以敛手也。既谓之敛手。不可以二幅敛也明矣。或谓死生异礼。死者之手。不必如生者之拱也。是不然。人之生也。收其四肢。不容放惰。故其始死也。人子不忍死其亲。袭用衣冠。与平日不少变。袭之敛手。恐或不无其义也。家礼刘氏注云。中掩之。手才相对也。用二幅裹手。各置于左右傍。则安有才相对之名乎。又有两端各有系。绕掔一匝。还从上自贯向上钩中指。反与绕掔者结于掌后节等语。仪礼云。牢中旁寸。疏曰。牢读为搂。义谓削约。握之中央以安手也。若如琼山之图。既失所谓牢中之制。而上下左右之系。各相对结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39H 页
 而已。何必绕掔一匝。从上自贯向上钩指。反与绕掔者结乎。又何必削约之。然后安其手乎。今以琼山之图。欲仿仪礼之制。非特不必为。亦不得为也。所谓两端各有系者。指左右之两端有系云耳。若如琼山之图。正与幎目同制。只曰四角有系。可也。何必两端有系云乎哉。
而已。何必绕掔一匝。从上自贯向上钩指。反与绕掔者结乎。又何必削约之。然后安其手乎。今以琼山之图。欲仿仪礼之制。非特不必为。亦不得为也。所谓两端各有系者。指左右之两端有系云耳。若如琼山之图。正与幎目同制。只曰四角有系。可也。何必两端有系云乎哉。握手之制。在仪礼,家礼。有不可晓处。奇明彦考订论辨。颇得详细。所以从来欲从其说。以为当用二幅。但其施用曲折。有未明了尔。今奉示谕。当用一幅。非二幅之意甚力。正与明彦说相反。滉以本未明了之见。安能定是非于其间耶。但私心终不能无疑于一幅之说者。仪礼用尺。必是周尺。则尺二寸之帛。仅当今尺四寸二分强。只用此一幅而裹两手。则两掌里面。犹有不足。何能包及手表。而可名为裹乎。(来谕谓之敛手。礼中。但云裹手。无敛手之说。)况仪礼。设决丽于掔。疏云。握手。长尺二寸。裹手二端。绕于手表必重。(二端之二。今本作一。必缺一画也。)若用一幅。短帛如彼。且不能出于手表。安有相重于手表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3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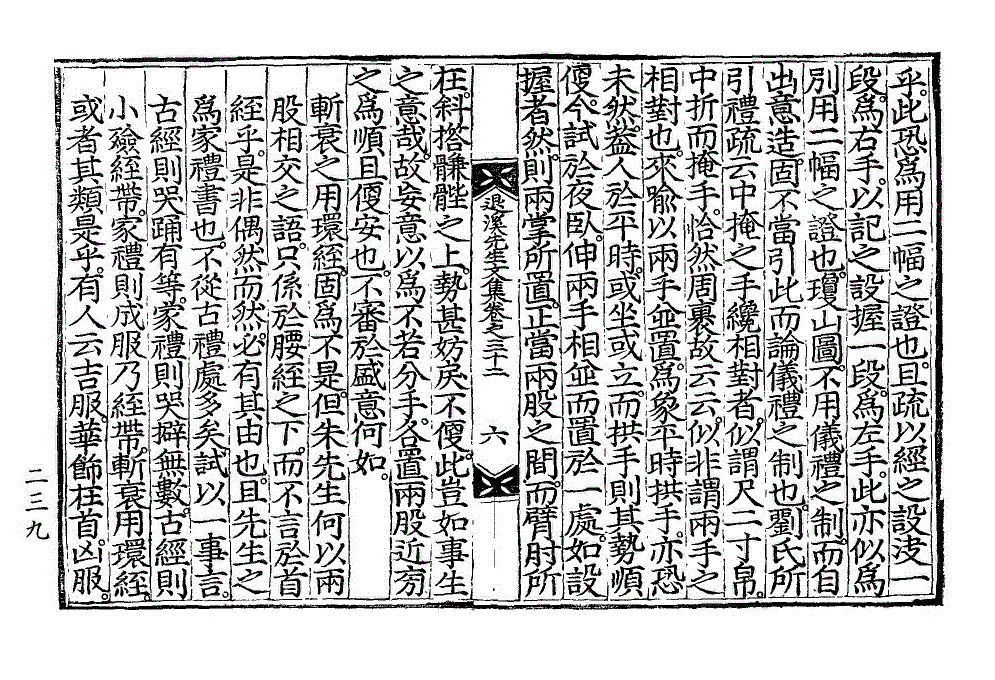 乎。此恐为用二幅之證也。且疏以经之设决一段。为右手。以记之设握一段。为左手。此亦似为别用二幅之證也。琼山图。不用仪礼之制。而自出意造。固不当引此而论仪礼之制也。刘氏所引礼疏云中掩之手才相对者。似谓尺二寸帛。中折而掩手。恰然周裹故云云。似非谓两手之相对也。来喻以两手并置。为象平时拱手。亦恐未然。盖人于平时。或坐或立。而拱手则其势顺便。今试于夜卧。伸两手相并而置于一处。如设握者然。则两掌所置。正当两股之间。而臂肘所在。斜搭䯡䯗之上。势甚妨戾不便。此岂如事生之意哉。故妄意以为不若分手。各置两股近旁之为顺且便安也。不审于盛意何如。
乎。此恐为用二幅之證也。且疏以经之设决一段。为右手。以记之设握一段。为左手。此亦似为别用二幅之證也。琼山图。不用仪礼之制。而自出意造。固不当引此而论仪礼之制也。刘氏所引礼疏云中掩之手才相对者。似谓尺二寸帛。中折而掩手。恰然周裹故云云。似非谓两手之相对也。来喻以两手并置。为象平时拱手。亦恐未然。盖人于平时。或坐或立。而拱手则其势顺便。今试于夜卧。伸两手相并而置于一处。如设握者然。则两掌所置。正当两股之间。而臂肘所在。斜搭䯡䯗之上。势甚妨戾不便。此岂如事生之意哉。故妄意以为不若分手。各置两股近旁之为顺且便安也。不审于盛意何如。斩衰之用环绖。固为不是。但朱先生何以两股相交之语。只系于腰绖之下。而不言于首绖乎。是非偶然而然。必有其由也。且先生之为家礼书也。不从古礼处多矣。试以一事言。古经则哭踊有等。家礼则哭擗无数。古经则小殓绖带。家礼则成服乃绖带。斩衰用环绖。或者其类是乎。有人云吉服。华饰在首。凶服。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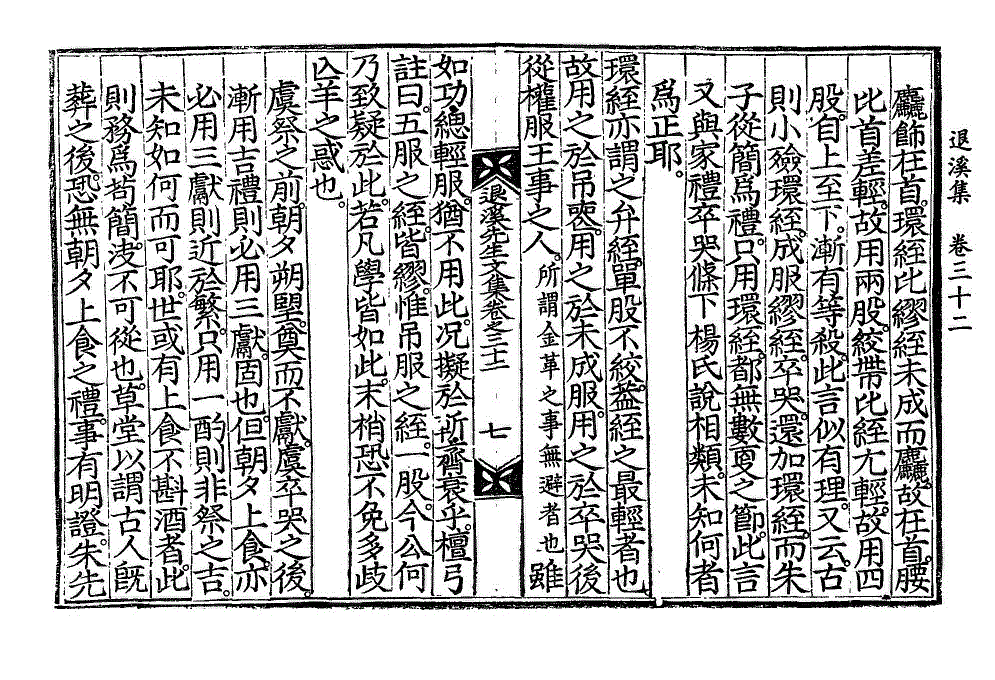 粗饰在首。环绖比缪绖未成而粗。故在首。腰比首差轻。故用两股。绞带比绖尤轻。故用四股。自上至下。渐有等杀。此言似有理。又云。古则小殓环绖。成服缪绖。卒哭。还加环绖。而朱子从简为礼。只用环绖。都无数更之节。此言又与家礼卒哭条下杨氏说相类。未知何者为正耶。
粗饰在首。环绖比缪绖未成而粗。故在首。腰比首差轻。故用两股。绞带比绖尤轻。故用四股。自上至下。渐有等杀。此言似有理。又云。古则小殓环绖。成服缪绖。卒哭。还加环绖。而朱子从简为礼。只用环绖。都无数更之节。此言又与家礼卒哭条下杨氏说相类。未知何者为正耶。环绖亦谓之弁绖。单股不绞。盖绖之最轻者也。故用之于吊丧。用之于未成服。用之于卒哭后从权服王事之人。(所谓金革之事无避者也)虽如功,缌轻服。犹不用此。况拟于斩,齐衰乎。檀弓注曰。五服之绖。皆缪。惟吊服之绖。一股。今公何乃致疑于此。若凡学皆如此。末梢恐不免多歧亡羊之惑也。
虞祭之前。朝夕朔望。奠而不献。虞卒哭之后。渐用吉礼则必用三献。固也。但朝夕上食。亦必用三献则近于繁。只用一酌则非祭之吉。未知如何而可耶。世或有上食不斟酒者。此则务为苟简。决不可从也。草堂以谓古人既葬之后。恐无朝夕上食之礼。事有明證。朱先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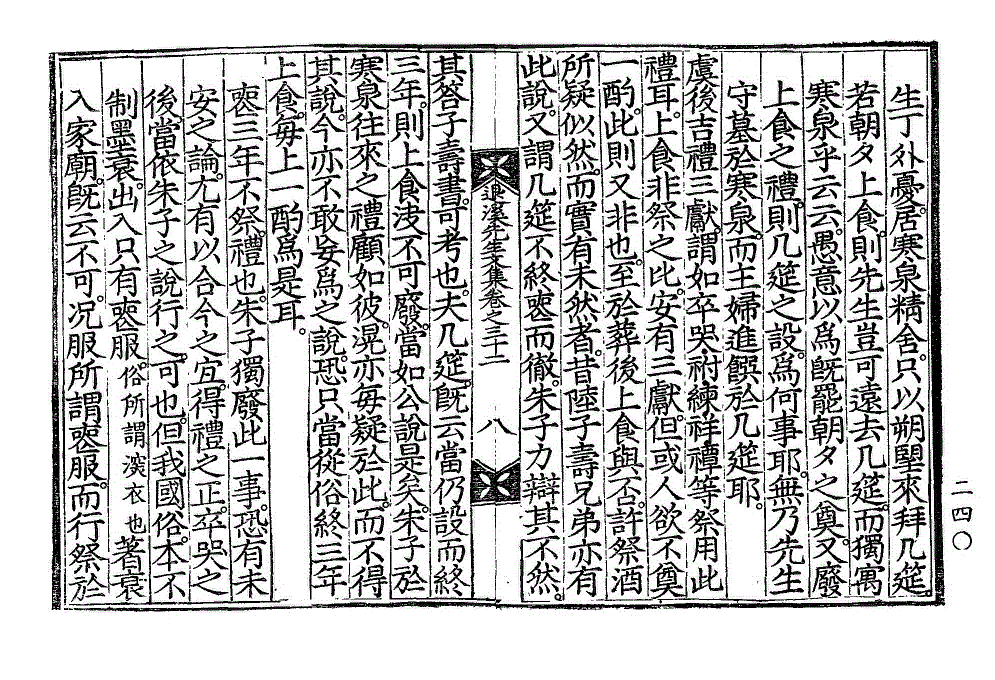 生丁外忧。居寒泉精舍。只以朔望来拜几筵。若朝夕上食。则先生岂可远去几筵。而独寓寒泉乎云云。愚意以为既罢朝夕之奠。又废上食之礼。则几筵之设。为何事耶。无乃先生守墓于寒泉。而主妇进馔于几筵耶。
生丁外忧。居寒泉精舍。只以朔望来拜几筵。若朝夕上食。则先生岂可远去几筵。而独寓寒泉乎云云。愚意以为既罢朝夕之奠。又废上食之礼。则几筵之设。为何事耶。无乃先生守墓于寒泉。而主妇进馔于几筵耶。虞后吉礼三献。谓如卒哭,祔,练,祥,禫等祭用此礼耳。上食非祭之比。安有三献。但或人欲不奠一酌。此则又非也。至于葬后上食与否。许祭酒所疑似然。而实有未然者。昔陆子寿兄弟亦有此说。又谓几筵不终丧而彻。朱子力辩其不然。其答子寿书。可考也。夫几筵。既云当仍设而终三年。则上食决不可废。当如公说是矣。朱子于寒泉往来之礼顾如彼。滉亦每疑于此。而不得其说。今亦不敢妄为之说。恐只当从俗终三年上食。每上一酌为是耳。
丧三年不祭。礼也。朱子独废此一事。恐有未安之论。尤有以合今之宜。得礼之正。卒哭之后。当依朱子之说行之。可也。但我国俗。本不制墨衰。出入只有丧服。(俗所谓深衣也)著衰入家庙。既云不可。况服所谓丧服。而行祭于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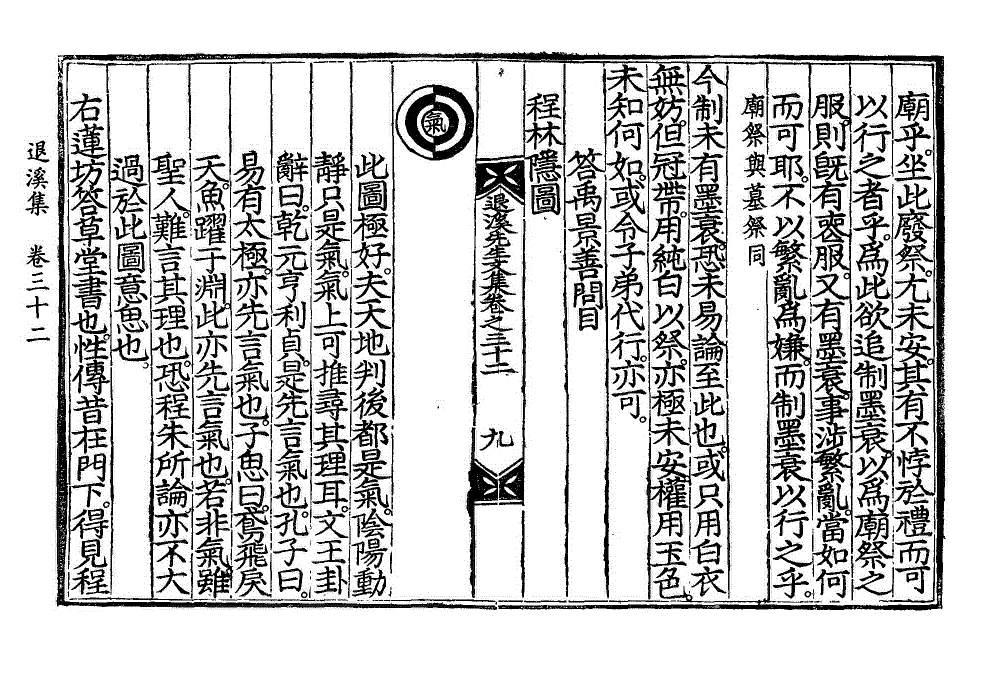 庙乎。坐此废祭。尤未安。其有不悖于礼而可以行之者乎。为此欲追制墨衰。以为庙祭之服。则既有丧服。又有墨衰。事涉繁乱。当如何而可耶。不以繁乱为嫌。而制墨衰以行之乎。(庙祭与墓祭同)
庙乎。坐此废祭。尤未安。其有不悖于礼而可以行之者乎。为此欲追制墨衰。以为庙祭之服。则既有丧服。又有墨衰。事涉繁乱。当如何而可耶。不以繁乱为嫌。而制墨衰以行之乎。(庙祭与墓祭同)今制未有墨衰。恐未易论至此也。或只用白衣无妨。但冠带。用纯白以祭。亦极未安。权用玉色。未知何如。或令子弟代行。亦可。
答禹景善问目
程林隐图
삽화 새창열기
此图极好。夫天地判后都是气。阴阳动静只是气。气上可推寻其理耳。文王卦辞曰。乾元亨利贞。是先言气也。孔子曰。易有太极。亦先言气也。子思曰。鸢飞戾天。鱼跃于渊。此亦先言气也。若非气。虽圣人。难言其理也。恐程朱所论。亦不大过于此图意思也。
右莲坊答草堂书也。性传昔在门下。得见程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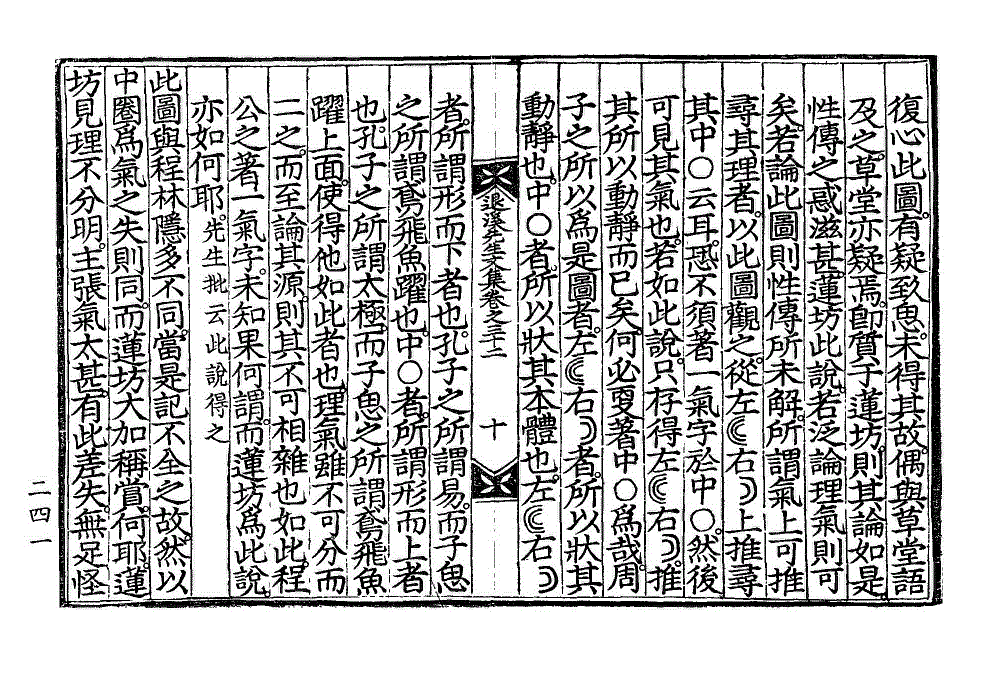 复心此图。有疑致思。未得其故。偶与草堂语及之。草堂亦疑焉。即质于莲坊。则其论如是。性传之惑滋甚。莲坊此说。若泛论理气则可矣。若论此图则性传所未解。所谓气上可推寻其理者。以此图观之。从左
复心此图。有疑致思。未得其故。偶与草堂语及之。草堂亦疑焉。即质于莲坊。则其论如是。性传之惑滋甚。莲坊此说。若泛论理气则可矣。若论此图则性传所未解。所谓气上可推寻其理者。以此图观之。从左此图与程林隐多不同。当是记不全之故。然以中圈为气之失则同。而莲坊大加称赏。何耶。莲坊见理不分明。主张气太甚。有此差失。无足怪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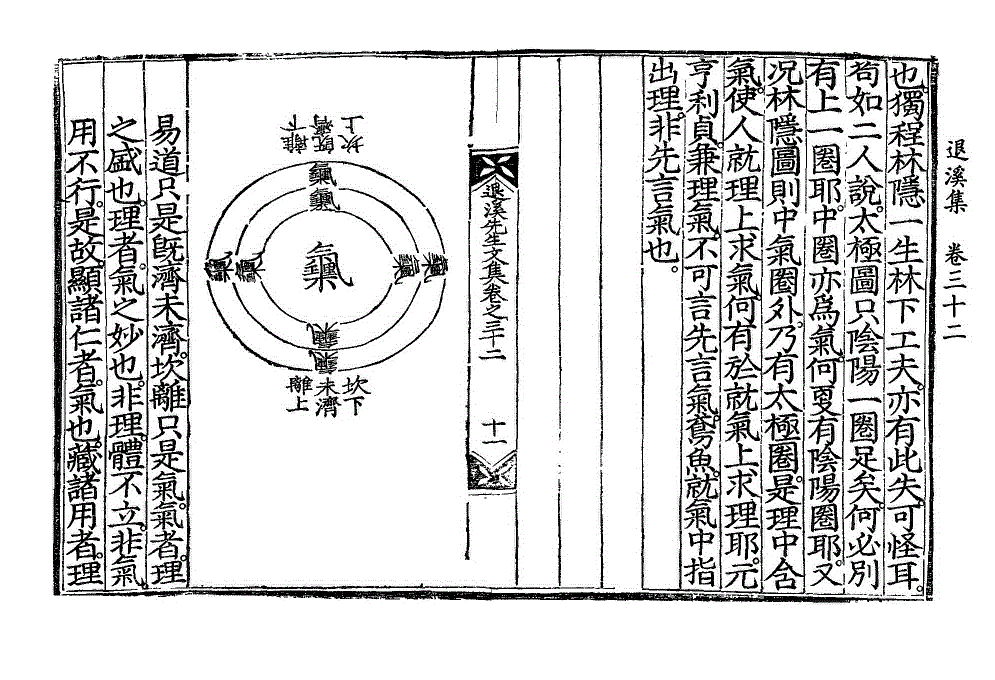 也。独程林隐一生林下工夫。亦有此失。可怪耳。苟如二人说。太极图只阴阳一圈足矣。何必别有上一圈耶。中圈亦为气。何更有阴阳圈耶。又况林隐图则中气圈外。乃有太极圈。是理中含气。使人就理上求气。何有于就气上求理耶。元亨利贞。兼理气。不可言先言气。鸢鱼。就气中指出理。非先言气也。
也。独程林隐一生林下工夫。亦有此失。可怪耳。苟如二人说。太极图只阴阳一圈足矣。何必别有上一圈耶。中圈亦为气。何更有阴阳圈耶。又况林隐图则中气圈外。乃有太极圈。是理中含气。使人就理上求气。何有于就气上求理耶。元亨利贞。兼理气。不可言先言气。鸢鱼。就气中指出理。非先言气也。삽화 새창열기
易道只是既济未济。坎离只是气。气者。理之盛也。理者。气之妙也。非理。体不立。非气。用不行。是故。显诸仁者。气也。藏诸用者。理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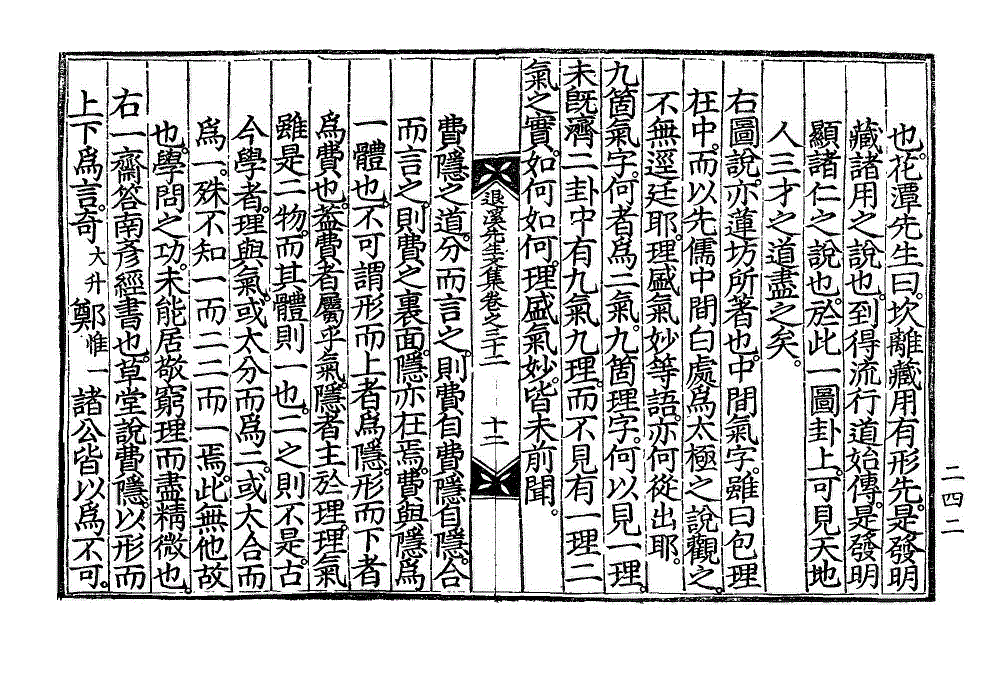 也。花潭先生曰。坎离藏用有形先。是发明藏诸用之说也。到得流行道始传。是发明显诸仁之说也。于此一图卦上。可见天地人三才之道尽之矣。
也。花潭先生曰。坎离藏用有形先。是发明藏诸用之说也。到得流行道始传。是发明显诸仁之说也。于此一图卦上。可见天地人三才之道尽之矣。右图说。亦莲坊所著也。中间气字。虽曰包理在中。而以先儒中间白处为太极之说观之。不无径廷耶。理盛气妙等语。亦何从出耶。
九个气字。何者为二气。九个理字。何以见一理。未既济二卦中有九气九理。而不见有一理二气之实。如何如何。理盛气妙。皆未前闻。
费隐之道。分而言之。则费自费隐自隐。合而言之。则费之里面。隐亦在焉。费与隐为一体也。不可谓形而上者为隐。形而下者为费也。盖费者属乎气。隐者主于理。理气虽是二物。而其体则一也。二之则不是。古今学者。理与气。或太分而为二。或太合而为一。殊不知一而二二而一焉。此无他故也。学问之功。未能居敬穷理而尽精微也。
右一斋答南彦经书也。草堂说费隐。以形而上下为言。奇(大升)郑(惟一)诸公皆以为不可。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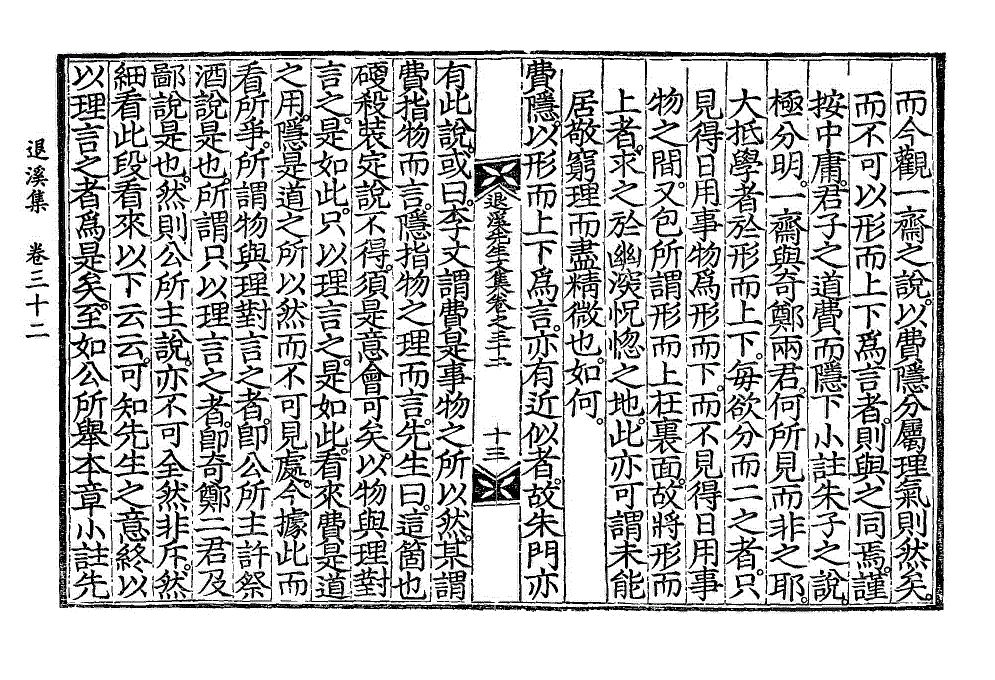 而今观一斋之说。以费隐分属理气则然矣。而不可以形而上下为言者。则与之同焉。谨按中庸。君子之道费而隐下小注朱子之说。极分明。一斋与奇郑两君。何所见而非之耶。大抵学者于形而上下。每欲分而二之者。只见得日用事物为形而下。而不见得日用事物之间。又包所谓形而上在里面。故将形而上者。求之于幽深恍惚之地。此亦可谓未能居敬穷理而尽精微也。如何。
而今观一斋之说。以费隐分属理气则然矣。而不可以形而上下为言者。则与之同焉。谨按中庸。君子之道费而隐下小注朱子之说。极分明。一斋与奇郑两君。何所见而非之耶。大抵学者于形而上下。每欲分而二之者。只见得日用事物为形而下。而不见得日用事物之间。又包所谓形而上在里面。故将形而上者。求之于幽深恍惚之地。此亦可谓未能居敬穷理而尽精微也。如何。费隐。以形而上下为言。亦有近似者。故朱门亦有此说。或曰。李丈谓费是事物之所以然。某谓费指物而言。隐指物之理而言。先生曰。这个也硬杀装定说不得。须是意会可矣。以物与理对言之。是如此。只以理言之。是如此。看来费是道之用。隐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见处。今据此而看所争。所谓物与理对言之者。即公所主许祭酒说是也。所谓只以理言之者。即奇郑二君及鄙说是也。然则公所主说。亦不可全然非斥。然细看此段看来以下云云。可知先生之意终以以理言之者为是矣。至如公所举本章小注先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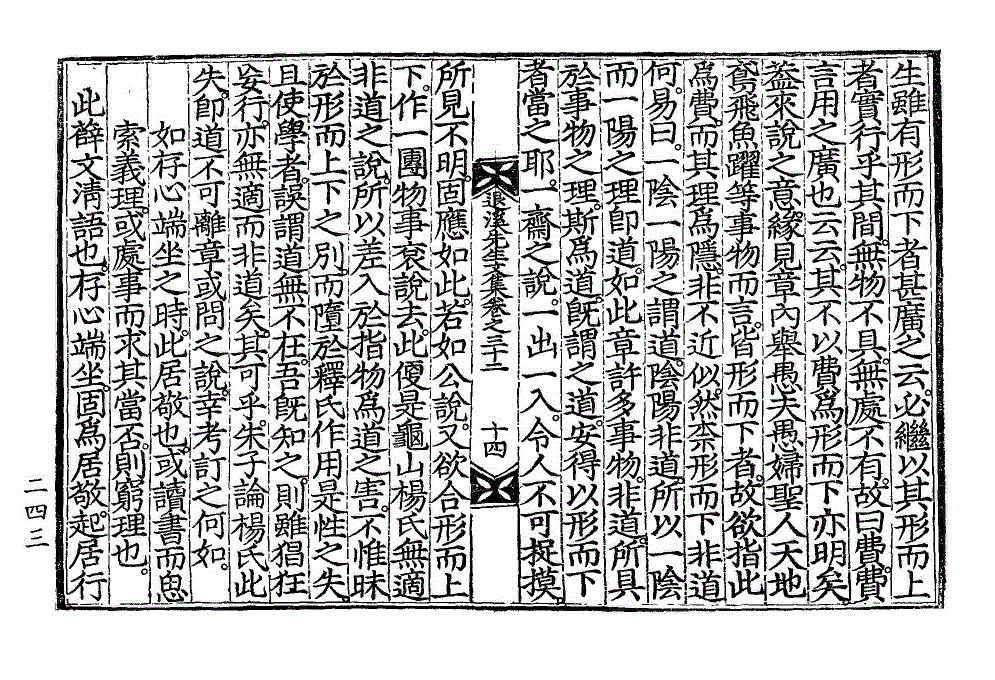 生虽有形而下者甚广之云。必继以其形而上者实行乎其间。无物不具。无处不有。故曰费。费言用之广也云云。其不以费为形而下亦明矣。盖来说之意。缘见章内举愚夫愚妇圣人天地鸢飞鱼跃等事物而言。皆形而下者。故欲指此为费。而其理为隐。非不近似。然柰形而下非道何。易曰。一阴一阳之谓道。阴阳非道。所以一阴而一阳之理即道。如此章许多事物。非道。所具于事物之理。斯为道。既谓之道。安得以形而下者当之耶。一斋之说。一出一入。令人不可捉摸。所见不明。固应如此。若如公说。又欲合形而上下。作一团物事衮说去。此便是龟山杨氏无适非道之说。所以差入于指物为道之害。不惟昧于形而上下之别。而堕于释氏作用是性之失。且使学者。误谓道无不在。吾既知之。则虽猖狂妄行。亦无适而非道矣。其可乎。朱子论杨氏此失。即道不可离章或问之说。幸考订之何如。
生虽有形而下者甚广之云。必继以其形而上者实行乎其间。无物不具。无处不有。故曰费。费言用之广也云云。其不以费为形而下亦明矣。盖来说之意。缘见章内举愚夫愚妇圣人天地鸢飞鱼跃等事物而言。皆形而下者。故欲指此为费。而其理为隐。非不近似。然柰形而下非道何。易曰。一阴一阳之谓道。阴阳非道。所以一阴而一阳之理即道。如此章许多事物。非道。所具于事物之理。斯为道。既谓之道。安得以形而下者当之耶。一斋之说。一出一入。令人不可捉摸。所见不明。固应如此。若如公说。又欲合形而上下。作一团物事衮说去。此便是龟山杨氏无适非道之说。所以差入于指物为道之害。不惟昧于形而上下之别。而堕于释氏作用是性之失。且使学者。误谓道无不在。吾既知之。则虽猖狂妄行。亦无适而非道矣。其可乎。朱子论杨氏此失。即道不可离章或问之说。幸考订之何如。如存心端坐之时。此居敬也。或读书而思索义理。或处事而求其当否。则穷理也。
此薜文清语也。存心端坐。固为居敬。起居行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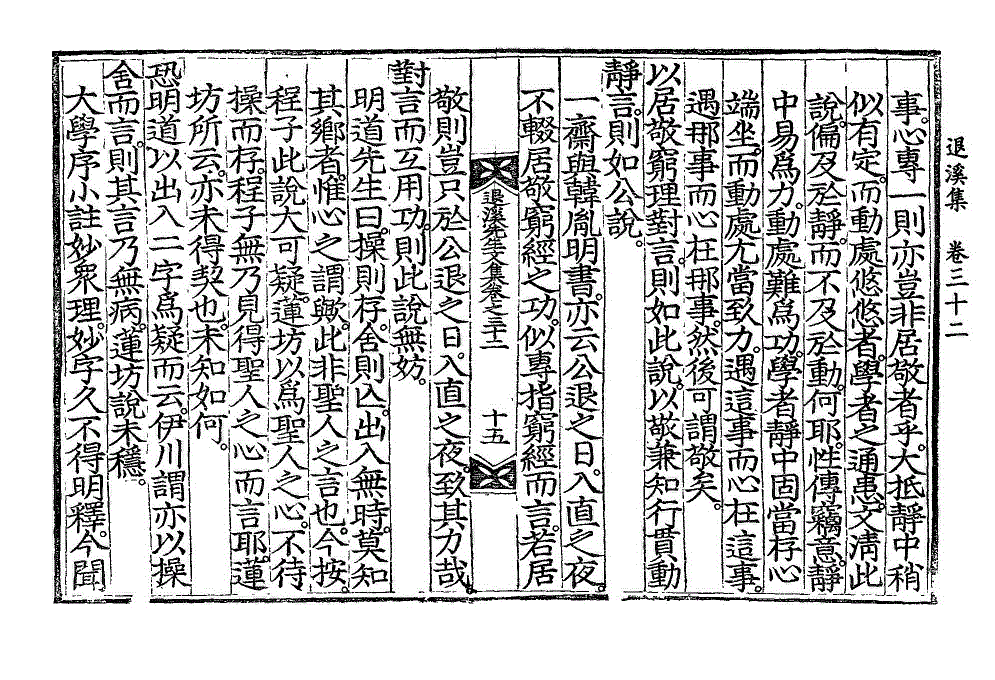 事。心专一则亦岂非居敬者乎。大抵静中稍似有定。而动处悠悠者。学者之通患。文清此说。偏及于静。而不及于动。何耶。性传窃意。静中易为力。动处难为功。学者静中固当存心端坐。而动处尤当致力。遇这事而心在这事。遇那事而心在那事。然后可谓敬矣。
事。心专一则亦岂非居敬者乎。大抵静中稍似有定。而动处悠悠者。学者之通患。文清此说。偏及于静。而不及于动。何耶。性传窃意。静中易为力。动处难为功。学者静中固当存心端坐。而动处尤当致力。遇这事而心在这事。遇那事而心在那事。然后可谓敬矣。以居敬穷理对言。则如此说。以敬兼知行贯动静言。则如公说。
一斋与韩胤明书。亦云公退之日。入直之夜。不辍居敬穷经之功。似专指穷经而言。若居敬则岂只于公退之日。入直之夜。致其力哉。
对言而互用功。则此说无妨。
明道先生曰。操则存。舍则亡。出入无时。莫知其乡者。惟心之谓欤。此非圣人之言也。今按。程子此说大可疑。莲坊以为圣人之心。不待操而存。程子无乃见得圣人之心而言耶。莲坊所云。亦未得契也。未知如何。
恐明道以出入二字为疑而云。伊川谓亦以操舍而言。则其言乃无病。莲坊说未稳。
大学序小注妙众理。妙字久不得明释。今闻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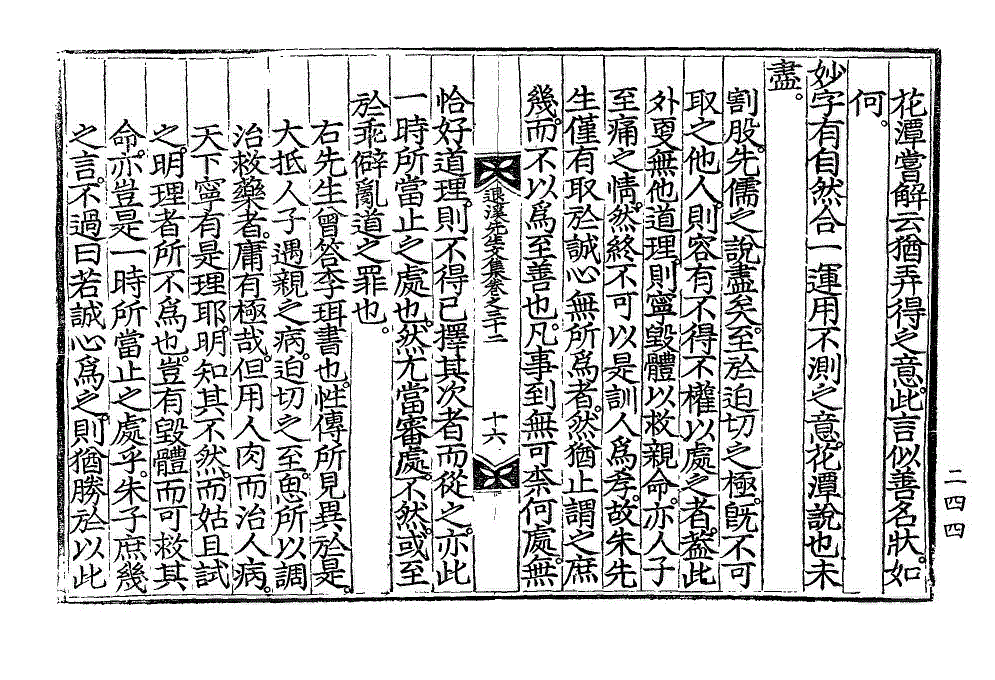 花潭尝解云犹弄得之意。此言似善名状。如何。
花潭尝解云犹弄得之意。此言似善名状。如何。妙字有自然合一运用不测之意。花潭说也未尽。
割股。先儒之说尽矣。至于迫切之极。既不可取之他人。则容有不得不权以处之者。盖此外更无他道理。则宁毁体以救亲命。亦人子至痛之情。然终不可以是训人为孝。故朱先生仅有取于诚心无所为者。然犹止谓之庶几。而不以为至善也。凡事到无可柰何处。无恰好道理。则不得已择其次者而从之。亦此一时所当止之处也。然尤当审处。不然。或至于乖僻乱道之罪也。
右先生曾答李珥书也。性传所见异于是。大抵人子遇亲之病。迫切之至。思所以调治救药者。庸有极哉。但用人肉而治人病。天下宁有是理耶。明知其不然。而姑且试之。明理者所不为也。岂有毁体而可救其命。亦岂是一时所当止之处乎。朱子庶几之言。不过曰若诚心为之。则犹胜于以此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5H 页
 要誉者云耳。非以此为是也。金濯缨作非鄠人对。以攻昌黎公。其言曰。就令善医引方书。以为非人肉合药无良云尔。将以彼为诞。坐视其母之死而不从耶。性传亦以为苟有善医者。必不为此言。濯缨虽惑于此言。而昌黎则必不惑于此言也。如何。
要誉者云耳。非以此为是也。金濯缨作非鄠人对。以攻昌黎公。其言曰。就令善医引方书。以为非人肉合药无良云尔。将以彼为诞。坐视其母之死而不从耶。性传亦以为苟有善医者。必不为此言。濯缨虽惑于此言。而昌黎则必不惑于此言也。如何。缘或问取其诚以为庶几。故向者为说如此。后来思之。终觉有未安处。此事当以昌黎与公说为正。
答禹景善(丁卯)
郑直讲来乡。时未相见。中和刊谬释事。时未详问。然子中之于我。可谓相知之深。不即毁去其刊本。恨怪恨怪。已作书恳于奇明彦。行到中和。必索取其板。烧火于眼中而后去。此人达理非龌龊。必能如人意也。文广文素有文名。而处心行事。多未合理。观此事。亦可知也。
答禹景善
江头黯然之恨。正如所谕。城中非不屡面。病思客况。苦无头绪。每见。见面而已。今而思之。似非吾所为。可谓自失其素志。可惧可惧。滉距行期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5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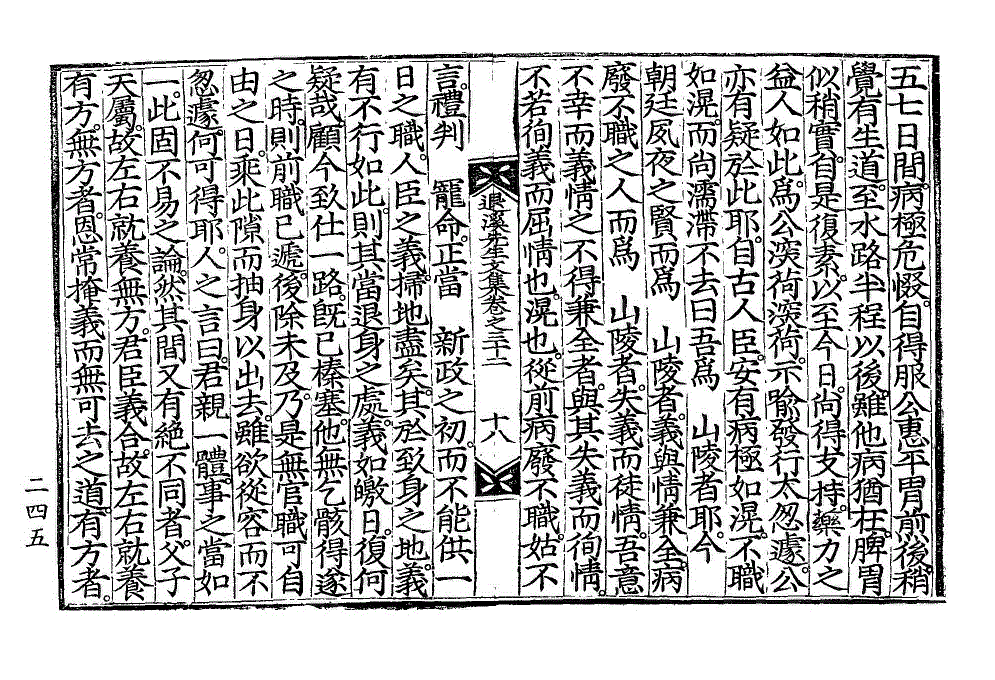 五七日间。病极危惙。自得服公惠平胃煎后。稍觉有生道。至水路半程以后。虽他病犹在。脾胃似稍实。自是复素。以至今日。尚得支持。药力之益人如此。为公深荷深荷。示喻发行太悤遽。公亦有疑于此耶。自古人臣。安有病极如滉。不职如滉。而尚濡滞不去曰吾为 山陵者耶。今 朝廷夙夜之贤而为 山陵者。义与情兼全。病废不职之人而为 山陵者。失义而徒情。吾意不幸而义情之不得兼全者。与其失义而徇情。不若徇义而屈情也。滉也。从前病废不职。姑不言。礼判 宠命。正当 新政之初。而不能供一日之职。人臣之义。扫地尽矣。其于致身之地。义有不行如此。则其当退身之处。义如皦日。复何疑哉。顾今致仕一路。既已榛塞。他无乞骸得遂之时。则前职已递。后除未及。乃是无官职可自由之日。乘此隙而抽身以出去。虽欲从容而不悤遽。何可得耶。人之言曰。君亲一体。事之当如一。此固不易之论。然其间又有绝不同者。父子天属。故左右就养无方。君臣义合。故左右就养有方。无方者。恩常掩义而无可去之道。有方者。
五七日间。病极危惙。自得服公惠平胃煎后。稍觉有生道。至水路半程以后。虽他病犹在。脾胃似稍实。自是复素。以至今日。尚得支持。药力之益人如此。为公深荷深荷。示喻发行太悤遽。公亦有疑于此耶。自古人臣。安有病极如滉。不职如滉。而尚濡滞不去曰吾为 山陵者耶。今 朝廷夙夜之贤而为 山陵者。义与情兼全。病废不职之人而为 山陵者。失义而徒情。吾意不幸而义情之不得兼全者。与其失义而徇情。不若徇义而屈情也。滉也。从前病废不职。姑不言。礼判 宠命。正当 新政之初。而不能供一日之职。人臣之义。扫地尽矣。其于致身之地。义有不行如此。则其当退身之处。义如皦日。复何疑哉。顾今致仕一路。既已榛塞。他无乞骸得遂之时。则前职已递。后除未及。乃是无官职可自由之日。乘此隙而抽身以出去。虽欲从容而不悤遽。何可得耶。人之言曰。君亲一体。事之当如一。此固不易之论。然其间又有绝不同者。父子天属。故左右就养无方。君臣义合。故左右就养有方。无方者。恩常掩义而无可去之道。有方者。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6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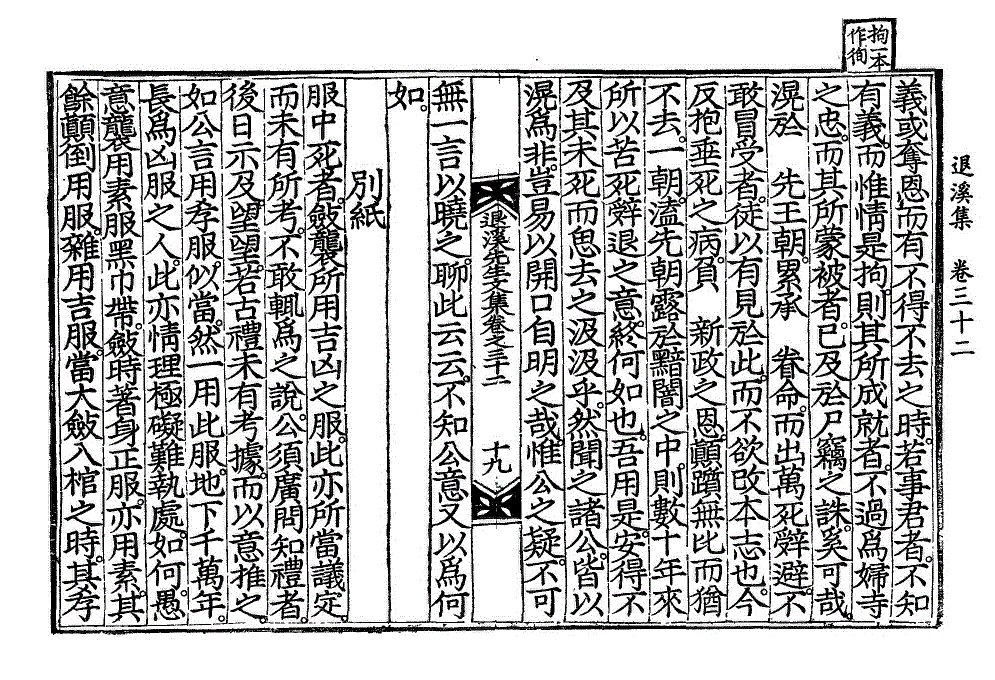 义或夺恩而有不得不去之时。若事君者。不知有义。而惟情是拘。(拘。一本作徇。)则其所成就者。不过为妇寺之忠。而其所蒙被者。已及于尸窃之诛。奚可哉。滉于 先王朝。累承 眷命。而出万死辞避。不敢冒受者。徒以有见于此。而不欲改本志也。今反抱垂死之病。负 新政之恩。颠踬无比而犹不去。一朝。溘先朝露于黯闇之中。则数十年来所以苦死辞退之意。终何如也。吾用是。安得不及其未死而思去之汲汲乎。然闻之诸公。皆以滉为非。岂易以开口自明之哉。惟公之疑。不可无一言以晓之。聊此云云。不知公意又以为何如。
义或夺恩而有不得不去之时。若事君者。不知有义。而惟情是拘。(拘。一本作徇。)则其所成就者。不过为妇寺之忠。而其所蒙被者。已及于尸窃之诛。奚可哉。滉于 先王朝。累承 眷命。而出万死辞避。不敢冒受者。徒以有见于此。而不欲改本志也。今反抱垂死之病。负 新政之恩。颠踬无比而犹不去。一朝。溘先朝露于黯闇之中。则数十年来所以苦死辞退之意。终何如也。吾用是。安得不及其未死而思去之汲汲乎。然闻之诸公。皆以滉为非。岂易以开口自明之哉。惟公之疑。不可无一言以晓之。聊此云云。不知公意又以为何如。别纸
服中死者。敛袭所用吉凶之服。此亦所当议定。而未有所考。不敢辄为之说。公须广问知礼者。后日示及。望望。若古礼未有考据。而以意推之。如公言用孝服。似当。然一用此服。地下千万年。长为凶服之人。此亦情理极碍难执处。如何。愚意袭用素服黑巾带。敛时著身正服。亦用素。其馀颠倒用服。杂用吉服。当大敛入棺之时。其孝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6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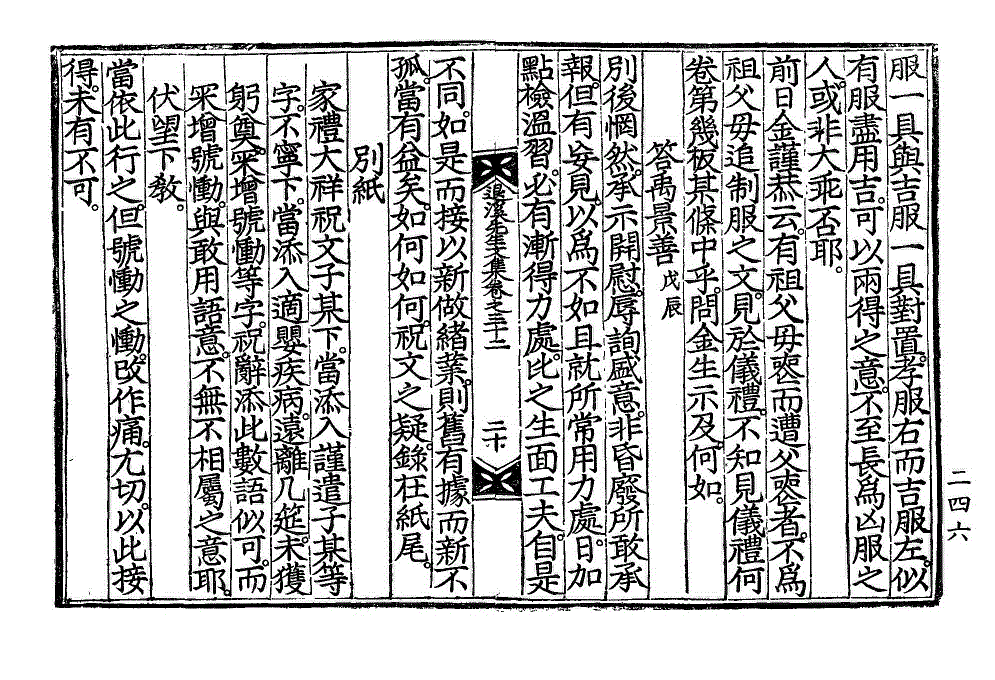 服一具与吉服一具对置。孝服右而吉服左。似有服尽用吉。可以两得之意。不至长为凶服之人。或非大乖否耶。
服一具与吉服一具对置。孝服右而吉服左。似有服尽用吉。可以两得之意。不至长为凶服之人。或非大乖否耶。前日金谨恭云。有祖父母丧而遭父丧者。不为祖父母追制服之文。见于仪礼。不知见仪礼何卷第几板某条中乎。问金生示及。何如。
答禹景善(戊辰)
别后惘然。承示开慰。辱询盛意。非昏废所敢承报。但有妄见。以为不如且就所常用力处。日加点检温习。必有渐得力处。比之生面工夫。自是不同。如是而接以新做绪业。则旧有据而新不孤。当有益矣。如何如何。祝文之疑。录在纸尾。
别纸
家礼大祥祝文子某下。当添入谨遣子某等字。不宁下。当添入适婴疾病。远离几筵。未获躬奠。冞增号恸等字。祝辞添此数语似可。而冞增号恸。与敢用语意。不无不相属之意耶。伏望下教。
当依此行之。但号恸之恸。改作痛。尤切。以此接得。未有不可。
答禹景善
郑君重遭大祸。天之于此。一何如是之酷耶。不忍道不忍闻。奔丧曲折。古无可据。虽有。吾未知之。何敢妄云。须更问知礼处。然以臆料言之。重丧既成服。在途恐只以重丧服行。而至彼行变成之礼。似可。盖重丧遭轻丧。当其事则服其服。既事。反重服云。则重服为常故也。何如何如。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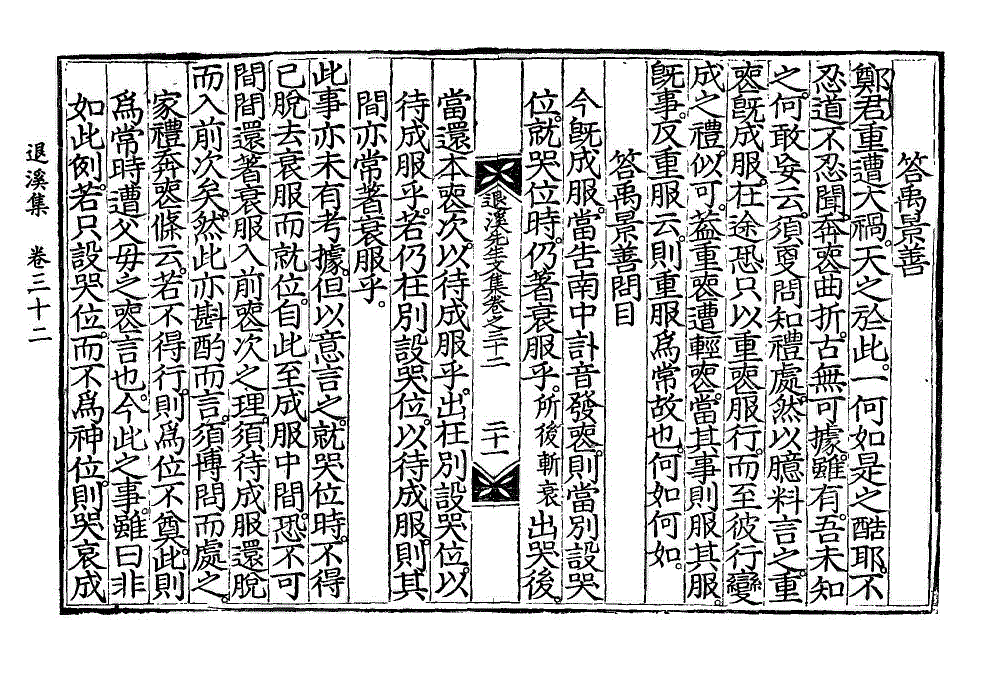 答禹景善问目
答禹景善问目今既成服。当告南中讣音发丧。则当别设哭位。就哭位时。仍著衰服乎。(所后斩衰)出哭后。当还本丧次。以待成服乎。出在别设哭位。以待成服乎。若仍在别设哭位。以待成服。则其间亦常著衰服乎。
此事亦未有考据。但以意言之。就哭位时。不得已脱去衰服而就位。自此至成服中间。恐不可间间还著衰服入前丧次之理。须待成服还脱而入前次矣。然此亦斟酌而言。须博问而处之。
家礼奔丧条云。若不得行。则为位不奠。此则为常时遭父母之丧言也。今此之事。虽曰非如此例。若只设哭位。而不为神位。则哭哀成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7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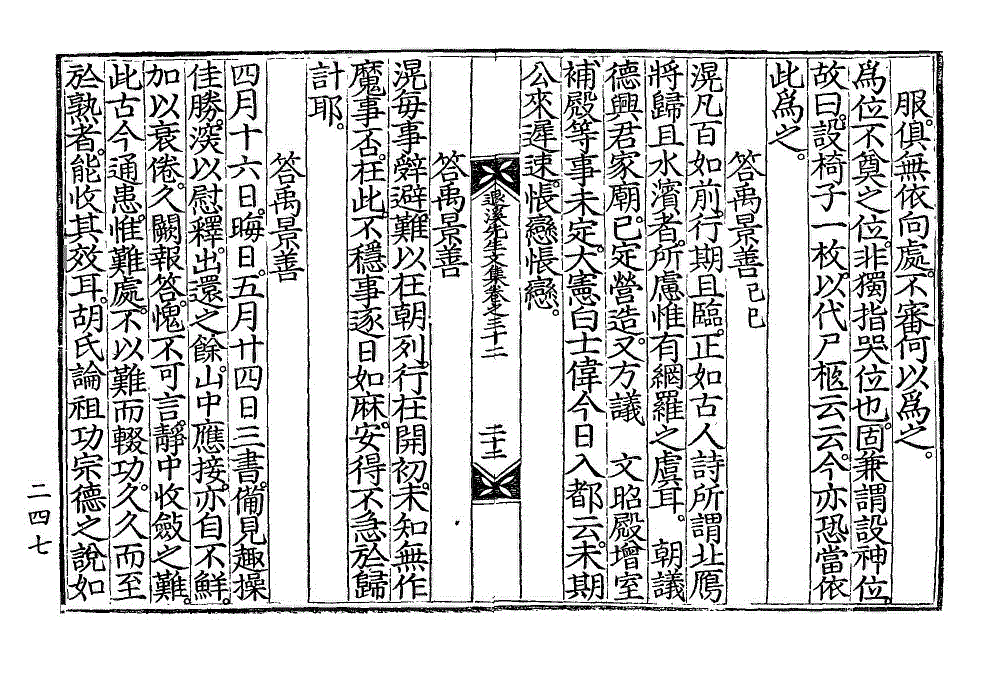 服。俱无依向处。不审何以为之。
服。俱无依向处。不审何以为之。为位不奠之位。非独指哭位也。固兼谓设神位。故曰。设椅子一枚。以代尸柩云云。今亦恐当依此为之。
答禹景善(己巳)
滉凡百如前。行期且临。正如古人诗所谓北雁将归且水滨者。所虑惟有网罗之虞耳。 朝议德兴君家庙。已定营造。又方议 文昭殿增室补殿等事未定。大宪白士伟今日入都云。未期公来迟速。怅恋怅恋。
答禹景善
滉每事辞避。难以在朝列。行在开初。未知无作魔事否。在此。不稳事逐日如麻。安得不急于归计耶。
答禹景善
四月十六日。晦日。五月廿四日三书。备见趣操佳胜。深以慰释。出还之馀。山中应接。亦自不鲜。加以衰倦。久阙报答。愧不可言。静中收敛之难。此古今通患。惟难处。不以难而辍功。久久而至于熟者。能收其效耳。胡氏论祖功宗德之说如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8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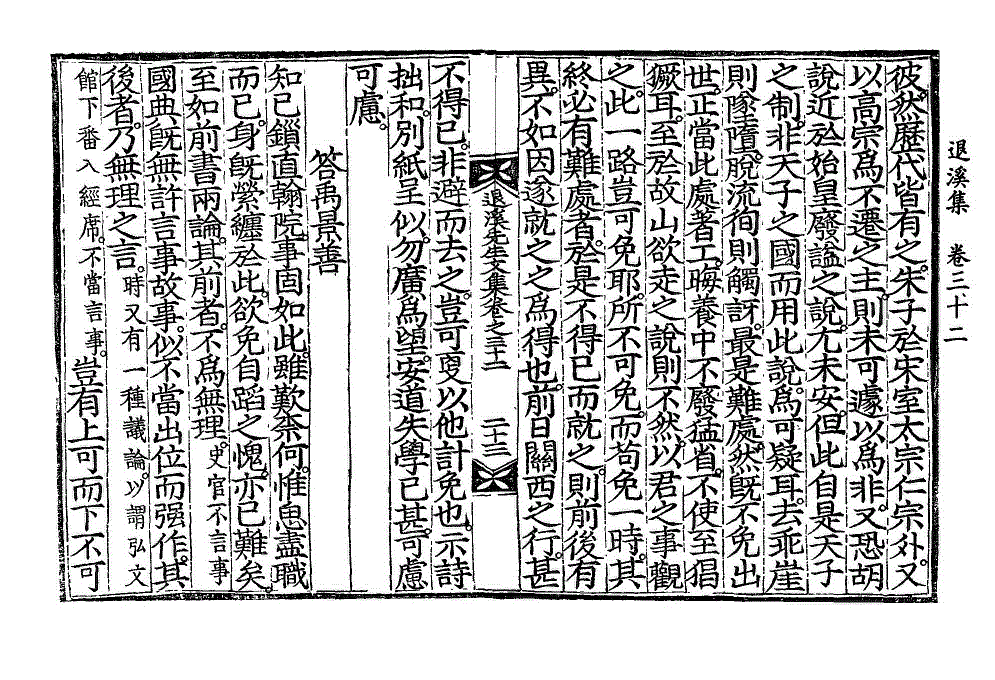 彼。然历代皆有之。朱子于宋室太宗仁宗外。又以高宗为不迁之主。则未可遽以为非。又恐胡说近于始皇废谥之说。尤未安。但此自是天子之制。非天子之国而用此说。为可疑耳。去乖崖则坠堕。脱流徇则触讶。最是难处。然既不免出世。正当此处著工。晦养中不废猛省。不使至猖獗耳。至于故山欲走之说则不然。以君之事观之。此一路岂可免耶。所不可免。而苟免一时。其终必有难处者。于是不得已而就之。则前后有异。不如因遂就之之为得也。前日关西之行。甚不得已。非避而去之。岂可更以他计免也。示诗拙和。别纸呈似。勿广为望。安道失学已甚。可虑可虑。
彼。然历代皆有之。朱子于宋室太宗仁宗外。又以高宗为不迁之主。则未可遽以为非。又恐胡说近于始皇废谥之说。尤未安。但此自是天子之制。非天子之国而用此说。为可疑耳。去乖崖则坠堕。脱流徇则触讶。最是难处。然既不免出世。正当此处著工。晦养中不废猛省。不使至猖獗耳。至于故山欲走之说则不然。以君之事观之。此一路岂可免耶。所不可免。而苟免一时。其终必有难处者。于是不得已而就之。则前后有异。不如因遂就之之为得也。前日关西之行。甚不得已。非避而去之。岂可更以他计免也。示诗拙和。别纸呈似。勿广为望。安道失学已甚。可虑可虑。答禹景善
知己锁直翰院。事固如此。虽叹柰何。惟思尽职而已。身既萦缠于此。欲免自蹈之愧。亦已难矣。至如前书两论。其前者。不为无理。(史官不言事)国典既无许言事故事。似不当出位而强作。其后者。乃无理之言。(时又有一种议论。以谓弘文馆下番入经席。不当言事。)岂有上可而下不可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8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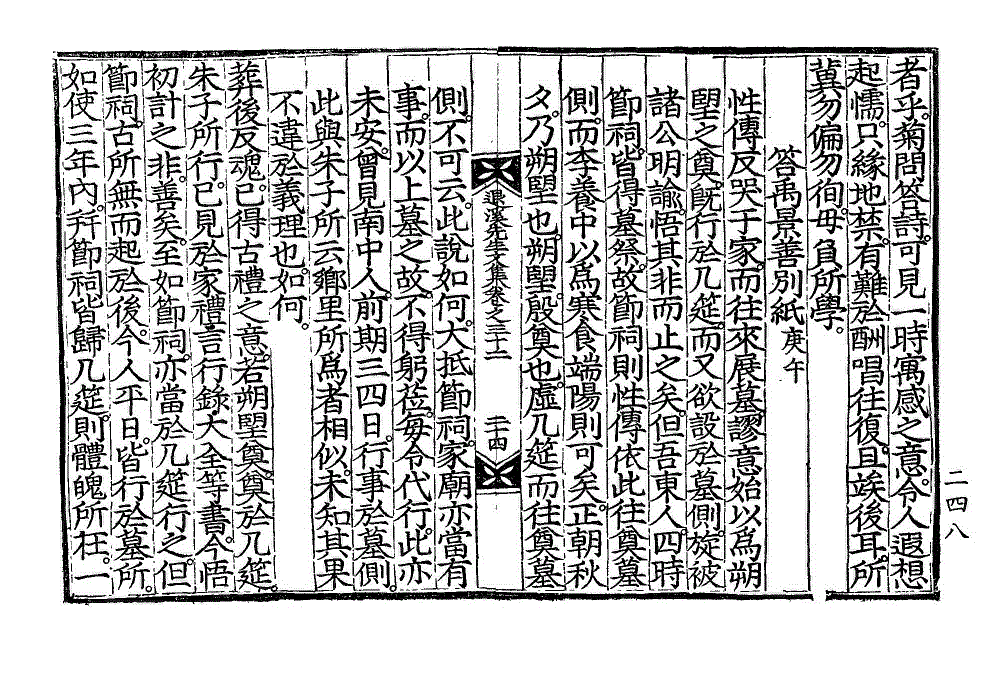 者乎。菊问答诗。可见一时寓感之意。令人遐想起懦。只缘地禁。有难于酬唱往复。且俟后耳。所冀勿偏勿徇。毋负所学。
者乎。菊问答诗。可见一时寓感之意。令人遐想起懦。只缘地禁。有难于酬唱往复。且俟后耳。所冀勿偏勿徇。毋负所学。答禹景善别纸(庚午)
性传反哭于家。而往来展墓。谬意始以为朔望之奠。既行于几筵。而又欲设于墓侧。旋被诸公明谕。悟其非而止之矣。但吾东人。四时节祠。皆得墓祭。故节祠则性传依此往奠墓侧。而李养中以为寒食端阳则可矣。正朝秋夕。乃朔望也。朔望。殷奠也。虚几筵而往奠墓侧。不可云。此说如何。大抵节祠。家庙亦当有事。而以上墓之故。不得躬莅。每令代行。此亦未安。曾见南中人。前期三四日。行事于墓侧。此与朱子所云乡里所为者相似。未知其果不违于义理也。如何。
葬后反魂。已得古礼之意。若朔望奠。奠于几筵。朱子所行。已见于家礼,言行录,大全等书。今悟初计之非。善矣。至如节祠。亦当于几筵行之。但节祠。古所无而起于后。今人平日。皆行于墓所。如使三年内。并节祠皆归几筵。则体魄所在。一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9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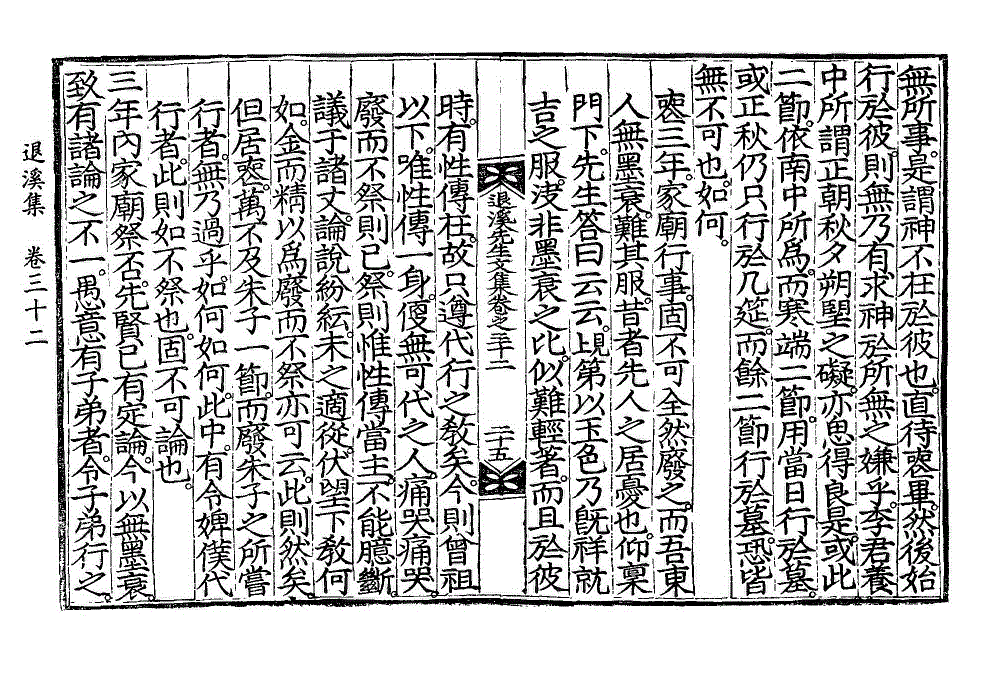 无所事。是谓神不在于彼也。直待丧毕。然后始行于彼。则无乃有求神于所无之嫌乎。李君养中所谓正朝秋夕朔望之碍。亦思得良是。或此二节。依南中所为。而寒端二节。用当日行于墓。或正秋仍只行于几筵。而馀二节行于墓。恐皆无不可也。如何。
无所事。是谓神不在于彼也。直待丧毕。然后始行于彼。则无乃有求神于所无之嫌乎。李君养中所谓正朝秋夕朔望之碍。亦思得良是。或此二节。依南中所为。而寒端二节。用当日行于墓。或正秋仍只行于几筵。而馀二节行于墓。恐皆无不可也。如何。丧三年。家庙行事。固不可全然废之。而吾东人无墨衰。难其服。昔者先人之居忧也。仰禀门下。先生答曰云云。(见上)第以玉色乃既祥就吉之服。决非墨衰之比。似难轻著。而且于彼时。有性传在。故只遵代行之教矣。今则曾祖以下。唯性传一身。便无可代之人。痛哭痛哭。废而不祭则已。祭则惟性传当主。不能臆断。议于诸丈。论说纷纭。未之适从。伏望下教何如。金而精以为废而不祭亦可云。此则然矣。但居丧。万不及朱子一节。而废朱子之所尝行者。无乃过乎。如何如何。此中。有令婢仆代行者。此则如不祭也。固不可论也。
三年内家庙祭否。先贤已有定论。今以无墨衰。致有诸论之不一。愚意有子弟者。令子弟行之。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4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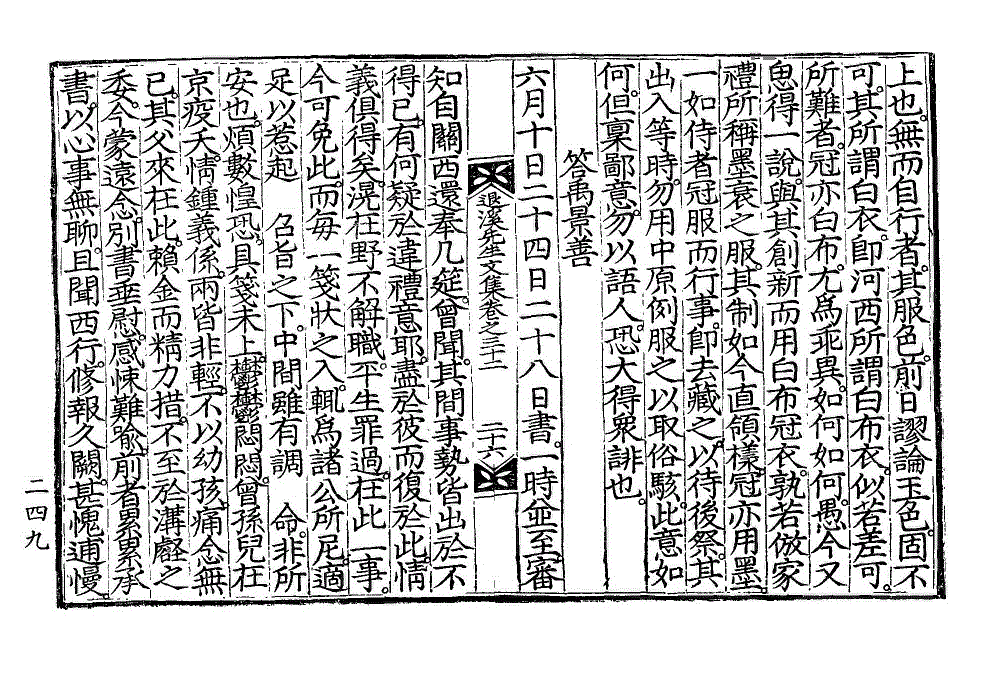 上也。无而自行者。其服色。前日谬论玉色。固不可。其所谓白衣。即河西所谓白布衣。似若差可。所难者。冠亦白布。尤为乖异。如何如何。愚今又思得一说。与其创新而用白布冠衣。孰若仿家礼所称墨衰之服。其制如今直领样。冠亦用墨。一如侍者冠服而行事。即去藏之。以待后祭。其出入等时。勿用中原例服之以取俗骇。此意如何。但禀鄙意。勿以语人。恐大得众诽也。
上也。无而自行者。其服色。前日谬论玉色。固不可。其所谓白衣。即河西所谓白布衣。似若差可。所难者。冠亦白布。尤为乖异。如何如何。愚今又思得一说。与其创新而用白布冠衣。孰若仿家礼所称墨衰之服。其制如今直领样。冠亦用墨。一如侍者冠服而行事。即去藏之。以待后祭。其出入等时。勿用中原例服之以取俗骇。此意如何。但禀鄙意。勿以语人。恐大得众诽也。答禹景善
六月十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书。一时并至。审知自关西还奉几筵。曾闻。其间事势皆出于不得已。有何疑于违礼意耶。尽于彼而复于此。情义俱得矣。滉在野不解职。平生罪过。在此一事。今可免此。而每一笺状之入。辄为诸公所尼。适足以惹起 召旨之下。中间虽有调 命。非所安也。烦数惶恐。具笺未上。郁郁闷闷。曾孙儿在京疫夭。情钟义系。两皆非轻。不以幼孩。痛念无已。其父来在此。赖金而精力措。不至于沟壑之委。今蒙远念。别书垂慰。感悚难喻。前者累累承书。以心事无聊。且闻西行。修报久阙。甚愧逋慢。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50H 页
 今以逃暑。来在易东。曾来诸书。在家中箱箧。未由搜取。只以顷来三书略报耳。伏惟照悉。惟祈以时循勉。不备谨状。
今以逃暑。来在易东。曾来诸书。在家中箱箧。未由搜取。只以顷来三书略报耳。伏惟照悉。惟祈以时循勉。不备谨状。别纸
前谕墨衰如侍者冠服云云。侍者。只有俗所谓头巾而无其冠。又当著何带。
墨衰冠带之制未详。率意言之未安。然似不过冠头巾而带亦墨耳。
期而功衰之文。只见于戴记问丧,杂记等篇。而未见于仪礼经传。是何耶。抑有之而性传不能详考耶。古者。卒哭亦有受服。而家礼无此节次。故性传依此行之。今于期。亦只依家礼。练布为冠。去首绖负版辟领衰。而不别有功衰耶。何以则不戾于圣贤制礼之意耶。家礼虽不言中衣。而性传依古礼制之。今不可不受以练。如何。
功衰之不见仪礼经传。亦不知何故。卒哭受服。家礼阙之。于期亦只练布为冠。去首绖等。不别有功衰。乃古今损益之宜。顷年 廷议。 国恤于练。亦以不别制服为定。今当遵依。练中衣则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5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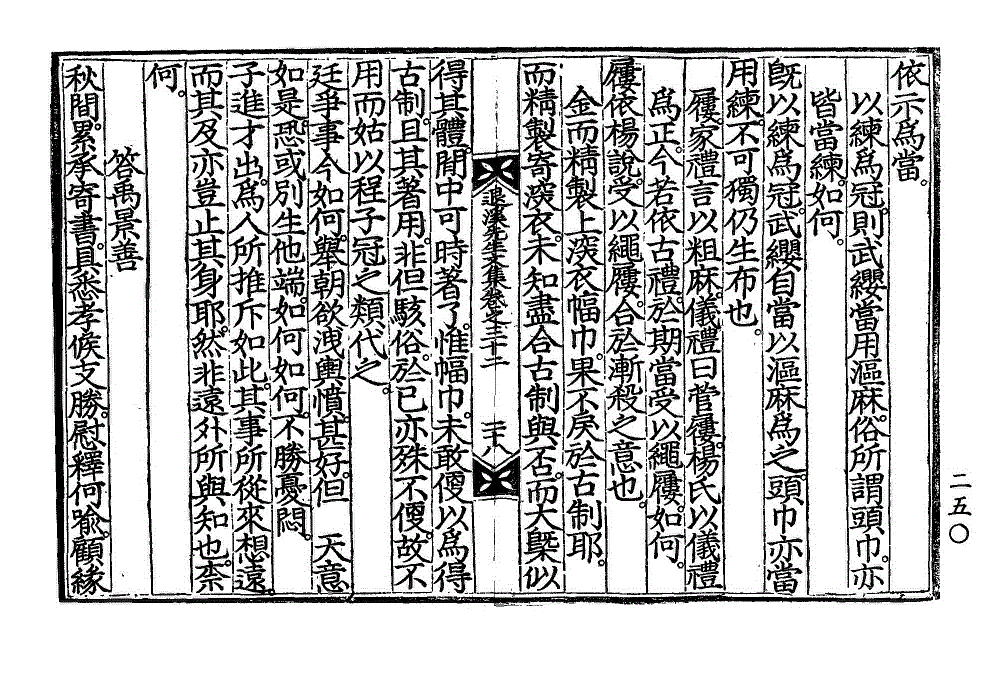 依示为当。
依示为当。以练为冠。则武缨当用沤麻。俗所谓头巾。亦皆当练。如何。
既以练为冠。武缨自当以沤麻为之。头巾亦当用练。不可独仍生布也。
屦。家礼言以粗麻。仪礼曰菅屦。杨氏以仪礼为正。今若依古礼。于期当受以绳屦。如何。
屦依杨说。受以绳屦。合于渐杀之意也。
金而精制上深衣,幅巾。果不戾于古制耶。
而精制寄深衣。未知尽合古制与否。而大槩似得其体。閒中可时著了。惟幅巾。未敢便以为得古制。且其著用。非但骇俗。于己亦殊不便。故不用而姑以程子冠之类代之。
廷争事今如何。举朝欲泄舆愤。甚好。但 天意如是。恐或别生他端。如何如何。不胜忧闷。
子进才出。为人所推斥如此。其事所从来想远。而其及亦岂止其身耶。然非远外所与知也。柰何。
答禹景善
秋间。累承寄书。具悉孝候支胜。慰释何喻。顾缘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5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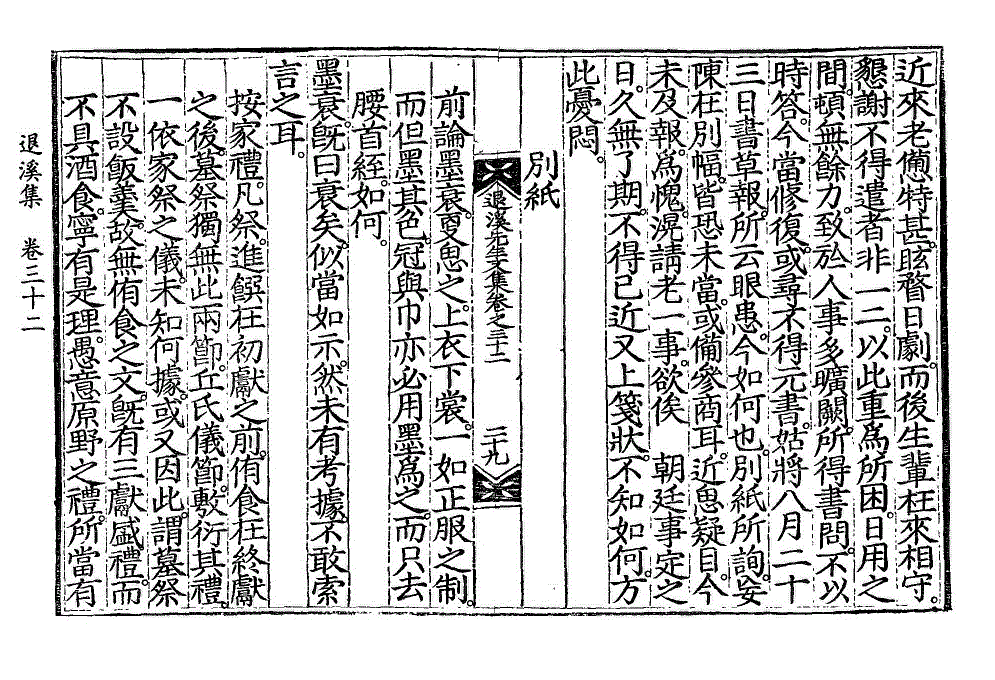 近来老惫特甚。眩瞀日剧。而后生辈枉来相守。恳谢不得遣者非一二。以此重为所困。日用之间。顿无馀力。致于人事多旷阙。所得书问。不以时答。今当修复。或寻不得元书。姑将八月二十三日书草报。所云眼患。今如何也。别纸所询。妄陈在别幅。皆恐未当。或备参商耳。近思疑目。今未及报。为愧。滉请老一事。欲俟 朝廷事定之日。久无了期。不得已近又上笺状。不知如何。方此忧闷。
近来老惫特甚。眩瞀日剧。而后生辈枉来相守。恳谢不得遣者非一二。以此重为所困。日用之间。顿无馀力。致于人事多旷阙。所得书问。不以时答。今当修复。或寻不得元书。姑将八月二十三日书草报。所云眼患。今如何也。别纸所询。妄陈在别幅。皆恐未当。或备参商耳。近思疑目。今未及报。为愧。滉请老一事。欲俟 朝廷事定之日。久无了期。不得已近又上笺状。不知如何。方此忧闷。别纸
前论墨衰。更思之。上衣下裳。一如正服之制。而但墨其色。冠与巾亦必用墨为之。而只去腰首绖。如何。
墨衰。既曰衰矣。似当如示。然未有考据。不敢索言之耳。
按家礼。凡祭。进馔在初献之前。侑食在终献之后。墓祭独无此两节。丘氏仪节。敷衍其礼。一依家祭之仪。未知何据。或又因此。谓墓祭不设饭羹。故无侑食之文。既有三献盛礼。而不具酒食。宁有是理。愚意原野之礼。所当有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5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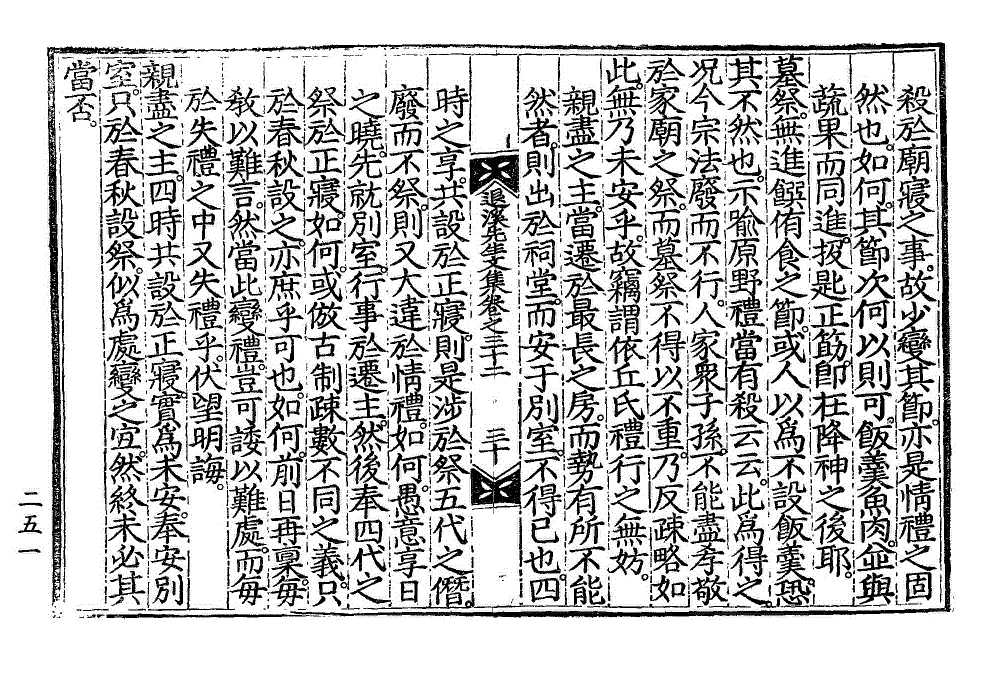 杀于庙寝之事。故少变其节。亦是情礼之固然也。如何。其节次何以则可。饭羹鱼肉。并与蔬果而同进。扱匙正箸。即在降神之后耶。
杀于庙寝之事。故少变其节。亦是情礼之固然也。如何。其节次何以则可。饭羹鱼肉。并与蔬果而同进。扱匙正箸。即在降神之后耶。墓祭。无进馔侑食之节。或人以为不设饭羹。恐其不然也。示喻原Î礼当有杀云云。此为得之。况今宗法废而不行。人家众子孙。不能尽孝敬于家庙之祭。而墓祭不得以不重。乃反疏略如此。无乃未安乎。故窃谓依丘氏礼行之无妨。
亲尽之主。当迁于最长之房。而势有所不能然者。则出于祠堂。而安于别室。不得已也。四时之享。共设于正寝。则是涉于祭五代之僭。废而不祭。则又大违于情礼。如何。愚意享日之晓。先就别室。行事于迁主。然后奉四代之祭于正寝。如何。或仿古制疏数不同之义。只于春秋设之。亦庶乎可也。如何。前日再禀。每教以难言。然当此变礼。岂可诿以难处。而每于失礼之中又失礼乎。伏望明诲。
亲尽之主。四时共设于正寝。实为未安。奉安别室。只于春秋设祭。似为处变之宜。然终未必其当否。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5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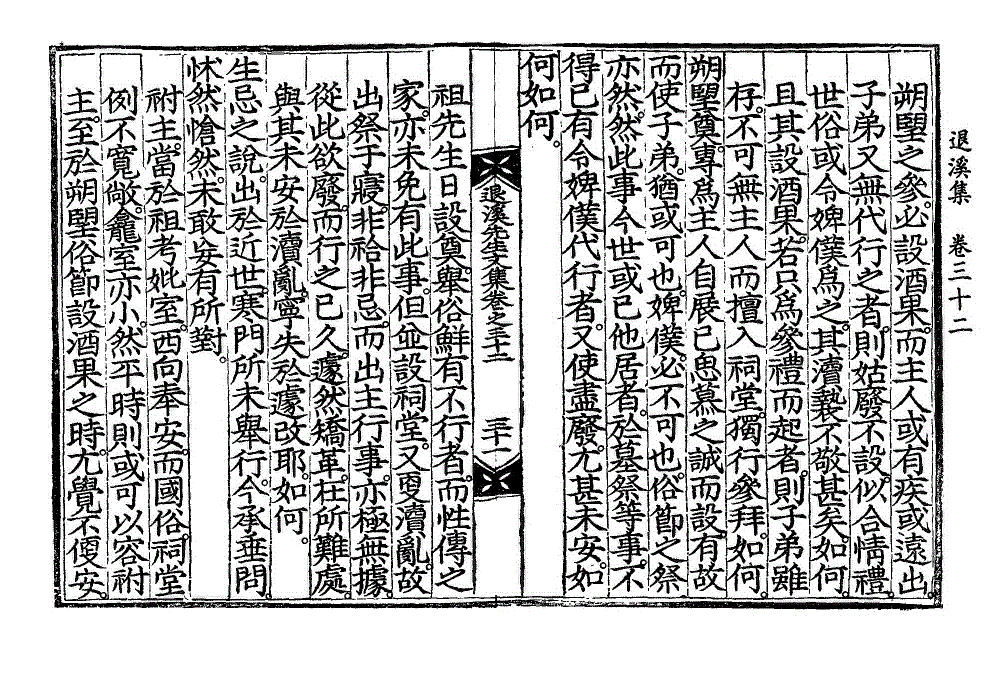 朔望之参。必设酒果。而主人或有疾或远出。子弟又无代行之者。则姑废不设。似合情礼。世俗或令婢仆为之。其渎亵不敬甚矣。如何。且其设酒果。若只为参礼而起者。则子弟虽存。不可无主人而擅入祠堂。独行参拜。如何。
朔望之参。必设酒果。而主人或有疾或远出。子弟又无代行之者。则姑废不设。似合情礼。世俗或令婢仆为之。其渎亵不敬甚矣。如何。且其设酒果。若只为参礼而起者。则子弟虽存。不可无主人而擅入祠堂。独行参拜。如何。朔望奠。专为主人自展已思慕之诚而设。有故而使子弟。犹或可也。婢仆。必不可也。俗节之祭亦然。然此事今世或已他居者。于墓祭等事。不得已有令婢仆代行者。又使尽废。尤甚未安。如何如何。
祖先生日设奠。举俗鲜有不行者。而性传之家。亦未免有此事。但并设祠堂。又更渎乱。故出祭于寝。非祫非忌。而出主行事。亦极无据。从此欲废。而行之已久。遽然矫革。在所难处。与其未安于渎乱。宁失于遽改耶。如何。
生忌之说。出于近世。寒门所未举行。今承垂问。怵然怆然。未敢妄有所对。
祔主。当于祖考妣室。西向奉安。而国俗。祠堂例不宽敞。龛室亦小。然平时则或可以容祔主。至于朔望俗节设酒果之时。尤觉不便安。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5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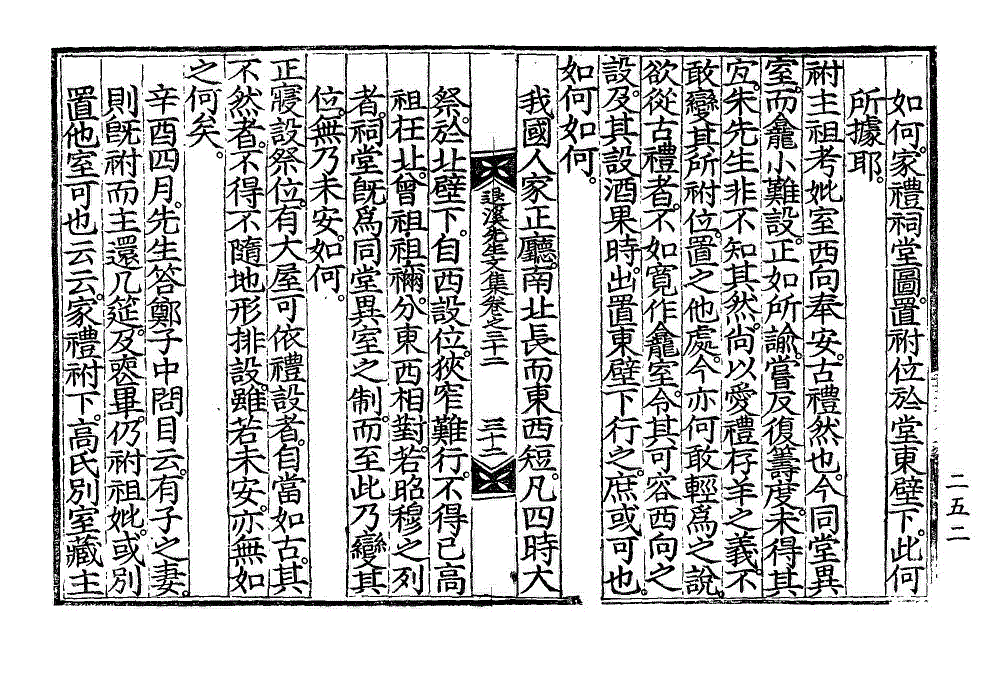 如何。家礼祠堂图。置祔位于堂东壁下。此何所据耶。
如何。家礼祠堂图。置祔位于堂东壁下。此何所据耶。祔主祖考妣室西向奉安。古礼然也。今同堂异室。而龛小难设。正如所谕。尝反复筹度。未得其宜。朱先生非不知其然。尚以爱礼存羊之义。不敢变其所祔位。置之他处。今亦何敢轻为之说。欲从古礼者。不如宽作龛室。令其可容西向之设。及其设酒果时。出置东壁下行之。庶或可也。如何如何。
我国人家正厅。南北长而东西短。凡四时大祭。于北壁下。自西设位。狭窄难行。不得已高祖在北。曾祖,祖,祢。分东西相对。若昭穆之列者。祠堂既为同堂异室之制。而至此乃变其位。无乃未安。如何。
正寝设祭位。有大屋可依礼设者。自当如古。其不然者。不得不随地形排设。虽若未安。亦无如之何矣。
辛酉四月。先生答郑子中问目云。有子之妻。则既祔而主还几筵。及丧毕。仍祔祖妣。或别置他室可也云云。家礼祔下。高氏别室藏主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5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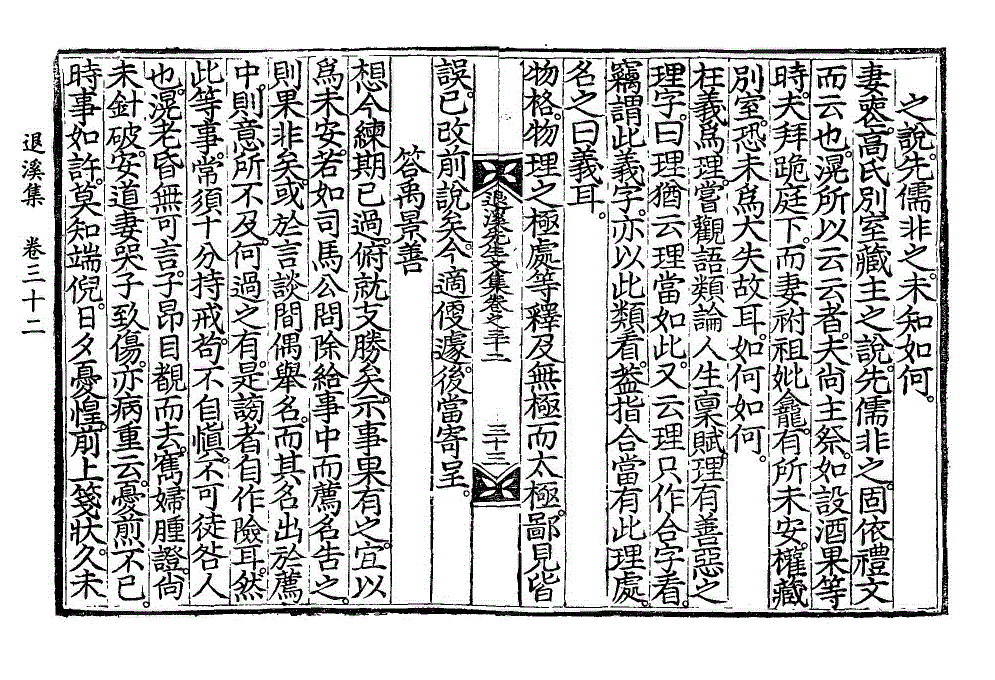 之说。先儒非之。未知如何。
之说。先儒非之。未知如何。妻丧。高氏别室藏主之说。先儒非之。固依礼文而云也。滉所以云云者。夫尚主祭。如设酒果等时。夫拜跪庭下。而妻祔祖妣龛。有所未安。权藏别室。恐未为大失故耳。如何如何。
在义为理。尝观语类论人生禀赋。理有善恶之理字。曰理犹云理当如此。又云理只作合字看。窃谓此义字。亦以此类看。盖指合当有此理处。名之曰义耳。
物格。物理之极处等释及无极而太极。鄙见皆误。已改前说矣。今适便遽。后当寄呈。
答禹景善
想今练期已过。俯就支胜矣。示事果有之。宜以为未安。若如司马公问除给事中而荐名告之。则果非矣。或于言谈间偶举名。而其名出于荐中。则意所不及。何过之有。是谤者自作险耳。然此等事。常须十分持戒。苟不自慎。不可徒咎人也。滉老昏无可言。子昂目睹而去。寯妇肿證。尚未针破。安道妻哭子致伤。亦病重云。忧煎不已。时事如许。莫知端倪。日夕忧惶。前上笺状。久未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5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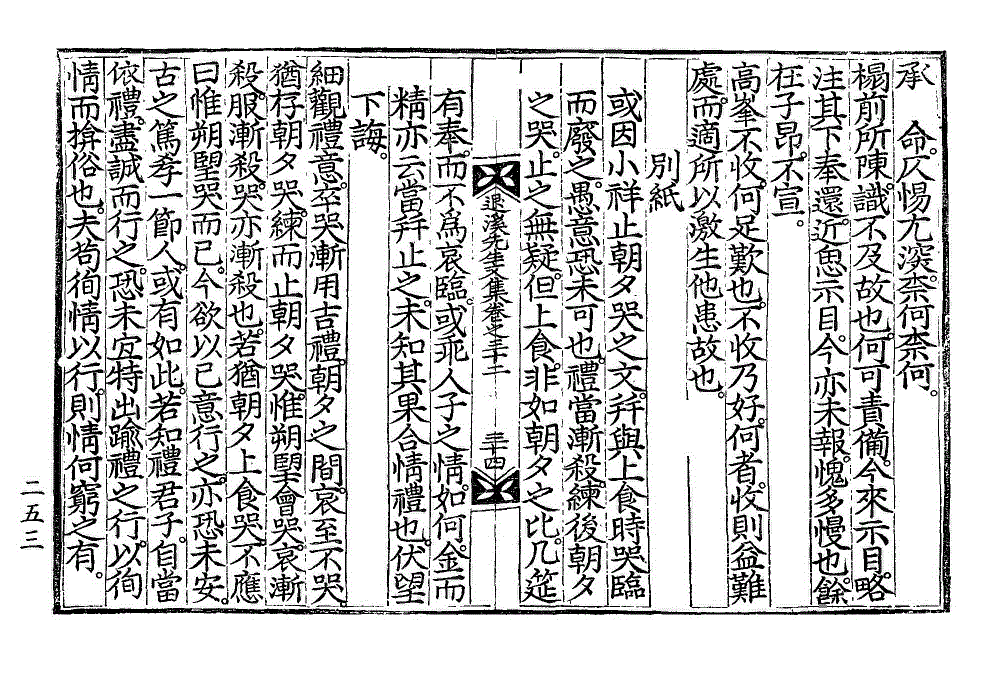 承 命。仄惕尤深。柰何柰何。
承 命。仄惕尤深。柰何柰何。榻前所陈。识不及故也。何可责备。今来示目。略注其下奉还。近思示目。今亦未报。愧多慢也。馀在子昂。不宣。
高峰不收。何足叹也。不收乃好。何者。收则益难处。而适所以激生他患故也。
别纸
或因小祥止朝夕哭之文。并与上食时哭临而废之。愚意恐未可也。礼当渐杀。练后朝夕之哭。止之无疑。但上食。非如朝夕之比。几筵有奉。而不为哀临。或乖人子之情。如何。金而精亦云当并止之。未知其果合情礼也。伏望下诲。
细观礼意。卒哭渐用吉礼。朝夕之间。哀至不哭。犹存朝夕哭。练而止朝夕哭。惟朔望会哭。哀渐杀。服渐杀。哭亦渐杀也。若犹朝夕上食哭。不应曰惟朔望哭而已。今欲以己意行之。亦恐未安。古之笃孝一节人。或有如此。若知礼君子。自当依礼。尽诚而行之。恐未宜特出踰礼之行。以徇情而掩俗也。夫苟徇情以行。则情何穷之有。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54H 页
 练后虽废朝夕之哭。而只于晨昏。展拜几筵。似合情礼。或云礼无明文。难以义起。或谓家礼有晨谒祠堂之文。依此只得晨谒为当。夕则不可。愚以为未然。几筵三年。不废生事之礼。恐与祠堂有异。晨昏之礼废之。实所不忍。且尝见朱门人问于先生曰。赵子直晨昏必谒影堂。而先生只行晨谒。如何。先生答云。昏则或在宴集之后。此似未安。故只用晨谒云云。以此观之。先生不以晨昏之谒为未当。而只以宴集等有碍不可行。故只存晨谒之礼也。忧人既无此等事。而况几筵与祠堂不同。晨昏之谒。未有所妨也。如何。金而精亦以鄙说为是。
练后虽废朝夕之哭。而只于晨昏。展拜几筵。似合情礼。或云礼无明文。难以义起。或谓家礼有晨谒祠堂之文。依此只得晨谒为当。夕则不可。愚以为未然。几筵三年。不废生事之礼。恐与祠堂有异。晨昏之礼废之。实所不忍。且尝见朱门人问于先生曰。赵子直晨昏必谒影堂。而先生只行晨谒。如何。先生答云。昏则或在宴集之后。此似未安。故只用晨谒云云。以此观之。先生不以晨昏之谒为未当。而只以宴集等有碍不可行。故只存晨谒之礼也。忧人既无此等事。而况几筵与祠堂不同。晨昏之谒。未有所妨也。如何。金而精亦以鄙说为是。来说欲行朝夕。至当至当。
金而精制深衣。用绵布。性传疑其当用白麻布。金云。凡礼言麻布者是麻布。只言布者。皆是绵布也。故大小敛之绞。皆用绵布为是。此说如何。五服之布。亦不言麻布。而只云生熟。此其为麻布。则深衣白细布之独为绵布。何义耶。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5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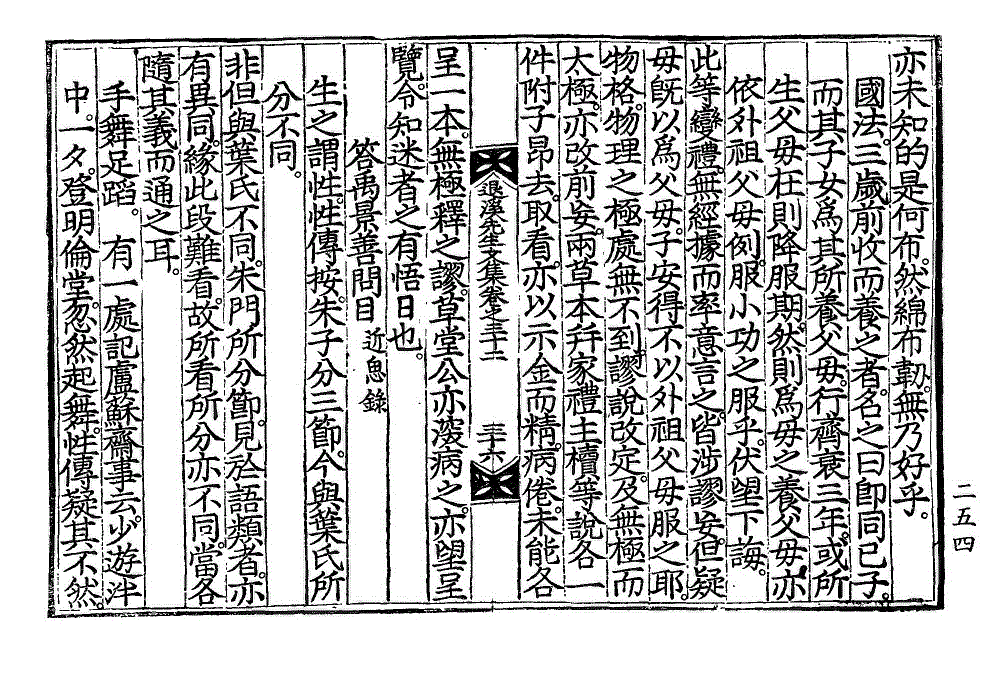 亦未知的是何布。然绵布韧。无乃好乎。
亦未知的是何布。然绵布韧。无乃好乎。国法。三岁前收而养之者。名之曰即同己子。而其子女为其所养父母。行齐衰三年。或所生父母在则降服期。然则为母之养父母。亦依外祖父母例。服小功之服乎。伏望下诲。
此等变礼。无经据而率意言之。皆涉谬妄。但疑母既以为父母。子安得不以外祖父母服之耶。物格。物理之极处无不到。谬说改定。及无极而太极。亦改前妄。两草本并家礼主椟等说各一件附子昂去。取看。亦以示金而精。病倦。未能各呈一本。无极释之谬。草堂公亦深病之。亦望呈览。令知迷者之有悟日也。
答禹景善问目(近思录)
生之谓性。性传按。朱子分三节。今与叶氏所分不同。
非但与叶氏不同。朱门所分节。见于语类者。亦有异同。缘此段难看。故所看所分亦不同。当各随其义而通之耳。
手舞足蹈。 有一处记卢苏斋事云。少游泮中。一夕。登明伦堂。忽然起舞。性传疑其不然。
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255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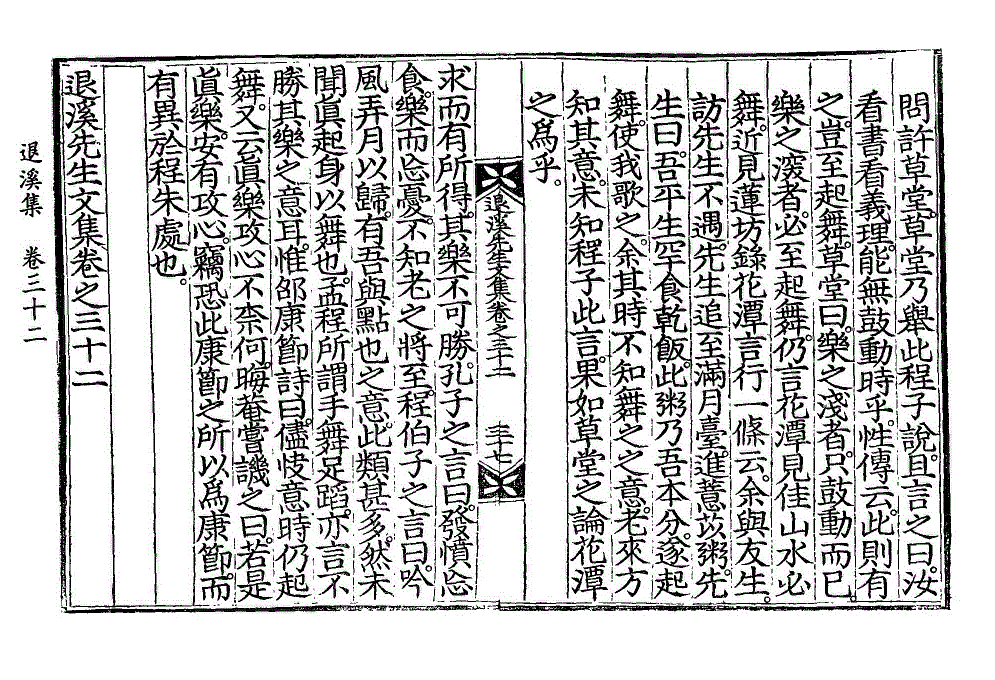 问许草堂。草堂乃举此程子说。且言之曰。汝看书看义理。能无鼓动时乎。性传云。此则有之。岂至起舞。草堂曰。乐之浅者。只鼓动而已。乐之深者。必至起舞。仍言花潭见佳山水必舞。近见莲坊录花潭言行一条云。余与友生。访先生不遇。先生追至满月台。进薏苡粥。先生曰。吾平生罕食乾饭。此粥乃吾本分。遂起舞。使我歌之。余其时不知舞之之意。老来方知其意。未知程子此言。果如草堂之论花潭之为乎。
问许草堂。草堂乃举此程子说。且言之曰。汝看书看义理。能无鼓动时乎。性传云。此则有之。岂至起舞。草堂曰。乐之浅者。只鼓动而已。乐之深者。必至起舞。仍言花潭见佳山水必舞。近见莲坊录花潭言行一条云。余与友生。访先生不遇。先生追至满月台。进薏苡粥。先生曰。吾平生罕食乾饭。此粥乃吾本分。遂起舞。使我歌之。余其时不知舞之之意。老来方知其意。未知程子此言。果如草堂之论花潭之为乎。求而有所得。其乐不可胜。孔子之言曰。发愤忘食。乐而忘忧。不知老之将至。程伯子之言曰。吟风弄月以归。有吾与点也之意。此类甚多。然未闻真起身以舞也。孟程所谓手舞足蹈。亦言不胜其乐之意耳。惟邵康节诗曰。尽快意时仍起舞。又云真乐攻心不柰何。晦庵尝讥之曰。若是真乐。安有攻心。窃恐此康节之所以为康节。而有异于程朱处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