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明: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.org,kanripo.org, db.itkc.or.kr 和 zh.wikisource.org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x 页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
杂著
杂著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08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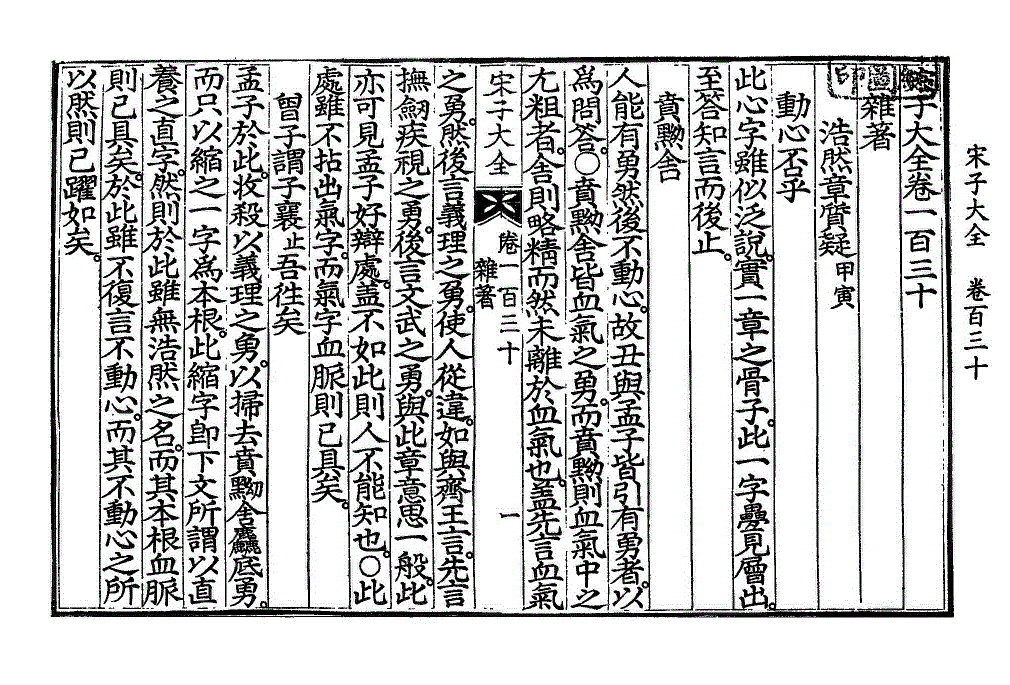 浩然章质疑(甲寅)
浩然章质疑(甲寅)动心否乎
此心字虽似泛说。实一章之骨子。此一字叠见层出。至答知言而后止。
贲黝舍
人能有勇然后不动心。故丑与孟子皆引有勇者。以为问答。○贲黝舍皆血气之勇。而贲黝则血气中之尤粗者。舍则略精而然未离于血气也。盖先言血气之勇。然后言义理之勇。使人从违。如与齐王言。先言抚剑疾视之勇。后言文武之勇。与此章意思一般。此亦可见孟子好辩处。盖不如此则人不能知也。○此处虽不拈出气字。而气字血脉则已具矣。
曾子谓子襄(止)吾往矣
孟子于此。收杀以义理之勇。以扫去贲黝舍粗底勇。而只以缩之一字为本根。此缩字即下文所谓以直养之直字。然则于此虽无浩然之名。而其本根血脉则已具矣。于此虽不复言不动心。而其不动心之所以然则已跃如矣。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08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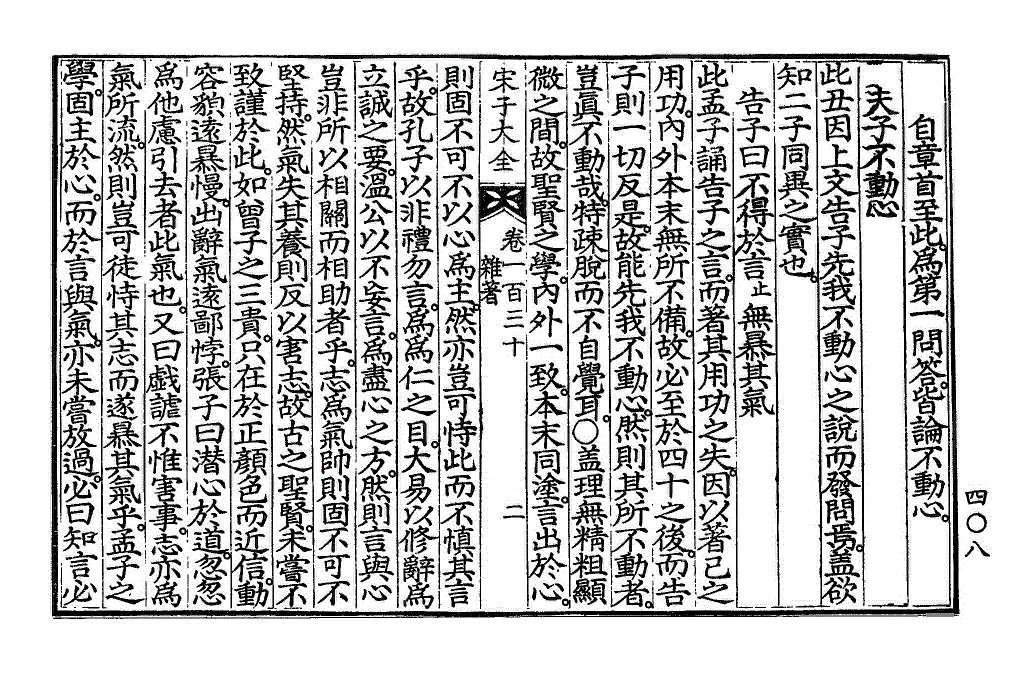 自章首至此。为第一问答。皆论不动心。
自章首至此。为第一问答。皆论不动心。夫子不动心
此丑因上文告子先我不动心之说而发问焉。盖欲知二子同异之实也。
告子曰不得于言(止)无暴其气
此孟子诵告子之言。而著其用功之失。因以著己之用功。内外本末无所不备。故必至于四十之后。而告子则一切反是。故能先我不动心。然则其所不动者。岂真不动哉。特疏脱而不自觉耳。○盖理无精粗显微之间。故圣贤之学。内外一致。本末同涂。言出于心。则固不可不以心为主。然亦岂可恃此而不慎其言乎。故孔子以非礼勿言。为为仁之目。大易以修辞为立诚之要。温公以不妄言。为尽心之方。然则言与心岂非所以相关而相助者乎。志为气帅则固不可不坚持。然气失其养则反以害志。故古之圣贤。未尝不致谨于此。如曾子之三贵。只在于正颜色而近信。动容貌远暴慢。出辞气远鄙悖。张子曰潜心于道。忽忽为他虑引去者此气也。又曰戏谑不惟害事。志亦为气所流。然则岂可徒恃其志而遂暴其气乎。孟子之学。固主于心。而于言与气。亦未尝放过。必曰知言必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09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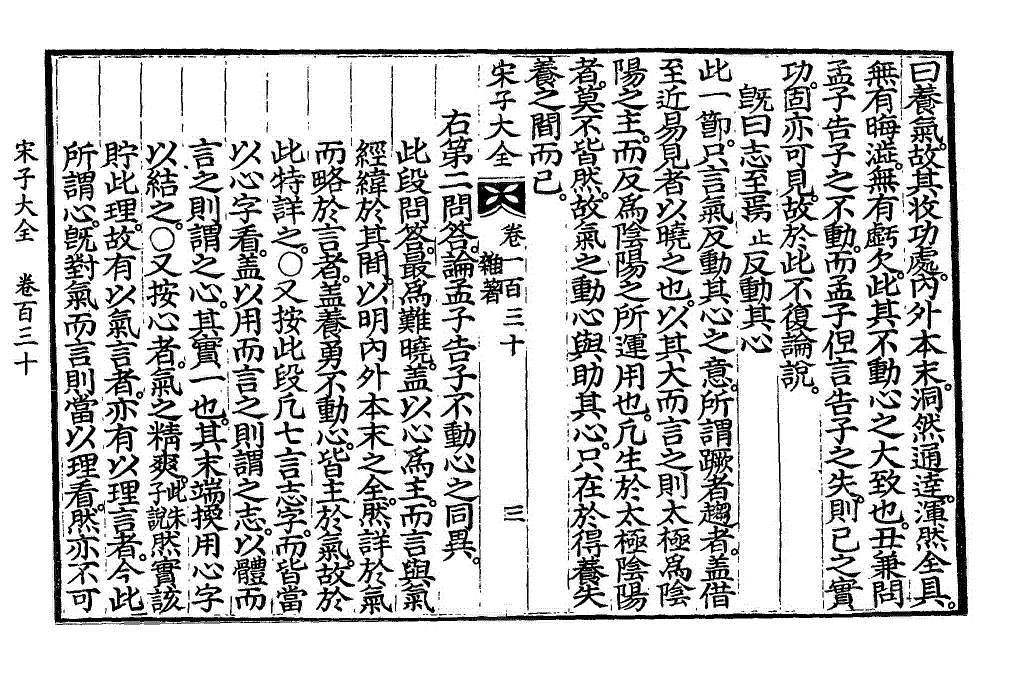 曰养气。故其收功处。内外本末。洞然通达。浑然全具。无有晦涩。无有亏欠。此其不动心之大致也。丑兼问孟子,告子之不动。而孟子但言告子之失。则己之实功。固亦可见。故于此不复论说。
曰养气。故其收功处。内外本末。洞然通达。浑然全具。无有晦涩。无有亏欠。此其不动心之大致也。丑兼问孟子,告子之不动。而孟子但言告子之失。则己之实功。固亦可见。故于此不复论说。既曰志至焉(止)反动其心
此一节。只言气反动其心之意。所谓蹶者趋者。盖借至近易见者以晓之也。以其大而言之则太极为阴阳之主。而反为阴阳之所运用也。凡生于太极阴阳者。莫不皆然。故气之动心与助其心。只在于得养失养之间而已。
右第二问答。论孟子,告子不动心之同异。
此段问答。最为难晓。盖以心为主。而言与气经纬于其间。以明内外本末之全。然详于气而略于言者。盖养勇不动心。皆主于气。故于此特详之。○又按此段凡七言志字。而皆当以心字看。盖以用而言之则谓之志。以体而言之则谓之心。其实一也。其末端换用心字以结之。○又按心者。气之精爽。(此朱子说)然实该贮此理。故有以气言者。亦有以理言者。今此所谓心。既对气而言则当以理看。然亦不可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0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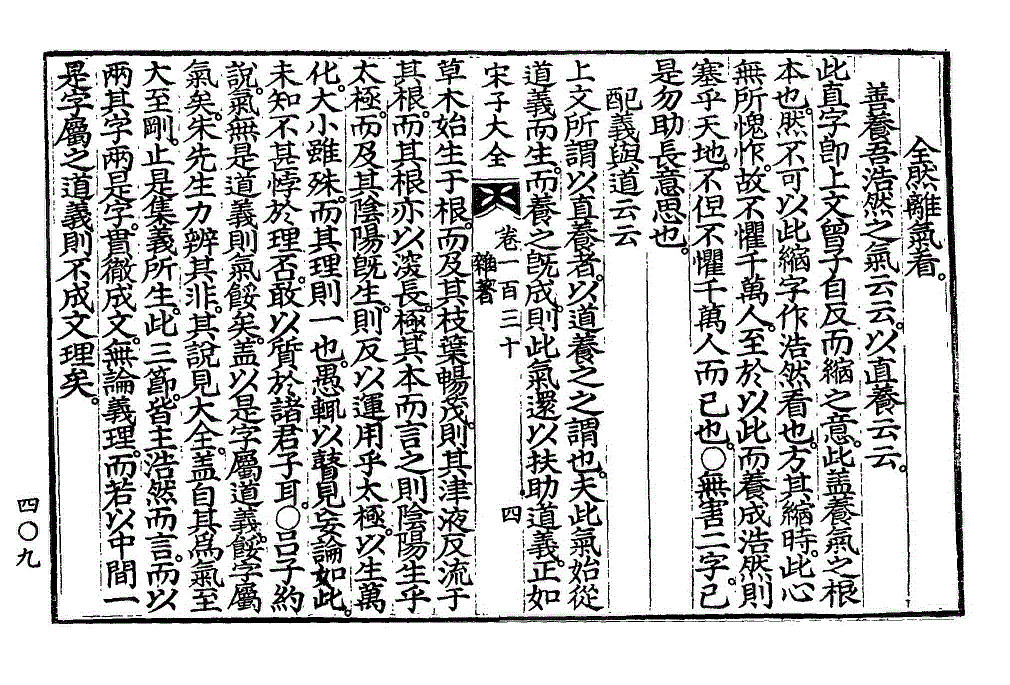 全然离气看。
全然离气看。善养吾浩然之气云云。以直养云云。
此直字即上文曾子自反而缩之意。此盖养气之根本也。然不可以此缩字作浩然看也。方其缩时。此心无所愧怍。故不惧千万人。至于以此而养成浩然则塞乎天地。不但不惧千万人而已也。○无害二字。已是勿助长意思也。
配义与道云云
上文所谓以直养者。以道养之之谓也。夫此气始从道义而生。而养之既成。则此气还以扶助道义。正如草木始生于根。而及其枝叶畅茂。则其津液反流于其根。而其根亦以深长。极其本而言之则阴阳生乎太极。而及其阴阳既生。则反以运用乎太极。以生万化。大小虽殊。而其理则一也。愚辄以瞽见妄论如此。未知不甚悖于理否。敢以质于诸君子耳。○吕子约说。气无是道义则气馁矣。盖以是字属道义。馁字属气矣。朱先生力辨其非。其说见大全。盖自其为气至大至刚。止是集义所生。此三节。皆主浩然而言。而以两其字两是字。贯彻成文。无论义理。而若以中间一是字属之道义则不成文理矣。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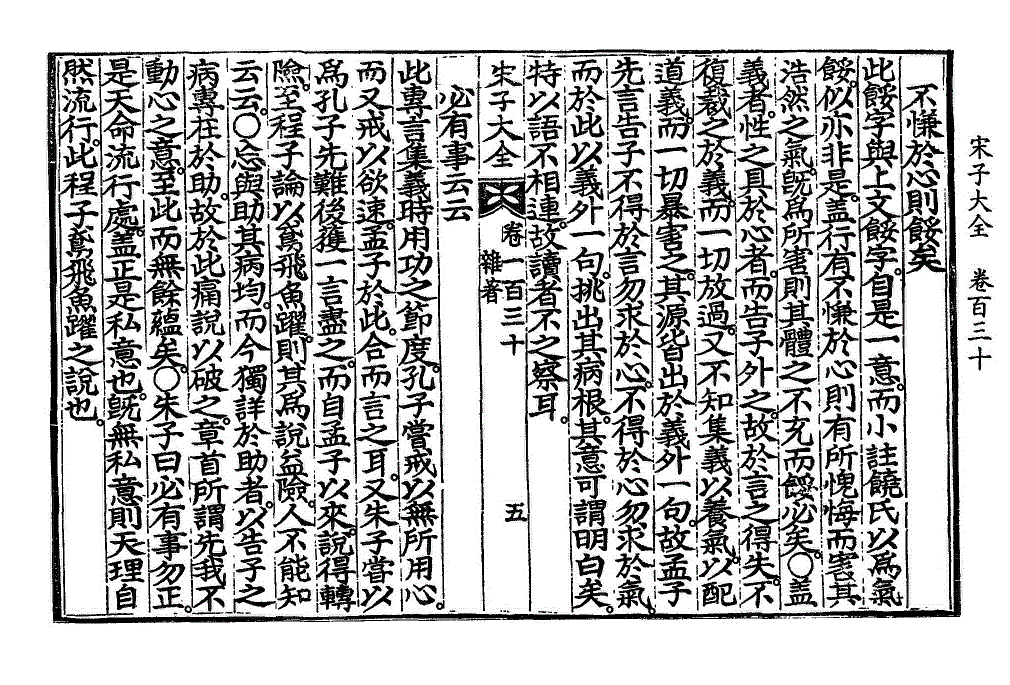 不慊于心则馁矣
不慊于心则馁矣此馁字与上文馁字。自是一意。而小注饶氏以为气馁。似亦非是。盖行有不慊于心则有所愧悔而害其浩然之气。既为所害则其体之不充而馁必矣。○盖义者。性之具于心者。而告子外之。故于言之得失。不复裁之于义。而一切放过。又不知集义以养气。以配道义。而一切暴害之。其源皆出于义外一句。故孟子先言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。不得于心勿求于气。而于此以义外一句。挑出其病根。其意可谓明白矣。特以语不相连。故读者不之察耳。
必有事云云
此专言集义时用功之节度。孔子尝戒以无所用心。而又戒以欲速。孟子于此。合而言之耳。又朱子尝以为孔子先难后获一言尽之。而自孟子以来。说得转险。至程子论以鸢飞鱼跃。则其为说益险。人不能知云云。○忘与助其病均。而今独详于助者。以告子之病专在于助。故于此痛说以破之。章首所谓先我不动心之意。至此而无馀蕴矣。○朱子曰必有事勿正。是天命流行处。盖正是私意也。既无私意则天理自然流行。此程子鸢飞鱼跃之说也。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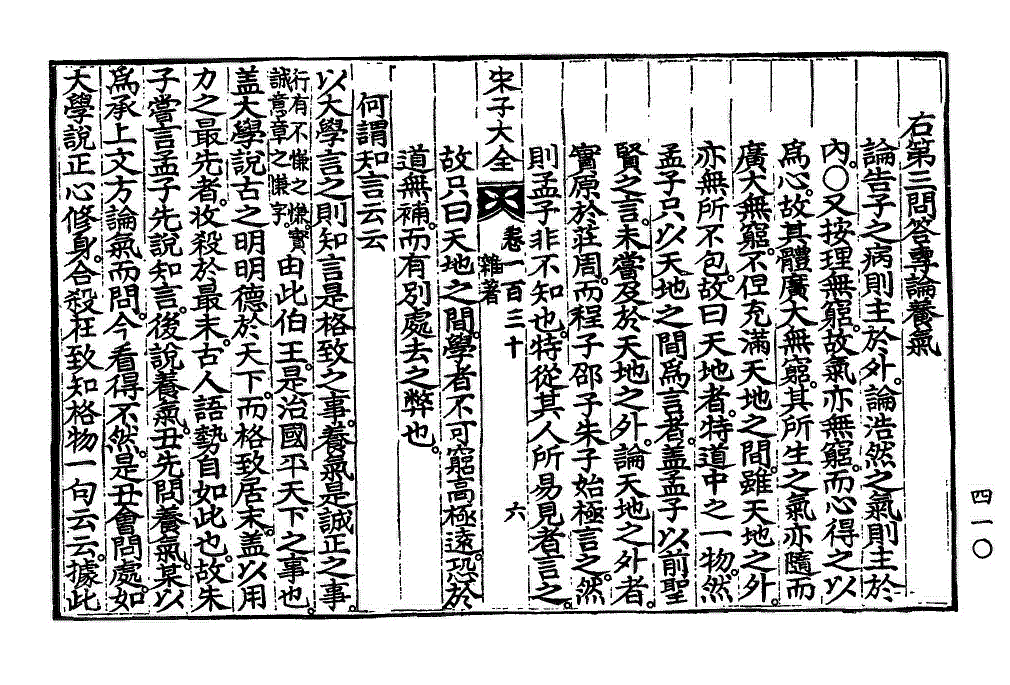 右第三问答专论养气
右第三问答专论养气论告子之病则主于外。论浩然之气则主于内。○又按理无穷。故气亦无穷。而心得之以为心。故其体广大无穷。其所生之气亦随而广大无穷。不但充满天地之间。虽天地之外。亦无所不包。故曰天地者。特道中之一物。然孟子只以天地之间为言者。盖孟子以前圣贤之言。未尝及于天地之外。论天地之外者。实原于庄周。而程子,邵子,朱子始极言之。然则孟子非不知也。特从其人所易见者言之。故只曰天地之间。学者不可穷高极远。恐于道无补。而有别处去之弊也。
何谓知言云云
以大学言之则知言是格致之事。养气是诚正之事。(行有不慊之慊。实诚意章之慊字。)由此伯王。是治国平天下之事也。盖大学说古之明明德于天下。而格致居末。盖以用力之最先者。收杀于最末。古人语势自如此也。故朱子尝言孟子先说知言。后说养气。丑先问养气。某以为承上文方论气而问。今看得不然。是丑会问处。如大学说正心修身。合杀在致知格物一句云云。据此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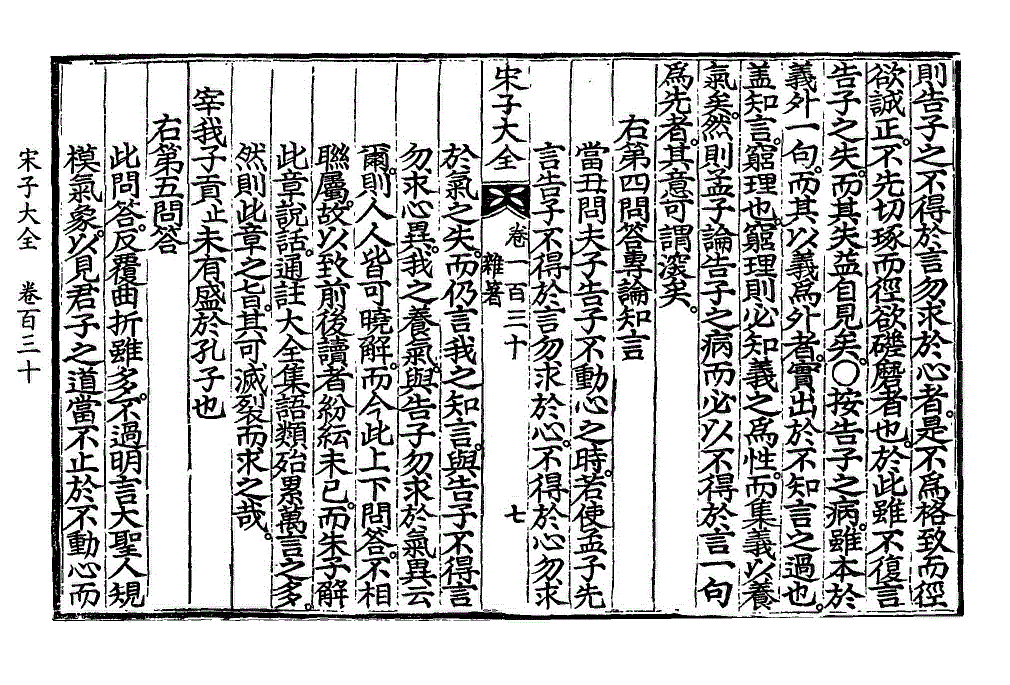 则告子之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。是不为格致而径欲诚正。不先切琢而径欲磋磨者也。于此虽不复言告子之失。而其失益自见矣。○按告子之病。虽本于义外一句。而其以义为外者。实出于不知言之过也。盖知言。穷理也。穷理则必知义之为性。而集义以养气矣。然则孟子论告子之病而必以不得于言一句为先者。其意可谓深矣。
则告子之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。是不为格致而径欲诚正。不先切琢而径欲磋磨者也。于此虽不复言告子之失。而其失益自见矣。○按告子之病。虽本于义外一句。而其以义为外者。实出于不知言之过也。盖知言。穷理也。穷理则必知义之为性。而集义以养气矣。然则孟子论告子之病而必以不得于言一句为先者。其意可谓深矣。右第四问答专论知言
当丑问夫子告子不动心之时。若使孟子先言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。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失。而仍言我之知言。与告子不得言勿求心异。我之养气。与告子勿求于气异云尔。则人人皆可晓解。而今此上下问答。不相联属。故以致前后读者纷纭未已。而朱子解此章说话。通注大全集语类殆累万言之多。然则此章之旨。其可灭裂而求之哉。
宰我子贡(止)未有盛于孔子也
右第五问答
此问答。反覆曲折虽多。不过明言大圣人规模气象。以见君子之道当不止于不动心而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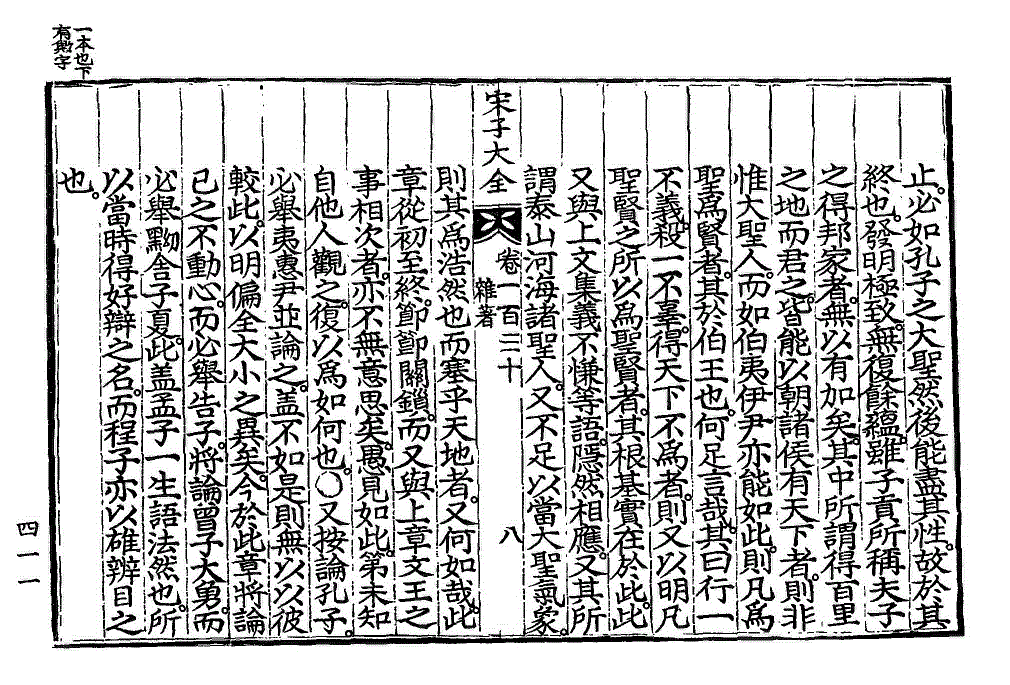 止。必如孔子之大圣然后能尽其性。故于其终也。发明极致。无复馀蕴。虽子贡所称夫子之得邦家者。无以有加矣。其中所谓得百里之地而君之。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者。则非惟大圣人。而如伯夷,伊尹亦能如此。则凡为圣为贤者。其于伯王也。何足言哉。其曰行一不义。杀一不辜。得天下不为者。则又以明凡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。其根基实在于此。此又与上文集义不慊等语。隐然相应。又其所谓泰山河海诸圣人。又不足以当大圣气象。则其为浩然也而塞乎天地者。又何如哉。此章从初至终。节节关锁。而又与上章文王之事相次者。亦不无意思矣。愚见如此。第未知自他人观之。复以为如何也。○又按论孔子。必举夷惠尹并论之。盖不如是则无以以彼较此。以明偏全大小之异矣。今于此章将论己之不动心。而必举告子。将论曾子大勇。而必举黝舍子夏。此盖孟子一生语法然也。所以当时得好辩之名。而程子亦以雄辨目之也(一本也下有欤字)。
止。必如孔子之大圣然后能尽其性。故于其终也。发明极致。无复馀蕴。虽子贡所称夫子之得邦家者。无以有加矣。其中所谓得百里之地而君之。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者。则非惟大圣人。而如伯夷,伊尹亦能如此。则凡为圣为贤者。其于伯王也。何足言哉。其曰行一不义。杀一不辜。得天下不为者。则又以明凡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。其根基实在于此。此又与上文集义不慊等语。隐然相应。又其所谓泰山河海诸圣人。又不足以当大圣气象。则其为浩然也而塞乎天地者。又何如哉。此章从初至终。节节关锁。而又与上章文王之事相次者。亦不无意思矣。愚见如此。第未知自他人观之。复以为如何也。○又按论孔子。必举夷惠尹并论之。盖不如是则无以以彼较此。以明偏全大小之异矣。今于此章将论己之不动心。而必举告子。将论曾子大勇。而必举黝舍子夏。此盖孟子一生语法然也。所以当时得好辩之名。而程子亦以雄辨目之也(一本也下有欤字)。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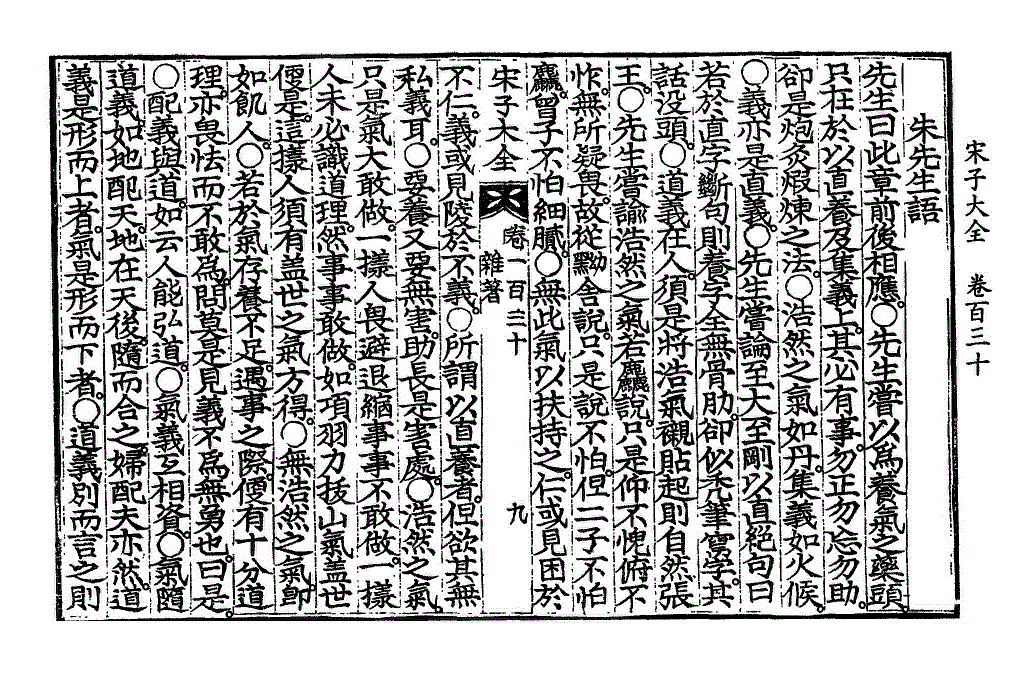 朱先生语
朱先生语先生曰此章前后相应。○先生尝以为养气之药头。只在于以直养及集义上。其必有事。勿正勿忘勿助。却是炮灸煅炼之法。○浩然之气如丹。集义如火候。○义亦是直义。○先生尝论至大至刚以直绝句曰若于直字断句则养字全无骨肋。却似秃笔写字。其话没头。○道义在人。须是将浩气衬贴起则自然张王。○先生尝谕浩然之气若粗说。只是仰不愧俯不怍。无所疑畏。故从黝舍说。只是说不怕。但二子不怕粗。曾子不怕细腻。○无此气以扶持之。仁或见困于不仁。义或见陵于不义。○所谓以直养者。但欲其无私义耳。○要养又要无害。助长是害处。○浩然之气。只是气大敢做。一样人畏避退缩事事不敢做。一样人未必识道理。然事事敢做。如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便是。这样人须有盖世之气方得。○无浩然之气。即如饥人。○若于气存养不足。遇事之际。便有十分道理。亦畏怯而不敢为。问莫是见义不为无勇也。曰是。○配义与道。如云人能弘道。○气义互相资。○气随道义。如地配天。地在天后。随而合之。妇配夫亦然。道义是形而上者。气是形而下者。○道义别而言之则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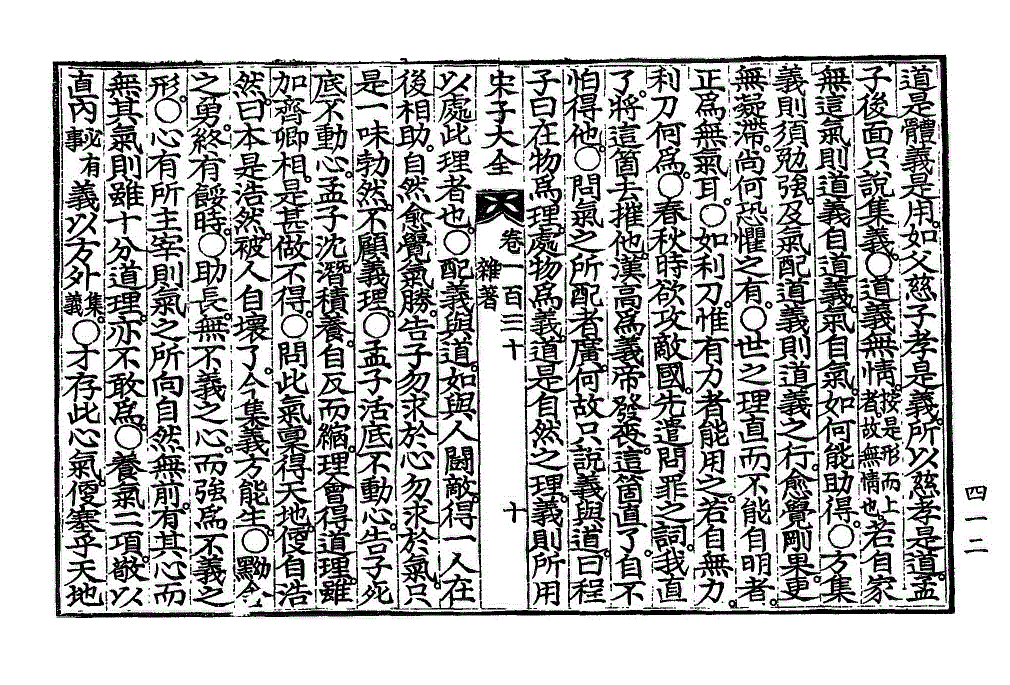 道是体义是用。如父慈子孝是义。所以慈孝是道。孟子后面只说集义。○道义无情。(按是形而上者。故无情也。)若自家无这气则道义自道义。气自气。如何能助得。○方集义则须勉强。及气配道义则道义之行。愈觉刚果。更无凝滞。尚何恐惧之有。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。正为无气耳。○如利刀。惟有力者能用之。若自无力。利刀何为。○春秋时欲攻敌国。先遣问罪之词。我直了。将这个去摧他。汉高为义帝发丧。这个直了。自不怕得他。○问气之所配者广。何故只说义与道。曰程子曰在物为理。处物为义。道是自然之理。义则所用以处此理者也。○配义与道。如与人斗敌。得一人在后相助。自然愈觉气胜。告子勿求于心勿求于气。只是一味勃然。不顾义理。○孟子活底不动心。告子死底不动心。孟子沈潜积养。自反而缩。理会得道理。虽加齐卿相。是甚做不得。○问此气禀得天地。便自浩然。曰本是浩然。被人自坏了。今集义方能生。○黝舍之勇。终有馁时。○助长。无不义之心。而强为不义之形。○心有所主宰则气之所向自然无前。有其心而无其气则虽十分道理。亦不敢为。○养气二项。敬以直内(必有事)义以方外(集义)。○才存此心气。便塞乎天地
道是体义是用。如父慈子孝是义。所以慈孝是道。孟子后面只说集义。○道义无情。(按是形而上者。故无情也。)若自家无这气则道义自道义。气自气。如何能助得。○方集义则须勉强。及气配道义则道义之行。愈觉刚果。更无凝滞。尚何恐惧之有。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。正为无气耳。○如利刀。惟有力者能用之。若自无力。利刀何为。○春秋时欲攻敌国。先遣问罪之词。我直了。将这个去摧他。汉高为义帝发丧。这个直了。自不怕得他。○问气之所配者广。何故只说义与道。曰程子曰在物为理。处物为义。道是自然之理。义则所用以处此理者也。○配义与道。如与人斗敌。得一人在后相助。自然愈觉气胜。告子勿求于心勿求于气。只是一味勃然。不顾义理。○孟子活底不动心。告子死底不动心。孟子沈潜积养。自反而缩。理会得道理。虽加齐卿相。是甚做不得。○问此气禀得天地。便自浩然。曰本是浩然。被人自坏了。今集义方能生。○黝舍之勇。终有馁时。○助长。无不义之心。而强为不义之形。○心有所主宰则气之所向自然无前。有其心而无其气则虽十分道理。亦不敢为。○养气二项。敬以直内(必有事)义以方外(集义)。○才存此心气。便塞乎天地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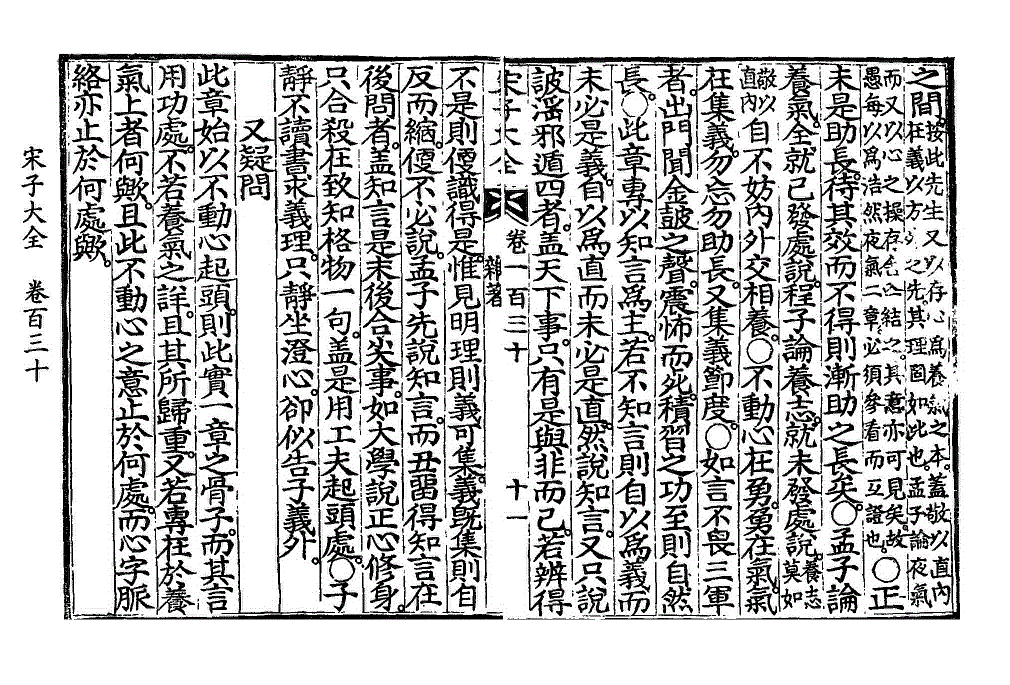 之间。(按此先生又以存心为养气之本。盖敬以直内在义以方外之先。其理固如此也。孟子论夜气而又以心之操存舍亡结之。其意亦可见矣。故愚每以为浩然夜气二章。必须参看而互證也。)○正未是助长。待其效而不得则渐助之长矣。○孟子论养气。全就已发处说。程子论养志。就未发处说。(养志莫如敬以直内)自不妨内外交相养。○不动心在勇。勇在气。气在集义。勿忘勿助长。又集义节度。○如言不畏三军者。出门闻金鼓之声。震怖而死。积习之功至则自然长。○此章专以知言为主。若不知言则自以为义而未必是义。自以为直而未必是直。然说知言。又只说诐淫邪遁四者。盖天下事。只有是与非而已。若辨得不是则便识得是。惟见明理则义可集。义既集则自反而缩。便不必说。孟子先说知言。而丑留得知言在后问者。盖知言是末后合尖事。如大学说正心修身。只合杀在致知格物一句。盖是用工夫起头处。○子静不读书求义理。只静坐澄心。却似告子义外。
之间。(按此先生又以存心为养气之本。盖敬以直内在义以方外之先。其理固如此也。孟子论夜气而又以心之操存舍亡结之。其意亦可见矣。故愚每以为浩然夜气二章。必须参看而互證也。)○正未是助长。待其效而不得则渐助之长矣。○孟子论养气。全就已发处说。程子论养志。就未发处说。(养志莫如敬以直内)自不妨内外交相养。○不动心在勇。勇在气。气在集义。勿忘勿助长。又集义节度。○如言不畏三军者。出门闻金鼓之声。震怖而死。积习之功至则自然长。○此章专以知言为主。若不知言则自以为义而未必是义。自以为直而未必是直。然说知言。又只说诐淫邪遁四者。盖天下事。只有是与非而已。若辨得不是则便识得是。惟见明理则义可集。义既集则自反而缩。便不必说。孟子先说知言。而丑留得知言在后问者。盖知言是末后合尖事。如大学说正心修身。只合杀在致知格物一句。盖是用工夫起头处。○子静不读书求义理。只静坐澄心。却似告子义外。又疑问
此章始以不动心起头。则此实一章之骨子。而其言用功处。不若养气之详。且其所归重。又若专在于养气上者何欤。且此不动心之意止于何处。而心字脉络亦止于何处欤。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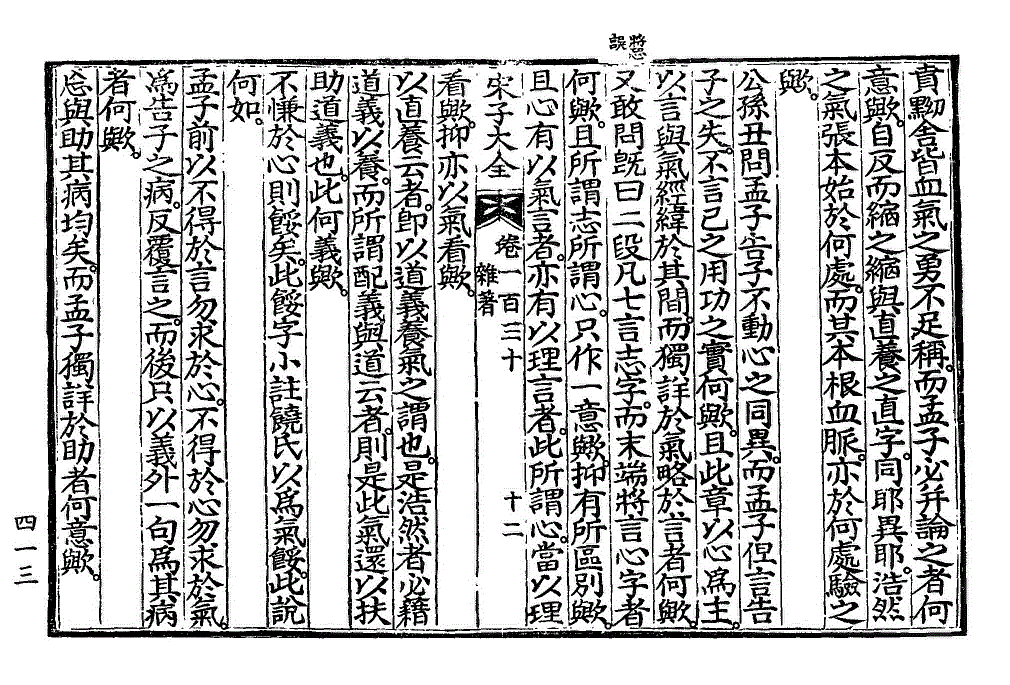 贲黝舍皆血气之勇不足称。而孟子必并论之者何意欤。自反而缩之缩与直养之直字。同耶异耶。浩然之气张本始于何处。而其本根血脉。亦于何处验之欤。
贲黝舍皆血气之勇不足称。而孟子必并论之者何意欤。自反而缩之缩与直养之直字。同耶异耶。浩然之气张本始于何处。而其本根血脉。亦于何处验之欤。公孙丑问孟子,告子不动心之同异。而孟子但言告子之失。不言己之用功之实何欤。且此章以心为主。以言与气经纬于其间。而独详于气略于言者何欤。又敢问既曰二段凡七言志字。而末端将(将恐误)言心字者何欤。且所谓志所谓心。只作一意欤。抑有所区别欤。且心有以气言者。亦有以理言者。此所谓心。当以理看欤。抑亦以气看欤。
以直养云者。即以道义养气之谓也。是浩然者必藉道义以养。而所谓配义与道云者。则是此气还以扶助道义也。此何义欤。
不慊于心则馁矣。此馁字小注饶氏以为气馁。此说何如。
孟子前以不得于言勿求于心。不得于心勿求于气。为告子之病。反覆言之。而后只以义外一句为其病者何欤。
忘与助其病均矣。而孟子独详于助者何意欤。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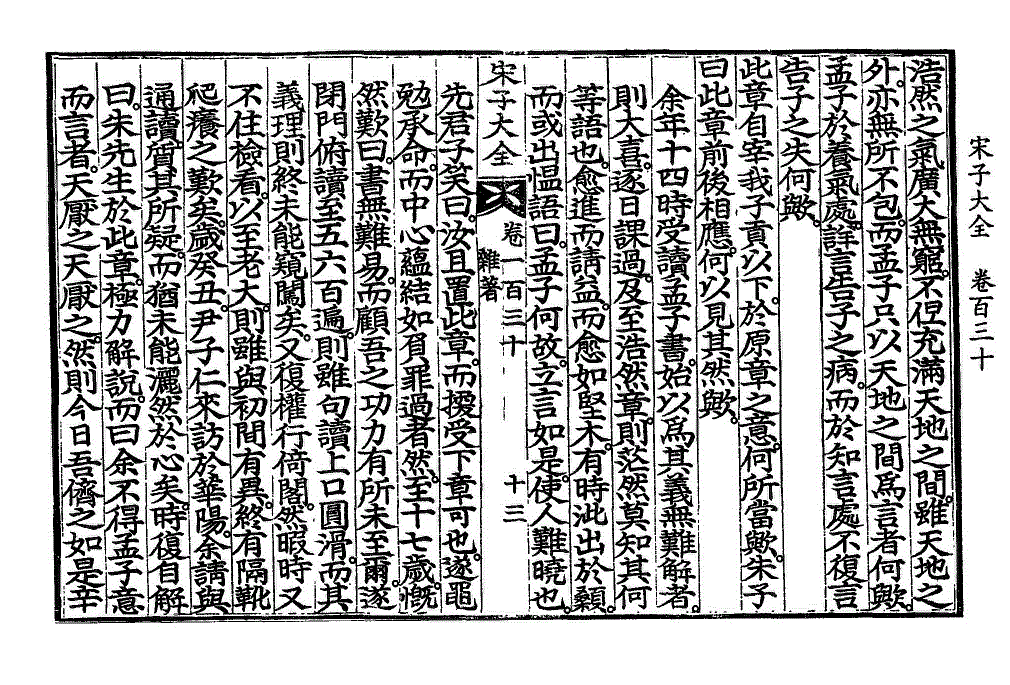 浩然之气广大无穷。不但充满天地之间。虽天地之外。亦无所不包。而孟子只以天地之间为言者何欤。孟子于养气处。详言告子之病。而于知言处不复言告子之失何欤。
浩然之气广大无穷。不但充满天地之间。虽天地之外。亦无所不包。而孟子只以天地之间为言者何欤。孟子于养气处。详言告子之病。而于知言处不复言告子之失何欤。此章自宰我子贡以下。于原章之意。何所当欤。失子曰此章前后相应。何以见其然欤。
余年十四时受读孟子书。始以为其义无难解者。则大喜。逐日课过。及至浩然章。则茫然莫知其何等语也。愈进而请益。而愈如坚木。有时泚出于颡。而或出愠语曰。孟子何故。立言如是。使人难晓也。先君子笑曰。汝且置此章。而换受下章可也。遂黾勉承命。而中心蕴结如负罪过者然。至十七岁。慨然叹曰。书无难易。而顾吾之功力有所未至尔。遂闭门俯读至五六百遍。则虽句读上口圆滑。而其义理则终未能窥闯矣。又复权行倚阁。然暇时又不住检看。以至老大。则虽与初间有异。终有隔靴爬痒之叹矣。岁癸丑。尹子仁来访于华阳。余请与通读。质其所疑。而犹未能洒然于心矣。时复自解曰。朱先生于此章。极力解说。而曰余不得孟子意而言者。天厌之天厌之。然则今日吾侪之如是辛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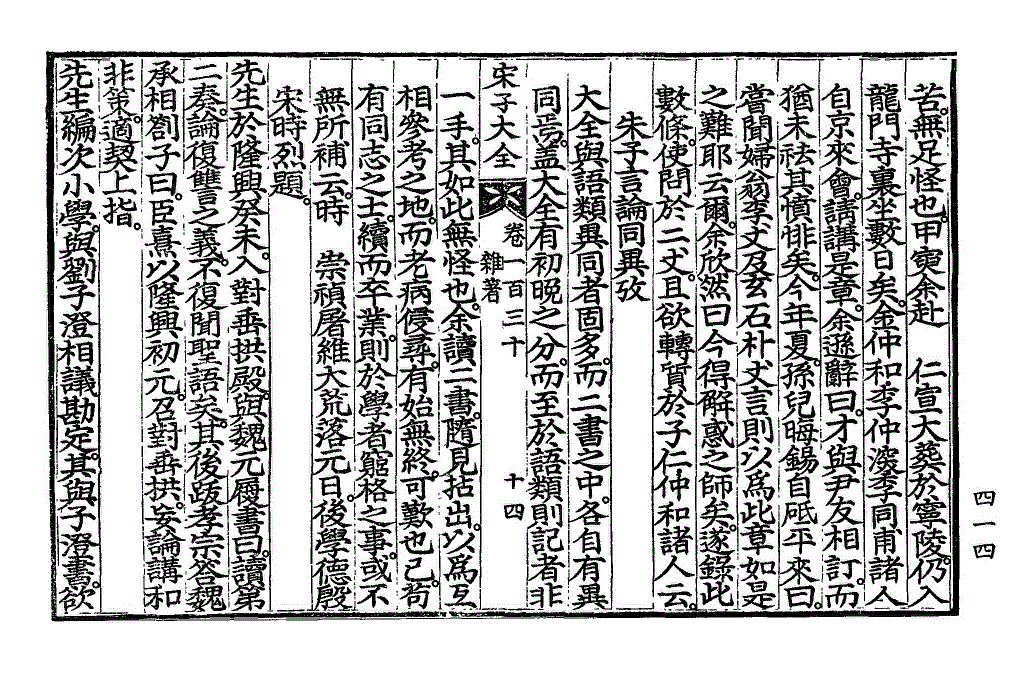 苦。无足怪也。甲寅余赴 仁宣大葬于宁陵。仍入龙门寺里坐数日矣。金仲和,李仲深,李同甫诸人自京来会。请讲是章。余逊辞曰。才与尹友相订。而犹未祛其愤悱矣。今年夏。孙儿晦锡自砥平来曰。尝闻妇翁李丈及玄石朴丈言则以为此章如是之难耶云尔。余欣然曰今得解惑之师矣。遂录此数条。使问于二丈。且欲转质于子仁,仲和诸人云。
苦。无足怪也。甲寅余赴 仁宣大葬于宁陵。仍入龙门寺里坐数日矣。金仲和,李仲深,李同甫诸人自京来会。请讲是章。余逊辞曰。才与尹友相订。而犹未祛其愤悱矣。今年夏。孙儿晦锡自砥平来曰。尝闻妇翁李丈及玄石朴丈言则以为此章如是之难耶云尔。余欣然曰今得解惑之师矣。遂录此数条。使问于二丈。且欲转质于子仁,仲和诸人云。朱子言论同异考
大全与语类异同者固多。而二书之中。各自有异同焉。盖大全有初晚之分。而至于语类则记者非一手。其如此无怪也。余读二书。随见拈出。以为互相参考之地。而老病侵寻。有始无终。可叹也已。苟有同志之士。续而卒业。则于学者穷格之事。或不无所补云。时 崇祯屠维大荒落元日。后学德殷宋时烈题。
先生于隆兴癸未。入对垂拱殿。与魏元履书曰。读第二奏。论复雠之义。不复闻圣语矣。其后跋孝宗答魏承相劄子曰。臣熹以隆兴初元。召对垂拱。妄论讲和非策。适契上指。
先生编次小学。与刘子澄相议勘定。其与子澄书。欲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5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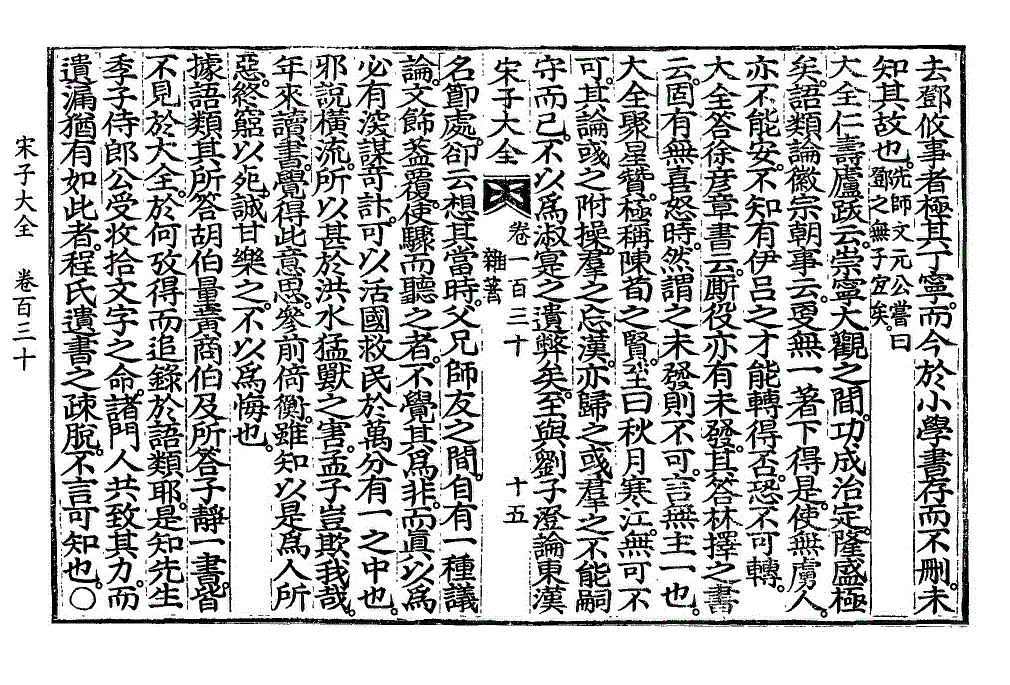 去邓攸事者极其丁宁。而今于小学书存而不删。未知其故也。(先师文元公尝曰邓之无子宜矣。)
去邓攸事者极其丁宁。而今于小学书存而不删。未知其故也。(先师文元公尝曰邓之无子宜矣。)大全仁寿庐跋云。崇宁大观之间。功成治定。隆盛极矣。语类论徽宗朝事云。更无一著下得是。使无虏人。亦不能安。不知有伊吕之才能转得否。恐不可转。
大全答徐彦章书云。厮役亦有未发。其答林择之书云。固有无喜怒时。然谓之未发则不可。言无主一也。大全聚星赞。极称陈荀之贤。至曰秋月寒江。无可不可。其论彧之附操。群之妄汉。亦归之彧,群之不能嗣守而已。不以为淑寔之遗弊矣。至与刘子澄论东汉名节处。却云想其当时。父兄师友之间。自有一种议论。文饰盖覆。使骤而听之者。不觉其为非。而真以为必有深谋奇计。可以活国救民于万分有一之中也。邪说横流。所以甚于洪水猛兽之害。孟子岂欺我哉。年来读书。觉得此意思。参前倚衡。虽知以是为人所恶。终穷以死。诚甘乐之。不以为悔也。
据语类其所答胡伯量,黄商伯及所答子静一书。皆不见于大全。于何考得而追录于语类耶。是知先生季子侍郎公受收拾文字之命。诸门人共致其力。而遗漏犹有如此者。程氏遗书之疏脱。不言可知也。○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5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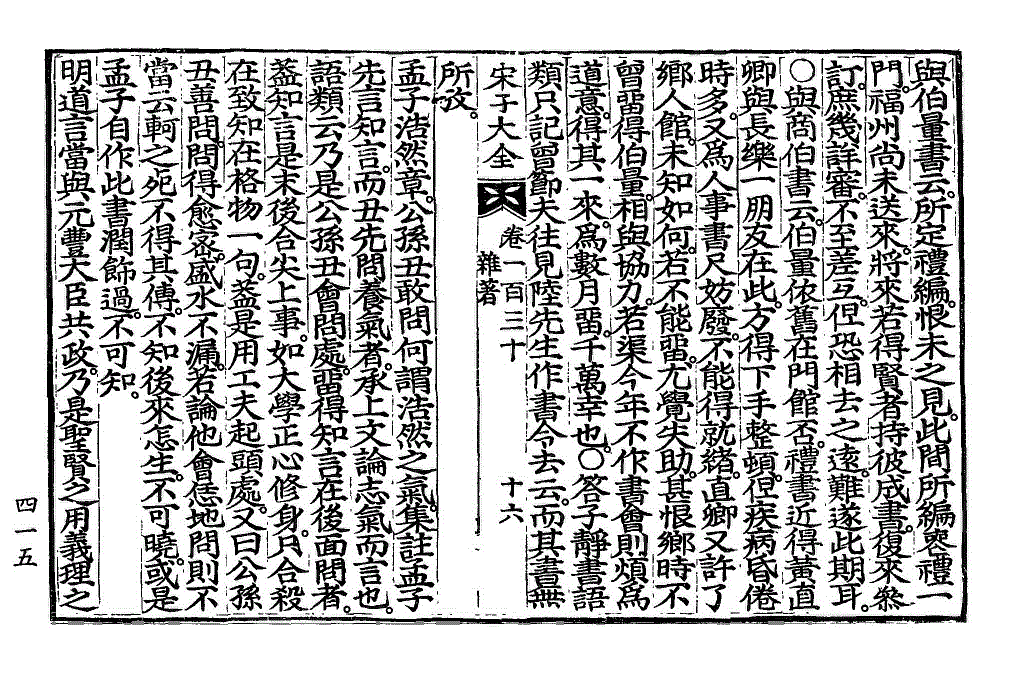 与伯量书云。所定礼编。恨未之见。此间所编丧礼一门。福州尚未送来。将来若得贤者持彼成书。复来参订。庶几详审。不至差互。但恐相去之远。难遂此期耳。○与商伯书云。伯量依旧在门馆否。礼书近得黄直卿与长乐一朋友在此。方得下手整顿。但疾病昏倦时多。又为人事书尺妨废。不能得就绪。直卿又许了乡人馆。未知如何。若不能留。尤觉失助。甚恨乡时不曾留得伯量。相与协力。若渠今年不作书会则烦为道意。得其一来。为数月留。千万幸也。○答子静书语类只记曾节夫往见陆先生作书令去云。而其书无所考。
与伯量书云。所定礼编。恨未之见。此间所编丧礼一门。福州尚未送来。将来若得贤者持彼成书。复来参订。庶几详审。不至差互。但恐相去之远。难遂此期耳。○与商伯书云。伯量依旧在门馆否。礼书近得黄直卿与长乐一朋友在此。方得下手整顿。但疾病昏倦时多。又为人事书尺妨废。不能得就绪。直卿又许了乡人馆。未知如何。若不能留。尤觉失助。甚恨乡时不曾留得伯量。相与协力。若渠今年不作书会则烦为道意。得其一来。为数月留。千万幸也。○答子静书语类只记曾节夫往见陆先生作书令去云。而其书无所考。孟子浩然章。公孙丑敢问何谓浩然之气。集注孟子先言知言。而丑先问养气者。承上文论志气而言也。语类云乃是公孙丑会问处。留得知言在后面问者。盖知言是末后合尖上事。如大学正心修身。只合杀在致知在格物一句。盖是用工夫起头处。又曰公孙丑善问。问得愈密。盛水不漏。若论他会恁地问则不当云轲之死不得其传。不知后来怎生。不可晓。或是孟子自作此书润饰过。不可知。
明道言当与元丰大臣共政。乃是圣贤之用义理之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6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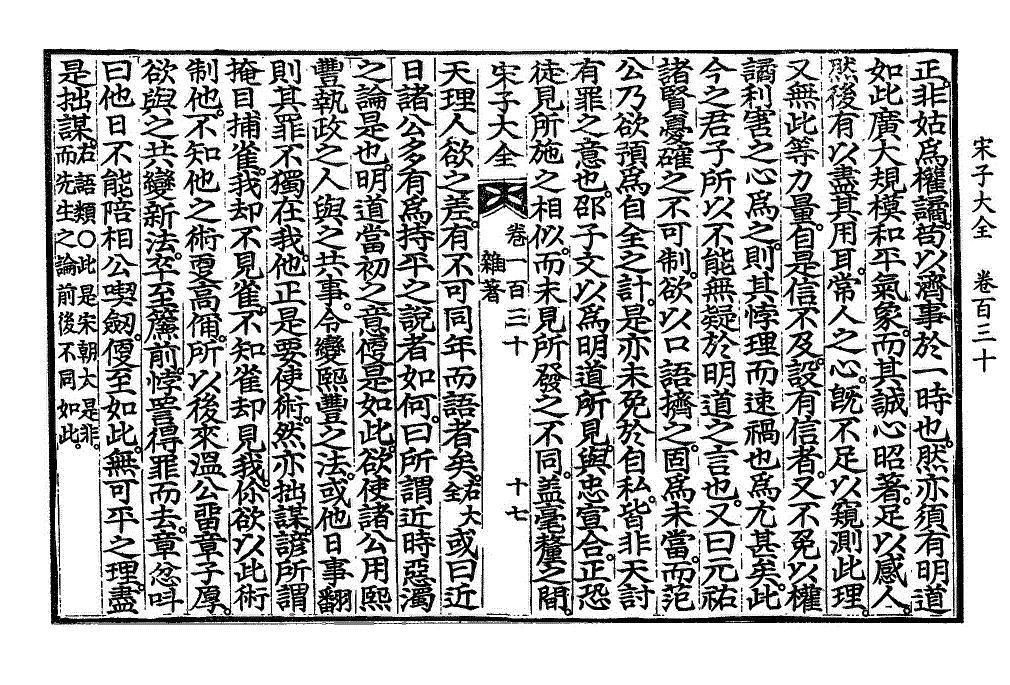 正。非姑为权谲。苟以济事于一时也。然亦须有明道如此广大规模和平气象。而其诚心昭著。足以感人。然后有以尽其用耳。常人之心。既不足以窥测此理。又无此等力量。自是信不及。设有信者。又不免以权谲利害之心为之。则其悖理而速祸也为尤甚矣。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无疑于明道之言也。又曰元祐诸贤忧确之不可制。欲以口语挤之。固为未当。而范公乃欲预为自全之计。是亦未免于自私。皆非天讨有罪之意也。邵子文以为明道所见。与忠宣合。正恐徒见所施之相似。而未见所发之不同。盖毫釐之间。天理人欲之差。有不可同年而语者矣。(右大全)或曰近日诸公多有为持平之说者如何。曰所谓近时恶浊之论是也。明道当初之意便是如此。欲使诸公用熙丰执政之人与之共事。令变熙丰之法。或他日事翻则其罪不独在我。他正是要使术。然亦拙谋。谚所谓掩目捕雀。我却不见雀。不知雀却见我。你欲以此术制他。不知他之术更高你。所以后来温公留章子厚。欲与之共变新法。卒至帘前。悖詈得罪而去。章忿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吃剑。便至如此。无可平之理。尽是拙谋。(右语类○此是宋朝大是非。而先生之论前后不同如此。)
正。非姑为权谲。苟以济事于一时也。然亦须有明道如此广大规模和平气象。而其诚心昭著。足以感人。然后有以尽其用耳。常人之心。既不足以窥测此理。又无此等力量。自是信不及。设有信者。又不免以权谲利害之心为之。则其悖理而速祸也为尤甚矣。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无疑于明道之言也。又曰元祐诸贤忧确之不可制。欲以口语挤之。固为未当。而范公乃欲预为自全之计。是亦未免于自私。皆非天讨有罪之意也。邵子文以为明道所见。与忠宣合。正恐徒见所施之相似。而未见所发之不同。盖毫釐之间。天理人欲之差。有不可同年而语者矣。(右大全)或曰近日诸公多有为持平之说者如何。曰所谓近时恶浊之论是也。明道当初之意便是如此。欲使诸公用熙丰执政之人与之共事。令变熙丰之法。或他日事翻则其罪不独在我。他正是要使术。然亦拙谋。谚所谓掩目捕雀。我却不见雀。不知雀却见我。你欲以此术制他。不知他之术更高你。所以后来温公留章子厚。欲与之共变新法。卒至帘前。悖詈得罪而去。章忿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吃剑。便至如此。无可平之理。尽是拙谋。(右语类○此是宋朝大是非。而先生之论前后不同如此。)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6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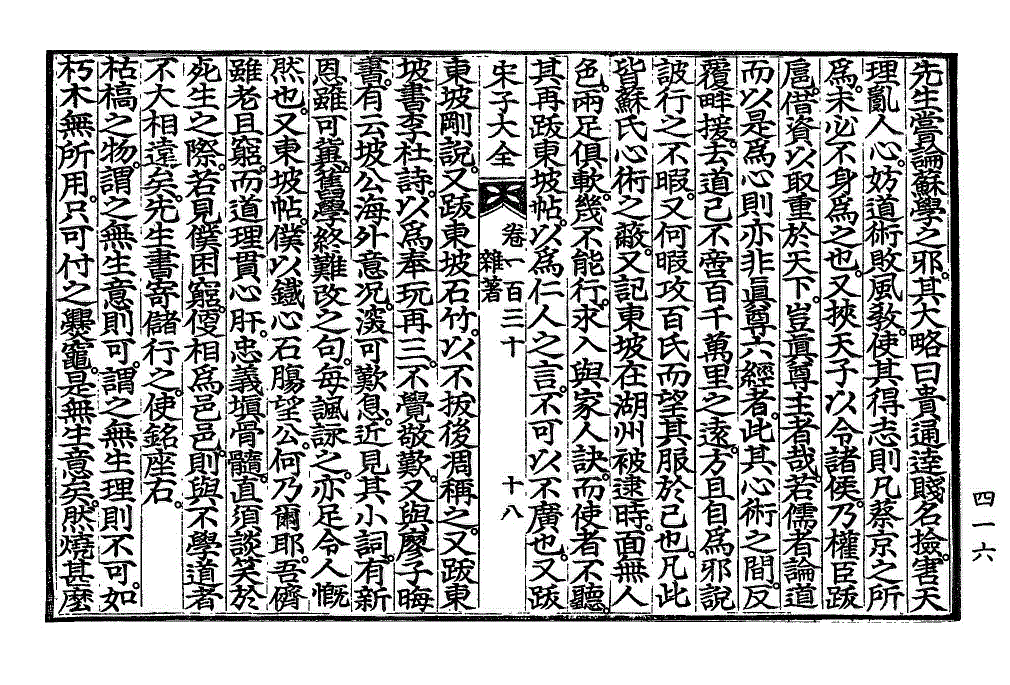 先生尝论苏学之邪。其大略曰贵通达贱名捡。害天理乱人心。妨道术败风教。使其得志则凡蔡京之所为。未必不身为之也。又挟天子以令诸侯。乃权臣跋扈。借资以取重于天下。岂真尊主者哉。若儒者论道而以是为心则亦非真尊六经者。此其心术之间。反覆畔援。去道已不啻百千万里之远。方且自为邪说诐行之不暇。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于己也。凡此皆苏氏心术之蔽。又记东坡在湖州被逮时。面无人色。两足俱软。几不能行。求入与家人诀。而使者不听。其再跋东坡帖。以为仁人之言。不可以不广也。又跋东坡刚说。又跋东坡石竹。以不拔后凋称之。又跋东坡书李杜诗。以为奉玩再三。不觉敬叹。又与廖子晦书。有云坡公海外意况。深可叹息。近见其小词。有新恩虽可冀。旧学终难改之句。每讽咏之。亦足令人慨然也。又东坡帖。仆以铁心石肠望公。何乃尔耶。吾侪虽老且穷。而道理贯心肝。忠义填骨髓。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。若见仆困穷。便相为邑邑。则与不学道者不大相远矣。先生书寄储行之。使铭座右。
先生尝论苏学之邪。其大略曰贵通达贱名捡。害天理乱人心。妨道术败风教。使其得志则凡蔡京之所为。未必不身为之也。又挟天子以令诸侯。乃权臣跋扈。借资以取重于天下。岂真尊主者哉。若儒者论道而以是为心则亦非真尊六经者。此其心术之间。反覆畔援。去道已不啻百千万里之远。方且自为邪说诐行之不暇。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于己也。凡此皆苏氏心术之蔽。又记东坡在湖州被逮时。面无人色。两足俱软。几不能行。求入与家人诀。而使者不听。其再跋东坡帖。以为仁人之言。不可以不广也。又跋东坡刚说。又跋东坡石竹。以不拔后凋称之。又跋东坡书李杜诗。以为奉玩再三。不觉敬叹。又与廖子晦书。有云坡公海外意况。深可叹息。近见其小词。有新恩虽可冀。旧学终难改之句。每讽咏之。亦足令人慨然也。又东坡帖。仆以铁心石肠望公。何乃尔耶。吾侪虽老且穷。而道理贯心肝。忠义填骨髓。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。若见仆困穷。便相为邑邑。则与不学道者不大相远矣。先生书寄储行之。使铭座右。枯槁之物。谓之无生意则可。谓之无生理则不可。如朽木无所用。只可付之爨灶。是无生意矣。然烧甚么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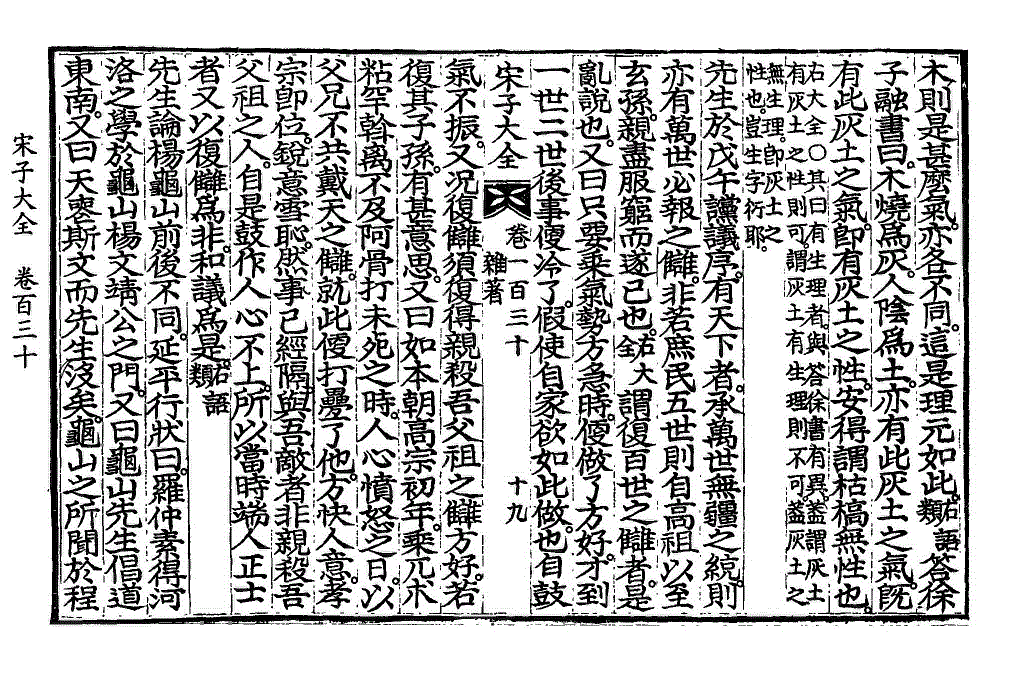 木则是甚么气。亦各不同。这是理元如此。(右语类)答徐子融书曰。木烧为灰。人阴为土。亦有此灰土之气。既有此灰土之气。即有灰土之性。安得谓枯槁无性也。(右大全○其曰有生理者。与答徐书有异。盖谓灰土有灰土之性则可。谓灰土有生理则不可。盖灰土之无生理。即灰土之性也。岂生字衍耶。)
木则是甚么气。亦各不同。这是理元如此。(右语类)答徐子融书曰。木烧为灰。人阴为土。亦有此灰土之气。既有此灰土之气。即有灰土之性。安得谓枯槁无性也。(右大全○其曰有生理者。与答徐书有异。盖谓灰土有灰土之性则可。谓灰土有生理则不可。盖灰土之无生理。即灰土之性也。岂生字衍耶。)先生于戊午谠议序。有天下者。承万世无疆之统。则亦有万世必报之雠。非若庶民五世则自高祖以至玄孙。亲尽服穷而遂已也。(右大全)谓复百世之雠者。是乱说也。又曰只要乘气势方急时。便做了方好。才到一世二世后事便冷了。假使自家欲如此做。也自鼓气不振。又况复雠须复得亲杀吾父祖之雠方好。若复其子孙。有甚意思。又曰如本朝高宗初年。乘兀朮粘罕斡离不及阿骨打未死之时。人心愤怒之日。以父兄不共戴天之雠。就此便打叠了他。方快人意。孝宗即位。锐意雪耻。然事已经隔。与吾敌者非亲杀吾父祖之人。自是鼓作人心不上。所以当时端人正士者又以复雠为非。和议为是。(右语类)
先生论杨龟山前后不同。延平行状曰。罗仲素得河洛之学于龟山杨文靖公之门。又曰龟山先生倡道东南。又曰天丧斯文而先生没矣。龟山之所闻于程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7L 页
 夫子而授之罗公者。至是而不得其传矣。西山先生墓表曰。龟山之所以教。西山之所以学。其亦足以观矣。至语类则论龟山学佛及出处之病。至曰张皇佛氏之势。亦如李邺张皇金虏也。又曰龟山做人也苟且。此与上文称道之说大不同。
夫子而授之罗公者。至是而不得其传矣。西山先生墓表曰。龟山之所以教。西山之所以学。其亦足以观矣。至语类则论龟山学佛及出处之病。至曰张皇佛氏之势。亦如李邺张皇金虏也。又曰龟山做人也苟且。此与上文称道之说大不同。周子太极通书解。据年谱实纪则成于乾道九年癸巳四月。而据大全通书记则通书成于淳熙丁未九月。其前后不同如是矣。岂年谱实纪误耶。
周子通书记。当在记类。而大全乃编于跋类。有不可知者矣。
先生于孟子好辩章末。有云苟有能为距杨墨之说者。则虽未必知道。亦是圣人之徒也。盖邪说害正。人人得而攻之。不必圣贤。如春秋之法。乱臣贼子。人人得而诛之。不必士师也。圣人救世立法之意。其切如此。若以此意推之。则不能攻讨而又唱为不必攻讨之说者。其为邪诐之徒。乱贼之党可知矣。答范伯崇书。异端害正。固君子所当辟。然须是吾学既明。洞见大本达道之全体。然后据天理以开有我之私。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。议论之间。彼此交尽而内外之道一以贯之。如孟子论养气而及告子义外之非。因夷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8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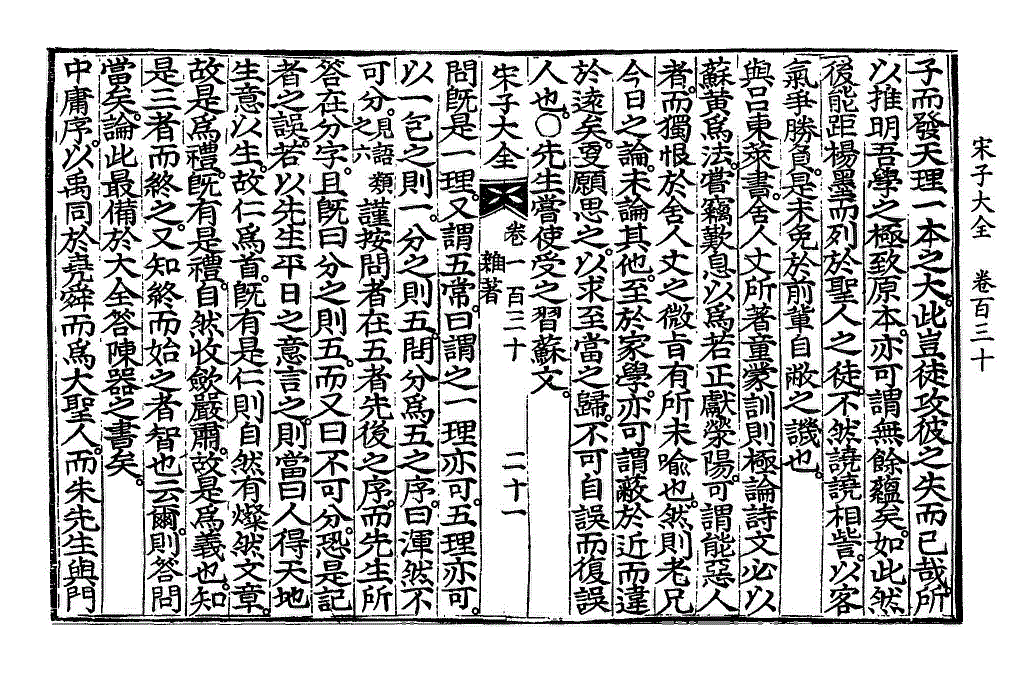 子而发天理一本之大。此岂徒攻彼之失而已哉。所以推明吾学之极致原本。亦可谓无馀蕴矣。如此然后能距杨墨而列于圣人之徒。不然譊譊相訾。以客气争胜负。是未免于前辈自敝之讥也。
子而发天理一本之大。此岂徒攻彼之失而已哉。所以推明吾学之极致原本。亦可谓无馀蕴矣。如此然后能距杨墨而列于圣人之徒。不然譊譊相訾。以客气争胜负。是未免于前辈自敝之讥也。与吕东莱书。舍人丈所著童蒙训则极论诗文必以苏黄为法。尝窃叹息以为若正献荥阳。可谓能恶人者。而独恨于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。然则老兄今日之论。未论其他。至于家学。亦可谓蔽于近而违于远矣。更愿思之。以求至当之归。不可自误而复误人也。○先生尝使受之习苏文。
问既是一理。又谓五常。曰谓之一理亦可。五理亦可。以一包之则一。分之则五。问分为五之序。曰浑然不可分。(见语类之六)谨按问者在五者先后之序。而先生所答在分字。且既曰分之则五。而又曰不可分。恐是记者之误。若以先生平日之意言之。则当曰人得天地生意以生。故仁为首。既有是仁则自然有灿然文章。故是为礼。既有是礼。自然收敛严肃。故是为义也。知是三者而终之。又知终而始之者智也云尔。则答问当矣。论此最备于大全答陈器之书矣。
中庸序。以禹同于尧舜而为大圣人。而朱先生与门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8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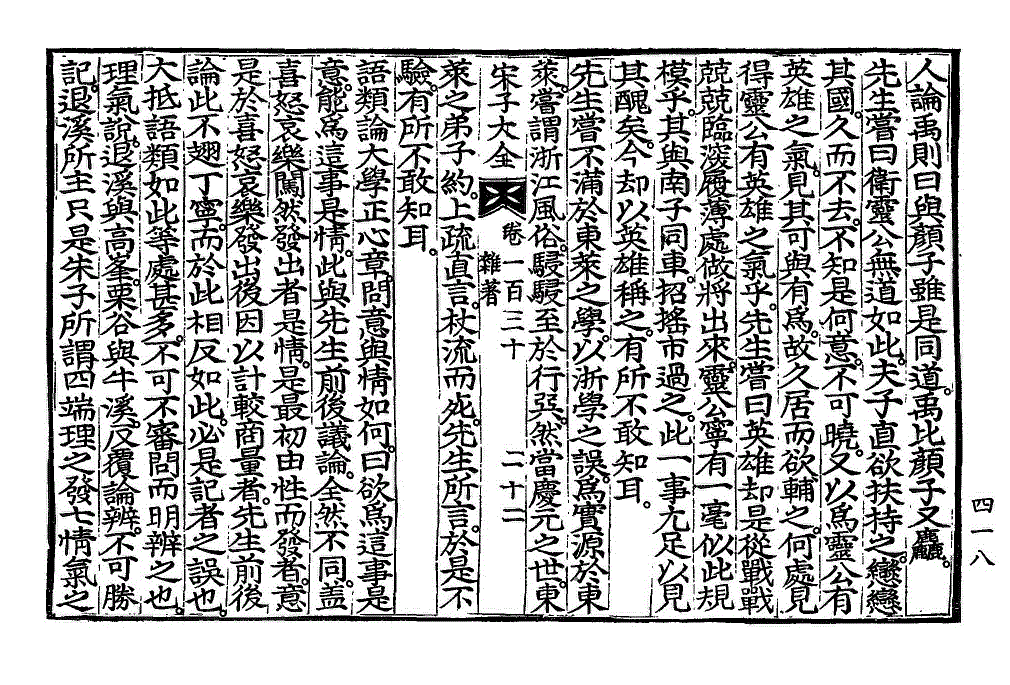 人论禹则曰与颜子虽是同道。禹比颜子又粗。
人论禹则曰与颜子虽是同道。禹比颜子又粗。先生尝曰卫灵公无道如此。夫子直欲扶持之。恋恋其国。久而不去。不知是何意。不可晓。又以为灵公有英雄之气。见其可与有为。故久居而欲辅之。何处见得灵公有英雄之气乎。先生尝曰英雄却是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。灵公宁有一毫似此规模乎。其与南子同车。招摇市过之。此一事尤足以见其丑矣。今却以英雄称之。有所不敢知耳。
先生尝不满于东莱之学。以浙学之误。为实源于东莱。尝谓浙江风俗。骎骎至于行巽。然当庆元之世。东莱之弟子约。上疏直言。杖流而死。先生所言。于是不验。有所不敢知耳。
语类论大学正心章。问意与情如何。曰欲为这事是意。能为这事是情。此与先生前后议论。全然不同。盖喜怒哀乐闯然发出者是情。是最初由性而发者。意是于喜怒哀乐发出后因以计较商量者。先生前后论此不翅丁宁。而于此相反如此。必是记者之误也。大抵语类如此等处甚多。不可不审问而明辨之也。理气说。退溪与高峰。栗谷与牛溪。反覆论辨。不可胜记。退溪所主只是朱子所谓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9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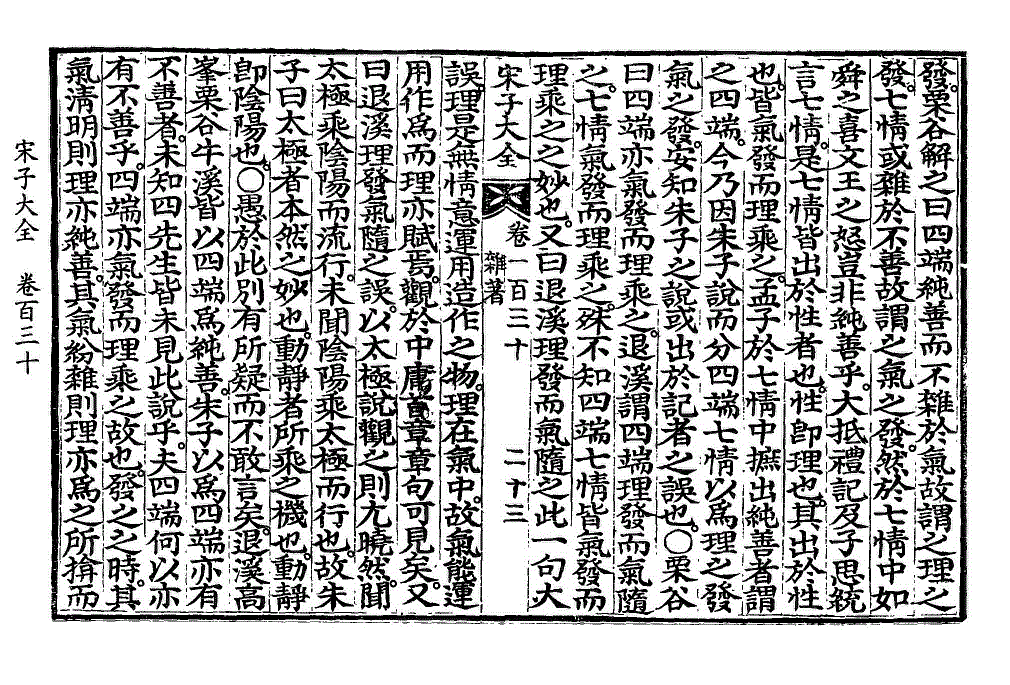 发。栗谷解之曰四端纯善而不杂于气故谓之理之发。七情或杂于不善故谓之气之发。然于七情中如舜之喜文王之怒。岂非纯善乎。大抵礼记及子思统言七情。是七情皆出于性者也。性即理也。其出于性也。皆气发而理乘之。孟子于七情中摭出纯善者谓之四端。今乃因朱子说而分四端七情以为理之发气之发。安知朱子之说或出于记者之误也。○栗谷曰四端亦气发而理乘之。退溪谓四端理发而气随之。七情气发而理乘之。殊不知四端七情皆气发而理乘之之妙也。又曰退溪理发而气随之。此一句大误。理是无情意运用造作之物。理在气中。故气能运用作为而理亦赋焉。观于中庸首章章句可见矣。又曰退溪理发气随之误。以太极说观之则尤晓然。闻太极乘阴阳而流行。未闻阴阳乘太极而行也。故朱子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。动静者所乘之机也。动静即阴阳也。○愚于此别有所疑而不敢言矣。退溪,高峰,栗谷,牛溪皆以四端为纯善。朱子以为四端亦有不善者。未知四先生皆未见此说乎。夫四端何以亦有不善乎。四端亦气发而理乘之故也。发之之时。其气清明则理亦纯善。其气纷杂则理亦为之所掩而
发。栗谷解之曰四端纯善而不杂于气故谓之理之发。七情或杂于不善故谓之气之发。然于七情中如舜之喜文王之怒。岂非纯善乎。大抵礼记及子思统言七情。是七情皆出于性者也。性即理也。其出于性也。皆气发而理乘之。孟子于七情中摭出纯善者谓之四端。今乃因朱子说而分四端七情以为理之发气之发。安知朱子之说或出于记者之误也。○栗谷曰四端亦气发而理乘之。退溪谓四端理发而气随之。七情气发而理乘之。殊不知四端七情皆气发而理乘之之妙也。又曰退溪理发而气随之。此一句大误。理是无情意运用造作之物。理在气中。故气能运用作为而理亦赋焉。观于中庸首章章句可见矣。又曰退溪理发气随之误。以太极说观之则尤晓然。闻太极乘阴阳而流行。未闻阴阳乘太极而行也。故朱子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。动静者所乘之机也。动静即阴阳也。○愚于此别有所疑而不敢言矣。退溪,高峰,栗谷,牛溪皆以四端为纯善。朱子以为四端亦有不善者。未知四先生皆未见此说乎。夫四端何以亦有不善乎。四端亦气发而理乘之故也。发之之时。其气清明则理亦纯善。其气纷杂则理亦为之所掩而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1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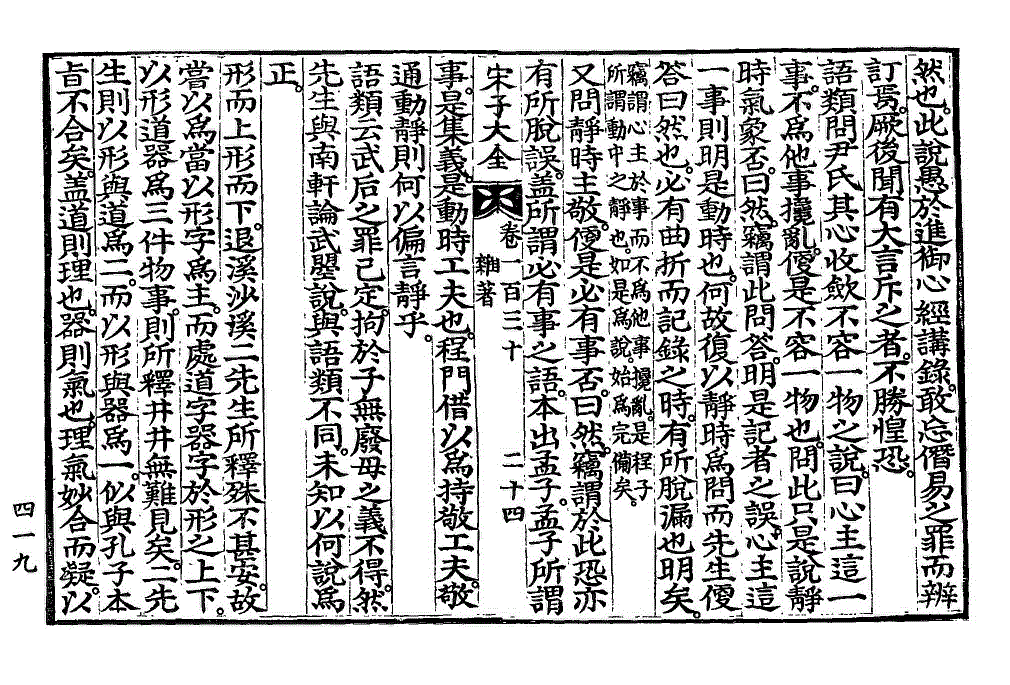 然也。此说愚于进御心经讲录。敢妄僭易之罪而辨订焉。厥后闻有大言斥之者。不胜惶恐。
然也。此说愚于进御心经讲录。敢妄僭易之罪而辨订焉。厥后闻有大言斥之者。不胜惶恐。语类问尹氏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之说。曰心主这一事。不为他事搀乱。便是不容一物也。问此只是说静时气象否。曰然。窃谓此问答。明是记者之误。心主这一事则明是动时也。何故复以静时为问而先生便答曰然也。必有曲折而记录之时。有所脱漏也明矣。(窃谓心主于事而不为他事搀乱。是程子所谓动中之静也。如是为说。始为完备矣。)
又问静时主敬。便是必有事否。曰然。窃谓于此恐亦有所脱误。盖所谓必有事之语。本出孟子。孟子所谓事。是集义。是动时工夫也。程门借以为持敬工夫。敬通动静则何以偏言静乎。
语类云武后之罪已定。拘于子无废母之义不得。然先生与南轩论武照说。与语类不同。未知以何说为正。
形而上形而下。退溪,沙溪二先生所释殊不甚安。故尝以为当以形字为主。而处道字器字于形之上下。以形道器为三件物事。则所释井井无难见矣。二先生则以形与道为二。而以形与器为一。似与孔子本旨不合矣。盖道则理也。器则气也。理气妙合而凝。以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2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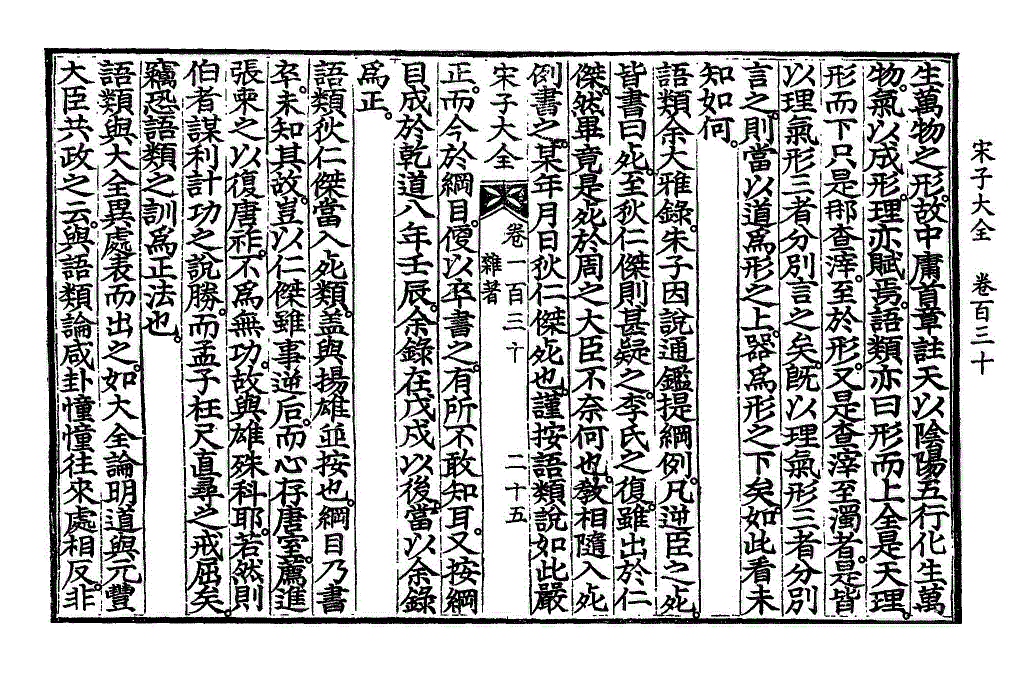 生万物之形。故中庸首章注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。气以成形。理亦赋焉。语类亦曰形而上全是天理。形而下只是那查滓。至于形。又是查滓至浊者。是皆以理气形三者分别言之矣。既以理气形三者分别言之。则当以道为形之上。器为形之下矣。如此看未知如何。
生万物之形。故中庸首章注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。气以成形。理亦赋焉。语类亦曰形而上全是天理。形而下只是那查滓。至于形。又是查滓至浊者。是皆以理气形三者分别言之矣。既以理气形三者分别言之。则当以道为形之上。器为形之下矣。如此看未知如何。语类余大雅录。朱子因说通鉴提纲例。凡逆臣之死。皆书曰死。至狄仁杰则甚疑之。李氏之复。虽出于仁杰。然毕竟是死于周之大臣不奈何也。教相随入死例书之。某年月日狄仁杰死也。谨按语类说如此严正。而今于纲目。便以卒书之。有所不敢知耳。又按纲目成于乾道八年壬辰。余录在戊戌以后。当以余录为正。
语类狄仁杰当入死类。盖与扬雄并按也。纲目乃书卒。未知其故。岂以仁杰虽事逆后。而心存唐室。荐进张柬之以复唐祚。不为无功。故与雄殊科耶。若然则伯者谋利计功之说胜。而孟子枉尺直寻之戒屈矣。窃恐语类之训为正法也。
语类与大全异处表而出之。如大全论明道与元丰大臣共政之云。与语类论咸卦憧憧往来处相反。非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2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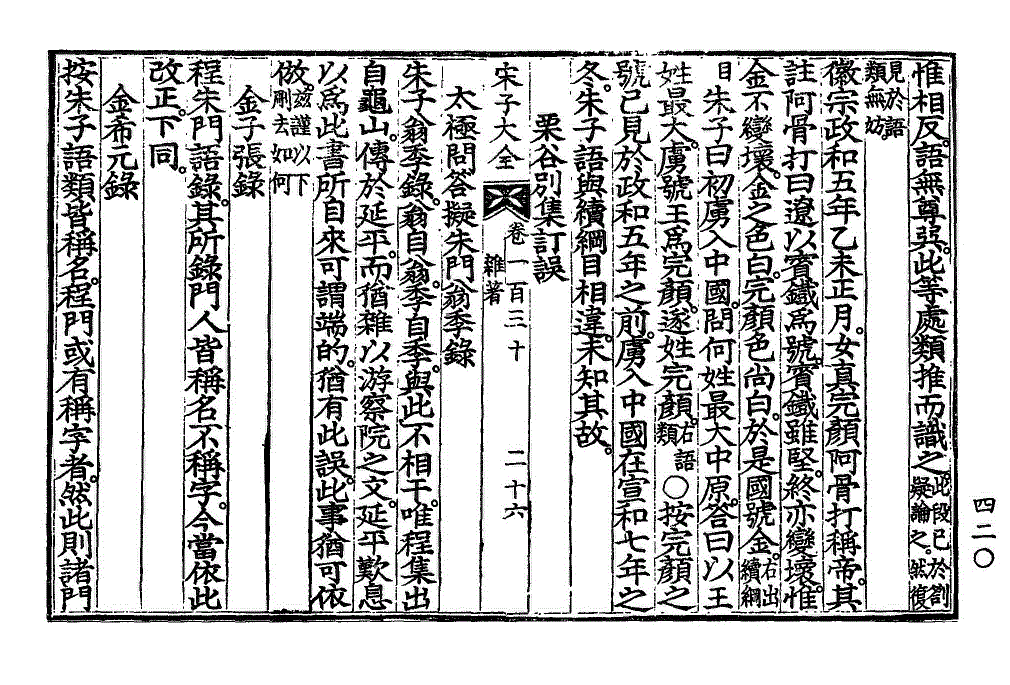 惟相反。语无尊巽。此等处类推而识之。(此段已于劄疑论之。然复见于语类无妨。)
惟相反。语无尊巽。此等处类推而识之。(此段已于劄疑论之。然复见于语类无妨。)徽宗政和五年乙未正月。女真完颜阿骨打称帝。其注阿骨打曰辽以宾铁为号。宾铁虽坚。终亦变坏。惟金不变坏。金之色白。完颜色尚白。于是国号金。(右出续纲目)朱子曰初虏入中国。问何姓最大中原。答曰以王姓最大。虏号王为完颜。遂姓完颜。(右语类)○按完颜之号已见于政和五年之前。虏入中国在宣和七年之冬。朱子语与续纲目相违。未知其故。
栗谷别集订误
太极问答拟朱门翁季录
朱子翁季录。翁自翁。季自季。与此不相干。唯程集出自龟山。传于延平。而犹杂以游察院之文。延平叹息以为此书所自来可谓端的。犹有此误。此事犹可依仿。(兹谨以下删去如何)
金子张录
程朱门语录。其所录门人皆称名不称字。今当依此改正。下同。
金希元录
按朱子语类皆称名。程门或有称字者。然此则诸门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2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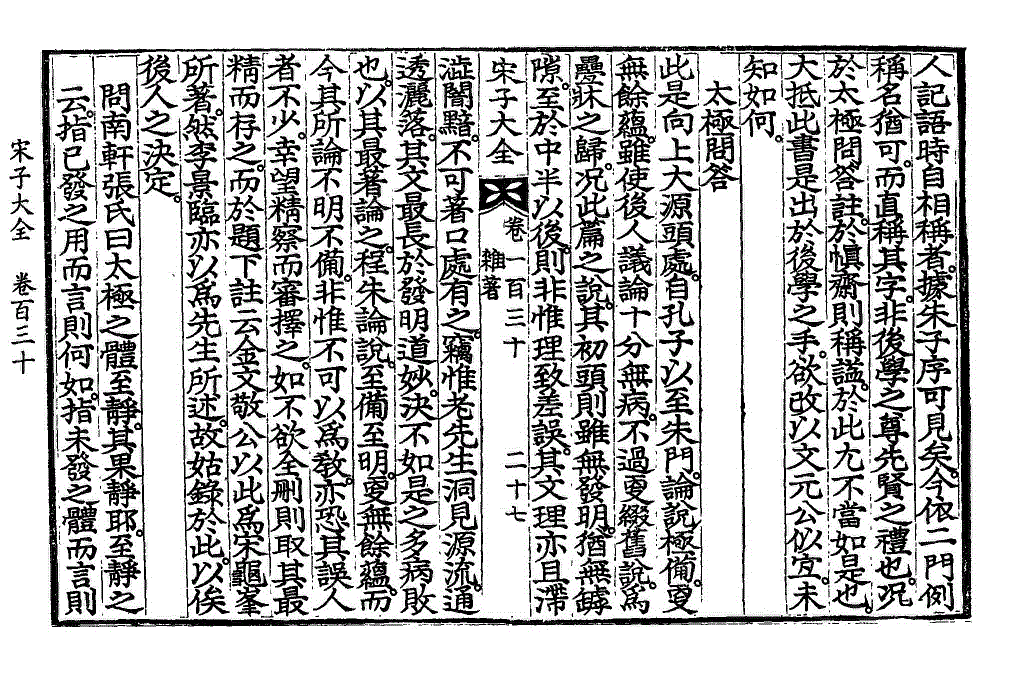 人记语时自相称者。据朱子序可见矣。今依二门例称名犹可。而直称其字。非后学之尊先贤之礼也。况于太极问答注。于慎斋则称谥。于此尤不当如是也。大抵此书是出于后学之手。欲改以文元公似宜。未知如何。
人记语时自相称者。据朱子序可见矣。今依二门例称名犹可。而直称其字。非后学之尊先贤之礼也。况于太极问答注。于慎斋则称谥。于此尤不当如是也。大抵此书是出于后学之手。欲改以文元公似宜。未知如何。太极问答
此是向上大源头处。自孔子以至朱门。论说极备。更无馀蕴。虽使后人议论十分无病。不过更缀旧说。为叠床之归。况此篇之说。其初头则虽无发明。犹无罅隙。至于中半以后。则非惟理致差误。其文理亦且滞涩闇黯。不可著口处有之。窃惟老先生洞见源流。通透洒落。其文最长于发明道妙。决不如是之多病败也。以其最著论之。程朱论说。至备至明。更无馀蕴。而今其所论不明不备。非惟不可以为教。亦恐其误人者不少。幸望精察而审择之。如不欲全删则取其最精而存之。而于题下注云金文敬公以此为宋龟峰所著。然李景临亦以为先生所述。故姑录于此。以俟后人之决定。
问南轩张氏曰太极之体至静。其果静耶。至静之云。指已发之用而言则何如。指未发之体而言则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2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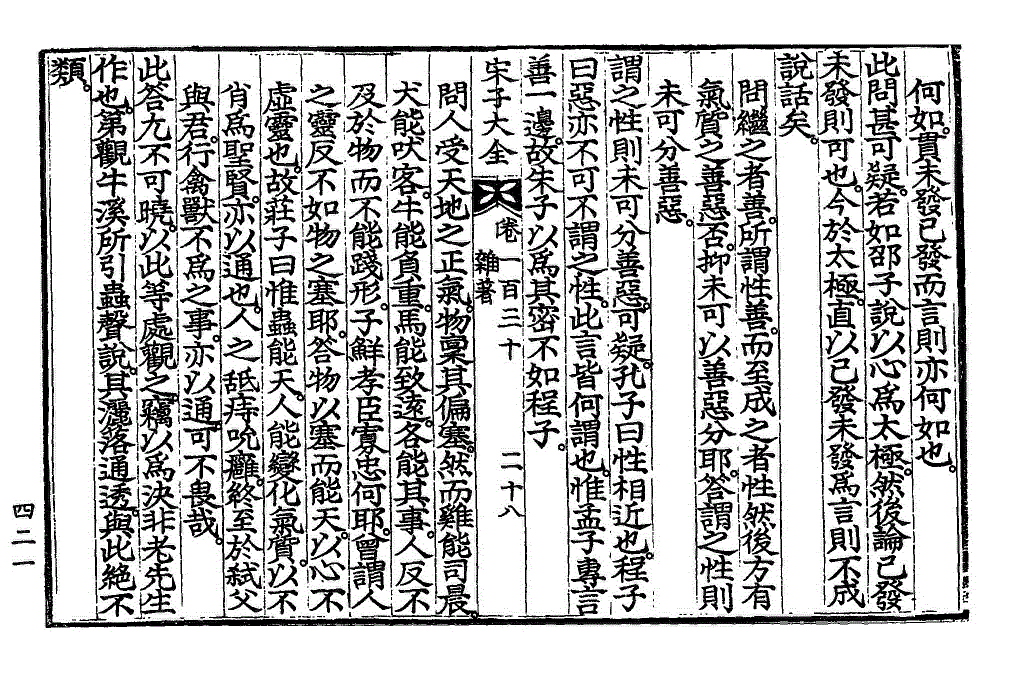 何如。贯未发已发而言则亦何如也。
何如。贯未发已发而言则亦何如也。此问甚可疑。若如邵子说以心为太极。然后论已发未发则可也。今于太极。直以已发未发为言则不成说话矣。
问继之者善。所谓性善。而至成之者性然后方有气质之善恶否。抑未可以善恶分耶。答谓之性则未可分善恶。
谓之性则未可分善恶。可疑。孔子曰性相近也。程子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。此言皆何谓也。惟孟子专言善一边。故朱子以为其密不如程子。
问人受天地之正气。物禀其偏塞。然而鸡能司晨。犬能吠客。牛能负重。马能致远。各能其事。人反不及于物而不能践形。子鲜孝臣寡忠何耶。曾谓人之灵反不如物之塞耶。答物以塞而能天。以心不虚灵也。故庄子曰惟虫能天。人能变化气质。以不肖为圣贤。亦以通也。人之舐痔吮痈。终至于弑父与君。行禽兽不为之事。亦以通。可不畏哉。
此答尤不可晓。以此等处观之。窃以为决非老先生作也。第观牛溪所引虫声说。其洒落通透。与此绝不类。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2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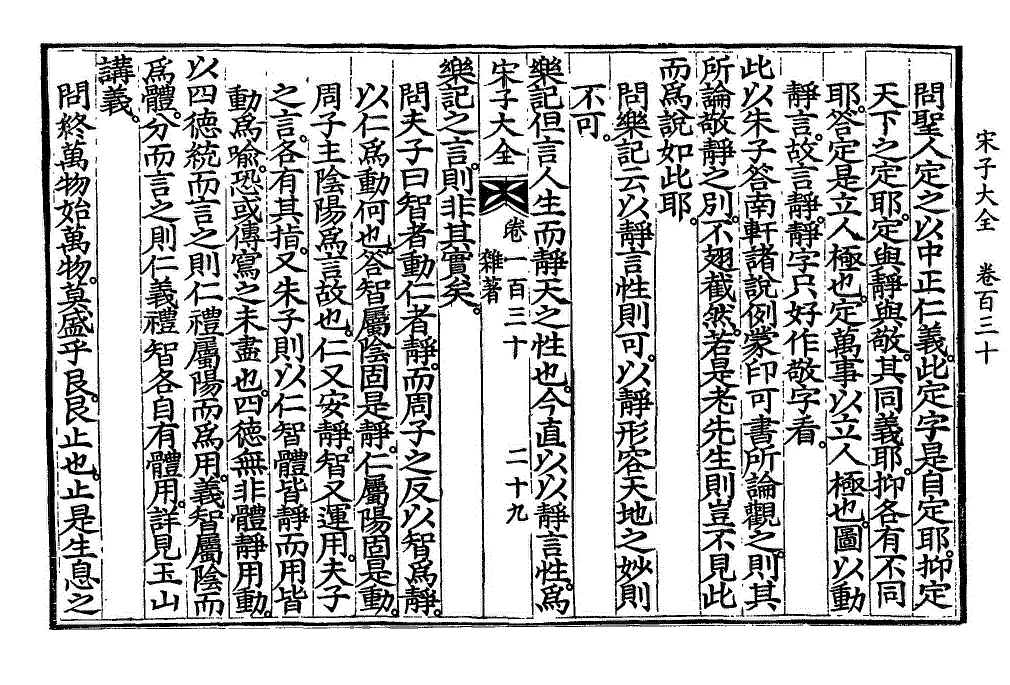 问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。此定字是自定耶。抑定天下之定耶。定与静与敬。其同义耶。抑各有不同耶。答定是立人极也。定万事以立人极也。图以动静言。故言静。静字只好作敬字看。
问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。此定字是自定耶。抑定天下之定耶。定与静与敬。其同义耶。抑各有不同耶。答定是立人极也。定万事以立人极也。图以动静言。故言静。静字只好作敬字看。此以朱子答南轩诸说例蒙印可书所论观之。则其所论敬静之别。不翅截然。若是老先生则岂不见此而为说如此耶。
问乐记云以静言性则可。以静形容天地之妙则不可。
乐记但言人生而静天之性也。今直以以静言性。为乐记之言。则非其实矣。
问夫子曰智者动仁者静。而周子之反以智为静。以仁为动何也。答智属阴固是静。仁属阳固是动。周子主阴阳为言故也。仁又安静。智又运用。夫子之言。各有其指。又朱子则以仁智体皆静而用皆动为喻。恐或传写之未尽也。四德无非体静用动。
以四德统而言之则仁礼属阳而为用。义智属阴而为体。分而言之则仁义礼智各自有体用。详见玉山讲义。
问终万物始万物。莫盛乎艮。艮止也。止是生息之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2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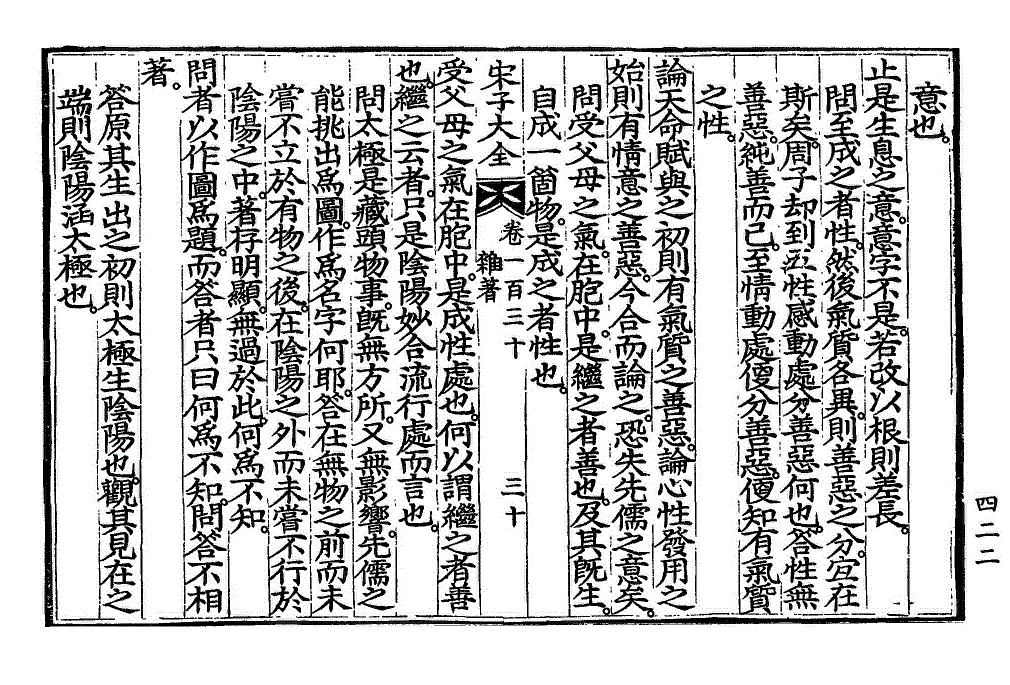 意也。
意也。止是生息之意。意字不是。若改以根则差长。
问至成之者性。然后气质各异。则善恶之分。宜在斯矣。周子却到五性感动处分善恶何也。答性无善恶。纯善而已。至情动处便分善恶。便知有气质之性。
论天命赋与之初则有气质之善恶。论心性发用之始则有情意之善恶。今合而论之。恐失先儒之意矣。
问受父母之气。在胞中。是继之者善也。及其既生。自成一个物。是成之者性也。
受父母之气在胞中。是成性处也。何以谓继之者善也。继之云者。只是阴阳妙合流行处而言也。
问太极是藏头物事。既无方所。又无影响。先儒之能挑出为图。作为名字何耶。答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。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于阴阳之中。著存明显。无过于此。何为不知。
问者以作图为题。而答者只曰何为不知。问答不相著。
答原其生出之初则太极生阴阳也。观其见在之端则阴阳涵太极也。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2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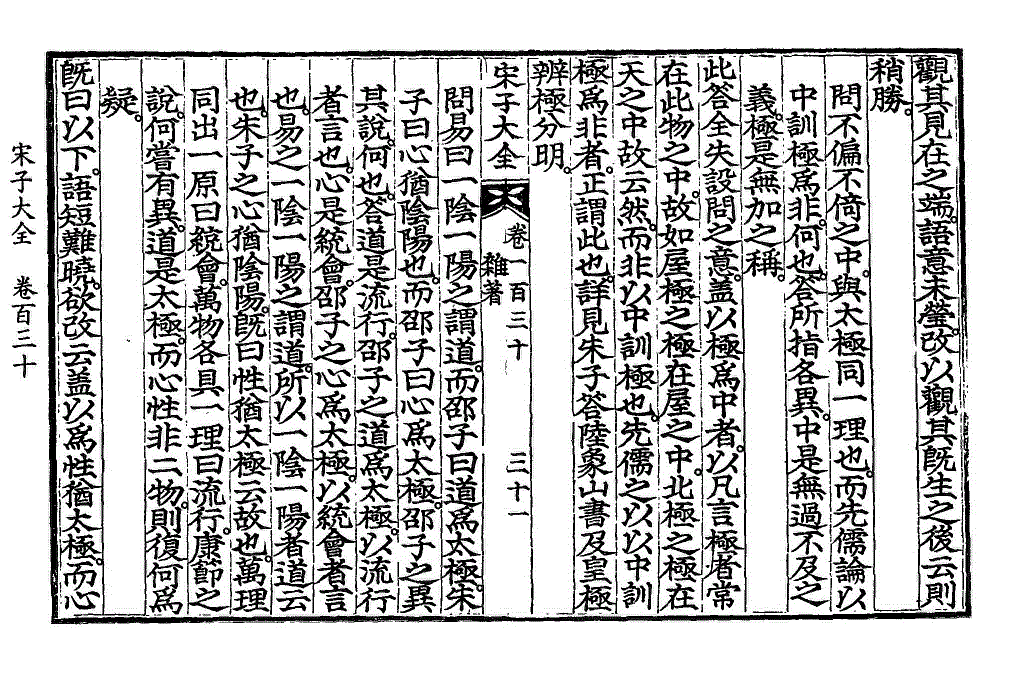 观其见在之端。语意未莹。改以观其既生之后云则稍胜。
观其见在之端。语意未莹。改以观其既生之后云则稍胜。问不偏不倚之中。与太极同一理也。而先儒论以中训极为非。何也。答所指各异。中是无过不及之义。极是无加之称。
此答全失设问之意。盖以极为中者。以凡言极者常在此物之中。故如屋极之极在屋之中。北极之极在天之中故云然。而非以中训极也。先儒之以以中训极为非者。正谓此也。详见朱子答陆象山书及皇极辨极分明。
问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。而邵子曰道为太极。朱子曰心犹阴阳也。而邵子曰心为太极。邵子之异其说。何也。答道是流行。邵子之道为太极。以流行者言也。心是统会。邵子之心为太极。以统会者言也。易之一阴一阳之谓道。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云也。朱子之心犹阴阳。既曰性犹太极云故也。万理同出一原曰统会。万物各具一理曰流行。康节之说。何尝有异。道是太极。而心性非二物。则复何为疑。
既曰以下。语短难晓。欲改云盖以为性犹太极。而心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2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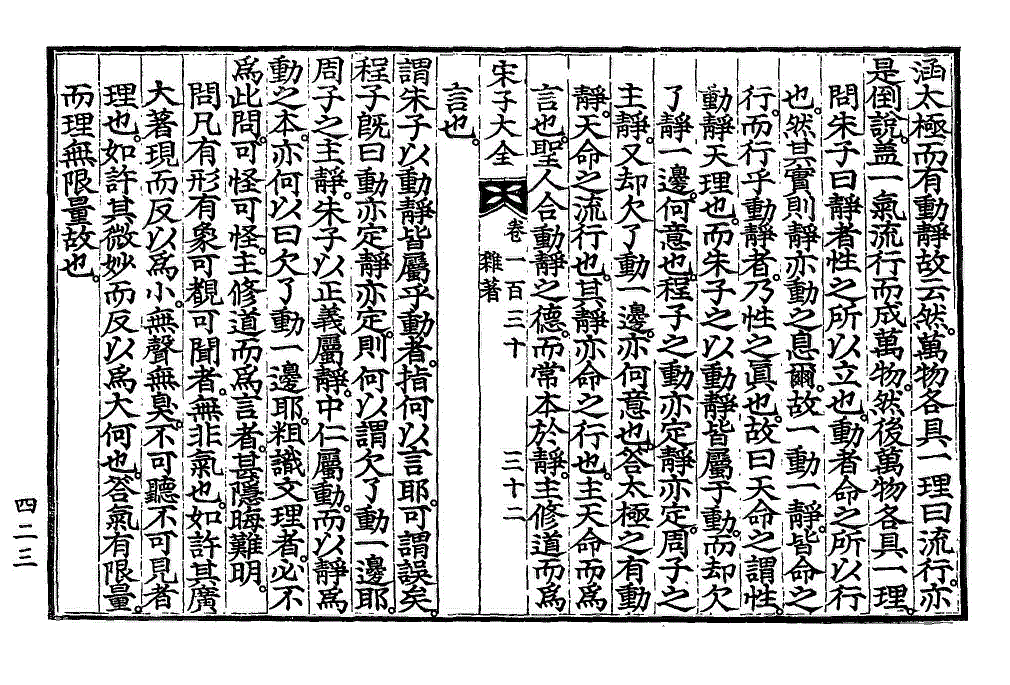 涵太极而有动静故云然。万物各具一理曰流行。亦是倒说。盖一气流行而成万物。然后万物各具一理。
涵太极而有动静故云然。万物各具一理曰流行。亦是倒说。盖一气流行而成万物。然后万物各具一理。问朱子曰静者性之所以立也。动者命之所以行也。然其实则静亦动之息尔。故一动一静。皆命之行。而行乎动静者。乃性之真也。故曰天命之谓性。动静天理也。而朱子之以动静皆属于动。而却欠了静一边。何意也。程子之动亦定静亦定。周子之主静。又却欠了动一边。亦何意也。答太极之有动静。天命之流行也。其静亦命之行也。主天命而为言也。圣人合动静之德。而常本于静。主修道而为言也。
谓朱子以动静皆属乎动者。指何以言耶。可谓误矣。程子既曰动亦定静亦定。则何以谓欠了动一边耶。周子之主静。朱子以正义属静。中仁属动。而以静为动之本。亦何以曰欠了动一边耶。粗识文理者。必不为此问。可怪可怪。主修道而为言者。甚隐晦难明。
问凡有形有象可睹可闻者。无非气也。如许其广大著现而反以为小。无声无臭。不可听不可见者理也。如许其微妙而反以为大何也。答气有限量。而理无限量故也。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2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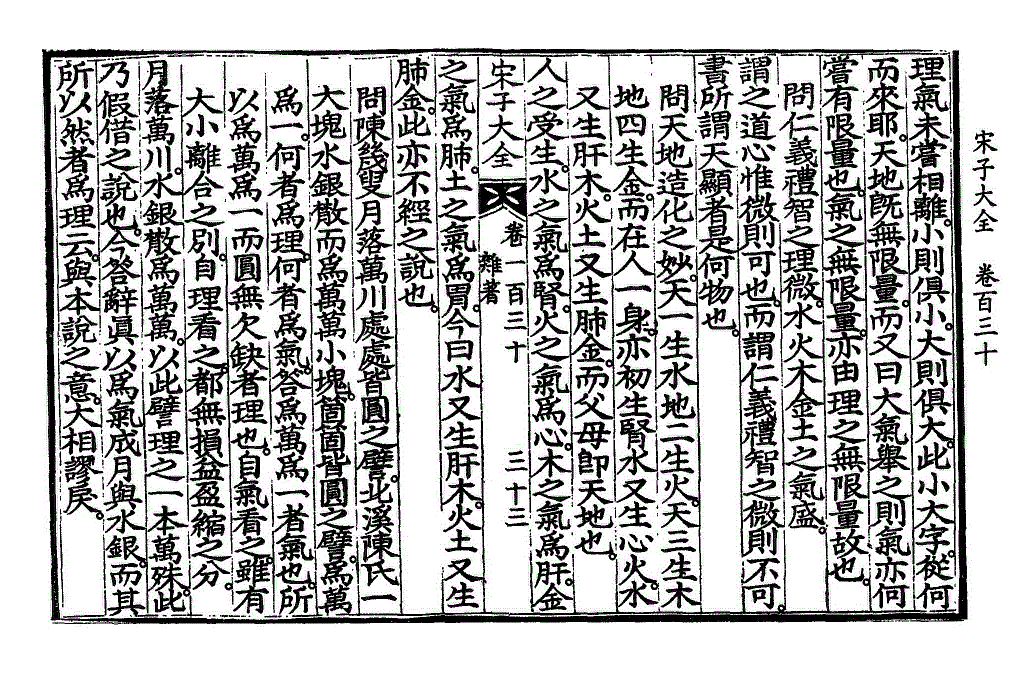 理气未尝相离。小则俱小。大则俱大。此小大字。从何而来耶。天地既无限量。而又曰大气举之则气亦何尝有限量也。气之无限量。亦由理之无限量故也。
理气未尝相离。小则俱小。大则俱大。此小大字。从何而来耶。天地既无限量。而又曰大气举之则气亦何尝有限量也。气之无限量。亦由理之无限量故也。问仁义礼智之理微。水火木金土之气盛。
谓之道心惟微则可也。而谓仁义礼智之微则不可。书所谓天显者是何物也。
问天地造化之妙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。天三生木地四生金。而在人一身。亦初生肾水又生心火。水又生肝木。火土又生肺金。而父母即天地也。
人之受生。水之气为肾。火之气为心。木之气为肝。金之气为肺。土之气为胃。今曰水又生肝木。火土又生肺金。此亦不经之说也。
问陈几叟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之譬。北溪陈氏一大块水银散而为万万小块。个个皆圆之譬。为万为一。何者为理。何者为气。答为万为一者气也。所以为万为一而圆无欠缺者理也。自气看之。虽有大小离合之别。自理看之。都无损益盈缩之分。
月落万川。水银散为万万。以此譬理之一本万殊。此乃假借之说也。今答辞真以为气成月与水银。而其所以然者为理云。与本说之意。大相谬戾。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2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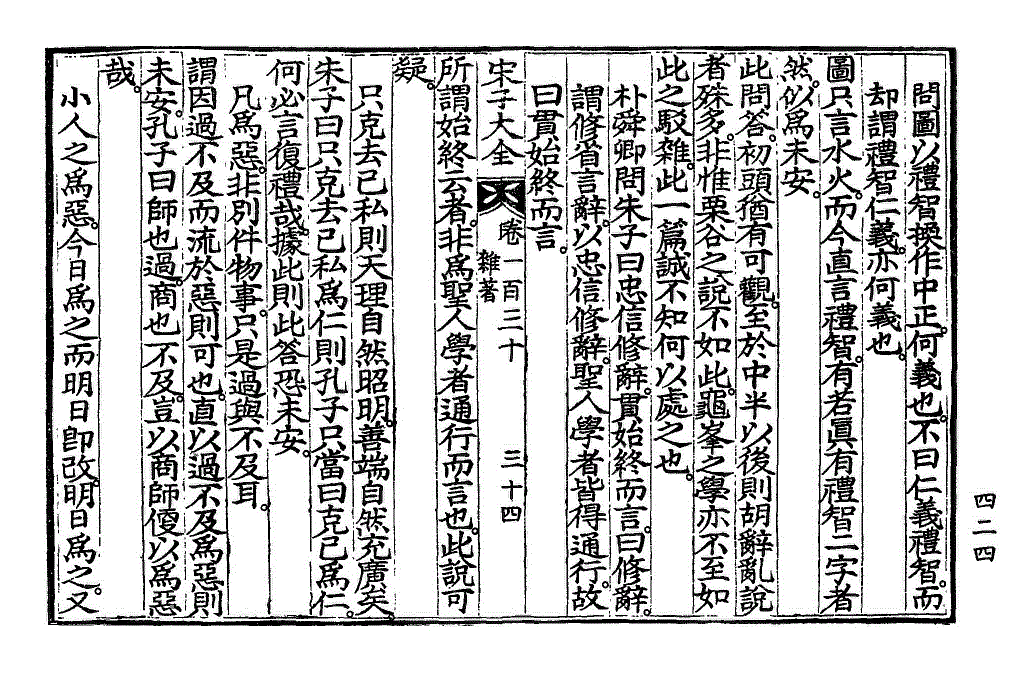 问图以礼智换作中正。何义也。不曰仁义礼智。而却谓礼智仁义。亦何义也。
问图以礼智换作中正。何义也。不曰仁义礼智。而却谓礼智仁义。亦何义也。图只言水火。而今直言礼智。有若真有礼智二字者然。似为未安。
此问答。初头犹有可观。至于中半以后则胡辞乱说者殊多。非惟栗谷之说不如此。龟峰之学亦不至如此之驳杂。此一篇诚不知何以处之也。
朴舜卿问朱子曰忠信修辞。贯始终而言。曰修辞。谓修省言辞。以忠信修辞。圣人学者皆得通行。故曰贯始终而言。
所谓始终云者。非为圣人学者通行而言也。此说可疑。
只克去己私则天理自然昭明。善端自然充广矣。
朱子曰只克去己私为仁则孔子只当曰克己为仁。何必言复礼哉。据此则此答恐未安。
凡为恶。非别件物事。只是过与不及耳。
谓因过不及而流于恶则可也。直以过不及为恶则未安。孔子曰师也过。商也不及。岂以商师便以为恶哉。
小人之为恶。今日为之而明日即改。明日为之。又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25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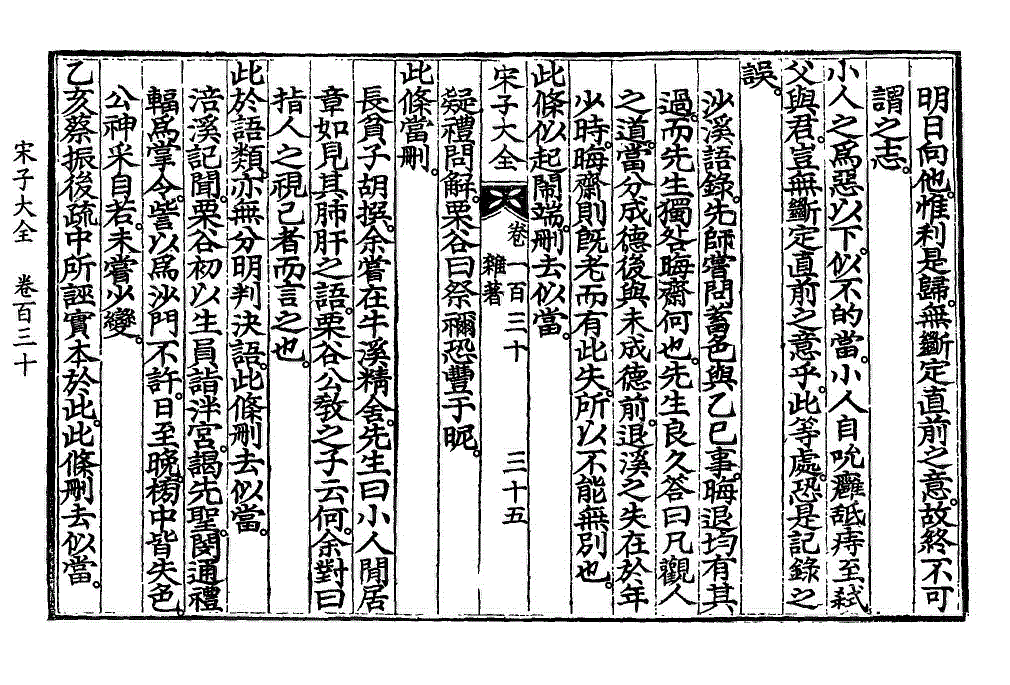 明日向他。惟利是归。无断定直前之意。故终不可谓之志。
明日向他。惟利是归。无断定直前之意。故终不可谓之志。小人之为恶以下。似不的当。小人自吮痈舐痔至弑父与君。岂无断定直前之意乎。此等处。恐是记录之误。
沙溪语录。先师尝问蓄色与乙巳事。晦退均有其过。而先生独咎晦斋何也。先生良久答曰凡观人之道。当分成德后与未成德前。退溪之失在于年少时。晦斋则既老而有此失。所以不能无别也。
此条似起闹端。删去似当。
疑礼问解。栗谷曰祭祢恐丰于昵。
此条当删。
长贫子胡撰。余尝在牛溪精舍。先生曰小人閒居章如见其肺肝之语。栗谷公教之子云何。余对曰指人之视己者而言之也。
此于语类。亦无分明判决语。此条删去似当。
涪溪记闻。栗谷初以生员诣泮宫。谒先圣。闵通礼辐为掌令。訾以为沙门不许。日至晚。榜中皆失色。公神采自若。未尝少变。
乙亥蔡振后疏中所诬实本于此。此条删去似当。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25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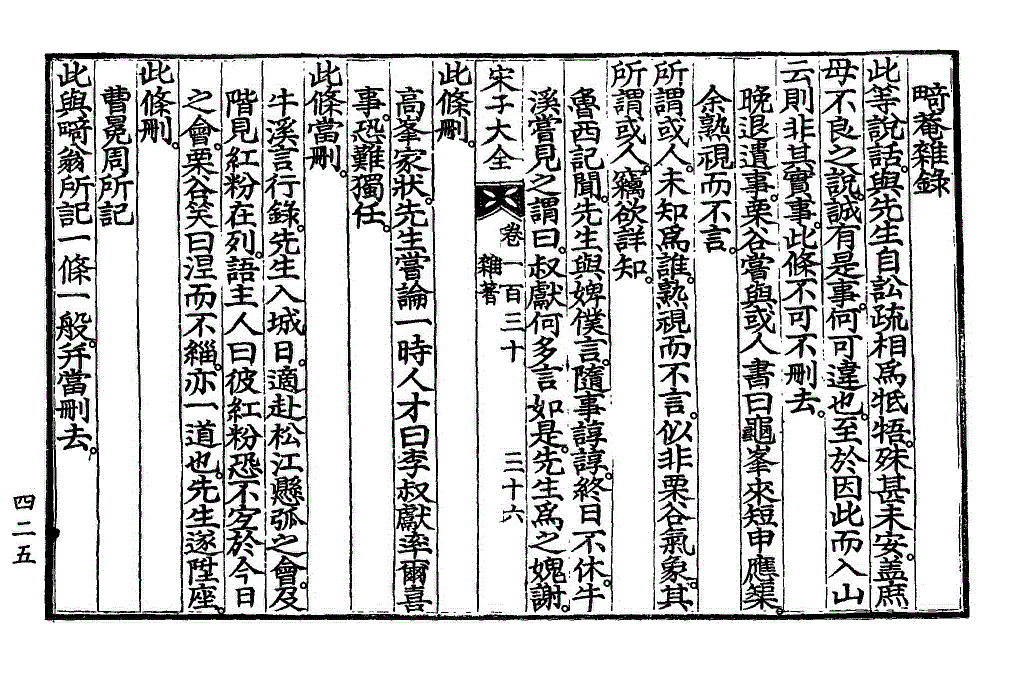 畸庵杂录
畸庵杂录此等说话。与先生自讼疏相为牴牾。殊甚未安。盖庶母不良之说。诚有是事。何可违也。至于因此而入山云则非其实事。此条不可不删去。
晚退遗事。栗谷尝与或人书曰龟峰来短申应矩。余熟视而不言。
所谓或人。未知为谁。熟视而不言。似非栗谷气象。其所谓或人。窃欲详知。
鲁西记闻。先生与婢仆言。随事谆谆。终日不休。牛溪尝见之谓曰。叔献何多言如是。先生为之愧谢。
此条删。
高峰家状。先生尝论一时人才曰李叔献率尔喜事。恐难独任。
此条当删。
牛溪言行录。先生入城日。适赴松江悬弧之会。及阶见红粉在列。语主人曰彼红粉恐不宜于今日之会。栗谷笑曰涅而不缁。亦一道也。先生遂升座。
此条删。
曹冕周所记
此与畸翁所记一条一般。并当删去。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26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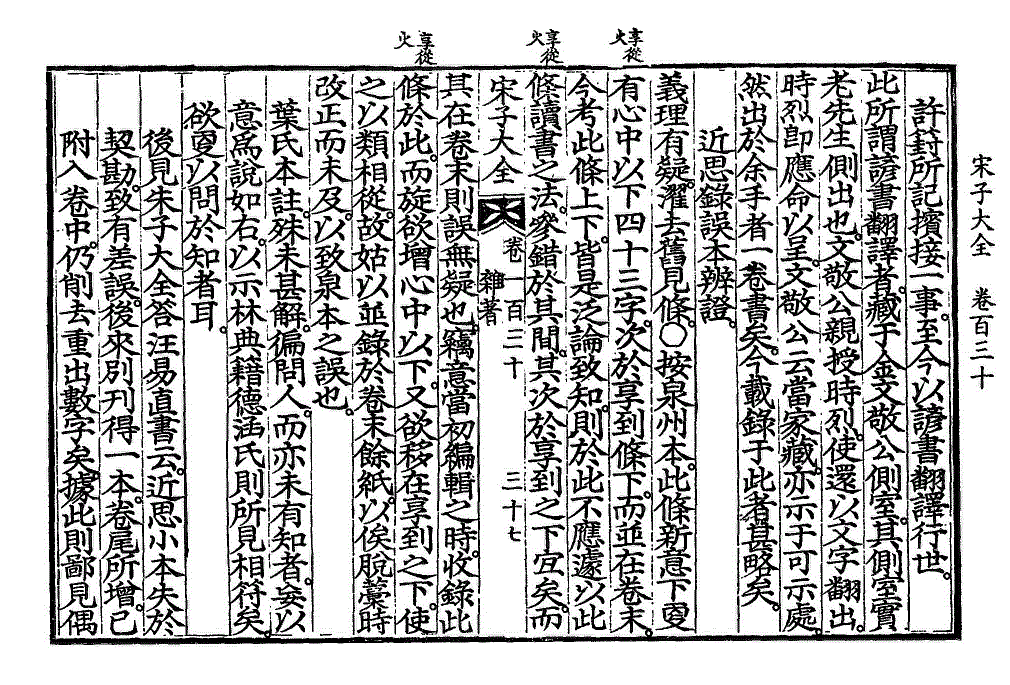 许篈所记摈接一事。至今以谚书翻译行世。
许篈所记摈接一事。至今以谚书翻译行世。此所谓谚书翻译者。藏于金文敬公侧室。其侧室实老先生侧出也。文敬公亲授时烈。使还以文字翻出。时烈即应命以呈。文敬公云当家藏。亦示于可示处。然出于余手者一卷书矣。今载录于此者甚略矣。
近思录误本辨證。
义理有疑。濯去旧见条。○按泉州本。此条新意下更有心中以下四十三字。次于享(享从火)到条下。而并在卷末。今考此条上下。皆是泛论致知。则于此不应遽以此条读书之法。参错于其间。其次于享(享从火)到之下宜矣。而其在卷末则误无疑也。窃意当初编辑之时。收录此条于此。而旋欲增心中以下。又欲移在享(享从火)到之下。使之以类相从。故姑以并录于卷末馀纸。以俟脱藁时改正而未及。以致泉本之误也。
叶氏本注。殊未甚解。遍问人。而亦未有知者。妄以意为说如右。以示林典籍德涵氏则所见相符矣。欲更以问于知者耳。
后见朱子大全答汪易直书云。近思小本失于契勘。致有差误。后来别刊得一本。卷尾所增。已附入卷中。仍削去重出数字矣。据此则鄙见偶
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 第 426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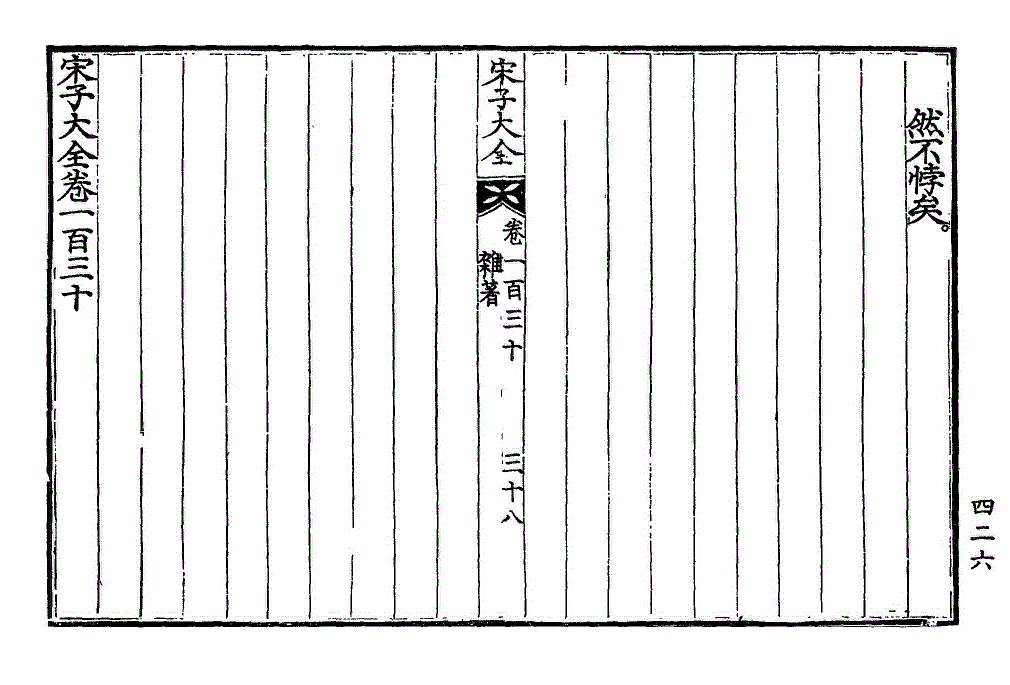 然不悖矣。
然不悖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