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明: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.org,kanripo.org, db.itkc.or.kr 和 zh.wikisource.org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x 页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
论
论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53H 页
 李泌好谈神仙诡诞论(课制)
李泌好谈神仙诡诞论(课制)臣尝读唐史。至李泌书卒下。只寂寥数语。不过曰好谈神仙诡诞。为世所轻而已。臣窃异之。私自语心曰。泌。唐之贤相也。得君如彼其专也。行乎国政。如彼其久也。功烈如彼其盛也。史氏乃书有谋略三字为褒。而以好谈神仙诡诞为贬。何也。且使泌知神仙之可谈而谈之则非智也。谓诡诞之不可谈而谈之则亦不可谓之智也。是未可知也。徐又自言曰。泌隐居衡山。山之中魁奇而迷溺者必多其人。与之游。自不觉骎骎然入于其中而然耶。久乃穷思而得之曰。如其智如其智。此泌之所以为泌。而人所难及者也。夫神仙之为虚伪。诡诞之为不经。乃寻常之人所易知者。曾谓泌之明达而不知乎此也。然且谈之不已。以至见轻于世。则其中必有所以。而众人固不识也。何者。泌初与太子为布衣交。晚被旌招。谒见灵武。常与对榻。事皆谋焉则宠厚矣。嫌疑之际。人所难处。而泌能处之父子之间。人所难言而泌能言之则迹奇矣。竭力周旋于泥露之中。终成中兴之业则功高矣。以宠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5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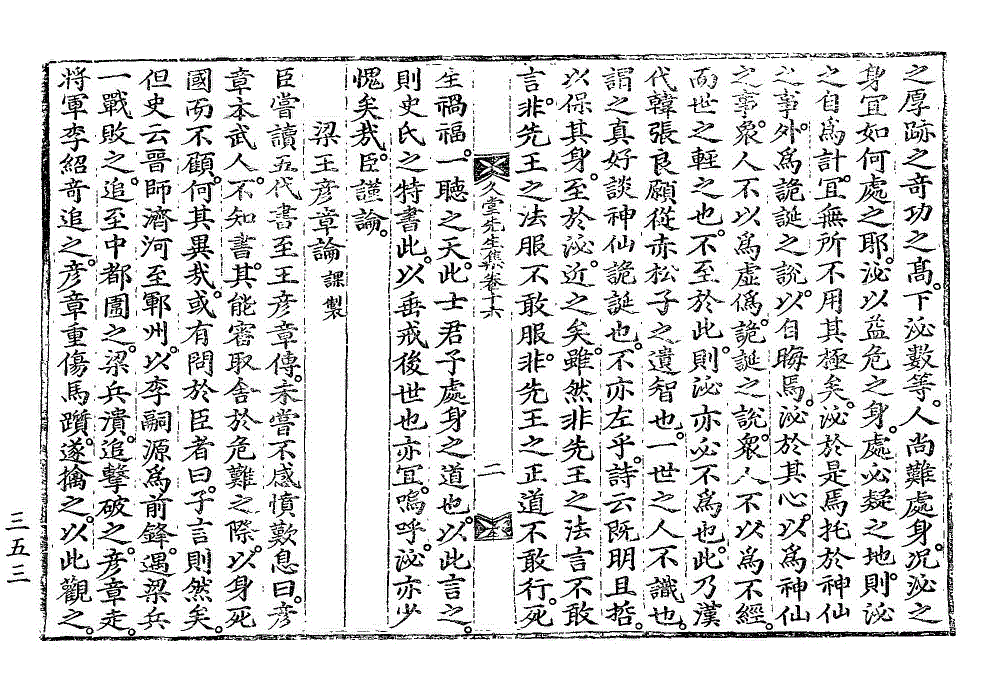 之厚迹之奇功之高。下泌数等。人尚难处身。况泌之身宜如何处之耶。泌以益危之身。处必疑之地。则泌之自为计。宜无所不用其极矣。泌于是焉托于神仙之事。外为诡诞之说。以自晦焉。泌于其心。以为神仙之事。众人不以为虚伪。诡诞之说。众人不以为不经。而世之轻之也。不至于此。则泌亦必不为也。此乃汉代韩张良愿从赤松子之遗智也。一世之人不识也。谓之真好谈神仙诡诞也。不亦左乎。诗云既明且哲。以保其身。至于泌。近之矣。虽然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。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。非先王之正道不敢行。死生祸福。一听之天。此士君子处身之道也。以此言之。则史氏之特书此。以垂戒后世也亦宜。呜呼。泌亦少愧矣哉。臣谨论。
之厚迹之奇功之高。下泌数等。人尚难处身。况泌之身宜如何处之耶。泌以益危之身。处必疑之地。则泌之自为计。宜无所不用其极矣。泌于是焉托于神仙之事。外为诡诞之说。以自晦焉。泌于其心。以为神仙之事。众人不以为虚伪。诡诞之说。众人不以为不经。而世之轻之也。不至于此。则泌亦必不为也。此乃汉代韩张良愿从赤松子之遗智也。一世之人不识也。谓之真好谈神仙诡诞也。不亦左乎。诗云既明且哲。以保其身。至于泌。近之矣。虽然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。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。非先王之正道不敢行。死生祸福。一听之天。此士君子处身之道也。以此言之。则史氏之特书此。以垂戒后世也亦宜。呜呼。泌亦少愧矣哉。臣谨论。梁王彦章论(课制)
臣尝读五代书至王彦章传。未尝不感愤叹息曰。彦章本武人。不知书。其能审取舍于危难之际。以身死国而不顾。何其异哉。或有问于臣者曰。子言则然矣。但史云晋师济河至郓州。以李嗣源为前锋。遇梁兵一战败之。追至中都围之。梁兵溃。追击破之。彦章走。将军李绍奇追之。彦章重伤马踬。遂擒之。以此观之。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54H 页
 则以王铁枪之兵而见败于斗鸡小儿。非勇也。梁兵一败而国之危。已凛凛乎无几矣。以其间走。走而见执。非忠也。为臣尽臣者。固若是乎。何子见之惑而言之易也。臣亦于此不能无疑。仰而读俯而思。徐又解之曰。呜呼噫嘻。我知之矣。其迹似矣而其情亦戚矣。何以言之。当梁之末年。主既暗懦。赵张擅权。旧臣宿将。被谗而怒。皆有怠心。而梁亦尽失河北。事势已去。诸将多怀顾望。为彦章者。以此时而为康延孝。顾不难矣。而独奋然自必。不少屈挠。则及其郓州之败而用檀公之策。岂其本心哉。于其心。不过曰以我一身之死生而国之存亡决焉。身死国乃亡。我岂若少须臾无死。以延如缕之国命哉。此所以挺身而走。欲收拾散卒。以图后效也。章章明矣。呜呼。章之言曰豹死留皮。人死留名。此岂真畏死而走者哉。当其走时。何暇念及于后人之议其迹。而后之人。亦安能尽知其志欲将以有为也。悲夫。其家传又云彦章有五子。而其二同彦章死节。其子之得于家庭观感之间者如此。则彦章之素所讲焉者。岂浅之为丈夫哉。观其答唐主之言。则其终始不屈之志。亦可知矣。不然何以后人至以铁枪名寺。而童儿牧竖。皆知王铁枪之名
则以王铁枪之兵而见败于斗鸡小儿。非勇也。梁兵一败而国之危。已凛凛乎无几矣。以其间走。走而见执。非忠也。为臣尽臣者。固若是乎。何子见之惑而言之易也。臣亦于此不能无疑。仰而读俯而思。徐又解之曰。呜呼噫嘻。我知之矣。其迹似矣而其情亦戚矣。何以言之。当梁之末年。主既暗懦。赵张擅权。旧臣宿将。被谗而怒。皆有怠心。而梁亦尽失河北。事势已去。诸将多怀顾望。为彦章者。以此时而为康延孝。顾不难矣。而独奋然自必。不少屈挠。则及其郓州之败而用檀公之策。岂其本心哉。于其心。不过曰以我一身之死生而国之存亡决焉。身死国乃亡。我岂若少须臾无死。以延如缕之国命哉。此所以挺身而走。欲收拾散卒。以图后效也。章章明矣。呜呼。章之言曰豹死留皮。人死留名。此岂真畏死而走者哉。当其走时。何暇念及于后人之议其迹。而后之人。亦安能尽知其志欲将以有为也。悲夫。其家传又云彦章有五子。而其二同彦章死节。其子之得于家庭观感之间者如此。则彦章之素所讲焉者。岂浅之为丈夫哉。观其答唐主之言。则其终始不屈之志。亦可知矣。不然何以后人至以铁枪名寺。而童儿牧竖。皆知王铁枪之名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5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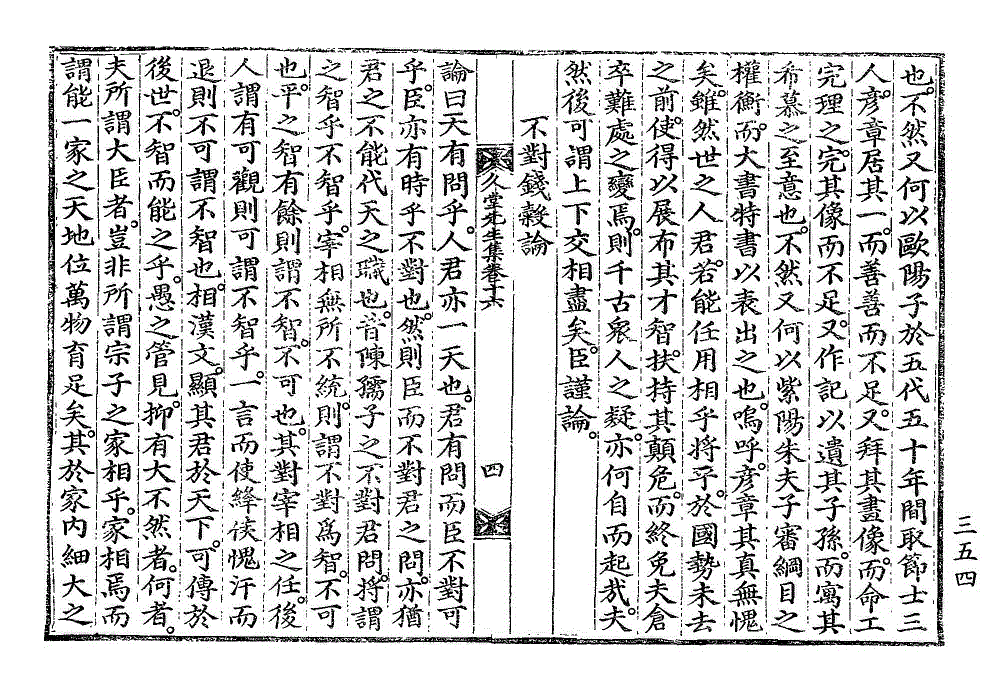 也。不然又何以欧阳子于五代五十年间取节士三人。彦章居其一。而善善而不足。又拜其画像。而命工完理之。完其像而不足。又作记以遗其子孙。而寓其希慕之至意也。不然又何以紫阳朱夫子审纲目之权衡。而大书特书以表出之也。呜呼。彦章其真无愧矣。虽然世之人君。若能任用相乎将乎。于国势未去之前。使得以展布其才智。扶持其颠危。而终免夫仓卒难处之变焉。则千古众人之疑。亦何自而起哉。夫然后可谓上下交相尽矣。臣谨论。
也。不然又何以欧阳子于五代五十年间取节士三人。彦章居其一。而善善而不足。又拜其画像。而命工完理之。完其像而不足。又作记以遗其子孙。而寓其希慕之至意也。不然又何以紫阳朱夫子审纲目之权衡。而大书特书以表出之也。呜呼。彦章其真无愧矣。虽然世之人君。若能任用相乎将乎。于国势未去之前。使得以展布其才智。扶持其颠危。而终免夫仓卒难处之变焉。则千古众人之疑。亦何自而起哉。夫然后可谓上下交相尽矣。臣谨论。不对钱谷论
论曰天有问乎。人君亦一天也。君有问而臣不对可乎。臣亦有时乎不对也。然则臣而不对君之问。亦犹君之不能代天之职也。昔陈孺子之不对君问。将谓之智乎不智乎。宰相无所不统。则谓不对为智。不可也。平之智有馀则谓不智。不可也。其对宰相之任。后人谓有可观则可谓不智乎。一言而使缝侯愧汗而退则不可谓不智也。相汉文。显其君于天下。可传于后世。不智而能之乎。愚之管见。抑有大不然者。何者。夫所谓大臣者。岂非所谓宗子之家相乎。家相焉而谓能一家之天地位万物育足矣。其于家内细大之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55H 页
 务。有不知也。而曰我能是职焉。则其智不智。不待智者而辨之矣。匹夫也一家也。犹且如此。则况于天下乎。所以辅佐大君。纲纪众事。大臣而已。四海之广。百责之萃。孰非吾度内。而其事之重且大。如钱谷之出入。国用之本也。决狱之多寡。民命之所系也。宰相不与焉。而曰我则理阴阳顺四时职耳。使天子责之曰各有主者。然则唐虞康哉之咏。周家任相之意。岂亶使然哉。使平而知此则是乃吾夫子所谓管子知礼之类也。谓其不智乎则不对是也。其所对之言。亦不几于孟子所谓又从而为之辞者乎。况乎乐尧舜而亲见伊尹之所以相汤也。学古入官。傅说之所以相高宗也。道学之同不同。固不可比拟于平也。平之相业本末轻重。若是其芒芒然。则愚未知平之平日。所读何书而所学何事耶。先儒云汉相失职。自平始。其有见于此乎。所可惜者。秦相之职分。盖由于焚裂周官。将古人所以体统维持之具。分散四出。众职既分。大臣莫统。而一世之人。胶于见闻之陋。醉生梦死。为法之萧。代萧之曹。亦所不免。则三代以上之人规模事业。亦何可责之于平乎。所可责者。代天理物。君逸臣劳。岂非人君之任乎。而文帝以汤武以上之资。履
务。有不知也。而曰我能是职焉。则其智不智。不待智者而辨之矣。匹夫也一家也。犹且如此。则况于天下乎。所以辅佐大君。纲纪众事。大臣而已。四海之广。百责之萃。孰非吾度内。而其事之重且大。如钱谷之出入。国用之本也。决狱之多寡。民命之所系也。宰相不与焉。而曰我则理阴阳顺四时职耳。使天子责之曰各有主者。然则唐虞康哉之咏。周家任相之意。岂亶使然哉。使平而知此则是乃吾夫子所谓管子知礼之类也。谓其不智乎则不对是也。其所对之言。亦不几于孟子所谓又从而为之辞者乎。况乎乐尧舜而亲见伊尹之所以相汤也。学古入官。傅说之所以相高宗也。道学之同不同。固不可比拟于平也。平之相业本末轻重。若是其芒芒然。则愚未知平之平日。所读何书而所学何事耶。先儒云汉相失职。自平始。其有见于此乎。所可惜者。秦相之职分。盖由于焚裂周官。将古人所以体统维持之具。分散四出。众职既分。大臣莫统。而一世之人。胶于见闻之陋。醉生梦死。为法之萧。代萧之曹。亦所不免。则三代以上之人规模事业。亦何可责之于平乎。所可责者。代天理物。君逸臣劳。岂非人君之任乎。而文帝以汤武以上之资。履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55L 页
 让三让再之位。天工人代。岂或昧焉。而其命相之举。徒袭秦之敝。使四海三代之遗民。终不得蒙至治之泽。呜呼。岂非世道之一大不幸也欤。虽然三代以后小康之世。必称汉文。汉文平之志。已见于社下。则亦岂可少之哉。谨论。
让三让再之位。天工人代。岂或昧焉。而其命相之举。徒袭秦之敝。使四海三代之遗民。终不得蒙至治之泽。呜呼。岂非世道之一大不幸也欤。虽然三代以后小康之世。必称汉文。汉文平之志。已见于社下。则亦岂可少之哉。谨论。解剑悬墓论(甲戌别试初试入格)
论曰谨按昔有吴延陵季子。聘于鲁。路于徐。徐君好季子之剑而口不敢请。季子知徐君之好其剑。而为使上国。未敢为献。盖先许以心也。及其还也。徐君已死。季子乃解其剑。悬之徐君墓树而去。是终不欺心也。或曰人之所难许者心也。人之所易欺者亦心也。而季子既能许其心。又能不欺其心。则非至信而能如是乎。曰吴君传位于兄弟。而季子让位。愿附子臧之义。鲁有天子礼乐。而季子之鲁。思观六代之仪。则若季子者。可谓高矣。然则悬剑之举。盖又有深意也。岂徒许其心。而又不欺其心者乎。然则曷为而悬其剑。曰立天下之名也。破其主之疑也。非专意于示其信也。或曰季子于徐君之生也。不解其剑者。为途路防身之无物也。及徐君之死也。乃悬其剑者。以肝胆许人以知己也。此所谓辟金之信也。曷谓立名。曷谓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56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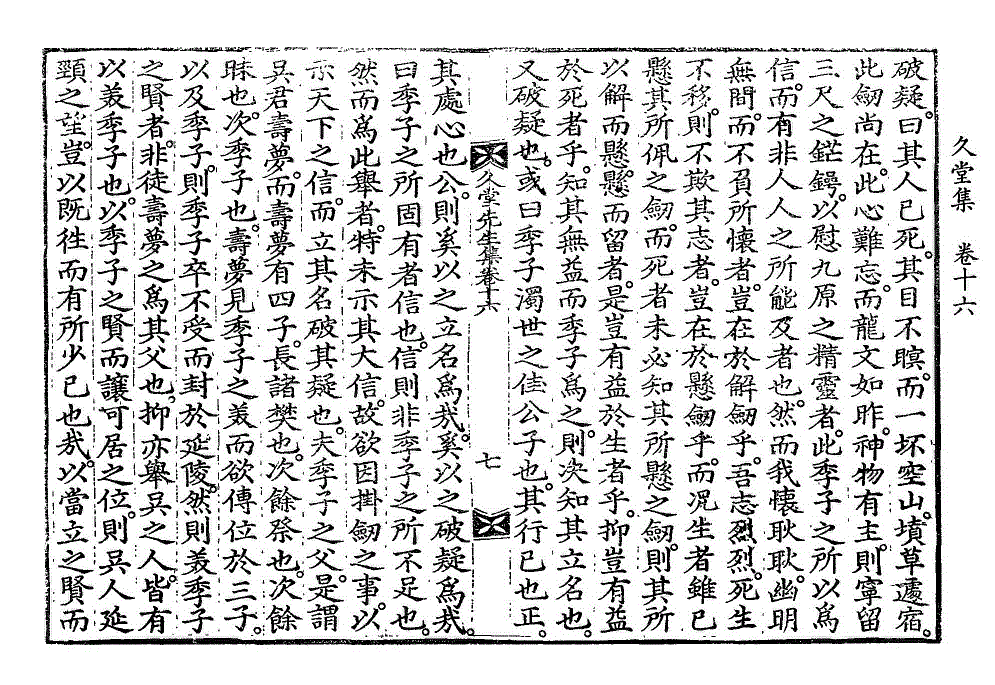 破疑。曰其人已死。其目不瞑。而一坏空山。坟草遽宿。此剑尚在。此心难忘。而龙文如昨。神物有主。则宁留三尺之铓锷。以慰九原之精灵者。此季子之所以为信。而有非人人之所能及者也。然而我怀耿耿。幽明无间。而不负所怀者。岂在于解剑乎。吾志烈烈。死生不移。则不欺其志者。岂在于悬剑乎。而况生者虽已悬其所佩之剑。而死者未必知其所悬之剑。则其所以解而悬。悬而留者。是岂有益于生者乎。抑岂有益于死者乎。知其无益而季子为之。则决知其立名也。又破疑也。或曰季子浊世之佳公子也。其行己也正。其处心也公。则奚以之立名为哉。奚以之破疑为哉。曰季子之所固有者信也。信则非季子之所不足也。然而为此举者。特未示其大信。故欲因挂剑之事。以示天下之信。而立其名破其疑也。夫季子之父。是谓吴君寿梦。而寿梦有四子。长诸樊也。次馀祭也。次馀昧也。次季子也。寿梦见季子之美而欲传位于三子。以及季子。则季子卒不受而封于延陵。然则美季子之贤者。非徒寿梦之为其父也。抑亦举吴之人。皆有以美季子也。以季子之贤而让可居之位。则吴人延颈之望。岂以既往而有所少已也哉。以当立之贤而
破疑。曰其人已死。其目不瞑。而一坏空山。坟草遽宿。此剑尚在。此心难忘。而龙文如昨。神物有主。则宁留三尺之铓锷。以慰九原之精灵者。此季子之所以为信。而有非人人之所能及者也。然而我怀耿耿。幽明无间。而不负所怀者。岂在于解剑乎。吾志烈烈。死生不移。则不欺其志者。岂在于悬剑乎。而况生者虽已悬其所佩之剑。而死者未必知其所悬之剑。则其所以解而悬。悬而留者。是岂有益于生者乎。抑岂有益于死者乎。知其无益而季子为之。则决知其立名也。又破疑也。或曰季子浊世之佳公子也。其行己也正。其处心也公。则奚以之立名为哉。奚以之破疑为哉。曰季子之所固有者信也。信则非季子之所不足也。然而为此举者。特未示其大信。故欲因挂剑之事。以示天下之信。而立其名破其疑也。夫季子之父。是谓吴君寿梦。而寿梦有四子。长诸樊也。次馀祭也。次馀昧也。次季子也。寿梦见季子之美而欲传位于三子。以及季子。则季子卒不受而封于延陵。然则美季子之贤者。非徒寿梦之为其父也。抑亦举吴之人。皆有以美季子也。以季子之贤而让可居之位。则吴人延颈之望。岂以既往而有所少已也哉。以当立之贤而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56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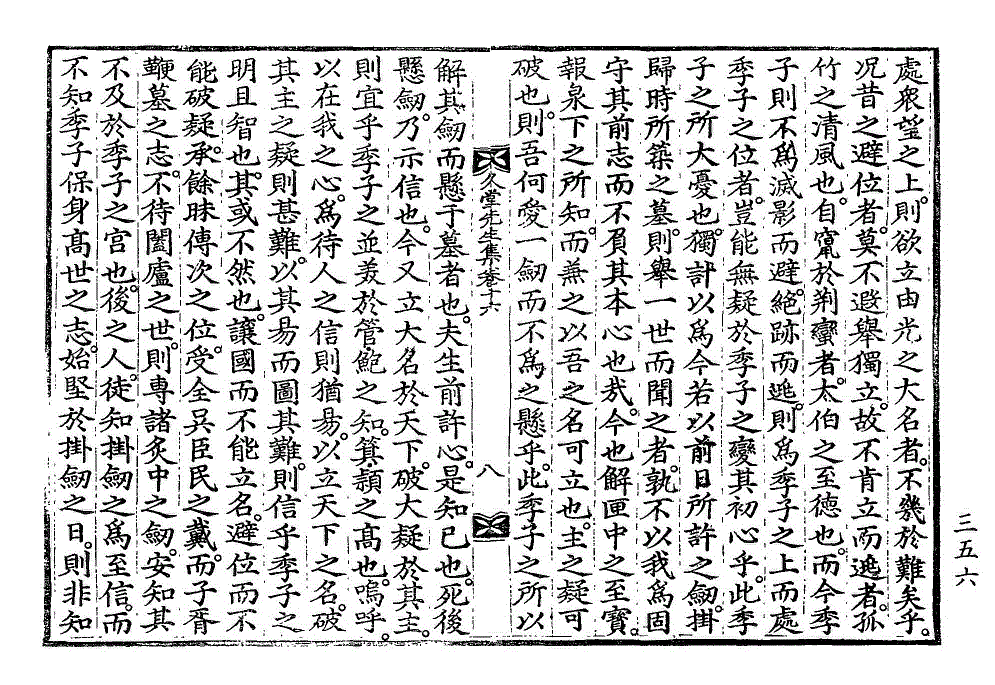 处众望之上。则欲立由光之大名者。不几于难矣乎。况昔之避位者。莫不遐举独立。故不肯立而逃者。孤竹之清风也。自窜于荆蛮者。太伯之至德也。而今季子则不为灭影而避。绝迹而逃。则为季子之上而处季子之位者。岂能无疑于季子之变其初心乎。此季子之所大忧也。独计以为今若以前日所许之剑。挂归时所筑之墓。则举一世而闻之者。孰不以我为固守其前志而不负其本心也哉。今也解匣中之至宝。报泉下之所知。而兼之以吾之名可立也。主之疑可破也。则吾何爱一剑而不为之悬乎。此季子之所以解其剑而悬于墓者也。夫生前许心。是知己也。死后悬剑。乃示信也。今又立大名于天下。破大疑于其主。则宜乎季子之并美于管,鲍之知。箕,颖之高也。呜呼。以在我之心。为待人之信则犹易。以立天下之名。破其主之疑则甚难。以其易而图其难。则信乎季子之明且智也。其或不然也。让国而不能立名。避位而不能破疑。承馀昧传次之位。受全吴臣民之戴。而子胥鞭墓之志。不待阖庐之世。则专诸炙中之剑。安知其不及于季子之宫也。后之人。徒知挂剑之为至信。而不知季子保身高世之志。始坚于挂剑之日。则非知
处众望之上。则欲立由光之大名者。不几于难矣乎。况昔之避位者。莫不遐举独立。故不肯立而逃者。孤竹之清风也。自窜于荆蛮者。太伯之至德也。而今季子则不为灭影而避。绝迹而逃。则为季子之上而处季子之位者。岂能无疑于季子之变其初心乎。此季子之所大忧也。独计以为今若以前日所许之剑。挂归时所筑之墓。则举一世而闻之者。孰不以我为固守其前志而不负其本心也哉。今也解匣中之至宝。报泉下之所知。而兼之以吾之名可立也。主之疑可破也。则吾何爱一剑而不为之悬乎。此季子之所以解其剑而悬于墓者也。夫生前许心。是知己也。死后悬剑。乃示信也。今又立大名于天下。破大疑于其主。则宜乎季子之并美于管,鲍之知。箕,颖之高也。呜呼。以在我之心。为待人之信则犹易。以立天下之名。破其主之疑则甚难。以其易而图其难。则信乎季子之明且智也。其或不然也。让国而不能立名。避位而不能破疑。承馀昧传次之位。受全吴臣民之戴。而子胥鞭墓之志。不待阖庐之世。则专诸炙中之剑。安知其不及于季子之宫也。后之人。徒知挂剑之为至信。而不知季子保身高世之志。始坚于挂剑之日。则非知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5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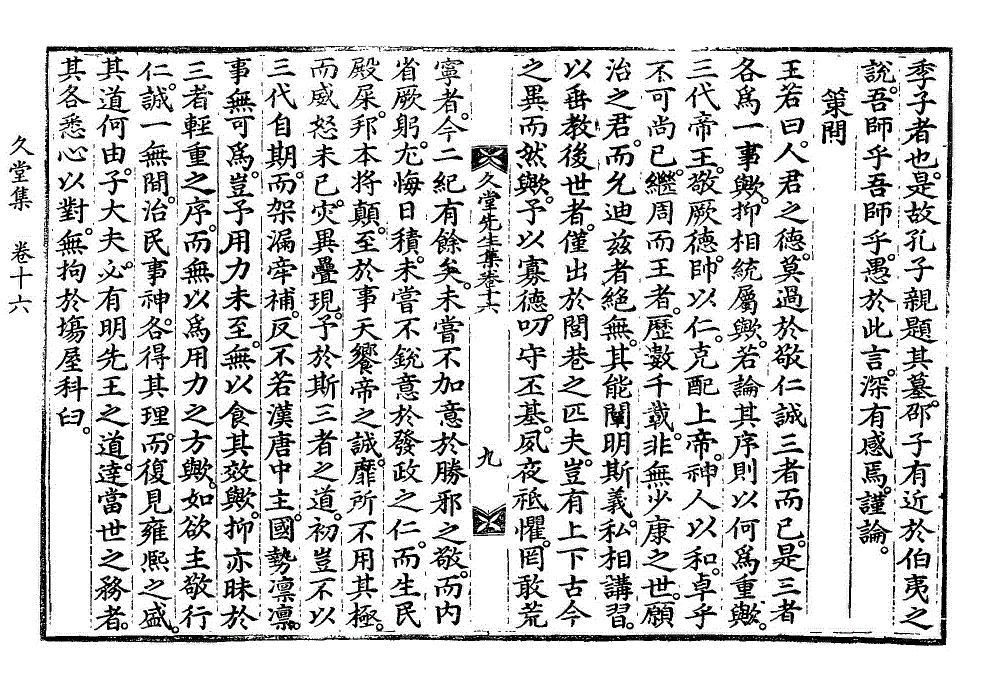 季子者也。是故孔子亲题其墓。邵子有近于伯夷之说。吾师乎吾师乎。愚于此言。深有感焉。谨论。
季子者也。是故孔子亲题其墓。邵子有近于伯夷之说。吾师乎吾师乎。愚于此言。深有感焉。谨论。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
策问
[敬仁诚]
王若曰。人君之德。莫过于敬仁诚三者而已。是三者各为一事欤。抑相统属欤。若论其序则以何为重欤。三代帝王。敬厥德。帅以仁。克配上帝。神人以和。卓乎不可尚已。继周而王者。历数千载。非无少康之世。愿治之君。而允迪玆者绝无。其能阐明斯义。私相讲习。以垂教后世者。仅出于闾巷之匹夫。岂有上下古今之异而然欤。予以寡德。叨守丕基。夙夜祗惧。罔敢荒宁者。今二纪有馀矣。未尝不加意于胜邪之敬。而内省厥躬。尤悔日积。未尝不锐意于发政之仁。而生民殿屎。邦本将颠。至于事天飨帝之诚。靡所不用其极。而威怒未已。灾异叠现。予于斯三者之道。初岂不以三代自期。而架漏牵补。反不若汉唐中主。国势凛凛。事无可为。岂予用力未至。无以食其效欤。抑亦昧于三者轻重之序。而无以为用力之方欤。如欲主敬行仁。诚一无间。治民事神。各得其理。而复见雍熙之盛。其道何由。子大夫。必有明先王之道。达当世之务者。其各悉心以对。无拘于场屋科臼。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57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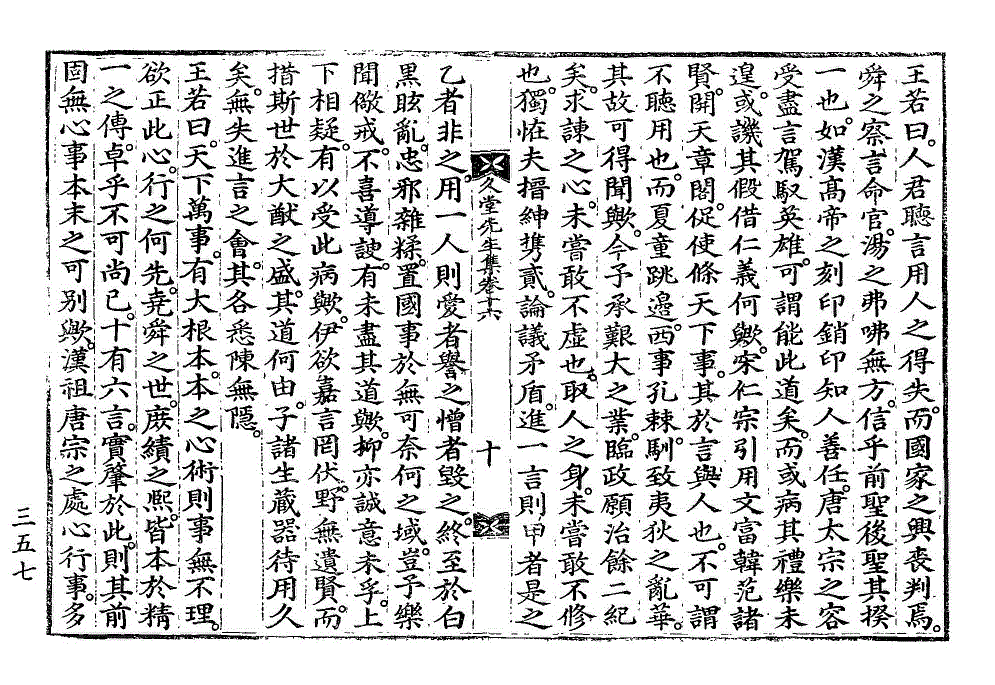 [听言用人]
[听言用人]王若曰。人君听言用人之得失。而国家之兴丧判焉。舜之察言命官。汤之弗咈无方。信乎前圣后圣其揆一也。如汉高帝之刻印销印知人善任。唐太宗之容受尽言驾驭英雄。可谓能此道矣。而或病其礼乐未遑。或讥其假借仁义何欤。宋仁宗引用文富韩范诸贤。开天章阁。促使条天下事。其于言与人也。不可谓不听用也。而夏童跳边。西事孔棘。驯致夷狄之乱华。其故可得闻欤。今予承艰大之业。临政愿治馀二纪矣。求谏之心。未尝敢不虚也。取人之身。未尝敢不修也。独怪夫搢绅携贰。论议矛盾。进一言则甲者是之乙者非之。用一人则爱者誉之憎者毁之。终至于白黑眩乱。忠邪杂糅。置国事于无可奈何之域。岂予乐闻儆戒。不喜导谀。有未尽其道欤。抑亦诚意未孚。上下相疑。有以受此病欤。伊欲嘉言罔伏。野无遗贤。而措斯世于大猷之盛。其道何由。子诸生藏器待用久矣。无失进言之会。其各悉陈无隐。
[心术]
王若曰。天下万事。有大根本。本之心术则事无不理。欲正此心。行之何先。尧舜之世。庶绩之熙。皆本于精一之传。卓乎不可尚已。十有六言。实肇于此。则其前固无心事本末之可别欤。汉祖唐宗之处心行事。多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58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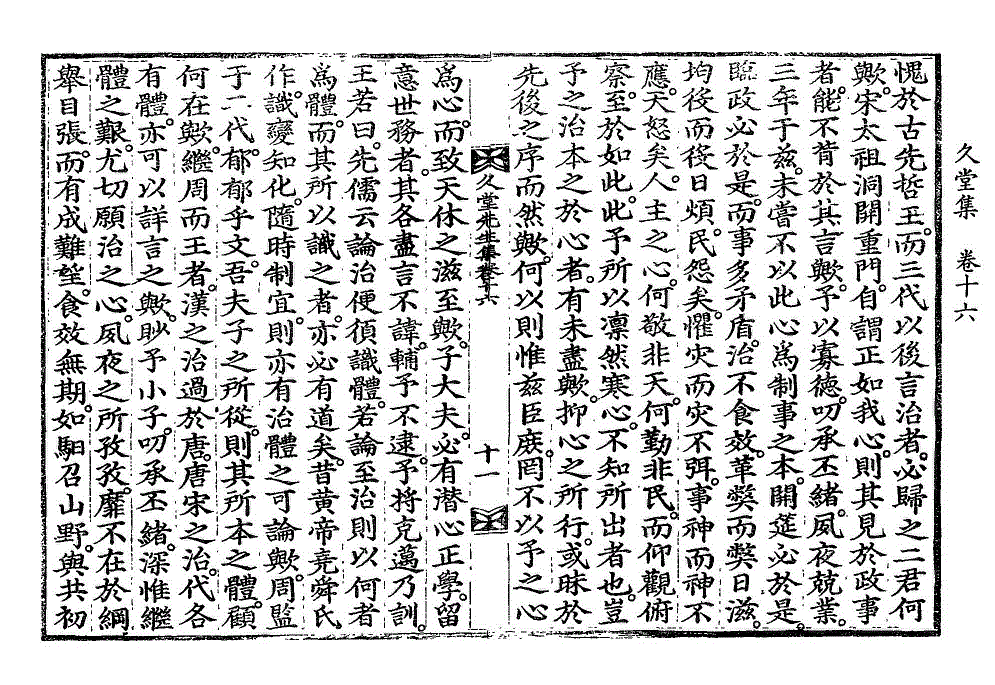 愧于古先哲王。而三代以后言治者。必归之二君何欤。宋太祖洞开重门。自谓正如我心。则其见于政事者。能不背于其言欤。予以寡德。叨承丕绪。夙夜兢业。三年于兹。未尝不以此心为制事之本。开筵必于是。临政必于是。而事多矛盾。治不食效。革弊而弊日滋。均役而役日烦。民怨矣。惧灾而灾不弭。事神而神不应。天怒矣。人主之心。何敬非天。何勤非民。而仰观俯察。至于如此。此予所以凛然寒心。不知所出者也。岂予之治本之于心者。有未尽欤。抑心之所行。或昧于先后之序而然欤。何以则惟兹臣庶。罔不以予之心为心。而致天休之滋至欤。子大夫。必有潜心正学。留意世务者。其各尽言不讳。辅予不逮。予将克迈乃训。
愧于古先哲王。而三代以后言治者。必归之二君何欤。宋太祖洞开重门。自谓正如我心。则其见于政事者。能不背于其言欤。予以寡德。叨承丕绪。夙夜兢业。三年于兹。未尝不以此心为制事之本。开筵必于是。临政必于是。而事多矛盾。治不食效。革弊而弊日滋。均役而役日烦。民怨矣。惧灾而灾不弭。事神而神不应。天怒矣。人主之心。何敬非天。何勤非民。而仰观俯察。至于如此。此予所以凛然寒心。不知所出者也。岂予之治本之于心者。有未尽欤。抑心之所行。或昧于先后之序而然欤。何以则惟兹臣庶。罔不以予之心为心。而致天休之滋至欤。子大夫。必有潜心正学。留意世务者。其各尽言不讳。辅予不逮。予将克迈乃训。[治体]
王若曰。先儒云论治便须识体。若论至治则以何者为体。而其所以识之者。亦必有道矣。昔黄帝,尧舜氏作。识变知化。随时制宜。则亦有治体之可论欤。周监于二代。郁郁乎文。吾夫子之所从。则其所本之体。顾何在欤。继周而王者。汉之治过于唐。唐宋之治。代各有体。亦可以详言之欤。眇予小子。叨承丕绪。深惟继体之艰。尤切愿治之心。夙夜之所孜孜。靡不在于纲举目张。而有成难望。食效无期。如驲召山野。与共初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58L 页
 政。待贤之体也。登崇耆哲。总理百官。择相之体也。虚心求谏。量材授任。听言用人之体也。引见守宰。复设常参。养民立政之体也。至于四维之张。国之大体也。予于兹前七者之体。亦不可谓不尽心焉耳矣。贤路不辟而体统日坏。忠言不闻而庶绩日隳。民心离而政归于文具。礼让扫而弊极于不可救。岂予图治而未得其体欤。亦尝论之。而其所以识之者。有未尽其道欤。抑别有要道急务。可以求之于体之外者欤。何以则立经陈纪。治具毕张。而致三代从欲之美欤。子大夫。体究经学。必有抱道而欲言者矣。其体予意。悉陈无隐。
政。待贤之体也。登崇耆哲。总理百官。择相之体也。虚心求谏。量材授任。听言用人之体也。引见守宰。复设常参。养民立政之体也。至于四维之张。国之大体也。予于兹前七者之体。亦不可谓不尽心焉耳矣。贤路不辟而体统日坏。忠言不闻而庶绩日隳。民心离而政归于文具。礼让扫而弊极于不可救。岂予图治而未得其体欤。亦尝论之。而其所以识之者。有未尽其道欤。抑别有要道急务。可以求之于体之外者欤。何以则立经陈纪。治具毕张。而致三代从欲之美欤。子大夫。体究经学。必有抱道而欲言者矣。其体予意。悉陈无隐。[内修外攘]
王若曰。先儒云内修外攘。譬如直内方外。直方之于修攘。精粗本末。疑若有异。而譬而同之。果何意欤。稽于古。心传精一。政本于心。而顽苗来格。能此道者。其惟舜乎。周宣中兴。克尽修攘之道。则诗之所称。亦举敬义之实欤。自兹以降。所谓彼善于此者。汉武之漠南无庭。唐宗之胡越一家。可谓能外攘矣。此亦有内修之本而致之欤。以仁厚有馀之宋。又得仁宗而为之君。庆历之治。亦不可不谓之内修。而夏童跳边。军旅累兴。其所以不能外攘者何欤。予自忝位以来。兢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59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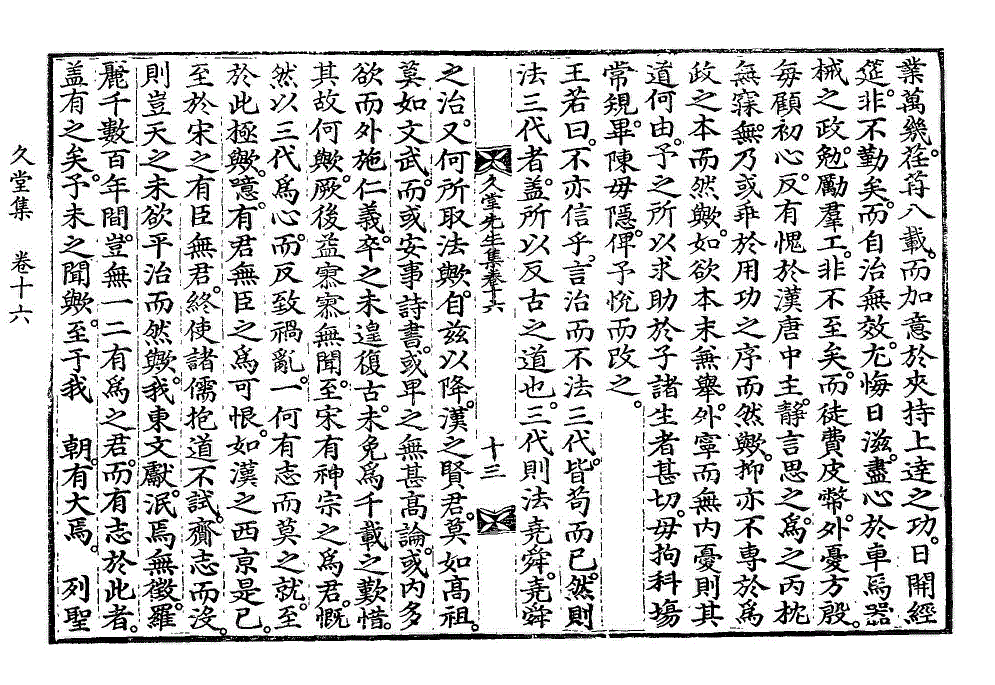 业万几。荏苒八载。而加意于夹持上达之功。日开经筵。非不勤矣。而自治无效。尤悔日滋。尽心于车马器械之政。勉励群工。非不至矣。而徒费皮币。外忧方殷。每顾初心。反有愧于汉唐中主。静言思之。为之丙枕无寐。无乃或乖于用功之序而然欤。抑亦不专于为政之本而然欤。如欲本末兼举。外宁而无内忧则其道何由。予之所以求助于子诸生者甚切。毋拘科场常规。毕陈毋隐。俾予悦而改之。
业万几。荏苒八载。而加意于夹持上达之功。日开经筵。非不勤矣。而自治无效。尤悔日滋。尽心于车马器械之政。勉励群工。非不至矣。而徒费皮币。外忧方殷。每顾初心。反有愧于汉唐中主。静言思之。为之丙枕无寐。无乃或乖于用功之序而然欤。抑亦不专于为政之本而然欤。如欲本末兼举。外宁而无内忧则其道何由。予之所以求助于子诸生者甚切。毋拘科场常规。毕陈毋隐。俾予悦而改之。[法三代]
王若曰。不亦信乎。言治而不法三代。皆苟而已。然则法三代者。盖所以反古之道也。三代则法尧舜。尧舜之治。又何所取法欤。自兹以降。汉之贤君。莫如高祖。莫如文武。而或安事诗书。或卑之无甚高论。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。卒之未遑复古。未免为千载之叹惜。其故何欤。厥后益寥寥无闻。至宋有神宗之为君。慨然以三代为心。而反致祸乱。一何有志而莫之就。至于此极欤。噫。有君无臣之为可恨。如汉之西京是已。至于宋之有臣无君。终使诸儒抱道不试。赍志而没。则岂天之未欲平治而然欤。我东文献。泯焉无徵。罗丽千数百年间。岂无一二有为之君。而有志于此者。盖有之矣。予未之闻欤。至于我 朝。有大焉。 列圣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5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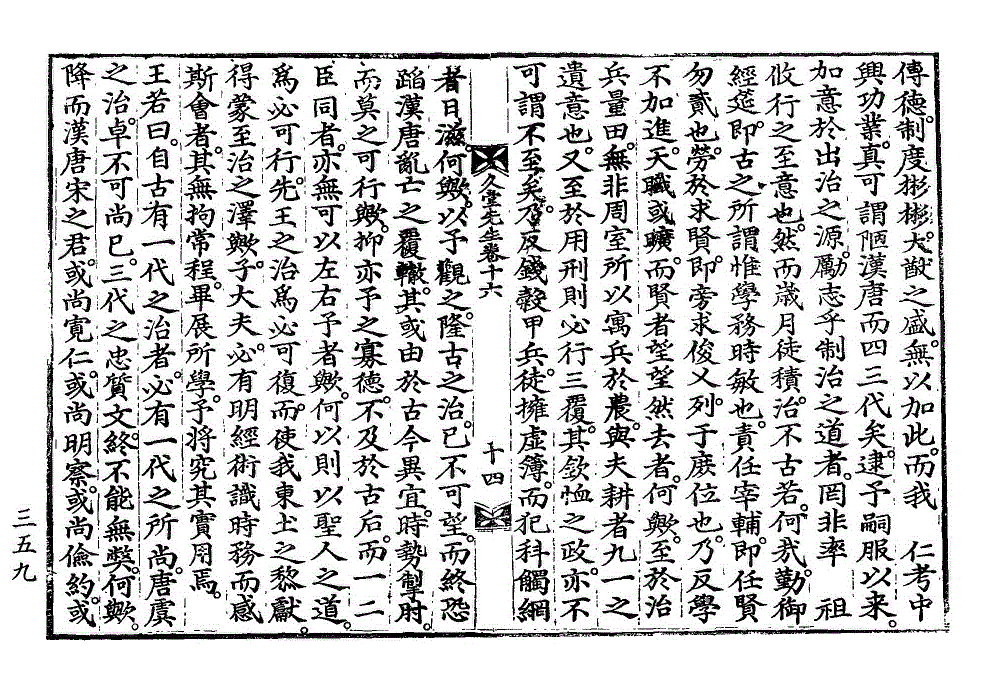 传德。制度彬彬。大猷之盛。无以加此。而我 仁考中兴功业。真可谓陋汉唐而四三代矣。逮予嗣服以来。加意于出治之源。励志乎制治之道者。罔非率 祖攸行之至意也。然而岁月徒积。治不古若。何哉。勤御经筵。即古之所谓惟学务时敏也。责任宰辅。即任贤勿贰也。劳于求贤。即旁求俊乂。列于庶位也。乃反学不加进。天职或旷。而贤者望望然去者。何欤。至于治兵量田。无非周室所以寓兵于农。与夫耕者九一之遗意也。又至于用刑则必行三覆。其钦恤之政。亦不可谓不至矣。乃反钱谷甲兵。徒拥虚簿。而犯科触网者日滋。何欤。以予观之。隆古之治。已不可望。而终恐蹈汉唐乱亡之覆辙。其或由于古今异宜。时势掣肘。而莫之可行欤。抑亦予之寡德。不及于古后。而一二臣同者。亦无可以左右予者欤。何以则以圣人之道。为必可行。先王之治为必可复。而使我东土之黎献。得蒙至治之泽欤。子大夫。必有明经术识时务而感斯会者。其无拘常程。毕展所学。予将究其实用焉。
传德。制度彬彬。大猷之盛。无以加此。而我 仁考中兴功业。真可谓陋汉唐而四三代矣。逮予嗣服以来。加意于出治之源。励志乎制治之道者。罔非率 祖攸行之至意也。然而岁月徒积。治不古若。何哉。勤御经筵。即古之所谓惟学务时敏也。责任宰辅。即任贤勿贰也。劳于求贤。即旁求俊乂。列于庶位也。乃反学不加进。天职或旷。而贤者望望然去者。何欤。至于治兵量田。无非周室所以寓兵于农。与夫耕者九一之遗意也。又至于用刑则必行三覆。其钦恤之政。亦不可谓不至矣。乃反钱谷甲兵。徒拥虚簿。而犯科触网者日滋。何欤。以予观之。隆古之治。已不可望。而终恐蹈汉唐乱亡之覆辙。其或由于古今异宜。时势掣肘。而莫之可行欤。抑亦予之寡德。不及于古后。而一二臣同者。亦无可以左右予者欤。何以则以圣人之道。为必可行。先王之治为必可复。而使我东土之黎献。得蒙至治之泽欤。子大夫。必有明经术识时务而感斯会者。其无拘常程。毕展所学。予将究其实用焉。[治与所尚]
王若曰。自古有一代之治者。必有一代之所尚。唐虞之治。卓不可尚已。三代之忠质文。终不能无弊。何欤。降而汉唐宋之君。或尚宽仁。或尚明察。或尚俭约。或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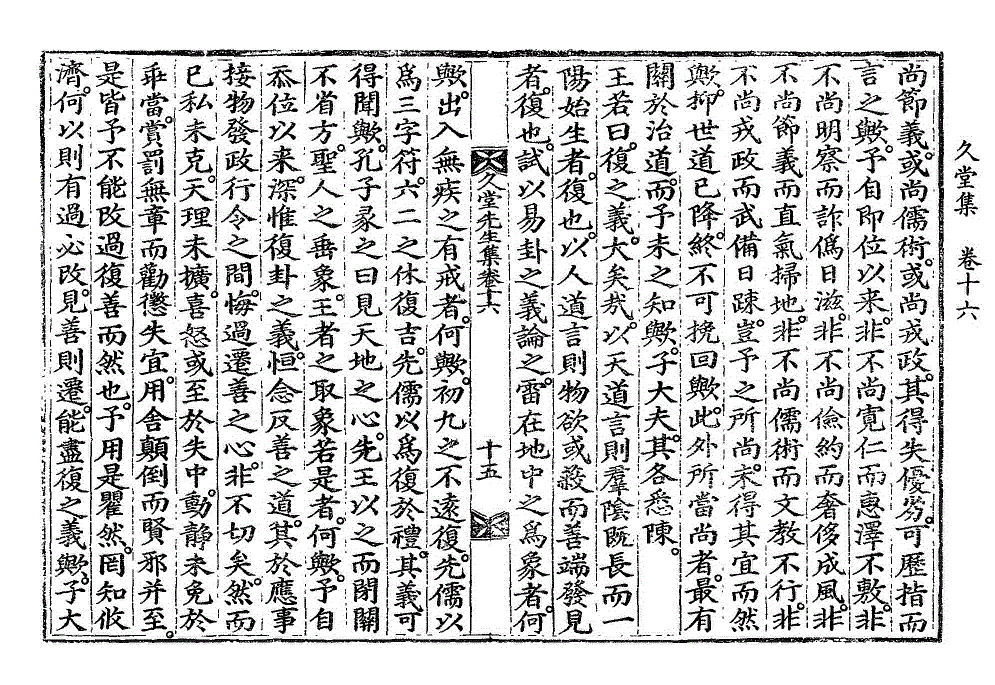 尚节义。或尚儒术。或尚戎政。其得失优劣。可历指而言之欤。予自即位以来。非不尚宽仁而惠泽不敷。非不尚明察而诈伪日滋。非不尚俭约而奢侈成风。非不尚节义而直气扫地。非不尚儒术而文教不行。非不尚戎政而武备日疏。岂予之所尚。未得其宜而然欤。抑世道已降。终不可挽回欤。此外所当尚者。最有关于治道。而予未之知欤。子大夫。其各悉陈。
尚节义。或尚儒术。或尚戎政。其得失优劣。可历指而言之欤。予自即位以来。非不尚宽仁而惠泽不敷。非不尚明察而诈伪日滋。非不尚俭约而奢侈成风。非不尚节义而直气扫地。非不尚儒术而文教不行。非不尚戎政而武备日疏。岂予之所尚。未得其宜而然欤。抑世道已降。终不可挽回欤。此外所当尚者。最有关于治道。而予未之知欤。子大夫。其各悉陈。[复之义]
王若曰。复之义。大矣哉。以天道言则群阴既长而一阳始生者。复也。以人道言则物欲或蔽而善端发见者。复也。试以易卦之义论之。雷在地中之为象者。何欤。出入无疾之有戒者。何欤。初九之不远复。先儒以为三字符。六二之休复吉。先儒以为复于礼。其义可得闻欤。孔子彖之曰见天地之心。先王以之而闭关不省方。圣人之垂象。王者之取象若是者。何欤。予自忝位以来。深惟复卦之义。恒念反善之道。其于应事接物发政行令之间。悔过迁善之心。非不切矣。然而己私未克。天理未扩。喜怒或至于失中。动静未免于乖当。赏罚无章而劝惩失宜。用舍颠倒而贤邪并至。是皆予不能改过复善而然也。予用是瞿然。罔知攸济。何以则有过必改。见善则迁。能尽复之义欤。子大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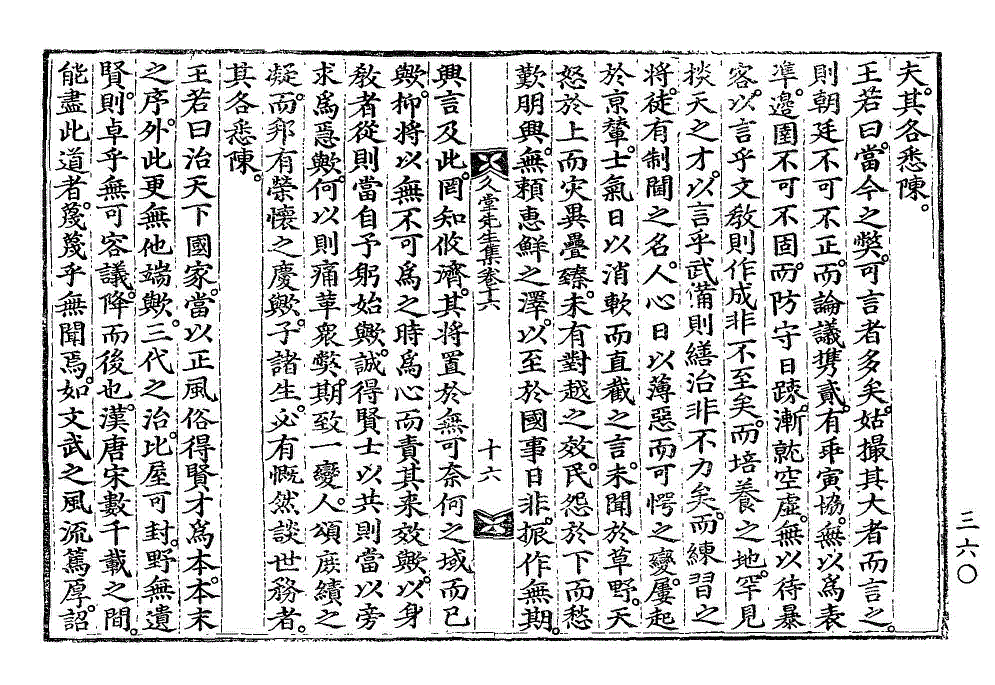 夫。其各悉陈。
夫。其各悉陈。[革弊]
王若曰。当今之弊。可言者多矣。姑撮其大者而言之。则朝廷不可不正。而论议携贰。有乖寅协。无以为表准。边圉不可不固。而防守日疏。渐就空虚。无以待暴客。以言乎文教则作成非不至矣。而培养之地。罕见掞天之才。以言乎武备则缮治非不力矣。而练习之将。徒有制阃之名。人心日以薄恶而可愕之变。屡起于京辇。士气日以消软而直截之言。未闻于草野。天怒于上而灾异叠臻。未有对越之效。民怨于下而愁叹朋兴。无赖惠鲜之泽。以至于国事日非。振作无期。兴言及此。罔知攸济。其将置于无可奈何之域而已欤。抑将以无不可为之时为心而责其来效欤。以身教者从则当自予躬始欤。诚得贤士以共则当以旁求为急欤。何以则痛革众弊。期致一变。人颂庶绩之凝。而邦有荣怀之庆欤。子诸生。必有慨然谈世务者。其各悉陈。
[正风俗得贤才]
王若曰治天下国家。当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。本末之序。外此更无他端欤。三代之治。比屋可封。野无遗贤。则卓乎无可容议。降而后也。汉唐宋数千载之间。能尽此道者。蔑蔑乎无闻焉。如文武之风流笃厚。诏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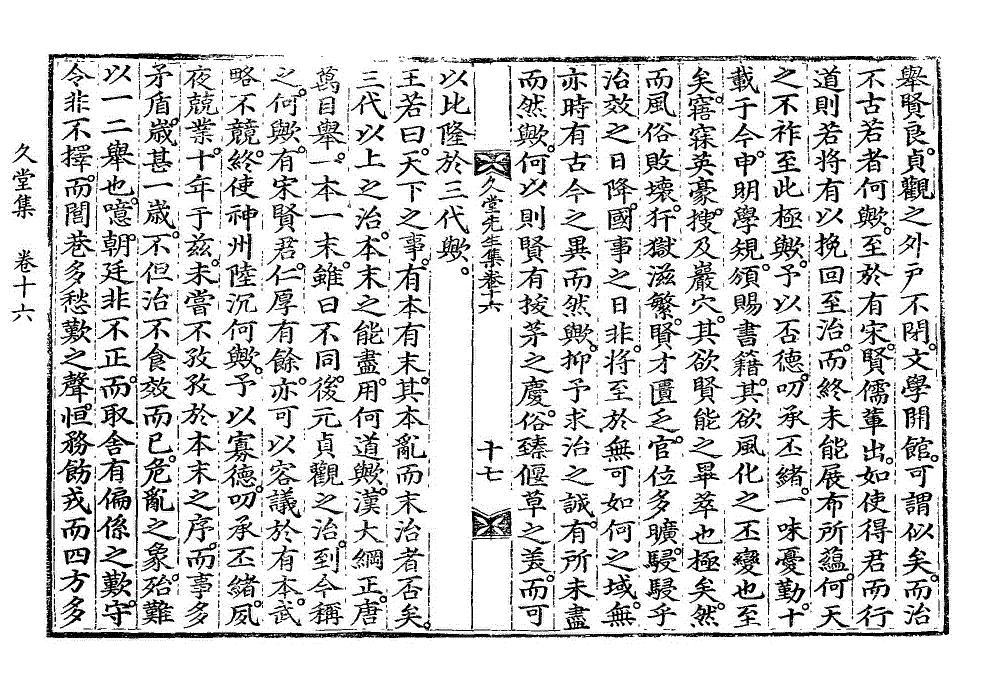 举贤良。贞观之外户不闭。文学开馆。可谓似矣。而治不古若者何欤。至于有宋。贤儒辈出。如使得君而行道则若将有以挽回至治。而终未能展布所蕴。何天之不祚至此极欤。予以否德。叨承丕绪。一味忧勤。十载于今。申明学规。颁赐书籍。其欲风化之丕变也至矣。窹寐英豪。搜及岩穴。其欲贤能之毕萃也极矣。然而风俗败坏。犴狱滋繁。贤才匮乏。官位多旷。骎骎乎治效之日降。国事之日非。将至于无可如何之域。无亦时有古今之异而然欤。抑予求治之诚。有所未尽而然欤。何以则贤有拔茅之庆。俗臻偃草之美。而可以比隆于三代欤。
举贤良。贞观之外户不闭。文学开馆。可谓似矣。而治不古若者何欤。至于有宋。贤儒辈出。如使得君而行道则若将有以挽回至治。而终未能展布所蕴。何天之不祚至此极欤。予以否德。叨承丕绪。一味忧勤。十载于今。申明学规。颁赐书籍。其欲风化之丕变也至矣。窹寐英豪。搜及岩穴。其欲贤能之毕萃也极矣。然而风俗败坏。犴狱滋繁。贤才匮乏。官位多旷。骎骎乎治效之日降。国事之日非。将至于无可如何之域。无亦时有古今之异而然欤。抑予求治之诚。有所未尽而然欤。何以则贤有拔茅之庆。俗臻偃草之美。而可以比隆于三代欤。[治之本末]
王若曰。天下之事。有本有末。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。三代以上之治。本末之能尽。用何道欤。汉大纲正。唐万目举。一本一末。虽曰不同。后元贞观之治。到今称之。何欤。有宋贤君。仁厚有馀。亦可以容议于有本。武略不竞。终使神州陆沈何欤。予以寡德。叨承丕绪。夙夜兢业。十年于兹。未尝不孜孜于本末之序。而事多矛盾。岁甚一岁。不但治不食效而已。危乱之象。殆难以一二举也。噫。朝廷非不正。而取舍有偏系之叹。守令非不择。而闾巷多愁叹之声。恒务饬戎而四方多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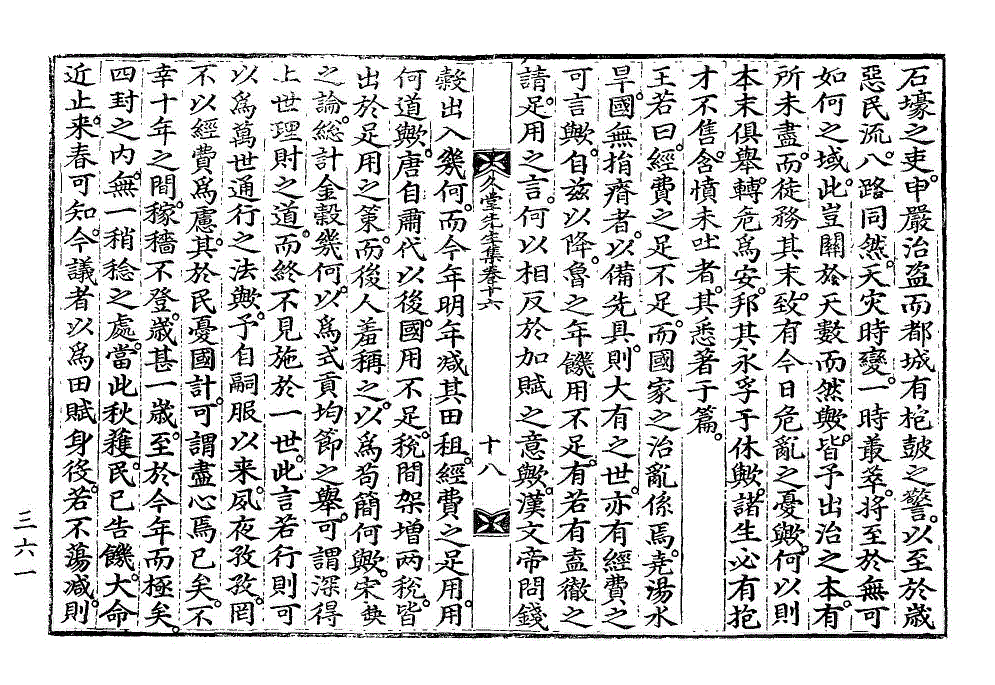 石壕之吏。申严治盗而都城有枹鼓之警。以至于岁恶民流。八路同然。天灾时变。一时丛萃。将至于无可如何之域。此岂关于天数而然欤。皆予出治之本。有所未尽。而徒务其末。致有今日危乱之忧欤。何以则本末俱举。转危为安。邦其永孚于休欤。诸生必有抱才不售。含愤未吐者。其悉著于篇。
石壕之吏。申严治盗而都城有枹鼓之警。以至于岁恶民流。八路同然。天灾时变。一时丛萃。将至于无可如何之域。此岂关于天数而然欤。皆予出治之本。有所未尽。而徒务其末。致有今日危乱之忧欤。何以则本末俱举。转危为安。邦其永孚于休欤。诸生必有抱才不售。含愤未吐者。其悉著于篇。[经费]
王若曰。经费之足不足。而国家之治乱系焉。尧汤水旱。国无捐瘠者。以备先具。则大有之世。亦有经费之可言欤。自兹以降。鲁之年饥用不足。有若有盍彻之请。足用之言。何以相反于加赋之意欤。汉文帝问钱谷出入几何。而今年明年减其田租。经费之足用。用何道欤。唐自肃代以后。国用不足。税间架增两税。皆出于足用之策。而后人羞称之。以为苟简何欤。宋(缺)之论。总计金谷几何。以为式贡均节之举。可谓深得上世理财之道。而终不见施于一世。此言若行则可以为万世通行之法欤。予自嗣服以来。夙夜孜孜。罔不以经费为虑。其于民忧国计。可谓尽心焉已矣。不幸十年之间。稼穑不登。岁甚一岁。至于今年而极矣。四封之内。无一稍稔之处。当此秋穫。民已告饥。大命近止。来春可知。今议者以为田赋身役。若不荡减。则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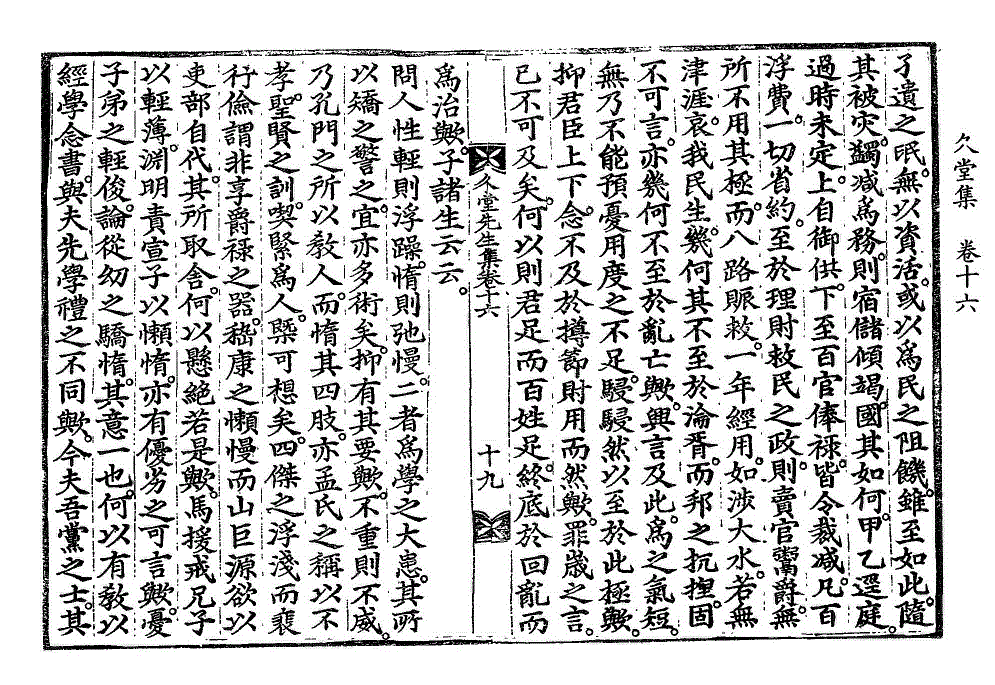 孑遗之氓。无以资活。或以为民之阻饥。虽至如此。随其被灾。蠲减为务。则宿储倾竭。国其如何。甲乙径庭。过时未定。上自御供。下至百官俸禄。皆令裁减。凡百浮费。一切省约。至于理财救民之政。则卖官鬻爵。无所不用其极。而八路赈救。一年经用。如涉大水。若无津涯。哀我民生。几何其不至于沦胥。而邦之杌隉。固不可言。亦几何不至于乱亡欤。兴言及此。为之气短。无乃不能预忧用度之不足。骎骎然以至于此极欤。抑君臣上下。念不及于撙节财用而然欤。罪岁之言。已不可及矣。何以则君足而百姓足。终底于回乱而为治欤。子诸生云云。
孑遗之氓。无以资活。或以为民之阻饥。虽至如此。随其被灾。蠲减为务。则宿储倾竭。国其如何。甲乙径庭。过时未定。上自御供。下至百官俸禄。皆令裁减。凡百浮费。一切省约。至于理财救民之政。则卖官鬻爵。无所不用其极。而八路赈救。一年经用。如涉大水。若无津涯。哀我民生。几何其不至于沦胥。而邦之杌隉。固不可言。亦几何不至于乱亡欤。兴言及此。为之气短。无乃不能预忧用度之不足。骎骎然以至于此极欤。抑君臣上下。念不及于撙节财用而然欤。罪岁之言。已不可及矣。何以则君足而百姓足。终底于回乱而为治欤。子诸生云云。[轻与惰]
问人性轻则浮躁。惰则弛慢。二者为学之大患。其所以矫之警之。宜亦多术矣。抑有其要欤。不重则不威。乃孔门之所以教人。而惰其四肢。亦孟氏之称以不孝。圣贤之训。吃紧为人。槩可想矣。四杰之浮浅而裴行俭谓非享爵禄之器。嵇康之懒慢而山巨源欲以吏部自代。其所取舍。何以悬绝若是欤。马援戒兄子以轻薄。渊明责宣子以懒惰。亦有优劣之可言欤。忧子弟之轻俊。论从幼之骄惰。其意一也。何以有教以经学念书。与夫先学礼之不同欤。今夫吾党之士。其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2L 页
 轻与惰。岂才之罪哉。亶由于父兄之所教诏。朋友之所劝勉。科举之是急而名利之是趋。则何怪乎敦厚勤笃者之见讥于时俗乎。甚至居家而游惰是事。入学而浮议是尚。滔滔者皆是。其害一至于此。岂不大可寒心哉。伊欲使士脱去一副当俗习缠绕。而真实心地。刻苦工夫。偕之大道。圣贤同归。则其道何由。诸生必有能言救时之策。愿闻之。
轻与惰。岂才之罪哉。亶由于父兄之所教诏。朋友之所劝勉。科举之是急而名利之是趋。则何怪乎敦厚勤笃者之见讥于时俗乎。甚至居家而游惰是事。入学而浮议是尚。滔滔者皆是。其害一至于此。岂不大可寒心哉。伊欲使士脱去一副当俗习缠绕。而真实心地。刻苦工夫。偕之大道。圣贤同归。则其道何由。诸生必有能言救时之策。愿闻之。[理与事]
问。事未始不根于理。理未始不该于事。然则何以有二字之别乎。二帝三王。治本于道。道本于心。其实一而已矣。孔子之时。此道素明。故以孝悌为为仁之本。而至子舆氏。乃述唐虞之德于战国纵横之日。则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。此则时之使然欤。汉唐宋千五百年间。士之记诵词章之习。反覆沈痼。甚至言理者归于老佛。论事者务于管商。理之于事。不啻背驰。而此个古今常在不灭之物。终殄灭他不得者。似亦有待于洛建诸儒之阐明。而亦终不得施之于天下者。何欤。道东千载。儒术兴行。至于今日而盛矣。百家可息。统纪可一。而求之于事理。乃反有以病焉。何欤。为士者。志于科举则以文行为二致。公卿大夫之所谈说。至以道学政术为两途。则国事民隐。亦安得不岐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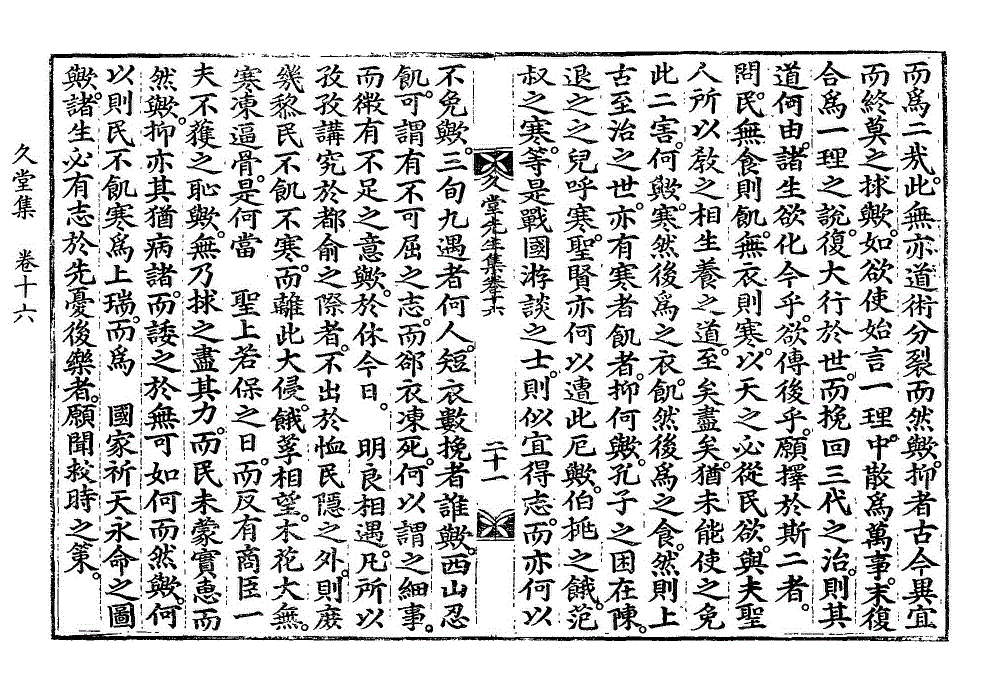 而为二哉。此无亦道术分裂而然欤。抑者古今异宜而终莫之救欤。如欲使始言一理。中散为万事。末复合为一理之说。复大行于世。而挽回三代之治。则其道何由。诸生欲化今乎。欲传后乎。愿择于斯二者。
而为二哉。此无亦道术分裂而然欤。抑者古今异宜而终莫之救欤。如欲使始言一理。中散为万事。末复合为一理之说。复大行于世。而挽回三代之治。则其道何由。诸生欲化今乎。欲传后乎。愿择于斯二者。[饥寒]
问。民无食则饥。无衣则寒。以天之必从民欲。与夫圣人所以教之相生养之道。至矣尽矣。犹未能使之免此二害。何欤。寒然后为之衣。饥然后为之食。然则上古至治之世。亦有寒者饥者。抑何欤。孔子之困在陈。退之之儿呼寒。圣贤亦何以遭此厄欤。伯桃之饿。范叔之寒。等是战国游谈之士。则似宜得志。而亦何以不免欤。三旬九遇者何人。短衣数挽者谁欤。西山忍饥。可谓有不可屈之志。而却衣冻死。何以谓之细事。而微有不足之意欤。于休今日。 明良相遇。凡所以孜孜讲究于都俞之际者。不出于恤民隐之外。则庶几黎民不饥不寒。而离此大侵。饿莩相望。木花大无。寒冻逼骨。是何当 圣上若保之日。而反有商臣一夫不获之耻欤。无乃救之尽其力。而民未蒙实惠而然欤。抑亦其犹病诸。而诿之于无可如何而然欤。何以则民不饥寒为上瑞。而为 国家祈天永命之图欤。诸生必有志于先忧后乐者。愿闻救时之策。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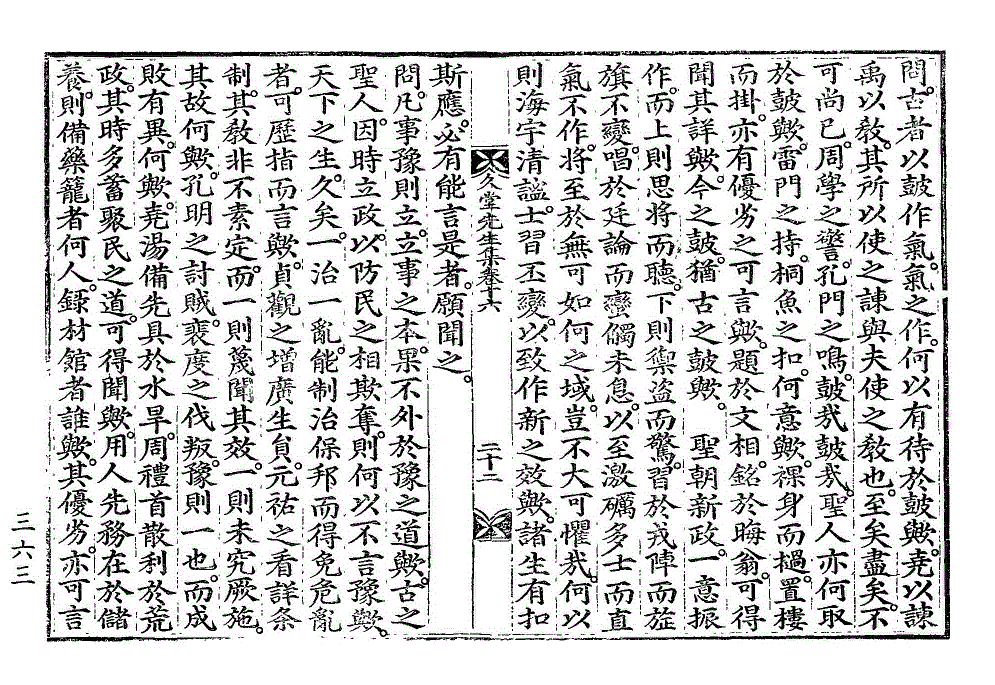 [鼓]
[鼓]问。古者以鼓作气。气之作。何以有待于鼓欤。尧以谏禹以教。其所以使之谏与夫使之教也。至矣尽矣。不可尚已。周学之警。孔门之鸣。鼓哉鼓哉。圣人亦何取于鼓欤。雷门之持。桐鱼之扣。何意欤。裸身而挝。置楼而挂。亦有优劣之可言欤。题于文相。铭于晦翁。可得闻其详欤。今之鼓。犹古之鼓欤。 圣朝新政。一意振作。而上则思将而听。下则御盗而惊。习于戎阵而旌旗不变。唱于廷论而蛮触未息。以至激砺多士而直气不作。将至于无可如何之域。岂不大可惧哉。何以则海宇清谧。士习丕变。以致作新之效欤。诸生有扣斯应。必有能言是者。愿闻之。
[豫]
问。凡事豫则立。立事之本。果不外于豫之道欤。古之圣人。因时立政。以防民之相欺夺。则何以不言豫欤。天下之生。久矣。一治一乱。能制治保邦而得免危乱者。可历指而言欤。贞观之增广生员。元祐之看详条制。其教非不素定。而一则蔑闻其效。一则未究厥施。其故何欤。孔明之讨贼。裴度之伐叛。豫则一也。而成败有异。何欤。尧汤备先具于水旱。周礼首散利于荒政。其时多蓄聚民之道。可得闻欤。用人先务在于储养。则备药笼者何人。录材馆者谁欤。其优劣。亦可言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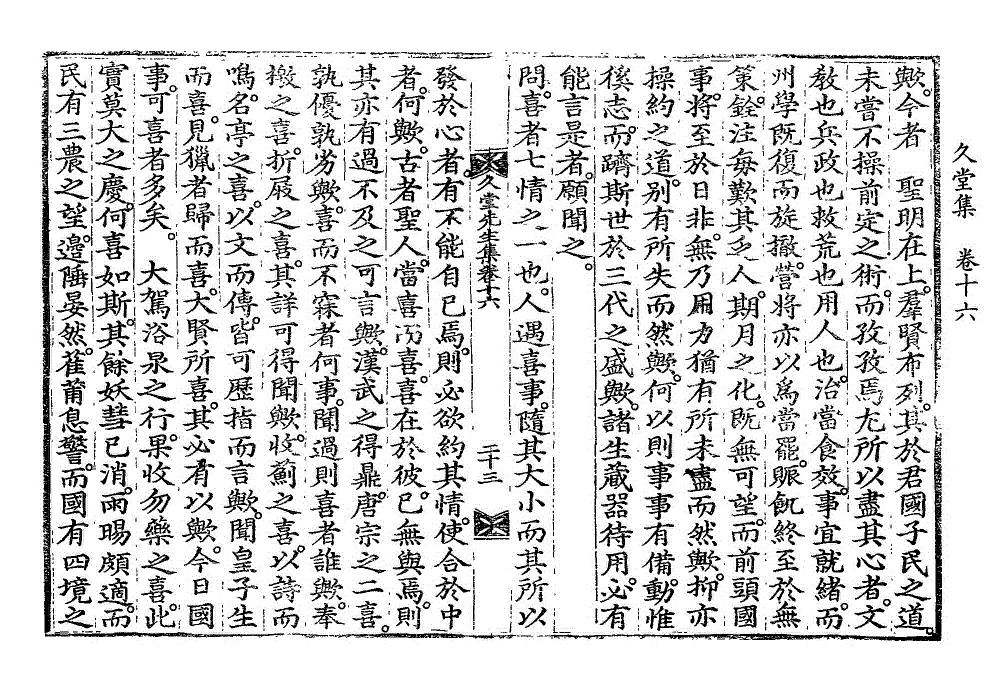 欤。今者 圣明在上。群贤布列。其于君国子民之道。未尝不操前定之术。而孜孜焉尤所以尽其心者。文教也兵政也救荒也用人也。治当食效。事宜就绪。而州学既复而旋撤。营将亦以为当罢。赈饥终至于无策。铨注每叹其乏人。期月之化。既无可望。而前头国事。将至于日非。无乃用力犹有所未尽而然欤。抑亦操约之道。别有所失而然欤。何以则事事有备。动惟徯志。而跻斯世于三代之盛欤。诸生藏器待用。必有能言是者。愿闻之。
欤。今者 圣明在上。群贤布列。其于君国子民之道。未尝不操前定之术。而孜孜焉尤所以尽其心者。文教也兵政也救荒也用人也。治当食效。事宜就绪。而州学既复而旋撤。营将亦以为当罢。赈饥终至于无策。铨注每叹其乏人。期月之化。既无可望。而前头国事。将至于日非。无乃用力犹有所未尽而然欤。抑亦操约之道。别有所失而然欤。何以则事事有备。动惟徯志。而跻斯世于三代之盛欤。诸生藏器待用。必有能言是者。愿闻之。[喜]
问。喜者七情之一也。人遇喜事。随其大小而其所以发于心者。有不能自已焉。则必欲约其情。使合于中者。何欤。古者圣人。当喜而喜。喜在于彼。已无与焉。则其亦有过不及之可言欤。汉武之得鼎。唐宗之二喜。孰优孰劣欤。喜而不寐者何事。闻过则喜者谁欤。奉檄之喜。折屐之喜。其详可得闻欤。收蓟之喜。以诗而鸣。名亭之喜。以文而传。皆可历指而言欤。闻皇子生而喜。见猎者归而喜。大贤所喜。其必有以欤。今日国事。可喜者多矣。 大驾浴泉之行。果收勿药之喜。此实莫大之庆。何喜如斯。其馀妖彗已消。雨晹(一作旸)颇适。而民有三农之望。边陲晏然。萑莆息警。而国有四境之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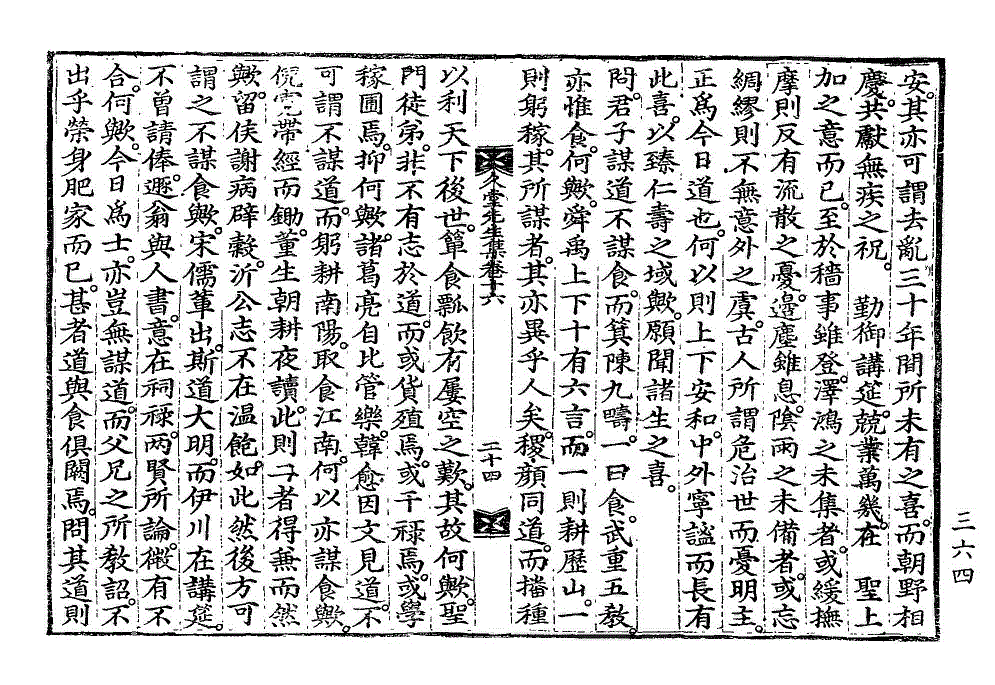 安。其亦可谓去乱三十年间所未有之喜。而朝野相庆。共献无疾之祝。 勤御讲筵。兢业万几。在 圣上加之意而已。至于穑事虽登。泽鸿之未集者。或缓抚摩则反有流散之忧。边尘虽息。阴雨之未备者。或忘绸缪则不无意外之虞。古人所谓危治世而忧明主。正为今日道也。何以则上下安和。中外宁谧而长有此喜。以臻仁寿之域欤。愿闻诸生之喜。
安。其亦可谓去乱三十年间所未有之喜。而朝野相庆。共献无疾之祝。 勤御讲筵。兢业万几。在 圣上加之意而已。至于穑事虽登。泽鸿之未集者。或缓抚摩则反有流散之忧。边尘虽息。阴雨之未备者。或忘绸缪则不无意外之虞。古人所谓危治世而忧明主。正为今日道也。何以则上下安和。中外宁谧而长有此喜。以臻仁寿之域欤。愿闻诸生之喜。[道与食]
问。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而箕陈九畴。一曰食。武重五教。亦惟食。何欤。舜禹上下十有六言。而一则耕历山。一则躬稼。其所谋者。其亦异乎人矣。稷,颜同道。而播种以利天下后世。箪食瓢饮有屡空之叹。其故何欤。圣门徒弟。非不有志于道。而或货殖焉。或干禄焉。或学稼圃焉。抑何欤。诸葛亮自比管乐。韩愈因文见道。不可谓不谋道。而躬耕南阳。取食江南。何以亦谋食欤。倪宽带经而锄。董生朝耕夜读。此则二者得兼而然欤。留侯谢病辟谷。沂公志不在温饱。如此然后方可谓之不谋食欤。宋儒辈出。斯道大明。而伊川在讲筵。不曾请俸。遁翁与人书。意在祠禄。两贤所论。微有不合。何欤。今日为士。亦岂无谋道。而父兄之所教诏。不出乎荣身肥家而已。甚者道与食俱阙焉。问其道则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5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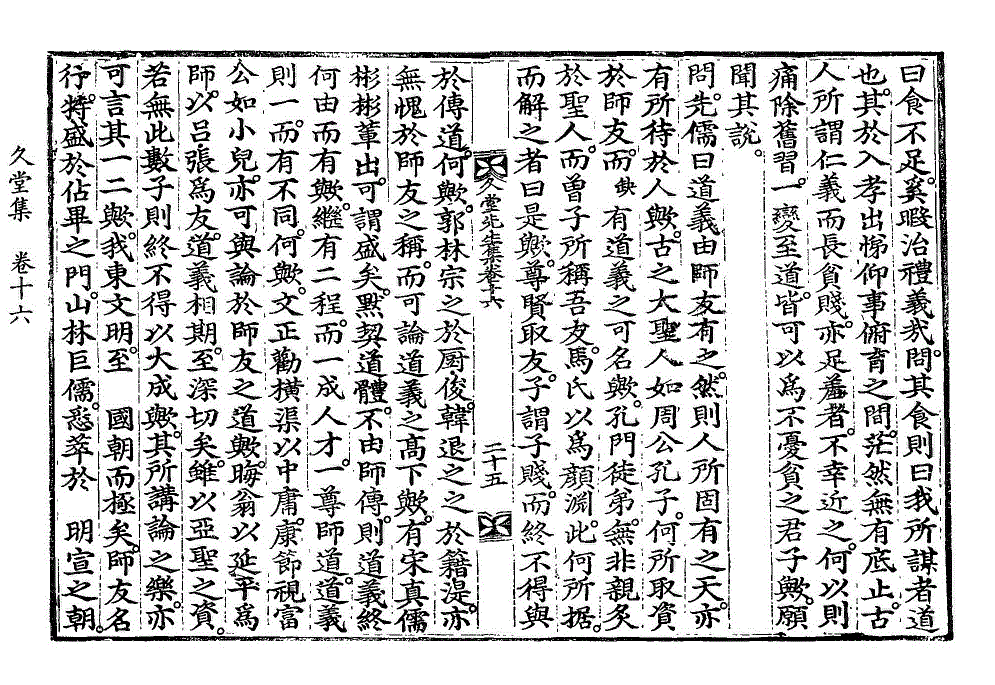 曰食不足。奚暇治礼义哉。问其食则曰我所谋者道也。其于入孝出悌仰事俯育之间。茫然无有底止。古人所谓仁义而长贫贱。亦足羞者。不幸近之。何以则痛除旧习。一变至道。皆可以为不忧贫之君子欤。愿闻其说。
曰食不足。奚暇治礼义哉。问其食则曰我所谋者道也。其于入孝出悌仰事俯育之间。茫然无有底止。古人所谓仁义而长贫贱。亦足羞者。不幸近之。何以则痛除旧习。一变至道。皆可以为不忧贫之君子欤。愿闻其说。[师友与道义]
问。先儒曰道义由师友有之。然则人所固有之天。亦有所待于人欤。古之大圣人如周公,孔子。何所取资于师友。而(缺)有道义之可名欤。孔门徒弟。无非亲炙于圣人。而曾子所称吾友。马氏以为颜渊。此何所据。而解之者曰是欤。尊贤取友。子谓子贱。而终不得与于传道。何欤。郭林宗之于厨,俊。韩退之之于籍,湜。亦无愧于师友之称。而可论道义之高下欤。有宋真儒彬彬辈出。可谓盛矣。默契道体。不由师传。则道义终何由而有欤。继有二程。而一成人才。一尊师道。道义则一。而有不同。何欤。文正劝横渠以中庸。康节视富公如小儿。亦可与论于师友之道欤。晦翁以延平为师。以吕,张为友。道义相期。至深切矣。虽以亚圣之资。若无此数子则终不得以大成欤。其所讲论之乐。亦可言其一二欤。我东文明。至 国朝而极矣。师友名行。特盛于佔毕之门。山林巨儒。悉萃于 明宣之朝。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5L 页
 相与讨论于古。有光此道之衰。又至今日而极耶。师友道义之际。其终不可得以复见耶。盖有之矣。或未之见耶。其谓之真无则时运之使然耶。抑导之乖其方欤。诸生亦必有慨然于斯者。其各悉陈救弊之策。
相与讨论于古。有光此道之衰。又至今日而极耶。师友道义之际。其终不可得以复见耶。盖有之矣。或未之见耶。其谓之真无则时运之使然耶。抑导之乖其方欤。诸生亦必有慨然于斯者。其各悉陈救弊之策。[静重]
问。大凡人之处大事。须是静重。曰静曰重之所以能处大事。用何道欤。孔门论学。揭以重威二字。曾子传之。又称弘毅。至宋儒始言静坐。学则一也。而何以有先后之序欤。霍光之进止有常似矣。而终有不学之病。谢安之围棋睹墅近矣。而未免矫情之讥。其故何欤。凝尘满砚。终日默坐者何人。不动颜色。天下泰山者谁欤。二人优劣。可得闻欤。狄公久为娄公之包容。子房不及孔明之正大。亦可得以详言之欤。三代以上。论九德最好。则其人品气像。亦可以想见。而降而后也。前汉人物。可谓近古。后汉不及于前。其以下则可观者无几人矣。宋之大贤辈出。其人资品学问。可轶三代。而终不见其措诸事。其故何欤。凡今之人。亦有静重可以了一世事者欤。朝廷搢绅。与夫草野韦布之士。其间罕有守静持重之人。盖有之矣。人未之见欤。以致势利奔趋。未免躁竞之习。论议纷纭。未见笃厚之风。人心之不古。世道之渐下。职由于此。良可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6H 页
 慨然。伊欲使斯世之人。静以修身。重于为己。穷养达施。终塞其受中以生之责。则其道何由。愿闻其说。
慨然。伊欲使斯世之人。静以修身。重于为己。穷养达施。终塞其受中以生之责。则其道何由。愿闻其说。[著述]
问。著述文字。盖为明道而传后也。抑著者自著。述者自述。无意于传世。而自不得不传欤。上古之世。惟圣与贤。皆达而在上。宜无待于治(缺)。而何以有八卦易之始。三坟书之始之言欤。孔子之删诗定书。孟子之难疑答问。曾子之大学。子思之中庸。亦有意于传世欤。文王之演易。左丘之作传。必待忧患而作者。何欤。五千道德。十万说林。皆可谓之著述。而亦有所补于后世欤。自汉以来。曰唐曰宋。上下数千年间。著述之家指不胜屈。其可历数而详言欤。孰为可行于世而可传于后欤。尧舜,禹汤之圣焉。而谟训之见于经传者甚鲜。濂洛关闽之贤焉。而其著述之夥。不啻充栋。羽翼夫道一也。而多小之不同。抑何欤。我东国于海隅。文献不足。罗丽之间。亦有著述之可称者欤。我 朝五贤辈出。道德卓卓可说。而著述之或存或无。何欤。近来载道之器。视古益盛。家藏经籍。人诵程,朱。宜乎斯道大行。而独善兼善。俱不及于古人者何欤。伊欲使斯世之士。绍复圣贤之遗绪。著书立言。为可法于后世。则其道何由。愿闻其说。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6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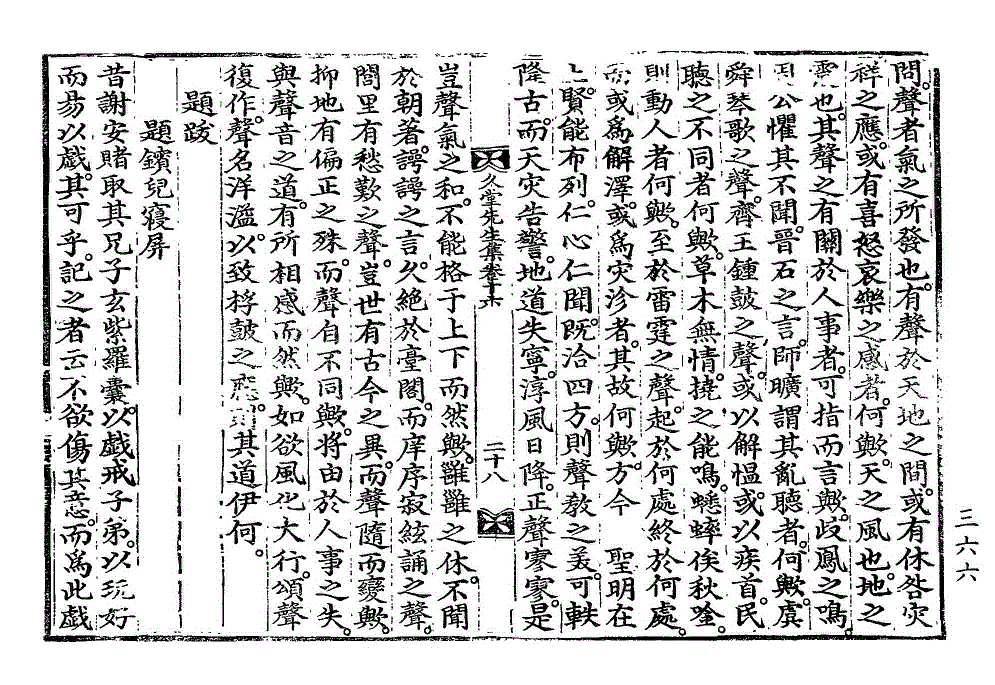 [声]
[声]问。声者气之所发也。有声于天地之间。或有休咎灾祥之应。或有喜怒哀乐之感者。何欤。天之风也。地之震也。其声之有关于人事者。可指而言欤。岐凤之鸣。周公惧其不闻。晋石之言。师旷谓其乱听者。何欤。虞舜琴歌之声。齐王钟鼓之声。或以解愠。或以疾首。民听之不同者何欤。草木无情。挠之能鸣。蟋蟀俟秋唫。则动人者何欤。至于雷霆之声。起于何处终于何处。而或为解泽。或为灾沴者。其故何欤。方今 圣明在上。贤能布列。仁心仁闻。既洽四方。则声教之美。可轶隆古。而天灾告警。地道失宁。淳风日降。正声寥寥。是岂声气之和。不能格于上下而然欤。雍雍之休。不闻于朝著。谔谔之言。久绝于台阁。而庠序寂弦诵之声。闾里有愁叹之声。岂世有古今之异。而声随而变欤。抑地有偏正之殊。而声自不同欤。将由于人事之失。与声音之道。有所相感而然欤。如欲风化大行。颂声复作。声名洋溢。以致桴鼓之应。则其道伊何。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
题跋
题镔儿寝屏
昔谢安赌取其兄子玄紫罗囊。以戏戒子弟。以玩好而易以戏。其可乎。记之者云不欲伤其意。而为此戏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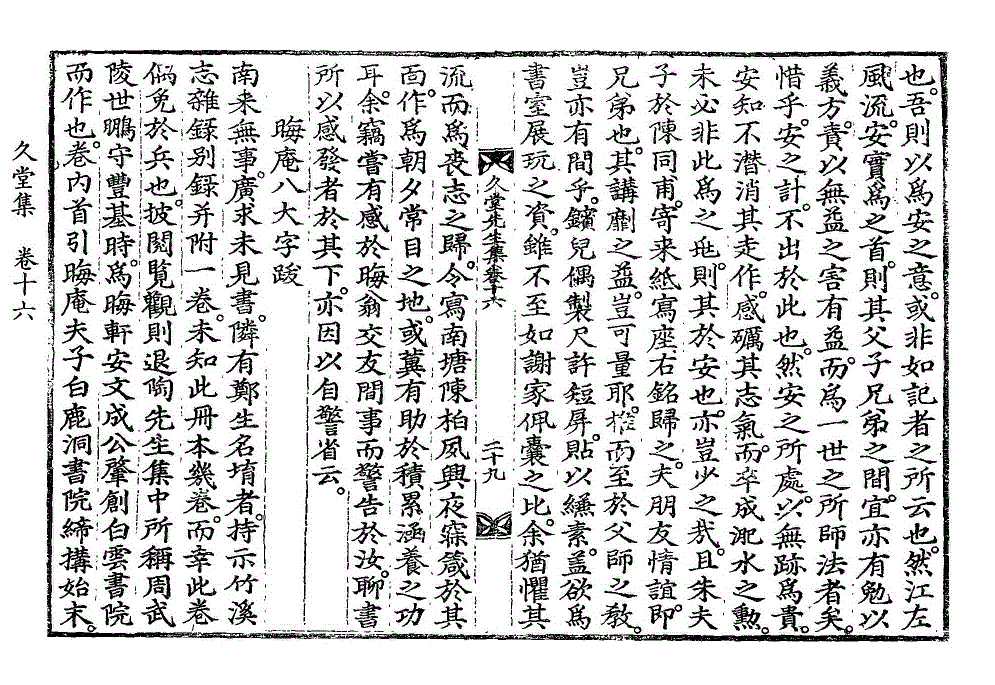 也。吾则以为安之意。或非如记者之所云也。然江左风流。安实为之首。则其父子兄弟之间。宜亦有勉以义方。责以无益之害有益。而为一世之所师法者矣。惜乎。安之计。不出于此也。然安之所处。以无迹为贵。安知不潜消其走作。感砺其志气。而卒成淝水之勋。未必非此为之兆。则其于安也。亦岂少之哉。且朱夫子于陈同甫。寄来纸写座右铭归之。夫朋友情谊。即兄弟也。其讲劘之益。岂可量耶。推而至于父师之教。岂亦有间乎。镔儿偶制尺许短屏。贴以缣素。盖欲为书室展玩之资。虽不至如谢家佩囊之比。余犹惧其流而为丧志之归。令写南塘陈柏夙兴夜寐箴于其面。作为朝夕常目之地。或冀有助于积累涵养之功耳。余窃尝有感于晦翁交友间事而警告于汝。聊书所以感发者于其下。亦因以自警省云。
也。吾则以为安之意。或非如记者之所云也。然江左风流。安实为之首。则其父子兄弟之间。宜亦有勉以义方。责以无益之害有益。而为一世之所师法者矣。惜乎。安之计。不出于此也。然安之所处。以无迹为贵。安知不潜消其走作。感砺其志气。而卒成淝水之勋。未必非此为之兆。则其于安也。亦岂少之哉。且朱夫子于陈同甫。寄来纸写座右铭归之。夫朋友情谊。即兄弟也。其讲劘之益。岂可量耶。推而至于父师之教。岂亦有间乎。镔儿偶制尺许短屏。贴以缣素。盖欲为书室展玩之资。虽不至如谢家佩囊之比。余犹惧其流而为丧志之归。令写南塘陈柏夙兴夜寐箴于其面。作为朝夕常目之地。或冀有助于积累涵养之功耳。余窃尝有感于晦翁交友间事而警告于汝。聊书所以感发者于其下。亦因以自警省云。晦庵八大字跋
南来无事。广求未见书。邻有郑生名堉者。持示竹溪志杂录别录并附一卷。未知此册本几卷。而幸此卷偶免于兵也。披阅览观则退陶先生集中所称周武陵世鹏守丰基时。为晦轩安文成公肇创白云书院而作也。卷内首引晦庵夫子白鹿洞书院缔搆始末。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7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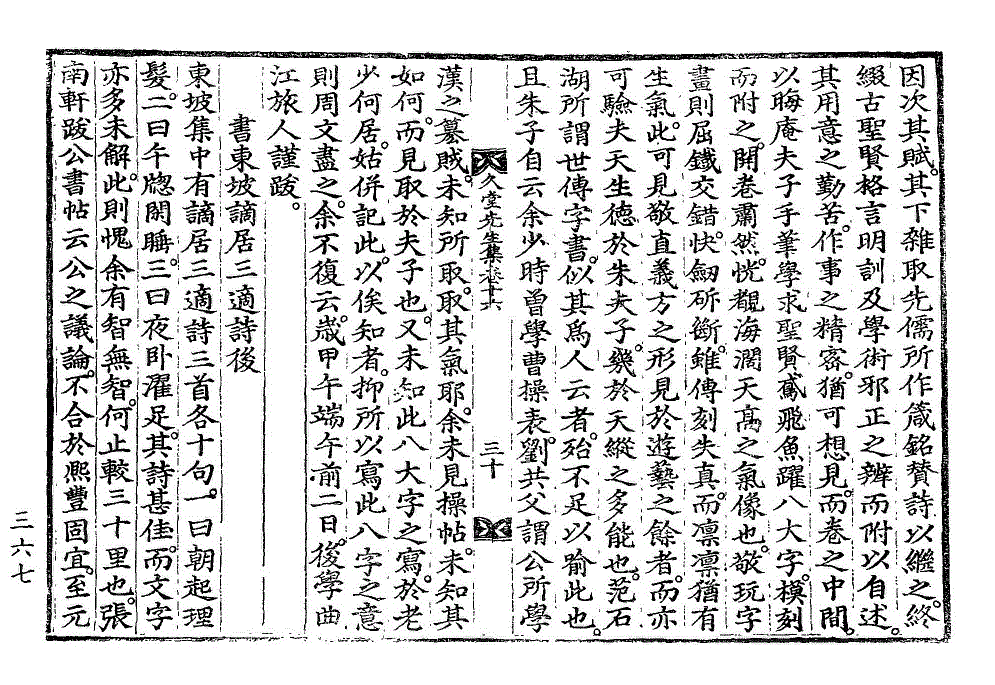 因次其赋。其下杂取先儒所作箴铭赞诗以继之。终缀古圣贤格言明训及学术邪正之辨而附以自述。其用意之勤苦。作事之精密。犹可想见。而卷之中间。以晦庵夫子手笔学求圣贤鸢飞鱼跃八大字。模刻而附之。开卷肃然。恍睹海阔天高之气像也。敬玩字画则屈铁交错。快剑斫断。虽传刻失真。而凛凛犹有生气。此可见敬直义方之形见于游艺之馀者。而亦可验夫天生德于朱夫子。几于天纵之多能也。范石湖所谓世传字书。似其为人云者。殆不足以喻此也。且朱子自云余少时曾学曹操表。刘共父谓公所学汉之篡贼。未知所取。取其气耶。余未见操帖。未知其如何。而见取于夫子也。又未知此八大字之写。于老少何居。姑并记此。以俟知者。抑所以写此八字之意则周文尽之。余不复云。岁甲午端午前二日。后学曲江旅人谨跋。
因次其赋。其下杂取先儒所作箴铭赞诗以继之。终缀古圣贤格言明训及学术邪正之辨而附以自述。其用意之勤苦。作事之精密。犹可想见。而卷之中间。以晦庵夫子手笔学求圣贤鸢飞鱼跃八大字。模刻而附之。开卷肃然。恍睹海阔天高之气像也。敬玩字画则屈铁交错。快剑斫断。虽传刻失真。而凛凛犹有生气。此可见敬直义方之形见于游艺之馀者。而亦可验夫天生德于朱夫子。几于天纵之多能也。范石湖所谓世传字书。似其为人云者。殆不足以喻此也。且朱子自云余少时曾学曹操表。刘共父谓公所学汉之篡贼。未知所取。取其气耶。余未见操帖。未知其如何。而见取于夫子也。又未知此八大字之写。于老少何居。姑并记此。以俟知者。抑所以写此八字之意则周文尽之。余不复云。岁甲午端午前二日。后学曲江旅人谨跋。书东坡谪居三适诗后
东坡集中有谪居三适诗三首各十句。一曰朝起理发。二曰午窗闲睡。三曰夜卧濯足。其诗甚佳。而文字亦多未解。此则愧余有智无智。何止较三十里也。张南轩跋公书帖云公之议论。不合于熙丰固宜。至元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8H 页
 祐初。诸老在朝。群贤汇征。及论役法。与己意少异。亦未尝一语苟同。可见公之心惟义之比。初无适莫。方贬黄州。无一毫挫折意。在他人已为难。然年尚壮也。至于投老炎荒。刚毅凛凛。略不少衰。此岂可及哉。忠义之气。未尝不蔚然见于笔墨间。真可畏而仰哉。其所以景仰称道之者。盖亦至矣。以是而观其形于诗词者。虽流离岭海而如在朝廷。足想其平生学道。以适其适者。无适不然而致之也。夫岂一日之积哉。以朱子所称与何人帖所谓遇事有尊主泽民者。便忘躯为之。祸福得丧。付与造物云者推之。其不动心。槩可见矣。余以为忘躯云者。为此三适之根柢何者。忘腰带之适也。忘足履之适也。其适也从忘字中生出来者。亦可推而委也。此虽非吾儒所谓道。而用志不分。乃凝于神。然后适意而游。庶乎无入而不自得矣。其与不知道者。岂不大相远乎。呜呼。东坡亦知道者哉。
祐初。诸老在朝。群贤汇征。及论役法。与己意少异。亦未尝一语苟同。可见公之心惟义之比。初无适莫。方贬黄州。无一毫挫折意。在他人已为难。然年尚壮也。至于投老炎荒。刚毅凛凛。略不少衰。此岂可及哉。忠义之气。未尝不蔚然见于笔墨间。真可畏而仰哉。其所以景仰称道之者。盖亦至矣。以是而观其形于诗词者。虽流离岭海而如在朝廷。足想其平生学道。以适其适者。无适不然而致之也。夫岂一日之积哉。以朱子所称与何人帖所谓遇事有尊主泽民者。便忘躯为之。祸福得丧。付与造物云者推之。其不动心。槩可见矣。余以为忘躯云者。为此三适之根柢何者。忘腰带之适也。忘足履之适也。其适也从忘字中生出来者。亦可推而委也。此虽非吾儒所谓道。而用志不分。乃凝于神。然后适意而游。庶乎无入而不自得矣。其与不知道者。岂不大相远乎。呜呼。东坡亦知道者哉。题李季周诗卷
夫人之为诗。必曰我学唐。唐岂易学哉。余则窃以为人果能致礼以治躬。致乐以治心。而领恶而全好。洗去多少夙生荤血。则其所感发于诗者。皆可一唱而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8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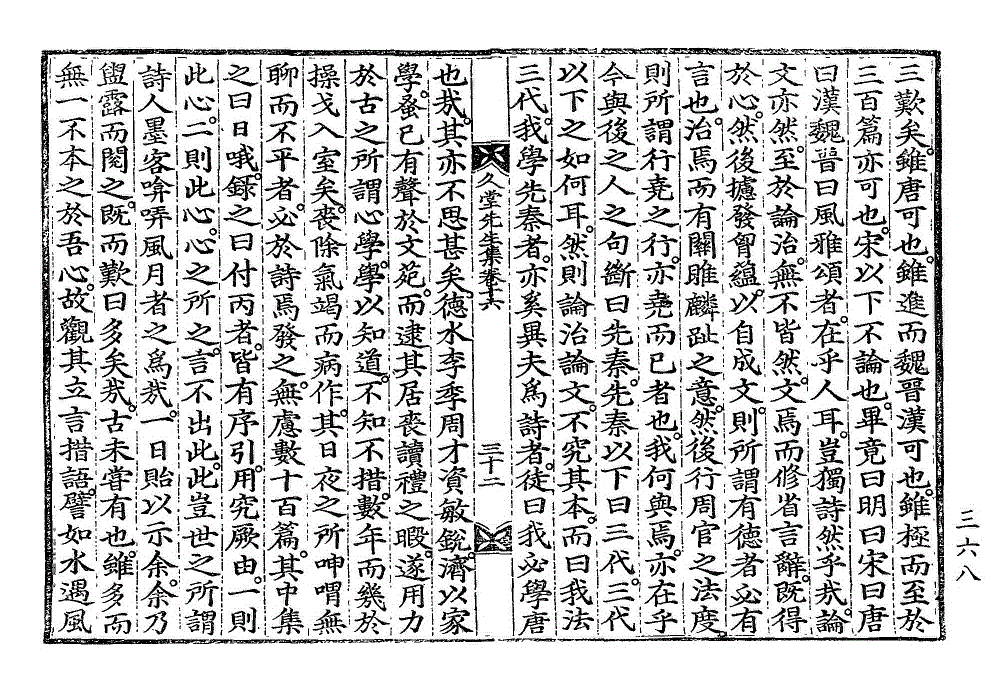 三叹矣。虽唐可也。虽进而魏晋汉可也。虽极而至于三百篇亦可也。宋以下不论也。毕竟曰明曰宋曰唐曰汉魏晋曰风雅颂者。在乎人耳。岂独诗然乎哉。论文亦然。至于论治。无不皆然。文焉而修省言辞。既得于心。然后摅发胸蕴。以自成文。则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。治焉而有关雎麟趾之意。然后行周官之法度。则所谓行尧之行。亦尧而已者也。我何与焉。亦在乎今与后之人之句断曰先秦。先秦以下曰三代。三代以下之如何耳。然则论治论文。不究其本。而曰我法三代。我学先秦者。亦奚异夫为诗者。徒曰我必学唐也哉。其亦不思甚矣。德水李季周才资敏锐。济以家学。蚤已有声于文苑。而逮其居丧读礼之暇。遂用力于古之所谓心学。学以知道。不知不措。数年而几于操戈入室矣。丧除气竭而病作。其日夜之所呻喟无聊而不平者。必于诗焉发之。无虑数十百篇。其中集之曰日哦。录之曰付丙者。皆有序引。用究厥由。一则此心。二则此心。心之所之。言不出此。此岂世之所谓诗人墨客啽哢风月者之为哉。一日贻以示余。余乃盥露而阅之。既而叹曰多矣哉。古未尝有也。虽多而无一不本之于吾心。故观其立言措语。譬如水遇风
三叹矣。虽唐可也。虽进而魏晋汉可也。虽极而至于三百篇亦可也。宋以下不论也。毕竟曰明曰宋曰唐曰汉魏晋曰风雅颂者。在乎人耳。岂独诗然乎哉。论文亦然。至于论治。无不皆然。文焉而修省言辞。既得于心。然后摅发胸蕴。以自成文。则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。治焉而有关雎麟趾之意。然后行周官之法度。则所谓行尧之行。亦尧而已者也。我何与焉。亦在乎今与后之人之句断曰先秦。先秦以下曰三代。三代以下之如何耳。然则论治论文。不究其本。而曰我法三代。我学先秦者。亦奚异夫为诗者。徒曰我必学唐也哉。其亦不思甚矣。德水李季周才资敏锐。济以家学。蚤已有声于文苑。而逮其居丧读礼之暇。遂用力于古之所谓心学。学以知道。不知不措。数年而几于操戈入室矣。丧除气竭而病作。其日夜之所呻喟无聊而不平者。必于诗焉发之。无虑数十百篇。其中集之曰日哦。录之曰付丙者。皆有序引。用究厥由。一则此心。二则此心。心之所之。言不出此。此岂世之所谓诗人墨客啽哢风月者之为哉。一日贻以示余。余乃盥露而阅之。既而叹曰多矣哉。古未尝有也。虽多而无一不本之于吾心。故观其立言措语。譬如水遇风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9H 页
 而成文。草木甘苦之实。得雨露而齐结。其与区区为诗而曰我学唐者。不啻秦楚之远也。何可以诗观诗而止哉。虽然曰唐曰宋则吾岂敢然。而苟推是心以往。何事不可济。发而为黼黻之文。出而资经纶之业。皆足以验他日之所就者。其在是欤。其在是欤。季周要题卷端甚切。顾余不自量而妄语之。近乎僭矣。然而因我不会做。皆使天下之人不做。亦近乎怠。故聊相为言之。
而成文。草木甘苦之实。得雨露而齐结。其与区区为诗而曰我学唐者。不啻秦楚之远也。何可以诗观诗而止哉。虽然曰唐曰宋则吾岂敢然。而苟推是心以往。何事不可济。发而为黼黻之文。出而资经纶之业。皆足以验他日之所就者。其在是欤。其在是欤。季周要题卷端甚切。顾余不自量而妄语之。近乎僭矣。然而因我不会做。皆使天下之人不做。亦近乎怠。故聊相为言之。题郑统制传后
统制使郑公讳起龙字某。氏于岭南之晋阳。世居昆阳之兑村。生于嘉靖壬戌。登万历丙戌虎榜。及夫壬辰之难。奋起行间。始以突击知名。守尚州通判。未满岁为真。无何又升守本州牧。即为真。一转而为右道兵马节度使。自是擢三道水军都统制者再。进阶辅国。年六十一。卒于营。盖尚为州。介于岭左右四达之冲。去壬丁干戈之际。受敌最甚。李镒以巡边。权吉以通判。败没于北川。或走或死之。至今民物未复太平之旧。及余出牧。去乱几七十年矣。试问其时。遗老几尽。而存者往往能言吾州有邑无之。而吾侪小人。终保有子孙。以至于今者。皆曰郑侯郑侯云。然尝考其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6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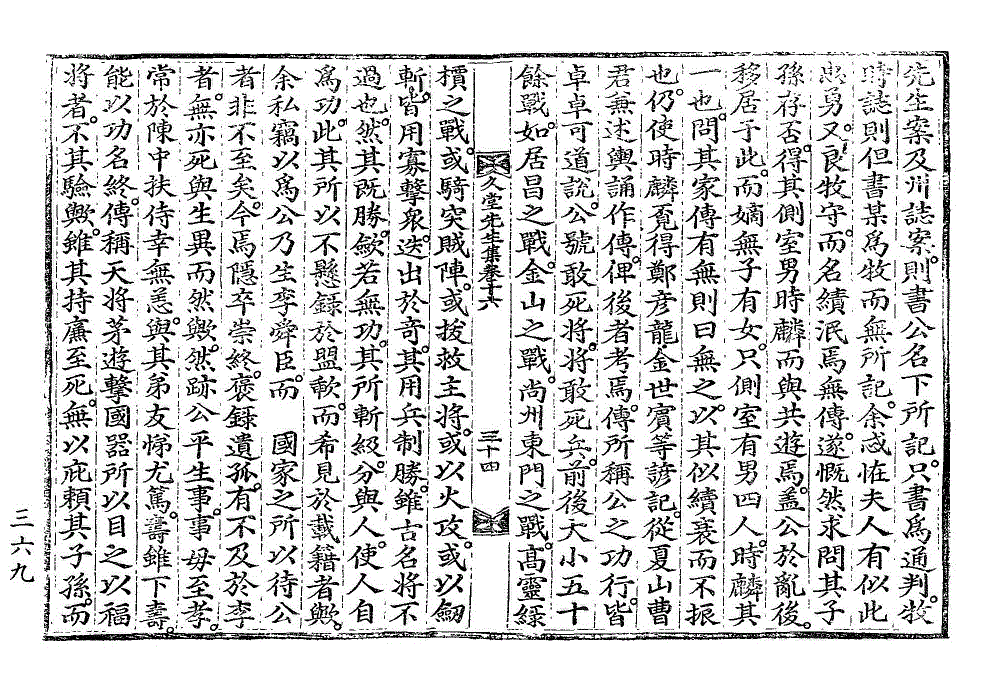 先生案及州志案。则书公名下所记。只书为通判。牧时志则但书某为牧而无所记。余忒怪夫人有似此忠勇。又良牧守。而名绩泯焉无传。遂慨然求问其子孙存否。得其侧室男时麟而与共游焉。盖公于乱后。移居于此。而嫡无子有女。只侧室有男四人。时麟其一也。问其家传有无则曰无之。以其似续衰而不振也。仍使时麟觅得郑彦龙,金世宾等谚记。从夏山曹君兼述舆诵作传。俾后者考焉。传所称公之功行。皆卓卓可道说。公号敢死将。将敢死兵。前后大小五十馀战。如居昌之战。金山之战。尚州东门之战。高灵绿槚之战。或骑突贼阵。或拔救主将。或以火攻。或以剑斩。皆用寡击众。迭出于奇。其用兵制胜。虽古名将不过也。然其既胜。敛若无功。其所斩级。分与人。使人自为功。此其所以不悬录于盟歃。而希见于载籍者欤。余私窃以为公乃生李舜臣。而 国家之所以待公者非不至矣。今焉隐卒崇终。褒录遗孤。有不及于李者。无亦死与生异而然欤。然迹公平生事。事母至孝。常于陈中扶侍幸无恙。与其弟友悌尤笃。寿虽下寿。能以功名终。传称天将茅游击国器所以目之以福将者。不其验欤。虽其持廉至死。无以庇赖其子孙。而
先生案及州志案。则书公名下所记。只书为通判。牧时志则但书某为牧而无所记。余忒怪夫人有似此忠勇。又良牧守。而名绩泯焉无传。遂慨然求问其子孙存否。得其侧室男时麟而与共游焉。盖公于乱后。移居于此。而嫡无子有女。只侧室有男四人。时麟其一也。问其家传有无则曰无之。以其似续衰而不振也。仍使时麟觅得郑彦龙,金世宾等谚记。从夏山曹君兼述舆诵作传。俾后者考焉。传所称公之功行。皆卓卓可道说。公号敢死将。将敢死兵。前后大小五十馀战。如居昌之战。金山之战。尚州东门之战。高灵绿槚之战。或骑突贼阵。或拔救主将。或以火攻。或以剑斩。皆用寡击众。迭出于奇。其用兵制胜。虽古名将不过也。然其既胜。敛若无功。其所斩级。分与人。使人自为功。此其所以不悬录于盟歃。而希见于载籍者欤。余私窃以为公乃生李舜臣。而 国家之所以待公者非不至矣。今焉隐卒崇终。褒录遗孤。有不及于李者。无亦死与生异而然欤。然迹公平生事。事母至孝。常于陈中扶侍幸无恙。与其弟友悌尤笃。寿虽下寿。能以功名终。传称天将茅游击国器所以目之以福将者。不其验欤。虽其持廉至死。无以庇赖其子孙。而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7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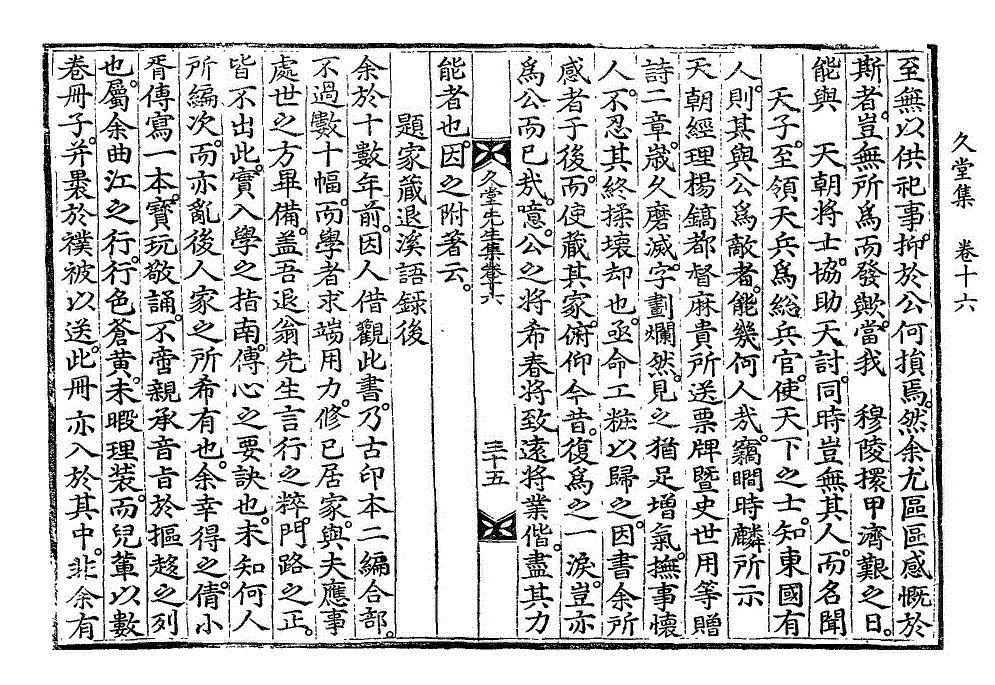 至无以供祀事。抑于公何损焉。然余尤区区感慨于斯者。岂无所为而发欤。当我 穆陵擐甲济艰之日。能与 天朝将士。协助天讨。同时岂无其人。而名闻 天子。至领天兵为总兵官。使天下之士。知东国有人。则其与公为敌者。能几何人哉。窃瞯时麟所示 天朝经理杨镐,都督麻贵所送票牌暨史世用等赠诗二章。岁久磨灭。字划烂然。见之犹足增气。抚事怀人。不忍其终揉坏却也。亟命工妆以归之。因书余所感者于后。而使藏其家。俯仰今昔。复为之一泪。岂亦为公而已哉。噫。公之将希春将致远将业偕。尽其力能者也。因之附著云。
至无以供祀事。抑于公何损焉。然余尤区区感慨于斯者。岂无所为而发欤。当我 穆陵擐甲济艰之日。能与 天朝将士。协助天讨。同时岂无其人。而名闻 天子。至领天兵为总兵官。使天下之士。知东国有人。则其与公为敌者。能几何人哉。窃瞯时麟所示 天朝经理杨镐,都督麻贵所送票牌暨史世用等赠诗二章。岁久磨灭。字划烂然。见之犹足增气。抚事怀人。不忍其终揉坏却也。亟命工妆以归之。因书余所感者于后。而使藏其家。俯仰今昔。复为之一泪。岂亦为公而已哉。噫。公之将希春将致远将业偕。尽其力能者也。因之附著云。题家藏退溪语录后
余于十数年前。因人借观此书。乃古印本二编合部。不过数十幅。而学者求端用力。修己居家。与夫应事处世之方毕备。盖吾退翁先生言行之粹。门路之正。皆不出此。实入学之指南。传心之要诀也。未知何人所编次。而亦乱后人家之所希有也。余幸得之。倩小胥传写一本。宝玩敬诵。不啻亲承音旨于抠趋之列也。属余曲江之行。行色苍黄。未暇理装。而儿辈以数卷册子。并裹于襆被以送。此册亦入于其中。非余有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7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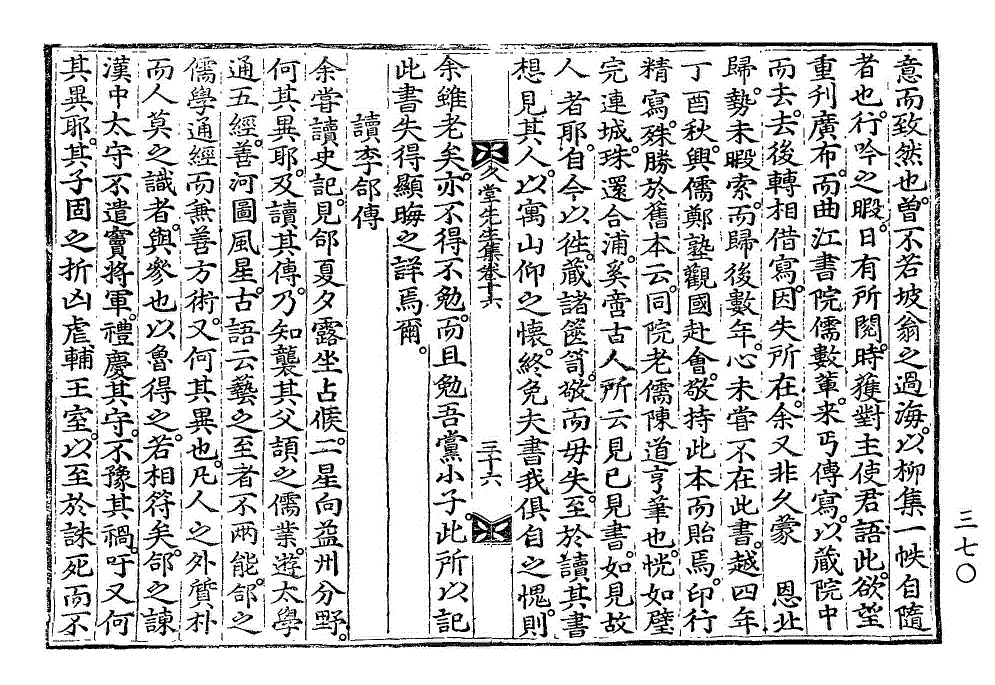 意而致然也。曾不若坡翁之过海。以柳集一帙自随者也。行吟之暇。日有所阅。时获对主使君语此。欲望重刊广布。而曲江书院儒数辈。来丐传写。以藏院中而去。去后转相借写。因失所在。余又非久蒙 恩北归。势未暇索。而归后数年。心未尝不在此书。越四年丁酉秋。兴儒郑塾观国赴会。敬持此本而贻焉。印行精写。殊胜于旧本云。同院老儒陈道亨笔也。恍如璧完连城。珠还合浦。奚啻古人所云见己见书。如见故人者耶。自今以往。藏诸箧笥。敬而毋失。至于读其书想见其人。以寓山仰之怀。终免夫书我俱自之愧。则余虽老矣。亦不得不勉。而且勉吾党小子。此所以记此书失得显晦之详焉尔。
意而致然也。曾不若坡翁之过海。以柳集一帙自随者也。行吟之暇。日有所阅。时获对主使君语此。欲望重刊广布。而曲江书院儒数辈。来丐传写。以藏院中而去。去后转相借写。因失所在。余又非久蒙 恩北归。势未暇索。而归后数年。心未尝不在此书。越四年丁酉秋。兴儒郑塾观国赴会。敬持此本而贻焉。印行精写。殊胜于旧本云。同院老儒陈道亨笔也。恍如璧完连城。珠还合浦。奚啻古人所云见己见书。如见故人者耶。自今以往。藏诸箧笥。敬而毋失。至于读其书想见其人。以寓山仰之怀。终免夫书我俱自之愧。则余虽老矣。亦不得不勉。而且勉吾党小子。此所以记此书失得显晦之详焉尔。读李合传
余尝读史记。见合夏夕露坐占候。二星向益州分野。何其异耶。及读其传。乃知袭其父颉之儒业。游太学通五经。善河图风星。古语云艺之至者不两能。合之儒学通经而兼善方术。又何其异也。凡人之外质朴而人莫之识者。与参也以鲁得之。若相符矣。合之谏汉中太守不遣窦将军。礼庆其守。不豫其祸。吁又何其异耶。其子固之折凶虐辅王室。以至于诛死而不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71H 页
 悔。盖有以也哉。然亦扶倾补败。弘济艰难。然后乃可谓克家子孙矣。
悔。盖有以也哉。然亦扶倾补败。弘济艰难。然后乃可谓克家子孙矣。读梁鸿传
余幼好缀文。欲学为词赋而未能。粗学科体赋。未能十首而止矣。科赋使梁鸿五噫歌语而曰。噫有五于梁生云尔。且学为诗。诗中多有孟光字。盖自古诗人谓妻为孟光。而亦不知孟光之为梁鸿妻。又不知梁鸿之为何代人。及读其传。其为人。盖党光以上人者非耶。其适吴作诗十二句。度越屈贾。以如此之才。作五噫之歌。而见非于明主。终殁于皋伯通之庑下。吁何其穷也。如伯通辈亦知其为非常人。为求葬地于吴。而葬于要离冢傍。咸曰要离烈士也。彼佣何其知音若此哉。思其友扶风高恢诗三句古矣。后世无继焉。恢乃少好老子者。而鸿则虽称受业太学。不举儒与老。得非与恢俱学老子者耶。是未可知也。
李判书,张别提书后跋。
东峡西溟。迂回阻隔。常思之邈然。忽得令翰。飨仪兼备。深认雅眷不替。感慰十分。信后岁换。惟侍奉吉庆。生自去腊。旧症添剧。委卧已两朔。尚未少苏。世缘当自此了矣。令侍福智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7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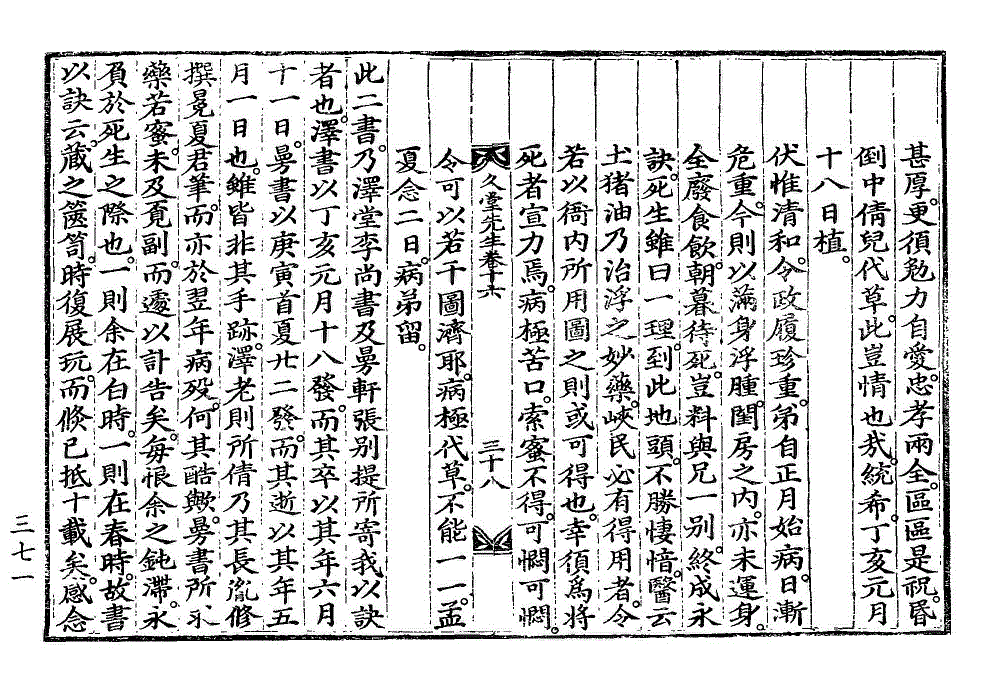 甚厚。更须勉力自爱。忠孝两全。区区是祝。昏倒中倩儿代草。此岂情也哉。统希。丁亥元月十八日植。
甚厚。更须勉力自爱。忠孝两全。区区是祝。昏倒中倩儿代草。此岂情也哉。统希。丁亥元月十八日植。伏惟清和。令政履珍重。弟自正月始病。日渐危重。今则以满身浮肿。闺房之内。亦未运身。全废食饮。朝暮待死。岂料与兄一别。终成永诀。死生虽曰一理。到此地头。不胜悽愔。医云土猪油乃治浮之妙药。峡民必有得用者。令若以衙内所用图之则或可得也。幸须为将死者宣力焉。病极苦口。索蜜不得。可悯可悯。令可以若干图济耶。病极代草。不能一一。孟夏念二日。病弟留。
此二书。乃泽堂李尚书及曼轩张别提所寄我以诀者也。泽书以丁亥元月十八发。而其卒以其年六月十一日。曼书以庚寅首夏廿二发。而其逝以其年五月一日也。虽皆非其手迹。泽老则所倩乃其长胤修撰冕夏君笔。而亦于翌年病殁。何其酷欤。曼书所求药若蜜。未及觅副。而遽以讣告矣。每恨余之钝滞。永负于死生之际也。一则余在白时。一则在春时。故书以诀云。藏之箧笥。时复展玩。而倏已抵十载矣。感念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7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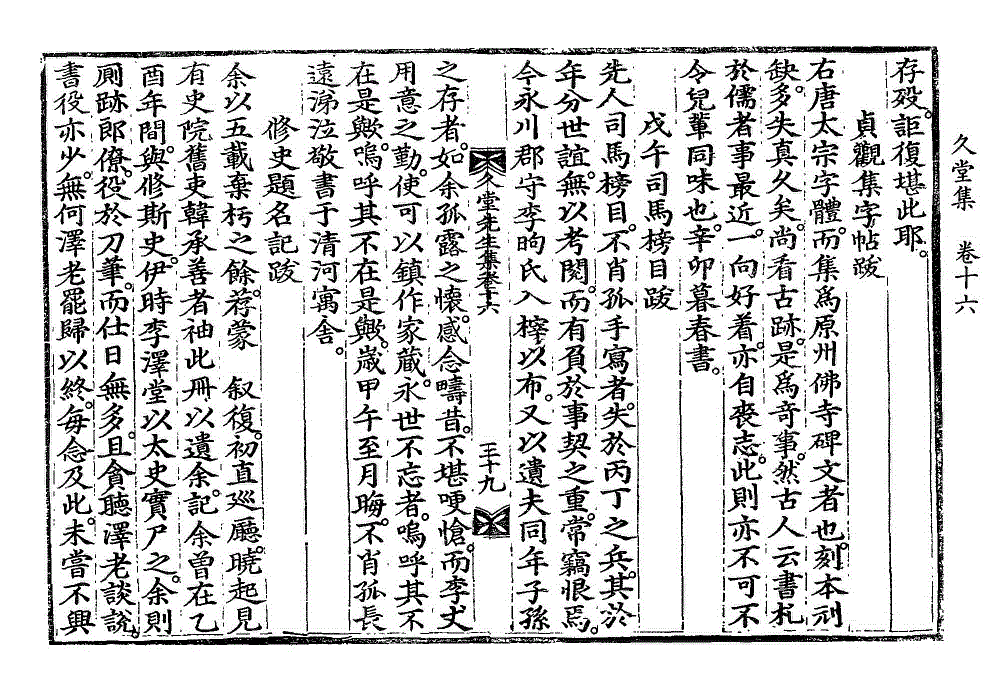 存殁。讵复堪此耶。
存殁。讵复堪此耶。贞观集字帖跋
右唐太宗字体。而集为原州佛寺碑文者也。刻本刓缺。多失真久矣。尚看古迹。是为奇事。然古人云书札于儒者事最近。一向好着。亦自丧志。此则亦不可不令儿辈同味也。辛卯暮春书。
戊午司马榜目跋
先人司马榜目。不肖孤手写者。失于丙丁之兵。其于年分世谊。无以考阅。而有负于事契之重。常窃恨焉。今永川郡守李煦氏入梓以布。又以遗夫同年子孙之存者。如余孤露之怀。感念畴昔。不堪哽怆。而李丈用意之勤。使可以镇作家藏。永世不忘者。呜呼其不在是欤。呜呼其不在是欤。岁甲午至月晦。不肖孤长远涕泣敬书于清河寓舍。
修史题名记跋
余以五载弃朽之馀。荐蒙 叙复。初直巡厅。晓起见有史院旧吏韩承善者袖此册以遗余。记余曾在乙酉年间。与修斯史。伊时李泽堂以太史实尸之。余则厕迹郎僚。役于刀笔。而仕日无多。且贪听泽老谈说。书役亦少。无何泽老罢归以终。每念及此。未尝不兴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7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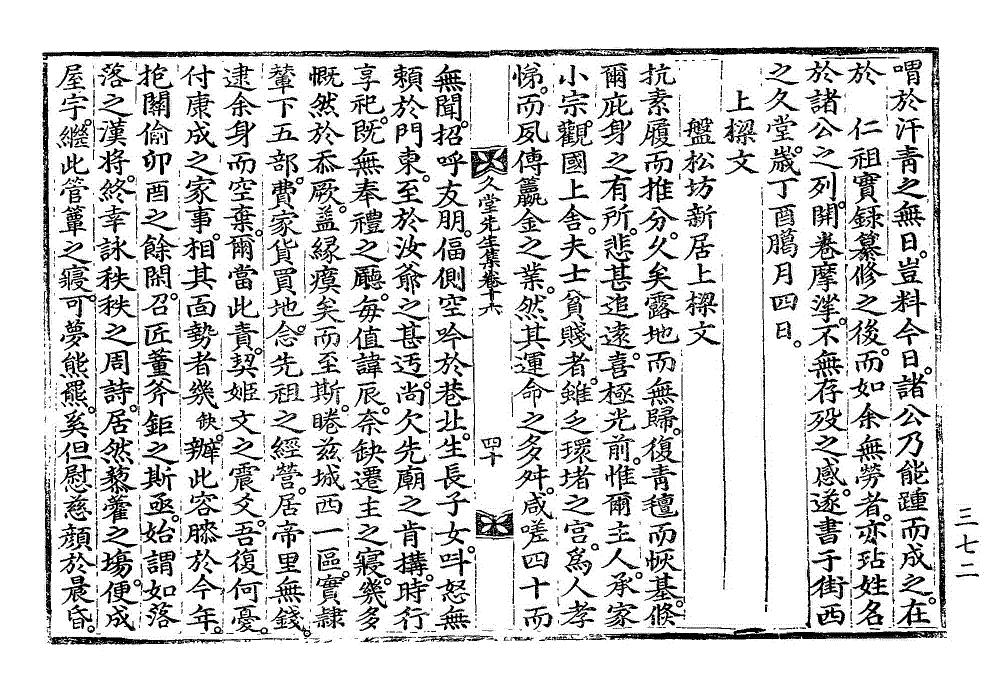 喟于汗青之无日。岂料今日。诸公乃能踵而成之。在于 仁祖实录纂修之后。而如余无劳者。亦玷姓名于诸公之列。开卷摩挲。不无存殁之感。遂书于街西之久堂。岁丁酉腊月四日。
喟于汗青之无日。岂料今日。诸公乃能踵而成之。在于 仁祖实录纂修之后。而如余无劳者。亦玷姓名于诸公之列。开卷摩挲。不无存殁之感。遂书于街西之久堂。岁丁酉腊月四日。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
上梁文
盘松坊新居上梁文
抗素履而推分。久矣露地而无归。复青毡而恢基。倏尔庇身之有所。悲甚追远。喜极光前。惟尔主人。承家小宗。观国上舍。夫士贫贱者。虽乏环堵之宫。为人孝悌。而夙传籯金之业。然其运命之多舛。咸嗟四十而无闻。招呼友朋。偪侧空吟于巷北。生长子女。叫怒无赖于门东。至于汝爷之甚迂。尚欠先庙之肯搆。时行享祀。既无奉礼之厅。每值讳辰。奈缺迁主之寝。几多慨然于忝厥。盖缘瘼矣而至斯。眷兹城西一区。实隶辇下五部。费家货买地。念先祖之经营。居帝里无钱。逮余身而空弃。尔当此责。契姬文之震爻。吾复何忧。付康成之家事。相其面势者几(缺)。办此容膝于今年。抱关偷卯酉之馀闲。召匠董斧钜之斯亟。始谓如落落之汉将。终幸咏秩秩之周诗。居然藜藿之场。便成屋宇。继此管簟之寝。可梦熊罴。奚但慰慈颜于晨昏。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73H 页
 抑亦赖先灵之扶佑。君子先立。虽少缺于宏规。来者可追。庶渐寻其坠绪。邻人交贺。过者腾谣。聊当上梁。不觉赞伟。
抑亦赖先灵之扶佑。君子先立。虽少缺于宏规。来者可追。庶渐寻其坠绪。邻人交贺。过者腾谣。聊当上梁。不觉赞伟。儿郎伟抛梁东。一面京城百雉崇。孝子由来有深爱。每看晨旭吐窗红。
儿郎伟抛梁西。饼岘鞍峰接路蹊。欲识太平佳气象。壮元坊里暮烟低。
儿郎伟抛梁南。石井天云下上涵。漱玉时时移杖步。青溪增目翠挼蓝。
儿郎伟抛梁北。万世仁王瞻峻极。忧国观星步夜蟾。祝尧圣寿弥千亿。
儿郎伟抛梁上。舍北一丘堪倚杖。冠麓芝山入眼青。松楸日日遥相望。
儿郎伟抛梁下。夜绩灯光共邻舍。只是门前有路岐。出为小草犹堪怕。
伏愿上梁之后。居家一乐。保躯千金。马勒继绳。佩户曹清白之训。蛙缩远步。绍交河忠厚之风。添尧民比屋之封。期杜老广厦之庇。俯同拾芥之青紫。要识行藏。森如立竹之曾玄。皆习诗礼。外此无可祝者。自馀又何足云。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 第 373L 页
 城西旧舍大门上梁文
城西旧舍大门上梁文身外即浮云。未完子荆之室。眼前见此屋。先起于公之门。人皆改观。过者称庆。主人风尘一出。簪组半生。朱门临衢。心久灰于富贵。黄金横带。志恒存于荜圭。聊将经乱之微躯。甘处抛荒之旧舍。先咷后笑。楚水十年归来。上雨傍风。洛城数间而已。胥徒呈身之无所。来客骑马而到阶。遂捐孟尉半俸之资。以办陶令常关之设。斧彼钜彼。粗费数日之工。经之营之。倏见双扉之启。每吟退食。庶可慰于倚闾。虽赋空囊。更无忧于御暴。第愧欧阳无一瓦之覆。幸祝万石由积善而兴。咨尔工师。听余谣颂。伏愿上梁之后。导鱼轩而出入无恙。拄鸠杖而往来适宜。学要窥藩。谁为立雪之士。身常处室。应无题凤之人。俨百神之撝诃。森众稚之相候。惟南献寿。拱北驰诚。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
箴
至日率占小箴示二子求和
冬至至日。一阳初动。善端绵绵。心具体用。体用一源。天地之心。人惟有欲。形役乃禽。要免禽兽。莫贵乎复。复之如何。亦贵庸玉。玉不在身。主善为师。嗟尔小子。盍勉于斯。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
铭
损斋铭
事有本末。惟华胜质。敬哉有土。损浮就实。有理有欲。惟欲难制。敬哉有土。损欲复礼。刻铭于斋。汤盘是替。
戏作破砚铭(并序)
南来得一石砚。砚池一隅微有瑕颣。常护而用之。忽为童子所涤濯而破。渠心懊欲就漆工而续之。余思之。此安知非弃而北归之兆耶。又安知使我绝意于操毫弄墨。而游心于邃古之初而然耶。勿令更续。笑而为之铭。铭曰。
惟尔之破。我之全兮。谢尔石交。反我画之前兮。
久堂先生集卷之十六
赞
陶靖节画像赞(梦作)
人间读史。梦里求仙。我拜遗像。不觉千年。
画像赞(辛亥病里作)
所貌者容。难写者心。焉廋在眸。可质来今。禄满宜退。被以野服。用贻子孙。明我心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