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明: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.org,kanripo.org, db.itkc.or.kr 和 zh.wikisource.org
渼湖集卷之十 第 x 页
渼湖集卷之十
书
书
渼湖集卷之十 第 199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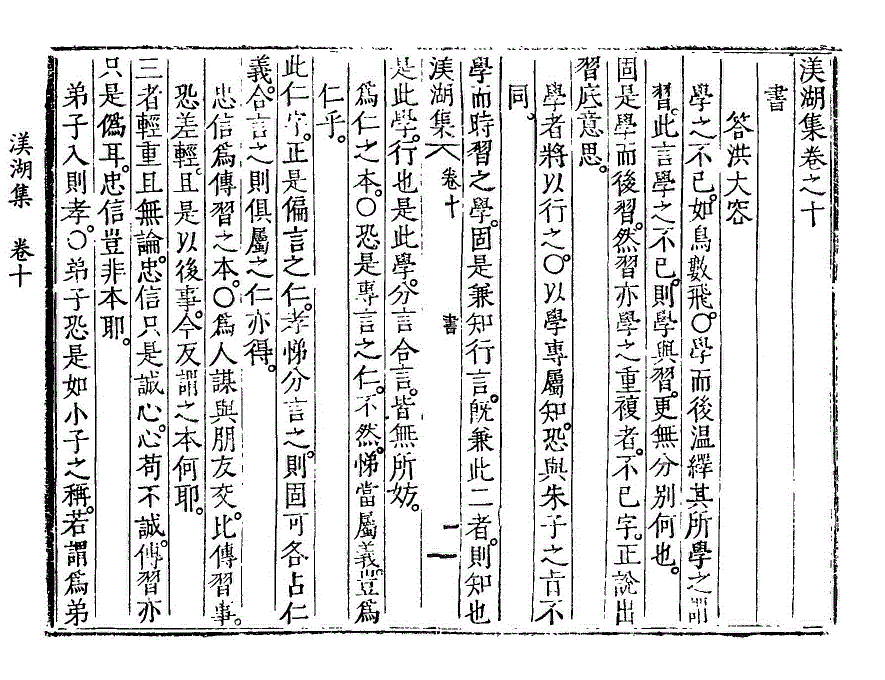 答洪大容
答洪大容学之不已。如鸟数飞。○学而后温绎其所学之谓习。此言学之不已。则学与习。更无分别何也。
固是学而后习。然习亦学之重复者。不已字。正说出习底意思。
学者将以行之。○以学专属知。恐与朱子之旨不同。
学而时习之学。固是兼知行言。既兼此二者。则知也是此学。行也是此学。分言合言。皆无所妨。
为仁之本。○恐是专言之仁。不然。悌当属义。岂为仁乎。
此仁字。正是偏言之仁。孝悌分言之。则固可各占仁义。合言之则俱属之仁亦得。
忠信为传习之本。○为人谋与朋友交。比传习事。恐差轻。且是以后事。今反谓之本何耶。
三者轻重且无论。忠信只是诚心。心苟不诚。传习亦只是伪耳。忠信岂非本耶。
弟子入则孝。○弟子恐是如小子之称。若谓为弟
渼湖集卷之十 第 19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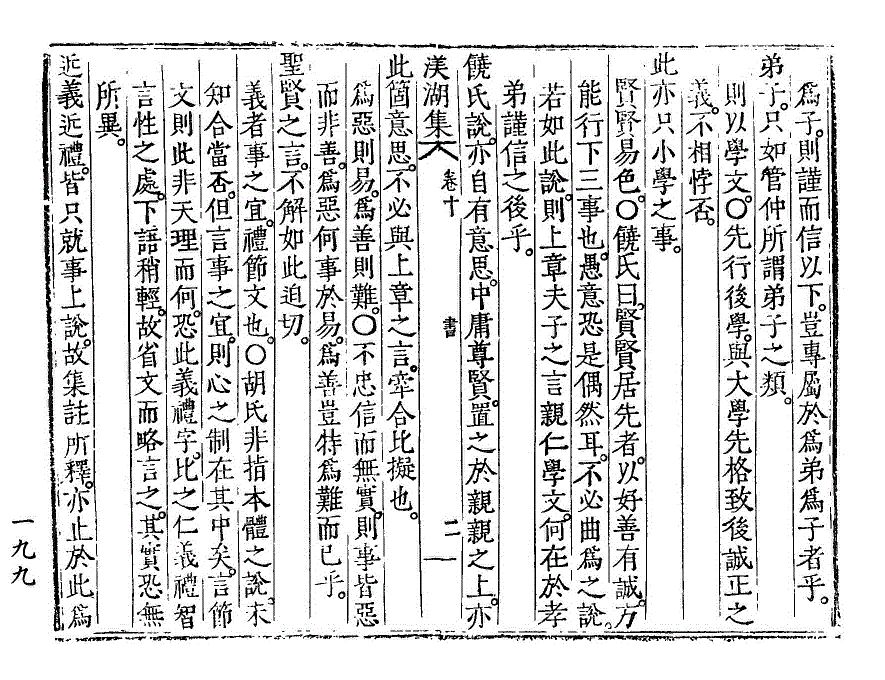 为子。则谨而信以下。岂专属于为弟为子者乎。
为子。则谨而信以下。岂专属于为弟为子者乎。弟子。只如管仲所谓弟子之类。
则以学文。○先行后学。与大学先格致后诚正之义。不相悖否。
此亦只小学之事。
贤贤易色。○饶氏曰。贤贤居先者。以好善有诚。方能行下三事也。愚意恐是偶然耳。不必曲为之说。若如此说。则上章夫子之言亲仁学文。何在于孝弟谨信之后乎。
饶氏说。亦自有意思。中庸尊贤。置之于亲亲之上。亦此个意思。不必与上章之言。牵合比拟也。
为恶则易。为善则难。○不忠信而无实。则事皆恶而非善。为恶何事于易。为善岂特为难而已乎。
圣贤之言。不解如此迫切。
义者事之宜。礼节文也。○胡氏非指本体之说。未知合当否。但言事之宜。则心之制在其中矣。言节文则此非天理而何。恐此义礼字。比之仁义礼智言性之处。下语稍轻。故省文而略言之。其实恐无所异。
近义近礼。皆只就事上说。故集注所释。亦止于此为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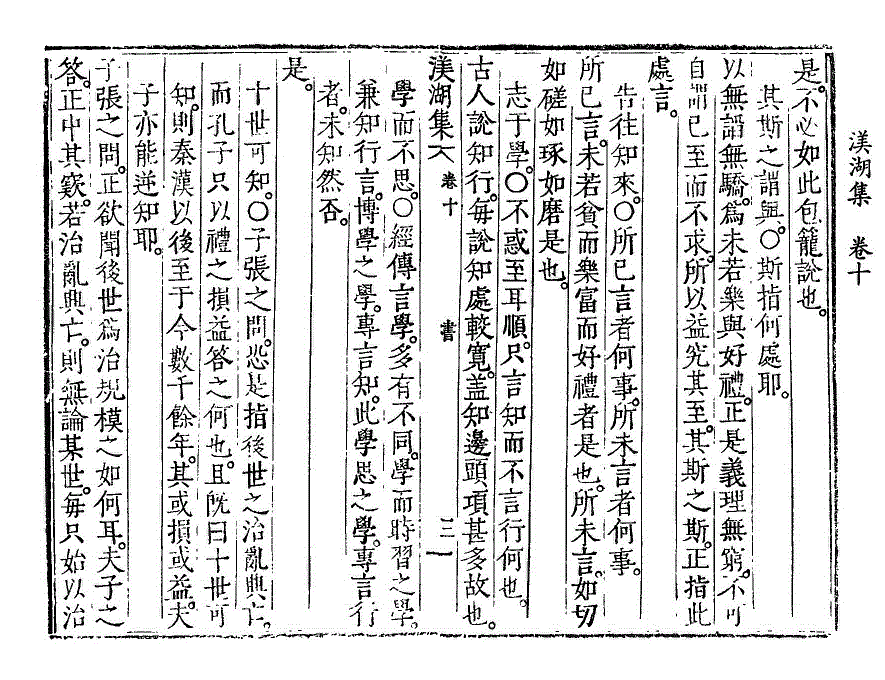 是。不必如此包笼说也。
是。不必如此包笼说也。其斯之谓与。○斯指何处耶。
以无谄无骄。为未若乐与好礼。正是义理无穷。不可自谓已至而不求。所以益究其至。其斯之斯。正指此处言。
告往知来。○所已言者何事。所未言者何事。
所已言。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是也。所未言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也。
志于学。○不惑至耳顺。只言知而不言行何也。
古人说知行。每说知处较宽。盖知边头项甚多故也。
学而不思。○经传言学。多有不同。学而时习之学。兼知行言。博学之学。专言知。此学思之学。专言行者。未知然否。
是。
十世可知。○子张之问。恐是指后世之治乱兴亡。而孔子只以礼之损益答之何也。且既曰十世可知。则秦汉以后至于今数千馀年。其或损或益。夫子亦能逆知耶。
子张之问。正欲闻后世为治规模之如何耳。夫子之答。正中其窾。若治乱兴亡。则无论某世。每只始以治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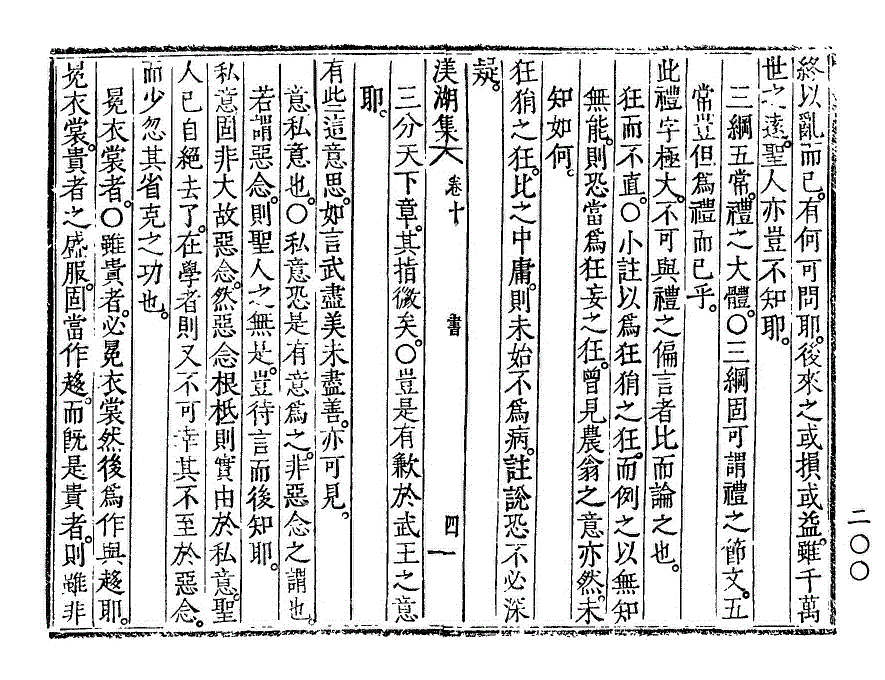 终以乱而已。有何可问耶。后来之或损或益。虽千万世之远。圣人亦岂不知耶。
终以乱而已。有何可问耶。后来之或损或益。虽千万世之远。圣人亦岂不知耶。三纲五常。礼之大体。○三纲固可谓礼之节文。五常岂但为礼而已乎。
此礼字极大。不可与礼之偏言者比而论之也。
狂而不直。○小注以为狂狷之狂。而例之以无知无能。则恐当为狂妄之狂。曾见农翁之意亦然。未知如何。
狂狷之狂。比之中庸。则未始不为病。注说恐不必深疑。
三分天下章。其指微矣。○岂是有歉于武王之意耶。
有些这意思。如言武尽美未尽善。亦可见。
意私意也。○私意恐是有意为之。非恶念之谓也。若谓恶念。则圣人之无是。岂待言而后知耶。
私意固非大故恶念。然恶念根柢则实由于私意。圣人已自绝去了。在学者则又不可幸其不至于恶念。而少忽其省克之功也。
冕衣裳者。○虽贵者。必冕衣裳然后为作与趍耶。
冕衣裳。贵者之盛服。固当作趍。而既是贵者。则虽非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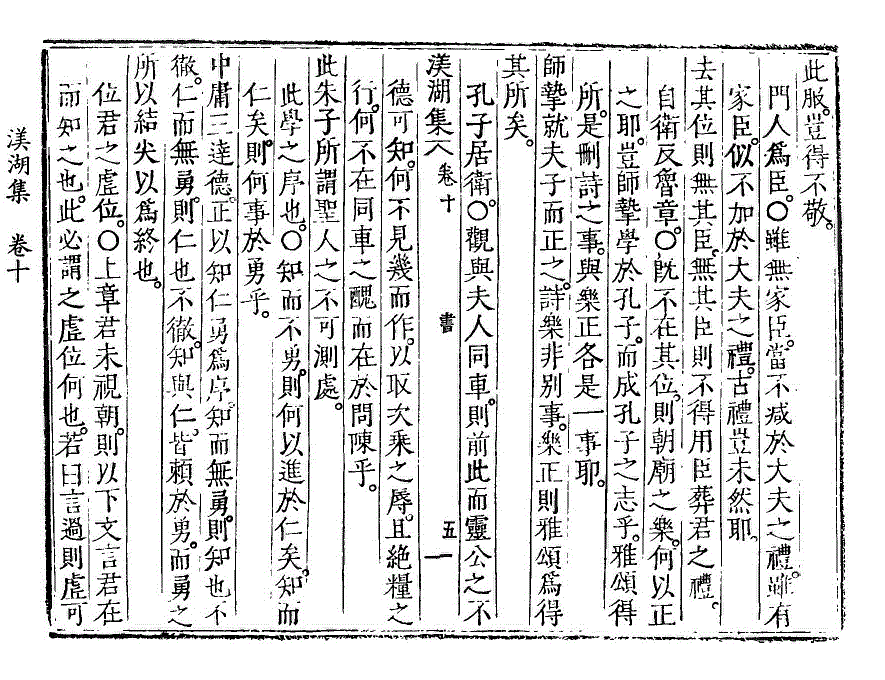 此服。岂得不敬。
此服。岂得不敬。门人为臣。○虽无家臣。当不减于大夫之礼。虽有家臣。似不加于大夫之礼。古礼岂未然耶。
去其位则无其臣。无其臣则不得用臣葬君之礼。
自卫反鲁章。○既不在其位。则朝庙之乐。何以正之耶。岂师挚学于孔子。而成孔子之志乎。雅颂得所。是删诗之事。与乐正各是一事耶。
师挚就夫子而正之。诗乐非别事。乐正则雅颂为得其所矣。
孔子居卫。○观与夫人同车。则前此而灵公之不德可知。何不见几而作。以取次乘之辱。且绝粮之行。何不在同车之丑而在于问陈乎。
此朱子所谓圣人之不可测处。
此学之序也。○知而不勇。则何以进于仁矣。知而仁矣。则何事于勇乎。
中庸三达德。正以知仁勇为序。知而无勇。则知也不彻。仁而无勇。则仁也不彻。知与仁。皆赖于勇。而勇之所以结尖以为终也。
位君之虚位。○上章君未视朝。则以下文言君在而知之也。此必谓之虚位何也。若曰言过则虚可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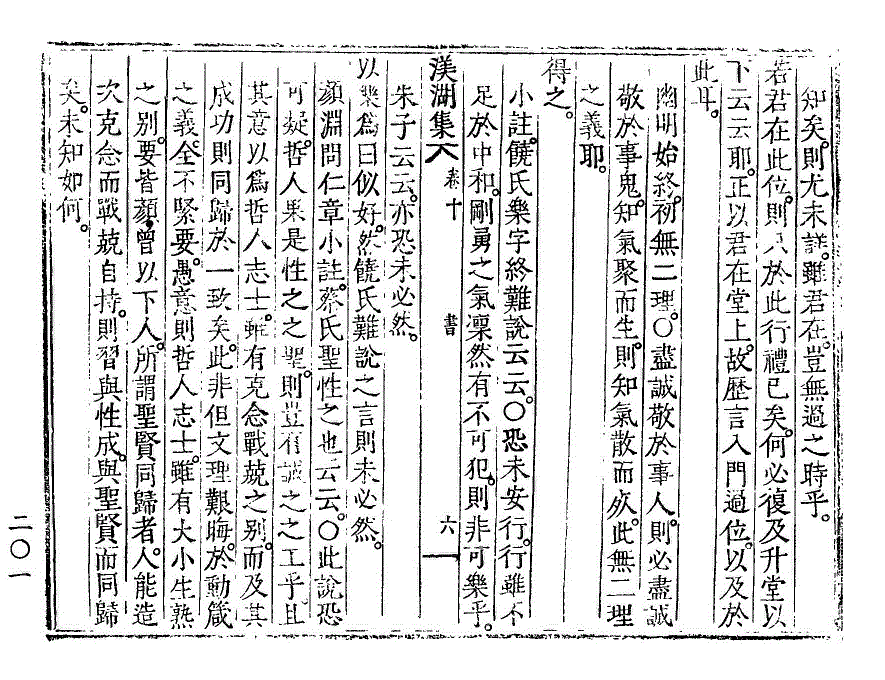 知矣。则尤未详。虽君在。岂无过之时乎。
知矣。则尤未详。虽君在。岂无过之时乎。若君在此位。则只于此行礼已矣。何必复及升堂以下云云耶。正以君在堂上。故历言入门过位。以及于此耳。
幽明始终。初无二理。○尽诚敬于事人。则必尽诚敬于事鬼。知气聚而生。则知气散而死。此无二理之义耶。
得之。
小注。饶氏乐字终难说云云。○恐未安行。行虽不足于中和。刚勇之气凛然有不可犯。则非可乐乎。朱子云云。亦恐未必然。
以乐为曰似好。然饶氏难说之言则未必然。
颜渊问仁章小注。蔡氏圣性之也云云。○此说恐可疑。哲人果是性之之圣。则岂有诚之之工乎。且其意以为哲人志士。虽有克念战兢之别。而及其成功则同归于一致矣。此非但文理艰晦。于动箴之义。全不紧要。愚意则哲人志士。虽有大小生熟之别。要皆颜,曾以下人。所谓圣贤同归者。人能造次克念而战兢自持。则习与性成。与圣贤而同归矣。未知如何。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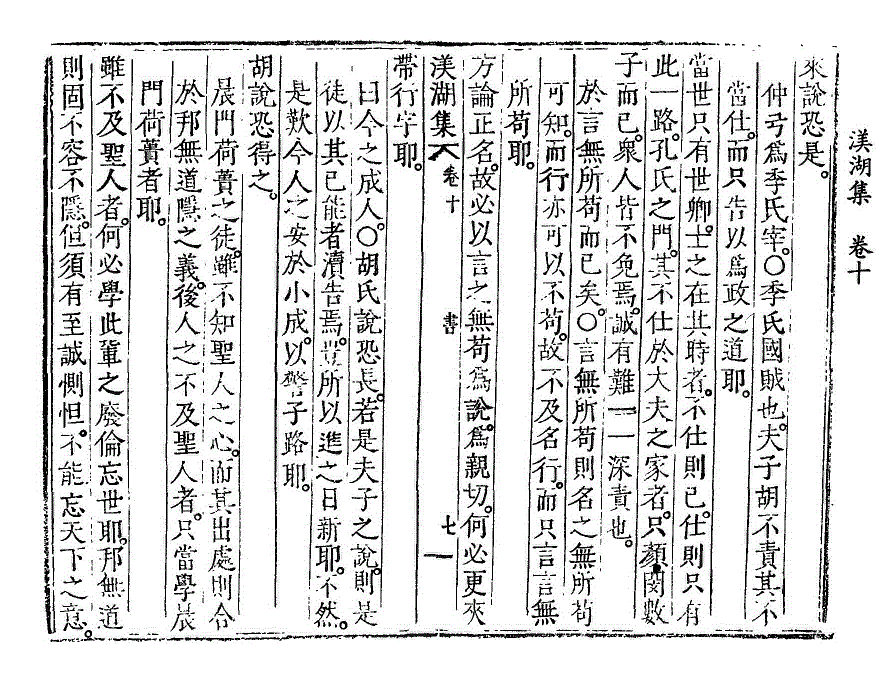 来说恐是。
来说恐是。仲弓为季氏宰。○季氏国贼也。夫子胡不责其不当仕。而只告以为政之道耶。
当世只有世卿。士之在其时者。不仕则已。仕则只有此一路。孔氏之门。其不仕于大夫之家者。只颜,闵数子而已。众人皆不免焉。诚有难一一深责也。
于言无所苟而已矣。○言无所苟则名之无所苟可知。而行亦可以不苟。故不及名行。而只言言无所苟耶。
方论正名。故必以言之无苟为说。为亲切。何必更夹带行字耶。
曰今之成人。○胡氏说恐长。若是夫子之说。则是徒以其已能者渎告焉。岂所以进之日新耶。不然。是叹今人之安于小成。以警子路耶。
胡说恐得之。
晨门荷蒉之徒。虽不知圣人之心。而其出处则合于邦无道隐之义。后人之不及圣人者。只当学晨门荷蒉者耶。
虽不及圣人者。何必学此辈之废伦忘世耶。邦无道则固不容不隐。但须有至诚恻怛。不能忘天下之意。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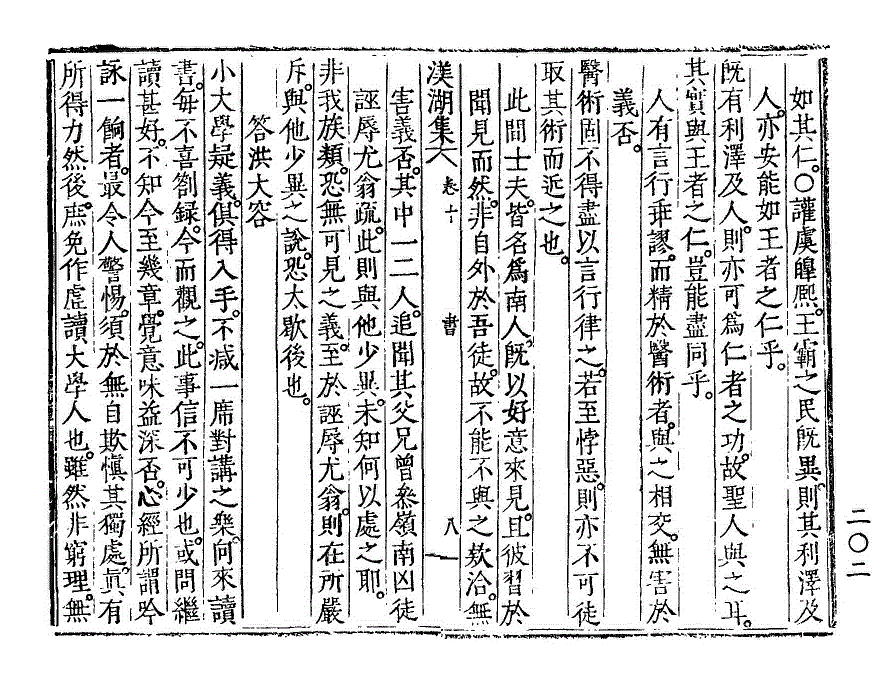 如其仁。○欢虞皞熙。王霸之民既异。则其利泽及人。亦安能如王者之仁乎。
如其仁。○欢虞皞熙。王霸之民既异。则其利泽及人。亦安能如王者之仁乎。既有利泽及人。则亦可为仁者之功。故圣人与之耳。其实与王者之仁。岂能尽同乎。
人有言行乖谬。而精于医术者。与之相交。无害于义否。
医术固不得尽以言行律之。若至悖恶。则亦不可徒取其术而近之也。
此间士夫。皆名为南人。既以好意来见。且彼习于闻见而然。非自外于吾徒。故不能不与之款洽。无害义否。其中一二人。追闻其父兄曾参岭南凶徒诬辱尤翁疏。此则与他少异。未知何以处之耶。
非我族类。恐无可见之义。至于诬辱尤翁。则在所严斥。与他少异之说。恐太歇后也。
答洪大容
小大学疑义。俱得入手。不减一席对讲之乐。向来读书。每不喜劄录。今而观之。此事信不可少也。或问继读甚好。不知今至几章。觉意味益深否。心经所谓吟咏一饷者。最令人警惕。须于无自欺慎其独处。真有所得力然后。庶免作虚读大学人也。虽然非穷理。无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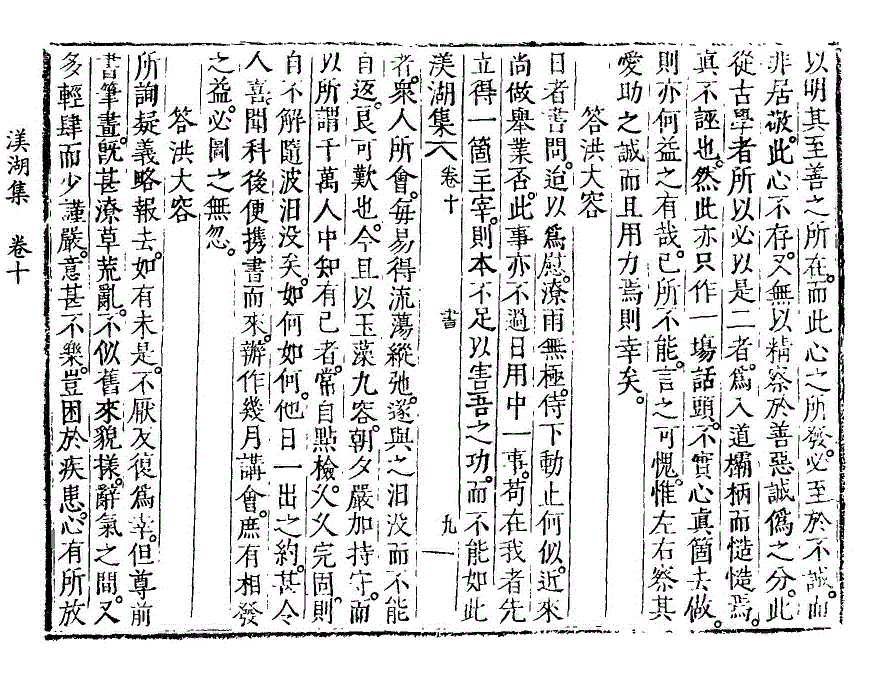 以明其至善之所在。而此心之所发。必至于不诚。而非居敬。此心不存。又无以精察于善恶诚伪之分。此从古学者所以必以是二者。为入道把柄而慥慥焉。真不诬也。然此亦只作一场话头。不实心真个去做。则亦何益之有哉。己所不能。言之可愧。惟左右察其爱助之诚而且用力焉则幸矣。
以明其至善之所在。而此心之所发。必至于不诚。而非居敬。此心不存。又无以精察于善恶诚伪之分。此从古学者所以必以是二者。为入道把柄而慥慥焉。真不诬也。然此亦只作一场话头。不实心真个去做。则亦何益之有哉。己所不能。言之可愧。惟左右察其爱助之诚而且用力焉则幸矣。答洪大容
日者书问。迨以为慰。潦雨无极。侍下动止何似。近来尚做举业否。此事亦不过日用中一事。苟在我者先立得一个主宰。则本不足以害吾之功。而不能如此者。众人所会。每易得流荡纵弛。遂与之汨没而不能自返。良可叹也。今且以玉藻九容。朝夕严加持守。而以所谓千万人中知有己者。常自点检。久久完固。则自不解随波汨没矣。如何如何。他日一出之约。甚令人喜。闻科后便携书而来。办作几月讲会。庶有相发之益。必图之无忽。
答洪大容
所询疑义略报去。如有未是。不厌反复为幸。但尊前书笔画。既甚潦草荒乱。不似旧来貌㨾。辞气之间。又多轻肆而少谨严。意甚不乐。岂困于疾患。心有所放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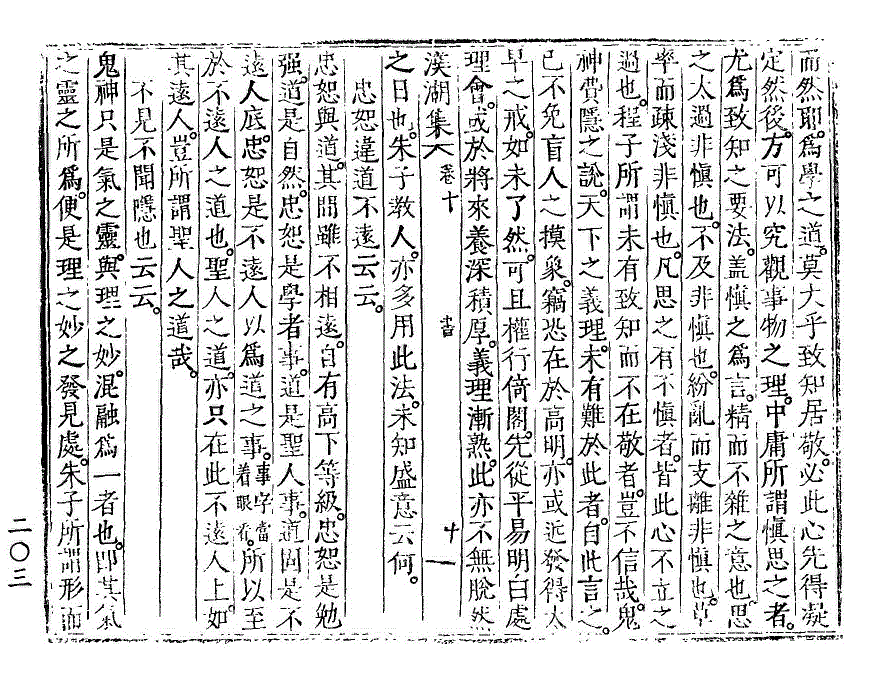 而然耶。为学之道。莫大乎致知居敬。必此心先得凝定然后。方可以究观事物之理。中庸所谓慎思之者。尤为致知之要法。盖慎之为言。精而不杂之意也。思之太过非慎也。不及非慎也。纷乱而支离非慎也。草率而疏浅非慎也。凡思之有不慎者。皆此心不立之过也。程子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。岂不信哉。鬼神费隐之说。天下之义理。未有难于此者。自此言之。已不免盲人之摸象。窃恐在于高明。亦或近发得太早之戒。如未了然。可且权行倚阁。先从平易明白处理会。或于将来养深积厚。义理渐熟。此亦不无脱然之日也。朱子教人。亦多用此法。未知盛意云何。
而然耶。为学之道。莫大乎致知居敬。必此心先得凝定然后。方可以究观事物之理。中庸所谓慎思之者。尤为致知之要法。盖慎之为言。精而不杂之意也。思之太过非慎也。不及非慎也。纷乱而支离非慎也。草率而疏浅非慎也。凡思之有不慎者。皆此心不立之过也。程子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。岂不信哉。鬼神费隐之说。天下之义理。未有难于此者。自此言之。已不免盲人之摸象。窃恐在于高明。亦或近发得太早之戒。如未了然。可且权行倚阁。先从平易明白处理会。或于将来养深积厚。义理渐熟。此亦不无脱然之日也。朱子教人。亦多用此法。未知盛意云何。忠恕违道不远云云。
忠恕与道。其间虽不相远。自有高下等级。忠恕是勉强。道是自然。忠恕是学者事。道是圣人事。道固是不远人底。忠恕是不远人以为道之事。(事字当着眼看。)所以至于不远人之道也。圣人之道。亦只在此不远人上。如其远人。岂所谓圣人之道哉。
不见不闻隐也云云。
鬼神只是气之灵。与理之妙。混融为一者也。即其气之灵之所为。便是理之妙之发见处。朱子所谓形而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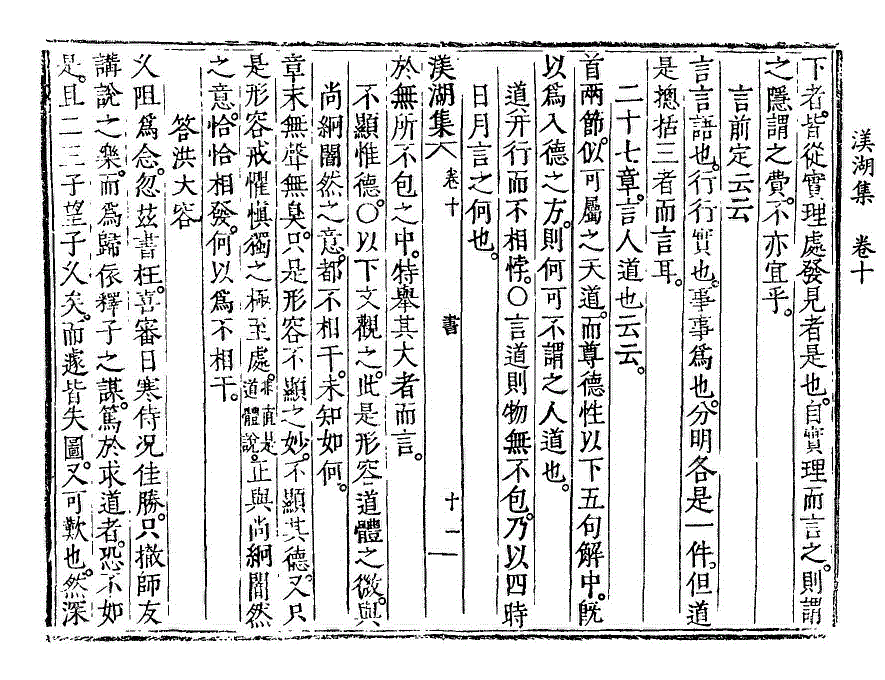 下者。皆从实理处发见者是也。自实理而言之。则谓之隐谓之费。不亦宜乎。
下者。皆从实理处发见者是也。自实理而言之。则谓之隐谓之费。不亦宜乎。言前定云云。
言言语也。行行实也。事事为也。分明各是一件。但道是总括三者而言耳。
二十七章。言人道也云云。
首两节。似可属之天道。而尊德性以下五句解中。既以为入德之方。则何可不谓之人道也。
道并行而不相悖。○言道则物无不包。乃以四时日月言之何也。
于无所不包之中。特举其大者而言。
不显惟德。○以下文观之。此是形容道体之微。与尚絅闇然之意。都不相干。未知如何。
章末无声无臭。只是形容不显之妙。不显其德。又只是形容戒惧慎独之极至处。(非直是道体说。)正与尚絅闇然之意。恰恰相发。何以为不相干。
答洪大容
久阻为念。忽玆书枉。喜审日寒侍况佳胜。只撤师友讲说之乐。而为归依释子之谋。笃于求道者。恐不如是。且二三子望子久矣。而遽皆失图。又可叹也。然深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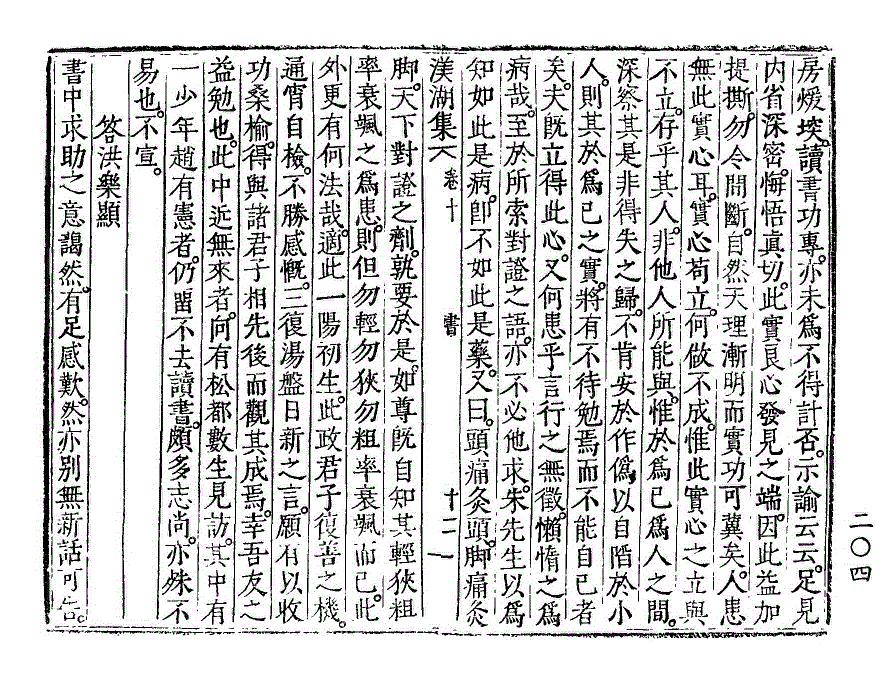 房煖突。读书功专。亦未为不得计否。示谕云云。足见内省深密。悔悟真切。此实良心发见之端。因此益加提撕。勿令间断。自然天理渐明而实功可冀矣。人患无此实心耳。实心苟立。何做不成。惟此实心之立与不立。存乎其人。非他人所能与。惟于为己为人之间。深察其是非得失之归。不肯安于作伪以自陷于小人。则其于为己之实。将有不待勉焉而不能自已者矣。夫既立得此心。又何患乎言行之无徵。懒惰之为病哉。至于所索对證之语。亦不必他求。朱先生以为知如此是病。即不如此是药。又曰。头痛灸头。脚痛灸脚。天下对證之剂。孰要于是。如尊既自知其轻狭粗率衰飒之为患。则但勿轻勿狭勿粗率衰飒而已。此外更有何法哉。适此一阳初生。此政君子复善之机。通宵自检。不胜感慨。三复汤盘日新之言。愿有以收功桑榆。得与诸君子相先后而观其成焉。幸吾友之益勉也。此中近无来者。向有松都数生见访。其中有一少年赵有宪者。仍留不去读书。颇多志尚。亦殊不易也。不宣。
房煖突。读书功专。亦未为不得计否。示谕云云。足见内省深密。悔悟真切。此实良心发见之端。因此益加提撕。勿令间断。自然天理渐明而实功可冀矣。人患无此实心耳。实心苟立。何做不成。惟此实心之立与不立。存乎其人。非他人所能与。惟于为己为人之间。深察其是非得失之归。不肯安于作伪以自陷于小人。则其于为己之实。将有不待勉焉而不能自已者矣。夫既立得此心。又何患乎言行之无徵。懒惰之为病哉。至于所索对證之语。亦不必他求。朱先生以为知如此是病。即不如此是药。又曰。头痛灸头。脚痛灸脚。天下对證之剂。孰要于是。如尊既自知其轻狭粗率衰飒之为患。则但勿轻勿狭勿粗率衰飒而已。此外更有何法哉。适此一阳初生。此政君子复善之机。通宵自检。不胜感慨。三复汤盘日新之言。愿有以收功桑榆。得与诸君子相先后而观其成焉。幸吾友之益勉也。此中近无来者。向有松都数生见访。其中有一少年赵有宪者。仍留不去读书。颇多志尚。亦殊不易也。不宣。答洪乐显
书中求助之意蔼然。有足感叹。然亦别无新话可告。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5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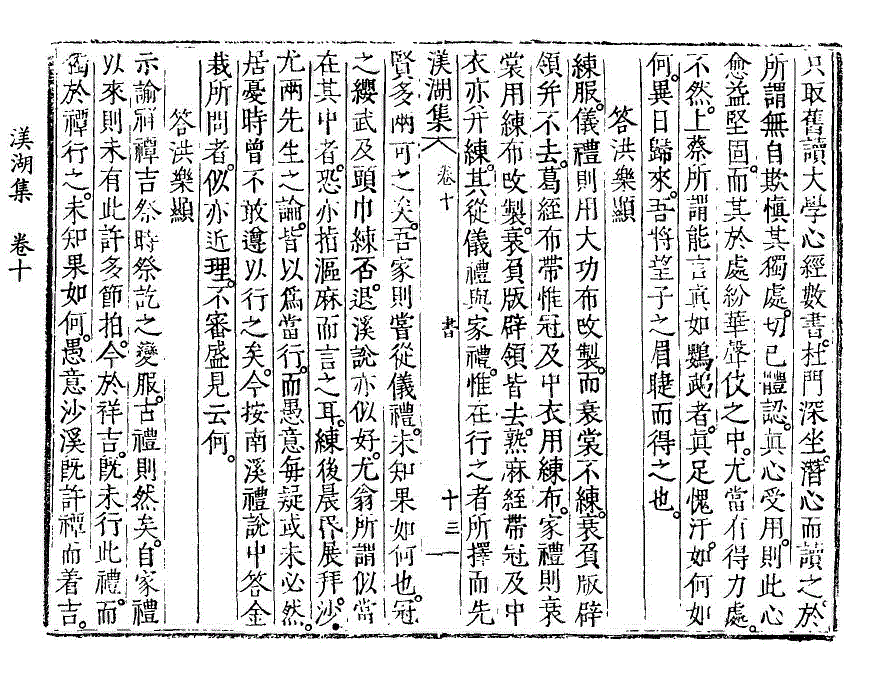 只取旧读大学心经数书。杜门深坐。潜心而读之。于所谓无自欺慎其独处。切己体认。真心受用。则此心愈益坚固。而其于处纷华声伎之中。尤当有得力处。不然。上蔡所谓能言真如鹦鹉者。真足愧汗。如何如何。异日归来。吾将望子之眉睫而得之也。
只取旧读大学心经数书。杜门深坐。潜心而读之。于所谓无自欺慎其独处。切己体认。真心受用。则此心愈益坚固。而其于处纷华声伎之中。尤当有得力处。不然。上蔡所谓能言真如鹦鹉者。真足愧汗。如何如何。异日归来。吾将望子之眉睫而得之也。答洪乐显
练服。仪礼则用大功布改制。而衰裳不练。衰负版辟领并不去。葛绖布带惟冠及中衣用练布。家礼则衰裳用练布改制。衰负版辟领皆去。熟麻绖带冠及中衣亦并练。其从仪礼与家礼。惟在行之者所择而先贤多两可之矣。吾家则尝从仪礼。未知果如何也。冠之缨武及头巾练否。退溪说亦似好。尤翁所谓似当在其中者。恐亦指沤麻而言之耳。练后晨昏展拜。沙,尤两先生之论。皆以为当行。而愚意每疑或未必然。居忧时曾不敢遵以行之矣。今按南溪礼说中答金栽所问者。似亦近理。不审盛见云何。
答洪乐显
示谕祥禫吉祭时祭讫之变服。古礼则然矣。自家礼以来则未有此许多节拍。今于祥吉。既未行此礼。而独于禫行之。未知果如何。愚意沙溪既许禫而着吉。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5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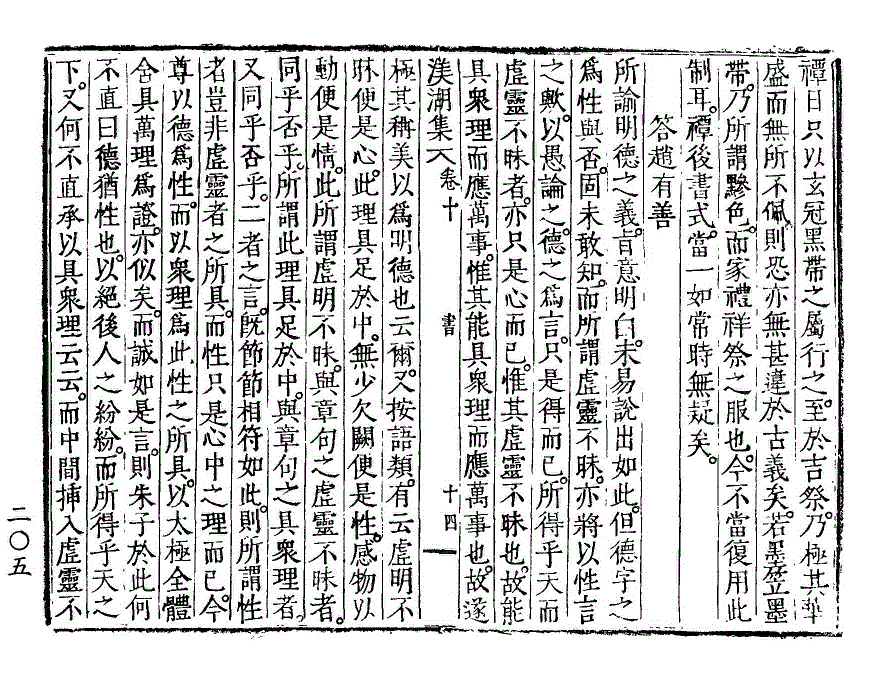 禫日只以玄冠黑带之属行之。至于吉祭。乃极其华盛而无所不佩。则恐亦无甚违于古义矣。若墨笠墨带。乃所谓黪色。而家礼祥祭之服也。今不当复用此制耳。禫后书式。当一如常时无疑矣。
禫日只以玄冠黑带之属行之。至于吉祭。乃极其华盛而无所不佩。则恐亦无甚违于古义矣。若墨笠墨带。乃所谓黪色。而家礼祥祭之服也。今不当复用此制耳。禫后书式。当一如常时无疑矣。答赵有善
所谕明德之义。旨意明白。未易说出如此。但德字之为性与否。固未敢知。而所谓虚灵不昧。亦将以性言之欤。以愚论之。德之为言。只是得而已。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者。亦只是心而已。惟其虚灵不昧也。故能具众理而应万事。惟其能具众理而应万事也。故遂极其称美以为明德也云尔。又按语类。有云虚明不昧便是心。此理具足于中。无少欠阙便是性。感物以动便是情。此所谓虚明不昧。与章句之虚灵不昧者。同乎否乎。所谓此理具足于中。与章句之具众理者。又同乎否乎。二者之言。既节节相符如此。则所谓性者岂非虚灵者之所具。而性只是心中之理而已。今尊以德为性。而以众理为此性之所具。以太极全体含具万理为證。亦似矣。而诚如是言。则朱子于此何不直曰德犹性也。以绝后人之纷纷。而所得乎天之下。又何不直承以具众理云云。而中间插入虚灵不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6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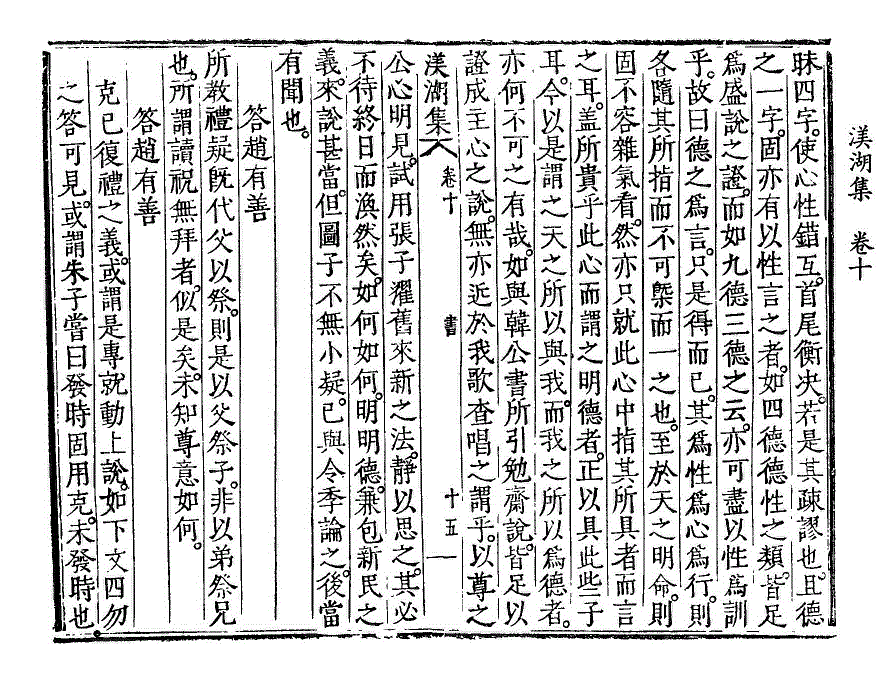 昧四字。使心性错互。首尾衡决。若是其疏谬也。且德之一字。固亦有以性言之者。如四德德性之类。皆足为盛说之證。而如九德三德之云。亦可尽以性为训乎。故曰德之为言。只是得而已。其为性为心为行。则各随其所指而不可槩而一之也。至于天之明命。则固不容杂气看。然亦只就此心中指其所具者而言之耳。盖所贵乎此心而谓之明德者。正以具此些子耳。今以是谓之天之所以与我。而我之所以为德者。亦何不可之有哉。如与韩公书所引勉斋说。皆足以證成主心之说。无亦近于我歌查唱之谓乎。以尊之公心明见。试用张子濯旧来新之法。静以思之。其必不待终日而涣然矣。如何如何。明明德。兼包新民之义。来说甚当。但图子不无小疑。已与令季论之。后当有闻也。
昧四字。使心性错互。首尾衡决。若是其疏谬也。且德之一字。固亦有以性言之者。如四德德性之类。皆足为盛说之證。而如九德三德之云。亦可尽以性为训乎。故曰德之为言。只是得而已。其为性为心为行。则各随其所指而不可槩而一之也。至于天之明命。则固不容杂气看。然亦只就此心中指其所具者而言之耳。盖所贵乎此心而谓之明德者。正以具此些子耳。今以是谓之天之所以与我。而我之所以为德者。亦何不可之有哉。如与韩公书所引勉斋说。皆足以證成主心之说。无亦近于我歌查唱之谓乎。以尊之公心明见。试用张子濯旧来新之法。静以思之。其必不待终日而涣然矣。如何如何。明明德。兼包新民之义。来说甚当。但图子不无小疑。已与令季论之。后当有闻也。答赵有善
所教礼疑既代父以祭。则是以父祭子。非以弟祭兄也。所谓读祝无拜者。似是矣。未知尊意如何。
答赵有善
克己复礼之义。或谓是专就动上说。如下文四勿之答可见。或谓朱子尝曰发时固用克。未发时也。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6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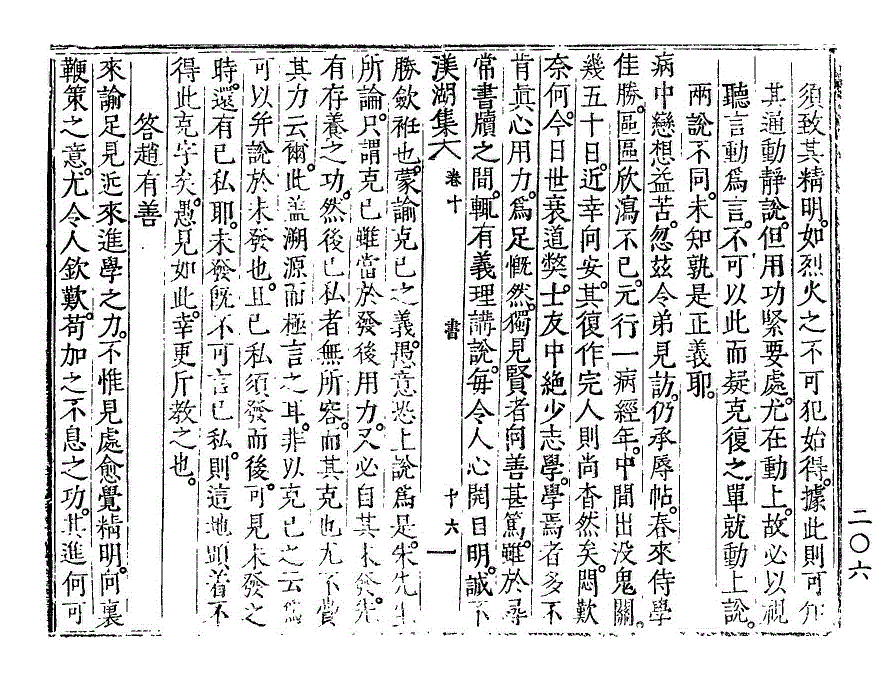 须致其精明。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。据此则可知其通动静说。但用功紧要处。尤在动上。故必以视听言动为言。不可以此而疑克复之单就动上说。两说不同。未知孰是正义耶。
须致其精明。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。据此则可知其通动静说。但用功紧要处。尤在动上。故必以视听言动为言。不可以此而疑克复之单就动上说。两说不同。未知孰是正义耶。病中恋想益苦。忽玆令弟见访。仍承辱帖。春来侍学佳胜。区区欣泻不已。元行一病经年。中间出没鬼关。几五十日。近幸向安。其复作完人则尚杳然矣。闷叹奈何。今日世衰道弊。士友中绝少志学。学焉者多不肯真心用力。为足慨然。独见贤者向善甚笃。虽于寻常书牍之间。辄有义理讲说。每令人心开目明。诚不胜敛衽也。蒙谕克己之义。愚意恐上说为是。朱先生所论。只谓克己虽当于发后用力。又必自其未发。先有存养之功。然后己私者无所容。而其克也尤不费其力云尔。此盖溯源而极言之耳。非以克己之云为可以并说于未发也。且己私须发而后。可见未发之时。还有己私耶。未发既不可言己私。则这地头着不得此克字矣。愚见如此。幸更斤教之也。
答赵有善
来谕足见近来进学之力。不惟见处愈觉精明。向里鞭策之意。尤令人钦叹。苟加之不息之功。其进何可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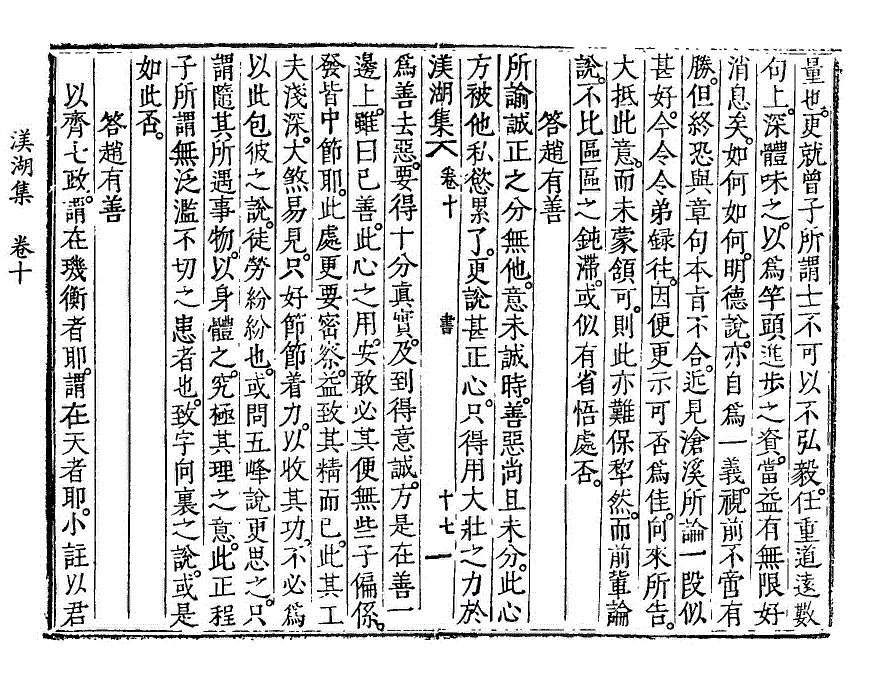 量也。更就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。任重道远数句上。深体味之。以为竿头进步之资。当益有无限好消息矣。如何如何。明德说。亦自为一义。视前不啻有胜。但终恐与章句本旨不合。近见沧溪所论一段似甚好。今令令弟录往。因便更示可否为佳。向来所告。大抵此意。而未蒙颔可。则此亦难保犁然。而前辈论说。不比区区之钝滞。或似有省悟处否。
量也。更就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。任重道远数句上。深体味之。以为竿头进步之资。当益有无限好消息矣。如何如何。明德说。亦自为一义。视前不啻有胜。但终恐与章句本旨不合。近见沧溪所论一段似甚好。今令令弟录往。因便更示可否为佳。向来所告。大抵此意。而未蒙颔可。则此亦难保犁然。而前辈论说。不比区区之钝滞。或似有省悟处否。答赵有善
所谕诚正之分无他。意未诚时。善恶尚且未分。此心方被他私欲累了。更说甚正心。只得用大壮之力于为善去恶。要得十分真实。及到得意诚。方是在善一边上。虽曰己善。此心之用。安敢必其便无些子偏系。发皆中节耶。此处更要密察。益致其精而已。此其工夫浅深。大煞易见。只好节节着力。以收其功。不必为以此包彼之说。徒劳纷纷也。或问五峰说更思之。只谓随其所遇事物。以身体之。究极其理之意。此正程子所谓无泛滥不切之患者也。致字向里之说。或是如此否。
答赵有善
以齐七政。谓在玑衡者耶。谓在天者耶。小注以君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7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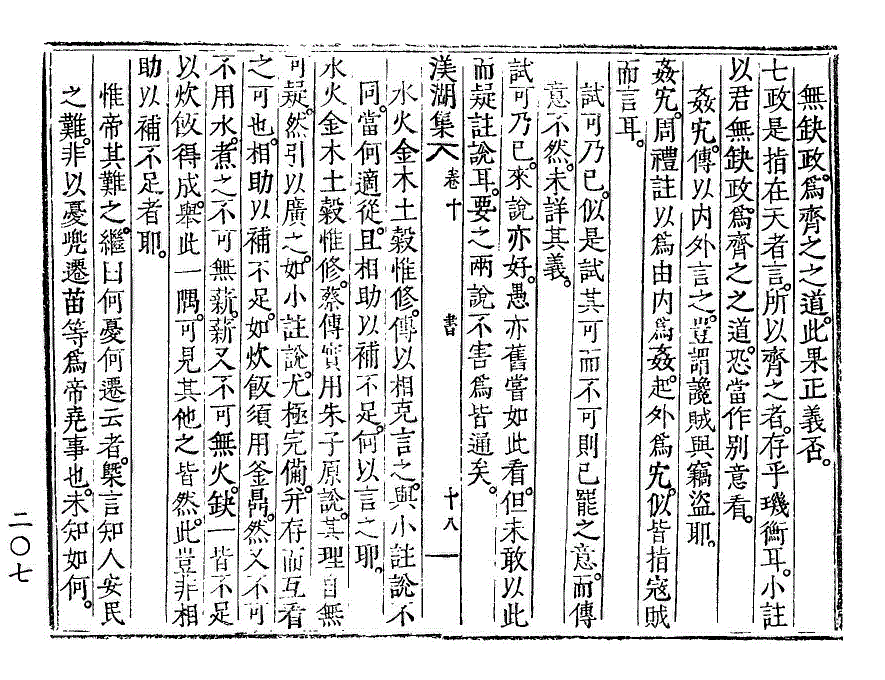 无缺政。为齐之之道。此果正义否。
无缺政。为齐之之道。此果正义否。七政是指在天者言。所以齐之者。存乎玑衡耳。小注以君无缺政。为齐之之道。恐当作别意看。
奸宄。传以内外言之。岂谓谗贼与窃盗耶。
奸宄。周礼注以为由内为奸。起外为宄。似皆指寇贼而言耳。
试可乃已。似是试其可而不可则已罢之意。而传意不然。未详其义。
试可乃已。来说亦好。愚亦旧尝如此看。但未敢以此而疑注说耳。要之两说不害为皆通矣。
水火金木土谷惟修。传以相克言之。与小注说不同。当何适从。且相助以补不足。何以言之耶。
水火金木土谷惟修。蔡传实用朱子原说。其理自无可疑。然引以广之。如小注说。尤极完备。并存而互看之可也。相助以补不足。如炊饭须用釜鼎。然又不可不用水。煮之不可无薪。薪又不可无火。缺一皆不足以炊饭得成。举此一隅。可见其他之皆然。此岂非相助以补不足者耶。
惟帝其难之。继曰何忧何迁云者。槩言知人安民之难。非以忧兜迁苗等为帝尧事也。未知如何。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8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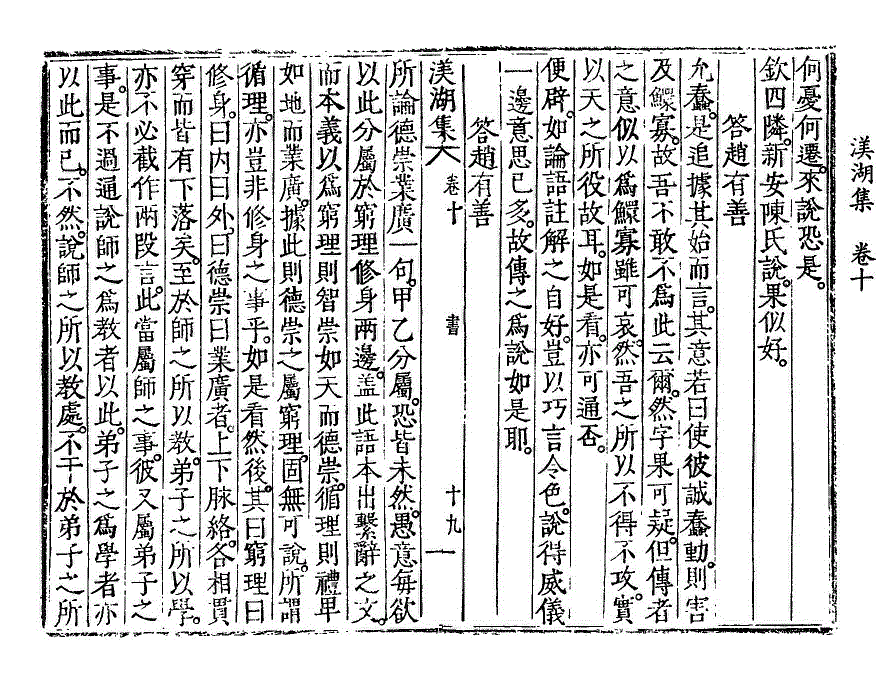 何忧何迁。来说恐是。
何忧何迁。来说恐是。钦四邻。新安陈氏说。果似好。
答赵有善
允蠢。是追据其始而言。其意若曰使彼诚蠢动。则害及鳏寡。故吾不敢不为此云尔。然字果可疑。但传者之意似以为鳏寡虽可哀。然吾之所以不得不攻。实以天之所役故耳。如是看。亦可通否。
便辟。如论语注解之自好。岂以巧言令色。说得威仪一边意思已多。故传之为说如是耶。
答赵有善
所论德崇业广一句。甲乙分属。恐皆未然。愚意每欲以此分属于穷理修身两边。盖此语本出系辞之文。而本义以为穷理则智崇如天而德崇。循理则礼卑如地而业广。据此则德崇之属穷理。固无可说。所谓循理。亦岂非修身之事乎。如是看然后。其曰穷理曰修身。曰内曰外。曰德崇曰业广者。上下脉络。各相贯穿而皆有下落矣。至于师之所以教。弟子之所以学。亦不必截作两段言。此当属师之事。彼又属弟子之事。是不过通说师之为教者以此。弟子之为学者亦以此而已。不然。说师之所以教处。不干于弟子之所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8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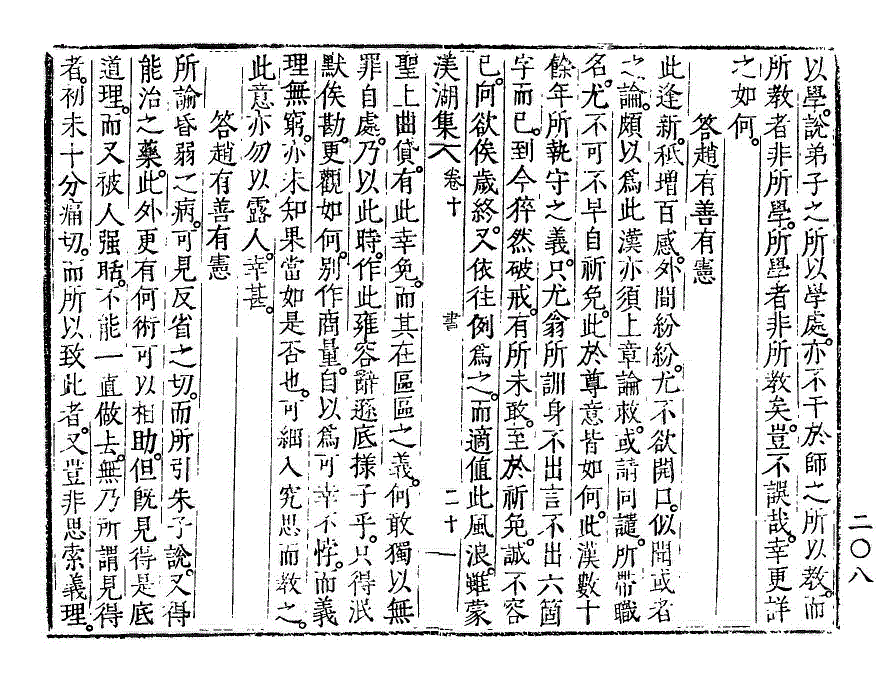 以学。说弟子之所以学处。亦不干于师之所以教。而所教者非所学。所学者非所教矣。岂不误哉。幸更详之如何。
以学。说弟子之所以学处。亦不干于师之所以教。而所教者非所学。所学者非所教矣。岂不误哉。幸更详之如何。答赵有善有宪
此逢新。秪增百感。外间纷纷。尤不欲开口。似闻或者之论。颇以为此汉亦须上章论救。或请同谴。所带职名。尤不可不早自祈免。此于尊意皆如何。此汉数十馀年所执守之义。只尤翁所训身不出言不出六个字而已。到今猝然破戒。有所未敢。至于祈免。诚不容已。向欲俟岁终。又依往例为之。而适值此风浪。虽蒙圣上曲贷。有此幸免。而其在区区之义。何敢独以无罪自处。乃以此时。作此雍容辞逊底㨾子乎。只得泯默俟勘。更观如何。别作商量。自以为可幸不悖。而义理无穷。亦未知果当如是否也。可细入究思而教之。此意亦勿以露人。幸甚。
答赵有善有宪
所谕昏弱之病。可见反省之切。而所引朱子说。又得能治之药。此外更有何术可以相助。但既见得是底道理。而又被人强聒。不能一直做去。无乃所谓见得者。初未十分痛切。而所以致此者。又岂非思索义理。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9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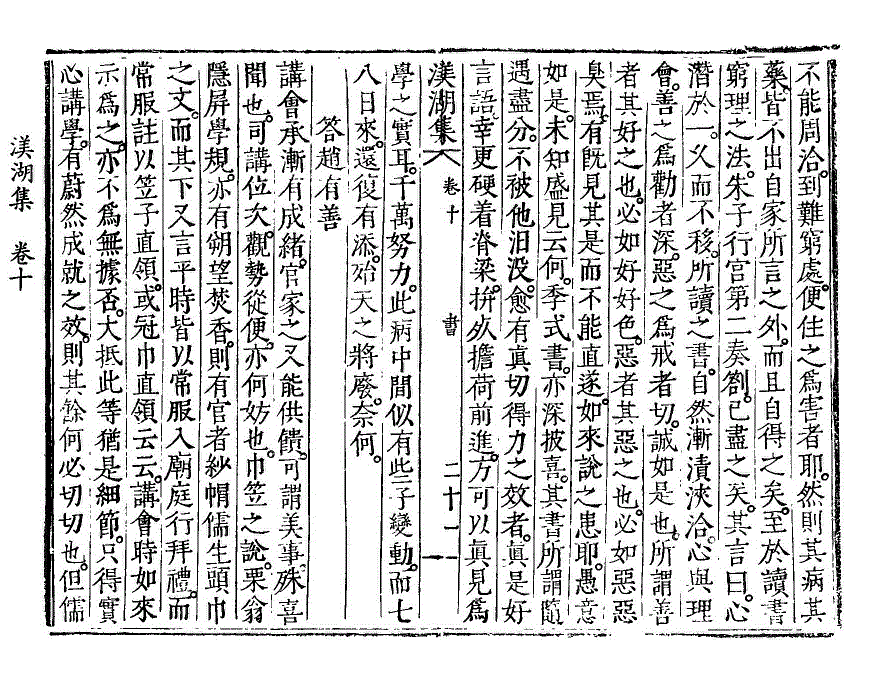 不能周洽。到难穷处。便住之为害者耶。然则其病其药。皆不出自家所言之外。而且自得之矣。至于读书穷理之法。朱子行宫第二奏劄。已尽之矣。其言曰。心潜于一。久而不移。所读之书。自然渐渍浃洽。心与理会。善之为劝者深。恶之为戒者切。诚如是也。所谓善者其好之也。必如好好色。恶者其恶之也。必如恶恶臭焉。有既见其是而不能直遂。如来说之患耶。愚意如是。未知盛见云何。季式书。亦深披喜。其书所谓随遇尽分。不被他汨没。愈有真切得力之效者。真是好言语。幸更硬着脊梁。拚死担荷前进。方可以真见为学之实耳。千万努力。此病中间似有些子变动。而七八日来。还复有添。殆天之将废。奈何。
不能周洽。到难穷处。便住之为害者耶。然则其病其药。皆不出自家所言之外。而且自得之矣。至于读书穷理之法。朱子行宫第二奏劄。已尽之矣。其言曰。心潜于一。久而不移。所读之书。自然渐渍浃洽。心与理会。善之为劝者深。恶之为戒者切。诚如是也。所谓善者其好之也。必如好好色。恶者其恶之也。必如恶恶臭焉。有既见其是而不能直遂。如来说之患耶。愚意如是。未知盛见云何。季式书。亦深披喜。其书所谓随遇尽分。不被他汨没。愈有真切得力之效者。真是好言语。幸更硬着脊梁。拚死担荷前进。方可以真见为学之实耳。千万努力。此病中间似有些子变动。而七八日来。还复有添。殆天之将废。奈何。答赵有善
讲会承渐有成绪。官家之又能供馈。可谓美事。殊喜闻也。司讲位次。观势从便。亦何妨也。巾笠之说。栗翁隐屏学规。亦有朔望焚香。则有官者纱帽儒生头巾之文。而其下又言平时皆以常服入庙庭行拜礼。而常服注以笠子直领。或冠巾直领云云。讲会时如来示为之。亦不为无据否。大抵此等犹是细节。只得实心讲学。有蔚然成就之效。则其馀何必切切也。但儒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0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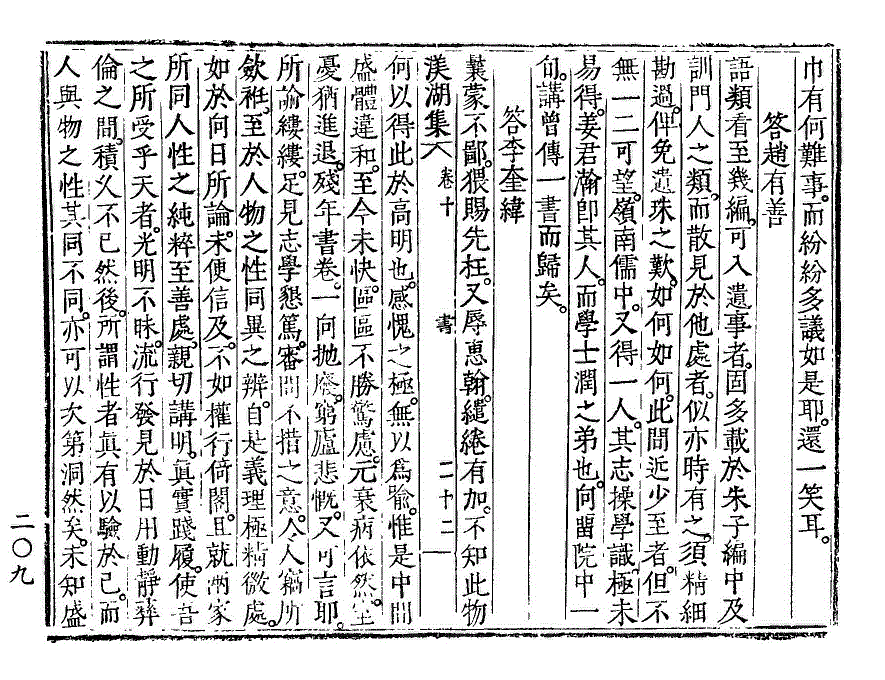 巾有何难事。而纷纷多议如是耶。还一笑耳。
巾有何难事。而纷纷多议如是耶。还一笑耳。答赵有善
语类看至几编。可入遗事者。固多载于朱子编中及训门人之类。而散见于他处者。似亦时有之。须精细勘过。俾免遗珠之叹。如何如何。此间近少至者。但不无一二可望。岭南儒中。又得一人。其志操学识。极未易得。姜君瀚即其人。而学士润之弟也。向留院中一旬。讲曾传一书而归矣。
答李奎纬
曩蒙不鄙。猥赐先枉。又辱惠翰。缱绻有加。不知此物何以得此于高明也。感愧之极。无以为喻。惟是中间盛体违和。至今未快。区区不胜惊虑。元衰病依然。室忧犹进退。残年书卷。一向抛废。穷庐悲慨。又可言耶。所谕缕缕。足见志学恳笃。审问不措之意。令人窃所敛衽。至于人物之性同异之辨。自是义理极精微处。如于向日所论。未便信及。不如权行倚阁。且就两家所同人性之纯粹至善处。亲切讲明。真实践履。使吾之所受乎天者。光明不昧。流行发见于日用动静彝伦之间。积久不已然后。所谓性者真有以验于己。而人与物之性其同不同。亦可以次第洞然矣。未知盛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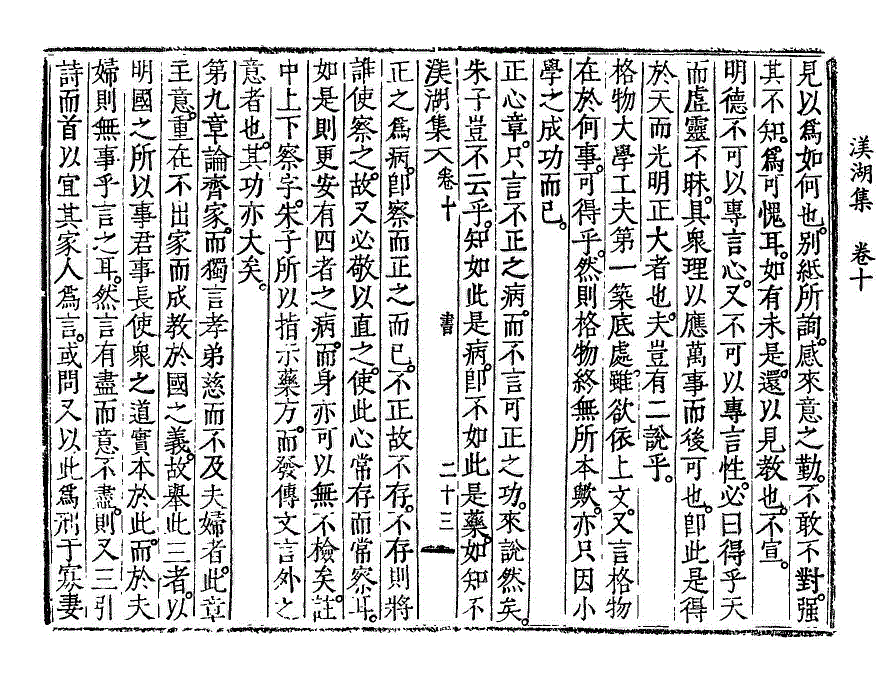 见以为如何也。别纸所询。感来意之勤。不敢不对。强其不知。为可愧耳。如有未是。还以见教也。不宣。
见以为如何也。别纸所询。感来意之勤。不敢不对。强其不知。为可愧耳。如有未是。还以见教也。不宣。明德不可以专言心。又不可以专言性。必曰得乎天而虚灵不昧。具众理以应万事而后可也。即此是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也。夫岂有二说乎。
格物大学工夫第一筑底处。虽欲依上文。又言格物在于何事。可得乎。然则格物终无所本欤。亦只因小学之成功而已。
正心章。只言不正之病。而不言可正之功。来说然矣。朱子岂不云乎。知如此是病。即不如此是药。如知不正之为病。即察而正之而已。不正故不存。不存则将谁使察之。故又必敬以直之。使此心常存而常察耳。如是则更安有四者之病。而身亦可以无不检矣。注中上下察字。朱子所以指示药方。而发传文言外之意者也。其功亦大矣。
第九章论齐家。而独言孝弟慈而不及夫妇者。此章主意。重在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之义。故举此三者。以明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实本于此。而于夫妇则无事乎言之耳。然言有尽而意不尽。则又三引诗而首以宜其家人为言。或问又以此为刑于寡妻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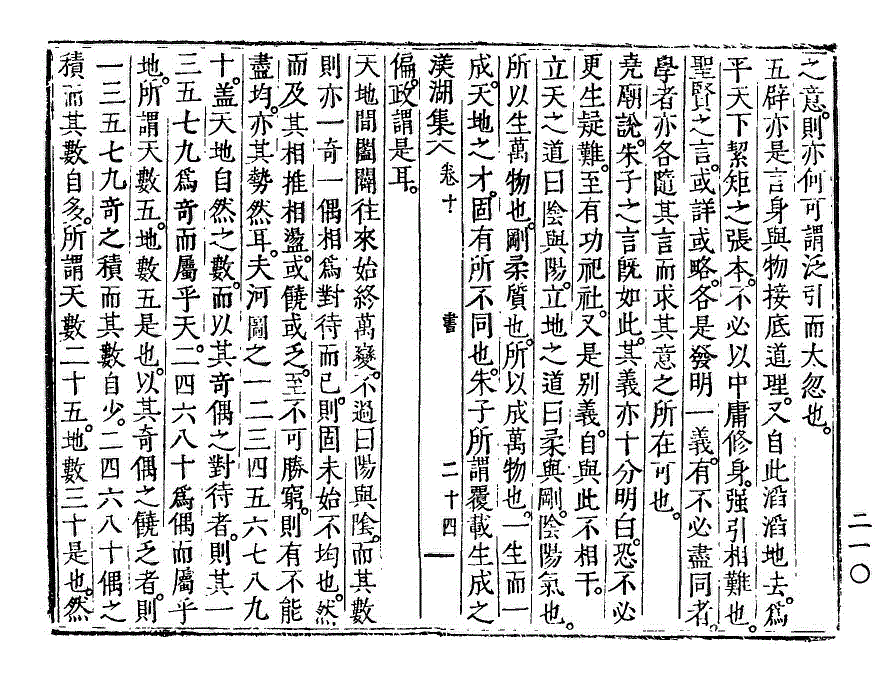 之意。则亦何可谓泛引而太忽也。
之意。则亦何可谓泛引而太忽也。五辟亦是言身与物接底道理。又自此滔滔地去。为平天下絜矩之张本。不必以中庸修身。强引相难也。圣贤之言。或详或略。各是发明一义。有不必尽同者。学者亦各随其言而求其意之所在可也。
尧庙说。朱子之言既如此。其义亦十分明白。恐不必更生疑难。至有功祀社。又是别义。自与此不相干。
立天之道曰阴与阳。立地之道曰柔与刚。阴阳气也。所以生万物也。刚柔质也。所以成万物也。一生而一成。天地之才。固有所不同也。朱子所谓覆载生成之偏。政谓是耳。
天地间阖辟往来始终万变。不过曰阳与阴。而其数则亦一奇一偶相为对待而已。则固未始不均也。然而及其相推相荡。或饶或乏。至不可胜穷。则有不能尽均。亦其势然耳。夫河图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盖天地自然之数。而以其奇偶之对待者。则其一三五七九为奇而属乎天。二四六八十为偶而属乎地。所谓天数五。地数五是也。以其奇偶之饶乏者。则一三五七九奇之积而其数自少。二四六八十偶之积而其数自多。所谓天数二十五。地数三十是也。然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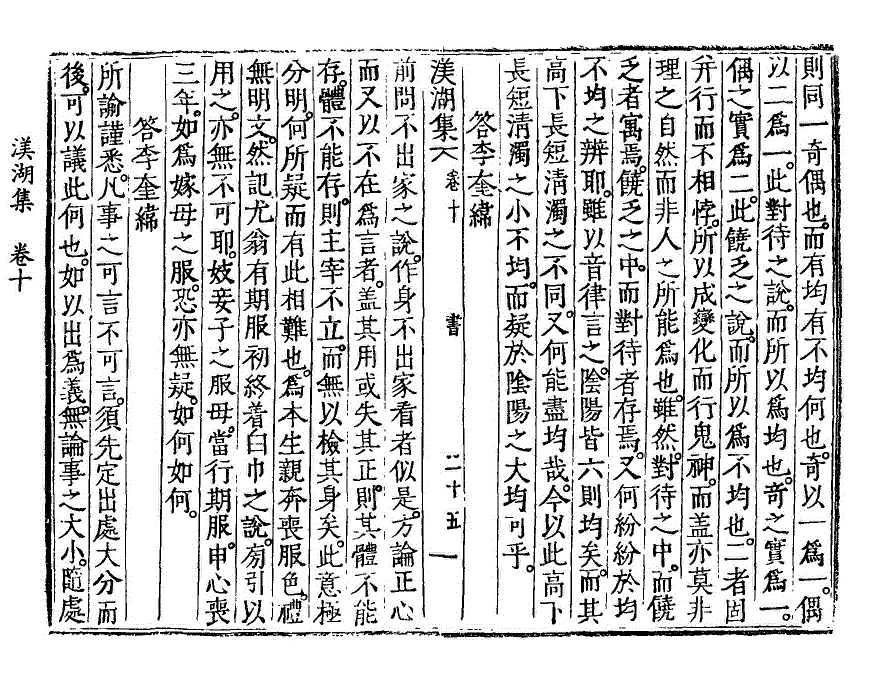 则同一奇偶也。而有均有不均何也。奇以一为一。偶以二为一。此对待之说。而所以为均也。奇之实为一。偶之实为二。此饶乏之说。而所以为不均也。二者固并行而不相悖。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。而盖亦莫非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虽然。对待之中。而饶乏者寓焉。饶乏之中。而对待者存焉。又何纷纷于均不均之辨耶。虽以音律言之。阴阳皆六则均矣。而其高下长短清浊之不同。又何能尽均哉。今以此高下长短清浊之小不均。而疑于阴阳之大均可乎。
则同一奇偶也。而有均有不均何也。奇以一为一。偶以二为一。此对待之说。而所以为均也。奇之实为一。偶之实为二。此饶乏之说。而所以为不均也。二者固并行而不相悖。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。而盖亦莫非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虽然。对待之中。而饶乏者寓焉。饶乏之中。而对待者存焉。又何纷纷于均不均之辨耶。虽以音律言之。阴阳皆六则均矣。而其高下长短清浊之不同。又何能尽均哉。今以此高下长短清浊之小不均。而疑于阴阳之大均可乎。答李奎纬
前问不出家之说。作身不出家看者似是。方论正心而又以不在为言者。盖其用或失其正。则其体不能存。体不能存。则主宰不立。而无以检其身矣。此意极分明。何所疑而有此相难也。为本生亲奔丧服色。礼无明文。然记尤翁有期服初终着白巾之说。旁引以用之。亦无不可耶。妓妾子之服母。当行期服。申心丧三年。如为嫁母之服。恐亦无疑。如何如何。
答李奎纬
所谕谨悉。凡事之可言不可言。须先定出处大分而后。可以议此何也。如以出为义。无论事之大小。随处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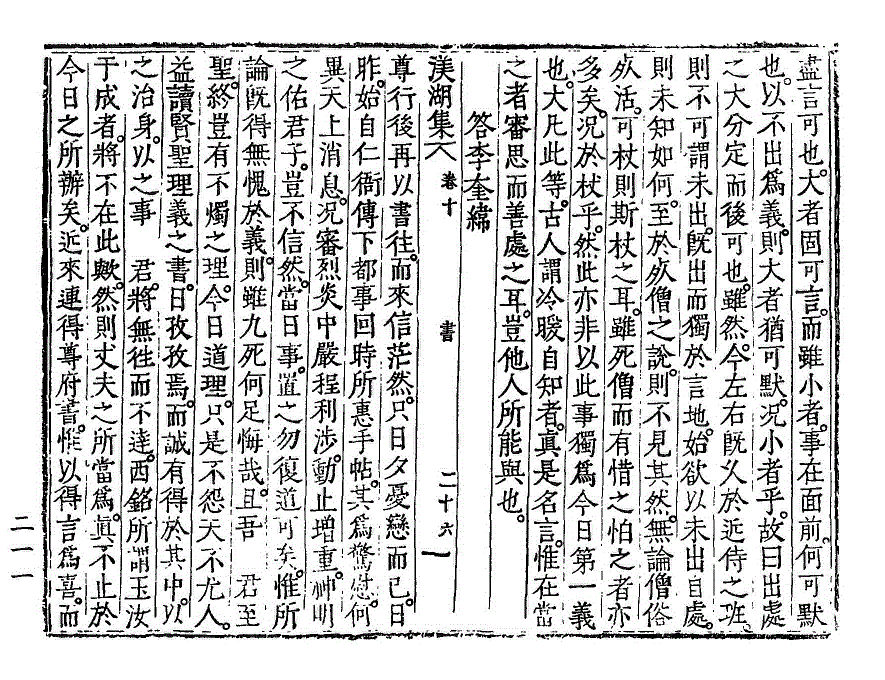 尽言可也。大者固可言。而虽小者。事在面前。何可默也。以不出为义。则大者犹可默。况小者乎。故曰出处之大分定而后可也。虽然。今左右既久于近侍之班。则不可谓未出。既出而独于言地。始欲以未出自处。则未知如何。至于死僧之说。则不见其然。无论僧俗死活。可杖则斯杖之耳。虽死僧而有惜之怕之者亦多矣。况于杖乎。然此亦非以此事独为今日第一义也。大凡此等。古人谓冷暖自知者。真是名言。惟在当之者审思而善处之耳。岂他人所能与也。
尽言可也。大者固可言。而虽小者。事在面前。何可默也。以不出为义。则大者犹可默。况小者乎。故曰出处之大分定而后可也。虽然。今左右既久于近侍之班。则不可谓未出。既出而独于言地。始欲以未出自处。则未知如何。至于死僧之说。则不见其然。无论僧俗死活。可杖则斯杖之耳。虽死僧而有惜之怕之者亦多矣。况于杖乎。然此亦非以此事独为今日第一义也。大凡此等。古人谓冷暖自知者。真是名言。惟在当之者审思而善处之耳。岂他人所能与也。答李奎纬
尊行后再以书往。而来信茫然。只日夕忧恋而已。日昨。始自仁衙传下都事回时所惠手帖。其为惊慰。何异天上消息。况审烈炎中严程利涉。动止增重。神明之佑君子。岂不信然。当日事。置之勿复道可矣。惟所论既得无愧于义。则虽九死何足悔哉。且吾 君至圣。终岂有不烛之理。今日道理。只是不怨天不尤人。益读贤圣理义之书。日孜孜焉。而诚有得于其中。以之治身。以之事 君。将无往而不达。西铭所谓玉汝于成者。将不在此欤。然则丈夫之所当为。真不止于今日之所办矣。近来连得尊府书。惟以得言为喜。而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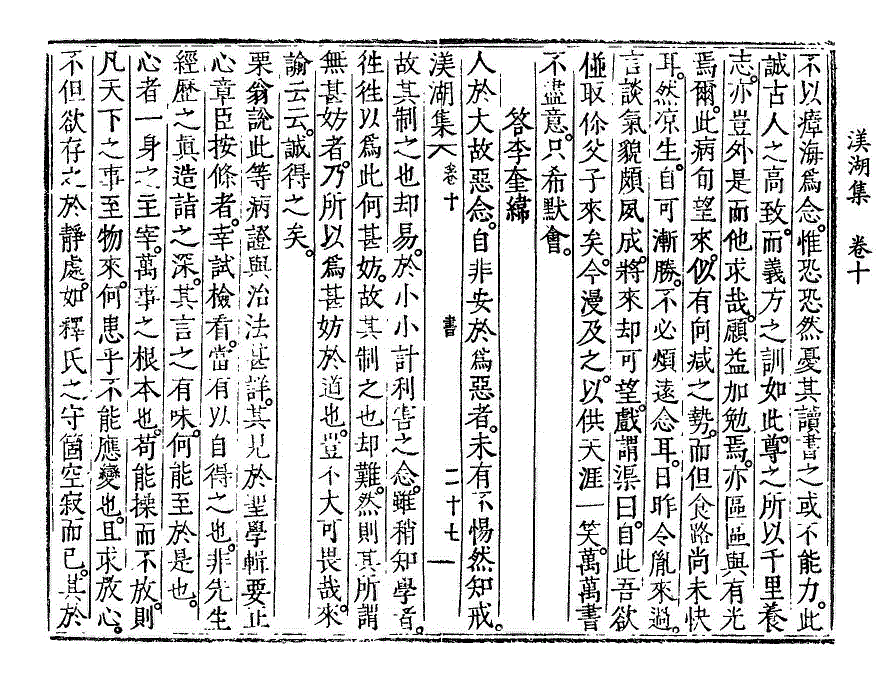 不以瘴海为念。惟恐恐然忧其读书之或不能力。此诚古人之高致。而义方之训如此。尊之所以千里养志。亦岂外是而他求哉。愿益加勉焉。亦区区与有光焉尔。此病旬望来。似有向减之势。而但食路尚未快耳。然凉生。自可渐胜。不必烦远念耳。日昨令胤来过。言谈气貌颇夙成。将来却可望。戏谓渠曰。自此吾欲并取你父子来矣。今漫及之。以供天涯一笑。万万书不尽意。只希默会。
不以瘴海为念。惟恐恐然忧其读书之或不能力。此诚古人之高致。而义方之训如此。尊之所以千里养志。亦岂外是而他求哉。愿益加勉焉。亦区区与有光焉尔。此病旬望来。似有向减之势。而但食路尚未快耳。然凉生。自可渐胜。不必烦远念耳。日昨令胤来过。言谈气貌颇夙成。将来却可望。戏谓渠曰。自此吾欲并取你父子来矣。今漫及之。以供天涯一笑。万万书不尽意。只希默会。答李奎纬
人于大故恶念。自非安于为恶者。未有不惕然知戒。故其制之也却易。于小小计利害之念。虽稍知学者。往往以为此何甚妨。故其制之也却难。然则其所谓无甚妨者。乃所以为甚妨于道也。岂不大可畏哉。来谕云云。诚得之矣。
栗翁说此等病證与治法甚详。其见于圣学辑要正心章臣按条者。幸试检看。当有以自得之也。非先生经历之真造诣之深。其言之有味。何能至于是也。
心者一身之主宰。万事之根本也。苟能操而不放。则凡天下之事至物来。何患乎不能应变也。且求放心。不但欲存之于静处。如释氏之守个空寂而已。其于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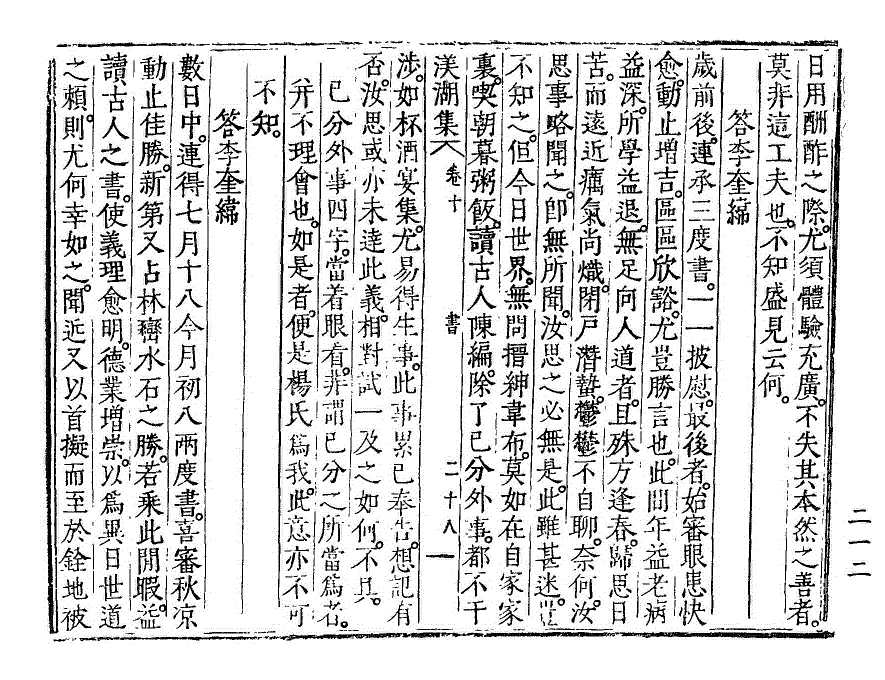 日用酬酢之际。尤须体验充广。不失其本然之善者。莫非这工夫也。不知盛见云何。
日用酬酢之际。尤须体验充广。不失其本然之善者。莫非这工夫也。不知盛见云何。答李奎纬
岁前后。连承三度书。一一披慰。最后者。始审眼患快愈。动止增吉。区区欣豁。尤岂胜言也。此间年益老病益深。所学益退。无足向人道者。且殊方逢春。归思日苦。而远近疠气尚炽。闭户潜蛰。郁郁不自聊。奈何。汝思事略闻之。即无所闻。汝思之必无是。此虽甚迷。岂不知之。但今日世界。无问搢绅韦布。莫如在自家家里。吃朝暮粥饭。读古人陈编。除了己分外事。都不干涉。如杯酒宴集。尤易得生事。此事累已奉告。想记有否。汝思或亦未达此义。相对试一及之如何。不具。
己分外事四字。当着眼看。非谓己分之所当为者。并不理会也。如是者。便是杨氏为我。此意亦不可不知。
答李奎纬
数日中。连得七月十八今月初八两度书。喜审秋凉动止佳胜。新第又占林峦水石之胜。若乘此閒暇。益读古人之书。使义理愈明。德业增崇。以为异日世道之赖。则尤何幸如之。闻近又以首拟而至于铨地被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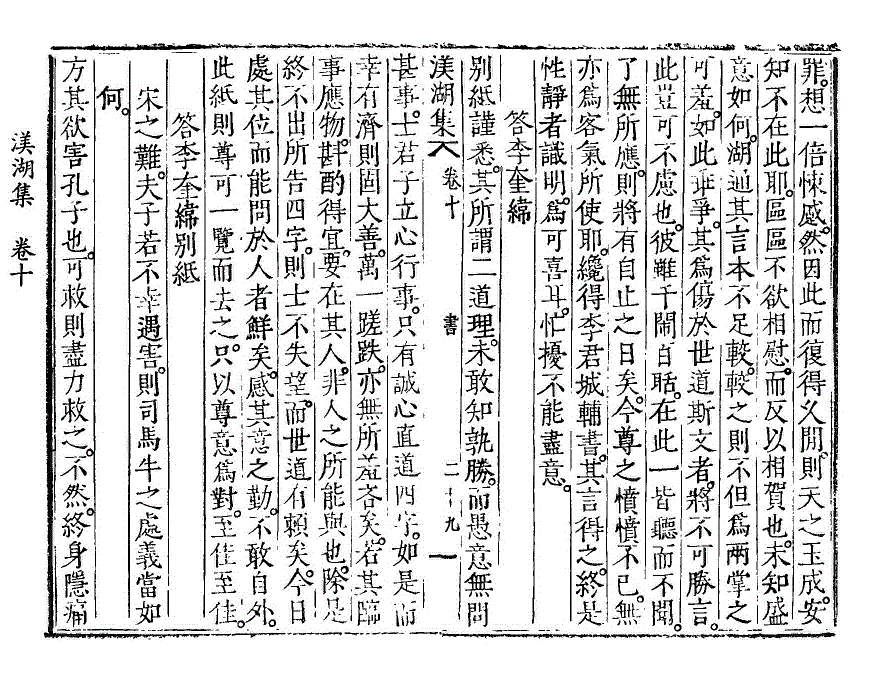 罪。想一倍悚蹙。然因此而复得久閒。则天之玉成。安知不在此耶。区区不欲相慰。而反以相贺也。未知盛意如何。湖通其言本不足较。较之则不但为两掌之可羞。如此乖争。其为伤于世道斯文者。将不可胜言。此岂可不虑也。彼虽千闹百聒。在此一皆听而不闻。了无所应。则将有自止之日矣。今尊之愤愤不已。无亦为客气所使耶。才得李君城辅书。其言得之。终是性静者识明。为可喜耳。忙扰不能尽意。
罪。想一倍悚蹙。然因此而复得久閒。则天之玉成。安知不在此耶。区区不欲相慰。而反以相贺也。未知盛意如何。湖通其言本不足较。较之则不但为两掌之可羞。如此乖争。其为伤于世道斯文者。将不可胜言。此岂可不虑也。彼虽千闹百聒。在此一皆听而不闻。了无所应。则将有自止之日矣。今尊之愤愤不已。无亦为客气所使耶。才得李君城辅书。其言得之。终是性静者识明。为可喜耳。忙扰不能尽意。答李奎纬
别纸谨悉。其所谓二道理。未敢知孰胜。而愚意无问甚事。士君子立心行事。只有诚心直道四字。如是而幸有济则固大善。万一蹉跌。亦无所羞吝矣。若其临事应物。斟酌得宜。要在其人。非人之所能与也。除是终不出所告四字。则士不失望。而世道有赖矣。今日处其位而能问于人者鲜矣。感其意之勤。不敢自外。此纸则尊可一览而去之。只以尊意为对。至佳至佳。
答李奎纬别纸
宋之难。夫子若不幸遇害。则司马牛之处义当如何。
方其欲害孔子也。可救则尽力救之。不然。终身隐痛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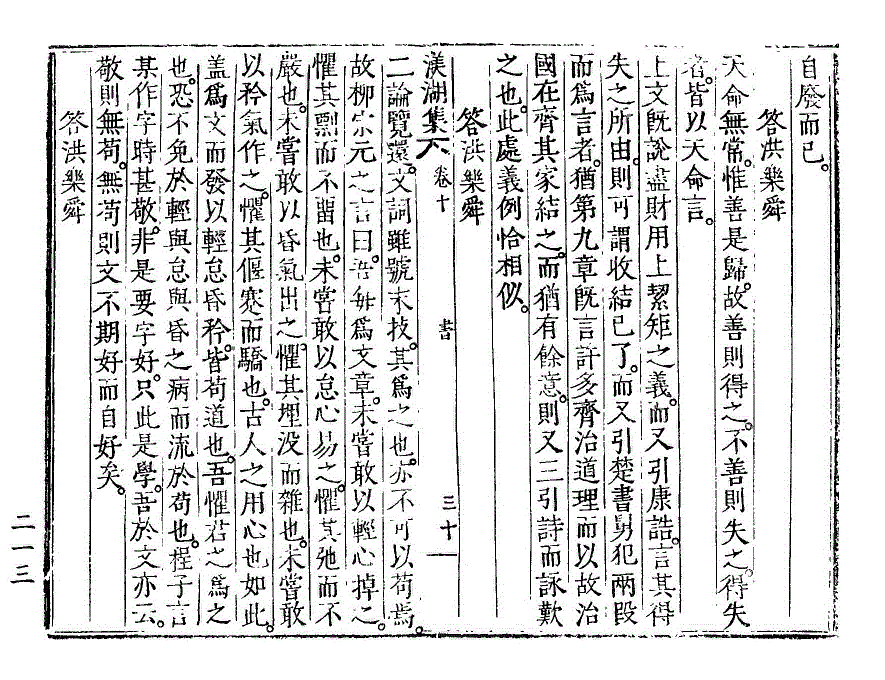 自废而已。
自废而已。答洪乐舜
天命无常。惟善是归。故善则得之。不善则失之。得失者。皆以天命言。
上文既说尽财用上絜矩之义。而又引康诰。言其得失之所由。则可谓收结已了。而又引楚书舅犯两段而为言者。犹第九章既言许多齐治道理而以故治国在齐其家结之。而犹有馀意。则又三引诗而咏叹之也。此处义例恰相似。
答洪乐舜
二论览还。文词虽号末技。其为之也。亦不可以苟焉。故柳宗元之言曰。吾每为文章。未尝敢以轻心掉之。惧其剽而不留也。未尝敢以怠心易之。惧其弛而不严也。未尝敢以昏气出之。惧其埋没而杂也。未尝敢以矜气作之。惧其偃蹇而骄也。古人之用心也如此。盖为文而发以轻怠昏矜。皆苟道也。吾惧君之为之也。恐不免于轻与怠与昏之病而流于苟也。程子言某作字时甚敬。非是要字好。只此是学。吾于文亦云。敬则无苟。无苟则文不期好而自好矣。
答洪乐舜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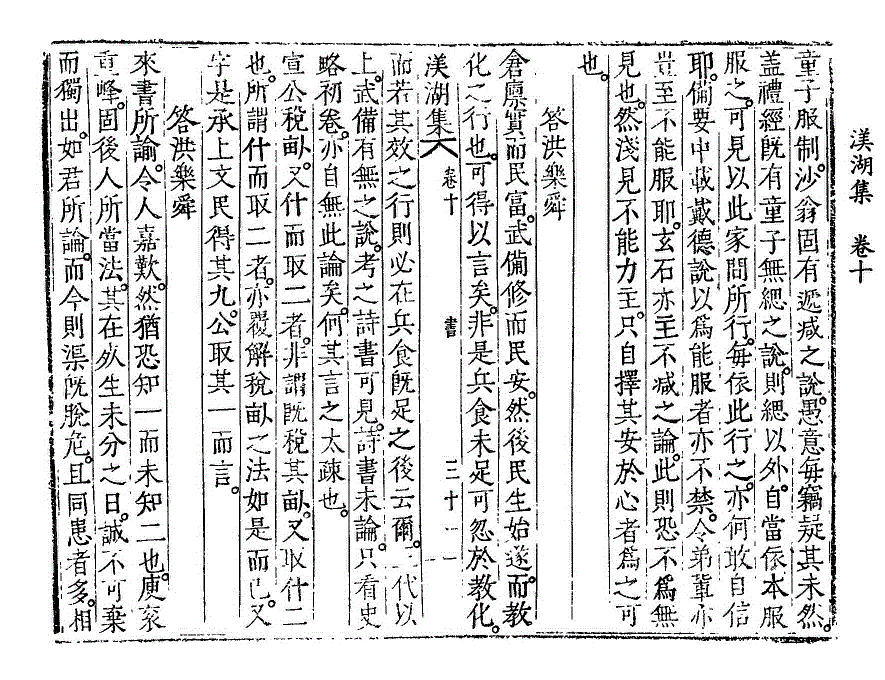 童子服制。沙翁固有递减之说。愚意每窃疑其未然。盖礼经既有童子无缌之说。则缌以外。自当依本服服之。可见以此家间所行。每依此行之。亦何敢自信耶。备要中载戴德说以为能服者亦不禁。令弟辈亦岂至不能服耶。玄石亦主不减之论。此则恐不为无见也。然浅见不能力主。只自择其安于心者为之可也。
童子服制。沙翁固有递减之说。愚意每窃疑其未然。盖礼经既有童子无缌之说。则缌以外。自当依本服服之。可见以此家间所行。每依此行之。亦何敢自信耶。备要中载戴德说以为能服者亦不禁。令弟辈亦岂至不能服耶。玄石亦主不减之论。此则恐不为无见也。然浅见不能力主。只自择其安于心者为之可也。答洪乐舜
仓廪实而民富。武备修而民安。然后民生始遂。而教化之行也。可得以言矣。非是兵食未足可忽于教化。而若其效之行则必在兵食既足之后云尔。三代以上。武备有无之说。考之诗书可见。诗书未论。只看史略初卷。亦自无此论矣。何其言之太疏也。
宣公税亩。又什而取二者。非谓既税其亩。又取什二也。所谓什而取二者。亦覆解税亩之法如是而已。又字是承上文民得其九。公取其一而言。
答洪乐舜
来书所谕。令人嘉叹。然犹恐知一而未知二也。庾衮重峰。固后人所当法。其在死生未分之日。诚不可弃而独出。如君所论。而今则渠既脱危。且同患者多。相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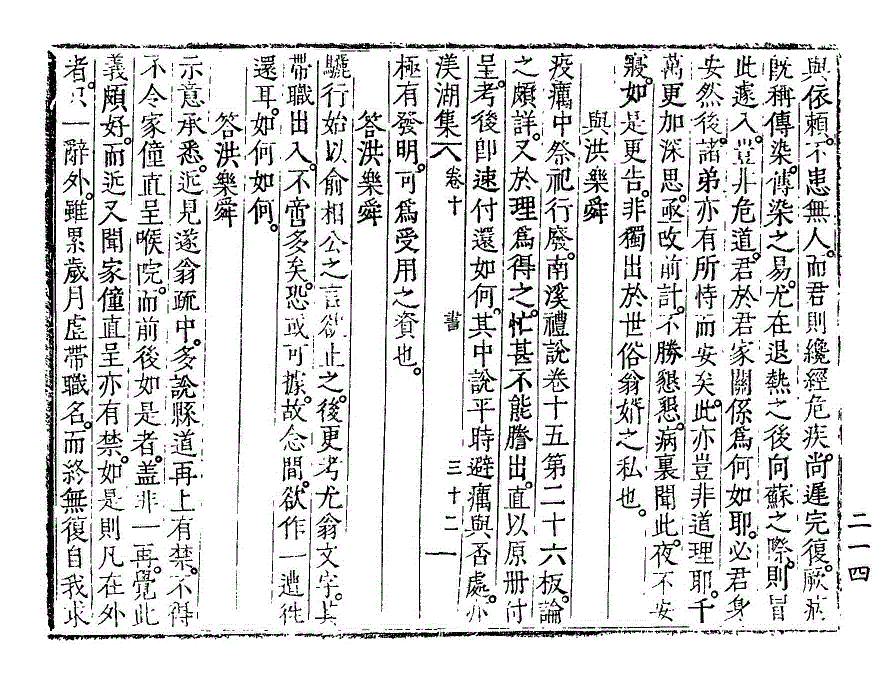 与依赖。不患无人。而君则才经危疾。尚迟完复。厥病既称传染。传染之易。尤在退热之后向苏之际。则冒此遽入。岂非危道。君于君家关系为何如耶。必君身安然后。诸弟亦有所恃而安矣。此亦岂非道理耶。千万更加深思。亟改前计。不胜恳恳。病里闻此。夜不安寝。如是更告。非独出于世俗翁婿之私也。
与依赖。不患无人。而君则才经危疾。尚迟完复。厥病既称传染。传染之易。尤在退热之后向苏之际。则冒此遽入。岂非危道。君于君家关系为何如耶。必君身安然后。诸弟亦有所恃而安矣。此亦岂非道理耶。千万更加深思。亟改前计。不胜恳恳。病里闻此。夜不安寝。如是更告。非独出于世俗翁婿之私也。与洪乐舜
疫疠中祭祀行废。南溪礼说卷十五第二十六板。论之颇详。又于理为得之。忙甚不能誊出。直以原册付呈。考后即速付还如何。其中说平时避疠与否处。亦极有发明。可为受用之资也。
答洪乐舜
骊行始以俞相公之言欲止之。后更考尤翁文字。其带职出入。不啻多矣。恐或可据。故念间。欲作一遭往还耳。如何如何。
答洪乐舜
示意承悉。近见遂翁疏中。多说县道再上有禁。不得不令家僮直呈喉院。而前后如是者。盖非一再。觉此义颇好。而近又闻家僮直呈亦有禁。如是则凡在外者。只一辞外。虽累岁月虚带职名。而终无复自我求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5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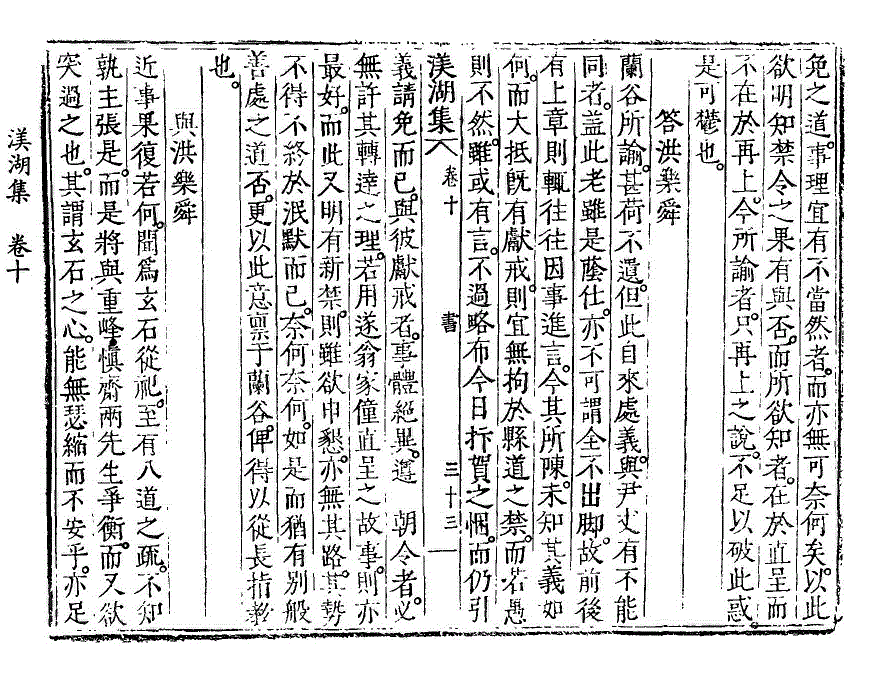 免之道。事理宜有不当然者。而亦无可奈何矣。以此欲明知禁令之果有与否。而所欲知者。在于直呈而不在于再上。今所谕者。只再上之说。不足以破此惑。是可郁也。
免之道。事理宜有不当然者。而亦无可奈何矣。以此欲明知禁令之果有与否。而所欲知者。在于直呈而不在于再上。今所谕者。只再上之说。不足以破此惑。是可郁也。答洪乐舜
兰谷所谕。甚荷不遗。但此自来处义。与尹丈有不能同者。盖此老虽是荫仕。亦不可谓全不出脚。故前后有上章则辄往往因事进言。今其所陈。未知其义如何。而大抵既有献戒。则宜无拘于县道之禁。而若愚则不然。虽或有言。不过略布今日抃贺之悃。而仍引义请免而已。与彼献戒者。事体绝异。遵 朝令者。必无许其转达之理。若用遂翁家僮直呈之故事。则亦最好。而此又明有新禁。则虽欲申恳。亦无其路。其势不得不终于泯默而已。奈何奈何。如是而犹有别般善处之道否。更以此意禀于兰谷。俾得以从长指教也。
与洪乐舜
近事果复若何。闻为玄石从祀。至有八道之疏。不知孰主张是。而是将与重峰,慎斋两先生争衡。而又欲突过之也。其谓玄石之心。能无瑟缩而不安乎。亦足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5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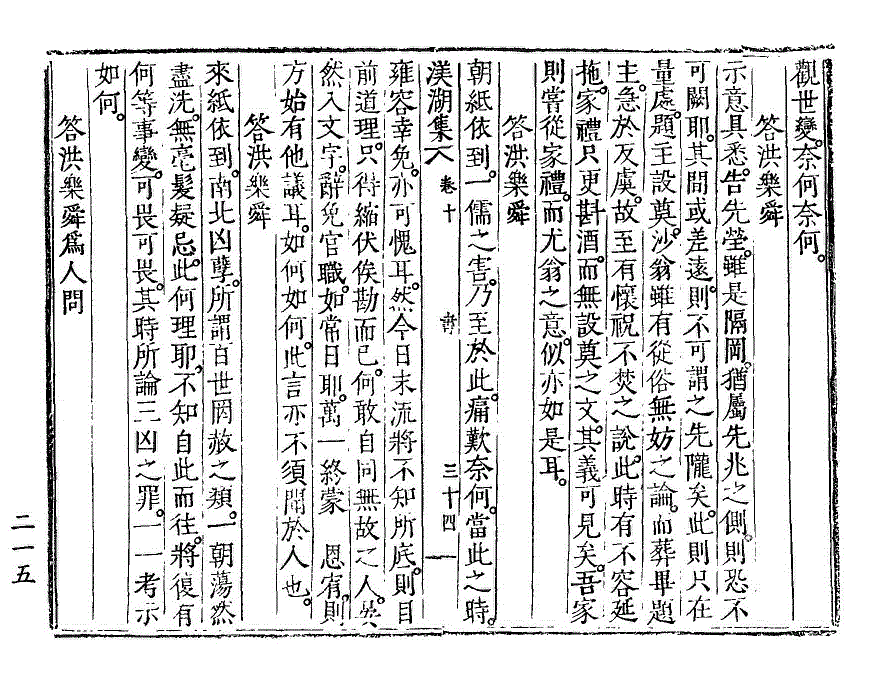 观世变。奈何奈何。
观世变。奈何奈何。答洪乐舜
示意具悉。告先茔。虽是隔冈。犹属先兆之侧。则恐不可阙耶。其间或差远。则不可谓之先陇矣。此则只在量处。题主设奠。沙翁虽有从俗无妨之论。而葬毕题主。急于反虞。故至有怀祝不焚之说。此时有不容延拖。家礼只更斟酒。而无设奠之文。其义可见矣。吾家则尝从家礼。而尤翁之意。似亦如是耳。
答洪乐舜
朝纸依到。一儒之害。乃至于此。痛叹奈何。当此之时。雍容幸免。亦可愧耳。然今日末流将不知所底。则目前道理。只得缩伏俟勘而已。何敢自同无故之人。晏然入文字。辞免官职。如常日耶。万一终蒙 恩宥。则方始有他议耳。如何如何。此言亦不须闻于人也。
答洪乐舜
来纸依到。南北凶孽。所谓百世罔赦之类。一朝荡然尽洗。无毫发疑忌。此何理耶。不知自此而往。将复有何等事变。可畏可畏。其时所论三凶之罪。一一考示如何。
答洪乐舜为人问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6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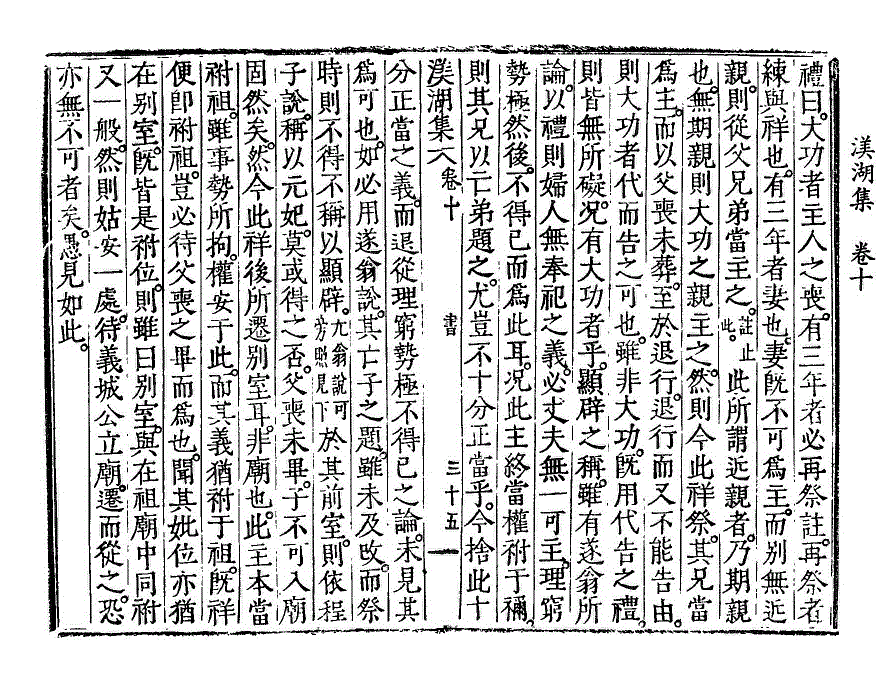 礼曰。大功者主人之丧。有三年者必再祭注。再祭者练与祥也。有三年者妻也。妻既不可为主。而别无近亲。则从父兄弟当主之。(注止此。)此所谓近亲者。乃期亲也。无期亲则大功之亲主之。然则今此祥祭。其兄当为主。而以父丧未葬。至于退行。退行而又不能告由。则大功者代而告之可也。虽非大功。既用代告之礼。则皆无所碍。况有大功者乎。显辟之称。虽有遂翁所论。以礼则妇人无奉祀之义。必丈夫无一可主。理穷势极然后。不得已而为此耳。况此主终当权祔于祢。则其兄以亡弟题之。尤岂不十分正当乎。今舍此十分正当之义。而退从理穷势极不得已之论。未见其为可也。如必用遂翁说。其亡子之题。虽未及改。而祭时则不得不称以显辟。(尤翁说可旁照见下。)于其前室。则依程子说。称以元妃。莫或得之否。父丧未毕。子不可入庙固然矣。然今此祥后所迁别室耳。非庙也。此主本当祔祖。虽事势所拘。权安于此。而其义犹祔于祖。既祥便即祔祖。岂必待父丧之毕而为也。闻其妣位亦犹在别室。既皆是祔位。则虽曰别室。与在祖庙中同祔又一般。然则姑安一处。待义城公立庙。迁而从之。恐亦无不可者矣。愚见如此。
礼曰。大功者主人之丧。有三年者必再祭注。再祭者练与祥也。有三年者妻也。妻既不可为主。而别无近亲。则从父兄弟当主之。(注止此。)此所谓近亲者。乃期亲也。无期亲则大功之亲主之。然则今此祥祭。其兄当为主。而以父丧未葬。至于退行。退行而又不能告由。则大功者代而告之可也。虽非大功。既用代告之礼。则皆无所碍。况有大功者乎。显辟之称。虽有遂翁所论。以礼则妇人无奉祀之义。必丈夫无一可主。理穷势极然后。不得已而为此耳。况此主终当权祔于祢。则其兄以亡弟题之。尤岂不十分正当乎。今舍此十分正当之义。而退从理穷势极不得已之论。未见其为可也。如必用遂翁说。其亡子之题。虽未及改。而祭时则不得不称以显辟。(尤翁说可旁照见下。)于其前室。则依程子说。称以元妃。莫或得之否。父丧未毕。子不可入庙固然矣。然今此祥后所迁别室耳。非庙也。此主本当祔祖。虽事势所拘。权安于此。而其义犹祔于祖。既祥便即祔祖。岂必待父丧之毕而为也。闻其妣位亦犹在别室。既皆是祔位。则虽曰别室。与在祖庙中同祔又一般。然则姑安一处。待义城公立庙。迁而从之。恐亦无不可者矣。愚见如此。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6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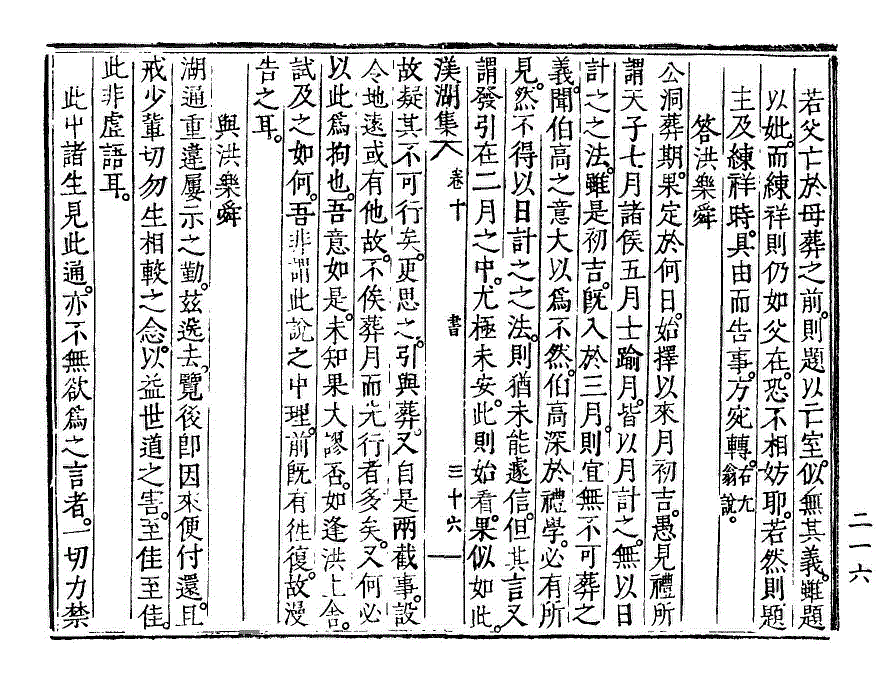 若父亡于母葬之前。则题以亡室。似无其义。虽题以妣。而练祥则仍如父在。恐不相妨耶。若然则题主及练祥时。具由而告事。方宛转。(右尤翁说)
若父亡于母葬之前。则题以亡室。似无其义。虽题以妣。而练祥则仍如父在。恐不相妨耶。若然则题主及练祥时。具由而告事。方宛转。(右尤翁说)答洪乐舜
公洞葬期。果定于何日。始择以来月初吉。愚见礼所谓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士踰月。皆以月计之。无以日计之之法。虽是初吉。既入于三月。则宜无不可葬之义。闻伯高之意大以为不然。伯高深于礼学。必有所见。然不得以日计之之法。则犹未能遽信。但其言又谓发引在二月之中。尤极未安。此则始看。果似如此。故疑其不可行矣。更思之。引与葬。又自是两截事。设令地远或有他故。不俟葬月而先行者多矣。又何必以此为拘也。吾意如是。未知果大谬否。如逢洪上舍。试及之如何。吾非谓此说之中理。前既有往复。故漫告之耳。
与洪乐舜
湖通重违屡示之勤。玆送去。览后即因来便付还。且戒少辈切勿生相较之念。以益世道之害。至佳至佳。此非虚语耳。
此中诸生见此通。亦不无欲为之言者。一切力禁
渼湖集卷之十 第 21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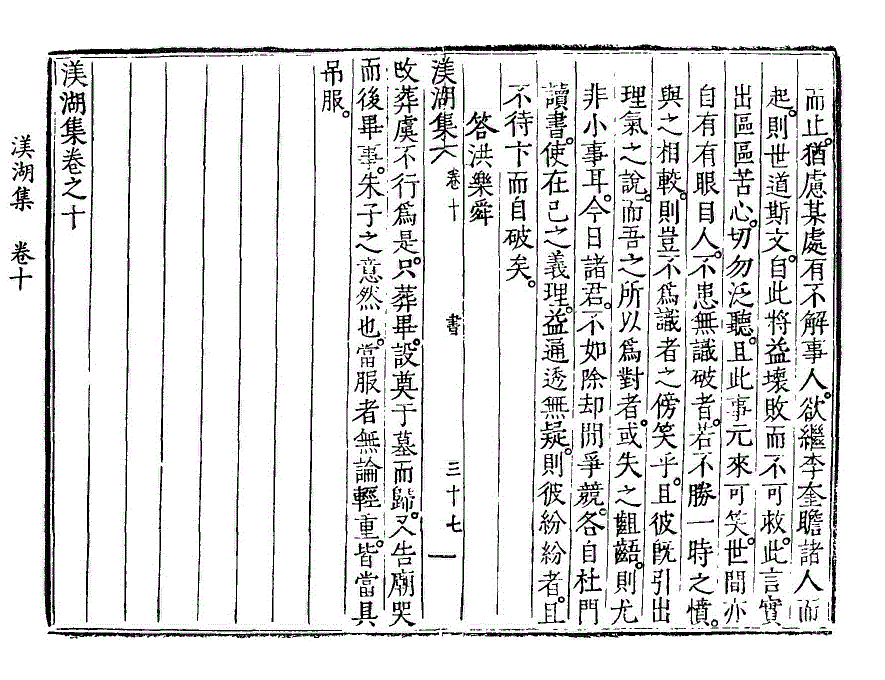 而止。犹虑某处有不解事人。欲继李奎瞻诸人而起。则世道斯文。自此将益坏败而不可救。此言实出区区苦心。切勿泛听。且此事元来可笑。世间亦自有有眼目人。不患无识破者。若不胜一时之愤。与之相较。则岂不为识者之傍笑乎。且彼既引出理气之说。而吾之所以为对者。或失之龃龉。则尤非小事耳。今日诸君。不如除却閒争竞。各自杜门读书。使在己之义理。益通透无疑。则彼纷纷者。且不待卞而自破矣。
而止。犹虑某处有不解事人。欲继李奎瞻诸人而起。则世道斯文。自此将益坏败而不可救。此言实出区区苦心。切勿泛听。且此事元来可笑。世间亦自有有眼目人。不患无识破者。若不胜一时之愤。与之相较。则岂不为识者之傍笑乎。且彼既引出理气之说。而吾之所以为对者。或失之龃龉。则尤非小事耳。今日诸君。不如除却閒争竞。各自杜门读书。使在己之义理。益通透无疑。则彼纷纷者。且不待卞而自破矣。答洪乐舜
改葬虞不行为是。只葬毕。设奠于墓而归。又告庙哭而后毕事。朱子之意然也。当服者无论轻重。皆当具吊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