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明: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.org,kanripo.org, db.itkc.or.kr 和 zh.wikisource.org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x 页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
记
记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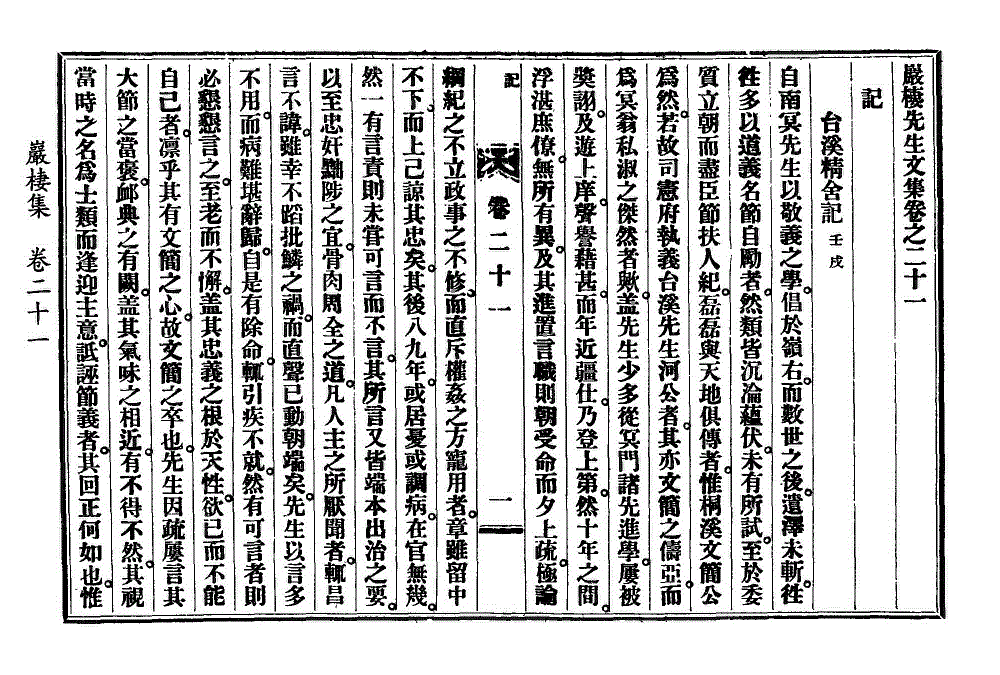 台溪精舍记(壬戌)
台溪精舍记(壬戌)自南冥先生以敬义之学。倡于岭右。而数世之后。遗泽未斩。往往多以道义名节自励者。然类皆沉沦蕴伏。未有所试。至于委质立朝而尽臣节扶人纪。磊磊与天地俱传者。惟桐溪文简公为然。若故司宪府执义台溪先生河公者。其亦文简之俦亚。而为冥翁私淑之杰然者欤。盖先生少多从冥门诸先进学。屡被奖诩。及游上庠。声誉藉甚。而年近疆仕。乃登上第。然十年之间。浮湛庶僚。无所有异。及其进置言职则朝受命而夕上疏。极论纲纪之不立政事之不修。而直斥权奸之方宠用者。章虽留中不下。而上已谅其忠矣。其后八九年。或居忧或调病。在官无几。然一有言责则未尝可言而不言。其所言又皆端本出治之要。以至忠奸黜陟之宜。骨肉周全之道。凡人主之所厌闻者。辄昌言不讳。虽幸不蹈批鳞之祸。而直声已动朝端矣。先生以言多不用。而病难堪辞归。自是有除命。辄引疾不就。然有可言者则必恳恳言之。至老而不懈。盖其忠义之根于天性。欲已而不能自已者。凛乎其有文简之心。故文简之卒也。先生因疏屡言其大节之当褒。恤典之有阙。盖其气味之相近。有不得不然。其视当时之名为士类而逢迎主意。诋诬节义者。其回正何如也。惟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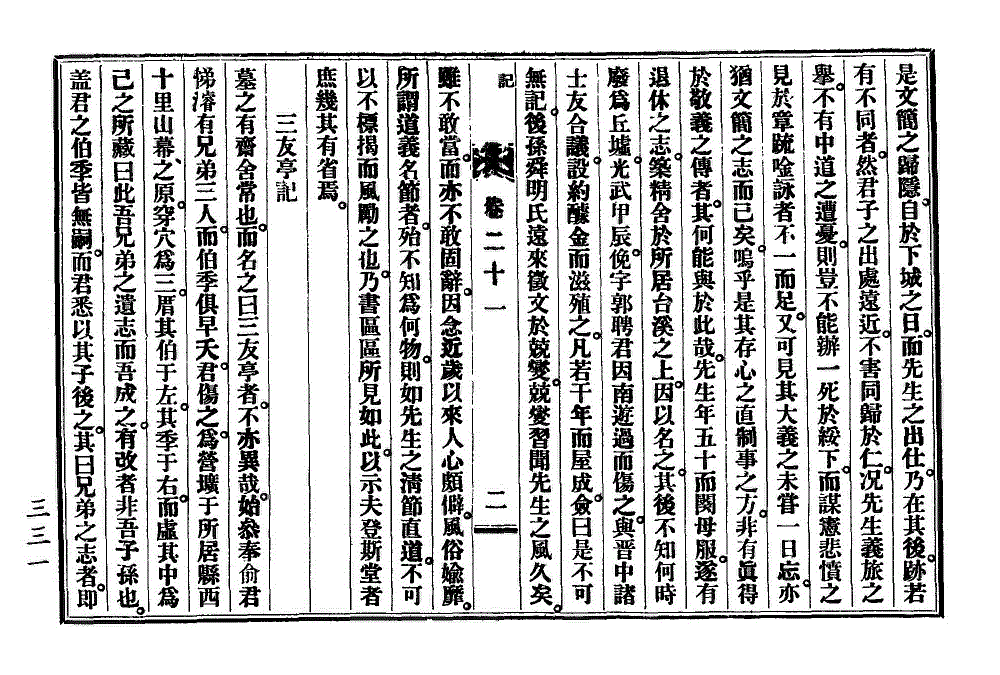 是文简之归隐。自于下城之日。而先生之出仕。乃在其后。迹若有不同者。然君子之出处远近。不害同归于仁。况先生义旅之举。不有中道之遭忧。则岂不能办一死于绥下。而谋宪悲愤之见于章疏唫咏者不一而足。又可见其大义之未尝一日忘。亦犹文简之志而已矣。呜乎是其存心之直制事之方。非有真得于敬义之传者。其何能与于此哉。先生年五十而阕母服。遂有退休之志。筑精舍于所居台溪之上。因以名之。其后不知何时废为丘墟。光武甲辰。俛宇郭聘君因南游过而伤之。与晋中诸士友合议。设约醵金而滋殖之。凡若干年而屋成。佥曰是不可无记。后孙舜明氏远来徵文于兢燮。兢燮习闻先生之风久矣。虽不敢当。而亦不敢固辞。因念近岁以来人心颇僻。风俗媮靡。所谓道义名节者。殆不知为何物。则如先生之清节直道。不可以不标揭而风励之也。乃书区区所见如此。以示夫登斯堂者庶几其有省焉。
是文简之归隐。自于下城之日。而先生之出仕。乃在其后。迹若有不同者。然君子之出处远近。不害同归于仁。况先生义旅之举。不有中道之遭忧。则岂不能办一死于绥下。而谋宪悲愤之见于章疏唫咏者不一而足。又可见其大义之未尝一日忘。亦犹文简之志而已矣。呜乎是其存心之直制事之方。非有真得于敬义之传者。其何能与于此哉。先生年五十而阕母服。遂有退休之志。筑精舍于所居台溪之上。因以名之。其后不知何时废为丘墟。光武甲辰。俛宇郭聘君因南游过而伤之。与晋中诸士友合议。设约醵金而滋殖之。凡若干年而屋成。佥曰是不可无记。后孙舜明氏远来徵文于兢燮。兢燮习闻先生之风久矣。虽不敢当。而亦不敢固辞。因念近岁以来人心颇僻。风俗媮靡。所谓道义名节者。殆不知为何物。则如先生之清节直道。不可以不标揭而风励之也。乃书区区所见如此。以示夫登斯堂者庶几其有省焉。三友亭记
墓之有斋舍常也。而名之曰三友亭者。不亦异哉。始参奉俞君悌浚有兄弟三人。而伯季俱早夭。君伤之。为营圹于所居县西十里山幕之原。穿穴为三。厝其伯于左。其季于右。而虚其中为己之所藏曰此吾兄弟之遗志而吾成之。有改者非吾子孙也。盖君之伯季皆无嗣。而君悉以其子后之。其曰兄弟之志者。即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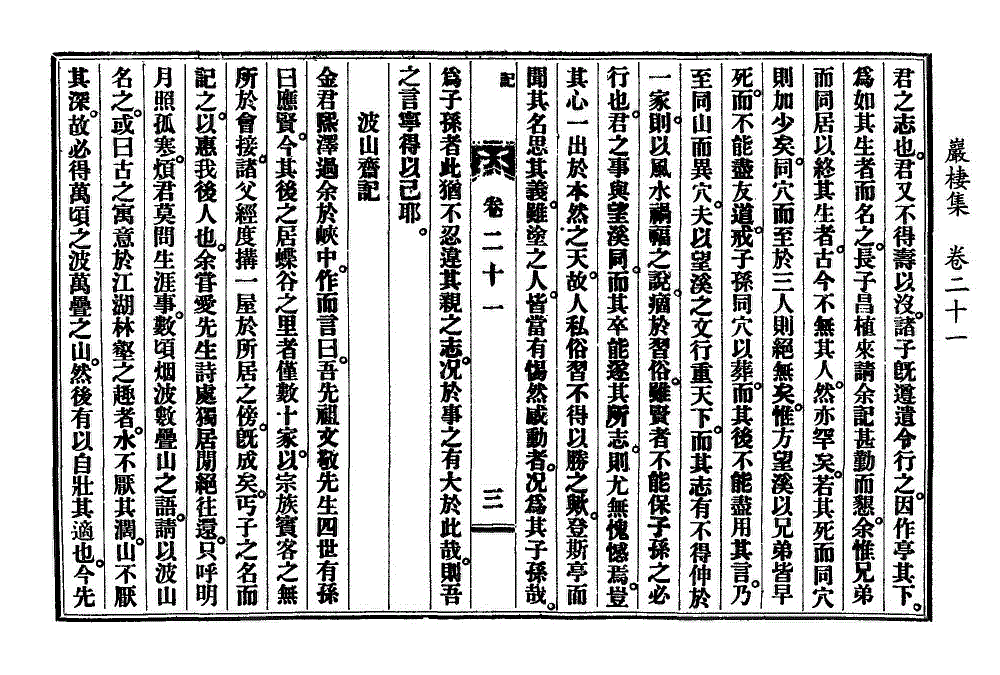 君之志也。君又不得寿以没。诸子既遵遗令行之。因作亭其下。为如其生者而名之。长子昌植来请余记甚勤而恳。余惟兄弟而同居以终其生者。古今不无其人。然亦罕矣。若其死而同穴则加少矣。同穴而至于三人则绝无矣。惟方望溪以兄弟皆早死。而不能尽友道。戒子孙同穴以葬。而其后不能尽用其言。乃至同山而异穴。夫以望溪之文行重天下。而其志有不得伸于一家。则以风水祸福之说。痼于习俗。虽贤者不能保子孙之必行也。君之事与望溪同。而其卒能遂其所志。则尤无愧憾焉。岂其心一出于本然之天。故人私俗习不得以胜之欤。登斯亭而闻其名思其义。虽涂之人。皆当有惕然感动者。况为其子孙哉。为子孙者此犹不忍违其亲之志。况于事之有大于此哉。则吾之言宁得以已耶。
君之志也。君又不得寿以没。诸子既遵遗令行之。因作亭其下。为如其生者而名之。长子昌植来请余记甚勤而恳。余惟兄弟而同居以终其生者。古今不无其人。然亦罕矣。若其死而同穴则加少矣。同穴而至于三人则绝无矣。惟方望溪以兄弟皆早死。而不能尽友道。戒子孙同穴以葬。而其后不能尽用其言。乃至同山而异穴。夫以望溪之文行重天下。而其志有不得伸于一家。则以风水祸福之说。痼于习俗。虽贤者不能保子孙之必行也。君之事与望溪同。而其卒能遂其所志。则尤无愧憾焉。岂其心一出于本然之天。故人私俗习不得以胜之欤。登斯亭而闻其名思其义。虽涂之人。皆当有惕然感动者。况为其子孙哉。为子孙者此犹不忍违其亲之志。况于事之有大于此哉。则吾之言宁得以已耶。波山斋记
金君熙泽过余于峡中。作而言曰。吾先祖文敬先生四世有孙曰应贤。今其后之居蝶谷之里者仅数十家。以宗族宾客之无所于会接。诸父经度搆一屋于所居之傍。既成矣。丐子之名而记之。以惠我后人也。余尝爱先生诗处独居閒绝往还。只呼明月照孤寒。烦君莫问生涯事。数顷烟波数叠山之语。请以波山名之。或曰古之寓意于江湖林壑之趣者。水不厌其阔。山不厌其深。故必得万顷之波万叠之山。然后有以自壮其适也。今先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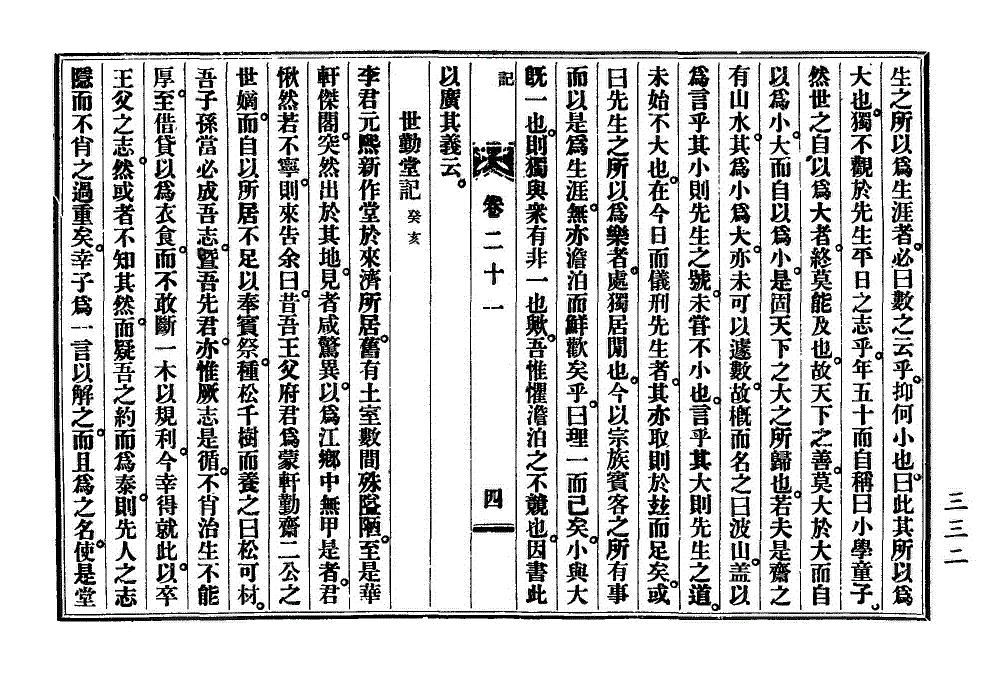 生之所以为生涯者。必曰数之云乎。抑何小也。曰此其所以为大也。独不观于先生平日之志乎。年五十而自称曰小学童子。然世之自以为大者。终莫能及也。故天下之善。莫大于大而自以为小。大而自以为小。是固天下之大之所归也。若夫是斋之有山水。其为小为大。亦未可以遽数。故概而名之曰波山。盖以为言乎其小则先生之号。未尝不小也。言乎其大则先生之道。未始不大也。在今日而仪刑先生者。其亦取则于玆而足矣。或曰先生之所以为乐者。处独居閒也。今以宗族宾客之所有事而以是为生涯。无亦澹泊而鲜欢矣乎。曰理一而已矣。小与大既一也。则独与众有非一也欤。吾惟惧澹泊之不竞也。因书此以广其义云。
生之所以为生涯者。必曰数之云乎。抑何小也。曰此其所以为大也。独不观于先生平日之志乎。年五十而自称曰小学童子。然世之自以为大者。终莫能及也。故天下之善。莫大于大而自以为小。大而自以为小。是固天下之大之所归也。若夫是斋之有山水。其为小为大。亦未可以遽数。故概而名之曰波山。盖以为言乎其小则先生之号。未尝不小也。言乎其大则先生之道。未始不大也。在今日而仪刑先生者。其亦取则于玆而足矣。或曰先生之所以为乐者。处独居閒也。今以宗族宾客之所有事而以是为生涯。无亦澹泊而鲜欢矣乎。曰理一而已矣。小与大既一也。则独与众有非一也欤。吾惟惧澹泊之不竞也。因书此以广其义云。世勤堂记(癸亥)
李君元熙新作堂于来济所居。旧有土室数间殊隘陋。至是华轩杰阁。突然出于其地。见者咸惊异。以为江乡中无甲是者。君愀然若不宁。则来告余曰。昔吾王父府君为蒙轩勤斋二公之世嫡。而自以所居不足以奉宾祭。种松千树而养之曰松可材。吾子孙当必成吾志。暨吾先君。亦惟厥志是循。不肖治生不能厚。至借贷以为衣食。而不敢断一木以规利。今幸得就此。以卒王父之志。然或者不知其然。而疑吾之约而为泰。则先人之志隐而不肖之过重矣。幸子为一言以解之。而且为之名。使是堂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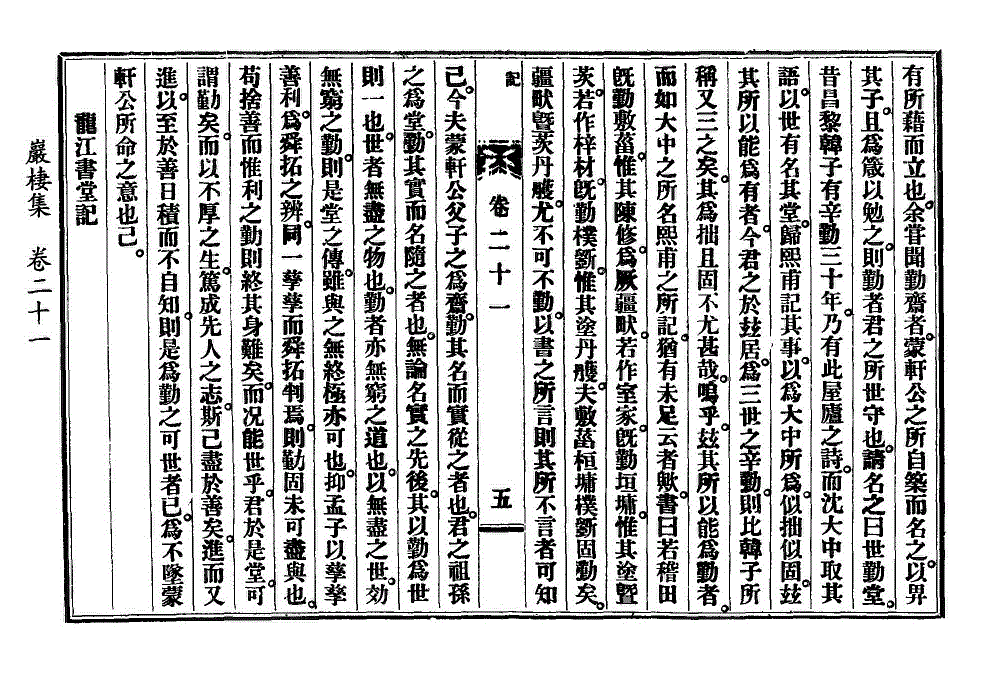 有所藉而立也。余尝闻勤斋者。蒙轩公之所自筑而名之。以畀其子。且为箴以勉之。则勤者君之所世守也。请名之曰世勤堂。昔昌黎韩子有辛勤三十年。乃有此屋庐之诗。而沈大中取其语。以世有名其堂。归熙甫记其事。以为大中所为。似拙似固。玆其所以能为有者。今君之于玆居。为三世之辛勤。则比韩子所称又三之矣。其为拙且固不尤甚哉。呜乎。玆其所以能为勤者。而如大中之所名熙甫之所记。犹有未足云者欤。书曰若稽田既勤敷菑。惟其陈修。为厥疆畎。若作室家。既勤垣墉。惟其涂暨茨。若作梓材。既勤朴斲。惟其涂丹雘。夫敷菑桓墉朴斲固勤矣。疆畎暨茨丹雘。尤不可不勤。以书之所言则其所不言者可知已。今夫蒙轩公父子之为斋。勤其名而实从之者也。君之祖孙之为堂。勤其实而名随之者也。无论名实之先后。其以勤为世则一也。世者无尽之物也。勤者亦无穷之道也。以无尽之世。效无穷之勤。则是堂之传。虽与之无终极亦可也。抑孟子以孳孳善利。为舜拓之辨。同一孳孳而舜拓判焉。则勤固未可尽与也。苟舍善而惟利之勤则终其身难矣。而况能世乎。君于是堂。可谓勤矣。而以不厚之生。笃成先人之志。斯已尽于善矣。进而又进。以至于善日积而不自知。则是为勤之可世者已。为不坠蒙轩公所命之意也已。
有所藉而立也。余尝闻勤斋者。蒙轩公之所自筑而名之。以畀其子。且为箴以勉之。则勤者君之所世守也。请名之曰世勤堂。昔昌黎韩子有辛勤三十年。乃有此屋庐之诗。而沈大中取其语。以世有名其堂。归熙甫记其事。以为大中所为。似拙似固。玆其所以能为有者。今君之于玆居。为三世之辛勤。则比韩子所称又三之矣。其为拙且固不尤甚哉。呜乎。玆其所以能为勤者。而如大中之所名熙甫之所记。犹有未足云者欤。书曰若稽田既勤敷菑。惟其陈修。为厥疆畎。若作室家。既勤垣墉。惟其涂暨茨。若作梓材。既勤朴斲。惟其涂丹雘。夫敷菑桓墉朴斲固勤矣。疆畎暨茨丹雘。尤不可不勤。以书之所言则其所不言者可知已。今夫蒙轩公父子之为斋。勤其名而实从之者也。君之祖孙之为堂。勤其实而名随之者也。无论名实之先后。其以勤为世则一也。世者无尽之物也。勤者亦无穷之道也。以无尽之世。效无穷之勤。则是堂之传。虽与之无终极亦可也。抑孟子以孳孳善利。为舜拓之辨。同一孳孳而舜拓判焉。则勤固未可尽与也。苟舍善而惟利之勤则终其身难矣。而况能世乎。君于是堂。可谓勤矣。而以不厚之生。笃成先人之志。斯已尽于善矣。进而又进。以至于善日积而不自知。则是为勤之可世者已。为不坠蒙轩公所命之意也已。龙江书堂记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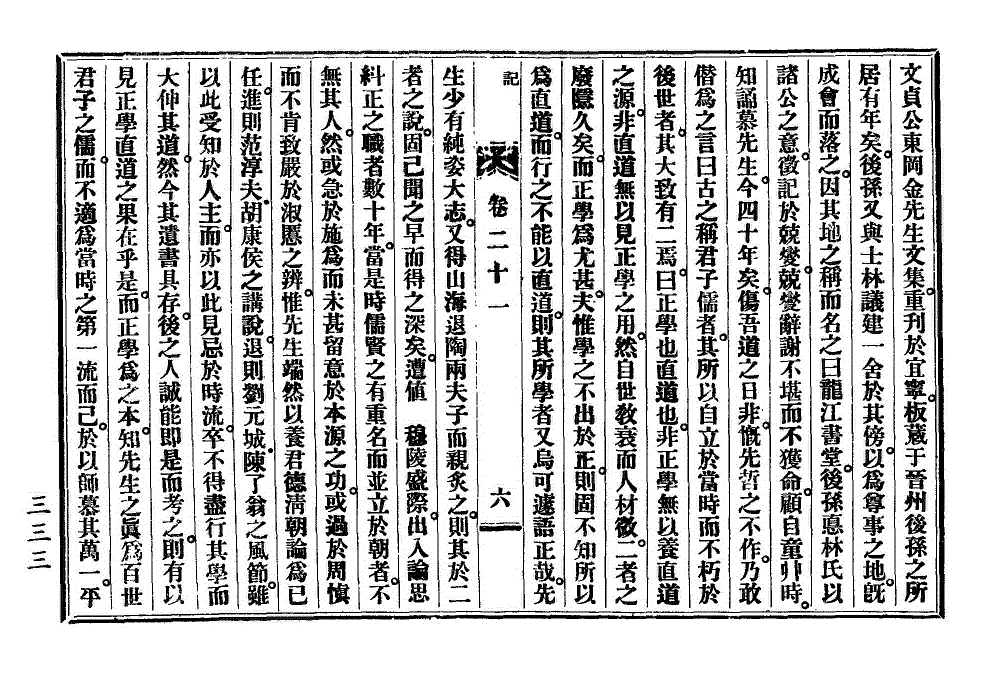 文贞公东冈金先生文集。重刊于宜宁。板藏于晋州后孙之所居有年矣。后孙又与士林议建一舍于其傍。以为尊事之地。既成会而落之。因其地之称而名之曰龙江书堂。后孙德林氏以诸公之意。徵记于兢燮。兢燮辞谢不堪而不获命。顾自童丱时。知诵慕先生。今四十年矣。伤吾道之日非。慨先哲之不作。乃敢僭为之言曰古之称君子儒者。其所以自立于当时而不朽于后世者。其大致有二焉。曰正学也直道也。非正学无以养直道之源。非直道无以见正学之用。然自世教衰而人材微。二者之废隐久矣。而正学为尤甚。夫惟学之不出于正。则固不知所以为直道。而行之不能以直道。则其所学者又乌可遽语正哉。先生少有纯姿大志。又得山海退陶两夫子而亲炙之。则其于二者之说。固已闻之早而得之深矣。遭值 穆陵盛际。出入论思纠正之职者数十年。当是时儒贤之有重名而并立于朝者。不无其人。然或急于施为而未甚留意于本源之功。或过于周慎而不肯致严于淑慝之辨。惟先生端然以养君德清朝论为己任。进则范淳夫,胡康侯之讲说。退则刘元城,陈了翁之风节。虽以此受知于人主。而亦以此见忌于时流。卒不得尽行其学而大伸其道。然今其遗书具存。后之人诚能即是而考之。则有以见正学直道之果在乎是。而正学为之本。知先生之真为百世君子之儒。而不适为当时之第一流而已。于以师慕其万一。平
文贞公东冈金先生文集。重刊于宜宁。板藏于晋州后孙之所居有年矣。后孙又与士林议建一舍于其傍。以为尊事之地。既成会而落之。因其地之称而名之曰龙江书堂。后孙德林氏以诸公之意。徵记于兢燮。兢燮辞谢不堪而不获命。顾自童丱时。知诵慕先生。今四十年矣。伤吾道之日非。慨先哲之不作。乃敢僭为之言曰古之称君子儒者。其所以自立于当时而不朽于后世者。其大致有二焉。曰正学也直道也。非正学无以养直道之源。非直道无以见正学之用。然自世教衰而人材微。二者之废隐久矣。而正学为尤甚。夫惟学之不出于正。则固不知所以为直道。而行之不能以直道。则其所学者又乌可遽语正哉。先生少有纯姿大志。又得山海退陶两夫子而亲炙之。则其于二者之说。固已闻之早而得之深矣。遭值 穆陵盛际。出入论思纠正之职者数十年。当是时儒贤之有重名而并立于朝者。不无其人。然或急于施为而未甚留意于本源之功。或过于周慎而不肯致严于淑慝之辨。惟先生端然以养君德清朝论为己任。进则范淳夫,胡康侯之讲说。退则刘元城,陈了翁之风节。虽以此受知于人主。而亦以此见忌于时流。卒不得尽行其学而大伸其道。然今其遗书具存。后之人诚能即是而考之。则有以见正学直道之果在乎是。而正学为之本。知先生之真为百世君子之儒。而不适为当时之第一流而已。于以师慕其万一。平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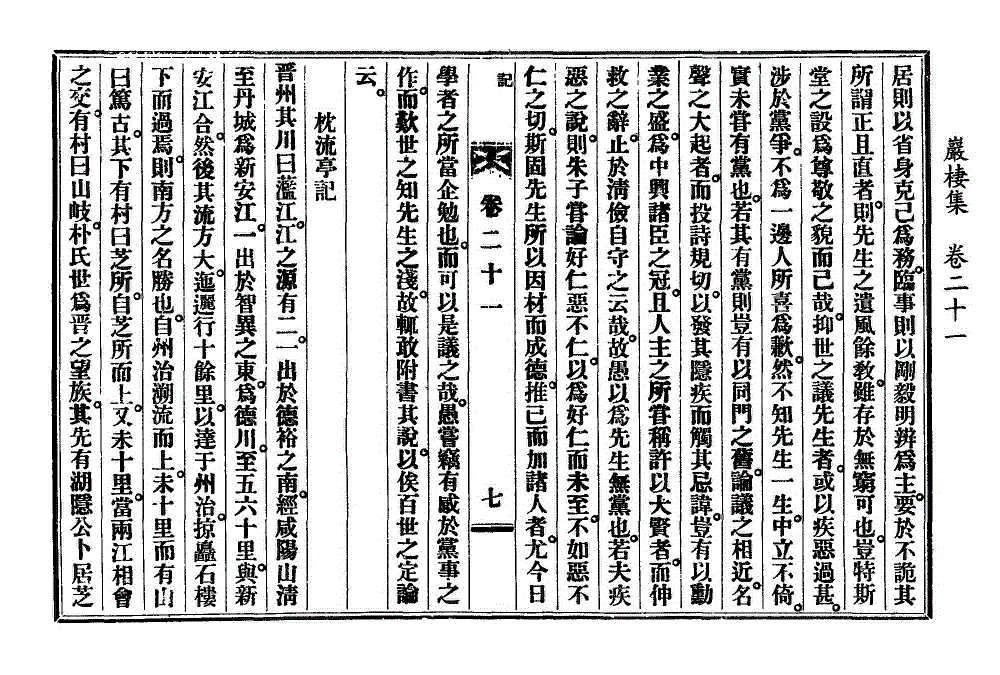 居则以省身克己为务。临事则以刚毅明辨为主。要于不诡其所谓正且直者。则先生之遗风馀教。虽存于无穷可也。岂特斯堂之设为尊敬之貌而已哉。抑世之议先生者。或以疾恶过甚。涉于党争。不为一边人所喜为歉。然不知先生一生。中立不倚。实未尝有党也。若其有党则岂有以同门之旧。论议之相近。名声之大起者。而投诗规切。以发其隐疾而触其忌讳。岂有以勋业之盛。为中兴诸臣之冠。且人主之所尝称许以大贤者。而伸救之辞。止于清俭自守之云哉。故愚以为先生无党也。若夫疾恶之说。则朱子尝论好仁恶不仁。以为好仁而未至。不如恶不仁之切。斯固先生所以因材而成德。推己而加诸人者。尤今日学者之所当企勉也。而可以是议之哉。愚尝窃有感于党事之作。而叹世之知先生之浅。故辄敢附书其说。以俟百世之定论云。
居则以省身克己为务。临事则以刚毅明辨为主。要于不诡其所谓正且直者。则先生之遗风馀教。虽存于无穷可也。岂特斯堂之设为尊敬之貌而已哉。抑世之议先生者。或以疾恶过甚。涉于党争。不为一边人所喜为歉。然不知先生一生。中立不倚。实未尝有党也。若其有党则岂有以同门之旧。论议之相近。名声之大起者。而投诗规切。以发其隐疾而触其忌讳。岂有以勋业之盛。为中兴诸臣之冠。且人主之所尝称许以大贤者。而伸救之辞。止于清俭自守之云哉。故愚以为先生无党也。若夫疾恶之说。则朱子尝论好仁恶不仁。以为好仁而未至。不如恶不仁之切。斯固先生所以因材而成德。推己而加诸人者。尤今日学者之所当企勉也。而可以是议之哉。愚尝窃有感于党事之作。而叹世之知先生之浅。故辄敢附书其说。以俟百世之定论云。枕流亭记
晋州其川曰蘫江。江之源有二。一出于德裕之南。经咸阳山清至丹城为新安江。一出于智异之东。为德川。至五六十里。与新安江合。然后其流方大。迤逦行十馀里。以达于州治。掠矗石楼下而过焉。则南方之名胜也。自州治溯流而上。未十里而有山曰笃古。其下有村曰芝所。自芝所而上。又未十里。当两江相会之交。有村曰山岐。朴氏世为晋之望族。其先有湖隐公卜居芝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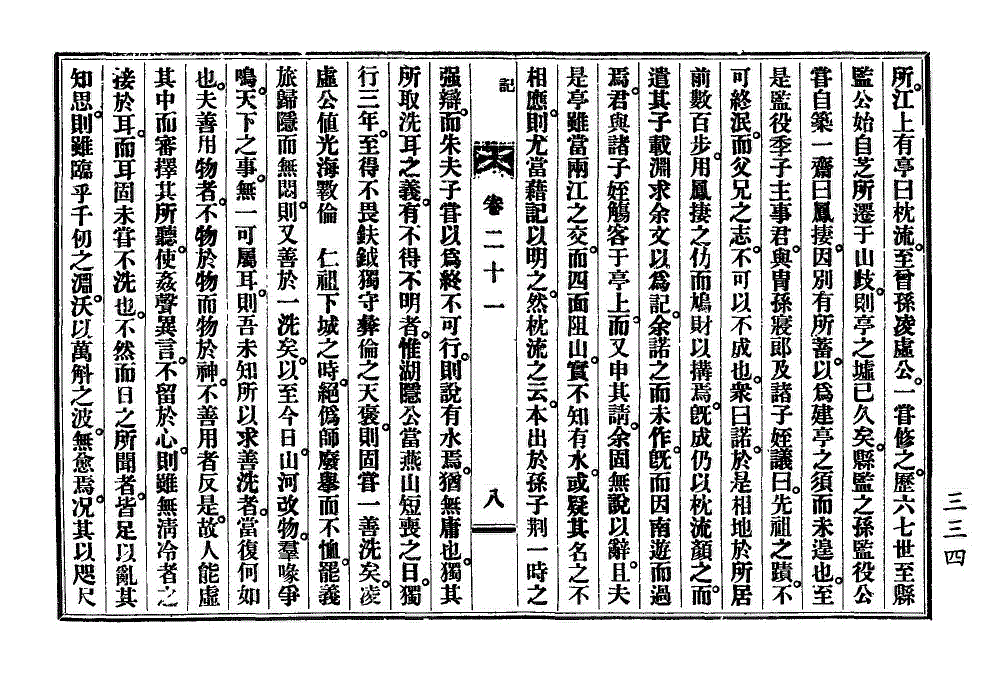 所。江上有亭曰枕流。至曾孙凌虚公。一尝修之。历六七世至县监公始自芝所迁于山歧。则亭之墟已久矣。县监之孙监役公尝自筑一斋曰凤栖。因别有所蓄。以为建亭之须而未遑也。至是监役季子主事君。与胄孙寝郎及诸子侄议曰。先祖之迹。不可终泯。而父兄之志。不可以不成也。众曰诺。于是相地于所居前数百步。用凤栖之仂而鸠财以搆焉。既成仍以枕流颜之。而遣其子载渊求余文以为记。余诺之而未作。既而因南游而过焉。君与诸子侄觞客于亭上。而又申其请。余固无说以辞。且夫是亭虽当两江之交。而四面阻山。实不知有水。或疑其名之不相应。则尤当藉记以明之。然枕流之云。本出于孙子荆一时之强辩。而朱夫子尝以为终不可行。则说有水焉。犹无庸也。独其所取洗耳之义。有不得不明者。惟湖隐公当燕山短丧之日。独行三年。至得不畏鈇钺独守彝伦之天褒。则固尝一善洗矣。凌虚公值光海斁伦 仁祖下城之时。绝伪师废举而不恤。罢义旅归隐而无闷。则又善于一洗矣。以至今日。山河改物。群喙争鸣。天下之事。无一可属耳。则吾未知所以求善洗者。当复何如也。夫善用物者。不物于物而物于神。不善用者反是。故人能虚其中而审择其所听。使奸声异言。不留于心。则虽无清冷者之接于耳。而耳固未尝不洗也。不然而日之所闻者。皆足以乱其知思。则虽临乎千仞之渊。沃以万斛之波。无愈焉。况其以咫尺
所。江上有亭曰枕流。至曾孙凌虚公。一尝修之。历六七世至县监公始自芝所迁于山歧。则亭之墟已久矣。县监之孙监役公尝自筑一斋曰凤栖。因别有所蓄。以为建亭之须而未遑也。至是监役季子主事君。与胄孙寝郎及诸子侄议曰。先祖之迹。不可终泯。而父兄之志。不可以不成也。众曰诺。于是相地于所居前数百步。用凤栖之仂而鸠财以搆焉。既成仍以枕流颜之。而遣其子载渊求余文以为记。余诺之而未作。既而因南游而过焉。君与诸子侄觞客于亭上。而又申其请。余固无说以辞。且夫是亭虽当两江之交。而四面阻山。实不知有水。或疑其名之不相应。则尤当藉记以明之。然枕流之云。本出于孙子荆一时之强辩。而朱夫子尝以为终不可行。则说有水焉。犹无庸也。独其所取洗耳之义。有不得不明者。惟湖隐公当燕山短丧之日。独行三年。至得不畏鈇钺独守彝伦之天褒。则固尝一善洗矣。凌虚公值光海斁伦 仁祖下城之时。绝伪师废举而不恤。罢义旅归隐而无闷。则又善于一洗矣。以至今日。山河改物。群喙争鸣。天下之事。无一可属耳。则吾未知所以求善洗者。当复何如也。夫善用物者。不物于物而物于神。不善用者反是。故人能虚其中而审择其所听。使奸声异言。不留于心。则虽无清冷者之接于耳。而耳固未尝不洗也。不然而日之所闻者。皆足以乱其知思。则虽临乎千仞之渊。沃以万斛之波。无愈焉。况其以咫尺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5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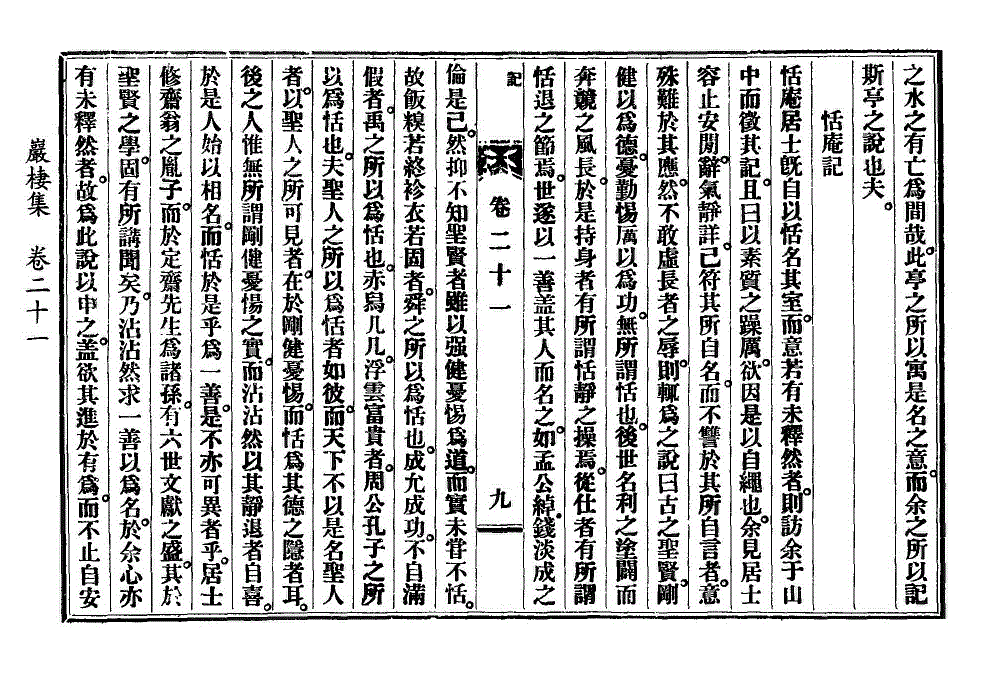 之水之有亡为间哉。此亭之所以寓是名之意。而余之所以记斯亭之说也夫。
之水之有亡为间哉。此亭之所以寓是名之意。而余之所以记斯亭之说也夫。恬庵记
恬庵居士既自以恬名其室。而意若有未释然者。则访余于山中而徵其记。且曰以素质之躁厉。欲因是以自绳也。余见居士容止安閒。辞气静详。已符其所自名。而不雠于其所自言者。意殊难于其应。然不敢虚长者之辱。则辄为之说曰古之圣贤。刚健以为德。忧勤惕厉以为功。无所谓恬也。后世名利之涂辟而奔竞之风长。于是持身者有所谓恬静之操焉。从仕者有所谓恬退之节焉。世遂以一善盖其人而名之。如孟公绰,钱淡成之伦是已。然抑不知圣贤者虽以强健忧惕为道。而实未尝不恬。故饭糗若终袗衣若固者。舜之所以为恬也。成允成功。不自满假者。禹之所以为恬也。赤舄几几。浮云富贵者。周公孔子之所以为恬也。夫圣人之所以为恬者如彼。而天下不以是名圣人者。以圣人之所可见者。在于刚健忧惕。而恬为其德之隐者耳。后之人惟无所谓刚健忧惕之实。而沾沾然以其静退者自喜。于是人始以相名。而恬于是乎为一善。是不亦可异者乎。居士修斋翁之胤子。而于定斋先生为诸孙。有六世文献之盛。其于圣贤之学。固有所讲闻矣。乃沾沾然求一善以为名。于余心亦有未释然者。故为此说以申之。盖欲其进于有为。而不止自安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5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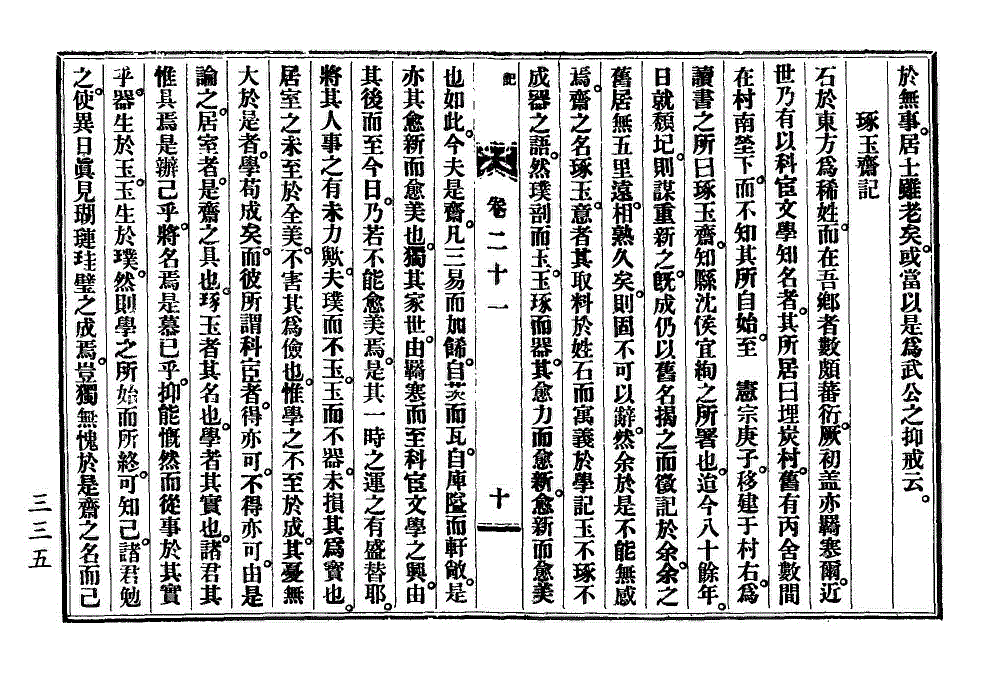 于无事。居士虽老矣。或当以是为武公之抑戒云。
于无事。居士虽老矣。或当以是为武公之抑戒云。琢玉斋记
石于东方为稀姓。而在吾乡者数颇蕃衍。厥初盖亦羁寒尔。近世乃有以科宦文学知名者。其所居曰埋炭村。旧有丙舍数间在村南茔下。而不知其所自始。至 宪宗庚子。移建于村右。为读书之所曰琢玉斋。知县沈侯宜绚之所署也。迨今八十馀年。日就颓圮。则谋重新之。既成仍以旧名揭之而徵记于余。余之旧居无五里远。相熟久矣。则固不可以辞。然余于是不能无感焉。斋之名琢玉。意者其取料于姓石而寓义于学记玉不琢不成器之语。然璞剖而玉。玉琢而器。其愈力而愈新。愈新而愈美也如此。今夫是斋。凡三易而加饰。自茨而瓦。自庳隘而轩敞。是亦其愈新而愈美也。独其家世。由羁寒而至科宦文学之兴。由其后而至今日。乃若不能愈美焉。是其一时之运之有盛替耶。将其人事之有未力欤。夫璞而不玉。玉而不器。未损其为宝也。居室之未至于全美。不害其为俭也。惟学之不至于成。其忧无大于是者。学苟成矣。而彼所谓科宦者。得亦可。不得亦可。由是论之。居室者。是斋之具也。琢玉者其名也。学者其实也。诸君其惟具焉是办已乎。将名焉是慕已乎。抑能慨然而从事于其实乎。器生于玉。玉生于璞。然则学之所始而所终。可知已。诸君勉之。使异日真见瑚琏圭璧之成焉。岂独无愧于是斋之名而已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6H 页
 哉。是为记。斋之建也。终始尸其事者。曰炳穆曰晋均。
哉。是为记。斋之建也。终始尸其事者。曰炳穆曰晋均。岁寒亭记(甲子)
余既因李君圣律之请。铭其伯父晴湖处士之藏。而圣律则又前请曰伯父晚年。有藏修之室曰岁寒亭。亭成而未有记。诸孤之意。并欲得子文以揭之。子必无拒。余于李氏。尝记其念修之斋而及处士公事矣。今又与之为铭则所可书者尽矣。无以加矣。以是辞而不获。则敬因其名亭之意而为之说曰。夫子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。斯语也其取譬之义甚博。而范氏独以临利害遇事变为言者。诚以人之所以受变于物。无此二者大焉。今夫庸夫细人其在平时。或端言庄色。或饰节矜行。泯然自列于君子之林。人亦无以别之也。及至利害乘其前。事变迫于后。小则丰约荣悴。大则死生祸福。于是而其素所自持者。不仓皇而失之。则必积渐以消之。卒复于庸夫细人之旧而已。若夫不为利而趍。不为害而避。不以常而存。不以变而亡。万事交于前而一心亘于中。礼约荣悴死生祸福。不足以移之。是其人也名曰君子。其在物也。惟岁寒之松柏似之。然后知夫子之言为万世不可易之至喻。而士之省己而观人者。亦审于此而定焉已矣。然余观今之士。恒居所自云云者。何尝不以松柏之操。而至临事不自觉其为凡卉众木之望秋而彫者。则是不惟其志之不坚。殆皆由于识之不明。故欲求坚其志者。必资学以明其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6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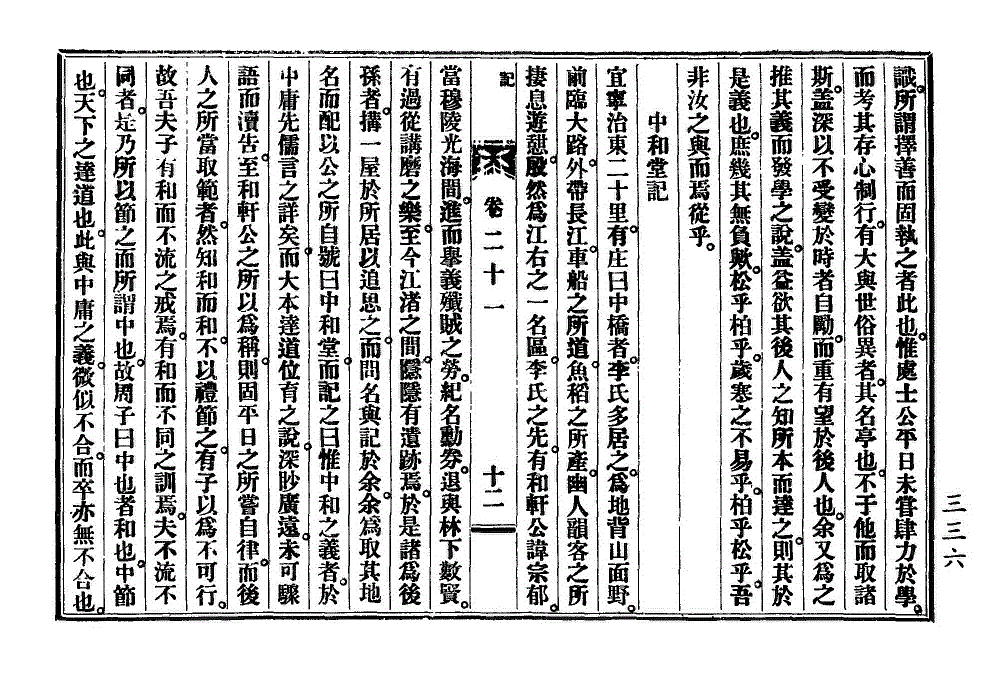 识。所谓择善而固执之者此也。惟处士公平日未尝肆力于学。而考其存心制行。有大与世俗异者。其名亭也。不于他而取诸斯。盖深以不受变于时者自励。而重有望于后人也。余又为之推其义而发学之说。盖益欲其后人之知所本而达之。则其于是义也。庶几其无负欤。松乎柏乎。岁寒之不易乎。柏乎松乎。吾非汝之与而焉从乎。
识。所谓择善而固执之者此也。惟处士公平日未尝肆力于学。而考其存心制行。有大与世俗异者。其名亭也。不于他而取诸斯。盖深以不受变于时者自励。而重有望于后人也。余又为之推其义而发学之说。盖益欲其后人之知所本而达之。则其于是义也。庶几其无负欤。松乎柏乎。岁寒之不易乎。柏乎松乎。吾非汝之与而焉从乎。中和堂记
宜宁治东二十里。有庄曰中桥者。李氏多居之。为地背山面野。前临大路。外带长江。车船之所道。鱼稻之所产。幽人韵客之所栖息游憩。殷然为江右之一名区。李氏之先。有和轩公讳宗郁。当穆陵光海间。进而举义歼贼之劳。纪名勋券。退与林下数贤。有过从讲磨之乐。至今江渚之间。隐隐有遗迹焉。于是诸为后孙者。搆一屋于所居以追思之。而问名与记于余。余为取其地名而配以公之所自号曰中和堂。而记之曰惟中和之义者。于中庸先儒言之详矣。而大本达道位育之说。深眇广远。未可骤语而渎告。至和轩公之所以为称。则固平日之所尝自律。而后人之所当取范者。然知和而和。不以礼节之。有子以为不可行。故吾夫子有和而不流之戒焉。有和而不同之训焉。夫不流不同者。是乃所以节之而所谓中也。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。中节也。天下之达道也。此与中庸之义。微似不合。而卒亦无不合也。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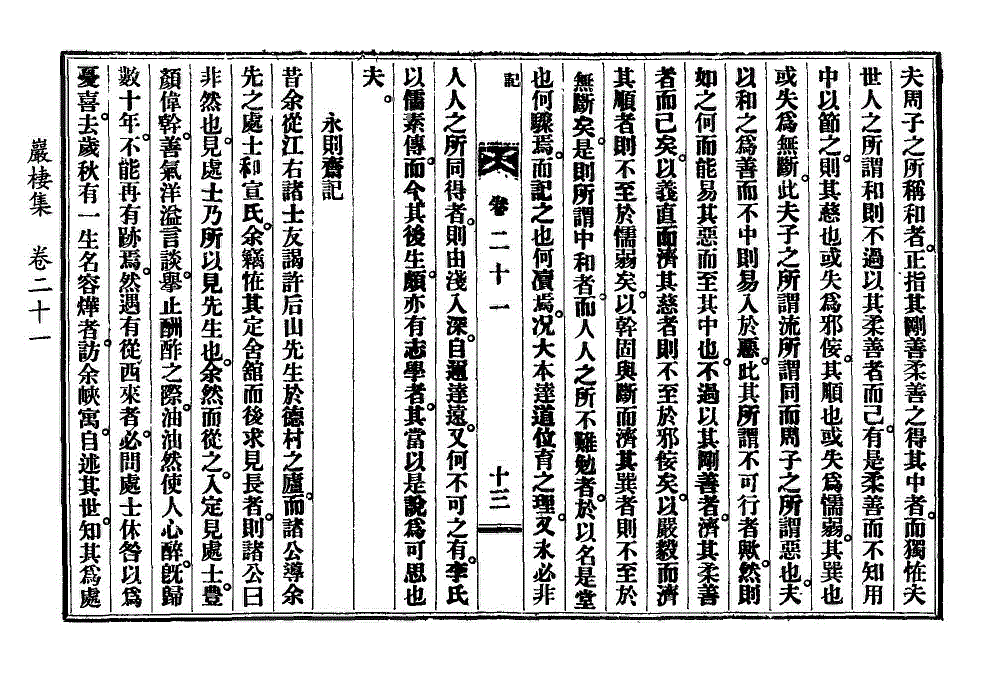 夫周子之所称和者。正指其刚善柔善之得其中者。而独怪夫世人之所谓和则不过以其柔善者而已。有是柔善而不知用中以节之。则其慈也或失为邪佞。其顺也或失为懦弱。其巽也或失为无断。此夫子之所谓流所谓同而周子之所谓恶也。夫以和之为善而不中则易入于恶。此其所谓不可行者欤。然则如之何而能易其恶而至其中也。不过以其刚善者。济其柔善者而已矣。以义直而济其慈者则不至于邪佞矣。以严毅而济其顺者则不至于懦弱矣。以干固与断而济其巽者则不至于无断矣。是则所谓中和者。而人人之所不难勉者。于以名是堂也何骤焉。而记之也何渎焉。况大本达道位育之理。又未必非人人之所同得者。则由浅入深。自迩达远。又何不可之有。李氏以儒素传。而今其后生。颇亦有志学者。其当以是说为可思也夫。
夫周子之所称和者。正指其刚善柔善之得其中者。而独怪夫世人之所谓和则不过以其柔善者而已。有是柔善而不知用中以节之。则其慈也或失为邪佞。其顺也或失为懦弱。其巽也或失为无断。此夫子之所谓流所谓同而周子之所谓恶也。夫以和之为善而不中则易入于恶。此其所谓不可行者欤。然则如之何而能易其恶而至其中也。不过以其刚善者。济其柔善者而已矣。以义直而济其慈者则不至于邪佞矣。以严毅而济其顺者则不至于懦弱矣。以干固与断而济其巽者则不至于无断矣。是则所谓中和者。而人人之所不难勉者。于以名是堂也何骤焉。而记之也何渎焉。况大本达道位育之理。又未必非人人之所同得者。则由浅入深。自迩达远。又何不可之有。李氏以儒素传。而今其后生。颇亦有志学者。其当以是说为可思也夫。永则斋记
昔余从江右诸士友谒许后山先生于德村之庐。而诸公导余先之处士和宣氏。余窃怪其定舍馆而后求见长者。则诸公曰非然也。见处士乃所以见先生也。余然而从之。入定见处士。礼颜伟干。善气洋溢言谈。举止酬酢之际。油油然使人心醉。既归数十年。不能再有迹焉。然遇有从西来者。必问处士休咎以为忧喜。去岁秋有一生名容烨者。访余峡寓。自述其世。知其为处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7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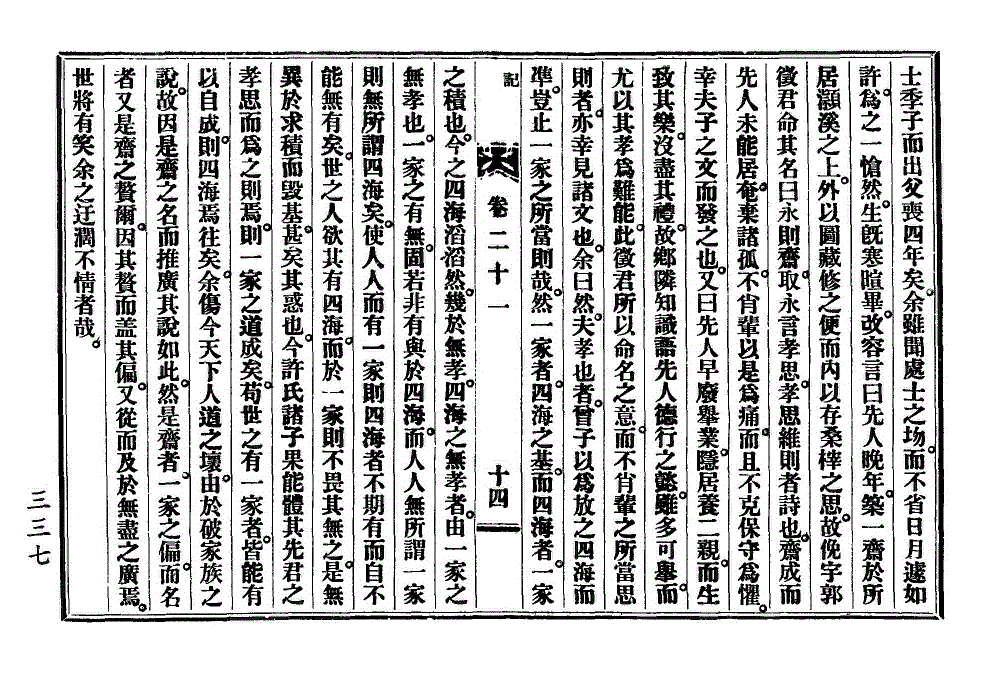 士季子而出父丧四年矣。余虽闻处士之殁。而不省日月遽如许。为之一怆然。生既寒暄毕。改容言曰先人晚年。筑一斋于所居𤃡溪之上。外以图藏修之便而内以存桑梓之思。故俛宇郭徵君命其名曰永则斋。取永言孝思。孝思维则者诗也。斋成而先人未能居。奄弃诸孤。不肖辈以是为痛。而且不克保守为惧。幸夫子之文而发之也。又曰先人早废举业。隐居养二亲。而生致其乐。没尽其礼。故乡邻知识语先人德行之懿。虽多可举。而尤以其孝为难能。此徵君所以命名之意。而不肖辈之所当思则者。亦幸见诸文也。余曰然。夫孝也者。曾子以为放之四海而准。岂止一家之所当则哉。然一家者。四海之基。而四海者。一家之积也。今之四海滔滔然。几于无孝。四海之无孝者。由一家之无孝也。一家之有无。固若非有与于四海。而人人无所谓一家则无所谓四海矣。使人人而有一家则四海者不期有而自不能无有矣。世之人欲其有四海。而于一家则不畏其无之。是无异于求积而毁基。甚矣其惑也。今许氏诸子果能体其先君之孝思而为之则焉。则一家之道成矣。苟世之有一家者。皆能有以自成。则四海焉往矣。余伤今天下人道之坏。由于破家族之说。故因是斋之名而推广其说如此。然是斋者。一家之偏。而名者又是斋之赘尔。因其赘而盖其偏。又从而及于无尽之广焉。世将有笑余之迂阔不情者哉。
士季子而出父丧四年矣。余虽闻处士之殁。而不省日月遽如许。为之一怆然。生既寒暄毕。改容言曰先人晚年。筑一斋于所居𤃡溪之上。外以图藏修之便而内以存桑梓之思。故俛宇郭徵君命其名曰永则斋。取永言孝思。孝思维则者诗也。斋成而先人未能居。奄弃诸孤。不肖辈以是为痛。而且不克保守为惧。幸夫子之文而发之也。又曰先人早废举业。隐居养二亲。而生致其乐。没尽其礼。故乡邻知识语先人德行之懿。虽多可举。而尤以其孝为难能。此徵君所以命名之意。而不肖辈之所当思则者。亦幸见诸文也。余曰然。夫孝也者。曾子以为放之四海而准。岂止一家之所当则哉。然一家者。四海之基。而四海者。一家之积也。今之四海滔滔然。几于无孝。四海之无孝者。由一家之无孝也。一家之有无。固若非有与于四海。而人人无所谓一家则无所谓四海矣。使人人而有一家则四海者不期有而自不能无有矣。世之人欲其有四海。而于一家则不畏其无之。是无异于求积而毁基。甚矣其惑也。今许氏诸子果能体其先君之孝思而为之则焉。则一家之道成矣。苟世之有一家者。皆能有以自成。则四海焉往矣。余伤今天下人道之坏。由于破家族之说。故因是斋之名而推广其说如此。然是斋者。一家之偏。而名者又是斋之赘尔。因其赘而盖其偏。又从而及于无尽之广焉。世将有笑余之迂阔不情者哉。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8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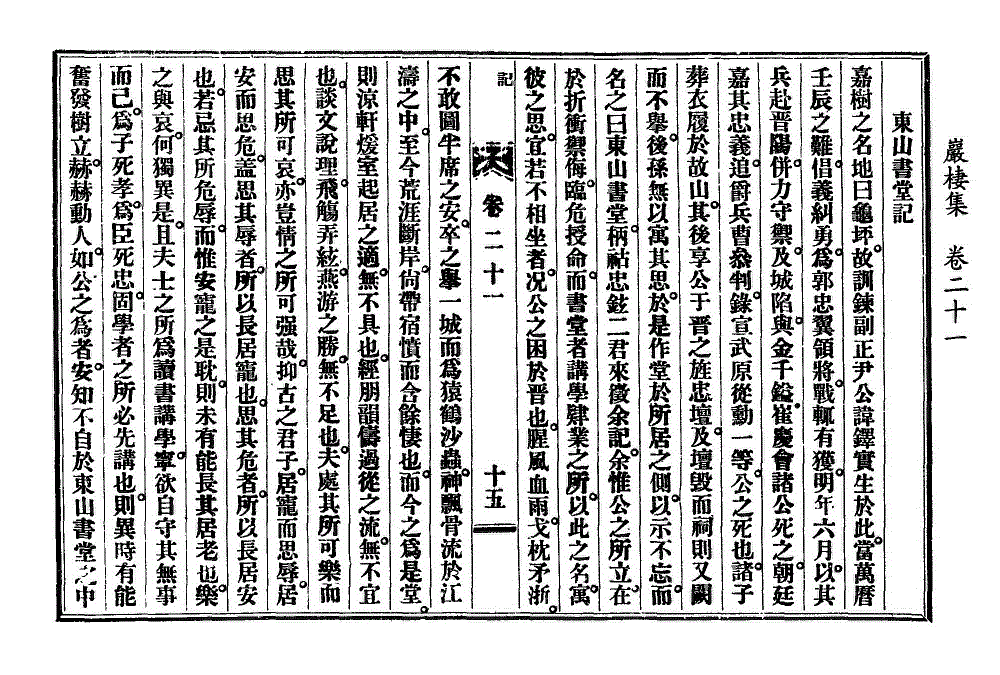 东山书堂记
东山书堂记嘉树之名地曰龟坪。故训鍊副正尹公讳铎实生于此。当万历壬辰之难。倡义纠勇。为郭忠翼领将。战辄有获。明年六月。以其兵赴晋阳。并力守御。及城陷。与金千镒,崔庆会诸公死之。朝廷嘉其忠义。追爵兵曹参判。录宣武原从勋一等。公之死也。诸子葬衣履于故山。其后享公于晋之旌忠坛。及坛毁而祠则又阙而不举。后孙无以寓其思。于是作堂于所居之侧。以示不忘。而名之曰东山书堂。柄祜忠铉二君来徵余记。余惟公之所立。在于折冲御侮。临危授命。而书堂者讲学肄业之所。以此之名。寓彼之思。宜若不相坐者。况公之困于晋也。腥风血雨。戈枕矛浙。不敢图半席之安。卒之举一城而为猿鹤沙虫。神飘骨流于江涛之中。至今荒涯断岸。尚带宿愤而含馀悽也。而今之为是堂。则凉轩煖室起居之适。无不具也。经朋韵俦过从之流。无不宜也。谈文说理。飞觞弄弦。燕游之胜。无不足也。夫处其所可乐而思其所可哀。亦岂情之所可强哉。抑古之君子。居宠而思辱。居安而思危。盖思其辱者。所以长居宠也。思其危者。所以长居安也。若忌其所危辱。而惟安宠之是耽。则未有能长其居老也。乐之与哀。何独异是。且夫士之所为读书讲学。宁欲自守其无事而已。为子死孝。为臣死忠。固学者之所必先讲也。则异时有能奋发树立。赫赫动人。如公之为者。安知不自于东山书堂之中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8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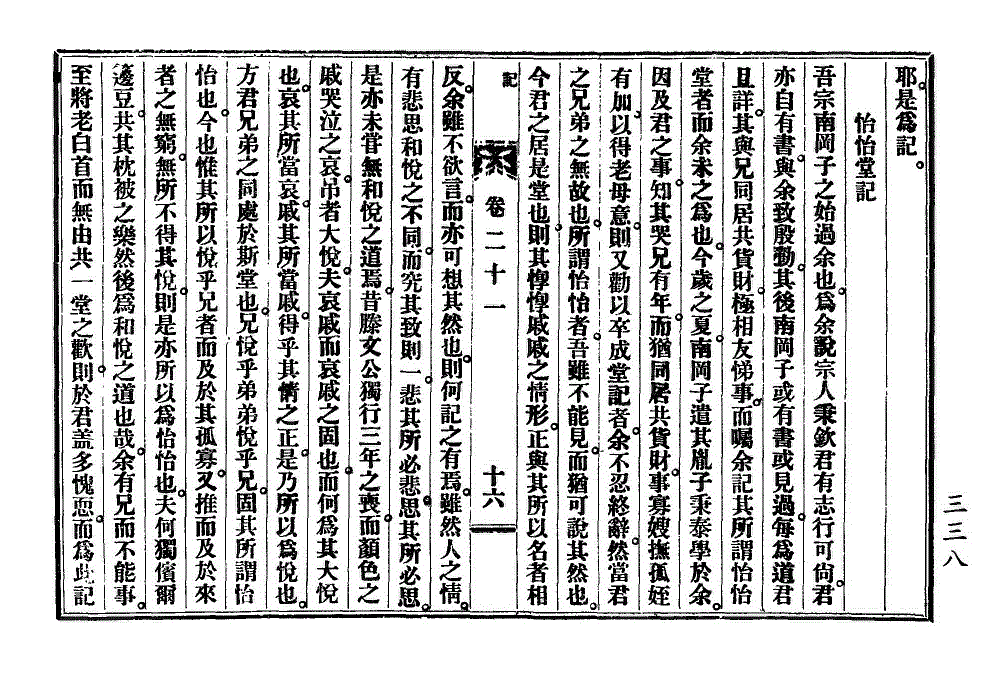 耶。是为记。
耶。是为记。怡怡堂记
吾宗南冈子之始过余也。为余说宗人秉钦君有志行可尚。君亦自有书。与余致殷勤。其后南冈子或有书或见过。每为道君且详。其与兄同居共货财。极相友悌事。而嘱余记其所谓怡怡堂者而余未之为也。今岁之夏。南冈子遣其胤子秉泰学于余。因及君之事。知其哭兄有年。而犹同居共货财。事寡嫂抚孤侄有加。以得老母意。则又劝以卒成堂记者。余不忍终辞。然当君之兄弟之无故也。所谓怡怡者。吾虽不能见。而犹可说其然也。今君之居是堂也。则其茕茕戚戚之情形。正与其所以名者相反。余虽不欲言。而亦可想其然也。则何记之有焉。虽然人之情。有悲思和悦之不同。而究其致则一。悲其所必悲。思其所必思。是亦未尝无和悦之道焉。昔膝文公独行三年之丧。而颜色之戚哭泣之哀。吊者大悦。夫哀戚而哀戚之固也。而何为其大悦也。哀其所当哀。戚其所当戚。得乎其情之正。是乃所以为悦也。方君兄弟之同处于斯堂也。兄悦乎弟弟悦乎兄。固其所谓怡怡也。今也惟其所以悦乎兄者而及于其孤寡。又推而及于来者之无穷。无所不得其悦。则是亦所以为怡怡也。夫何独傧尔笾豆。共其枕被之乐然后为和悦之道也哉。余有兄而不能事。至将老白首而无由共一堂之欢。则于君盖多愧恧。而为此记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9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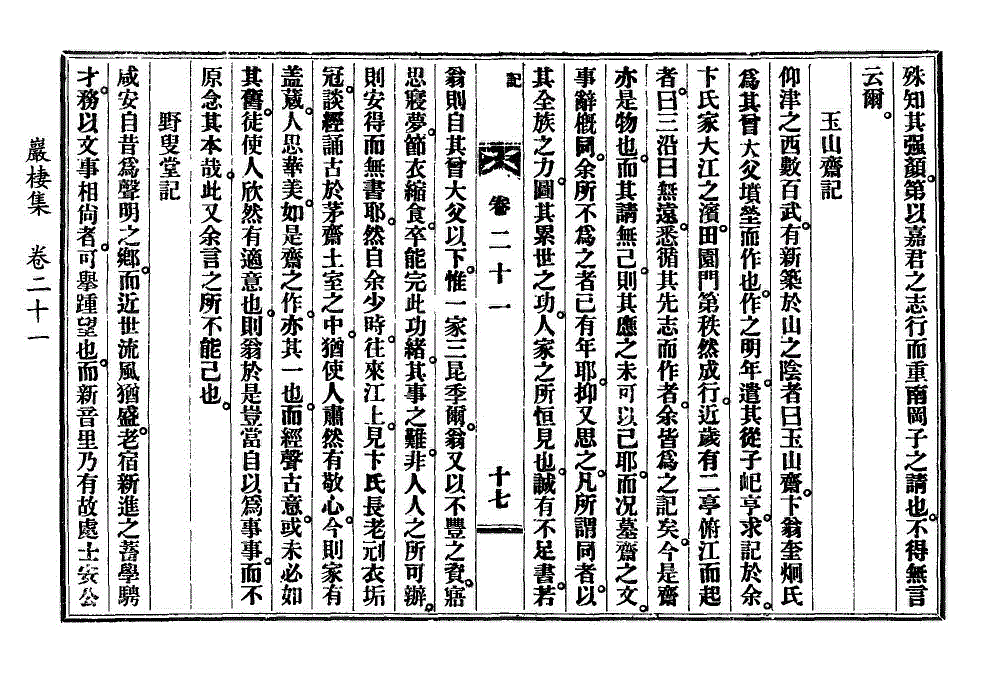 殊知其强颜。第以嘉君之志行而重南冈子之请也。不得无言云尔。
殊知其强颜。第以嘉君之志行而重南冈子之请也。不得无言云尔。玉山斋记
仰津之西数百武。有新筑于山之阴者曰玉山斋。卞翁奎炯氏为其曾大父坟茔而作也。作之明年。遣其从子屺亨。求记于余。卞氏家大江之滨。田园门第秩然成行。近岁有二亭俯江而起者。曰三沿曰无远。悉循其先志而作者。余皆为之记矣。今是斋亦是物也。而其请无已。则其应之未可以已耶。而况墓斋之文。事辞概同。余所不为之者已有年耶。抑又思之。凡所谓同者。以其全族之力。图其累世之功。人家之所恒见也。诚有不足书。若翁则自其曾大父以下。惟一家三昆季尔。翁又以不丰之资。寤思寝梦。节衣缩食。卒能完此功绪。其事之难。非人人之所可办。则安得而无书耶。然自余少时。往来江上。见卞氏长老刓衣垢冠。谈经诵古于茅斋土室之中。犹使人肃然有敬心。今则家有盖藏。人思华美。如是斋之作。亦其一也。而经声古意。或未必如其旧。徒使人欣然有适意也。则翁于是岂当自以为事事。而不原念其本哉。此又余言之所不能已也。
野叟堂记
咸安自昔为声明之乡。而近世流风犹盛。老宿新进之蓄学骋才。务以文事相尚者。可举踵望也。而新音里乃有故处士安公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39L 页
 自以野叟名其堂者。处士为人。孝敬以事亲。勤俭以成家。宽恕以待物。为乡人所称愿者。骎骎然进于文矣。夫野之于文远已。以其地则鄙。以其质则略。以其名则谚。而处士之独乐就于此何欤。以处士为自处以无文也。则世之无而为有。惟恐人之见其无者多矣。以处士为自表其平生之实也。则凡孝敬勤俭宽恕。为处士之实而可名者不少矣。而独是之为。呜乎。此处士所以托意之远。而非人之所能几者欤。天下之弊。恒生于文。而惟野可以反之。今夫挟简牍摄褒博。尧行而舜趍。自以为文也。而率桅蜡焉已矣。珠山银海。飞艇奔轮。四时无昼夜之辨。千里通瞬息之期。自以为文也。而举膏血焉已矣。虚伪之相罔。争夺之相残。推原其故。未有不自于文者。故在今而求救其弊。惟有反诸野而已。意者处士殆有见于此欤。则其意不亦远矣乎。处士既没而嗣孙敩中直其所居之傍。别营一馆。以处士之命命之。甫成而敩中又不幸夭逝。处士从子鼎台来请记。余异其名之质而推处士之意为之说如此。令来者有所思焉。
自以野叟名其堂者。处士为人。孝敬以事亲。勤俭以成家。宽恕以待物。为乡人所称愿者。骎骎然进于文矣。夫野之于文远已。以其地则鄙。以其质则略。以其名则谚。而处士之独乐就于此何欤。以处士为自处以无文也。则世之无而为有。惟恐人之见其无者多矣。以处士为自表其平生之实也。则凡孝敬勤俭宽恕。为处士之实而可名者不少矣。而独是之为。呜乎。此处士所以托意之远。而非人之所能几者欤。天下之弊。恒生于文。而惟野可以反之。今夫挟简牍摄褒博。尧行而舜趍。自以为文也。而率桅蜡焉已矣。珠山银海。飞艇奔轮。四时无昼夜之辨。千里通瞬息之期。自以为文也。而举膏血焉已矣。虚伪之相罔。争夺之相残。推原其故。未有不自于文者。故在今而求救其弊。惟有反诸野而已。意者处士殆有见于此欤。则其意不亦远矣乎。处士既没而嗣孙敩中直其所居之傍。别营一馆。以处士之命命之。甫成而敩中又不幸夭逝。处士从子鼎台来请记。余异其名之质而推处士之意为之说如此。令来者有所思焉。喜惧堂记
裴君孝必新作堂于佳渊之所居。于是二亲皆耋矣。乃取论语父母之年不可不知。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之义。题之曰喜惧堂。来请余以记。君吾门之自出也。情有所不可辞。则为之说曰。人之情有七。而其发也有可并者有不可并者。可并者情之相近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4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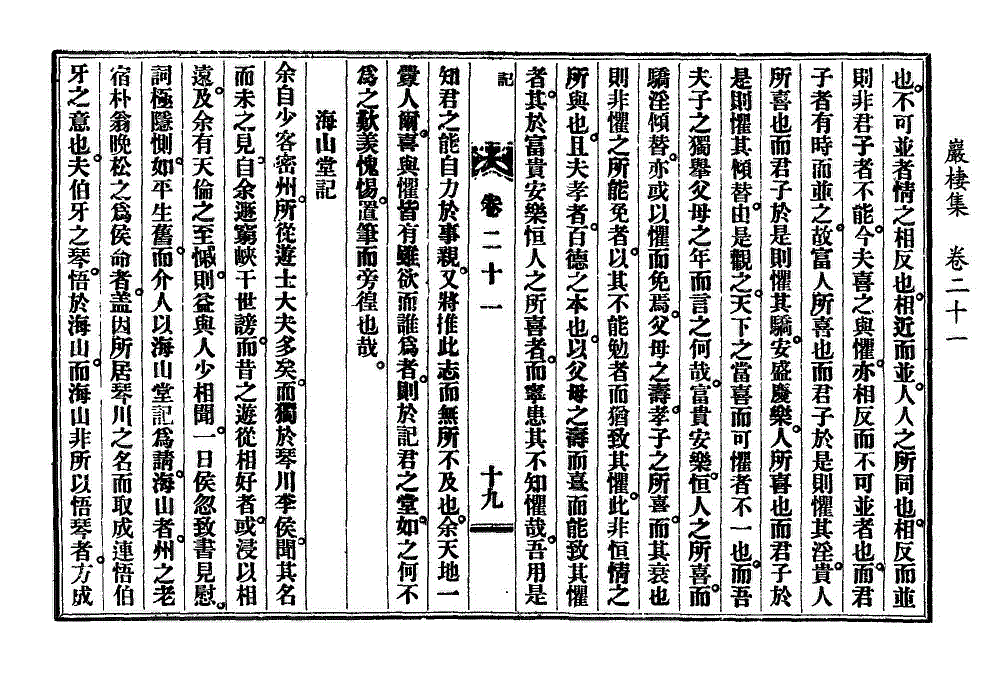 也。不可并者情之相反也。相近而并。人人之所同也。相反而并则非君子者不能。今夫喜之与惧。亦相反而不可并者也。而君子者有时而并之。故富人所喜也而君子于是则惧其淫。贵人所喜也而君子于是则惧其骄。安盛庆乐。人所喜也而君子于是则惧其倾替。由是观之。天下之当喜而可惧者不一也。而吾夫子之独举父母之年而言之何哉。富贵安乐。恒人之所喜。而骄淫倾替。亦或以惧而免焉。父母之寿。孝子之所喜。而其衰也则非惧之所能免者。以其不能勉者而犹致其惧。此非恒情之所与也。且夫孝者。百德之本也。以父母之寿而喜而能致其惧者。其于富贵安乐恒人之所喜者。而宁患其不知惧哉。吾用是知君之能自力于事亲。又将推此志而无所不及也。余天地一衅人尔。喜与惧皆有虽欲而谁为者。则于记君之堂。如之何不为之叹羡愧惕。置笔而旁徨也哉。
也。不可并者情之相反也。相近而并。人人之所同也。相反而并则非君子者不能。今夫喜之与惧。亦相反而不可并者也。而君子者有时而并之。故富人所喜也而君子于是则惧其淫。贵人所喜也而君子于是则惧其骄。安盛庆乐。人所喜也而君子于是则惧其倾替。由是观之。天下之当喜而可惧者不一也。而吾夫子之独举父母之年而言之何哉。富贵安乐。恒人之所喜。而骄淫倾替。亦或以惧而免焉。父母之寿。孝子之所喜。而其衰也则非惧之所能免者。以其不能勉者而犹致其惧。此非恒情之所与也。且夫孝者。百德之本也。以父母之寿而喜而能致其惧者。其于富贵安乐恒人之所喜者。而宁患其不知惧哉。吾用是知君之能自力于事亲。又将推此志而无所不及也。余天地一衅人尔。喜与惧皆有虽欲而谁为者。则于记君之堂。如之何不为之叹羡愧惕。置笔而旁徨也哉。海山堂记
余自少客密州。所从游士大夫多矣。而独于琴川李侯。闻其名而未之见。自余遁穷峡干世谤。而昔之游从相好者。或浸以相远。及余有天伦之至戚。则益与人少相闻。一日侯忽致书见慰。词极隐恻。如平生旧。而介人以海山堂记为请。海山者。州之老宿朴翁晚松之为侯命者。盖因所居琴川之名而取成连悟伯牙之意也。夫伯牙之琴。悟于海山。而海山非所以悟琴者。方成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4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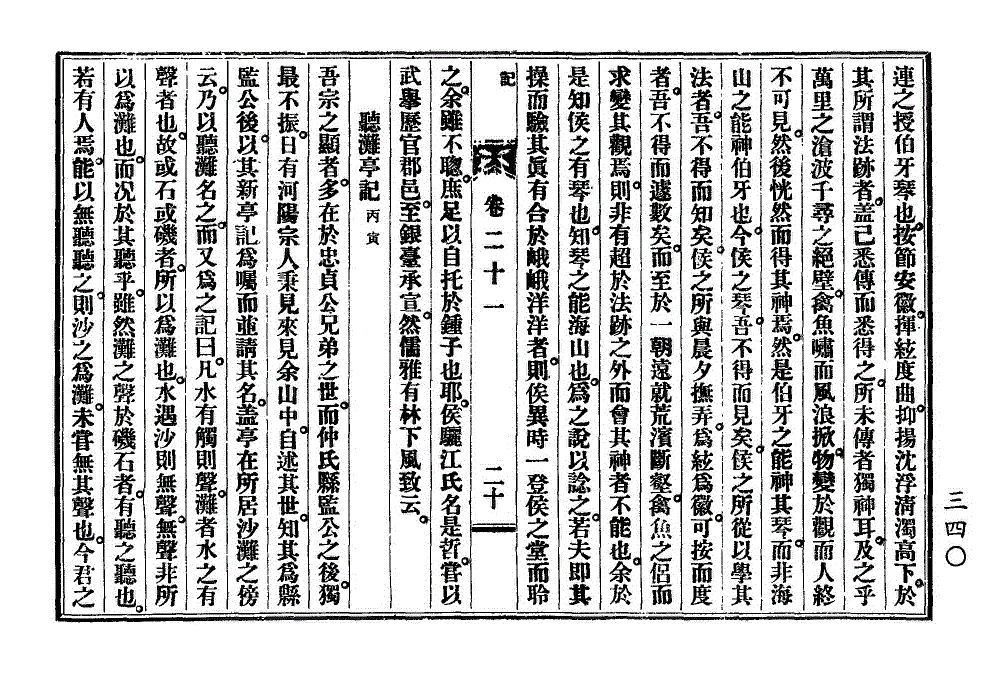 连之授伯牙琴也。按节安徽。挥弦度曲。抑扬沈浮清浊高下。于其所谓法迹者。盖已悉传而悉得之。所未传者独神耳。及之乎万里之沧波千寻之绝壁。禽鱼啸而风浪掀。物变于观而人终不可见。然后恍然而得其神焉。然是伯牙之能神其琴。而非海山之能神伯牙也。今侯之琴。吾不得而见矣。侯之所从以学其法者。吾不得而知矣。侯之所与晨夕抚弄。为弦为徽。可按而度者。吾不得而遽数矣。而至于一朝远就荒滨断壑。禽鱼之侣而求变其观焉。则非有超于法迹之外而会其神者不能也。余于是知侯之有琴也。知琴之能海山也。为之说以谂之。若夫即其操而验其真有合于峨峨洋洋者。则俟异时一登侯之堂而聆之。余虽不聪。庶足以自托于钟子也耶。侯骊江氏名是哲。尝以武举历官郡邑。至银台承宣。然儒雅有林下风致云。
连之授伯牙琴也。按节安徽。挥弦度曲。抑扬沈浮清浊高下。于其所谓法迹者。盖已悉传而悉得之。所未传者独神耳。及之乎万里之沧波千寻之绝壁。禽鱼啸而风浪掀。物变于观而人终不可见。然后恍然而得其神焉。然是伯牙之能神其琴。而非海山之能神伯牙也。今侯之琴。吾不得而见矣。侯之所从以学其法者。吾不得而知矣。侯之所与晨夕抚弄。为弦为徽。可按而度者。吾不得而遽数矣。而至于一朝远就荒滨断壑。禽鱼之侣而求变其观焉。则非有超于法迹之外而会其神者不能也。余于是知侯之有琴也。知琴之能海山也。为之说以谂之。若夫即其操而验其真有合于峨峨洋洋者。则俟异时一登侯之堂而聆之。余虽不聪。庶足以自托于钟子也耶。侯骊江氏名是哲。尝以武举历官郡邑。至银台承宣。然儒雅有林下风致云。听滩亭记(丙寅)
吾宗之显者。多在于忠贞公兄弟之世。而仲氏县监公之后。独最不振。日有河阳宗人秉见来见余山中。自述其世。知其为县监公后。以其新亭记为嘱而并请其名。盖亭在所居沙滩之傍云。乃以听滩名之。而又为之记曰。凡水有触则声。滩者水之有声者也。故或石或矶者。所以为滩也。水遇沙则无声。无声非所以为滩也。而况于其听乎。虽然滩之声于矶石者。有听之听也。若有人焉。能以无听听之。则沙之为滩。未尝无其声也。今君之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4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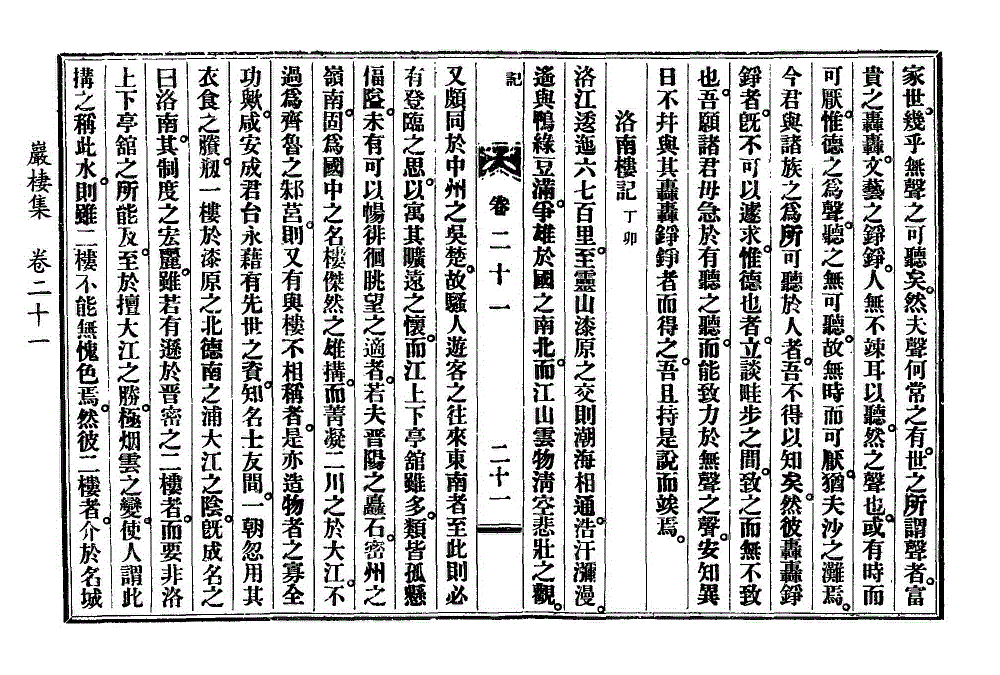 家世。几乎无声之可听矣。然夫声何常之有。世之所谓声者。富贵之轰轰。文艺之铮铮。人无不竦耳以听。然之声也。或有时而可厌。惟德之为声。听之无可听。故无时而可厌。犹夫沙之滩焉。今君与诸族之为所可听于人者。吾不得以知矣。然彼轰轰铮铮者。既不可以遽求。惟德也者。立谈畦步之间。致之而无不致也。吾愿诸君毋急于有听之听。而能致力于无声之声。安知异日不并与其轰轰铮铮者而得之。吾且持是说而俟焉。
家世。几乎无声之可听矣。然夫声何常之有。世之所谓声者。富贵之轰轰。文艺之铮铮。人无不竦耳以听。然之声也。或有时而可厌。惟德之为声。听之无可听。故无时而可厌。犹夫沙之滩焉。今君与诸族之为所可听于人者。吾不得以知矣。然彼轰轰铮铮者。既不可以遽求。惟德也者。立谈畦步之间。致之而无不致也。吾愿诸君毋急于有听之听。而能致力于无声之声。安知异日不并与其轰轰铮铮者而得之。吾且持是说而俟焉。洛南楼记(丁卯)
洛江逶迤六七百里。至灵山漆原之交则潮海相通。浩汗㳽漫。遥与鸭绿,豆满。争雄于国之南北。而江山云物清空悲壮之观。又颇同于中州之吴楚。故骚人游客之往来东南者至此则必有登临之思。以寓其旷远之怀。而江上下亭馆虽多。类皆孤悬偪隘。未有可以畅徘徊眺望之适者。若夫晋阳之矗石。密州之岭南。固为国中之名楼杰然之雄构。而菁凝二川之于大江。不过为齐鲁之邾莒。则又有与楼不相称者。是亦造物者之寡全功欤。咸安成君台永藉有先世之资。知名士友间。一朝忽用其衣食之剩。刱一楼于漆原之北德南之浦大江之阴。既成名之曰洛南。其制度之宏丽。虽若有逊于晋密之二楼者。而要非洛上下亭馆之所能及。至于擅大江之胜。极烟云之变。使人谓此搆之称此水。则虽二楼不能无愧色焉。然彼二楼者。介于名城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4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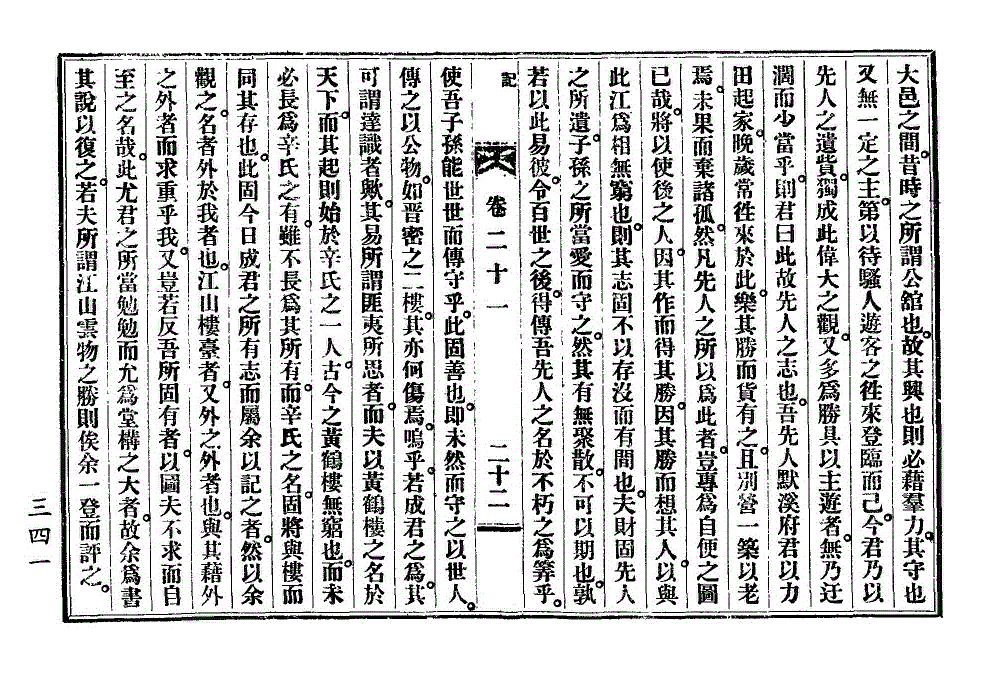 大邑之间。昔时之所谓公馆也。故其兴也则必藉群力。其守也又无一定之主。第以待骚人游客之往来登临而已。今君乃以先人之遗赀。独成此伟大之观。又多为胜具以主游者。无乃迂阔而少当乎。则君曰此故先人之志也。吾先人默溪府君以力田起家。晚岁常往来于此。乐其胜而货有之。且别营一筑以老焉。未果而弃诸孤。然凡先人之所以为此者。岂专为自便之图已哉。将以使后之人。因其作而得其胜。因其胜而想其人。以与此江为相无穷也。则其志固不以存没而有间也。夫财固先人之所遗。子孙之所当爱而守之。然其有无聚散。不可以期也。孰若以此易彼。令百世之后。得传吾先人之名于不朽之为算乎。使吾子孙能世世而传守乎。此固善也。即未然而守之以世人。传之以公物。如晋密之二楼。其亦何伤焉。呜乎。若成君之为。其可谓达识者欤。其易所谓匪夷所思者。而夫以黄鹤楼之名于天下。而其起则始于辛氏之一人。古今之黄鹤楼无穷也。而未必长为辛氏之有。虽不长为其所有。而辛氏之名。固将与楼而同其存也。此固今日成君之所有志而属余以记之者。然以余观之。名者外于我者也。江山楼台者。又外之外者也。与其藉外之外者而求重乎我。又岂若反吾所固有者。以图夫不求而自至之名哉。此尤君之所当勉勉而允为堂构之大者。故余为书其说以复之。若夫所谓江山云物之胜则俟余一登而评之。
大邑之间。昔时之所谓公馆也。故其兴也则必藉群力。其守也又无一定之主。第以待骚人游客之往来登临而已。今君乃以先人之遗赀。独成此伟大之观。又多为胜具以主游者。无乃迂阔而少当乎。则君曰此故先人之志也。吾先人默溪府君以力田起家。晚岁常往来于此。乐其胜而货有之。且别营一筑以老焉。未果而弃诸孤。然凡先人之所以为此者。岂专为自便之图已哉。将以使后之人。因其作而得其胜。因其胜而想其人。以与此江为相无穷也。则其志固不以存没而有间也。夫财固先人之所遗。子孙之所当爱而守之。然其有无聚散。不可以期也。孰若以此易彼。令百世之后。得传吾先人之名于不朽之为算乎。使吾子孙能世世而传守乎。此固善也。即未然而守之以世人。传之以公物。如晋密之二楼。其亦何伤焉。呜乎。若成君之为。其可谓达识者欤。其易所谓匪夷所思者。而夫以黄鹤楼之名于天下。而其起则始于辛氏之一人。古今之黄鹤楼无穷也。而未必长为辛氏之有。虽不长为其所有。而辛氏之名。固将与楼而同其存也。此固今日成君之所有志而属余以记之者。然以余观之。名者外于我者也。江山楼台者。又外之外者也。与其藉外之外者而求重乎我。又岂若反吾所固有者。以图夫不求而自至之名哉。此尤君之所当勉勉而允为堂构之大者。故余为书其说以复之。若夫所谓江山云物之胜则俟余一登而评之。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4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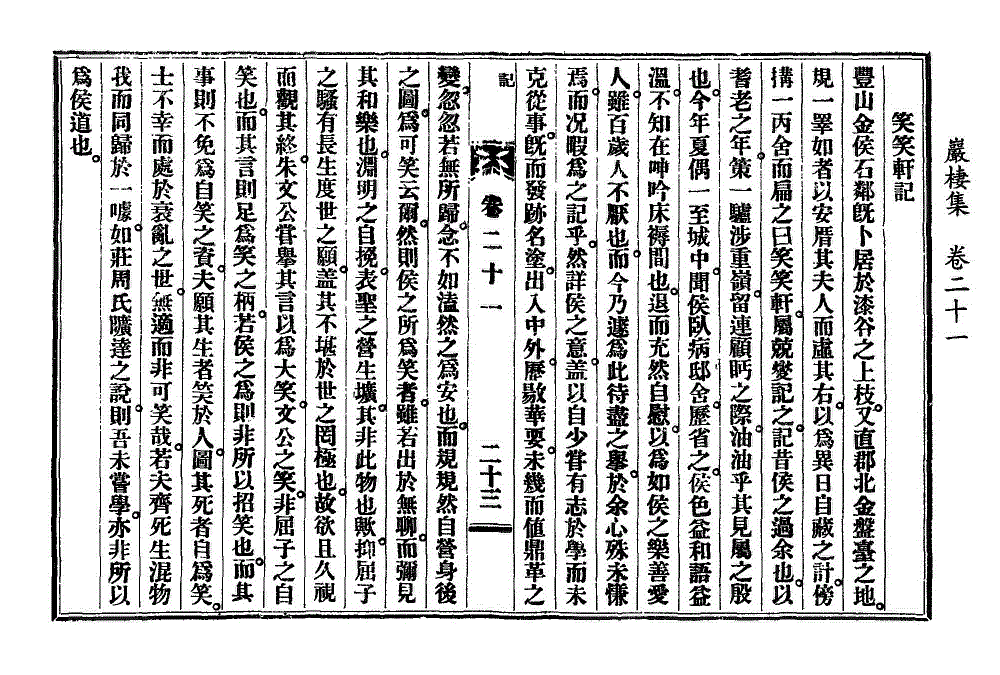 笑笑轩记
笑笑轩记丰山金侯石邻既卜居于漆谷之上枝。又直郡北金盘台之地。规一睪如者以安厝其夫人而虚其右。以为异日自藏之计。傍搆一丙舍而扁之曰笑笑轩。属兢燮记之。记昔侯之过余也。以耆老之年。策一驴涉重岭。留连顾眄之际。油油乎其见属之殷也。今年夏偶一至城中。闻侯卧病邸舍。历省之。侯色益和语益温。不知在呻吟床褥间也。退而充然自慰。以为如侯之乐善爱人。虽百岁人不厌也。而今乃遽为此待尽之举。于余心殊未慊焉。而况暇为之记乎。然详侯之意。盖以自少尝有志于学而未克从事。既而发迹名涂。出入中外。历扬华要。未几而值鼎革之变。忽忽若无所归。念不如溘然之为安也。而规规然自营身后之图。为可笑云尔。然则侯之所为笑者。虽若出于无聊。而弥见其和乐也。渊明之自挽。表圣之营生圹。其非此物也欤。抑屈子之骚有长生度世之愿。盖其不堪于世之罔极也。故欲且久视而观其终。朱文公尝举其言以为大笑。文公之笑。非屈子之自笑也。而其言则足为笑之柄。若侯之为则非所以招笑也。而其事则不免为自笑之资。夫愿其生者笑于人。图其死者自为笑。士不幸而处于衰乱之世。无适而非可笑哉。若夫齐死生混物我而同归于一噱。如庄周氏旷达之说。则吾未尝学。亦非所以为侯道也。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4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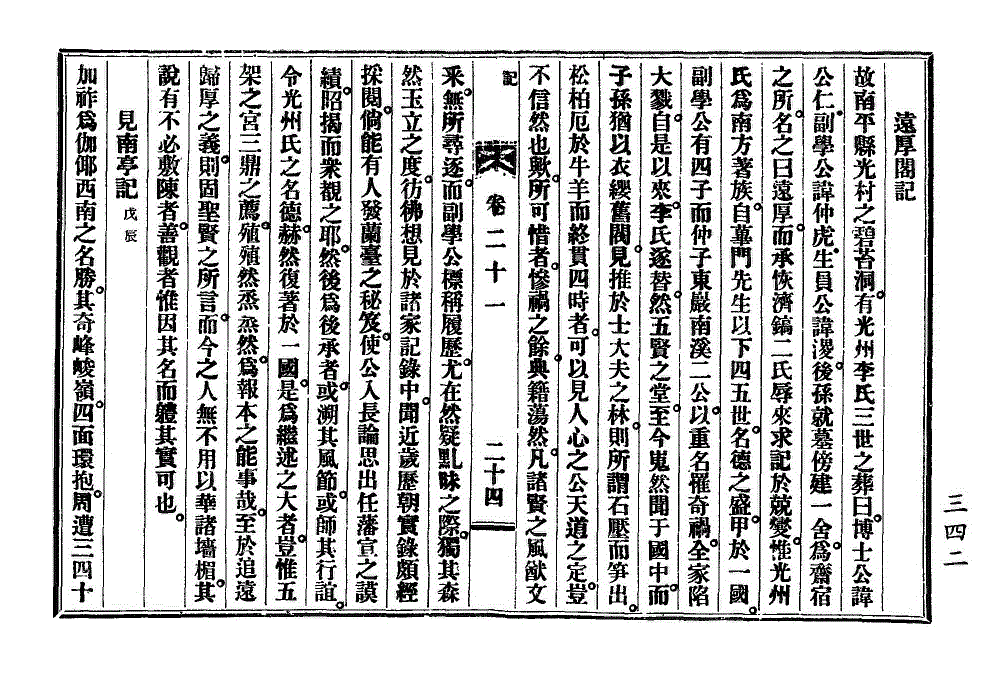 远厚阁记
远厚阁记故南平县光村之碧苔洞。有光州李氏三世之葬曰。博士公讳公仁,副学公讳仲虎,生员公讳溭。后孙就墓傍建一舍。为斋宿之所。名之曰远厚。而承恢,济镐二氏辱来求记于兢燮。惟光州氏为南方著族。自荜门先生以下四五世。名德之盛。甲于一国。副学公有四子而仲子东岩,南溪二公。以重名罹奇祸。全家陷大戮。自是以来。李氏遂替。然五贤之堂。至今嵬然闻于国中。而子孙犹以衣缨旧阀。见推于士大夫之林。则所谓石压而笋出。松柏厄于牛羊而终贯四时者。可以见人心之公天道之定。岂不信然也欤。所可惜者。惨祸之馀。典籍荡然。凡诸贤之风猷文采。无所寻逐。而副学公标称履历。尤在然疑䵝昧之际。独其森然玉立之度。彷佛想见于诸家记录中。闻近岁历朝实录颇经采阅。倘能有人发兰台之秘笈。使公入长论思出任藩宣之谟绩。昭揭而众睹之耶。然后为后承者。或溯其风节。或师其行谊。令光州氏之名德。赫然复著于一国。是为继述之大者。岂惟五架之宫三鼎之荐。殖殖然烝烝然。为报本之能事哉。至于追远归厚之义。则固圣贤之所言。而今之人无不用以华诸墙楣。其说有不必敷陈者。善观者惟因其名而体其实可也。
见南亭记(戊辰)
加祚为伽倻西南之名胜。其奇峰峻岭。四面环抱。周遭三四十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4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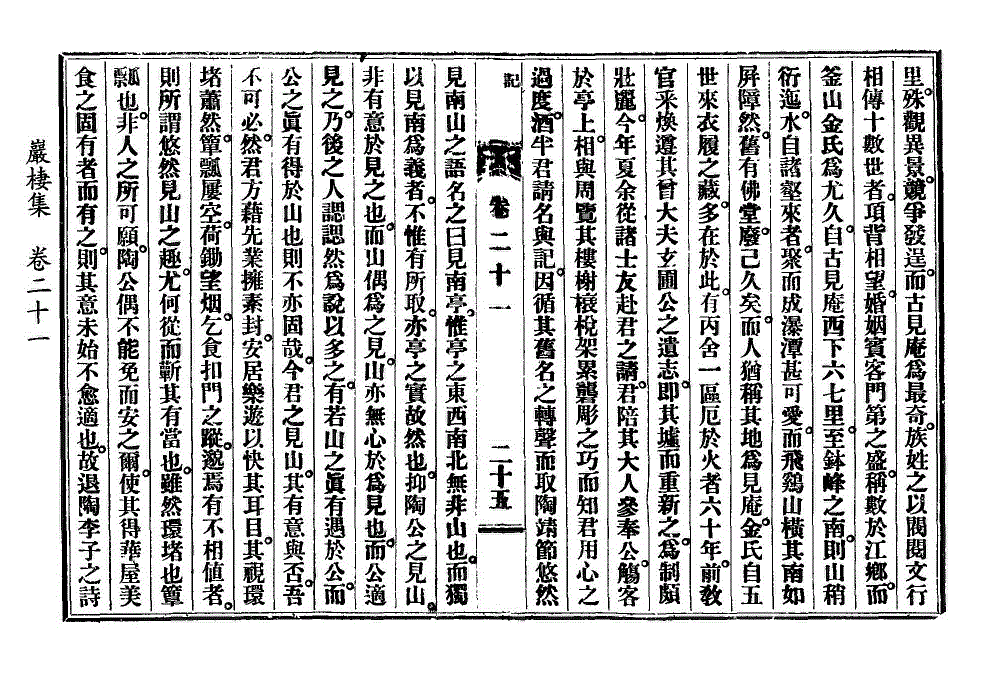 里。殊观异景。竞争发逞。而古见庵为最奇。族姓之以阀阅文行相传十数世者。项背相望。婚姻宾客门第之盛。称数于江乡。而釜山金氏为尤久。自古见庵西下六七里。至钵峰之南。则山稍衍迤。水自诸壑来者。聚而成瀑潭甚可爱。而飞鸡山横其南如屏障然。旧有佛堂。废已久矣。而人犹称其地为见庵。金氏自五世来衣履之藏。多在于此。有丙舍一区厄于火者六十年。前教官采焕遵其曾大夫玄圃公之遗志。即其墟而重新之。为制颇壮丽。今年夏余从诸士友赴君之请。君陪其大人参奉公。觞客于亭上。相与周览其楼榭榱棁架累砻彫之巧而知君用心之过度。酒半君请名与记。因循其旧名之转声而取陶靖节悠然见南山之语名之曰见南亭。惟亭之东西南北无非山也。而独以见南为义者。不惟有所取。亦亭之实故然也。抑陶公之见山。非有意于见之也。而山偶为之见。山亦无心于为见也。而公适见之。乃后之人諰諰然为说以多之。有若山之真有遇于公。而公之真有得于山也则不亦固哉。今君之见山。其有意与否。吾不可必。然君方藉先业拥素封。安居乐游以快其耳目。其视环堵萧然。箪瓢屡空。荷锄望烟。乞食扣门之踪。邈焉有不相值者。则所谓悠然见山之趣。尤何从而蕲其有当也。虽然环堵也簟瓢也。非人之所可愿。陶公偶不能免而安之尔。使其得华屋美食之固有者而有之。则其意未始不愈适也。故退陶李子之诗
里。殊观异景。竞争发逞。而古见庵为最奇。族姓之以阀阅文行相传十数世者。项背相望。婚姻宾客门第之盛。称数于江乡。而釜山金氏为尤久。自古见庵西下六七里。至钵峰之南。则山稍衍迤。水自诸壑来者。聚而成瀑潭甚可爱。而飞鸡山横其南如屏障然。旧有佛堂。废已久矣。而人犹称其地为见庵。金氏自五世来衣履之藏。多在于此。有丙舍一区厄于火者六十年。前教官采焕遵其曾大夫玄圃公之遗志。即其墟而重新之。为制颇壮丽。今年夏余从诸士友赴君之请。君陪其大人参奉公。觞客于亭上。相与周览其楼榭榱棁架累砻彫之巧而知君用心之过度。酒半君请名与记。因循其旧名之转声而取陶靖节悠然见南山之语名之曰见南亭。惟亭之东西南北无非山也。而独以见南为义者。不惟有所取。亦亭之实故然也。抑陶公之见山。非有意于见之也。而山偶为之见。山亦无心于为见也。而公适见之。乃后之人諰諰然为说以多之。有若山之真有遇于公。而公之真有得于山也则不亦固哉。今君之见山。其有意与否。吾不可必。然君方藉先业拥素封。安居乐游以快其耳目。其视环堵萧然。箪瓢屡空。荷锄望烟。乞食扣门之踪。邈焉有不相值者。则所谓悠然见山之趣。尤何从而蕲其有当也。虽然环堵也簟瓢也。非人之所可愿。陶公偶不能免而安之尔。使其得华屋美食之固有者而有之。则其意未始不愈适也。故退陶李子之诗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4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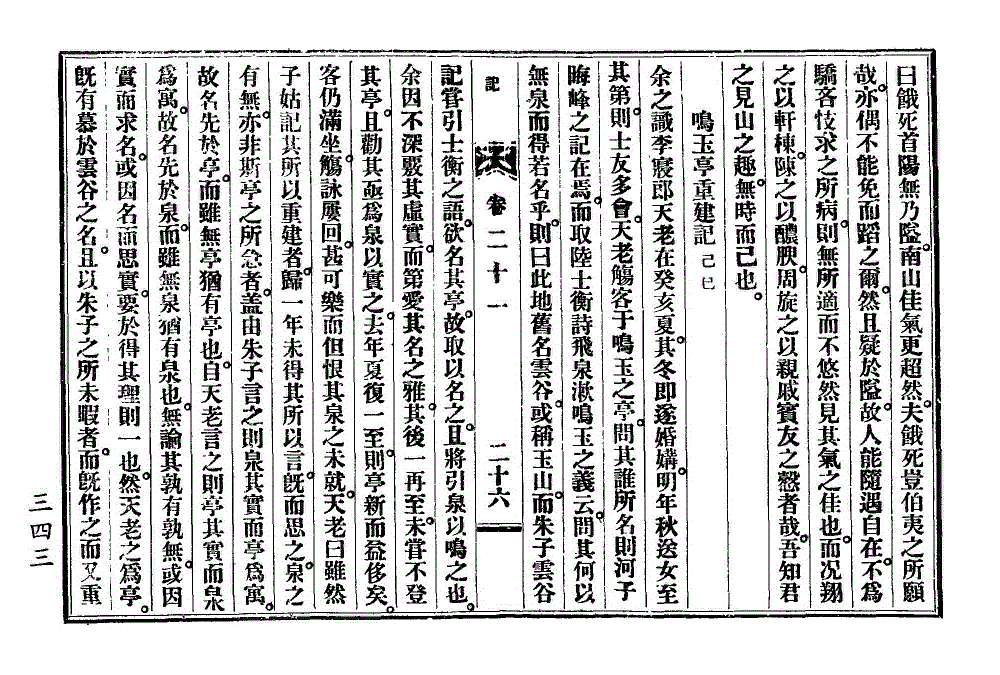 曰饿死首阳无乃隘。南山佳气更超然。夫饿死岂伯夷之所愿哉。亦偶不能免而蹈之尔。然且疑于隘。故人能随遇自在。不为骄吝忮求之所病。则无所适而不悠然见其气之佳也。而况翔之以轩栋。陈之以醲腴。周旋之以亲戚宾友之悫者哉。吾知君之见山之趣。无时而已也。
曰饿死首阳无乃隘。南山佳气更超然。夫饿死岂伯夷之所愿哉。亦偶不能免而蹈之尔。然且疑于隘。故人能随遇自在。不为骄吝忮求之所病。则无所适而不悠然见其气之佳也。而况翔之以轩栋。陈之以醲腴。周旋之以亲戚宾友之悫者哉。吾知君之见山之趣。无时而已也。鸣玉亭重建记(己巳)
余之识李寝郎天老在癸亥夏。其冬即遂婚媾。明年秋送女至其第。则士友多会。天老觞客于鸣玉之亭。问其谁所名则河子晦峰之记在焉。而取陆士衡诗飞泉漱鸣玉之义云。问其何以无泉而得若名乎。则曰此地旧名云谷。或称玉山。而朱子云谷记尝引士衡之语。欲名其亭。故取以名之。且将引泉以鸣之也。余因不深覈其虚实。而第爱其名之雅。其后一再至。未尝不登其亭。且劝其亟为泉以实之。去年夏复一至。则亭新而益侈矣。客仍满坐。觞咏屡回。甚可乐而但恨其泉之未就。天老曰虽然子姑记其所以重建者。归一年未得其所以言。既而思之。泉之有无。亦非斯亭之所急者。盖由朱子言之则泉其实而亭为寓。故名先于亭。而虽无亭犹有亭也。自天老言之则亭其实而泉为寓。故名先于泉。而虽无泉犹有泉也。无论其孰有孰无。或因实而求名。或因名而思实。要于得其理则一也。然天老之为亭。既有慕于云谷之名。且以朱子之所未暇者。而既作之而又重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4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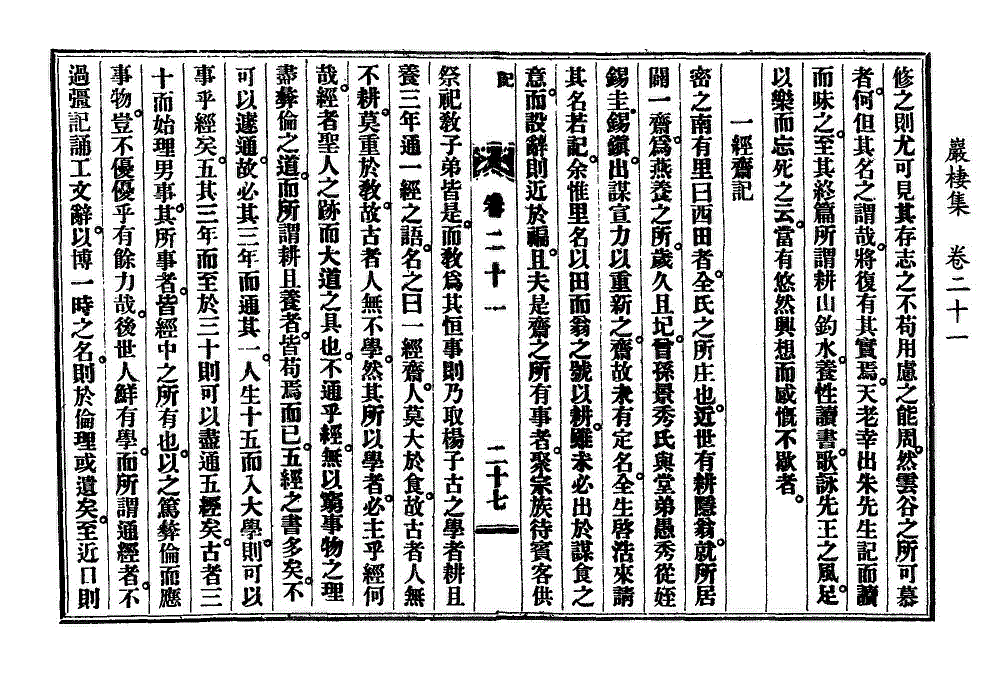 修之则尤可见其存志之不苟用虑之能周。然云谷之所可慕者。何但其名之谓哉。将复有其实焉。天老幸出朱先生记而读而味之。至其终篇所谓耕山钓水。养性读书。歌咏先王之风。足以乐而忘死之云。当有悠然兴想而感慨不歇者。
修之则尤可见其存志之不苟用虑之能周。然云谷之所可慕者。何但其名之谓哉。将复有其实焉。天老幸出朱先生记而读而味之。至其终篇所谓耕山钓水。养性读书。歌咏先王之风。足以乐而忘死之云。当有悠然兴想而感慨不歇者。一经斋记
密之南有里曰西田者。全氏之所庄也。近世有耕隐翁。就所居辟一斋。为燕养之所。岁久且圮。曾孙景秀氏与堂弟愚秀从侄锡圭,锡镇。出谋宣力以重新之。斋故未有定名。全生启浩来请其名若记。余惟里名以田而翁之号以耕。虽未必出于谋食之意。而设辞则近于褊。且夫是斋之所有事者。聚宗族待宾客供祭祀教子弟皆是。而教为其恒事则乃取杨子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经之语。名之曰一经斋。人莫大于食。故古者人无不耕。莫重于教。故古者人无不学。然其所以学者。必主乎经何哉。经者圣人之迹而大道之具也。不通乎经。无以穷事物之理尽彝伦之道。而所谓耕且养者。皆苟焉而已。五经之书多矣。不可以遽通。故必其三年而通其一。人生十五而入大学。则可以事乎经矣。五其三年而至于三十则可以尽通五经矣。古者三十而始理男事。其所事者。皆经中之所有也。以之笃彝伦而应事物。岂不优优乎有馀力哉。后世人鲜有学。而所谓通经者。不过彊记诵工文辞。以博一时之名。则于伦理或遗矣。至近日则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4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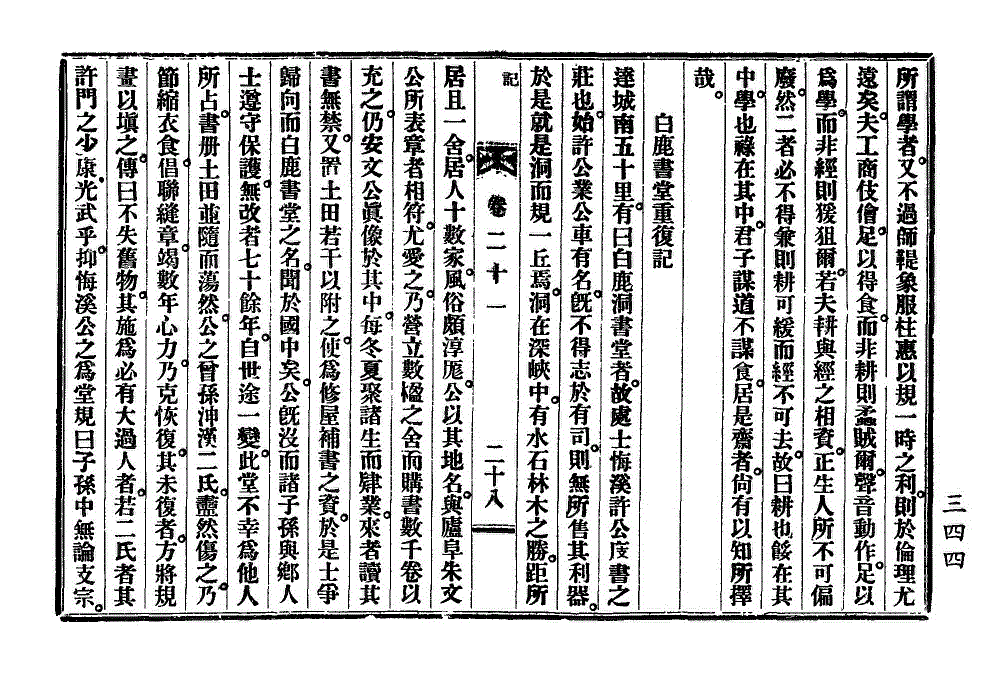 所谓学者。又不过师鞮象服柱惠以规一时之利。则于伦理尤远矣。夫工商伎侩。足以得食。而非耕则蟊贼尔。声音动作。足以为学。而非经则猿狙尔。若夫耕与经之相资。正生人所不可偏废。然二者必不得兼则耕可缓而经不可去。故曰耕也馁在其中。学也禄在其中。君子谋道不谋食。居是斋者。尚有以知所择哉。
所谓学者。又不过师鞮象服柱惠以规一时之利。则于伦理尤远矣。夫工商伎侩。足以得食。而非耕则蟊贼尔。声音动作。足以为学。而非经则猿狙尔。若夫耕与经之相资。正生人所不可偏废。然二者必不得兼则耕可缓而经不可去。故曰耕也馁在其中。学也禄在其中。君子谋道不谋食。居是斋者。尚有以知所择哉。白鹿书堂重复记
达城南五十里。有曰白鹿洞书堂者。故处士悔溪许公庋书之庄也。始许公业公车有名。既不得志于有司。则无所售其利器。于是就是洞而规一丘焉。洞在深峡中。有水石林木之胜。距所居且一舍。居人十数家。风俗颇淳厖。公以其地名。与庐阜朱文公所表章者相符。尤爱之。乃营立数楹之舍而购书数千卷以充之。仍安文公真像于其中。每冬夏聚诸生而肄业。来者读其书无禁。又置土田若干以附之。使为修屋补书之资。于是士争归向而白鹿书堂之名。闻于国中矣。公既没而诸子孙与乡人士遵守保护。无改者七十馀年。自世途一变。此堂不幸为他人所占。书册土田并随而荡然。公之曾孙𣳑汉二氏。䀌然伤之。乃节缩衣食。倡联缝章。竭数年心力。乃克恢复。其未复者。方将规画以填之。传曰不失旧物。其施为必有大过人者。若二氏者其许门之少康,光武乎。抑悔溪公之为堂规曰子孙中无论支宗。
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345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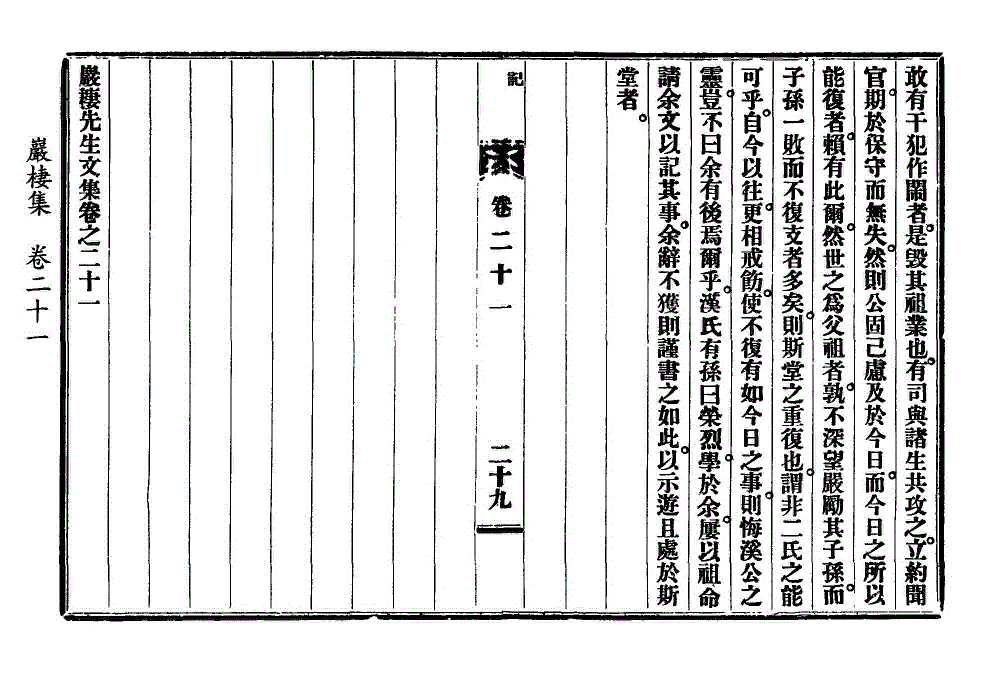 敢有干犯作闹者。是毁其祖业也。有司与诸生共攻之。立约闻官。期于保守而无失。然则公固已虑及于今日。而今日之所以能复者。赖有此尔。然世之为父祖者。孰不深望严励其子孙。而子孙一败而不复支者多矣。则斯堂之重复也。谓非二氏之能可乎。自今以往。更相戒饬。使不复有如今日之事。则悔溪公之灵。岂不曰余有后焉尔乎。汉氏有孙曰荣烈。学于余。屡以祖命请余文以记其事。余辞不获则谨书之如此。以示游且处于斯堂者。
敢有干犯作闹者。是毁其祖业也。有司与诸生共攻之。立约闻官。期于保守而无失。然则公固已虑及于今日。而今日之所以能复者。赖有此尔。然世之为父祖者。孰不深望严励其子孙。而子孙一败而不复支者多矣。则斯堂之重复也。谓非二氏之能可乎。自今以往。更相戒饬。使不复有如今日之事。则悔溪公之灵。岂不曰余有后焉尔乎。汉氏有孙曰荣烈。学于余。屡以祖命请余文以记其事。余辞不获则谨书之如此。以示游且处于斯堂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