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明: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.org,kanripo.org, db.itkc.or.kr 和 zh.wikisource.org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x 页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
中庸讲义条对[一](抄 启应制○丁巳)
中庸讲义条对[一](抄 启应制○丁巳)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18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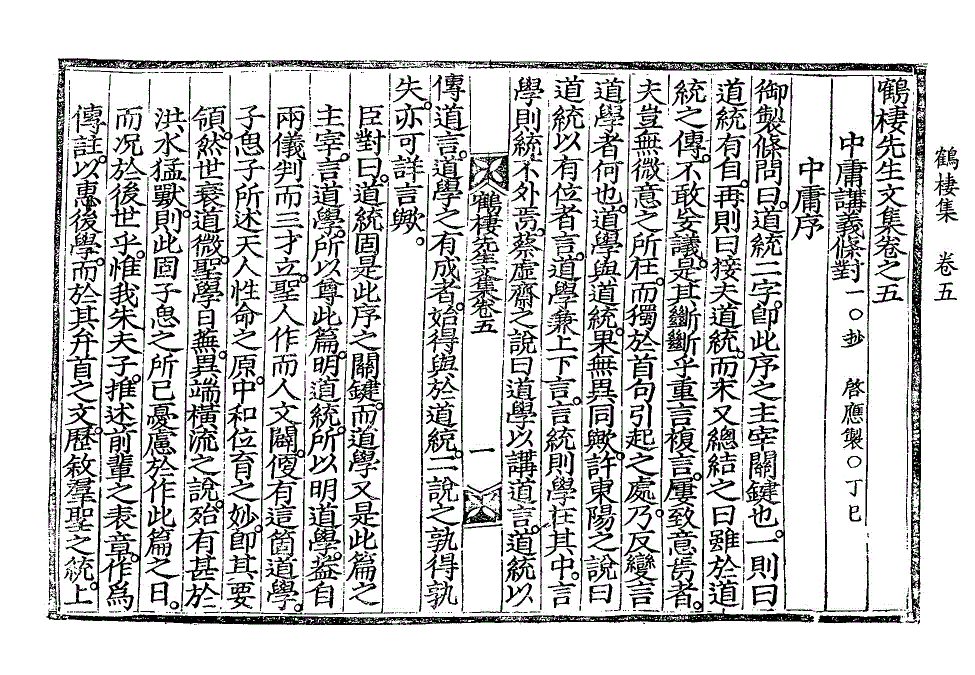 中庸序
中庸序御制条问曰。道统二字。即此序之主宰关键也。一则曰道统有自。再则曰接夫道统。而末又总结之曰虽于道统之传。不敢妄议。是其断断乎重言复言。屡致意焉者。夫岂无微意之所在。而独于首句引起之处。乃反变言道学者何也。道学与道统。果无异同欤。许东阳之说曰道统以有位者言。道学兼上下言。言统则学在其中。言学则统不外焉。蔡虚斋之说曰道学以讲道言。道统以传道言。道学之有成者。始得与于道统。二说之孰得孰失。亦可详言欤。
臣对曰。道统固是此序之关键。而道学又是此篇之主宰。言道学。所以尊此篇。明道统。所以明道学。盖自两仪判而三才立。圣人作而人文辟。便有这个道学。子思子所述天人性命之原。中和位育之妙。即其要领。然世衰道微。圣学日芜。异端横流之说。殆有甚于洪水猛兽。则此固子思之所已忧虑于作此篇之日。而况于后世乎。惟我朱夫子。推述前辈之表章。作为传注。以惠后学。而于其弁首之文。历叙群圣之统。上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18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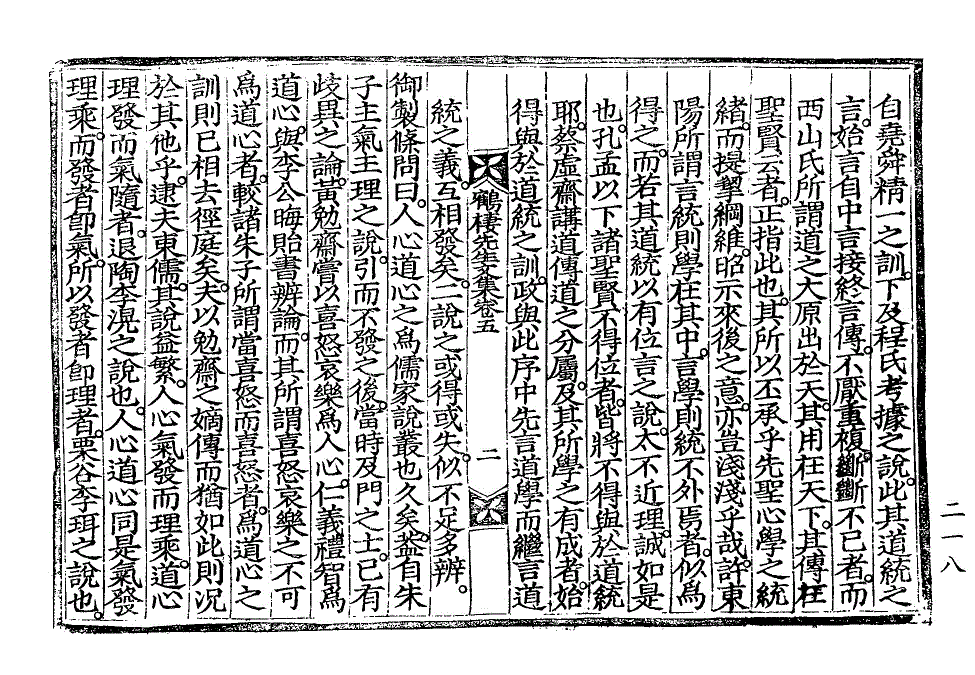 自尧舜精一之训。下及程氏考据之说。此其道统之言。始言自中言接终言传。不厌重复。断断不已者。而西山氏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。其用在天下。其传在圣贤云者。正指此也。其所以丕承乎先圣心学之统绪。而提挈纲维。昭示来后之意。亦岂浅浅乎哉。许东阳所谓言统则学在其中。言学则统不外焉者。似为得之。而若其道统以有位言之说。太不近理。诚如是也。孔孟以下诸圣贤不得位者。皆将不得与于道统耶。蔡虚斋讲道传道之分属。及其所学之有成者。始得与于道统之训。政与此序中先言道学而继言道统之义。互相发矣。二说之或得或失。似不足多辨。
自尧舜精一之训。下及程氏考据之说。此其道统之言。始言自中言接终言传。不厌重复。断断不已者。而西山氏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。其用在天下。其传在圣贤云者。正指此也。其所以丕承乎先圣心学之统绪。而提挈纲维。昭示来后之意。亦岂浅浅乎哉。许东阳所谓言统则学在其中。言学则统不外焉者。似为得之。而若其道统以有位言之说。太不近理。诚如是也。孔孟以下诸圣贤不得位者。皆将不得与于道统耶。蔡虚斋讲道传道之分属。及其所学之有成者。始得与于道统之训。政与此序中先言道学而继言道统之义。互相发矣。二说之或得或失。似不足多辨。御制条问曰。人心道心之为儒家说丛也久矣。盖自朱子主气主理之说。引而不发之后。当时及门之士。已有歧异之论。黄勉斋尝以喜怒哀乐为人心。仁义礼智为道心。与李公晦贻书辨论。而其所谓喜怒哀乐之不可为道心者。较诸朱子所谓当喜怒而喜怒者。为道心之训则已相去径庭矣。夫以勉斋之嫡传而犹如此则况于其他乎。逮夫东儒。其说益繁。人心气发而理乘。道心理发而气随者。退陶李滉之说也。人心道心同是气发理乘。而发者即气。所以发者即理者。栗谷李珥之说也。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19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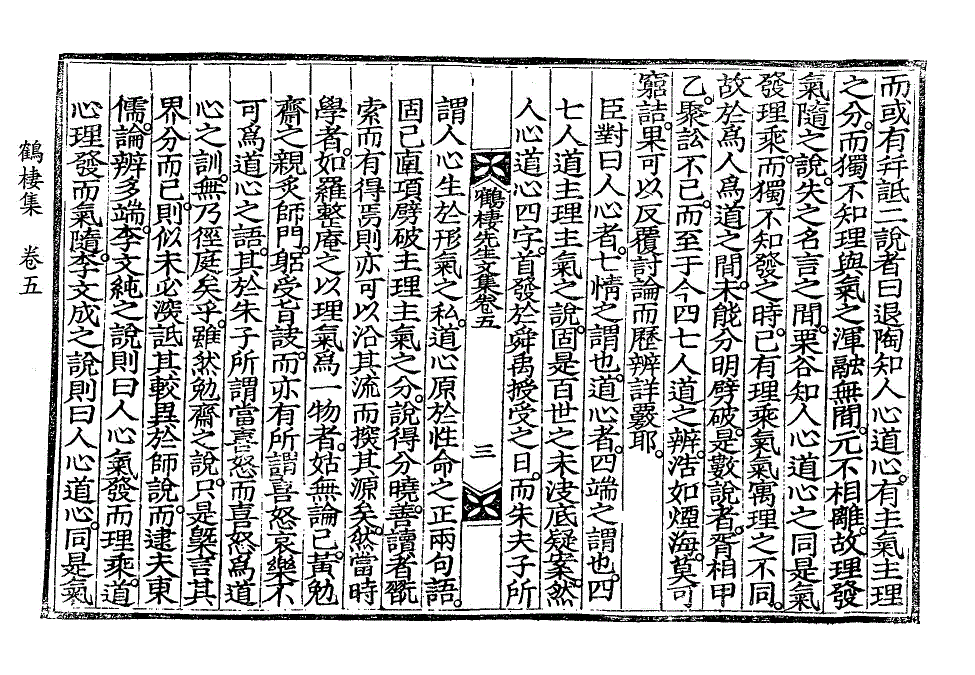 而或有并诋二说者曰退陶知人心道心。有主气主理之分。而独不知理与气之浑融无间。元不相离。故理发气随之说。失之名言之间。栗谷知人心道心之同是气发理乘。而独不知发之时。已有理乘气气寓理之不同。故于为人为道之间。未能分明劈破。是数说者。胥相甲乙。聚讼不已。而至于今四七人道之辨。浩如烟海。莫可穷诘。果可以反覆讨论而历辨详覈耶。
而或有并诋二说者曰退陶知人心道心。有主气主理之分。而独不知理与气之浑融无间。元不相离。故理发气随之说。失之名言之间。栗谷知人心道心之同是气发理乘。而独不知发之时。已有理乘气气寓理之不同。故于为人为道之间。未能分明劈破。是数说者。胥相甲乙。聚讼不已。而至于今四七人道之辨。浩如烟海。莫可穷诘。果可以反覆讨论而历辨详覈耶。臣对曰人心者。七情之谓也。道心者。四端之谓也。四七人道主理主气之说。固是百世之未决底疑案。然人心道心四字。首发于舜禹授受之日。而朱夫子所谓人心生于形气之私。道心原于性命之正两句语。固已直项劈破主理主气之分。说得分晓。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亦可以沿其流而探其源矣。然当时学者。如罗整庵之以理气为一物者。姑无论已。黄勉斋之亲炙师门。躬受旨诀。而亦有所谓喜怒哀乐不可为道心之语。其于朱子所谓当喜怒而喜怒为道心之训。无乃径庭矣乎。虽然勉斋之说。只是槩言其界分而已。则似未必深诋其较异于师说。而逮夫东儒。论辨多端。李文纯之说则曰人心气发而理乘。道心理发而气随。李文成之说则曰人心道心。同是气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1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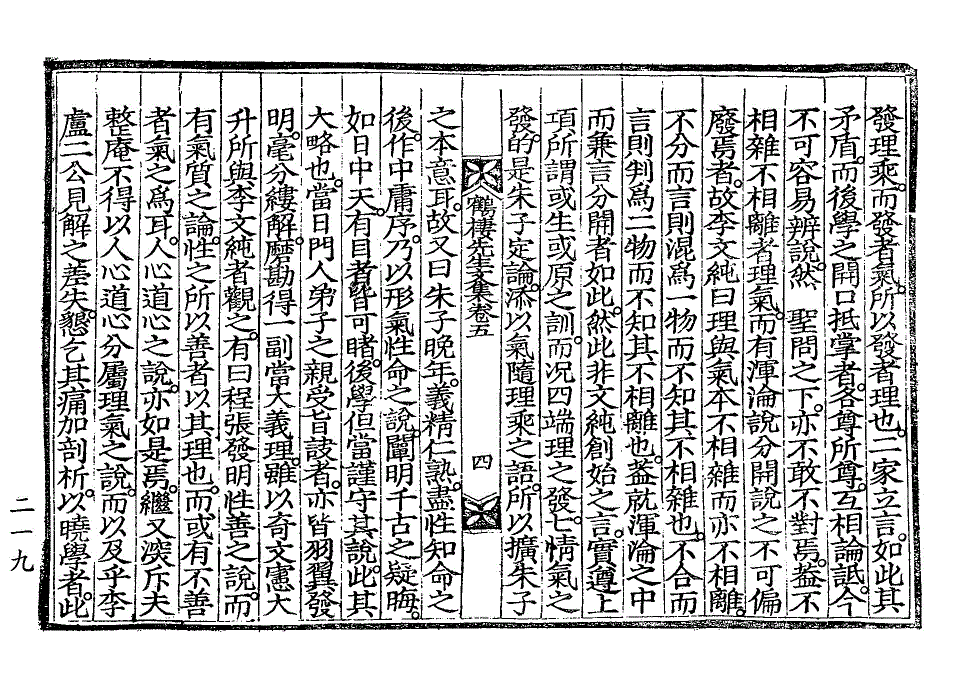 发理乘。而发者气。所以发者理也。二家立言。如此其矛盾。而后学之开口抵掌者。各尊所尊。互相论诋。今不可容易辨说。然 圣问之下。亦不敢不对焉。盖不相杂不相离者理气。而有浑沦说分开说之不可偏废焉者。故李文纯曰理与气本不相杂而亦不相离。不分而言则混为一物而不知其不相杂也。不合而言则判为二物而不知其不相离也。盖就浑沦之中而兼言分开者如此。然此非文纯创始之言。实遵上项所谓或生或原之训。而况四端理之发。七情气之发。的是朱子定论。添以气随理乘之语。所以扩朱子之本意耳。故又曰朱子晚年。义精仁熟。尽性知命之后。作中庸序。乃以形气性命之说。阐明千古之疑晦。如日中天。有目者皆可睹。后学但当谨守其说。此其大略也。当日门人弟子之亲受旨诀者。亦皆羽翼发明。毫分缕解。磨勘得一副当大义理。虽以奇文宪大升所与李文纯者观之。有曰程张发明性善之说。而有气质之论。性之所以善者以其理也。而或有不善者气之为耳。人心道心之说。亦如是焉。继又深斥夫整庵不得以人心道心分属理气之说。而以及乎李卢二公见解之差失。恳乞其痛加剖析。以晓学者。此
发理乘。而发者气。所以发者理也。二家立言。如此其矛盾。而后学之开口抵掌者。各尊所尊。互相论诋。今不可容易辨说。然 圣问之下。亦不敢不对焉。盖不相杂不相离者理气。而有浑沦说分开说之不可偏废焉者。故李文纯曰理与气本不相杂而亦不相离。不分而言则混为一物而不知其不相杂也。不合而言则判为二物而不知其不相离也。盖就浑沦之中而兼言分开者如此。然此非文纯创始之言。实遵上项所谓或生或原之训。而况四端理之发。七情气之发。的是朱子定论。添以气随理乘之语。所以扩朱子之本意耳。故又曰朱子晚年。义精仁熟。尽性知命之后。作中庸序。乃以形气性命之说。阐明千古之疑晦。如日中天。有目者皆可睹。后学但当谨守其说。此其大略也。当日门人弟子之亲受旨诀者。亦皆羽翼发明。毫分缕解。磨勘得一副当大义理。虽以奇文宪大升所与李文纯者观之。有曰程张发明性善之说。而有气质之论。性之所以善者以其理也。而或有不善者气之为耳。人心道心之说。亦如是焉。继又深斥夫整庵不得以人心道心分属理气之说。而以及乎李卢二公见解之差失。恳乞其痛加剖析。以晓学者。此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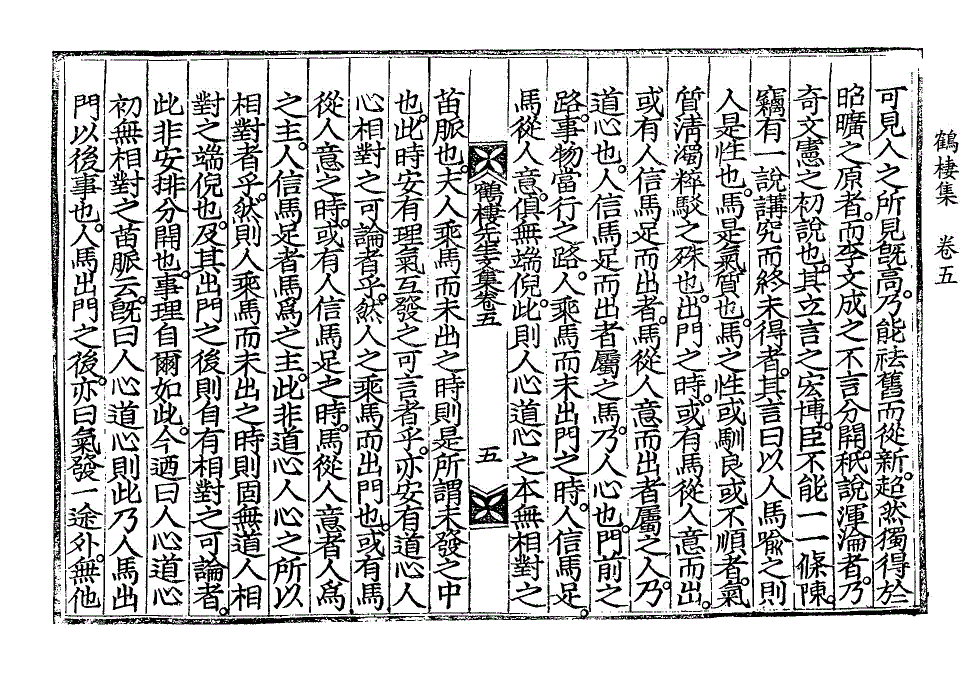 可见人之所见既高。乃能祛旧而从新。超然独得于昭旷之原者。而李文成之不言分开。秖说浑沦者。乃奇文宪之初说也。其立言之宏博。臣不能一一条陈。窃有一说讲究而终未得者。其言曰以人马喻之则人是性也。马是气质也。马之性或驯良或不顺者。气质清浊粹驳之殊也。出门之时。或有马从人意而出。或有人信马足而出者。马从人意而出者属之人。乃道心也。人信马足而出者属之马。乃人心也。门前之路。事物当行之路。人乘马而未出门之时。人信马足。马从人意。俱无端倪。此则人心道心之本无相对之苗脉也。夫人乘马而未出之时则是所谓未发之中也。此时安有理气互发之可言者乎。亦安有道心人心相对之可论者乎。然人之乘马而出门也。或有马从人意之时。或有人信马足之时。马从人意者人为之主。人信马足者马为之主。此非道心人心之所以相对者乎。然则人乘马而未出之时则固无道人相对之端倪也。及其出门之后则自有相对之可论者。此非安排分开也。事理自尔如此。今乃曰人心道心初无相对之苗脉云。既曰人心道心则此乃人马出门以后事也。人马出门之后。亦曰气发一途外。无他
可见人之所见既高。乃能祛旧而从新。超然独得于昭旷之原者。而李文成之不言分开。秖说浑沦者。乃奇文宪之初说也。其立言之宏博。臣不能一一条陈。窃有一说讲究而终未得者。其言曰以人马喻之则人是性也。马是气质也。马之性或驯良或不顺者。气质清浊粹驳之殊也。出门之时。或有马从人意而出。或有人信马足而出者。马从人意而出者属之人。乃道心也。人信马足而出者属之马。乃人心也。门前之路。事物当行之路。人乘马而未出门之时。人信马足。马从人意。俱无端倪。此则人心道心之本无相对之苗脉也。夫人乘马而未出之时则是所谓未发之中也。此时安有理气互发之可言者乎。亦安有道心人心相对之可论者乎。然人之乘马而出门也。或有马从人意之时。或有人信马足之时。马从人意者人为之主。人信马足者马为之主。此非道心人心之所以相对者乎。然则人乘马而未出之时则固无道人相对之端倪也。及其出门之后则自有相对之可论者。此非安排分开也。事理自尔如此。今乃曰人心道心初无相对之苗脉云。既曰人心道心则此乃人马出门以后事也。人马出门之后。亦曰气发一途外。无他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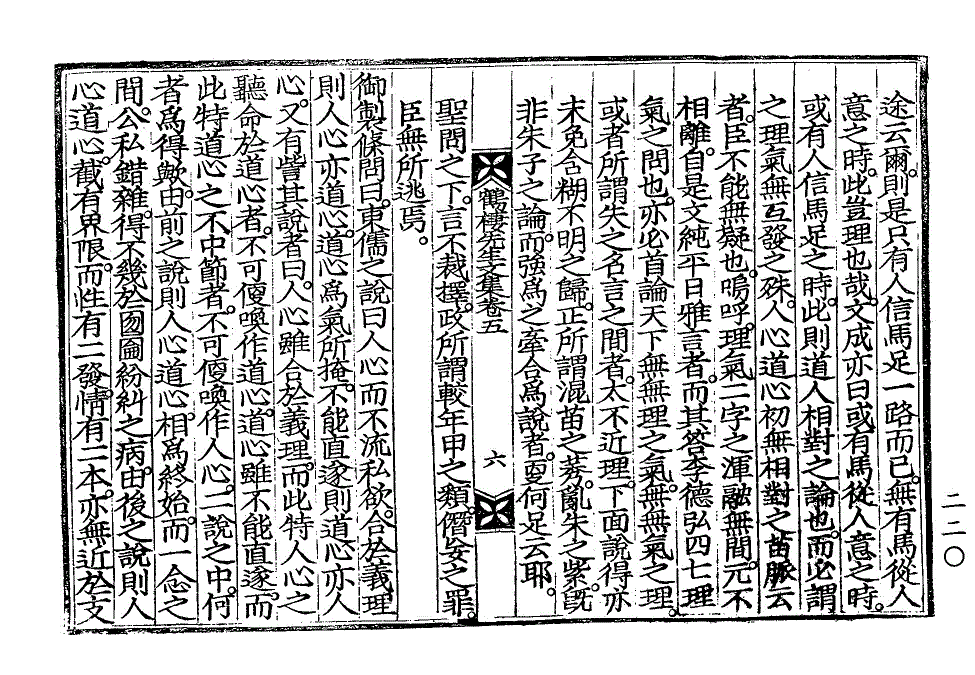 途云尔。则是只有人信马足一路而已。无有马从人意之时。此岂理也哉。文成亦曰或有马从人意之时。或有人信马足之时。此则道人相对之论也。而必谓之理气无互发之殊。人心道心初无相对之苗脉云者。臣不能无疑也。呜呼。理气二字之浑融无间。元不相离。自是文纯平日雅言者。而其答李德弘四七理气之问也。亦必首论天下无无理之气。无无气之理。或者所谓失之名言之间者。太不近理。下面说得亦未免含糊不明之归。正所谓混苗之莠。乱朱之紫。既非朱子之论。而强为之牵合为说者。更何足云耶。 圣问之下。言不裁择。政所谓较年甲之类。僭妄之罪。臣无所逃焉。
途云尔。则是只有人信马足一路而已。无有马从人意之时。此岂理也哉。文成亦曰或有马从人意之时。或有人信马足之时。此则道人相对之论也。而必谓之理气无互发之殊。人心道心初无相对之苗脉云者。臣不能无疑也。呜呼。理气二字之浑融无间。元不相离。自是文纯平日雅言者。而其答李德弘四七理气之问也。亦必首论天下无无理之气。无无气之理。或者所谓失之名言之间者。太不近理。下面说得亦未免含糊不明之归。正所谓混苗之莠。乱朱之紫。既非朱子之论。而强为之牵合为说者。更何足云耶。 圣问之下。言不裁择。政所谓较年甲之类。僭妄之罪。臣无所逃焉。御制条问曰。东儒之说曰人心而不流私欲。合于义理则人心亦道心。道心为气所掩。不能直遂则道心亦人心。又有訾其说者曰。人心虽合于义理。而此特人心之听命于道心者。不可便唤作道心。道心虽不能直遂。而此特道心之不中节者。不可便唤作人心。二说之中。何者为得欤。由前之说则人心道心。相为终始。而一念之间。公私错杂。得不几于囫囵纷纠之病。由后之说则人心道心。截有界限。而性有二发。情有二本。亦无近于支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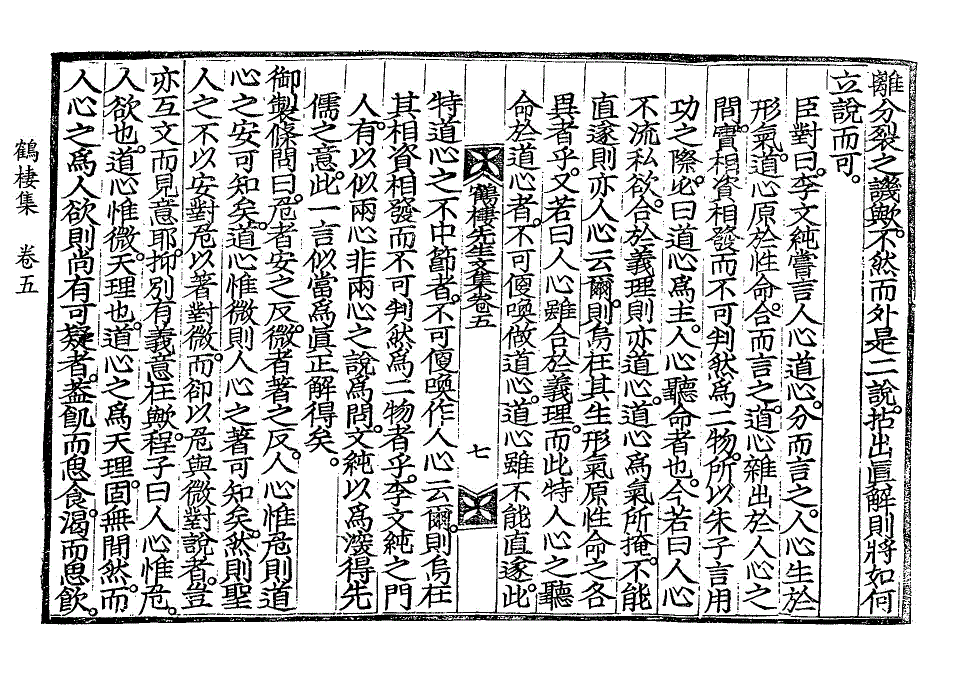 离分裂之讥欤。不然而外是二说。拈出真解则将如何立说而可。
离分裂之讥欤。不然而外是二说。拈出真解则将如何立说而可。臣对曰。李文纯尝言人心道心。分而言之。人心生于形气。道心原于性命。合而言之。道心杂出于人心之间。实相资相发而不可判然为二物。所以朱子言用功之际。必曰道心为主。人心听命者也。今若曰人心不流私欲。合于义理则亦道心。道心为气所掩。不能直遂则亦人心云尔。则乌在其生形气原性命之各异者乎。又若曰人心虽合于义理。而此特人心之听命于道心者。不可便唤做道心。道心虽不能直遂。此特道心之不中节者。不可便唤作人心云尔。则乌在其相资相发而不可判然为二物者乎。李文纯之门人。有以似两心非两心之说为问。文纯以为深得先儒之意。此一言似当为真正解得矣。
御制条问曰。危者安之反。微者著之反。人心惟危则道心之安可知矣。道心惟微则人心之著可知矣。然则圣人之不以安对危以著对微。而却以危与微对说者。岂亦互文而见意耶。抑别有义意在欤。程子曰人心惟危。人欲也。道心惟微。天理也。道心之为天理。固无间然。而人心之为人欲则尚有可疑者。盖饥而思食。渴而思饮。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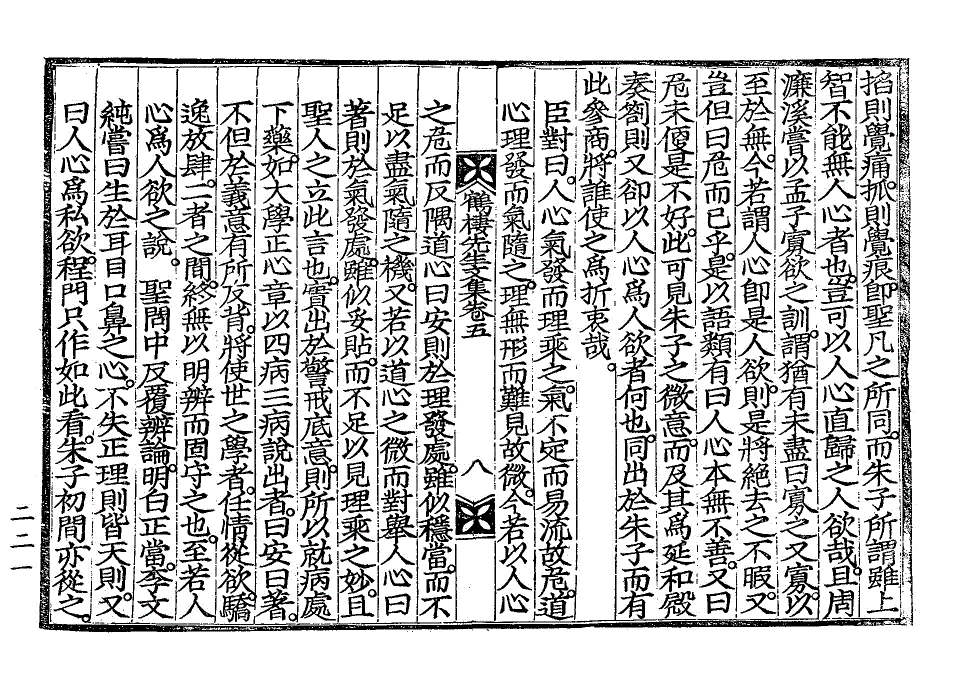 掐则觉痛。抓则觉痕。即圣凡之所同。而朱子所谓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者也。岂可以人心直归之人欲哉。且周濂溪尝以孟子寡欲之训。谓犹有未尽曰寡之又寡。以至于无。今若谓人心即是人欲。则是将绝去之不暇。又岂但曰危而已乎。是以语类有曰人心本无不善。又曰危未便是不好。此可见朱子之微意。而及其为延和殿奏劄则又却以人心为人欲者何也。同出于朱子而有此参商。将谁使之为折衷哉。
掐则觉痛。抓则觉痕。即圣凡之所同。而朱子所谓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者也。岂可以人心直归之人欲哉。且周濂溪尝以孟子寡欲之训。谓犹有未尽曰寡之又寡。以至于无。今若谓人心即是人欲。则是将绝去之不暇。又岂但曰危而已乎。是以语类有曰人心本无不善。又曰危未便是不好。此可见朱子之微意。而及其为延和殿奏劄则又却以人心为人欲者何也。同出于朱子而有此参商。将谁使之为折衷哉。臣对曰。人心气发而理乘之。气不定而易流故危。道心理发而气随之。理无形而难见故微。今若以人心之危而反隅道心曰安则于理发处。虽似稳当。而不足以尽气随之机。又若以道心之微而对举人心曰著则于气发处。虽似妥贴。而不足以见理乘之妙。且圣人之立此言也。实出于警戒底意。则所以就病处下药。如大学正心章以四病三病说出者。曰安曰著。不但于义意有所反背。将使世之学者。任情从欲。骄逸放肆。二者之间。终无以明辨而固守之也。至若人心为人欲之说。 圣问中反覆辨论。明白正当。李文纯尝曰生于耳目口鼻之心。不失正理则皆天则。又曰人心为私欲。程门只作如此看。朱子初间亦从之。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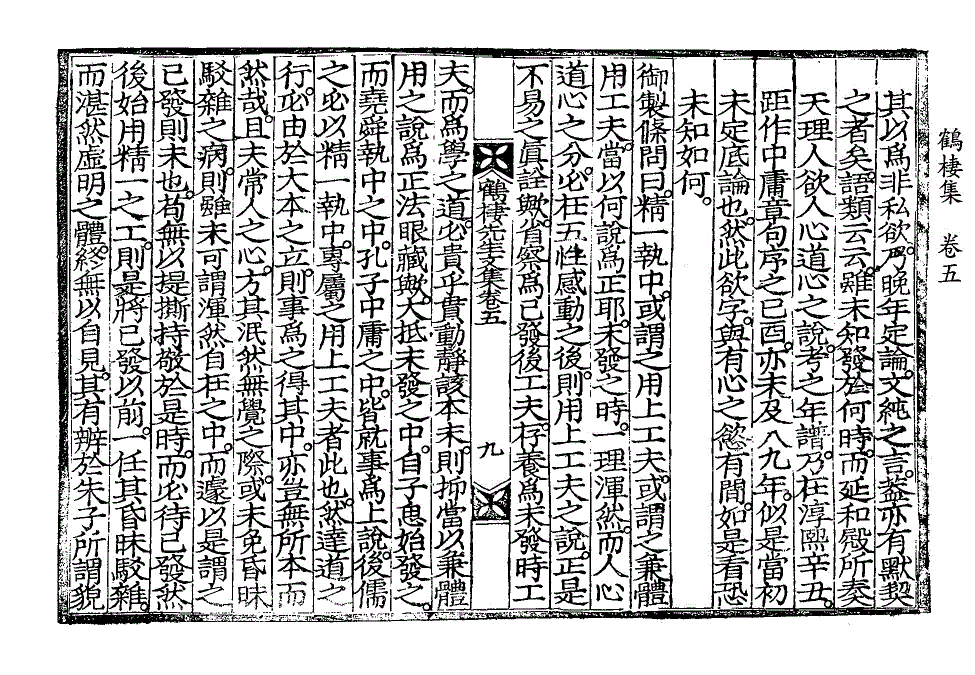 其以为非私欲。乃晚年定论。文纯之言。盖亦有默契之者矣。语类云云。虽未知发于何时。而延和殿所奏天理人欲人心道心之说。考之年谱。乃在淳熙辛丑。距作中庸章句序之己酉。亦未及八九年。似是当初未定底论也。然此欲字。与有心之欲有间。如是看恐未知如何。
其以为非私欲。乃晚年定论。文纯之言。盖亦有默契之者矣。语类云云。虽未知发于何时。而延和殿所奏天理人欲人心道心之说。考之年谱。乃在淳熙辛丑。距作中庸章句序之己酉。亦未及八九年。似是当初未定底论也。然此欲字。与有心之欲有间。如是看恐未知如何。御制条问曰。精一执中。或谓之用上工夫。或谓之兼体用工夫。当以何说为正耶。未发之时。一理浑然。而人心道心之分。必在五性感动之后。则用上工夫之说。正是不易之真诠欤。省察为已发后工夫。存养为未发时工夫。而为学之道。必贵乎贯动静该本末。则抑当以兼体用之说为正法眼藏欤。大抵未发之中。自子思始发之。而尧舜执中之中。孔子中庸之中。皆就事为上说。后儒之必以精一执中。专属之用上工夫者此也。然达道之行。必由于大本之立。则事为之得其中。亦岂无所本而然哉。且夫常人之心。方其泯然无觉之际。或未免昏昧驳杂之病。则虽未可谓浑然自在之中。而遽以是谓之已发则未也。苟无以提撕持敬于是时。而必待已发然后始用精一之工。则是将已发以前。一任其昏昧驳杂。而湛然虚明之体。终无以自见。其有辨于朱子所谓貌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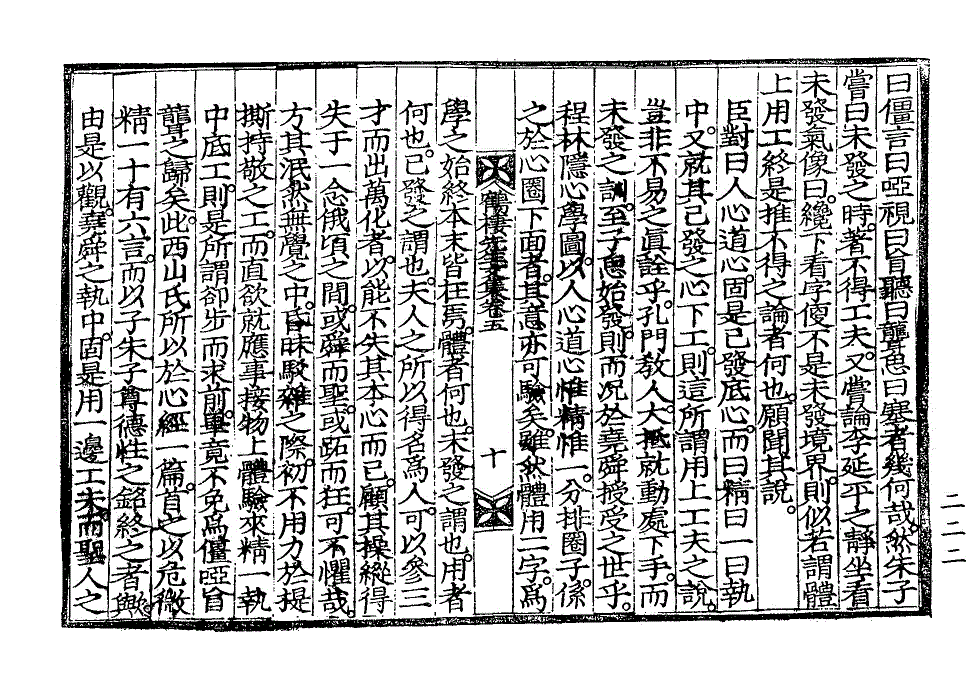 曰僵言曰哑视曰盲听曰聋思曰塞者几何哉。然朱子尝曰未发之时。著不得工夫。又尝论李延平之静坐看未发气像曰。才下看字便不是未发境界。则似若谓体上用工终是推不得之论者何也。愿闻其说。
曰僵言曰哑视曰盲听曰聋思曰塞者几何哉。然朱子尝曰未发之时。著不得工夫。又尝论李延平之静坐看未发气像曰。才下看字便不是未发境界。则似若谓体上用工终是推不得之论者何也。愿闻其说。臣对曰人心道心。固是已发底心。而曰精曰一曰执中。又就其已发之心下工。则这所谓用上工夫之说。岂非不易之真诠乎。孔门教人。大抵就动处下手。而未发之训。至子思始发。则而况于尧舜授受之世乎。程林隐心学图。以人心道心惟精惟一。分排圈子。系之于心圈下面者。其意亦可验矣。虽然体用二字。为学之始终本末皆在焉。体者何也。未发之谓也。用者何也。已发之谓也。夫人之所以得名为人。可以参三才而出万化者。以能不失其本心而已。顾其操纵得失于一念俄顷之间。或舜而圣。或蹠而狂。可不惧哉。方其泯然无觉之中。昏昧驳杂之际。初不用力于提撕持敬之工。而直欲就应事接物上体验来精一执中底工。则是所谓却步而求前。毕竟不免为僵哑盲聋之归矣。此西山氏所以于心经一篇。首之以危微精一十有六言。而以子朱子尊德性之铭终之者欤。由是以观。尧舜之执中。固是用一边工夫。而圣人之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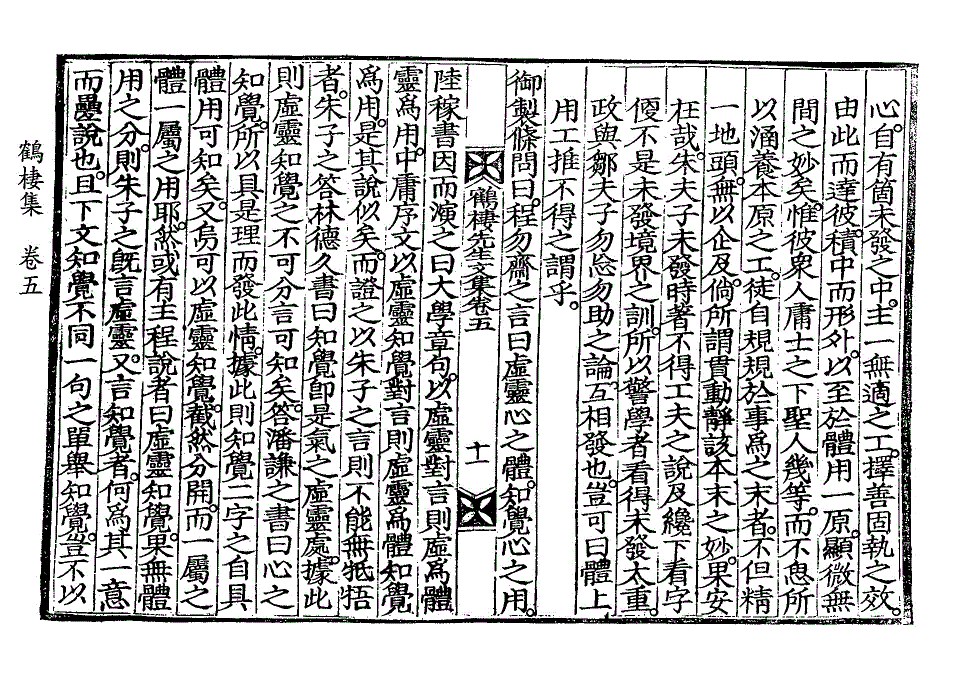 心。自有个未发之中。主一无适之工。择善固执之效。由此而达彼。积中而形外。以至于体用一原。显微无间之妙矣。惟彼众人庸士之下圣人几等。而不思所以涵养本原之工。徒自规规于事为之末者。不但精一地头。无以企及。倘所谓贯动静该本末之妙。果安在哉。朱夫子未发时著不得工夫之说及才下看字便不是未发境界之训。所以警学者看得未发太重。政与邹夫子勿忘勿助之论。互相发也。岂可曰体上用工推不得之谓乎。
心。自有个未发之中。主一无适之工。择善固执之效。由此而达彼。积中而形外。以至于体用一原。显微无间之妙矣。惟彼众人庸士之下圣人几等。而不思所以涵养本原之工。徒自规规于事为之末者。不但精一地头。无以企及。倘所谓贯动静该本末之妙。果安在哉。朱夫子未发时著不得工夫之说及才下看字便不是未发境界之训。所以警学者看得未发太重。政与邹夫子勿忘勿助之论。互相发也。岂可曰体上用工推不得之谓乎。御制条问曰。程勿斋之言曰虚灵心之体。知觉心之用。陆稼书因而演之曰大学章句。以虚灵对言则虚为体灵为用。中庸序文以虚灵知觉对言则虚灵为体知觉为用。是其说似矣。而證之以朱子之言则不能无牴牾者。朱子之答林德久书曰知觉即是气之虚灵处。据此则虚灵知觉之不可分言可知矣。答潘谦之书曰心之知觉。所以具是理而发此情。据此则知觉二字之自具体用可知矣。又乌可以虚灵知觉。截然分开。而一属之体一属之用耶。然或有主程说者曰虚灵知觉。果无体用之分。则朱子之既言虚灵。又言知觉者。何为其一意而叠说也。且下文知觉不同一句之单举知觉。岂不以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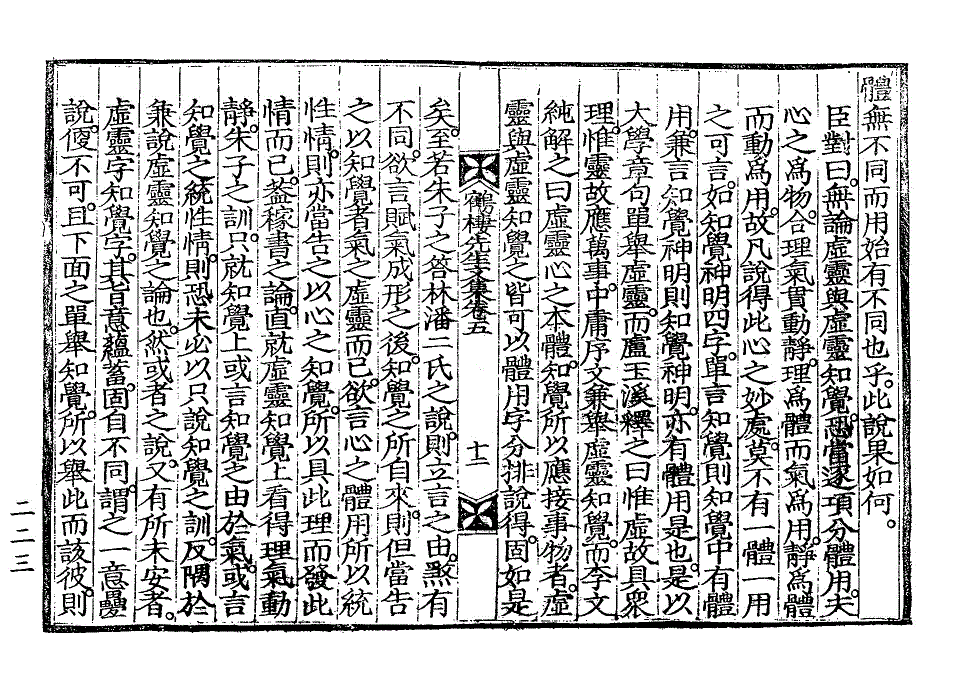 体无不同而用始有不同也乎。此说果如何。
体无不同而用始有不同也乎。此说果如何。臣对曰。无论虚灵与虚灵知觉。恐当逐项分体用。夫心之为物。合理气贯动静。理为体而气为用。静为体而动为用。故凡说得此心之妙处。莫不有一体一用之可言。如知觉神明四字。单言知觉则知觉中有体用。兼言知觉神明则知觉神明。亦有体用是也。是以大学章句单举虚灵。而卢玉溪释之曰惟虚故具众理。惟灵故应万事。中庸序文兼举虚灵知觉。而李文纯解之曰虚灵心之本体。知觉所以应接事物者。虚灵与虚灵知觉之皆可以体用字分排说得。固如是矣。至若朱子之答林潘二氏之说。则立言之由。煞有不同。欲言赋气成形之后。知觉之所自来。则但当告之以知觉者气之虚灵而已。欲言心之体用所以统性情。则亦当告之以心之知觉。所以具此理而发此情而已。盖稼书之论。直就虚灵知觉上看得理气动静。朱子之训。只就知觉上或言知觉之由于气。或言知觉之统性情。则恐未必以只说知觉之训。反隅于兼说虚灵知觉之论也。然或者之说。又有所未安者。虚灵字知觉字。其旨意蕴蓄。固自不同。谓之一意叠说。便不可。且下面之单举知觉。所以举此而该彼。则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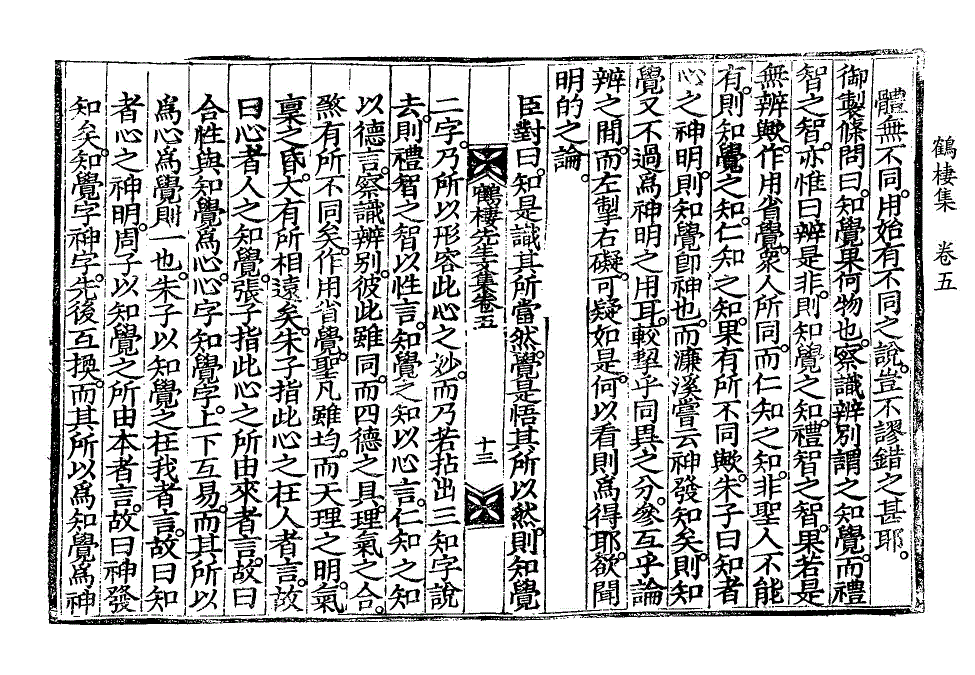 体无不同。用始有不同之说。岂不谬错之甚耶。
体无不同。用始有不同之说。岂不谬错之甚耶。御制条问曰。知觉果何物也。察识辨别谓之知觉。而礼智之智。亦惟曰辨是非。则知觉之知。礼智之智。果若是无辨欤。作用省觉。众人所同。而仁知之知。非圣人不能有。则知觉之知。仁知之知。果有所不同欤。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。则知觉即神也。而濂溪尝云神发知矣。则知觉又不过为神明之用耳。较挈乎同异之分。参互乎论辨之间。而左掣右碍。可疑如是。何以看则为得耶。欲闻明的之论。
臣对曰。知是识其所当然。觉是悟其所以然。则知觉二字。乃所以形容此心之妙。而乃若拈出三知字说去。则礼智之智以性言。知觉之知以心言。仁知之知以德言。察识辨别。彼此虽同。而四德之具。理气之合。煞有所不同矣。作用省觉。圣凡虽均。而天理之明。气禀之昏。大有所相远矣。朱子指此心之在人者言。故曰心者人之知觉。张子指此心之所由来者言。故曰合性与知觉为心。心字知觉字。上下互易。而其所以为心为觉则一也。朱子以知觉之在我者言。故曰知者心之神明。周子以知觉之所由本者言。故曰神发知矣。知觉字神字。先后互换。而其所以为知觉为神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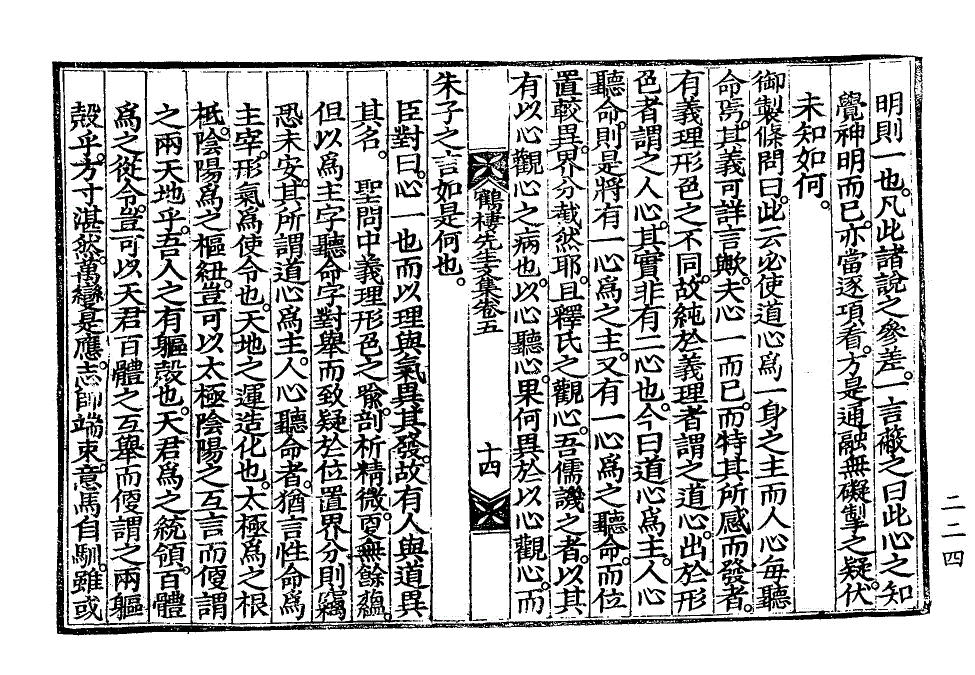 明则一也。凡此诸说之参差。一言蔽之曰此心之知觉神明而已。亦当逐项看。方是通融无碍掣之疑。伏未知如何。
明则一也。凡此诸说之参差。一言蔽之曰此心之知觉神明而已。亦当逐项看。方是通融无碍掣之疑。伏未知如何。御制条问曰。此云必使道心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。其义可详言欤。夫心一而已。而特其所感而发者。有义理形色之不同。故纯于义理者谓之道心。出于形色者谓之人心。其实非有二心也。今曰道心为主。人心听命。则是将有一心为之主。又有一心为之听命。而位置较异。界分截然耶。且释氏之观心。吾儒讥之者。以其有以心观心之病也。以心听心。果何异于以心观心。而朱子之言如是何也。
臣对曰。心一也而以理与气异其发。故有人与道异其名。 圣问中义理形色之喻。剖析精微。更无馀蕴。但以为主字听命字对举而致疑于位置界分则窃恐未安。其所谓道心为主。人心听命者。犹言性命为主宰。形气为使令也。天地之运造化也。太极为之根柢。阴阳为之枢纽。岂可以太极阴阳之互言而便谓之两天地乎。吾人之有躯壳也。天君为之统领。百体为之从令。岂可以天君百体之互举而便谓之两躯壳乎。方寸湛然。万变是应。志帅端束。意马自驯。虽或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5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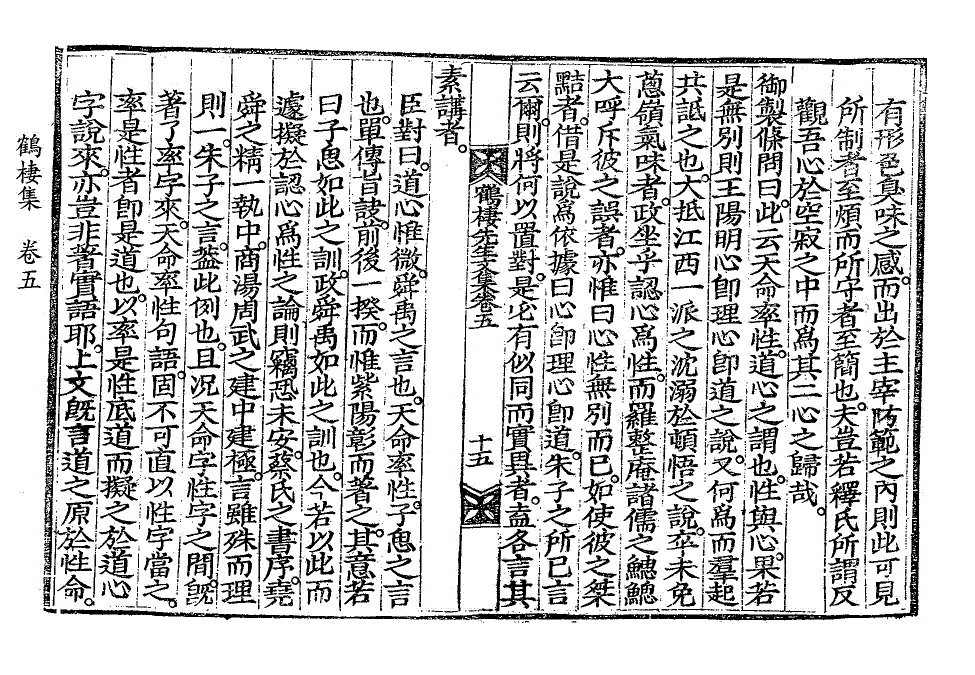 有形色臭味之感。而出于主宰防范之内则此可见所制者至烦而所守者至简也。夫岂若释氏所谓反观吾心于空寂之中而为其二心之归哉。
有形色臭味之感。而出于主宰防范之内则此可见所制者至烦而所守者至简也。夫岂若释氏所谓反观吾心于空寂之中而为其二心之归哉。御制条问曰。此云天命率性。道心之谓也。性与心。果若是无别则王阳明心即理心即道之说。又何为而群起共诋之也。大抵江西一派之沈溺于顿悟之说。卒未免葱岭气味者。政坐乎认心为性。而罗整庵诸儒之鳃鳃大呼斥彼之误者。亦惟曰心性无别而已。如使彼之桀黠者。借是说为依据曰心即理心即道。朱子之所已言云尔。则将何以置对。是必有似同而实异者。盍各言其素讲者。
臣对曰。道心惟微。舜禹之言也。天命率性。子思之言也。单传旨诀。前后一揆。而惟紫阳彰而著之。其意若曰子思如此之训。政舜禹如此之训也。今若以此而遽拟于认心为性之论。则窃恐未安。蔡氏之书序。尧舜之精一执中。商汤周武之建中建极。言虽殊而理则一。朱子之言。盖此例也。且况天命字性字之间。既著了率字来。天命率性句语。固不可直以性字当之。率是性者即是道也。以率是性底道而拟之于道心字说来。亦岂非著实语耶。上文既言道之原于性命。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5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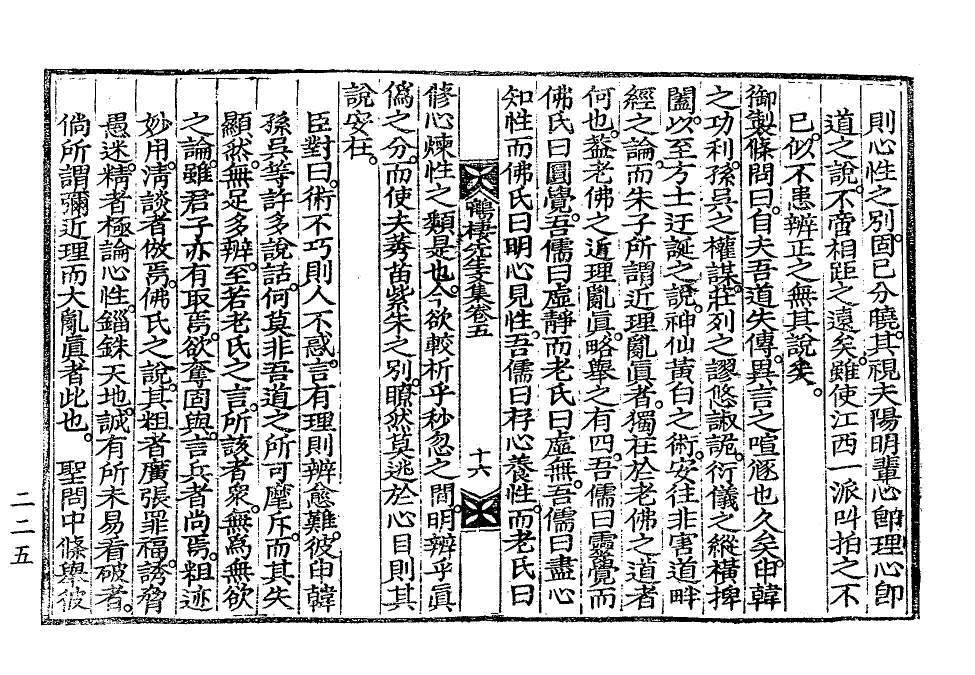 则心性之别。固已分晓。其视夫阳明辈心即理心即道之说。不啻相距之远矣。虽使江西一派叫拍之不已。似不患辨正之无其说矣。
则心性之别。固已分晓。其视夫阳明辈心即理心即道之说。不啻相距之远矣。虽使江西一派叫拍之不已。似不患辨正之无其说矣。御制条问曰。自夫吾道失传。异言之喧豗也久矣。申韩之功利。孙吴之权谋。庄列之谬悠諔诡。衍仪之纵横捭阖。以至方士迂诞之说。神仙黄白之术。安往非害道畔经之论。而朱子所谓近理乱真者。独在于老佛之道者何也。盖老佛之近理乱真。略举之有四。吾儒曰灵觉而佛氏曰圆觉。吾儒曰虚静而老氏曰虚无。吾儒曰尽心知性而佛氏曰明心见性。吾儒曰存心养性。而老氏曰修心炼性之类是也。今欲较析乎秒忽之间。明辨乎真伪之分。而使夫莠苗紫朱之别。瞭然莫逃于心目则其说安在。
臣对曰。术不巧则人不惑。言有理则辨愈难。彼申韩孙吴等许多说话。何莫非吾道之所可麾斥。而其失显然。无足多辨。至若老氏之言。所该者众。无为无欲之论。虽君子亦有取焉。欲夺固与。言兵者尚焉。粗迹妙用。清谈者仿焉。佛氏之说。其粗者广张罪福。诱胁愚迷。精者极论心性。锱铢天地。诚有所未易看破者。倘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此也。 圣问中条举彼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6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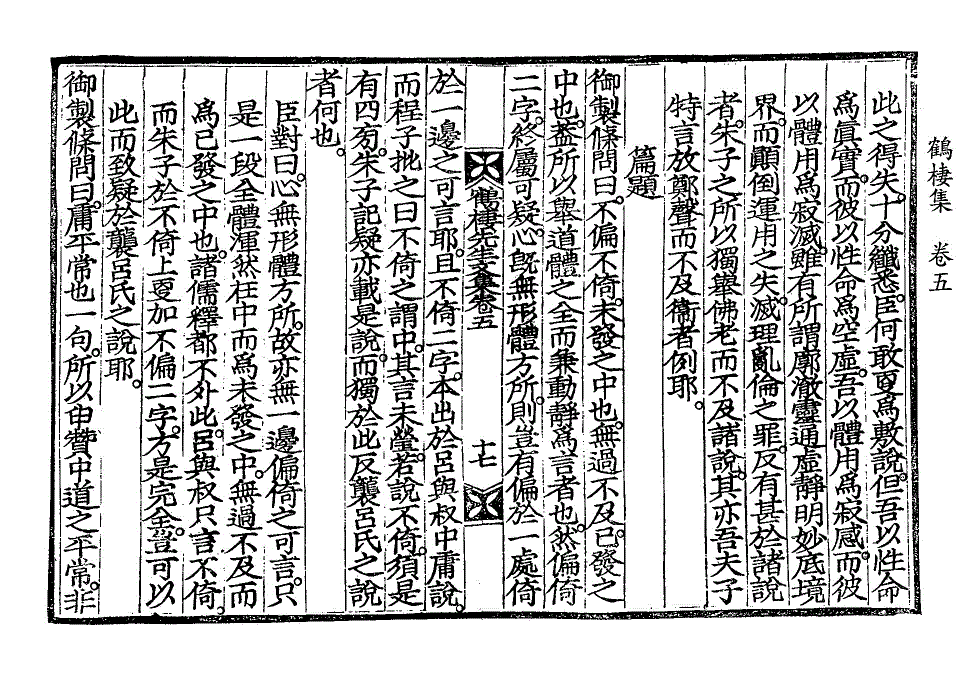 此之得失。十分纤悉。臣何敢更为敷说。但吾以性命为真实。而彼以性命为空虚。吾以体用为寂感。而彼以体用为寂灭。虽有所谓廓澈灵通虚静明妙底境界。而颠倒运用之失。灭理乱伦之罪。反有甚于诸说者。朱子之所以独举佛老而不及诸说。其亦吾夫子特言放郑声而不及卫者例耶。
此之得失。十分纤悉。臣何敢更为敷说。但吾以性命为真实。而彼以性命为空虚。吾以体用为寂感。而彼以体用为寂灭。虽有所谓廓澈灵通虚静明妙底境界。而颠倒运用之失。灭理乱伦之罪。反有甚于诸说者。朱子之所以独举佛老而不及诸说。其亦吾夫子特言放郑声而不及卫者例耶。篇题
御制条问曰。不偏不倚。未发之中也。无过不及。已发之中也。盖所以举道体之全而兼动静为言者也。然偏倚二字。终属可疑。心既无形体方所。则岂有偏于一处倚于一边之可言耶。且不倚二字。本出于吕与叔中庸说。而程子批之曰不倚之谓中。其言未莹。若说不倚。须是有四旁。朱子记疑亦载是说。而独于此反袭吕氏之说者何也。
臣对曰。心无形体方所。故亦无一边偏倚之可言。只是一段全体浑然在中而为未发之中。无过不及而为已发之中也。诸儒释都不外此。吕与叔只言不倚。而朱子于不倚上更加不偏二字。方是完全。岂可以此而致疑于袭吕氏之说耶。
御制条问曰。庸平常也一句。所以申赞中道之平常。非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6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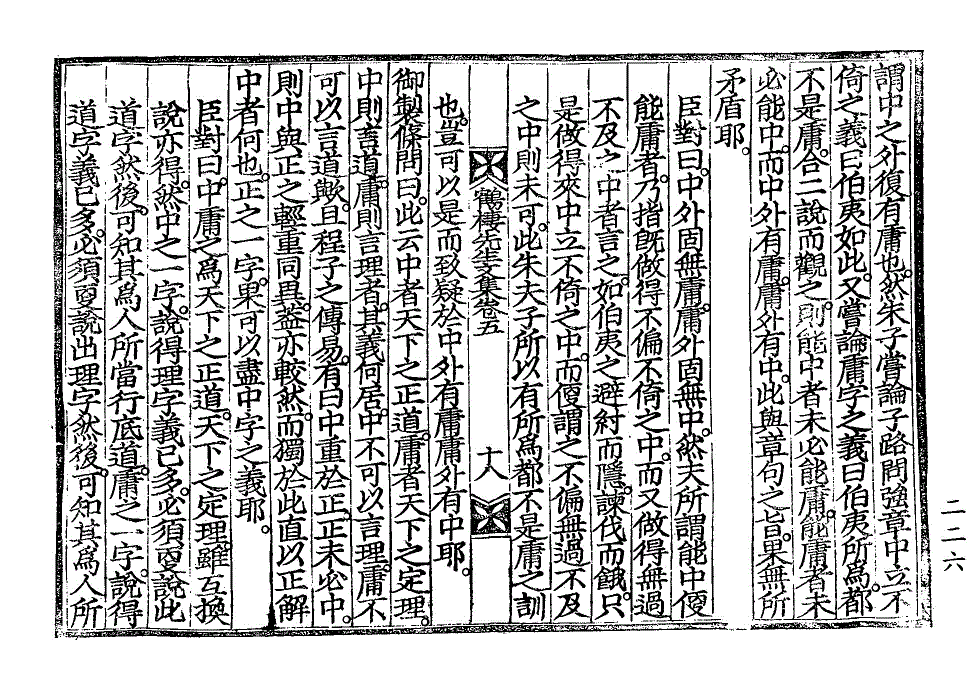 谓中之外复有庸也。然朱子尝论子路问强章中立不倚之义曰伯夷如此。又尝论庸字之义曰伯夷所为。都不是庸。合二说而观之。则能中者未必能庸。能庸者未必能中。而中外有庸。庸外有中。此与章句之旨。果无所矛盾耶。
谓中之外复有庸也。然朱子尝论子路问强章中立不倚之义曰伯夷如此。又尝论庸字之义曰伯夷所为。都不是庸。合二说而观之。则能中者未必能庸。能庸者未必能中。而中外有庸。庸外有中。此与章句之旨。果无所矛盾耶。臣对曰。中外固无庸。庸外固无中。然夫所谓能中便能庸者。乃指既做得不偏不倚之中。而又做得无过不及之中者言之。如伯夷之避纣而隐。谏伐而饿。只是做得来中立不倚之中。而便谓之不偏无过不及之中则未可。此朱夫子所以有所为都不是庸之训也。岂可以是而致疑于中外有庸庸外有中耶。
御制条问曰。此云中者天下之正道。庸者天下之定理。中则言道。庸则言理者。其义何居。中不可以言理。庸不可以言道欤。且程子之传易。有曰中重于正。正未必中。则中与正之轻重同异。盖亦较然。而独于此直以正解中者何也。正之一字。果可以尽中字之义耶。
臣对曰。中庸之为天下之正道。天下之定理。虽互换说亦得。然中之一字。说得理字义已多。必须更说此道字然后。可知其为人所当行底道。庸之一字。说得道字义已多。必须更说出理字然后。可知其为人所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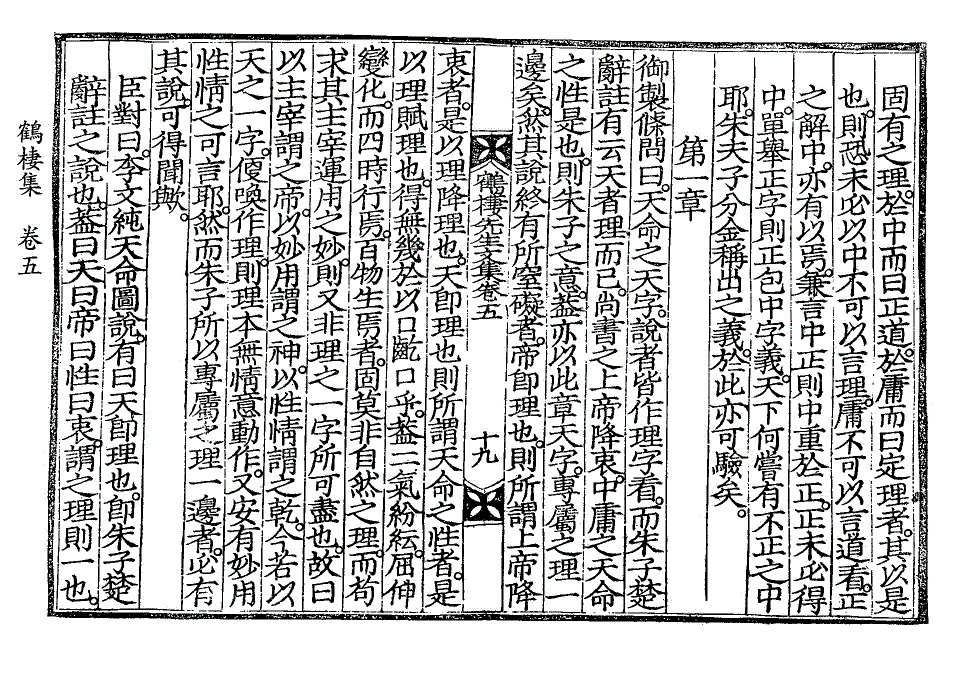 固有之理。于中而曰正道。于庸而曰定理者。其以是也。则恐未必以中不可以言理。庸不可以言道看。正之解中。亦有以焉。兼言中正则中重于正。正未必得中。单举正字则正包中字义。天下何尝有不正之中耶。朱夫子分金称出之义。于此亦可验矣。
固有之理。于中而曰正道。于庸而曰定理者。其以是也。则恐未必以中不可以言理。庸不可以言道看。正之解中。亦有以焉。兼言中正则中重于正。正未必得中。单举正字则正包中字义。天下何尝有不正之中耶。朱夫子分金称出之义。于此亦可验矣。第一章
御制条问曰。天命之天字。说者皆作理字看。而朱子楚辞注有云天者理而已。尚书之上帝降衷。中庸之天命之性是也。则朱子之意。盖亦以此章天字。专属之理一边矣。然其说终有所窒碍者。帝即理也。则所谓上帝降衷者。是以理降理也。天即理也则所谓天命之性者。是以理赋理也。得无几于以口龁口乎。盖二气纷纭。屈伸变化。而四时行焉。百物生焉者。固莫非自然之理。而苟求其主宰运用之妙。则又非理之一字所可尽也。故曰以主宰谓之帝。以妙用谓之神。以性情谓之乾。今若以天之一字。便唤作理。则理本无情意动作。又安有妙用性情之可言耶。然而朱子所以专属之理一边者。必有其说。可得闻欤。
臣对曰。李文纯天命图说。有曰天即理也。即朱子楚辞注之说也。盖曰天曰帝曰性曰衷。谓之理则一也。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7L 页
 而天也帝也。即其主张造化底理。故能赋性于万物。降衷于下民。在天之理。即在人在物之理。在人在物之理。即在天之理。彼此上下。一理无间。而惟其天与物对言。故曰赋。帝与民互举。故曰降。今若于上面著理字。下面著理字。就其中便下来赋字降字。而曰理赋理理降理云尔。则其与天赋性帝降衷之说。语意得失。不亦相去之远乎。盖尝论之。天地之间。有理有气。才有理便有气眹焉。才有气便有理主焉。所谓理者四德是也。所谓气者五行是也。此天之所以有主宰妙用性情之称。而生人物之大本立焉。李文纯所以于天命圈左右。以理妙气凝四字著了者也。然朱子之必以这个天字。专属之理一边者。抑有以焉。子思所谓天命之理。已是就理气妙合之中。独指其无极之理。以明其纯善无杂之体。则推明乎这个理所从出之天。而其可不直就理一边说去乎。且其二气纷纭屈伸变化。而四时行百物生者。理之乘气而运用者。以人乘马。固当主人。故朱子曰先有个天理了却有气。气积为质而性具焉。观于此亦可见专主理字底义也。
而天也帝也。即其主张造化底理。故能赋性于万物。降衷于下民。在天之理。即在人在物之理。在人在物之理。即在天之理。彼此上下。一理无间。而惟其天与物对言。故曰赋。帝与民互举。故曰降。今若于上面著理字。下面著理字。就其中便下来赋字降字。而曰理赋理理降理云尔。则其与天赋性帝降衷之说。语意得失。不亦相去之远乎。盖尝论之。天地之间。有理有气。才有理便有气眹焉。才有气便有理主焉。所谓理者四德是也。所谓气者五行是也。此天之所以有主宰妙用性情之称。而生人物之大本立焉。李文纯所以于天命圈左右。以理妙气凝四字著了者也。然朱子之必以这个天字。专属之理一边者。抑有以焉。子思所谓天命之理。已是就理气妙合之中。独指其无极之理。以明其纯善无杂之体。则推明乎这个理所从出之天。而其可不直就理一边说去乎。且其二气纷纭屈伸变化。而四时行百物生者。理之乘气而运用者。以人乘马。固当主人。故朱子曰先有个天理了却有气。气积为质而性具焉。观于此亦可见专主理字底义也。御制条问曰。天命之性。朱子以为兼人物而言。然则人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8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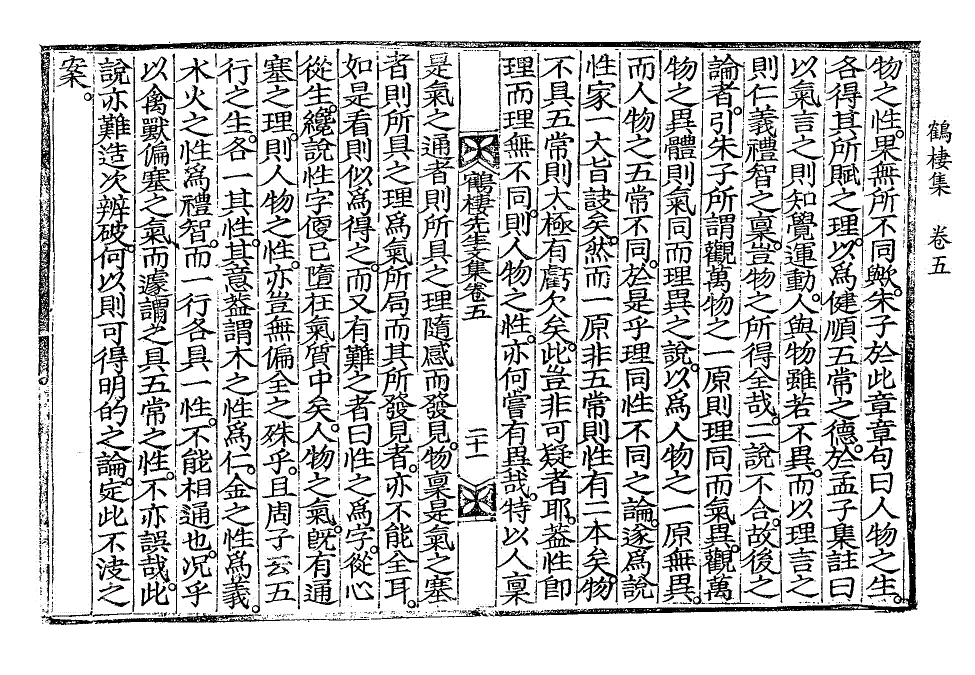 物之性。果无所不同欤。朱子于此章章句曰人物之生。各得其所赋之理。以为健顺五常之德。于孟子集注曰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。人与物虽若不异。而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。岂物之所得全哉。二说不合。故后之论者。引朱子所谓观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同而理异之说。以为人物之一原无异。而人物之五常不同。于是乎理同性不同之论。遂为说性家一大旨诀矣。然而一原非五常则性有二本矣。物不具五常则太极有亏欠矣。此岂非可疑者耶。盖性即理而理无不同。则人物之性。亦何尝有异哉。特以人禀是气之通者则所具之理随感而发见。物禀是气之塞者则所具之理为气所局而其所发见者。亦不能全耳。如是看则似为得之。而又有难之者曰性之为字。从心从生。才说性字便已堕在气质中矣。人物之气。既有通塞之理。则人物之性。亦岂无偏全之殊乎。且周子云五行之生。各一其性。其意盖谓木之性为仁。金之性为义。水火之性为礼智。而一行各具一性。不能相通也。况乎以禽兽偏塞之气而遽谓之具五常之性。不亦误哉。此说亦难造次辨破。何以则可得明的之论。定此不决之案。
物之性。果无所不同欤。朱子于此章章句曰人物之生。各得其所赋之理。以为健顺五常之德。于孟子集注曰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。人与物虽若不异。而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。岂物之所得全哉。二说不合。故后之论者。引朱子所谓观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同而理异之说。以为人物之一原无异。而人物之五常不同。于是乎理同性不同之论。遂为说性家一大旨诀矣。然而一原非五常则性有二本矣。物不具五常则太极有亏欠矣。此岂非可疑者耶。盖性即理而理无不同。则人物之性。亦何尝有异哉。特以人禀是气之通者则所具之理随感而发见。物禀是气之塞者则所具之理为气所局而其所发见者。亦不能全耳。如是看则似为得之。而又有难之者曰性之为字。从心从生。才说性字便已堕在气质中矣。人物之气。既有通塞之理。则人物之性。亦岂无偏全之殊乎。且周子云五行之生。各一其性。其意盖谓木之性为仁。金之性为义。水火之性为礼智。而一行各具一性。不能相通也。况乎以禽兽偏塞之气而遽谓之具五常之性。不亦误哉。此说亦难造次辨破。何以则可得明的之论。定此不决之案。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8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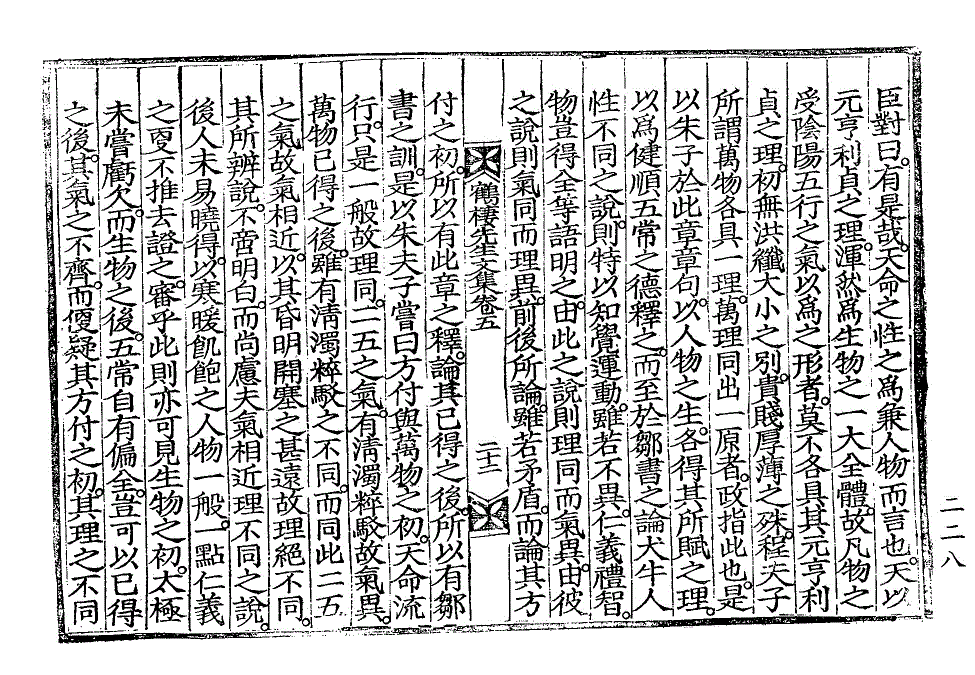 臣对曰。有是哉。天命之性之为兼人物而言也。天以元亨利贞之理。浑然为生物之一大全体。故凡物之受阴阳五行之气以为之形者。莫不各具其元亨利贞之理。初无洪纤大小之别。贵贱厚薄之殊。程夫子所谓万物各具一理。万理同出一原者。政指此也。是以朱子于此章章句。以人物之生。各得其所赋之理。以为健顺五常之德释之。而至于邹书之论犬牛人性不同之说。则特以知觉运动。虽若不异。仁义礼智。物岂得全等语明之。由此之说则理同而气异。由彼之说则气同而理异。前后所论。虽若矛盾。而论其方付之初。所以有此章之释。论其已得之后。所以有邹书之训。是以朱夫子尝曰方付与万物之初。天命流行。只是一般故理同。二五之气。有清浊粹驳故气异。万物已得之后。虽有清浊粹驳之不同。而同此二五之气故气相近。以其昏明开塞之甚远故理绝不同。其所辨说。不啻明白。而尚虑夫气相近理不同之说。后人未易晓得。以寒暖饥饱之人物一般。一点仁义之更不推去證之。审乎此则亦可见生物之初。太极未尝亏欠。而生物之后。五常自有偏全。岂可以已得之后。其气之不齐。而便疑其方付之初。其理之不同
臣对曰。有是哉。天命之性之为兼人物而言也。天以元亨利贞之理。浑然为生物之一大全体。故凡物之受阴阳五行之气以为之形者。莫不各具其元亨利贞之理。初无洪纤大小之别。贵贱厚薄之殊。程夫子所谓万物各具一理。万理同出一原者。政指此也。是以朱子于此章章句。以人物之生。各得其所赋之理。以为健顺五常之德释之。而至于邹书之论犬牛人性不同之说。则特以知觉运动。虽若不异。仁义礼智。物岂得全等语明之。由此之说则理同而气异。由彼之说则气同而理异。前后所论。虽若矛盾。而论其方付之初。所以有此章之释。论其已得之后。所以有邹书之训。是以朱夫子尝曰方付与万物之初。天命流行。只是一般故理同。二五之气。有清浊粹驳故气异。万物已得之后。虽有清浊粹驳之不同。而同此二五之气故气相近。以其昏明开塞之甚远故理绝不同。其所辨说。不啻明白。而尚虑夫气相近理不同之说。后人未易晓得。以寒暖饥饱之人物一般。一点仁义之更不推去證之。审乎此则亦可见生物之初。太极未尝亏欠。而生物之后。五常自有偏全。岂可以已得之后。其气之不齐。而便疑其方付之初。其理之不同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9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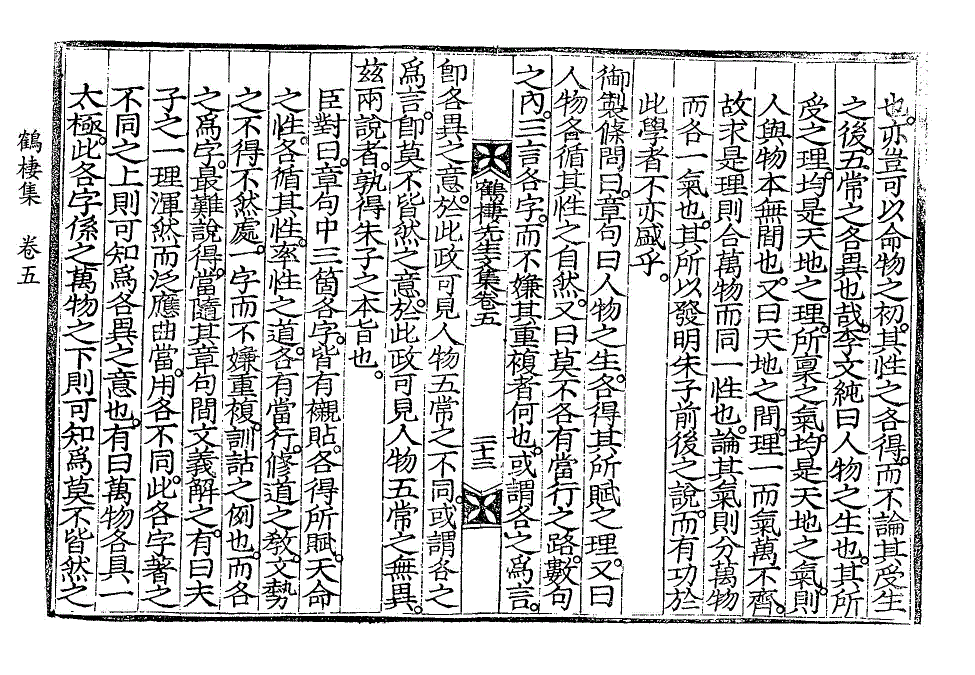 也。亦岂可以命物之初。其性之各得。而不论其受生之后。五常之各异也哉。李文纯曰人物之生也。其所受之理。均是天地之理。所禀之气。均是天地之气。则人与物本无间也。又曰天地之间。理一而气万不齐。故求是理则合万物而同一性也。论其气则分万物而各一气也。其所以发明朱子前后之说。而有功于此学者不亦盛乎。
也。亦岂可以命物之初。其性之各得。而不论其受生之后。五常之各异也哉。李文纯曰人物之生也。其所受之理。均是天地之理。所禀之气。均是天地之气。则人与物本无间也。又曰天地之间。理一而气万不齐。故求是理则合万物而同一性也。论其气则分万物而各一气也。其所以发明朱子前后之说。而有功于此学者不亦盛乎。御制条问曰。章句曰人物之生。各得其所赋之理。又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。又曰莫不各有当行之路。数句之内。三言各字。而不嫌其重复者何也。或谓各之为言。即各异之意。于此政可见人物五常之不同。或谓各之为言。即莫不皆然之意。于此政可见人物五常之无异。玆两说者。孰得朱子之本旨也。
臣对曰。章句中三个各字。皆有衬贴。各得所赋。天命之性。各循其性。率性之道。各有当行。修道之教。文势之不得不然处。一字而不嫌重复。训诂之例也。而各之为字。最难说得。当随其章句间文义解之。有曰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。用各不同。此各字著之不同之上则可知为各异之意也。有曰万物各具一太极。此各字系之万物之下则可知为莫不皆然之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2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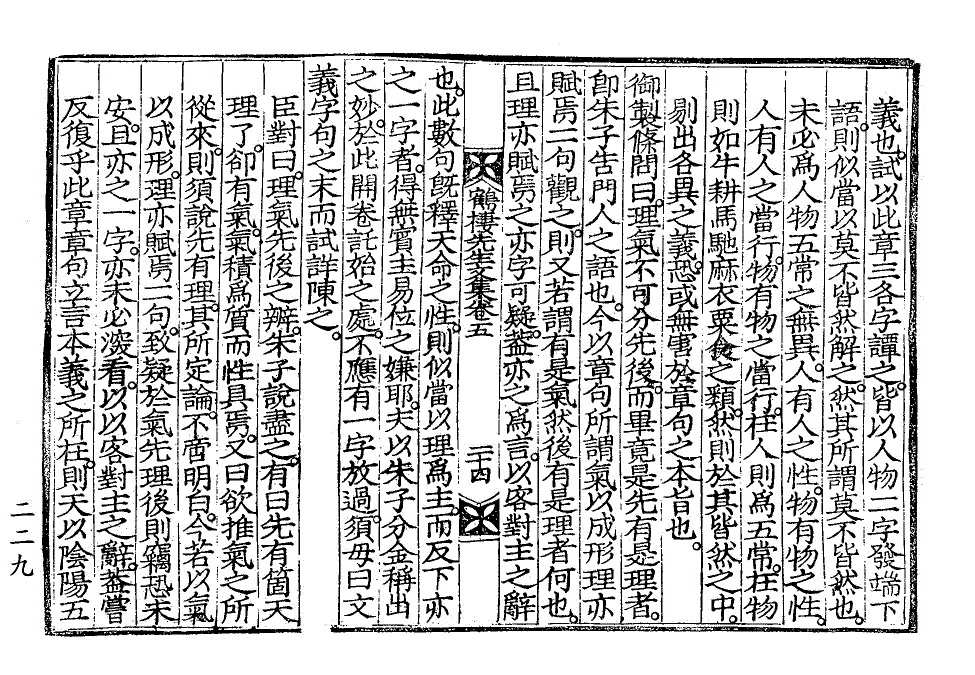 义也。试以此章三各字谭之。皆以人物二字发端下语。则似当以莫不皆然解之。然其所谓莫不皆然也。未必为人物五常之无异。人有人之性。物有物之性。人有人之当行。物有物之当行。在人则为五常。在物则如牛耕马驰麻衣粟食之类。然则于其皆然之中。剔出各异之义。恐或无害于章句之本旨也。
义也。试以此章三各字谭之。皆以人物二字发端下语。则似当以莫不皆然解之。然其所谓莫不皆然也。未必为人物五常之无异。人有人之性。物有物之性。人有人之当行。物有物之当行。在人则为五常。在物则如牛耕马驰麻衣粟食之类。然则于其皆然之中。剔出各异之义。恐或无害于章句之本旨也。御制条问曰。理气不可分先后。而毕竟是先有是理者。即朱子告门人之语也。今以章句所谓气以成形理亦赋焉二句观之。则又若谓有是气然后有是理者何也。且理亦赋焉之亦字可疑。盖亦之为言。以客对主之辞也。此数句既释天命之性。则似当以理为主。而反下亦之一字者。得无宾主易位之嫌耶。夫以朱子分金称出之妙。于此开卷托始之处。不应有一字放过。须毋曰文义字句之末而试详陈之。
臣对曰。理气先后之辨。朱子说尽之。有曰先有个天理了。却有气。气积为质而性具焉。又曰欲推气之所从来。则须说先有理。其所定论。不啻明白。今若以气以成形。理亦赋焉二句。致疑于气先理后则窃恐未安。且亦之一字。亦未必深看。以以客对主之辞。盖尝反复乎此章章句立言本义之所在。则天以阴阳五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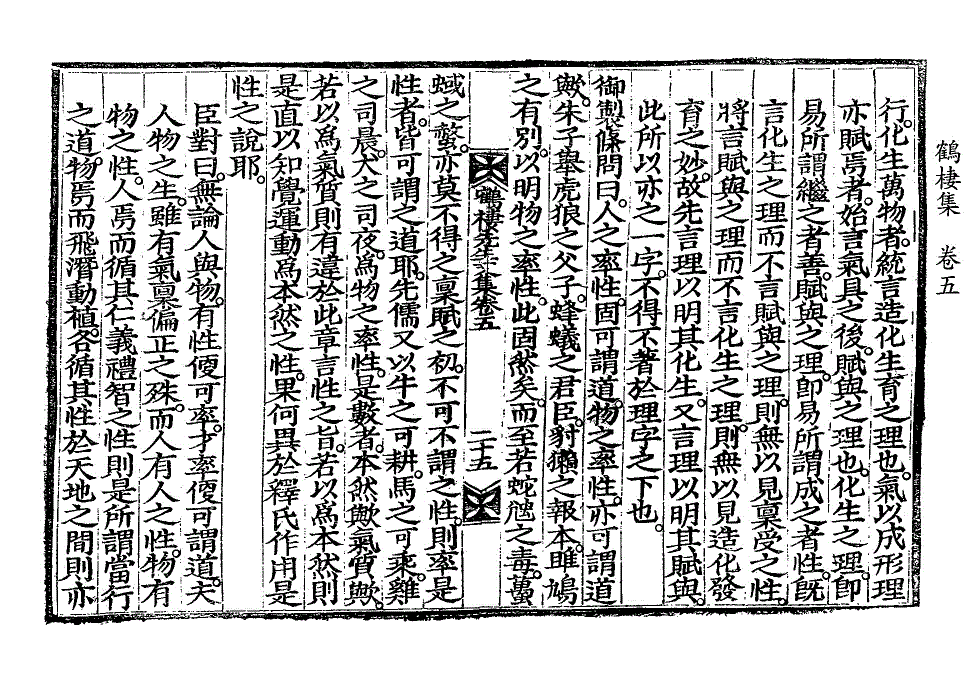 行。化生万物者。统言造化生育之理也。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者。始言气具之后。赋与之理也。化生之理。即易所谓继之者善。赋与之理。即易所谓成之者性。既言化生之理而不言赋与之理。则无以见禀受之性。将言赋与之理而不言化生之理。则无以见造化发育之妙。故先言理以明其化生。又言理以明其赋与。此所以亦之一字。不得不著于理字之下也。
行。化生万物者。统言造化生育之理也。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者。始言气具之后。赋与之理也。化生之理。即易所谓继之者善。赋与之理。即易所谓成之者性。既言化生之理而不言赋与之理。则无以见禀受之性。将言赋与之理而不言化生之理。则无以见造化发育之妙。故先言理以明其化生。又言理以明其赋与。此所以亦之一字。不得不著于理字之下也。御制条问曰。人之率性。固可谓道。物之率性。亦可谓道欤。朱子举虎狼之父子。蜂蚁之君臣。豺獭之报本。雎鸠之有别。以明物之率性。此固然矣。而至若蛇虺之毒。虿蜮之螫。亦莫不得之禀赋之初。不可不谓之性。则率是性者。皆可谓之道耶。先儒又以牛之可耕。马之可乘。鸡之司晨。犬之司夜。为物之率性。是数者。本然欤气质欤。若以为气质则有违于此章言性之旨。若以为本然则是直以知觉运动为本然之性。果何异于释氏作用是性之说耶。
臣对曰。无论人与物。有性便可率。才率便可谓道。夫人物之生。虽有气禀偏正之殊。而人有人之性。物有物之性。人焉而循其仁义礼智之性则是所谓当行之道。物焉而飞潜动植。各循其性于天地之间则亦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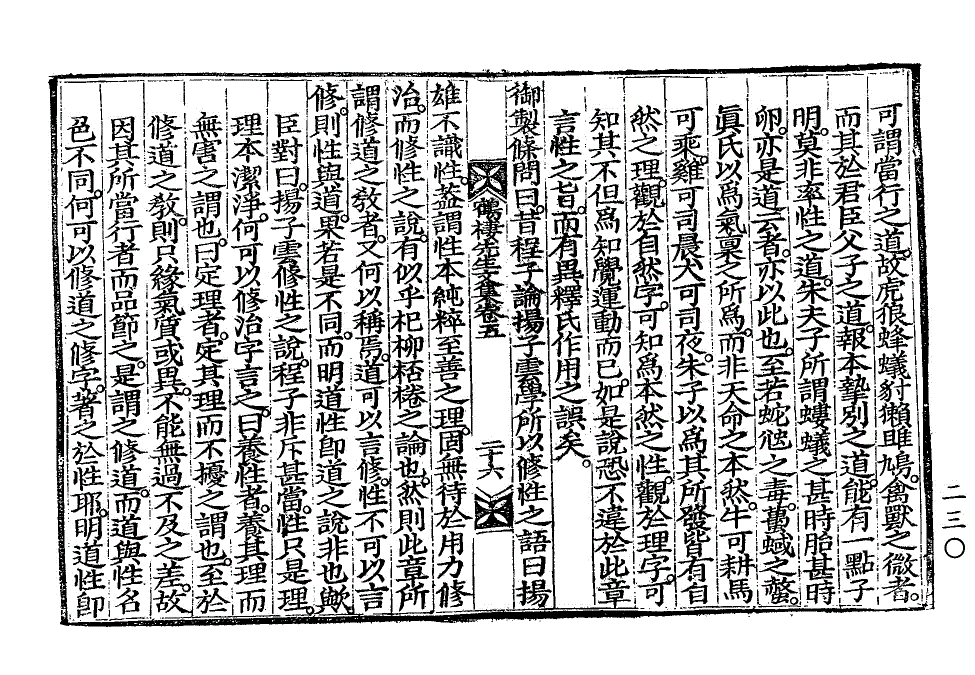 可谓当行之道。故虎狼蜂蚁豺獭雎鸠。禽兽之微者。而其于君臣父子之道。报本挚别之道。能有一点子明。莫非率性之道。朱夫子所谓蝼蚁之甚时胎甚时卵。亦是道云者。亦以此也。至若蛇虺之毒。虿蜮之螫。真氏以为气禀之所为。而非天命之本然。牛可耕马可乘。鸡可司晨犬可司夜。朱子以为其所发皆有自然之理。观于自然字。可知为本然之性。观于理字。可知其不但为知觉运动而已。如是说恐不违于此章言性之旨。而有异释氏作用之误矣。
可谓当行之道。故虎狼蜂蚁豺獭雎鸠。禽兽之微者。而其于君臣父子之道。报本挚别之道。能有一点子明。莫非率性之道。朱夫子所谓蝼蚁之甚时胎甚时卵。亦是道云者。亦以此也。至若蛇虺之毒。虿蜮之螫。真氏以为气禀之所为。而非天命之本然。牛可耕马可乘。鸡可司晨犬可司夜。朱子以为其所发皆有自然之理。观于自然字。可知为本然之性。观于理字。可知其不但为知觉运动而已。如是说恐不违于此章言性之旨。而有异释氏作用之误矣。御制条问曰。昔程子论扬子云学所以修性之语曰扬雄不识性。盖谓性本纯粹至善之理。固无待于用力修治。而修性之说。有似乎杞柳杯棬之论也。然则此章所谓修道之教者。又何以称焉。道可以言修。性不可以言修。则性与道。果若是不同。而明道性即道之说非也欤。
臣对曰。扬子云修性之说。程子非斥甚当。性只是理。理本洁净。何可以修治字言之。曰养性者。养其理而无害之谓也。曰定理者。定其理而不扰之谓也。至于修道之教。则只缘气质或异。不能无过不及之差。故因其所当行者而品节之。是谓之修道。而道与性名色不同。何可以修道之修字。著之于性耶。明道性即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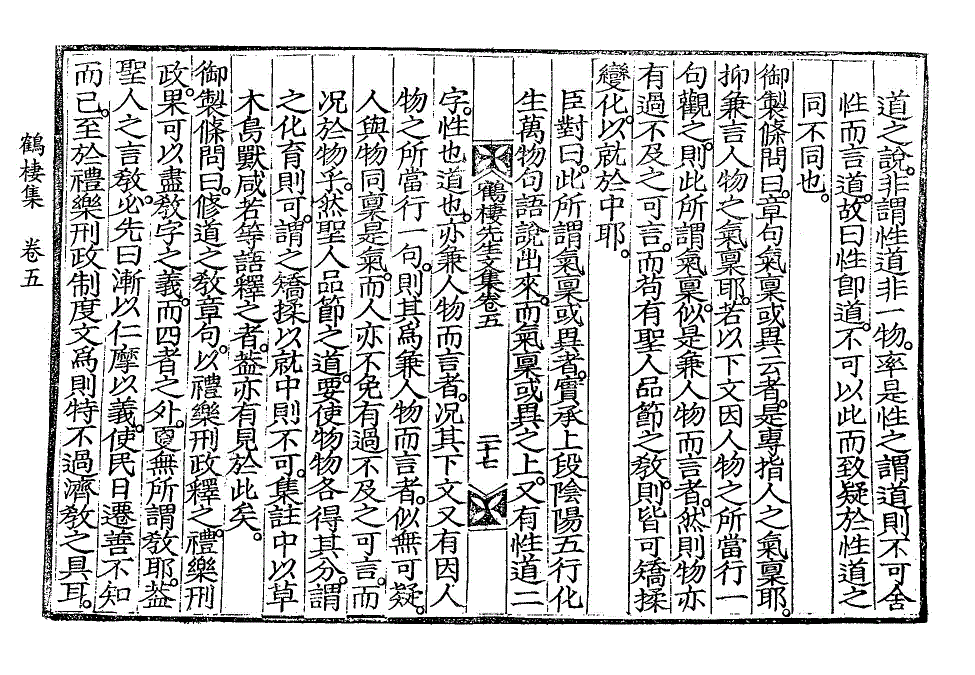 道之说。非谓性道非一物。率是性之谓道则不可舍性而言道。故曰性即道。不可以此而致疑于性道之同不同也。
道之说。非谓性道非一物。率是性之谓道则不可舍性而言道。故曰性即道。不可以此而致疑于性道之同不同也。御制条问曰。章句气禀或异云者。是专指人之气禀耶。抑兼言人物之气禀耶。若以下文因人物之所当行一句观之。则此所谓气禀。似是兼人物而言者。然则物亦有过不及之可言。而苟有圣人品节之教。则皆可矫揉变化。以就于中耶。
臣对曰。此所谓气禀或异者。实承上段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句语说出来。而气禀或异之上。又有性道二字。性也道也。亦兼人物而言者。况其下文又有因人物之所当行一句。则其为兼人物而言者。似无可疑。人与物同禀是气。而人亦不免有过不及之可言。而况于物乎。然圣人品节之道。要使物物各得其分。谓之化育则可。谓之矫揉以就中则不可。集注中以草木鸟兽咸若等语释之者。盖亦有见于此矣。
御制条问曰。修道之教章句。以礼乐刑政释之。礼乐刑政。果可以尽教字之义。而四者之外。更无所谓教耶。盖圣人之言教。必先曰渐以仁摩以义。使民日迁善不知而已。至于礼乐刑政制度文为则特不过济教之具耳。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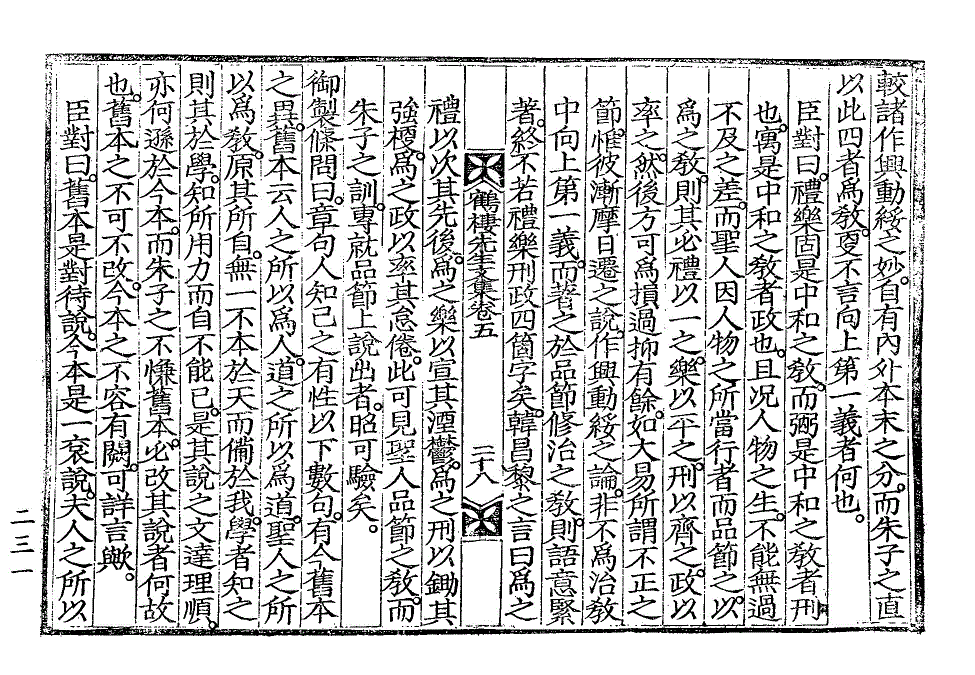 较诸作兴动绥之妙。自有内外本末之分。而朱子之直以此四者为教。更不言向上第一义者何也。
较诸作兴动绥之妙。自有内外本末之分。而朱子之直以此四者为教。更不言向上第一义者何也。臣对曰。礼乐固是中和之教。而弼是中和之教者刑也。寓是中和之教者政也。且况人物之生。不能无过不及之差。而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。以为之教。则其必礼以一之。乐以平之。刑以齐之。政以率之。然后方可为损过抑有馀。如大易所谓不正之节。惟彼渐摩日迁之说。作兴动绥之论。非不为治教中向上第一义。而著之于品节修治之教。则语意紧著。终不若礼乐刑政四个字矣。韩昌黎之言曰为之礼以次其先后。为之乐以宣其湮郁。为之刑以锄其强梗。为之政以率其怠倦。此可见圣人品节之教。而朱子之训。专就品节上说出者。昭可验矣。
御制条问曰。章句人知己之有性以下数句。有今旧本之异。旧本云人之所以为人。道之所以为道。圣人之所以为教。原其所自。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。学者知之则其于学。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。是其说之文达理顺。亦何逊于今本。而朱子之不慊旧本。必改其说者何故也。旧本之不可不改。今本之不容有阙。可详言欤。
臣对曰。旧本是对待说。今本是一衮说。夫人之所以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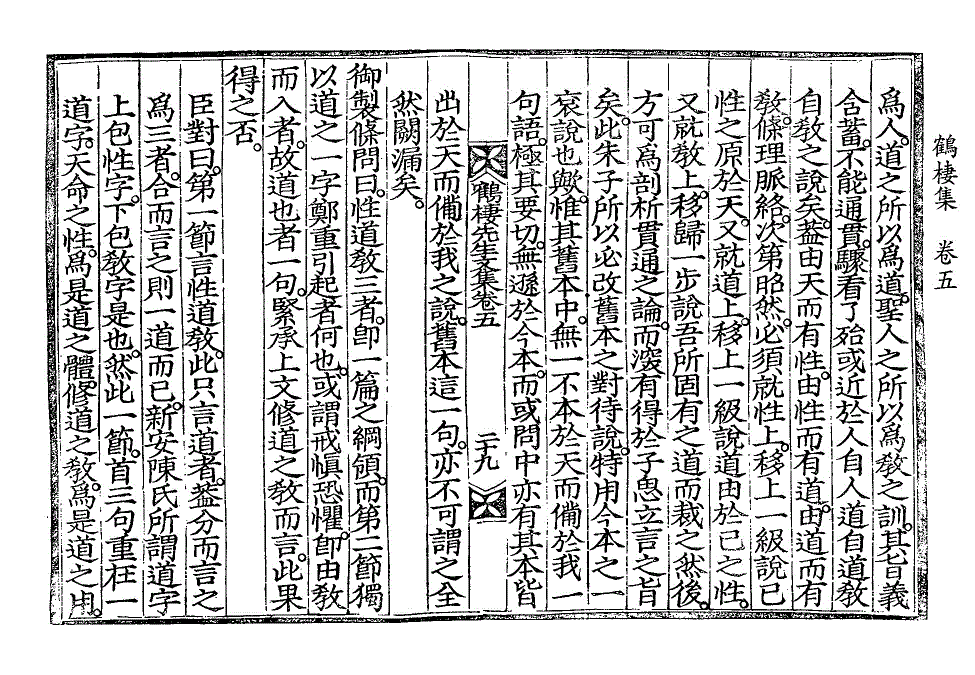 为人。道之所以为道。圣人之所以为教之训。其旨义含蓄。不能通贯。骤看了殆或近于人自人道自道教自教之说矣。盖由天而有性。由性而有道。由道而有教。条理脉络。次第昭然。必须就性上。移上一级说己性之原于天。又就道上。移上一级说道由于己之性。又就教上。移归一步说吾所固有之道而裁之然后。方可为剖析贯通之论。而深有得于子思立言之旨矣。此朱子所以必改旧本之对待说。特用今本之一衮说也欤。惟其旧本中。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一句语。极其要切。无逊于今本。而或问中亦有其本皆出于天而备于我之说。旧本这一句。亦不可谓之全然阙漏矣。
为人。道之所以为道。圣人之所以为教之训。其旨义含蓄。不能通贯。骤看了殆或近于人自人道自道教自教之说矣。盖由天而有性。由性而有道。由道而有教。条理脉络。次第昭然。必须就性上。移上一级说己性之原于天。又就道上。移上一级说道由于己之性。又就教上。移归一步说吾所固有之道而裁之然后。方可为剖析贯通之论。而深有得于子思立言之旨矣。此朱子所以必改旧本之对待说。特用今本之一衮说也欤。惟其旧本中。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一句语。极其要切。无逊于今本。而或问中亦有其本皆出于天而备于我之说。旧本这一句。亦不可谓之全然阙漏矣。御制条问曰。性道教三者。即一篇之纲领。而第二节独以道之一字郑重引起者何也。或谓戒慎恐惧。即由教而入者。故道也者一句。紧承上文修道之教而言。此果得之否。
臣对曰。第一节言性道教。此只言道者。盖分而言之为三者。合而言之则一道而已。新安陈氏所谓道字上包性字。下包教字是也。然此一节。首三句重在一道字。天命之性。为是道之体。修道之教。为是道之用。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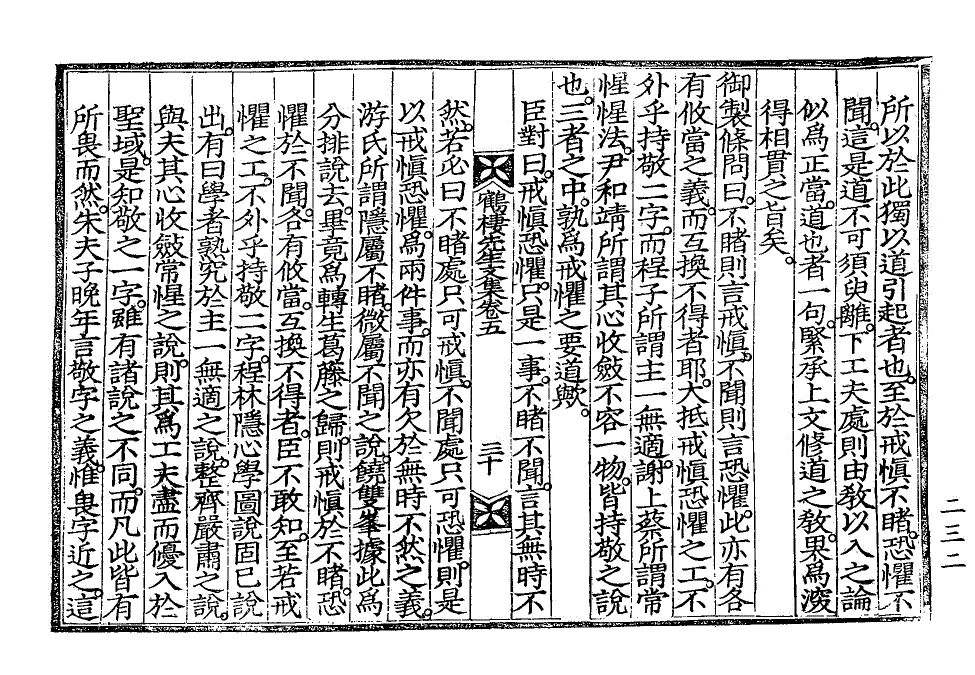 所以于此独以道引起者也。至于戒慎不睹。恐惧不闻。这是道不可须臾离。下工夫处则由教以入之论似为正当。道也者一句。紧承上文修道之教。果为深得相贯之旨矣。
所以于此独以道引起者也。至于戒慎不睹。恐惧不闻。这是道不可须臾离。下工夫处则由教以入之论似为正当。道也者一句。紧承上文修道之教。果为深得相贯之旨矣。御制条问曰。不睹则言戒慎。不闻则言恐惧。此亦有各有攸当之义。而互换不得者耶。大抵戒慎恐惧之工。不外乎持敬二字。而程子所谓主一无适。谢上蔡所谓常惺惺法。尹和靖所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。皆持敬之说也。三者之中。孰为戒惧之要道欤。
臣对曰。戒慎恐惧。只是一事。不睹不闻。言其无时不然。若必曰不睹处只可戒慎。不闻处只可恐惧。则是以戒慎恐惧。为两件事。而亦有欠于无时不然之义。游氏所谓隐属不睹。微属不闻之说。饶双峰据此为分排说去。毕竟为转生葛藤之归。则戒慎于不睹。恐惧于不闻。各有攸当。互换不得者。臣不敢知。至若戒惧之工。不外乎持敬二字。程林隐心学图说固已说出。有曰学者熟究于主一无适之说。整齐严肃之说。与夫其心收敛常惺之说。则其为工夫尽而优入于圣域。是知敬之一字。虽有诸说之不同。而凡此皆有所畏而然。朱夫子晚年言敬字之义。惟畏字近之。这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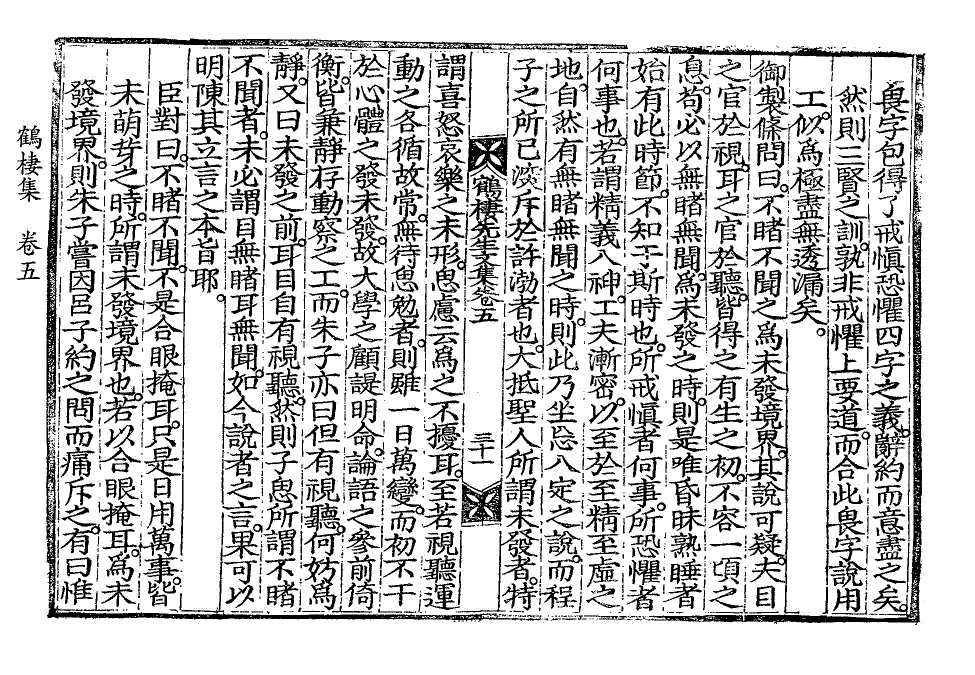 畏字包得了戒慎恐惧四字之义。辞约而意尽之矣。然则三贤之训。孰非戒惧上要道。而合此畏字说用工。似为极尽无透漏矣。
畏字包得了戒慎恐惧四字之义。辞约而意尽之矣。然则三贤之训。孰非戒惧上要道。而合此畏字说用工。似为极尽无透漏矣。御制条问曰。不睹不闻之为未发境界。其说可疑。夫目之官于视。耳之官于听。皆得之有生之初。不容一顷之息。苟必以无睹无闻。为未发之时。则是唯昏昧熟睡者始有此时节。不知于斯时也。所戒慎者何事。所恐惧者何事也。若谓精义入神。工夫渐密。以至于至精至虚之地。自然有无睹无闻之时。则此乃坐忘入定之说。而程子之所已深斥于许渤者也。大抵圣人所谓未发者。特谓喜怒哀乐之未形。思虑云为之不扰耳。至若视听运动之各循故常。无待思勉者。则虽一日万变。而初不干于心体之发未发。故大学之顾諟明命。论语之参前倚衡。皆兼静存动察之工。而朱子亦曰但有视听。何妨为静。又曰未发之前。耳目自有视听。然则子思所谓不睹不闻者。未必谓目无睹耳无闻。如今说者之言。果可以明陈其立言之本旨耶。
臣对曰。不睹不闻。不是合眼掩耳。只是日用万事。皆未萌芽之时。所谓未发境界也。若以合眼掩耳。为未发境界。则朱子尝因吕子约之问而痛斥之。有曰惟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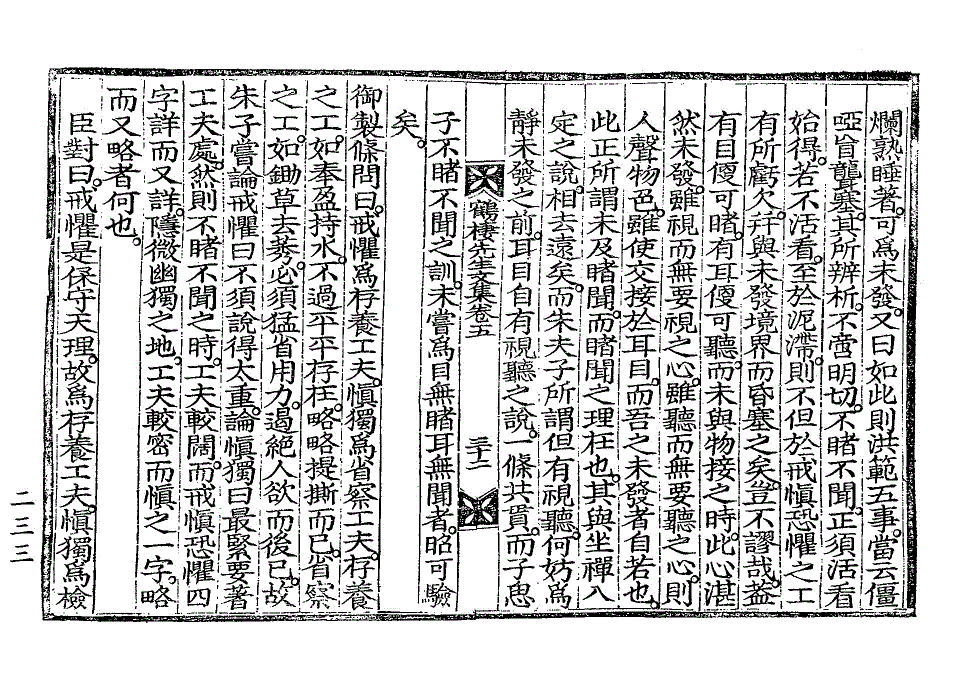 烂熟睡著。可为未发。又曰如此则洪范五事。当云僵哑盲聋塞。其所辨析。不啻明切。不睹不闻。正须活看始得。若不活看。至于泥滞。则不但于戒慎恐惧之工有所亏欠。并与未发境界而昏塞之矣。岂不谬哉。盖有目便可睹。有耳便可听。而未与物接之时。此心湛然未发。虽视而无要视之心。虽听而无要听之心。则人声物色。虽使交接于耳目。而吾之未发者自若也。此正所谓未及睹闻。而睹闻之理在也。其与坐禅入定之说。相去远矣。而朱夫子所谓但有视听。何妨为静未发之前。耳目自有视听之说。一条共贯。而子思子不睹不闻之训。未尝为目无睹耳无闻者。昭可验矣。
烂熟睡著。可为未发。又曰如此则洪范五事。当云僵哑盲聋塞。其所辨析。不啻明切。不睹不闻。正须活看始得。若不活看。至于泥滞。则不但于戒慎恐惧之工有所亏欠。并与未发境界而昏塞之矣。岂不谬哉。盖有目便可睹。有耳便可听。而未与物接之时。此心湛然未发。虽视而无要视之心。虽听而无要听之心。则人声物色。虽使交接于耳目。而吾之未发者自若也。此正所谓未及睹闻。而睹闻之理在也。其与坐禅入定之说。相去远矣。而朱夫子所谓但有视听。何妨为静未发之前。耳目自有视听之说。一条共贯。而子思子不睹不闻之训。未尝为目无睹耳无闻者。昭可验矣。御制条问曰。戒惧为存养工夫。慎独为省察工夫。存养之工。如奉盈持水。不过平平存在。略略提撕而已。省察之工。如锄草去莠。必须猛省用力。遏绝人欲而后已。故朱子尝论戒惧曰不须说得太重。论慎独曰最紧要著工夫处。然则不睹不闻之时。工夫较阔。而戒慎恐惧四字详而又详。隐微幽独之地。工夫较密而慎之一字。略而又略者何也。
臣对曰。戒惧是保守天理。故为存养工夫。慎独为检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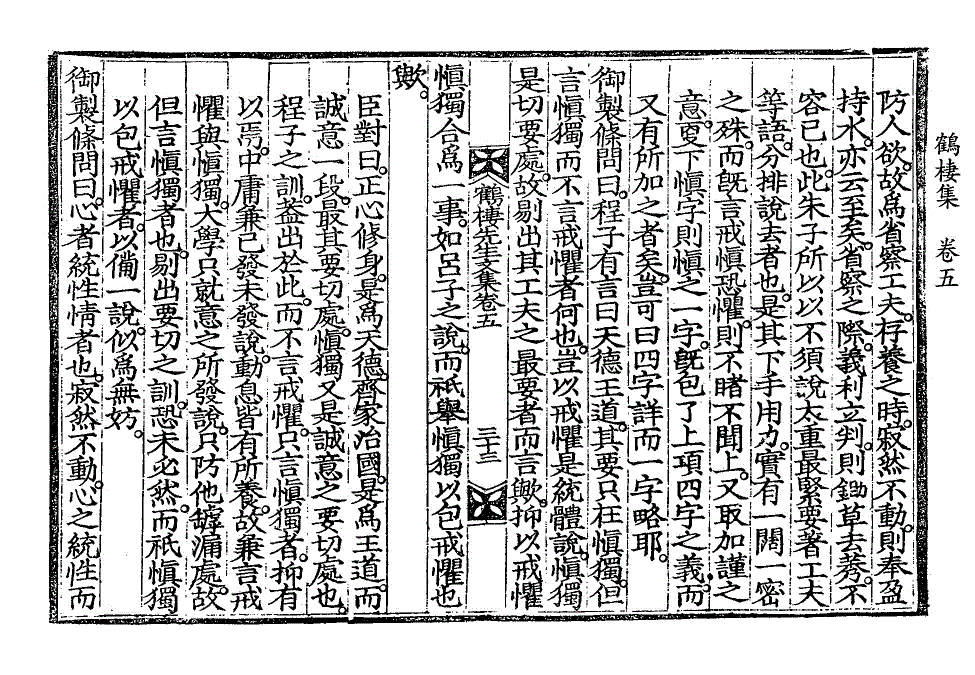 防人欲。故为省察工夫。存养之时。寂然不动。则奉盈持水。亦云至矣。省察之际。义利立判。则锄草去莠。不容已也。此朱子所以以不须说太重最紧要著工夫等语。分排说去者也。是其下手用力。实有一阔一密之殊。而既言戒慎恐惧。则不睹不闻上。又取加谨之意。更下慎字则慎之一字。既包了上项四字之义。而又有所加之者矣。岂可曰四字详而一字略耶。
防人欲。故为省察工夫。存养之时。寂然不动。则奉盈持水。亦云至矣。省察之际。义利立判。则锄草去莠。不容已也。此朱子所以以不须说太重最紧要著工夫等语。分排说去者也。是其下手用力。实有一阔一密之殊。而既言戒慎恐惧。则不睹不闻上。又取加谨之意。更下慎字则慎之一字。既包了上项四字之义。而又有所加之者矣。岂可曰四字详而一字略耶。御制条问曰。程子有言曰天德王道。其要只在慎独。但言慎独而不言戒惧者何也。岂以戒惧是统体说。慎独是切要处。故剔出其工夫之最要者而言欤。抑以戒惧慎独合为一事。如吕子之说。而祇举慎独以包戒惧也欤。
臣对曰。正心修身。是为天德。齐家治国。是为王道。而诚意一段。最其要切处。慎独又是诚意之要切处也。程子之训。盖出于此。而不言戒惧。只言慎独者。抑有以焉。中庸兼已发未发说。动息皆有所养。故兼言戒惧与慎独。大学只就意之所发说。只防他罅漏处。故但言慎独者也。剔出要切之训。恐未必然。而祇慎独以包戒惧者。以备一说。似为无妨。
御制条问曰。心者统性情者也。寂然不动。心之统性而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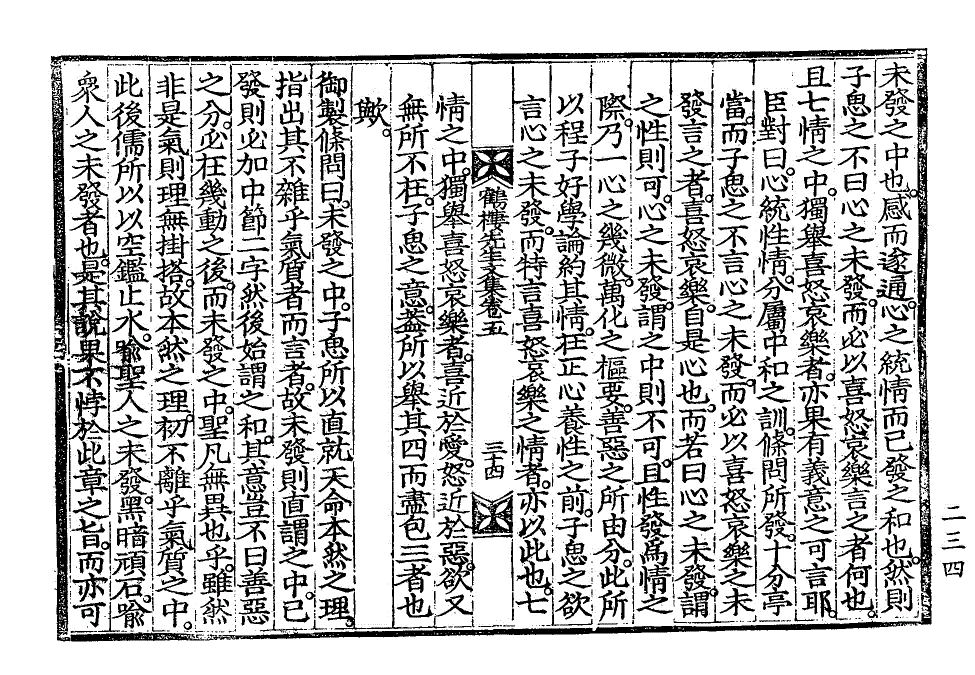 未发之中也。感而遂通。心之统情而已发之和也。然则子思之不曰心之未发。而必以喜怒哀乐言之者何也。且七情之中。独举喜怒哀乐者。亦果有义意之可言耶。
未发之中也。感而遂通。心之统情而已发之和也。然则子思之不曰心之未发。而必以喜怒哀乐言之者何也。且七情之中。独举喜怒哀乐者。亦果有义意之可言耶。臣对曰。心统性情。分属中和之训。条问所发。十分亭当。而子思之不言心之未发。而必以喜怒哀乐之未发言之者。喜怒哀乐。自是心也。而若曰心之未发。谓之性则可。心之未发。谓之中则不可。且性发为情之际。乃一心之几微。万化之枢要。善恶之所由分。此所以程子好学论约其情。在正心养性之前。子思之欲言心之未发。而特言喜怒哀乐之情者。亦以此也。七情之中。独举喜怒哀乐者。喜近于爱。怒近于恶。欲又无所不在。子思之意。盖所以举其四而尽包三者也欤。
御制条问曰。未发之中。子思所以直就天命本然之理。指出其不杂乎气质者而言者。故未发则直谓之中。已发则必加中节二字然后始谓之和。其意岂不曰善恶之分。必在几动之后。而未发之中。圣凡无异也乎。虽然非是气则理无挂搭。故本然之理。初不离乎气质之中。此后儒所以以空鉴止水。喻圣人之未发。黑暗顽石。喻众人之未发者也。是其说果不悖于此章之旨。而亦可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5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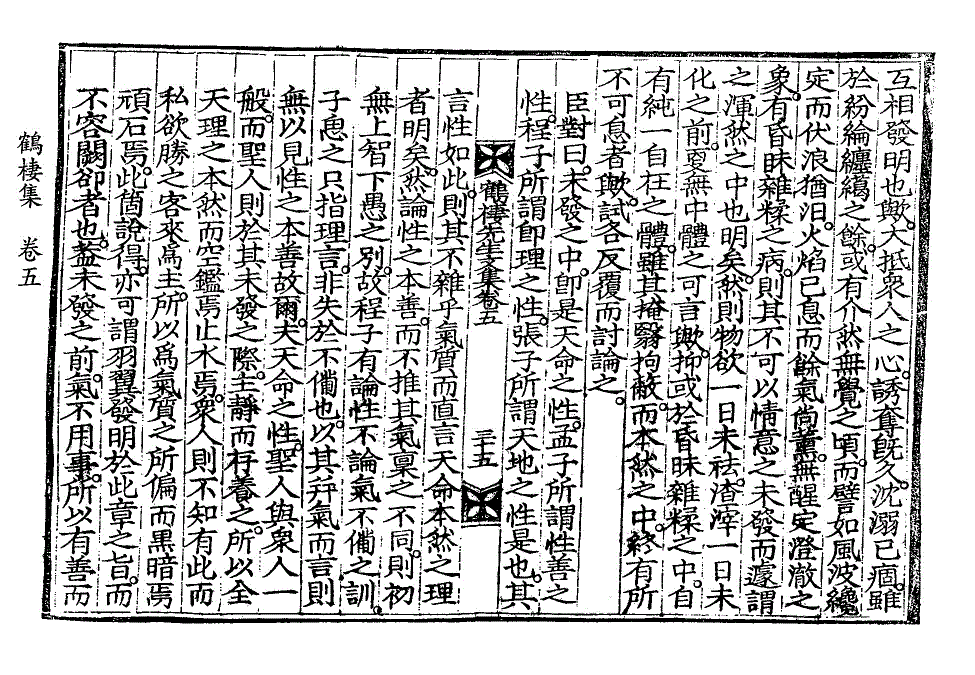 互相发明也欤。大抵众人之心。诱夺既久。沈溺已痼。虽于纷纶缠𦅶之馀。或有介然无觉之顷。而譬如风波才定而伏浪犹汩。火焰已息而馀气尚薰。无醒定澄澈之象。有昏眛杂糅之病。则其不可以情意之未发而遽谓之浑然之中也明矣。然则物欲一日未祛。渣滓一日未化之前。更无中体之可言欤。抑或于昏昧杂糅之中。自有纯一自在之体。虽其掩翳拘蔽。而本然之中。终有所不可息者欤。试各反覆而讨论之。
互相发明也欤。大抵众人之心。诱夺既久。沈溺已痼。虽于纷纶缠𦅶之馀。或有介然无觉之顷。而譬如风波才定而伏浪犹汩。火焰已息而馀气尚薰。无醒定澄澈之象。有昏眛杂糅之病。则其不可以情意之未发而遽谓之浑然之中也明矣。然则物欲一日未祛。渣滓一日未化之前。更无中体之可言欤。抑或于昏昧杂糅之中。自有纯一自在之体。虽其掩翳拘蔽。而本然之中。终有所不可息者欤。试各反覆而讨论之。臣对曰。未发之中。即是天命之性。孟子所谓性善之性。程子所谓即理之性。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。其言性如此。则其不杂乎气质而直言天命本然之理者明矣。然论性之本善。而不推其气禀之不同。则初无上智下愚之别。故程子有论性不论气不备之训。子思之只指理言。非失于不备也。以其并气而言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尔。夫天命之性。圣人与众人一般。而圣人则于其未发之际。主静而存养之。所以全天理之本然而空鉴焉止水焉。众人则不知有此而私欲胜之客来为主。所以为气质之所偏而黑暗焉顽石焉。此个说得。亦可谓羽翼发明于此章之旨。而不容阙却者也。盖未发之前。气不用事。所以有善而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5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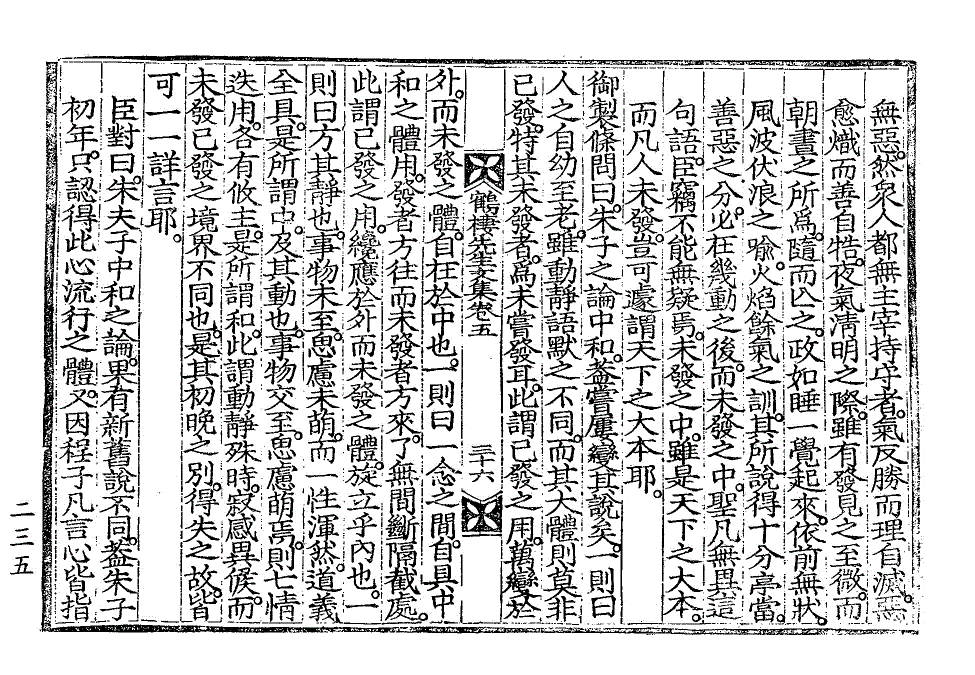 无恶。然众人都无主宰持守者。气反胜而理自灭。恶愈炽而善自牿。夜气清明之际。虽有发见之至微。而朝昼之所为。随而亡之。政如睡一觉起来。依前无状。风波伏浪之喻。火焰馀气之训。其所说得十分亭当。善恶之分。必在几动之后。而未发之中。圣凡无异这句语。臣窃不能无疑焉。未发之中。虽是天下之大本。而凡人未发。岂可遽谓天下之大本耶。
无恶。然众人都无主宰持守者。气反胜而理自灭。恶愈炽而善自牿。夜气清明之际。虽有发见之至微。而朝昼之所为。随而亡之。政如睡一觉起来。依前无状。风波伏浪之喻。火焰馀气之训。其所说得十分亭当。善恶之分。必在几动之后。而未发之中。圣凡无异这句语。臣窃不能无疑焉。未发之中。虽是天下之大本。而凡人未发。岂可遽谓天下之大本耶。御制条问曰。朱子之论中和。盖尝屡变其说矣。一则曰人之自幼至老。虽动静语默之不同。而其大体则莫非已发。特其未发者。为未尝发耳。此谓已发之用。万变于外。而未发之体。自在于中也。一则曰一念之间。自具中和之体用。发者方往而未发者方来。了无间断隔截处。此谓已发之用。才应于外而未发之体。旋立乎内也。一则曰方其静也。事物未至。思虑未萌。而一性浑然。道义全具。是所谓中。及其动也。事物交至。思虑萌焉。则七情迭用。各有攸主。是所谓和。此谓动静殊时。寂感异候。而未发已发之境界不同也。是其初晚之别。得失之故。皆可一一详言耶。
臣对曰。朱夫子中和之论。果有新旧说不同。盖朱子初年。只认得此心流行之体。又因程子凡言心皆指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6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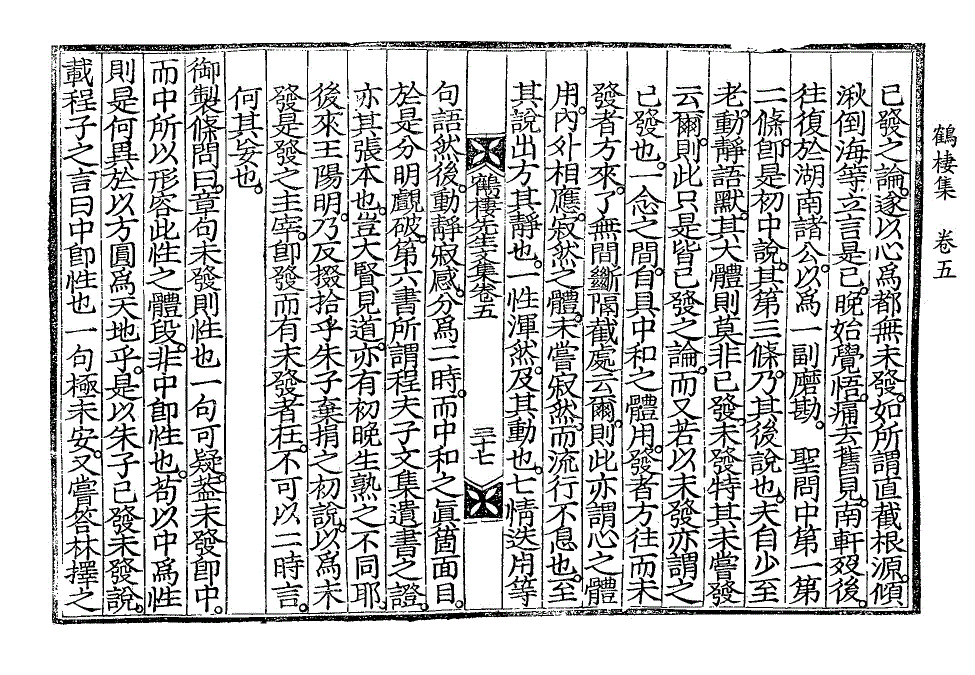 已发之论。遂以心为都无未发。如所谓直截根源。倾湫倒海等立言是已。晚始觉悟。痛去旧见。南轩殁后。往复于湖南诸公。以为一副磨勘。 圣问中第一第二条。即是初中说。其第三条。乃其后说也。夫自少至老。动静语默。其大体则莫非已发。未发特其未尝发云尔。则此只是皆已发之论。而又若以未发亦谓之已发也。一念之间。自具中和之体用。发者方往而未发者方来。了无间断隔截处云尔。则此亦谓心之体用。内外相应。寂然之体。未尝寂然。而流行不息也。至其说出方其静也。一性浑然。及其动也。七情迭用等句语然后。动静寂感。分为二时。而中和之真个面目。于是分明觑破。第六书所谓程夫子文集遗书之證。亦其张本也。岂大贤见道。亦有初晚生熟之不同耶。后来王阳明。乃反掇拾乎朱子弃捐之初说。以为未发是发之主宰。即发而有未发者在。不可以二时言。何其妄也。
已发之论。遂以心为都无未发。如所谓直截根源。倾湫倒海等立言是已。晚始觉悟。痛去旧见。南轩殁后。往复于湖南诸公。以为一副磨勘。 圣问中第一第二条。即是初中说。其第三条。乃其后说也。夫自少至老。动静语默。其大体则莫非已发。未发特其未尝发云尔。则此只是皆已发之论。而又若以未发亦谓之已发也。一念之间。自具中和之体用。发者方往而未发者方来。了无间断隔截处云尔。则此亦谓心之体用。内外相应。寂然之体。未尝寂然。而流行不息也。至其说出方其静也。一性浑然。及其动也。七情迭用等句语然后。动静寂感。分为二时。而中和之真个面目。于是分明觑破。第六书所谓程夫子文集遗书之證。亦其张本也。岂大贤见道。亦有初晚生熟之不同耶。后来王阳明。乃反掇拾乎朱子弃捐之初说。以为未发是发之主宰。即发而有未发者在。不可以二时言。何其妄也。御制条问曰。章句未发则性也一句可疑。盖未发即中。而中所以形容此性之体段。非中即性也。苟以中为性则是何异于以方圆为天地乎。是以朱子已发未发说。载程子之言曰中即性也一句极未安。又尝答林择之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6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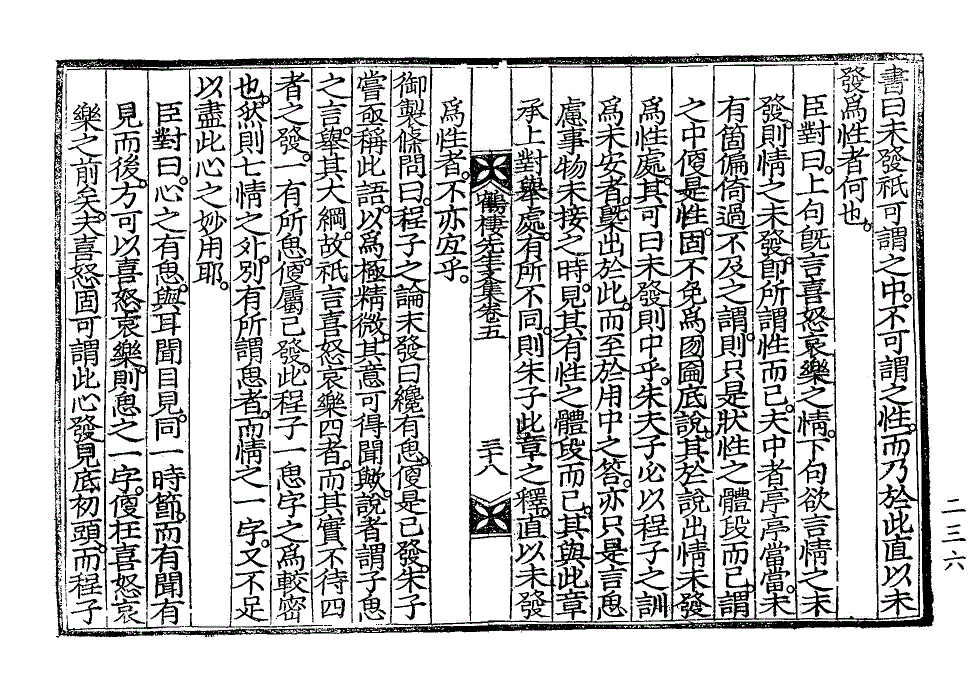 书曰未发祇可谓之中。不可谓之性。而乃于此直以未发为性者何也。
书曰未发祇可谓之中。不可谓之性。而乃于此直以未发为性者何也。臣对曰。上句既言喜怒哀乐之情。下句欲言情之未发。则情之未发。即所谓性而已。夫中者亭亭当当。未有个偏倚过不及之谓。则只是状性之体段而已。谓之中便是性。固不免为囫囵底说。其于说出情未发为性处。其可曰未发则中乎。朱夫子必以程子之训为未安者。槩出于此。而至于用中之答。亦只是言思虑事物未接之时。见其有性之体段而已。其与此章承上对举处。有所不同。则朱子此章之释。直以未发为性者。不亦宜乎。
御制条问曰。程子之论未发曰才有思。便是已发。朱子尝亟称此语。以为极精微。其意可得闻欤。说者谓子思之言。举其大纲。故祇言喜怒哀乐四者。而其实不待四者之发。一有所思。便属已发。此程子一思字之为较密也。然则七情之外。别有所谓思者。而情之一字。又不足以尽此心之妙用耶。
臣对曰。心之有思。与耳闻目见。同一时节。而有闻有见而后。方可以喜怒哀乐。则思之一字。便在喜怒哀乐之前矣。夫喜怒固可谓此心发见底初头。而程子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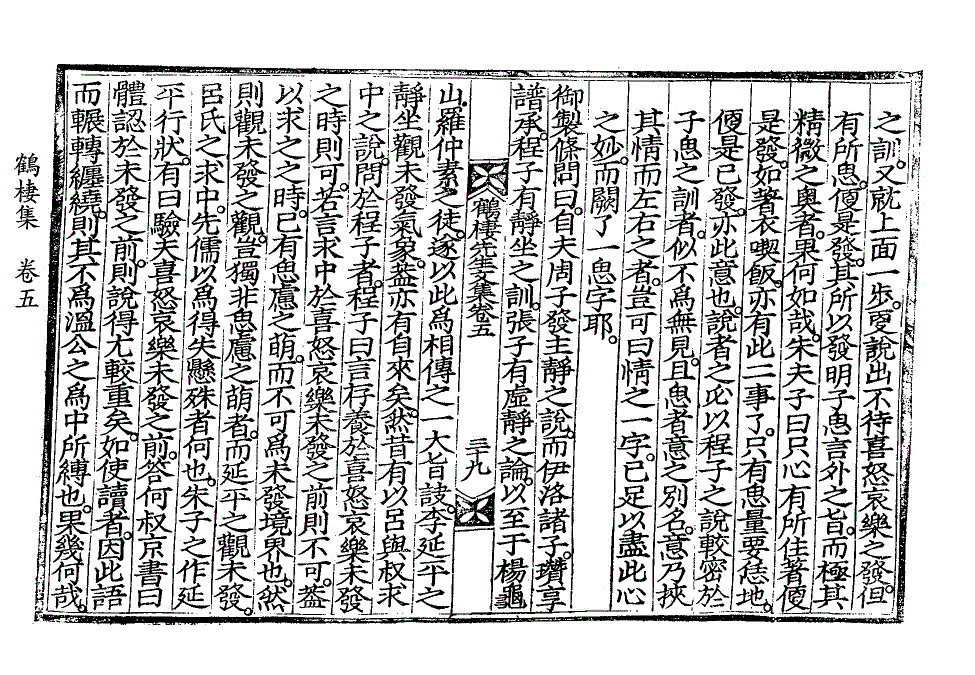 之训。又就上面一步。更说出不待喜怒哀乐之发。但有所思。便是发。其所以发明子思言外之旨。而极其精微之奥者。果何如哉。朱夫子曰只心有所住著便是发。如著衣吃饭。亦有此二事了。只有思量要恁地。便是已发。亦此意也。说者之必以程子之说较密于子思之训者。似不为无见。且思者意之别名。意乃挟其情而左右之者。岂可曰情之一字。已足以尽此心之妙。而阙了一思字耶。
之训。又就上面一步。更说出不待喜怒哀乐之发。但有所思。便是发。其所以发明子思言外之旨。而极其精微之奥者。果何如哉。朱夫子曰只心有所住著便是发。如著衣吃饭。亦有此二事了。只有思量要恁地。便是已发。亦此意也。说者之必以程子之说较密于子思之训者。似不为无见。且思者意之别名。意乃挟其情而左右之者。岂可曰情之一字。已足以尽此心之妙。而阙了一思字耶。御制条问曰。自夫周子发主静之说。而伊洛诸子。瓒享谱承。程子有静坐之训。张子有虚静之论。以至于杨龟山,罗仲素之徒。遂以此为相传之一大旨诀。李延平之静坐观未发气象。盖亦有自来矣。然昔有以吕与叔求中之说。问于程子者。程子曰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则可。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。盖以求之之时。已有思虑之萌。而不可为未发境界也。然则观未发之观。岂独非思虑之萌者。而延平之观未发。吕氏之求中。先儒以为得失悬殊者何也。朱子之作延平行状。有曰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。答何叔京书曰体认于未发之前。则说得尤较重矣。如使读者。因此语而辗转缠绕。则其不为温公之为中所缚也。果几何哉。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7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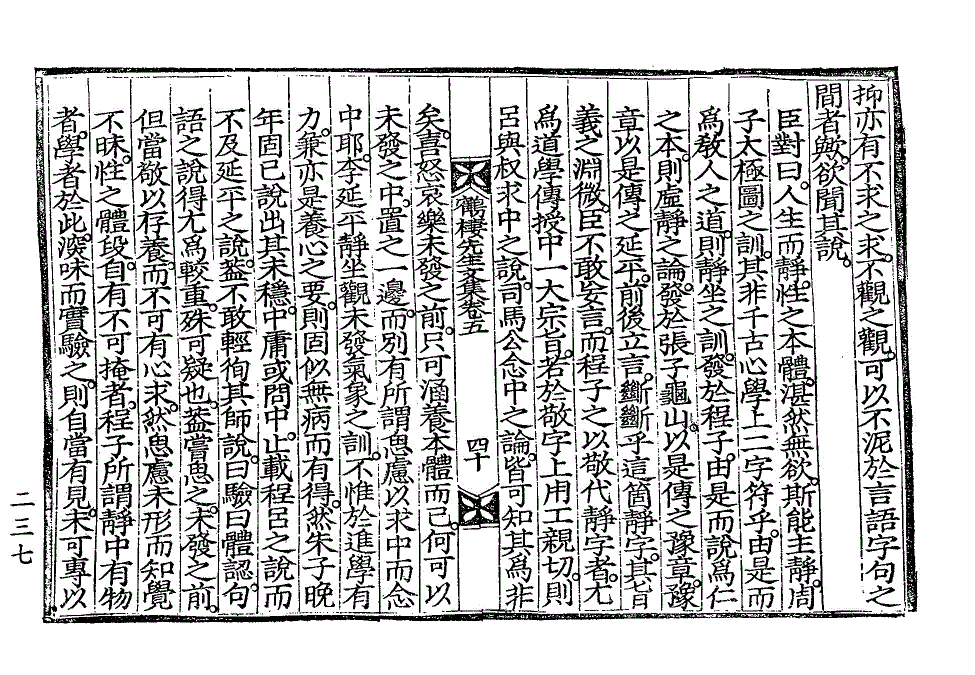 抑亦有不求之求。不观之观。可以不泥于言语字句之间者欤。欲闻其说。
抑亦有不求之求。不观之观。可以不泥于言语字句之间者欤。欲闻其说。臣对曰。人生而静。性之本体。湛然无欲。斯能主静。周子太极图之训。其非千古心学上二字符乎。由是而为教人之道。则静坐之训。发于程子。由是而说为仁之本。则虚静之论。发于张子龟山。以是传之豫章。豫章以是传之延平。前后立言。断断乎这个静字。其旨义之渊微。臣不敢妄言。而程子之以敬代静字者。尤为道学传授中一大宗旨。若于敬字上用工亲切。则吕与叔求中之说。司马公念中之论。皆可知其为非矣。喜怒哀乐未发之前。只可涵养本体而已。何可以未发之中。置之一边。而别有所谓思虑以求中而念中耶。李延平静坐观未发气象之训。不惟于进学有力。兼亦是养心之要。则固似无病而有得。然朱子晚年固已说出其未稳。中庸或问中。止载程吕之说而不及延平之说。盖不敢轻徇其师说。曰验曰体认。句语之说得尤为较重。殊可疑也。盖尝思之。未发之前。但当敬以存养。而不可有心求。然思虑未形而知觉不昧。性之体段。自有不可掩者。程子所谓静中有物者。学者于此。深味而实验之。则自当有见。未可专以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8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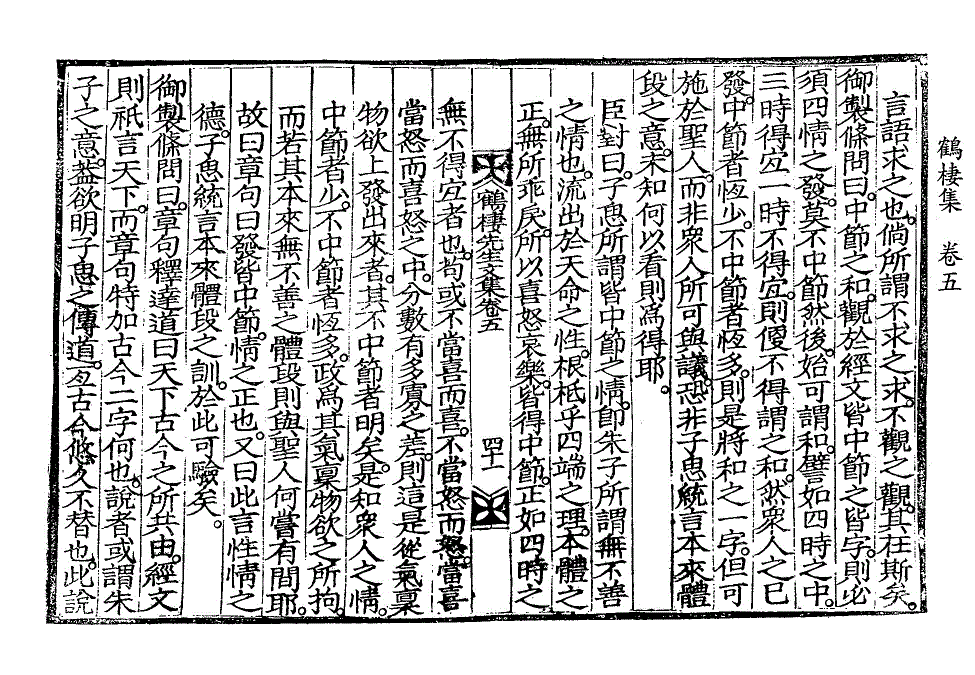 言语求之也。倘所谓不求之求。不观之观。其在斯矣。
言语求之也。倘所谓不求之求。不观之观。其在斯矣。御制条问曰。中节之和。观于经文皆中节之皆字。则必须四情之发。莫不中节然后。始可谓和。譬如四时之中。三时得宜一时不得宜。则便不得谓之和。然众人之已发。中节者恒少。不中节者恒多。则是将和之一字。但可施于圣人。而非众人所可与议。恐非子思统言本来体段之意。未知何以看则为得耶。
臣对曰。子思所谓皆中节之情。即朱子所谓无不善之情也。流出于天命之性。根柢乎四端之理。本体之正。无所乖戾。所以喜怒哀乐。皆得中节。正如四时之无不得宜者也。苟或不当喜而喜。不当怒而怒。当喜当怒而喜怒之中。分数有多寡之差。则这是从气禀物欲上发出来者。其不中节者明矣。是知众人之情。中节者少。不中节者恒多。政为其气禀物欲之所拘。而若其本来无不善之体段则与圣人何尝有间耶。故曰章句曰发皆中节。情之正也。又曰此言性情之德。子思统言本来体段之训。于此可验矣。
御制条问曰。章句释达道曰天下古今之所共由。经文则祇言天下。而章句特加古今二字何也。说者或谓朱子之意。盖欲明子思之传道。亘古今悠久不替也。此说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8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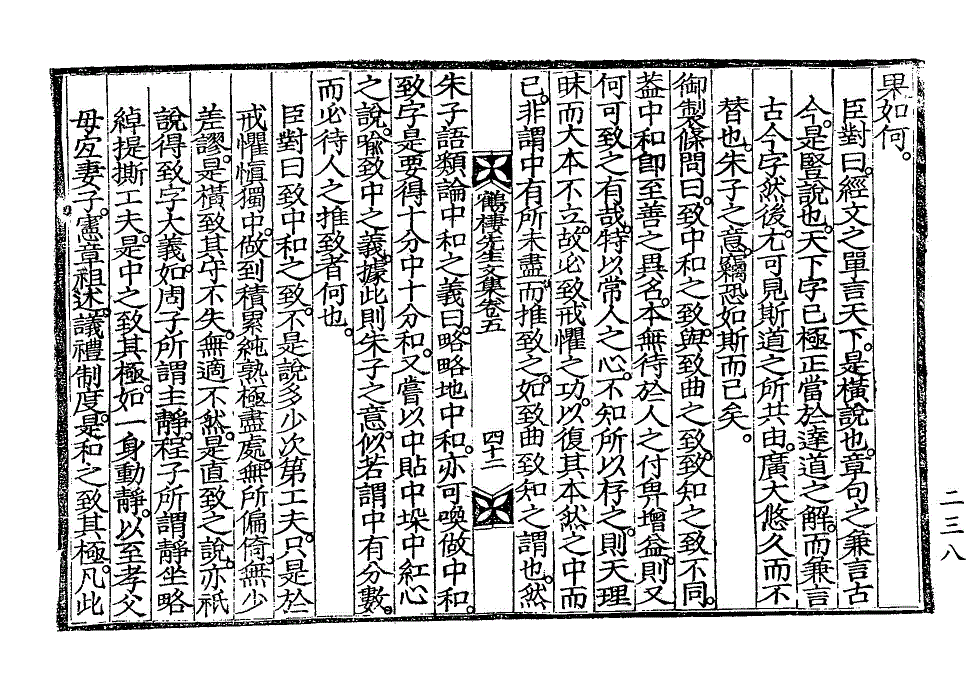 果如何。
果如何。臣对曰。经文之单言天下。是横说也。章句之兼言古今。是竖说也。天下字已极正当于达道之解。而兼言古今字然后。尤可见斯道之所共由。广大悠久而不替也。朱子之意。窃恐如斯而已矣。
御制条问曰。致中和之致。与致曲之致。致知之致不同。盖中和即至善之异名。本无待于人之付畁增益。则又何可致之有哉。特以常人之心。不知所以存之。则天理昧而大本不立。故必致戒惧之功。以复其本然之中而已。非谓中有所未尽而推致之。如致曲致知之谓也。然朱子语类论中和之义曰。略略地中和。亦可唤做中和。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。又尝以中贴中垛中红心之说。喻致中之义。据此则朱子之意。似若谓中有分数。而必待人之推致者何也。
臣对曰致中和之致。不是说多少次第工夫。只是于戒惧慎独中。做到积累纯熟极尽处。无所偏倚。无少差谬。是横致其守不失。无适不然。是直致之说。亦祇说得致字大义。如周子所谓主静。程子所谓静坐略绰提撕工夫。是中之致其极。如一身动静。以至孝父母宜妻子。宪章祖述。议礼制度。是和之致其极。凡此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9H 页
 皆推以极之于纯粹至善天然自有之理。而无待乎付畁增益。则夫岂有多少次第之工。如致曲致知之致耶。语类所谓略略十分之说。贴垛红心之喻。皆所以警学者必致戒惧之功。以复其本然之中而已。似亦不是中有分数而待人用力推致之谓也。
皆推以极之于纯粹至善天然自有之理。而无待乎付畁增益。则夫岂有多少次第之工。如致曲致知之致耶。语类所谓略略十分之说。贴垛红心之喻。皆所以警学者必致戒惧之功。以复其本然之中而已。似亦不是中有分数而待人用力推致之谓也。御制条问曰。章句自戒惧而约之一句。解之者有二说。或谓自其有睹有闻之时。已用戒慎恐惧之工而渐约之。以至于不睹不闻之时。或谓戒惧工夫。虽本通贯动静。而此所谓戒惧。既与谨独对言。则当专属之静一边。盖戒惧是静时工夫之始。而工夫自有浅深。故必约之然后。可以至于无所偏倚之极工也。是二说孰为正解也。
臣对曰自戒惧而约之一句。解二说皆得。而但约之云者。自外而内。自大而小。既收敛又收敛。以至于至静之中。无所偏倚之谓也。若以工夫浅深为言则窃恐未安。
御制条问曰。不曰致中而天地位。致和而万物育。则何以知天地位之必应致中。万物育之必应致和也。岂以致中而后致和。天地位而后万物育。而体用先后。自然如此也欤。抑别有分属之不可易者欤。先儒有以致中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39L 页
 为穷神继志。致和为知化述事者。有以致中为敬格天心。致和为恕平物情者。有以致中为礼之别宜。致和为乐之敦和者。向所谓分属之不可易者。果在于此耶。
为穷神继志。致和为知化述事者。有以致中为敬格天心。致和为恕平物情者。有以致中为礼之别宜。致和为乐之敦和者。向所谓分属之不可易者。果在于此耶。臣对曰。天地位。只是大纲都好了。故致大本之中。其效便能如此。万物育。只是天下事事都好了。故须致达道之和。其效方能如此。是其一动一静之间。一体一用之际。大纲之与大本。事事之与达道。分排说去。各有攸当者也。虽然中和位育。自是一统底事。致中便可致和。位天地便可育万物。体立用行。初非两事。朱子之始以分言释之。末又合言以结之者。岂非的确乎实底论耶。至若穷格别宜之属中。知恕敦和之属和。盖亦有见于体用先后之别而随处下语者。此其逐项分属之不可易者。然一向太分析。恐或流于穿凿支离之病也。
御制条问曰。章句学问之极功一句。以致中和言。圣人之能事一句。以位育言欤。言极功与能事。并指位育之事欤。若谓分属于中和位育。则此二句既承上文。所谓效验如此之下。不应于此更言工夫。若谓并指位育之事则又未免叠床架屋。何以看则为得耶。
臣对曰学问之极功。以致中和言。圣人之能事。以位
鹤栖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24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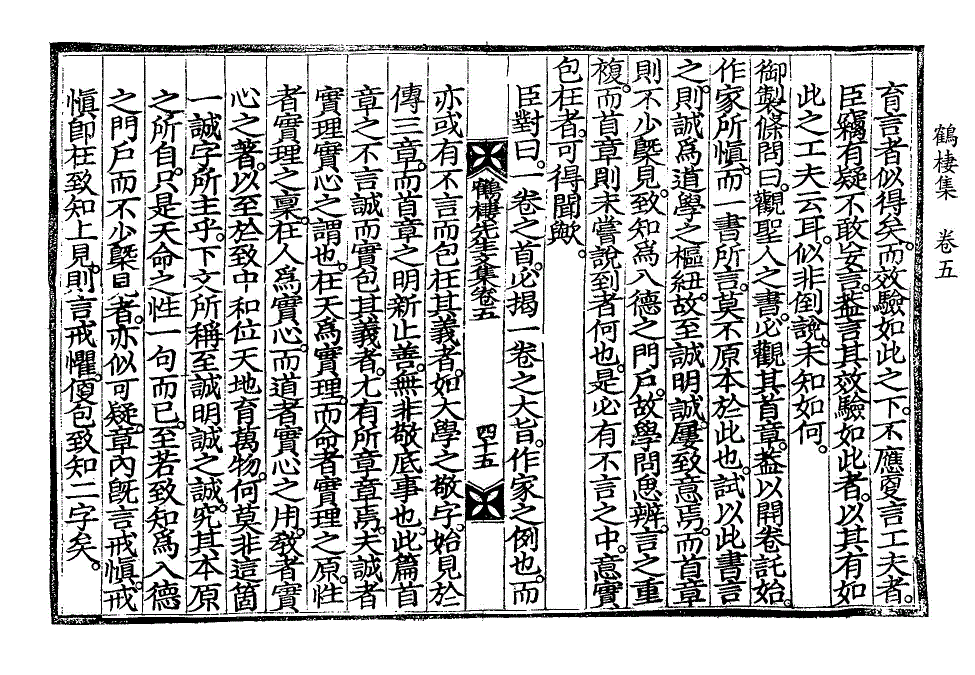 育言者似得矣。而效验如此之下。不应更言工夫者。臣窃有疑不敢妄言。盖言其效验如此者。以其有如此之工夫云耳。似非倒说。未知如何。
育言者似得矣。而效验如此之下。不应更言工夫者。臣窃有疑不敢妄言。盖言其效验如此者。以其有如此之工夫云耳。似非倒说。未知如何。御制条问曰。观圣人之书。必观其首章。盖以开卷托始。作家所慎。而一书所言。莫不原本于此也。试以此书言之。则诚为道学之枢纽。故至诚明诚。屡致意焉。而首章则不少槩见。致知为入德之门户。故学问思辨。言之重复。而首章则未尝说到者何也。是必有不言之中。意实包在者。可得闻欤。
臣对曰。一卷之首。必揭一卷之大旨。作家之例也。而亦或有不言而包在其义者。如大学之敬字。始见于传三章。而首章之明新止善。无非敬底事也。此篇首章之不言诚而实包其义者。尤有所章章焉。夫诚者实理实心之谓也。在天为实理。而命者实理之原。性者实理之禀。在人为实心。而道者实心之用。教者实心之著。以至于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。何莫非这个一诚字所主乎。下文所称至诚明诚之诚。究其本原之所自。只是天命之性一句而已。至若致知为入德之门户而不少槩见者。亦似可疑。章内既言戒慎。戒慎即在致知上见。则言戒惧。便包致知二字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