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明: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.org,kanripo.org, db.itkc.or.kr 和 zh.wikisource.org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x 页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
记
记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58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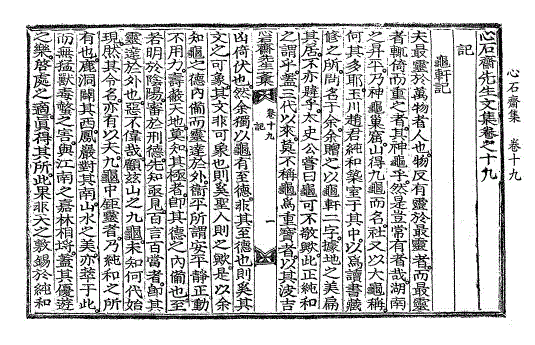 龟轩记
龟轩记夫最灵于万物者人也。物反有灵于最灵者。而最灵者辄倚而重之者。其神龟乎。然是岂常有者哉。湖南之升平。乃神龟巢窟。山得九龟而名。社又以大龟称。何其多耶。玉川赵君纯和筑室于其中。以为读书藏修之所。问名于余。余赠之以龟轩二字。据地之美扁其居。不亦韪乎。太史公尝曰龟可不敬欤。此正纯和之谓乎。盖三代以来。莫不称龟为重宝者。以其决吉凶倚伏也。然余独以龟有至德。非其至德也则奚其文之可象。其文非可象也则奚圣人则之欤。是以余知龟之德内备而灵达于外。卫平所谓安平静正。动不用力。寿蔽天地。莫知其极者。即其德之内备也。至若明于阴阳。审于刑德。先知亟见。百言百当者。即其灵达于外也。恶不伟哉。顾玆山之九龟。未知何代始现。然其令名。亦有以夫。九龟中钜灵者。乃纯和之所有也。鹿洞辟其西。凤岩对其南。山水之美。亦萃于此。而无猛兽毒螫之害。与江南之嘉林相埒。盖其优游之乐。启处之适。真得其所。此果非天之敷锡于纯和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58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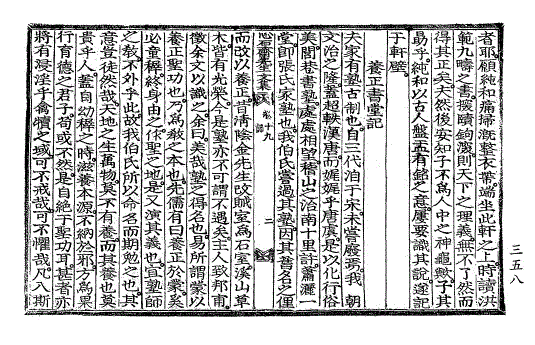 者耶。愿纯和痛扫溉整衣带。端坐此轩之上。时读洪范九畴之书。探赜钩深。则天下之理义。无不了然而得其正矣。夫然后安知子不为人中之神龟欤。子其勖乎。纯和以古人盘盂有铭之意。屡要识其说。遂记于轩壁。
者耶。愿纯和痛扫溉整衣带。端坐此轩之上。时读洪范九畴之书。探赜钩深。则天下之理义。无不了然而得其正矣。夫然后安知子不为人中之神龟欤。子其勖乎。纯和以古人盘盂有铭之意。屡要识其说。遂记于轩壁。养正书堂记
夫家有塾古制也。自三代洎于宋。未尝废焉。我 朝文治之隆。盖超轶汉唐。而娓娓乎唐虞。是以化行俗美。闾巷书塾。处处相望。稽山之治南十里许。萧洒一堂。即张氏家塾也。我伯氏尝过其塾。因其旧名之俚而改以养正。昔清阴金先生改贼室为石室。溪山草木。皆有光荣。今是塾亦不可谓不遇矣。主人致邦甫。徵余文以识之。余曰。美哉塾之得名也。易所谓蒙以养正圣功也。乃为教之本也。先儒有曰养正于蒙。奚必童稚。终身由之。作圣之地。是又演其义也。宜塾师之教。不外乎此。故我伯氏所以命名而期勉之也。其意岂徒然哉。天地之生万物。莫不有养。而其养也莫贵乎人。盖自幼稚之时。滋养本源。不纳于邪。方为果行育德之君子。苟或不然。是自绝于圣功耳。甚者亦将有浸淫乎禽犊之域。可不戒哉。可不惧哉。凡入斯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59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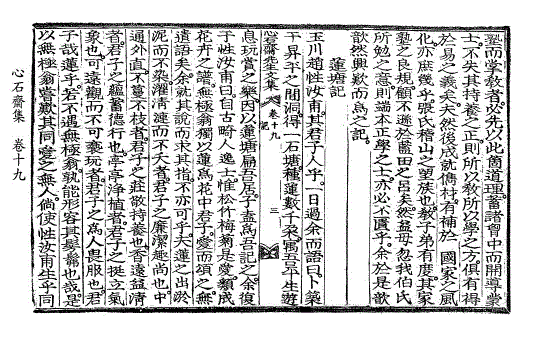 塾而掌教者。必先以此个道理。蓄诸胸中而开导蒙士。不失其持养之正。则所以教所以学之方。俱有得于易之义矣。夫然后成就俊材。有补于 国家之风化。亦庶几乎。张氏稽山之望族也。教子弟有度。其家塾之良规。顾不逊于蓝田之吕矣。然益毋忽我伯氏所勉之意。则端本正学之士。亦必不匮乎。余于是歆歆然兴叹而为之记。
塾而掌教者。必先以此个道理。蓄诸胸中而开导蒙士。不失其持养之正。则所以教所以学之方。俱有得于易之义矣。夫然后成就俊材。有补于 国家之风化。亦庶几乎。张氏稽山之望族也。教子弟有度。其家塾之良规。顾不逊于蓝田之吕矣。然益毋忽我伯氏所勉之意。则端本正学之士。亦必不匮乎。余于是歆歆然兴叹而为之记。莲塘记
玉川赵性汝甫。其君子人乎。一日过余而语曰。卜筑于升平之间洞。得一石塘。种莲数千朵。寓吾平生游息玩赏之乐。因以莲塘扁吾居。子盍为吾记之。余复于性汝甫曰。自古畸人逸士。惟松竹梅菊是爱。类成花卉之谱。无极翁独以莲为花中君子。爱而颂之。无遗语矣。余就其说而求其指。不亦可乎。夫莲之出淤泥而不染。濯清涟而不夭者。君子之廉洁趣尚也。中通外直。不蔓不枝者。君子之庄敬持养也。香远益清者。君子之蕴蓄德行也。亭亭净植者。君子之挺立气象也。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者。君子之为人畏服也。君子哉莲乎。若不遇无极翁。孰能形容其髣髴也哉。是以无极翁尝叹其同爱之无人。倘使性汝甫生乎同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5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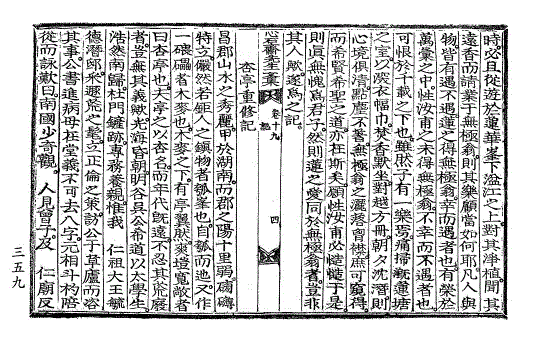 时。必且从游于莲华峰下湓江之上。对其净植。闻其远香而请业于无极翁。则其乐顾当如何耶。凡人与物。皆有遇不遇。莲之得无极翁。幸而遇者也。有荣于万汇之中。性汝甫之未得无极翁。不幸而不遇者也。可恨于千载之下也。虽然子有一乐焉。痛扫溉莲塘之室。以深衣幅巾。焚香默坐。对越方册。朝夕沈潜。则心境俱清。点尘不著。无极翁之洒落胸襟。庶可窥得。而希贤希圣之道。亦在斯矣。愿性汝甫必慥慥于是。则真无愧为君子。然则莲之爱同于无极翁者。岂非其人欤。遂为之记。
时。必且从游于莲华峰下湓江之上。对其净植。闻其远香而请业于无极翁。则其乐顾当如何耶。凡人与物。皆有遇不遇。莲之得无极翁。幸而遇者也。有荣于万汇之中。性汝甫之未得无极翁。不幸而不遇者也。可恨于千载之下也。虽然子有一乐焉。痛扫溉莲塘之室。以深衣幅巾。焚香默坐。对越方册。朝夕沈潜。则心境俱清。点尘不著。无极翁之洒落胸襟。庶可窥得。而希贤希圣之道。亦在斯矣。愿性汝甫必慥慥于是。则真无愧为君子。然则莲之爱同于无极翁者。岂非其人欤。遂为之记。杏亭重修记
昌郡山水之秀丽。甲于湖南。而郡之阳十里弱。磅礴特立。俨然若钜人之镇物者瓠峰也。自瓠而迤。又作一碨礧者木麦也。木麦之下。有亭翼然。爽垲宽敞者曰杏亭也。夫亭之以杏名。而年代既远。不忍其荒废者。岂无其义欤。光海昏朝。明谷吴公希道以太学生。浩然南归。杜门铲迹。专务养亲。惟我 仁祖大王毓德潜邸。采遁荒之髦。立正伦之策。访公于草庐而咨其事。公书进病母在堂义不可去八字。元相斗杓陪从而咏叹曰。南国少奇观。▣人见曾子。及 仁庙反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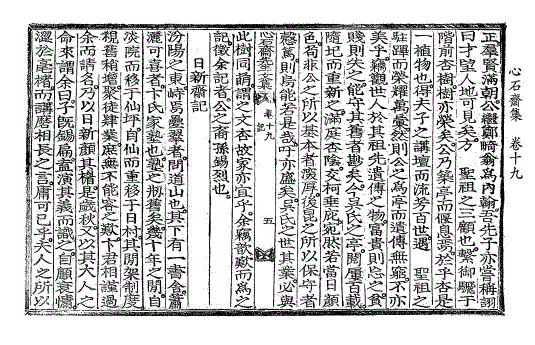 正。群贤满朝。公继郑畸翁为内翰。吾先子亦尝称诩曰才望人地可见矣。方 圣祖之三顾也。系御騛于阶前杏树。树亦荣矣。公乃筑亭而偃息焉。于乎杏是一植物也。得夫子之讲坛而流芳百世。遇 圣祖之驻跸而荣耀万汇。然则公之为亭而遗传无穷。不亦美乎。窃观世人于其祖先遗传之物。富贵则忘之。贫贱则失之。能守其旧者鲜矣。今吴氏之亭。阅屡百载。随圮而重新之。满庭杏阴。交柯垂庇。宛然若当日颜色。苟非公之所以基本者深厚。后昆之所以保守者悫笃。则乌能若是哉。吁亦盛矣。吴氏之世其业。必与此树同萌。谓之文杏故家亦宜乎。余窃歆叹而为之记。徵余记者。公之裔孙锡烈也。
正。群贤满朝。公继郑畸翁为内翰。吾先子亦尝称诩曰才望人地可见矣。方 圣祖之三顾也。系御騛于阶前杏树。树亦荣矣。公乃筑亭而偃息焉。于乎杏是一植物也。得夫子之讲坛而流芳百世。遇 圣祖之驻跸而荣耀万汇。然则公之为亭而遗传无穷。不亦美乎。窃观世人于其祖先遗传之物。富贵则忘之。贫贱则失之。能守其旧者鲜矣。今吴氏之亭。阅屡百载。随圮而重新之。满庭杏阴。交柯垂庇。宛然若当日颜色。苟非公之所以基本者深厚。后昆之所以保守者悫笃。则乌能若是哉。吁亦盛矣。吴氏之世其业。必与此树同萌。谓之文杏故家亦宜乎。余窃歆叹而为之记。徵余记者。公之裔孙锡烈也。日新斋记
汾阳之东。峙焉叠翠者。问道山也。其下有一书舍。萧洒可喜者。卞氏家塾也。塾之刱旧矣。几十年之閒。自淡院而移于仙坪。自仙而重移于日村。其閒架制度。视旧稍增。聚徒肄业。庶无不能容之叹。卞君相谨过余而请名。乃以日新颜其楣。是岁秋。又以其大人之命来谓余曰。子既锡扁。盍演其义而识之。自顾衰慵。涩于毫楮。而讲磨相长之言。庸可已乎。夫人之所以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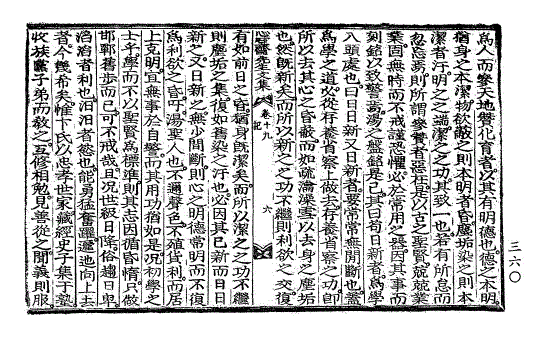 为人而参天地赞化育者。以其有明德也。德之本明。犹身之本洁。物欲蔽之则本明者昏。尘垢染之则本洁者污。明之之端。洁之之功。其致一也。若有所怠而忽忘焉。则所谓参赞者恶在。是以古之圣贤。兢兢业业。固无时而不戒谨恐惧。必于常用之器。因其事而刻铭以致警焉。汤之盘铭是已。其曰苟日新者。为学入头处也。曰日日新又日新者。要常常无閒断也。盖为学之道。必从存养省察上做去。存养省察之功。即所以去其心之昏蔽。而如疏瀹澡雪以去身之尘垢也。然既新矣。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继则利欲之交。复有如前日之昏。犹身既洁矣。而所以洁之之功不继则尘垢之集。复如旧染之污也。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。又日新之。无少间断。则心之明德常明而不复为利欲之昏。吁。汤圣人也。不迩声色。不殖货利。而居上克明。宜无事于自警。而其用功犹如是。况初学之士乎。学而不以圣贤为标准。则其志因循昏惰。只做邯郸旧步而已。可不戒哉。且况世级日降。俗趋日卑。滔滔者利也。汩汩者欲也。能勇猛奋跃。逦迤向上去者。今几希矣。惟卞氏以忠孝世家。藏经史子集于塾。收族党子弟而教之。互修相勉。见善从之。闻义则服。
为人而参天地赞化育者。以其有明德也。德之本明。犹身之本洁。物欲蔽之则本明者昏。尘垢染之则本洁者污。明之之端。洁之之功。其致一也。若有所怠而忽忘焉。则所谓参赞者恶在。是以古之圣贤。兢兢业业。固无时而不戒谨恐惧。必于常用之器。因其事而刻铭以致警焉。汤之盘铭是已。其曰苟日新者。为学入头处也。曰日日新又日新者。要常常无閒断也。盖为学之道。必从存养省察上做去。存养省察之功。即所以去其心之昏蔽。而如疏瀹澡雪以去身之尘垢也。然既新矣。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继则利欲之交。复有如前日之昏。犹身既洁矣。而所以洁之之功不继则尘垢之集。复如旧染之污也。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。又日新之。无少间断。则心之明德常明而不复为利欲之昏。吁。汤圣人也。不迩声色。不殖货利。而居上克明。宜无事于自警。而其用功犹如是。况初学之士乎。学而不以圣贤为标准。则其志因循昏惰。只做邯郸旧步而已。可不戒哉。且况世级日降。俗趋日卑。滔滔者利也。汩汩者欲也。能勇猛奋跃。逦迤向上去者。今几希矣。惟卞氏以忠孝世家。藏经史子集于塾。收族党子弟而教之。互修相勉。见善从之。闻义则服。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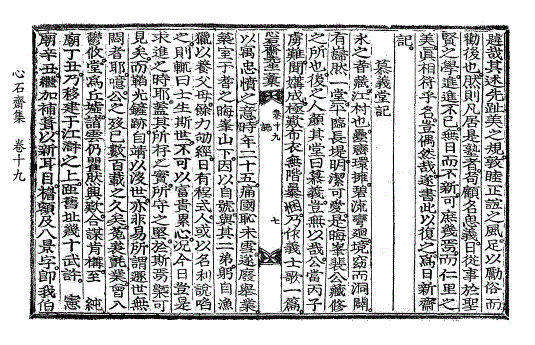 韪哉其述先趾美之规。敦睦正谊之风。足以励俗而劝后也。然则凡居是塾者。苟顾名思义。日从事于圣贤之学。进进不已。无日而不新。可庶几焉。而仁里之美。真相符乎名。岂偶然哉。遂书此以复之。为日新斋记。
韪哉其述先趾美之规。敦睦正谊之风。足以励俗而劝后也。然则凡居是塾者。苟顾名思义。日从事于圣贤之学。进进不已。无日而不新。可庶几焉。而仁里之美。真相符乎名。岂偶然哉。遂书此以复之。为日新斋记。慕义堂记
永之耆藏。江村也。叠峦环拥。碧流弯回。境窈而洞辟。有岿然一堂。平临长堤。明洁可爱。是晦峰裴公藏修之所也。后之人颜其堂曰慕义。岂无以哉。公当丙子虏难。闻媾成。极叹布衣无阶㬥悃。乃作义士歌一篇。以寓忠愤之意。时年二十五。痛国耻未雪。遂废举业。筑室于耆之晦峰山下。因以自号。与其二弟。躬自渔猎以养父母。馀力劬经。日有程式。人或以名利说啖之。则辄曰士生斯世。不可以富贵累心。况今日岂是求进之时耶。盖其所存之实。所守之坚。于斯焉槩可见矣。而韬光铲迹。自靖以没世。亦非易所谓遁世无闷者耶。噫。公之殁已数百载之久矣。菟裘毡业。曾入郁攸。堂为丘墟。诸云仍瞿然兴叹。合谋肯构。至 纯庙丁丑。乃移建于江浒之上。距旧址几十武许。 宪庙辛丑。继加补葺。以新耳目。楣额及八景字。即我伯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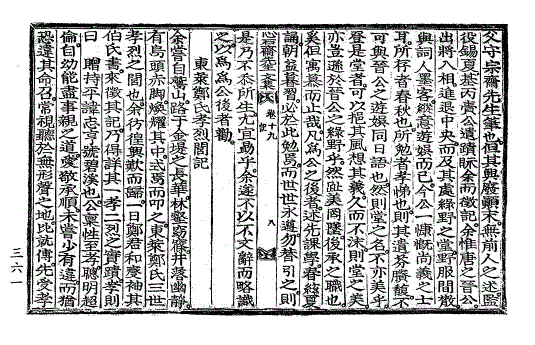 父守宗斋先生笔也。但其兴废颠末。无前人之述。监役锡夏,基丙赍公遗迹视余而徵记。余惟唐之晋公。出将入相。进退中央。而及其处绿野之堂。野服间散。与词人墨客。纵意游娱而已。今公一慷慨尚义之士耳。所存者春秋也。所勉者孝悌也。则其遗芬剩馥。不可与晋公之游娱同日语也。然则堂之名。不亦美乎。登是堂者。可以挹其风想其义。久而不沫。则堂之美。亦岂逊于晋公之绿野乎。然趾美罔坠。后承之职也。奚但寓慕而止哉。凡为公之后者。述先课学。春弦夏诵。朝益暮习。必于此勉焉。而世世永遵。勿替引之。则是乃不忝所生。尤宜勖乎。余遂不以不文辞而略识之。以为为公后者劝。
父守宗斋先生笔也。但其兴废颠末。无前人之述。监役锡夏,基丙赍公遗迹视余而徵记。余惟唐之晋公。出将入相。进退中央。而及其处绿野之堂。野服间散。与词人墨客。纵意游娱而已。今公一慷慨尚义之士耳。所存者春秋也。所勉者孝悌也。则其遗芬剩馥。不可与晋公之游娱同日语也。然则堂之名。不亦美乎。登是堂者。可以挹其风想其义。久而不沫。则堂之美。亦岂逊于晋公之绿野乎。然趾美罔坠。后承之职也。奚但寓慕而止哉。凡为公之后者。述先课学。春弦夏诵。朝益暮习。必于此勉焉。而世世永遵。勿替引之。则是乃不忝所生。尤宜勖乎。余遂不以不文辞而略识之。以为为公后者劝。东莱郑氏孝烈闾记
余尝自鹫山。路于金堤之长华。林壑窈窱。井落幽静。有乌头赤脚。焕耀其中。式焉而叩之。东莱郑氏三世孝烈之闾也。余彷徨兴叹而归。一日郑君和燮袖其伯氏书。来徵其记。乃得详其一孝二烈之实迹。孝则曰 赠持平讳志亨号碧溪也。公禀性至孝。聪明超伦。自幼能尽事亲之道。爱敬承顺。未尝少有违。而犹恐违其命召。常视听于无形声之地。比就傅。先受孝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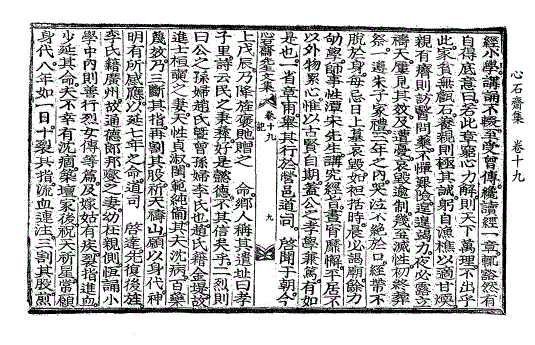 经,小学。讲诵不辍。至受曾传。才读经一章。辄豁然有自得底意曰。若此章穷心力解。则天下万理。不出乎此。家贫无甔石。养亲则极其诚。躬自渔樵以适甘暖。亲有癠则访医问药。不惮艰险。遑遑竭力。夜必露立祷天。屡见其效。及遭忧。哀毁逾制。几至灭性。初终葬祭。一遵朱子家礼。三年之内。哭泣不绝于口。绖带不脱于身。每忌日上墓哀毁。如袒括时。晨必谒庙。馀力劬学。师事性潭宋先生。讲究经旨。昼宵靡懈。平居不以外物累心。惟以古贤自期。盖公之孝学兼笃。有如是也。一省章甫。举其行于营邑道司。 启闻于朝。今上戊辰。乃降旌褒貤赠之 命。乡人称其遗址曰孝子里。诗云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。不其信矣乎。二烈则曰公之孙妇赵氏暨曾孙妇李氏也。赵氏籍金堤。故进士桓奭之妻。天性贞淑。闺范纯备。其夫沈病。百药蔑效。乃三断其指。再割其股。祈天祷山。愿以身代。神明有所感应。以延七年之命。道司 启达。先复后旌。李氏籍广州。故通德郎邦燮之妻。幼在亲侧。恒诵小学中内则善行烈女传等篇。及嫁姑有疾。裂指进血。少延其命。夫不幸有沈痼。筑坛家后。祝天祈星。常愿身代。八年如一日。十裂其指。流血连注。三割其股。煎
经,小学。讲诵不辍。至受曾传。才读经一章。辄豁然有自得底意曰。若此章穷心力解。则天下万理。不出乎此。家贫无甔石。养亲则极其诚。躬自渔樵以适甘暖。亲有癠则访医问药。不惮艰险。遑遑竭力。夜必露立祷天。屡见其效。及遭忧。哀毁逾制。几至灭性。初终葬祭。一遵朱子家礼。三年之内。哭泣不绝于口。绖带不脱于身。每忌日上墓哀毁。如袒括时。晨必谒庙。馀力劬学。师事性潭宋先生。讲究经旨。昼宵靡懈。平居不以外物累心。惟以古贤自期。盖公之孝学兼笃。有如是也。一省章甫。举其行于营邑道司。 启闻于朝。今上戊辰。乃降旌褒貤赠之 命。乡人称其遗址曰孝子里。诗云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。不其信矣乎。二烈则曰公之孙妇赵氏暨曾孙妇李氏也。赵氏籍金堤。故进士桓奭之妻。天性贞淑。闺范纯备。其夫沈病。百药蔑效。乃三断其指。再割其股。祈天祷山。愿以身代。神明有所感应。以延七年之命。道司 启达。先复后旌。李氏籍广州。故通德郎邦燮之妻。幼在亲侧。恒诵小学中内则善行烈女传等篇。及嫁姑有疾。裂指进血。少延其命。夫不幸有沈痼。筑坛家后。祝天祈星。常愿身代。八年如一日。十裂其指。流血连注。三割其股。煎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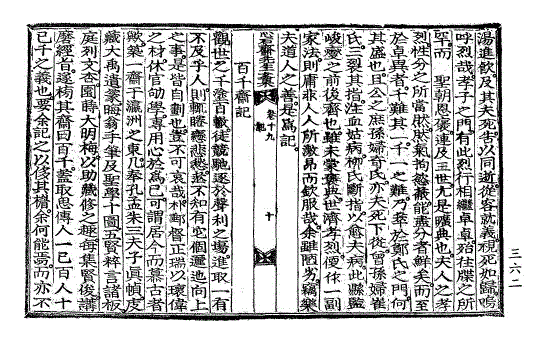 汤进饮。及其夫死。告以同逝。从容就义。视死如归。呜呼烈哉。孝子之门。有此烈行相继卓卓。殆往牒之所罕。而 圣朝恩褒。连及三世。尤是旷典也。夫人之孝烈。性分之所当然。然气拘欲蔽。能尽分者鲜矣。而至于卓异者。千难其一。千一之难。乃萃于郑氏之门。何其盛也。且公之庶孙妇奇氏。亦夫死下从。曾孙妇崔氏。三裂其指。注血姑病。柳氏断指。以愈夫病。此县监峻燮之前后齐也。虽未蒙褒典。世济孝烈。便作一副家法。则庸非人人所激昂而钦服哉。余虽陋劣。窃乐夫道人之善。是为记。
汤进饮。及其夫死。告以同逝。从容就义。视死如归。呜呼烈哉。孝子之门。有此烈行相继卓卓。殆往牒之所罕。而 圣朝恩褒。连及三世。尤是旷典也。夫人之孝烈。性分之所当然。然气拘欲蔽。能尽分者鲜矣。而至于卓异者。千难其一。千一之难。乃萃于郑氏之门。何其盛也。且公之庶孙妇奇氏。亦夫死下从。曾孙妇崔氏。三裂其指。注血姑病。柳氏断指。以愈夫病。此县监峻燮之前后齐也。虽未蒙褒典。世济孝烈。便作一副家法。则庸非人人所激昂而钦服哉。余虽陋劣。窃乐夫道人之善。是为记。百千斋记
观世之千涂百辙。徒竞驰逐于声利之场。进取一有不及乎人。则辄眷恋悲愁。茫不知有它个逦迤向上之事。是皆自划也。岂不可哀哉。朴邮督正瑞以瑰伟之材。休官劬学。专用心于为己。可谓居今而慕古者欤。筑一斋于瀛洲之东。几奉孔孟朱三夫子真帧。庋藏大禹遗篆,晦翁手笔及圣学十图,五贤粹言诸板。庭列文杏。园莳大明梅。以助藏修之趣。每集贤俊。讲磨经旨。遂榜其斋曰百千。盖取思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义也。要余记之以侈其楣。余何能焉。而亦不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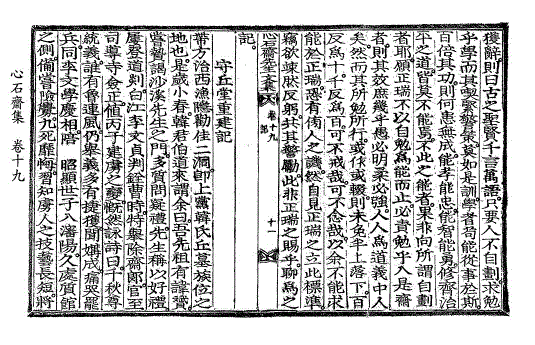 获辞。则曰古之圣贤千言万语。只要人不自划。求勉乎学而其吃紧警策。莫如是训。学者苟能从事于斯。百倍其功。则何患无成。能孝能忠。能智能勇。修齐治平之道。皆莫不能焉。不此之能者。果非向所谓自划者耶。愿正瑞不以自勉为能而止。必责勉乎入是斋者。则其效庶几乎愚必明柔必强。人人为道义中人矣。然而其所勉所行。或作或辍。则未免半上落下。百反为十。千反为百。可不戒哉。可不念哉。以余不能求能于正瑞。恐有傍人之讥。然自见正瑞之立此标准。窃欲竦然反躬。共其警励。此非正瑞之赐乎。聊为之记。
获辞。则曰古之圣贤千言万语。只要人不自划。求勉乎学而其吃紧警策。莫如是训。学者苟能从事于斯。百倍其功。则何患无成。能孝能忠。能智能勇。修齐治平之道。皆莫不能焉。不此之能者。果非向所谓自划者耶。愿正瑞不以自勉为能而止。必责勉乎入是斋者。则其效庶几乎愚必明柔必强。人人为道义中人矣。然而其所勉所行。或作或辍。则未免半上落下。百反为十。千反为百。可不戒哉。可不念哉。以余不能求能于正瑞。恐有傍人之讥。然自见正瑞之立此标准。窃欲竦然反躬。共其警励。此非正瑞之赐乎。聊为之记。守丘堂重建记
带方治西渔隐劝佳二洞。即上党韩氏丘墓族位之地也。是岁小春。韩君伯道来谓余曰。吾先祖有讳赟。尝贽谒沙溪先生之门。多质问疑礼。先生称以好礼。屡登道剡。白江李文贞判铨曹时。特举除斋郎。官至司导寺佥正。值丙子建虏之变。慨然咏诗曰。千秋尊统义。谁有鲁连风。仍举义多有捷获。闻媾成。痛哭罢兵。同李文学庆相。陪 昭显世子入沈阳。久处质馆之侧。备尝险衅。九死靡悔。习知虏人之技艺长短。将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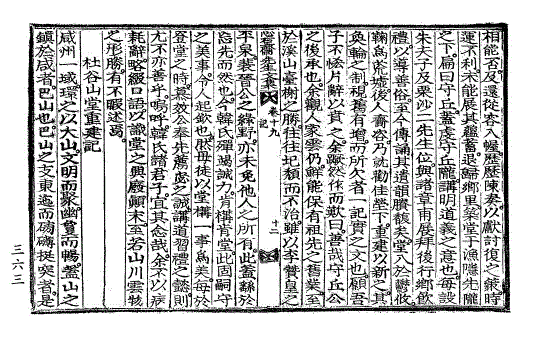 相能否。及还从容入幄。历历陈奏。以献讨复之策。时运不利。未能展其蕴蓄。退归乡里。筑堂于渔隐先陇之下。扁曰守丘。盖虔守丘陇。讲明道义之意也。每设朱夫子及栗沙二先生位。与诸章甫展拜后行乡饮礼。以导善俗。至今传诵其遗韵剩馥矣。堂入于郁攸。鞠为荒墟。后人赍咨。乃就劝佳茔下。重建以新之。其奂轮之制。视旧有增。而所欠者一记实之文也。愿吾子不吝片辞以贲之。余蹶然作而叹曰。善哉守丘公之后承也。余观人家云仍。鲜能保有祖先之旧业。至于溪山台榭之胜。往往圮颓而不治。虽以李赞皇之平泉。裴晋公之绿野。亦未免他人之所有。此盖繇于忘先而然也。今韩氏殚竭诚力。肯构肯堂。此固嗣守之美事。令人起钦也。然毋徒以堂构一事为美。每于登堂之时。慕效公奉先荐苾之诚。讲道习礼之懿。则尤不亦善乎。呜呼。韩氏诸君子。宜其念哉。余不以病耗辞。略缀口语。以识堂之兴废颠末。至若山川云物之形胜。有不暇述焉。
相能否。及还从容入幄。历历陈奏。以献讨复之策。时运不利。未能展其蕴蓄。退归乡里。筑堂于渔隐先陇之下。扁曰守丘。盖虔守丘陇。讲明道义之意也。每设朱夫子及栗沙二先生位。与诸章甫展拜后行乡饮礼。以导善俗。至今传诵其遗韵剩馥矣。堂入于郁攸。鞠为荒墟。后人赍咨。乃就劝佳茔下。重建以新之。其奂轮之制。视旧有增。而所欠者一记实之文也。愿吾子不吝片辞以贲之。余蹶然作而叹曰。善哉守丘公之后承也。余观人家云仍。鲜能保有祖先之旧业。至于溪山台榭之胜。往往圮颓而不治。虽以李赞皇之平泉。裴晋公之绿野。亦未免他人之所有。此盖繇于忘先而然也。今韩氏殚竭诚力。肯构肯堂。此固嗣守之美事。令人起钦也。然毋徒以堂构一事为美。每于登堂之时。慕效公奉先荐苾之诚。讲道习礼之懿。则尤不亦善乎。呜呼。韩氏诸君子。宜其念哉。余不以病耗辞。略缀口语。以识堂之兴废颠末。至若山川云物之形胜。有不暇述焉。杜谷山堂重建记
咸州一域。环之以大山。文明而聚。幽夐而畅。盖山之镇于咸者。巴山也。巴山之支东迤而磅礴挺突者。是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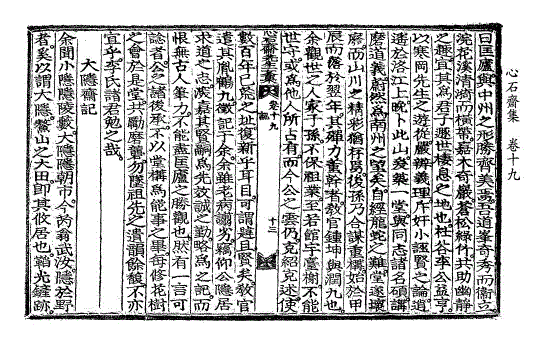 曰匡庐。与中州之形胜齐美焉。吾道峰奇秀而卫立。浣花溪清漪而横带。嘉木奇岩。苍松绿竹。共助幽静之趣。宜其为君子遁世栖息之地也。杜谷李公益亨。以寒冈先生之游从。严辨义理。斥奸小诬贤之论。逍遥于洛江上。晚卜此山。爰筑一堂。与同志诸名硕。讲磨道义。蔚然为南州之望矣。自经龙蛇之难。堂遂坏废。而山川之精彩犹存焉。后孙乃合谋重构。始于甲辰而落于翌年。其殚力董干者。教官钟坤与润九也。余观世之人家子孙。不保祖业。至若馆宇台榭。不能世守。或为他人所占有。而今公之云仍。克绍克述。使数百年已荒之址。复新乎耳目。可谓韪且贤矣。教官遣其胤鹤九。徵记于余。余虽老病谫劣。窃仰公隐居求道之志。深嘉其贤嗣为先效诚之勤。略为之记。而恨无古人笔力。不能尽匡庐之胜观也。然有一言可谂者。公之诸后承。不以堂构为能事之毕。每修花树之会于是堂。共励磨砻。勿坠祖先之遗韵馀馥。不亦宜乎。李氏诸君勉之哉。
曰匡庐。与中州之形胜齐美焉。吾道峰奇秀而卫立。浣花溪清漪而横带。嘉木奇岩。苍松绿竹。共助幽静之趣。宜其为君子遁世栖息之地也。杜谷李公益亨。以寒冈先生之游从。严辨义理。斥奸小诬贤之论。逍遥于洛江上。晚卜此山。爰筑一堂。与同志诸名硕。讲磨道义。蔚然为南州之望矣。自经龙蛇之难。堂遂坏废。而山川之精彩犹存焉。后孙乃合谋重构。始于甲辰而落于翌年。其殚力董干者。教官钟坤与润九也。余观世之人家子孙。不保祖业。至若馆宇台榭。不能世守。或为他人所占有。而今公之云仍。克绍克述。使数百年已荒之址。复新乎耳目。可谓韪且贤矣。教官遣其胤鹤九。徵记于余。余虽老病谫劣。窃仰公隐居求道之志。深嘉其贤嗣为先效诚之勤。略为之记。而恨无古人笔力。不能尽匡庐之胜观也。然有一言可谂者。公之诸后承。不以堂构为能事之毕。每修花树之会于是堂。共励磨砻。勿坠祖先之遗韵馀馥。不亦宜乎。李氏诸君勉之哉。大隐斋记
余闻小隐隐陵薮。大隐隐朝市。今芮翁武汝。隐于野者。奚以谓大隐。鳌山之大田。即其攸居也。韬光铲迹。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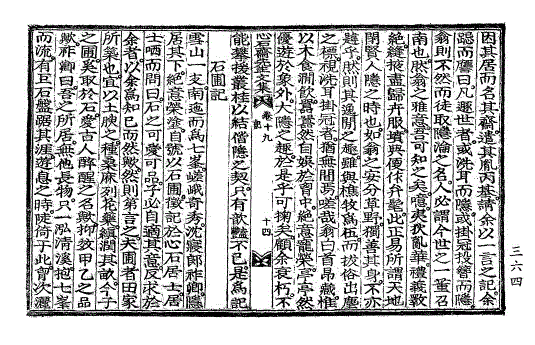 因其居而名其斋。遣其胤丙基。请余以一言之记。余跽而应曰。凡遁世者。或洗耳而隐。或挂冠投簪而隐。翁则不然而徒取隐沦之名。人必谓今世之一董召南也。然翁之雅意。吾可知之矣。噫。夷狄乱华。礼义斁绝。缝掖尽归卉服。坟典便作弁髦。此正易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也。如翁之安分草野。独善其身。不亦韪乎。然则其逸閒之趣。虽与樵牧为伍。而拔俗出尘之标。视洗耳挂冠者。犹无间焉。嗟哉翁白首昂藏。惟以木食涧饮。嚣嚣然自娱于胸中。绝意宠荣。亭亭然优游于象外。大隐之趣。于是乎可掬矣。顾余衰朽。不能攀援丛桂以结偕隐之契。只有歆艳不已。是为记。
因其居而名其斋。遣其胤丙基。请余以一言之记。余跽而应曰。凡遁世者。或洗耳而隐。或挂冠投簪而隐。翁则不然而徒取隐沦之名。人必谓今世之一董召南也。然翁之雅意。吾可知之矣。噫。夷狄乱华。礼义斁绝。缝掖尽归卉服。坟典便作弁髦。此正易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也。如翁之安分草野。独善其身。不亦韪乎。然则其逸閒之趣。虽与樵牧为伍。而拔俗出尘之标。视洗耳挂冠者。犹无间焉。嗟哉翁白首昂藏。惟以木食涧饮。嚣嚣然自娱于胸中。绝意宠荣。亭亭然优游于象外。大隐之趣。于是乎可掬矣。顾余衰朽。不能攀援丛桂以结偕隐之契。只有歆艳不已。是为记。石圃记
雪山一支。南迤而为七峰。嵯峨奇秀。沈寝郎祚卿。隐居其下。绝意荣涂。自号以石圃。徵记于心石居士。居士哂而问曰。石之可爱可品。子必自适其意。反求于余者。以余为知己而然欤。然则第言之。夫圃者田家所筑也。宜以土腴之。种桑麻列花药。缜润其亩。今子之圃。奚取于石。爱古人醉醒之名欤。抑效甲乙之品欤。祚卿曰。吾之所居。无他长物。只一泓清溪。抱七峰而流。有巨石盘踞其涯。游息之时。陡倚于此。胸次洒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5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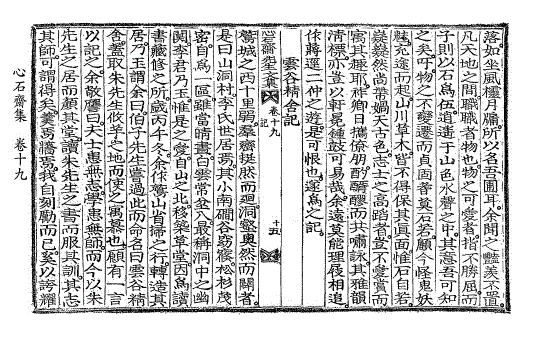 落。如坐风棂月牖。所以名吾圃耳。余闻之艳羡不置。凡天地之间。职职者物也。物之可爱者。指不胜屈。而子则以石为伍。逍遥于山色水声之中。其意吾可知之矣。吁。物之不变迁而贞固耆莫石若。顾今怪鬼妖魅。充途而起。山川草木。皆不得保其真面。惟石自若。嶷嶷然尚带娲天古色。志士之高蹈者。岂不爱赏而寓其趣耶。祚卿日携僚朋。酌醑醪而共啸咏。其雅韵清标。亦岂以轩冕钟鼓可易哉。余远莫能理屐相追。作蒋径二仲之游。是可恨也。遂为之记。
落。如坐风棂月牖。所以名吾圃耳。余闻之艳羡不置。凡天地之间。职职者物也。物之可爱者。指不胜屈。而子则以石为伍。逍遥于山色水声之中。其意吾可知之矣。吁。物之不变迁而贞固耆莫石若。顾今怪鬼妖魅。充途而起。山川草木。皆不得保其真面。惟石自若。嶷嶷然尚带娲天古色。志士之高蹈者。岂不爱赏而寓其趣耶。祚卿日携僚朋。酌醑醪而共啸咏。其雅韵清标。亦岂以轩冕钟鼓可易哉。余远莫能理屐相追。作蒋径二仲之游。是可恨也。遂为之记。云谷精舍记
鹫城之西十里弱。群峦挺然而回。洞壑奥然而辟者。是曰山洞村。李氏世居焉。其小南涧谷窈窱。松杉茂密。自为一区。虽当晴昼。白云常坌入。最称洞中之幽阒。李君乃玉。惟是之爱。自山之北。移筑草堂。因为读书藏修之所。岁丙午冬。余作鹫山省扫之行。转造其居。乃玉谓余曰。伯子先生尝过此而命名曰云谷精舍。盖取朱先生攸芋之地而使之寓慕也。愿有一言以记之。余敬应曰。夫士患无志。学患无师。而今以朱先生之居而颜其堂。读朱先生之书而服其训。其志其师。可谓得矣。羹焉墙焉。我自刻励而已。奚以誇耀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5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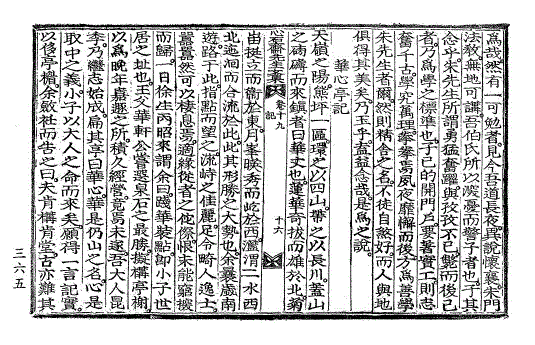 为哉。然有一可勉者。见今吾道长夜。异说怀襄。朱门法教。无地可讲。吾伯氏所以深忧而警子者也。子其念乎。朱先生所谓勇猛奋跃。与孜孜不已。毙而后已者。乃为学之标准也。子已的开门户。要著实工。则志奋千古。学究万理。拳拳焉夙夜靡懈而后。方为善学朱先生者尔。然则精舍之名。不徒自煞好。而人与地俱得其美矣。乃玉乎。盍益念哉。是为之说。
为哉。然有一可勉者。见今吾道长夜。异说怀襄。朱门法教。无地可讲。吾伯氏所以深忧而警子者也。子其念乎。朱先生所谓勇猛奋跃。与孜孜不已。毙而后已者。乃为学之标准也。子已的开门户。要著实工。则志奋千古。学究万理。拳拳焉夙夜靡懈而后。方为善学朱先生者尔。然则精舍之名。不徒自煞好。而人与地俱得其美矣。乃玉乎。盍益念哉。是为之说。华心亭记
天岭之阳。熊坪一区。环之以四山。带之以长川。盖山之磅礴而来镇者曰华丈也。莲华奇拔而雄于北。菊岫挺立而卫于东。月峰映秀而屹于西。灆渭二水西北迤洄而合流于此。此其形胜之大势也。余曩岁南游。路于此。指点而望之。流峙之佳丽。足令畸人逸士。嚣嚣然可以栖息焉。适缘从者之佗傺。恨未能穷探而归。一日徐生丙昭来谓余曰。践华装点。即小子世居之址也。王父华轩公尝选泉石之最胜。拟构亭榭。以为晚年嘉遁之所。积久经营。竟焉未遂。吾大人昆季。乃继志始成。扁其亭曰华心。华是仍山之名。心是取中之义。小子以大人之命而来矣。愿得一言记实。以侈亭楣。余敛衽而告之曰。夫肯构肯堂。古亦难其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6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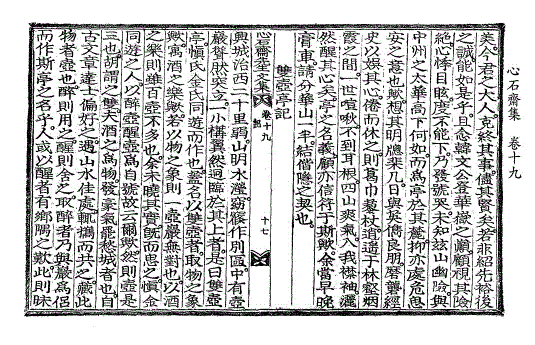 美。今君之大人。克终其事。尽其贤矣。若非绍先裕后之诚。能如是乎。且念韩文公登华岳之巅。顾视其险绝。心悸目眩。度不能下。乃发号哭。未知玆山幽险。与中州之太华高下何如。而为亭于其麓。抑亦处危思安之意也欤。想其明窗棐几。日与英俊良朋。磨砻经史以娱其心。倦而休之。则葛巾藜杖。逍遥于林壑烟霞之间。一世喧啾。不到耳根。四山爽气。入我襟袖。洒然醒其心矣。亭之名义。顾亦信符于斯欤。余当早晚膏车。请分华山一半。结偕隐之契也。
美。今君之大人。克终其事。尽其贤矣。若非绍先裕后之诚。能如是乎。且念韩文公登华岳之巅。顾视其险绝。心悸目眩。度不能下。乃发号哭。未知玆山幽险。与中州之太华高下何如。而为亭于其麓。抑亦处危思安之意也欤。想其明窗棐几。日与英俊良朋。磨砻经史以娱其心。倦而休之。则葛巾藜杖。逍遥于林壑烟霞之间。一世喧啾。不到耳根。四山爽气。入我襟袖。洒然醒其心矣。亭之名义。顾亦信符于斯欤。余当早晚膏车。请分华山一半。结偕隐之契也。双壶亭记
兴城治西二十里弱。山明水滢。窈窱作别区。中有壶岩耸然突立。一小构翼然迥临于其上者。是曰双壶亭。慎氏金氏同游而作也。盖名以双壶者。取物之象欤。寓酒之乐欤。若以物之象则一壶岩无对也。以酒之乐则虽百壶不多也。余未晓其实。既而思之。慎金同游之人。以醉壶醒壶为自号故云尔欤。然则壶是三也。胡谓之双。夫酒之为物。发豪气罢愁城者也。自古文章达士偏好之。遇山水佳处。辄携而共之。藏此物者壶也。醉则用之。醒则舍之。取醉者乃与岩为侣而作斯亭之名乎。人或以醒者有乡隅之叹。此则昧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6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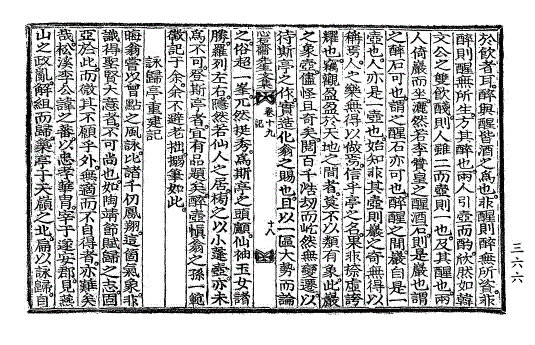 于饮者耳。醉与醒皆酒之为也。非醒则醉无所资。非醉则醒无所生。方其醉也。两人引壶而酌。欣然如韩文公之双饮盏。则人虽二而壶则一也。及其醒也。两人倚岩而坐。洒然若李赞皇之醒酒石。则是岩也谓之醉石可也。谓之醒石亦可也。醉醒之间。岩自是一壶也。人亦是一壶也。始知非其壶则岩之奇无得以称焉。人之乐无得以做焉。信乎亭之名。果非捺虚誇耀也。窃观盈盈于天地之间者。莫不以类有象。此岩之象壶。尽怪且奇矣。阅百千浩劫而屹然无变迁。以待斯亭之作。实造化翁之赐也。且以一区大势而论之。俗超一峰。兀然挺秀。为斯亭之头颅。仙袖玉女诸胜。罗列左右。隐然若仙人之居。榜之以小蓬壶。亦未为不可。登斯亭者。宜有品题矣。醉壶慎翁之孙一范徵记于余。余不避老拙。搦笔如此。
于饮者耳。醉与醒皆酒之为也。非醒则醉无所资。非醉则醒无所生。方其醉也。两人引壶而酌。欣然如韩文公之双饮盏。则人虽二而壶则一也。及其醒也。两人倚岩而坐。洒然若李赞皇之醒酒石。则是岩也谓之醉石可也。谓之醒石亦可也。醉醒之间。岩自是一壶也。人亦是一壶也。始知非其壶则岩之奇无得以称焉。人之乐无得以做焉。信乎亭之名。果非捺虚誇耀也。窃观盈盈于天地之间者。莫不以类有象。此岩之象壶。尽怪且奇矣。阅百千浩劫而屹然无变迁。以待斯亭之作。实造化翁之赐也。且以一区大势而论之。俗超一峰。兀然挺秀。为斯亭之头颅。仙袖玉女诸胜。罗列左右。隐然若仙人之居。榜之以小蓬壶。亦未为不可。登斯亭者。宜有品题矣。醉壶慎翁之孙一范徵记于余。余不避老拙。搦笔如此。咏归亭重建记
晦翁尝以曾点之风咏。比诸千仞凤翔。这个气象。非识得圣贤大意者。不可尚也。如陶靖节赋归之志。固亚于此。而微其不愿乎外。无适而不自得者。亦难矣哉。松溪李公讳之蕃。以忠孝华胄。宰于遂安郡。见燕山之政乱。解组而归。筑亭于天岭之北。扁以咏归。自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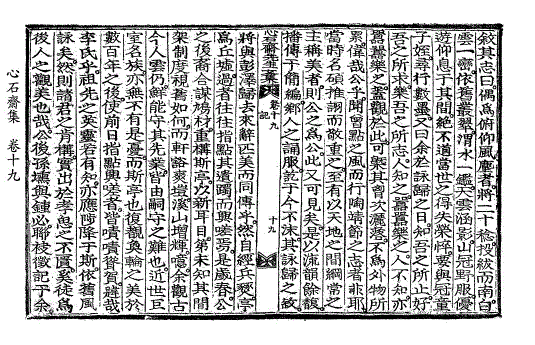 叙其志曰。偶为俯仰风尘者。将二十稔。投绂而南。白云一峦。依旧丛翠。渭水一鉴。天云涵影。山冠野服。优游仰息于其间。绝不道当世之得失荣悴。要与冠童子侄。寻行数墨。又曰余于咏归之日。知吾之所止。好吾之所求。乐吾之所志。人知之。嚣嚣乐之。人不知。亦嚣嚣乐之。盖观于此。可槩其胸次洒落。不为外物所累。伟哉公乎。闻曾点之风而行陶靖节之志者非耶。当时名硕推诩而敬重之。至有以天地之间纲常之主称美者。则公之为公。此又可见矣。是以流韵馀馥。播传于𥳑编。乡人之诵服。讫于今不沫。其咏归之叙。将与彭泽归去来辞匹美而同传乎。然自经兵燹。亭为丘墟。过者往往指点其遗躅而兴嗟焉。是岁春。公之后裔合谋鸠材。重构斯亭。以新耳目。第未知其间架制度视旧如何。而轩豁爽垲。溪山增辉。噫。余观古今人云仍。鲜能守其先业。皆由嗣守之难也。近世巨室名族。亦无不有是忧。而斯亭也复睹奂轮之美于数百年之后。使前日指点兴嗟者。皆啧啧耸贺。韪哉李氏乎。祖先之英灵若有知。亦应陟降于斯。依旧风咏矣。然则诸君之肯构。实出于孝思之不匮。奚徒为后人之观美也哉。公后孙埙与钟必。联袂徵记于余。
叙其志曰。偶为俯仰风尘者。将二十稔。投绂而南。白云一峦。依旧丛翠。渭水一鉴。天云涵影。山冠野服。优游仰息于其间。绝不道当世之得失荣悴。要与冠童子侄。寻行数墨。又曰余于咏归之日。知吾之所止。好吾之所求。乐吾之所志。人知之。嚣嚣乐之。人不知。亦嚣嚣乐之。盖观于此。可槩其胸次洒落。不为外物所累。伟哉公乎。闻曾点之风而行陶靖节之志者非耶。当时名硕推诩而敬重之。至有以天地之间纲常之主称美者。则公之为公。此又可见矣。是以流韵馀馥。播传于𥳑编。乡人之诵服。讫于今不沫。其咏归之叙。将与彭泽归去来辞匹美而同传乎。然自经兵燹。亭为丘墟。过者往往指点其遗躅而兴嗟焉。是岁春。公之后裔合谋鸠材。重构斯亭。以新耳目。第未知其间架制度视旧如何。而轩豁爽垲。溪山增辉。噫。余观古今人云仍。鲜能守其先业。皆由嗣守之难也。近世巨室名族。亦无不有是忧。而斯亭也复睹奂轮之美于数百年之后。使前日指点兴嗟者。皆啧啧耸贺。韪哉李氏乎。祖先之英灵若有知。亦应陟降于斯。依旧风咏矣。然则诸君之肯构。实出于孝思之不匮。奚徒为后人之观美也哉。公后孙埙与钟必。联袂徵记于余。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7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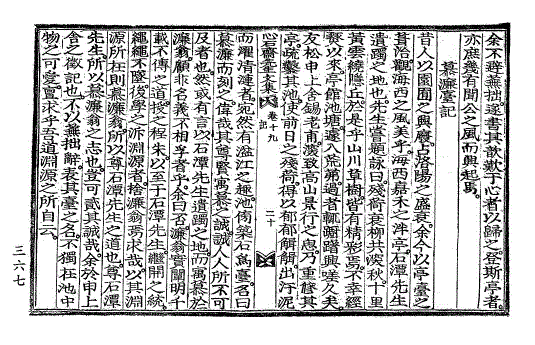 余不避芜拙。遂书其歆叹于心者以归之。登斯亭者。亦庶几有闻公之风而兴起焉。
余不避芜拙。遂书其歆叹于心者以归之。登斯亭者。亦庶几有闻公之风而兴起焉。慕濂台记
昔人以园囿之兴废。占洛阳之盛衰。余今以亭台之葺治。观海西之风美乎。海西嘉禾之泮亭。石潭先生遗躅之地也。先生尝题咏曰。残荷衰柳共深秋。十里黄云绕隐丘。于是乎山川草树。皆有精彩焉。不幸经燹以来。亭馆池塘。遽入荒茀。过者辄蹰躇兴嗟久矣。友松申上舍锡老甫。深致高山景行之思。乃重修其亭。疏凿其池。使前日之残荷。得以郁郁𧤏𧤏。出污泥而濯清涟者。宛然有湓江之趣。池傍筑石为台。名曰慕濂而刻之。伟哉其尊贤寓慕之诚。诚人人所不可及者也。然或有言以石潭先生遗躅之地。而寓慕于濂翁。顾非名义不相孚者乎。余曰否。濂翁实阐明千载不传之道。授之程朱。以至于石潭先生。继开之统。绳绳不坠。后学之溯渊源者。舍濂翁焉求哉。以其渊源所在则慕濂翁。所以尊石潭先生之道也。尊石潭先生。所以慕濂翁之志也。岂可贰其诚哉。余于申上舍之徵记也。不以芜拙辞。表其台之名。不独在池中物之可爱。亶求乎吾道渊源之所自云。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8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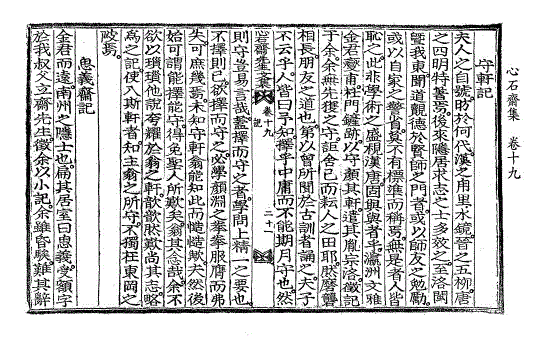 守轩记
守轩记夫人之自号。昉于何代。汉之甪里,水镜。晋之五柳。唐之四明特著焉。后来隐居求志之士多效之。至洛闽暨我东。闻道觌德于贤师之门者。或以师友之勉励。或以自家之警省。莫不有标准而称焉。无是者人皆耻之。此非学术之盛视汉唐。固与与者乎。瀛洲文雅金君燮甫。杜门铲迹。以守颜其轩。遣其胤宗洛。徵记于余。余无先获之守。讵舍己而耘人之田耶。然磨砻相长。朋友之道也。第以曾所闻于古训者诵之。夫子不云乎。人皆曰予知。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。然则守岂易言哉。盖择而守之者。学问上精一之要也。不择则已。欲择而守之。必学颜渊之拳拳服膺而弗失。可庶几焉。未知守轩翁能知此而慥慥欤。夫然后始可谓能择能守。得免圣人所叹矣。翁其念哉。余不欲以琐琐他说夸耀于翁之轩。歆歆然叹尚其志。略为之记。使入斯轩者。知主翁之所守。不独在东冈之陂焉。
思义斋记
金君而远。南州之隐士也。扁其居室曰思义。受额字于我叔父立斋先生。徵余以小记。余虽昏騃。难其辞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8L 页
 曰。子之所思。是对仁之义欤。对利之义欤。若对仁也则自在乎子之性中。只好养而体验之。若对利也则毅然如一剑两段。事事物物。处得其宜。使计较利害之私不容于胸中。始可曰义耳。然统而论之。对仁与对利。皆理之宜也。奉顺乎天而已。是以夫子以喻义喻利。判君子小人。余观而远名斋之意。可知其欲为君子儒也欤。况今叔季。忘义趋利者。滔滔若狂澜争奔。而子能自励奋跃则其志尤可尚也。晦翁尝洞析义与利曰。天下只有一理。此是则彼非。此非则彼是。不容并立。故古之圣贤心存目见。只有义理。都不见有利害可计较。日用之间。应事接物。直是判断得直截分明。推以及人。吐心吐胆。亦只如此。若信得及。即相与入圣贤之域。此盖万古成训。揭如日星矣。惟而远苟于此训信之。若耳提面命而拳拳服膺已足矣。奚求余赘言哉。然窃有一焉。敬义夹持。自是做工夫之纲领。此心之未发也。敬以养之。私欲之有萌也。义以制之。显微动静之间。无少违戾。方立得临大节而不可夺底气象。盖敬与义废一不得。子其念哉。
曰。子之所思。是对仁之义欤。对利之义欤。若对仁也则自在乎子之性中。只好养而体验之。若对利也则毅然如一剑两段。事事物物。处得其宜。使计较利害之私不容于胸中。始可曰义耳。然统而论之。对仁与对利。皆理之宜也。奉顺乎天而已。是以夫子以喻义喻利。判君子小人。余观而远名斋之意。可知其欲为君子儒也欤。况今叔季。忘义趋利者。滔滔若狂澜争奔。而子能自励奋跃则其志尤可尚也。晦翁尝洞析义与利曰。天下只有一理。此是则彼非。此非则彼是。不容并立。故古之圣贤心存目见。只有义理。都不见有利害可计较。日用之间。应事接物。直是判断得直截分明。推以及人。吐心吐胆。亦只如此。若信得及。即相与入圣贤之域。此盖万古成训。揭如日星矣。惟而远苟于此训信之。若耳提面命而拳拳服膺已足矣。奚求余赘言哉。然窃有一焉。敬义夹持。自是做工夫之纲领。此心之未发也。敬以养之。私欲之有萌也。义以制之。显微动静之间。无少违戾。方立得临大节而不可夺底气象。盖敬与义废一不得。子其念哉。思厚斋记
湖南牟阳之嘉植洞。即平山申氏两世衣履所藏也。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9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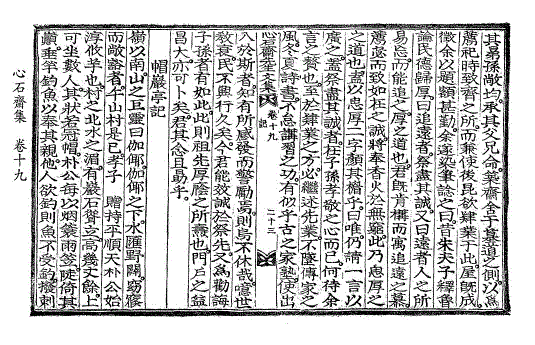 其昆孙敞均。承其父兄命。筑斋舍于墓道之侧。以为荐祀时致齐之所。而兼使后昆欲肄业于此。屋既成。徵余以题额甚勤。余遂染笔谂之曰。昔朱夫子释鲁论民德归厚。曰追远者。祭尽其诚。又曰远者人之所易忘。而能追之。厚之道也。君既肯构而寓追远之慕。荐苾而致如在之诚。将奉香火于无穷。此乃思厚之之道也。盍以思厚二字颜其楣乎。曰唯。仍请一言以广之。盖祭尽其诚者。在子孙孝敬之心而已。何待余言之赘也。至于肄业之方。必继述先业。不坠传家之风。冬夏诗书。不怠讲习之功。有似乎古之家塾。使出入于斯者。知有所感发而警励焉。则乌不休哉。噫世教衰。民不兴行久矣。今君能效诚于祭先。又为劝诲子孙者有如此。此则祖先厚荫之所焘也。门户之益昌大。亦可卜矣。君其念且勖乎。
其昆孙敞均。承其父兄命。筑斋舍于墓道之侧。以为荐祀时致齐之所。而兼使后昆欲肄业于此。屋既成。徵余以题额甚勤。余遂染笔谂之曰。昔朱夫子释鲁论民德归厚。曰追远者。祭尽其诚。又曰远者人之所易忘。而能追之。厚之道也。君既肯构而寓追远之慕。荐苾而致如在之诚。将奉香火于无穷。此乃思厚之之道也。盍以思厚二字颜其楣乎。曰唯。仍请一言以广之。盖祭尽其诚者。在子孙孝敬之心而已。何待余言之赘也。至于肄业之方。必继述先业。不坠传家之风。冬夏诗书。不怠讲习之功。有似乎古之家塾。使出入于斯者。知有所感发而警励焉。则乌不休哉。噫世教衰。民不兴行久矣。今君能效诚于祭先。又为劝诲子孙者有如此。此则祖先厚荫之所焘也。门户之益昌大。亦可卜矣。君其念且勖乎。帽岩亭记
岭以南。山之巨灵曰伽倻。伽倻之下。水汇野辟。窈窱而敞豁者。午山村是已。孝子 赠持平顺天朴公始淳攸芋也。村之北水之湄。有岩石耸立。高几丈馀。上可坐数人。其状若冠帽。朴公每以烟蓑雨笠。陡倚其巅。垂竿钓鱼以奉其亲。他人欲钓则鱼不受钓。拨剌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6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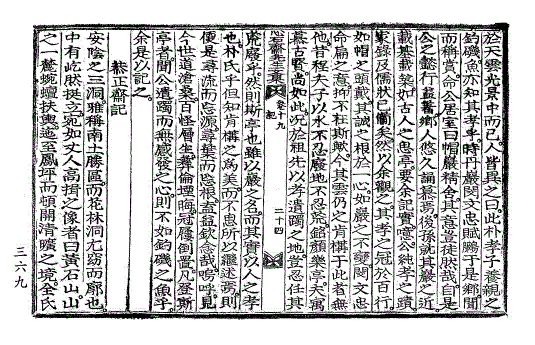 于天云光景中而已。人皆异之曰。此朴孝子养亲之钓矶。鱼亦知其孝乎。时丹岩闵文忠赋鵩于是乡。闻而称赏。命公居室曰帽岩精舍。其意岂徒然哉。自是公之懿行益著。乡人悠久诵慕焉。后孙就其岩之近。载基载筑。如古人之思亭。要余记实。噫。公纯孝之迹。家录及儒状已备矣。然以余观之。其孝之冠于百行。如帽之头戴。其诚之根于一心。如岩之不变。闵文忠命扁之意。抑不在斯欤。今其云仍之肯构于此者无他。昔程夫子以水不忍废地不忍荒。铭颜乐亭。夫寓慕古贤。尚如此。况于祖先以孝遗躅之地。岂忍任其荒废乎。然则斯亭也虽以岩之名。而其实以人之孝也。朴氏乎但知肯构之为美。而不思所以继述焉。则便是寻流而忘源。寻叶而忘根。盍益钦念哉。呜呼。见今世道沧桑。百怪层生。彝伦堙晦。冠屦倒置。凡登斯亭者。闻公遗躅而无感发之心。则不如钓矶之鱼乎。余是以记之。
于天云光景中而已。人皆异之曰。此朴孝子养亲之钓矶。鱼亦知其孝乎。时丹岩闵文忠赋鵩于是乡。闻而称赏。命公居室曰帽岩精舍。其意岂徒然哉。自是公之懿行益著。乡人悠久诵慕焉。后孙就其岩之近。载基载筑。如古人之思亭。要余记实。噫。公纯孝之迹。家录及儒状已备矣。然以余观之。其孝之冠于百行。如帽之头戴。其诚之根于一心。如岩之不变。闵文忠命扁之意。抑不在斯欤。今其云仍之肯构于此者无他。昔程夫子以水不忍废地不忍荒。铭颜乐亭。夫寓慕古贤。尚如此。况于祖先以孝遗躅之地。岂忍任其荒废乎。然则斯亭也虽以岩之名。而其实以人之孝也。朴氏乎但知肯构之为美。而不思所以继述焉。则便是寻流而忘源。寻叶而忘根。盍益钦念哉。呜呼。见今世道沧桑。百怪层生。彝伦堙晦。冠屦倒置。凡登斯亭者。闻公遗躅而无感发之心。则不如钓矶之鱼乎。余是以记之。恭正斋记
安阴之三洞。雅称南土胜区。而花林洞尤窈而廓也。中有屹然挺立。宛如丈人高揖之像者曰黄石山。山之一麓蜿蟺扶舆。迤至凤坪而顿开清旷之境。全氏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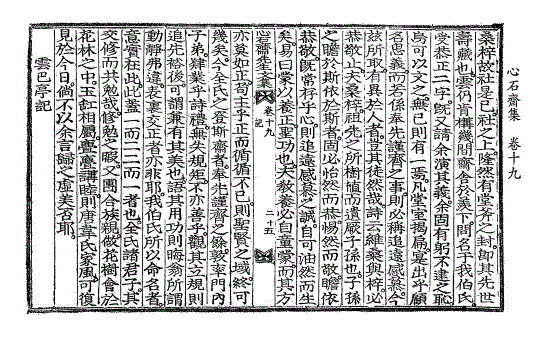 桑梓故社是已。社之上。隆然有堂斧之封。即其先世寿藏也。云仍肯构几间斋舍于羡下。问名于我伯氏。受恭正二字。既又请余演其义。余固有躬不逮之耻。乌可以文之。无已则有一焉。凡堂室揭扁。寔出乎顾名思义。而若系奉先谨齐之事。则必称追远感慕。今玆所取。有异于人者。岂其徒然哉。诗云维桑与梓。必恭敬止。夫桑梓。祖先之所树植而遗厥子孙也。子孙之瞻于斯依于斯者。固必怡然而恭。惕然而敬。瞻依恭敬。既常存乎心。则追远感慕之诚。自可油然而生矣。易曰蒙以养正。圣功也。夫教养必自童蒙。而其方亦莫如正。苟主乎正而循循不已。则圣贤之域。终可几矣。今全氏之登斯斋者。奉先谨齐之馀。敦率门内子弟。肄业乎诗礼。无失规矩。不亦善乎。观其立规则追先裕后。可谓兼有其美也。语其用功则晦翁所谓动静弗违。表里交正者亦非耶。我伯氏所以命名者。意实在此。此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。全氏诸君子。其交修而共勉哉。修勉之暇。又团合族亲。做花树会于花林之中。玉缸相属。亹亹讲睦。则唐韦氏家风。可复见于今日。倘不以余言归之虚美否耶。
桑梓故社是已。社之上。隆然有堂斧之封。即其先世寿藏也。云仍肯构几间斋舍于羡下。问名于我伯氏。受恭正二字。既又请余演其义。余固有躬不逮之耻。乌可以文之。无已则有一焉。凡堂室揭扁。寔出乎顾名思义。而若系奉先谨齐之事。则必称追远感慕。今玆所取。有异于人者。岂其徒然哉。诗云维桑与梓。必恭敬止。夫桑梓。祖先之所树植而遗厥子孙也。子孙之瞻于斯依于斯者。固必怡然而恭。惕然而敬。瞻依恭敬。既常存乎心。则追远感慕之诚。自可油然而生矣。易曰蒙以养正。圣功也。夫教养必自童蒙。而其方亦莫如正。苟主乎正而循循不已。则圣贤之域。终可几矣。今全氏之登斯斋者。奉先谨齐之馀。敦率门内子弟。肄业乎诗礼。无失规矩。不亦善乎。观其立规则追先裕后。可谓兼有其美也。语其用功则晦翁所谓动静弗违。表里交正者亦非耶。我伯氏所以命名者。意实在此。此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。全氏诸君子。其交修而共勉哉。修勉之暇。又团合族亲。做花树会于花林之中。玉缸相属。亹亹讲睦。则唐韦氏家风。可复见于今日。倘不以余言归之虚美否耶。云巴亭记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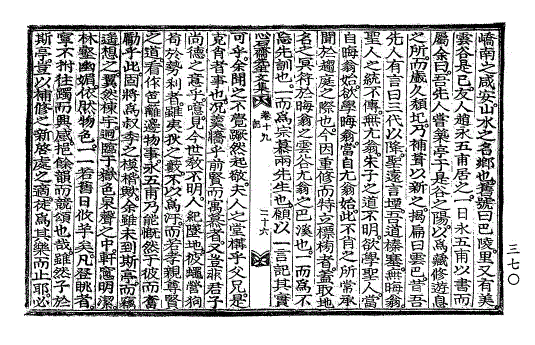 峤南之咸安。山水之名乡也。旧号曰巴陵。里又有美。云谷是已。友人赵永五甫居之。一日永五甫以书而属余曰。吾先人尝筑亭于是谷之阳。以为藏修游息之所。而岁久颓圮。乃补葺以新之。揭扁曰云巴。昔吾先人有言曰三代以降。圣远言堙。吾道榛塞。无晦翁。圣人之统不传。无尤翁。朱子之道不明。欲学圣人。当自晦翁始。欲学晦翁。当自尤翁始。此不肖之所常承闻于趋庭之际也。今因重修而特立标榜者。盖取地名之冥符于晦翁之云谷尤翁之巴溪也。一而为不忘先训也。一而为宗慕两先生也。愿以一言记其实可乎。余闻之不觉蹶然起敬。夫人之堂构乎父兄。是克肖者事也。况羹墙乎前贤而寓慕者。又岂非君子尚德之意乎。噫。见今世教不明。人纪坠地。彼蝇营狗苟于势利者。虽夷狄之薮。不以为污。而若孝亲尊贤之道。看作笆篱边物事。永五甫乃能慨然于彼而奋励乎此。固将为叔季之模楷欤。余虽未到斯亭。而窃遥想之。翼然栋宇。迥临于岳色泉声之中。轩窗明洁。林壑幽媚。依然物色。一一若旧日攸芋矣。凡登眺者。宁不拊往躅而兴感。挹馀韵而竞颂也哉。虽然子于斯亭。岂以补修之新启处之适。徒为其乐而止耶。必
峤南之咸安。山水之名乡也。旧号曰巴陵。里又有美。云谷是已。友人赵永五甫居之。一日永五甫以书而属余曰。吾先人尝筑亭于是谷之阳。以为藏修游息之所。而岁久颓圮。乃补葺以新之。揭扁曰云巴。昔吾先人有言曰三代以降。圣远言堙。吾道榛塞。无晦翁。圣人之统不传。无尤翁。朱子之道不明。欲学圣人。当自晦翁始。欲学晦翁。当自尤翁始。此不肖之所常承闻于趋庭之际也。今因重修而特立标榜者。盖取地名之冥符于晦翁之云谷尤翁之巴溪也。一而为不忘先训也。一而为宗慕两先生也。愿以一言记其实可乎。余闻之不觉蹶然起敬。夫人之堂构乎父兄。是克肖者事也。况羹墙乎前贤而寓慕者。又岂非君子尚德之意乎。噫。见今世教不明。人纪坠地。彼蝇营狗苟于势利者。虽夷狄之薮。不以为污。而若孝亲尊贤之道。看作笆篱边物事。永五甫乃能慨然于彼而奋励乎此。固将为叔季之模楷欤。余虽未到斯亭。而窃遥想之。翼然栋宇。迥临于岳色泉声之中。轩窗明洁。林壑幽媚。依然物色。一一若旧日攸芋矣。凡登眺者。宁不拊往躅而兴感。挹馀韵而竞颂也哉。虽然子于斯亭。岂以补修之新启处之适。徒为其乐而止耶。必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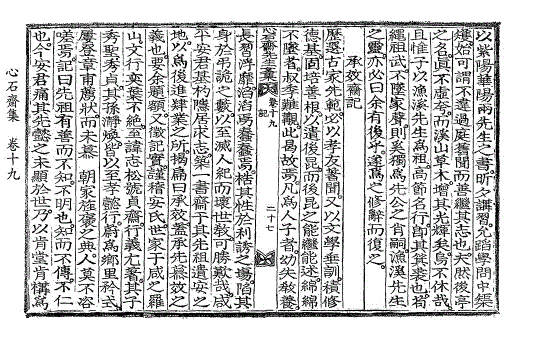 以紫阳华阳两先生之书。昕夕讲习。允蹈学问中矩矱。始可谓不违过庭旧闻而善继其志也。夫然后亭之名。真不虚夸。而溪山草木。增其光辉矣。乌不休哉。且惟子以渔溪先生为祖。高节名行。即其箕裘也。苟绳祖武。不坠家声。则奚独为先公之肖嗣。渔溪先生之灵。亦必曰余有后乎。遂为之修辞而复之。
以紫阳华阳两先生之书。昕夕讲习。允蹈学问中矩矱。始可谓不违过庭旧闻而善继其志也。夫然后亭之名。真不虚夸。而溪山草木。增其光辉矣。乌不休哉。且惟子以渔溪先生为祖。高节名行。即其箕裘也。苟绳祖武。不坠家声。则奚独为先公之肖嗣。渔溪先生之灵。亦必曰余有后乎。遂为之修辞而复之。承效斋记
历选古家先范。必以孝友著闻。又以文学垂训。积修德基。固培善根。以遗后昆。而后昆之能继能述。绵绵不坠者。叔季难觏。此曷故焉。凡为人子者。幼失教养。长习浮靡。滔滔焉蠢蠢焉。梏其性于利诱之场。陷其身于吊诡之薮。以至灭人纪而坏世教。可胜叹哉。咸平安君基杓隐居求志。筑一书斋于其先祖遗安之地。以为后进肄业之所。揭扁曰承效。盖承先慕效之义也。要余题额。又徵记实。谨稽安氏。世家于咸之罗山。文行奕叶不绝。至讳志松号贞斋。行义尤著。其子秀圣,秀贞。其孙净焕。皆以至孝懿行。蔚为乡里矜式。屡登章甫荐状。而未慕 朝家旌褒之典。人莫不咨嗟焉。记曰先祖有善而不知。不明也。知而不传。不仁也。今安君痛其先懿之未显于世。乃以肯堂肯构为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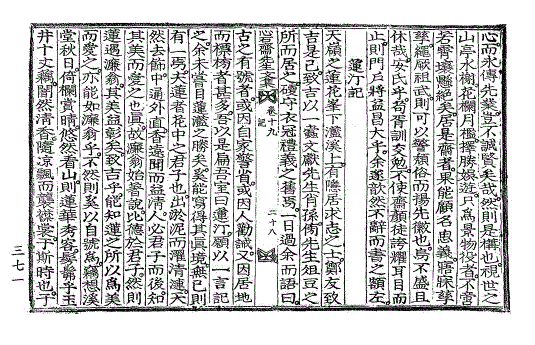 心。而永传先业。岂不诚贤矣哉。然则是构也。视世之山亭水榭。花栏月槛。择胜娱游。只为景物役者。不啻若霄壤悬绝矣。居是斋者。果能顾名思义。寤寐孳孳。绳厥祖武。则可以警颓俗而扬先徽也。乌不盛且休哉。安氏乎。苟胥训交勉。不使斋颜徒誇耀耳目而止。则门户将益昌大乎。余遂歆然不辞而书之额左。
心。而永传先业。岂不诚贤矣哉。然则是构也。视世之山亭水榭。花栏月槛。择胜娱游。只为景物役者。不啻若霄壤悬绝矣。居是斋者。果能顾名思义。寤寐孳孳。绳厥祖武。则可以警颓俗而扬先徽也。乌不盛且休哉。安氏乎。苟胥训交勉。不使斋颜徒誇耀耳目而止。则门户将益昌大乎。余遂歆然不辞而书之额左。莲汀记
天岭之莲花峰下灆溪上。有隐居求志之士。郑友致吉是已。致吉以一蠹文献先生肖孙。傍先生俎豆之所而居之。硬守衣冠礼义之旧焉。一日过余而语曰。古之有号者。或因自家警省。或因人劝诫。又因居地而标榜者甚多。吾以是扁吾室曰莲汀。愿以一言记之。余未尝目莲灆之胜矣。奚能写得其真境。无已则有一焉。夫莲者花中之君子也。出淤泥而濯清涟。天然去饰。中通外直。香远闻而益清。人必君子而后。知其美而爱之也真。故濂翁始著说。比德于君子。然则莲遇濂翁。其美益彰矣。致吉乎。能知莲之所以为美而爱之。亦能如濂翁乎。不然则奚以自号为。窃想溪堂秋日。倚栏赏晴。悠然看山。则莲华秀容。髣髴乎玉井十丈藕。闇然清香。随凉飘而袭襟裳。于斯时也。子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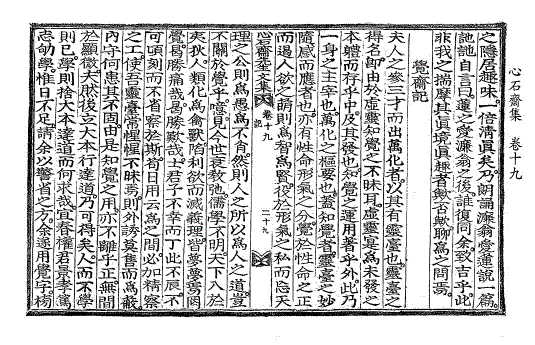 之隐居趣味。一倍清真矣。乃朗诵濂翁爱莲说一篇。訑訑自言曰。莲之爱濂翁之后。谁复同余。致吉乎。此非我之揣摩其真境真趣者欤否欤。聊为之问焉。
之隐居趣味。一倍清真矣。乃朗诵濂翁爱莲说一篇。訑訑自言曰。莲之爱濂翁之后。谁复同余。致吉乎。此非我之揣摩其真境真趣者欤否欤。聊为之问焉。觉斋记
夫人之参三才而出万化者。以其有灵台也。灵台之得名。即由于虚灵知觉之不昧耳。虚灵寔为未发之本体而存乎中。及其发也。知觉之运用著乎外。此乃一身之主宰也。万化之枢要也。盖知觉者。灵台之妙随感而应者也。亦有性命形气之分。觉于性命之正而遏人欲之萌则为智为贤。役于形气之私而忘天理之公则为愚为不肖。然则人之所以为人之道。岂不关于觉乎。噫。见今世衰教弛。儒学不明。天下入于夷狄。人类化为禽兽。陷利欲而灭义理。皆梦梦焉罔觉。曷胜痛哉。曷胜叹哉。士君子不幸而丁此不辰。不可顷刻而不省察于斯。苟日用云为之间。必加精察之工。使吾灵台常惺惺不昧焉。则外诱莫售而为蔽。内守何患其不固。由是知觉之用。亦不离乎正。无间于显微。夫然后立大本行达道。乃可得矣。人而不学则已。学则舍大本达道而何求哉。宜春权君景孝笃志劬学。惟日不足。请余以警省之方。余遂用觉字。榜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2L 页
 其读书之斋。仍为小记以遗之。盖觉之义。见于经者非一二。而其要莫尚乎朱先生说。君其温绎而勉之哉。
其读书之斋。仍为小记以遗之。盖觉之义。见于经者非一二。而其要莫尚乎朱先生说。君其温绎而勉之哉。芝山处士安公旌闾记
旌别淑慝。表厥宅里。昉于成周而为昭代盛典。吾东列圣朝声教之化。可轶成周。孝烈贞忠之绰楔。磊落相望。是岂非彰善之政。上行下效。捷于影响者欤。湖南诗山之瑞芝村。乌头赤脚。煌煌映耀者。故孝子芝山处士安在頀之闾也。诚孝根天。粤自童年。定省温凊。不学而自能。及受小学书。体认力践。以为事亲绳尺。人必称之曰此真小学中人。亲有疾。辄沐浴祷天。十岁出系其从叔父。而家甚贫寠。力服稼穑。奉养尽诚。本生母癠。断指注血。辄得回苏。此虽小学之所无。盖迫于情焦而然耳。及其两庭遭艰。擗踊毁瘠。居庐尽制。亲茔松楸。虫患连生。公泣祝三日。虫患自消。路人指其松曰孝子松。制阕犹每日省墓。虽风雨寒暑不止。晨夕必谒庙。事之如生。每当忌日。宿齐预戒。以尽诚敬。至老靡懈。可谓终身慕者也。构一堂于芝山之阳。谢绝公车。力求经学。贮屡百卷书。以教训子侄。导迪乡秀为己任。及其卒年。移藏其书于武城院。以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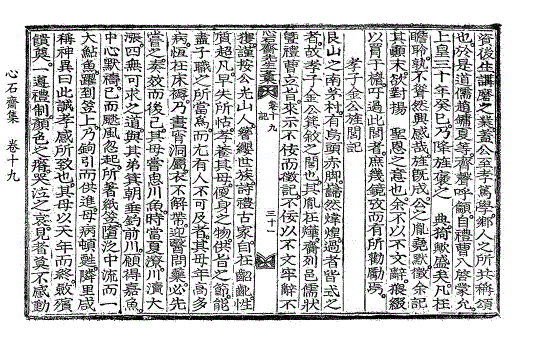 资后生讲磨之业。盖公至孝笃学。乡人之所共称颂也。于是道儒赵镛夏等。齐声呼龥。自礼曹入启蒙允。上皇三十年癸巳。乃降旌褒之 典。猗欤盛矣。凡在瞻聆。孰不耸然兴感哉。旌既成。公之胤尧默。徵余记其颠末。欲对扬 圣恩之意也。余不以不文辞。猥缀以罥于楣。吁过此闾者。庶几镜考而有所劝励焉。
资后生讲磨之业。盖公至孝笃学。乡人之所共称颂也。于是道儒赵镛夏等。齐声呼龥。自礼曹入启蒙允。上皇三十年癸巳。乃降旌褒之 典。猗欤盛矣。凡在瞻聆。孰不耸然兴感哉。旌既成。公之胤尧默。徵余记其颠末。欲对扬 圣恩之意也。余不以不文辞。猥缀以罥于楣。吁过此闾者。庶几镜考而有所劝励焉。孝子金公旌闾记
艮山之南茅村。有乌头赤脚。岿然炜煌。过者皆式之者。故孝子金公箕叙之闾也。其胤在烨。赍列邑儒状暨礼曹立旨。来示不佞而徵记。不佞以不文牢辞不获。谨按公光山人。簪缨世族。诗礼古家。自在龆龀。性质超凡。早失所怙。孝养其母。便身之物。供旨之节。能尽子职之所当为。而尤有人不可及者。其母年高多病。恒在床褥。乃昼宵洞属。衣不解带。迎医问药。必先尝之。奏效而后已。其母尝思川鱼。时当夏潦。川渎大涨。四无可求之道。与其弟箕朝垂钓前川。愿得嘉鱼。中心默祷。已而飙风忽起。所著纸笠。堕泛中流而一大鲇鱼。跃到笠上。乃钩引而供进。母病顿苏。邻里咸称神异曰此诚孝感所致也。其母以天年而终。敛殡馈奠。一遵礼制。颜色之瘠。哭泣之哀。见者莫不感动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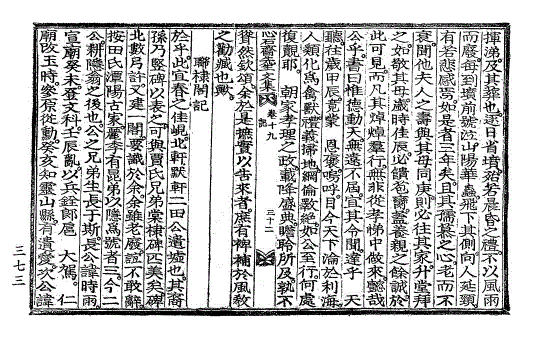 挥涕。及其葬也。逐日省坟。殆若晨昏之礼。不以风雨而废。每到坟前号泣。山阳华虫。飞下其侧。向人延颈。有若悲感焉。如是者三年矣。且其孺慕之心。老而不衰。闻他夫人之寿与其母同庚。则必往其家。升堂拜之。如敬其母。岁时佳辰。必馈苞脔。盖养亲之馀诚。于此可见。而凡其焯焯群行。无非从孝悌中做来。懿哉公乎。书曰惟德动天。无远不届。宜其令闻。达乎 天听。往岁甲辰。竟蒙 恩褒。呜呼。目今天下沦于利海。人类化为禽兽。礼义扫地。纲伦斁绝。如公至行。何处复觌耶。 朝家孝理之政。载降盛典。瞻聆所及。孰不耸然钦颂。余于是摭实以告来者。庶有裨补于风教之劝臧也欤。
挥涕。及其葬也。逐日省坟。殆若晨昏之礼。不以风雨而废。每到坟前号泣。山阳华虫。飞下其侧。向人延颈。有若悲感焉。如是者三年矣。且其孺慕之心。老而不衰。闻他夫人之寿与其母同庚。则必往其家。升堂拜之。如敬其母。岁时佳辰。必馈苞脔。盖养亲之馀诚。于此可见。而凡其焯焯群行。无非从孝悌中做来。懿哉公乎。书曰惟德动天。无远不届。宜其令闻。达乎 天听。往岁甲辰。竟蒙 恩褒。呜呼。目今天下沦于利海。人类化为禽兽。礼义扫地。纲伦斁绝。如公至行。何处复觌耶。 朝家孝理之政。载降盛典。瞻聆所及。孰不耸然钦颂。余于是摭实以告来者。庶有裨补于风教之劝臧也欤。联棣阁记
于乎。此宜春之佳岘。北轩,默轩二田公遗墟也。其裔孙乃竖碑以表之。可与贾氏兄弟棠棣碑匹美矣。碑北数弓许。又建一阁。要识于余。余虽老废。谊不敢辞。按田氏潭阳古家。丽季有昆弟以隐为号者三。今二公。耕隐翁之后也。公之兄弟生长于斯。长公讳时雨。宣庙癸未。登文科。壬辰乱。以兵铨郎扈 大驾。 仁庙改玉时。参原从勋。癸亥知灵山县。有遗爱。次公讳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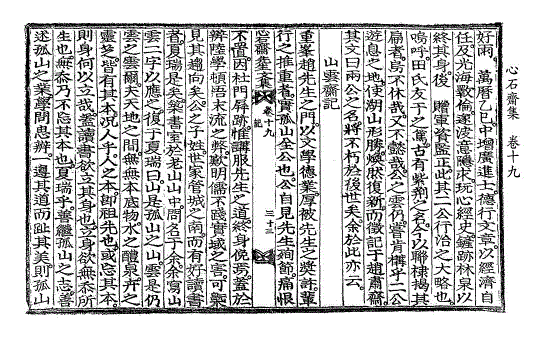 好雨。 万历乙巳。中增广进士。德行文章。以经济自任。及光海斁伦。遂决意隐求。玩心经史。铲迹林泉以终其身。后 赠军资监正。此其二公行治之大略也。呜呼。田氏友于之笃。古有紫荆之名。今以联棣揭其扁者。乌不休哉。又不懿哉。公之云仍。尝肯构乎二公游息之地。使湖山形胜。焕然复新。而徵记于赵肃斋。其文曰两公之名。将不朽于后世矣。余于此亦云。
好雨。 万历乙巳。中增广进士。德行文章。以经济自任。及光海斁伦。遂决意隐求。玩心经史。铲迹林泉以终其身。后 赠军资监正。此其二公行治之大略也。呜呼。田氏友于之笃。古有紫荆之名。今以联棣揭其扁者。乌不休哉。又不懿哉。公之云仍。尝肯构乎二公游息之地。使湖山形胜。焕然复新。而徵记于赵肃斋。其文曰两公之名。将不朽于后世矣。余于此亦云。山云斋记
重峰赵先生之门。以文学德业。厚被先生之奖许。辈行之推重者。实孤山全公也。公自见先生殉节。痛恨不置。因杜门屏迹。惟讲服先生之道。终身俛焉。盖于辨陆学顿悟末流之弊。叹明儒不践实域之害。可槩见其趋向矣。公之子姓。世家管城之南。而有好读书者。夏瑞是矣。筑书室于老山山中。问名于余。余写山云二字以应之。复于夏瑞曰。山是孤山之山。云是仍云之云尔。夫天地之间。无无本底物。水之醴泉。卉之灵芝。皆有其本。况人乎。人之本。即祖先也。或忘其本。则身何以立哉。盖读书欲立其身也。立身欲无忝所生也。无忝乃不忘其本也。夏瑞乎。善继孤山之志。善述孤山之业。学问思辨。一遵其道而趾其美。则孤山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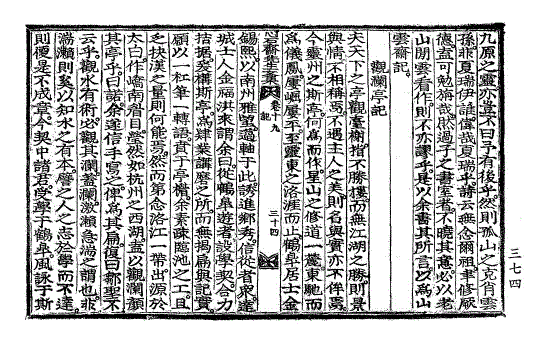 九原之灵。亦岂不曰予有后乎。然则孤山之克肖云孙。非夏瑞伊谁。伟哉夏瑞乎。诗云无念尔祖。聿修厥德。盍可勉旃哉。然过子之书室者。不晓其意。必以老山閒云看作。则不亦谬乎。是以余书其所言。以为山云斋记。
九原之灵。亦岂不曰予有后乎。然则孤山之克肖云孙。非夏瑞伊谁。伟哉夏瑞乎。诗云无念尔祖。聿修厥德。盍可勉旃哉。然过子之书室者。不晓其意。必以老山閒云看作。则不亦谬乎。是以余书其所言。以为山云斋记。观澜亭记
夫天下之亭观台榭。指不胜搂。而无江湖之胜。则景与情不相称焉。不遇主人之美。则名与实亦不侔焉。今灵州之斯亭。何为而作。星山之修道一麓。东驰而为仪凤。屡崛屡平。至灵东之洛涯而止。鹤皋居士金锡熙。以南州雅望。薖轴于此。诱进乡秀。信从者众。达城士人金福洪来谓余曰。从鹤皋游者设学契。合力拮据。爰构斯亭。为肄业讲磨之所。而无揭扁与记实。愿以一杠笔一转语。贲于亭楣。余素疏临池之工。且乏抉汉之量则何能焉。然而第念洛江一带。出源于太白。作峤南眉目。莹然如杭州之西湖。盍以观澜颜其亭乎。曰诺。余遂信手写之。俾为其扁。复曰邹圣不云乎。观水有术。必观其澜。盖澜。激濑急湍之谓也。非湍濑则奚以知水之有本。譬之人之志于学而不达。则便是不成章。今契中诸君。受学于鹤皋。风咏于斯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5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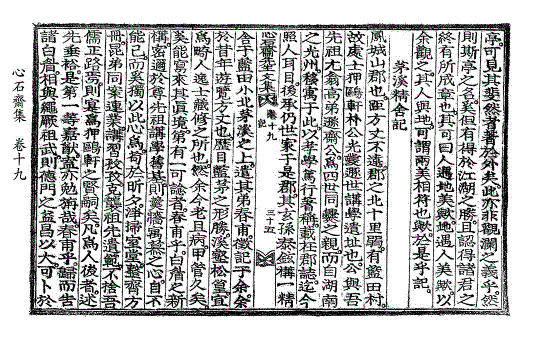 亭。可见其斐然者著于外矣。此亦非观澜之义乎。然则斯亭之名。奚但有得于江湖之胜。且认得诸君之终有所成章也。其可曰人遇地美欤。地遇人美欤。以余观之。其人与地。可谓两美相符也欤。于是乎记。
亭。可见其斐然者著于外矣。此亦非观澜之义乎。然则斯亭之名。奚但有得于江湖之胜。且认得诸君之终有所成章也。其可曰人遇地美欤。地遇人美欤。以余观之。其人与地。可谓两美相符也欤。于是乎记。茅溪精舍记
凤城山郡也。距方丈不远。郡之北十里弱。有蓝田村。故处士狎鸥轩朴公光夔遁世讲学遗址也。公与吾先祖尤翁高弟逊斋公。为四世同爨之亲。而自湖南之光州。移寓于此。以孝学笃行著称。载在郡志。迄今照人耳目。后承仍世家于是郡。其玄孙泰铉构一精舍于蓝田小北茅溪之上。遣其弟春甫。徵记于余。余于昔年游览方丈也。历目蓝茅之形胜。溪壑松篁。宜为畸人逸士藏修之所也。然余今老且病。甲管久矣。奚能写来其真境。第有一可谂者。春甫乎。白眉之新构。密迩于尊先祖讲学旧基。则羹墙寓慕之心。自不能已。而奚独以此心为。苟于昕夕。净扫室堂。整齐方册。昆弟同案连业。讲习孜孜。克袭祖先遗范。不舍吾儒正路焉。则寔为狎鸥轩之贤嗣矣。凡为人后者。述先垂裕。是第一等嘉猷。盍亦勉旃哉。春甫乎。归而告诸白眉。相与绳厥祖武。则德门之益昌以大。可卜于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5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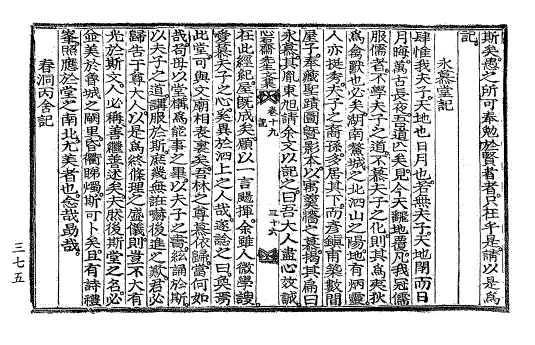 斯矣。愚之所可奉勉于贤者者。只在乎是。请以是为记。
斯矣。愚之所可奉勉于贤者者。只在乎是。请以是为记。永慕堂记
肆惟我夫子。天地也日月也。若无夫子。天地闭而日月晦。万古长夜。吾道亡矣。见今天翻地覆。凡我冠儒服儒者。不学夫子之道。不慕夫子之化。则其为夷狄为禽兽也必矣。湖南鳌城之北泗山之阳。地有炳灵。人亦挺秀。夫子之裔孙。多居其下。而彦镇甫筑数间屋子。奉藏圣迹图暨影本。以寓羹墙之慕。揭其扁曰永慕。其胤东旭请余文以记之。曰吾大人尽心效诚。在此经纪。屋既成矣。愿以一言飏挥。余虽人微学謏。爱慕夫子之心。奚异于泗上之人哉。遂谂之曰。奂焉此堂。可与文庙相表里矣。吾林之尊慕依归。当何如哉。苟毋以堂构为能事之毕。以夫子之书。弦诵于斯。以夫子之道。讲服于斯。庶几无诳吓后进之叹。君必归告于尊大人。以是为终条理之盛仪。则岂不大有光于斯文。人必称善继善述矣。夫然后斯堂之名。必并美于鲁城之阙里。昏衢睇烛。斯可卜矣。且有诗礼峰。照应于堂之南北。尤美者也。念哉勖哉。
春洞丙舍记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6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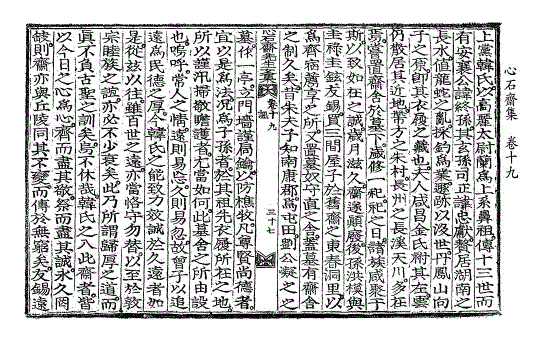 上党韩氏。以高丽太尉兰为上系鼻祖。传十三世而有安襄公讳终孙。其玄孙司正讳忠献。赘居湖南之长水。值龙蛇之乱。采钓为业。遁迹以没世。丹凤山向子之原。即其衣履之藏也。夫人咸昌金氏祔其左。云仍散居其近地。带方之朱村。长州之长溪天川。多在焉。尝置斋舍于墓下。岁修一祀。祀之日。诸族咸聚于斯。以致如在之诚。岁月滋久。斋遂颠废。后孙洪模与圭禄,圭铉,友锡。买三间屋子于旧斋之东春洞里。以为齐宿荐享之所。又置墓奴守直之舍。盖墓有斋舍之制久矣。昔朱夫子知南康郡。为屯田。刘公凝之之墓。作一亭。立门墙谨扃钥。以防樵牧。凡尊贤尚德者。宜以是为法。况为子孙者。于其祖先衣履所在之地。所以谨汛扫敬瞻护者。尤当如何。此墓舍之所由设也。呜呼。常人之情。远则易忘。久则易忽。故曾子以追远为民德之厚。今韩氏之能致力效诚于久远者如是。从玆以往。虽百世之远。亦当恪守勿替。以至于敦宗睦族之谊。亦必不少衰矣。此乃所谓归厚之道。而真不负古圣之训矣。乌不休哉。韩氏之入此斋者。皆以今日之心为心。齐而尽其敬。祭而尽其诚。永久罔缺。则斋亦与丘陵同其不变。而传于无穷矣。友锡远
上党韩氏。以高丽太尉兰为上系鼻祖。传十三世而有安襄公讳终孙。其玄孙司正讳忠献。赘居湖南之长水。值龙蛇之乱。采钓为业。遁迹以没世。丹凤山向子之原。即其衣履之藏也。夫人咸昌金氏祔其左。云仍散居其近地。带方之朱村。长州之长溪天川。多在焉。尝置斋舍于墓下。岁修一祀。祀之日。诸族咸聚于斯。以致如在之诚。岁月滋久。斋遂颠废。后孙洪模与圭禄,圭铉,友锡。买三间屋子于旧斋之东春洞里。以为齐宿荐享之所。又置墓奴守直之舍。盖墓有斋舍之制久矣。昔朱夫子知南康郡。为屯田。刘公凝之之墓。作一亭。立门墙谨扃钥。以防樵牧。凡尊贤尚德者。宜以是为法。况为子孙者。于其祖先衣履所在之地。所以谨汛扫敬瞻护者。尤当如何。此墓舍之所由设也。呜呼。常人之情。远则易忘。久则易忽。故曾子以追远为民德之厚。今韩氏之能致力效诚于久远者如是。从玆以往。虽百世之远。亦当恪守勿替。以至于敦宗睦族之谊。亦必不少衰矣。此乃所谓归厚之道。而真不负古圣之训矣。乌不休哉。韩氏之入此斋者。皆以今日之心为心。齐而尽其敬。祭而尽其诚。永久罔缺。则斋亦与丘陵同其不变。而传于无穷矣。友锡远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6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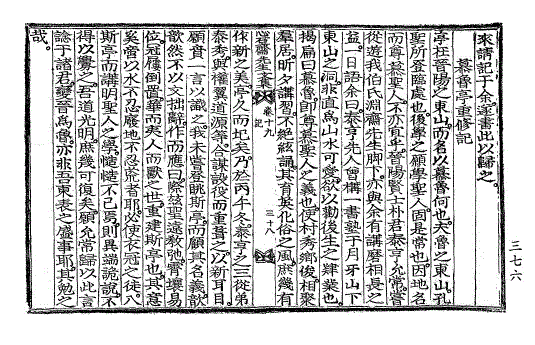 来请记于余。遂书此以归之。
来请记于余。遂书此以归之。慕鲁亭重修记
亭在晋阳之东山。而名以慕鲁何也。夫鲁之东山。孔圣所登临处也。后学之愿学圣人。固是常也。因地名而尊慕圣人。不亦宜乎。晋阳贤士朴君泰亨允常。尝从游我伯氏渊斋先生脚下。亦与余有讲磨相长之益。一日语余曰。泰亨先人曾构一书塾于月牙山下东山之洞。非直为山水可爱。欲以劝后生之肄业也。揭扁曰慕鲁。即尊慕圣人之义也。使村秀乡俊。相聚群居。昕夕讲习。不绝弦诵。其育英化俗之风。庶几有作新之美。亭久而圮矣。乃于丙午冬。泰亨之三从弟泰秀。与权翼道源等。合谋设役而重葺之。以新耳目。愿贲一言以识之。我未尝登眺斯亭。而顾其名义。歆歆然不以文拙辞。作而应曰。际玆圣远教弛。霄壤易位。冠屦倒置。华而夷人而兽之世。重建斯亭也。其意奚啻以水不忍废地不忍荒者耶。必使衣冠之徒。入斯亭而讲明圣人之学。慥慥不已焉。则异端诡说。不得以衅之。吾道光明。庶几可复矣。愿允常归以此言谂于诸君。变晋为鲁。亦非吾东表之盛事耶。其勉之哉。
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第 37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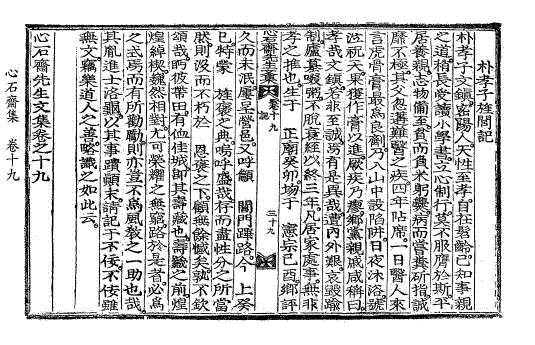 朴孝子旌闾记
朴孝子旌闾记朴孝子文镇。密阳人。天性至孝。自在髫龄。已知事亲之道。稍长受读小学书。立心制行。莫不服膺于斯。平居养亲。志物备至。贫而负米躬爨。病而尝粪斫指。诚靡不极。其父忽遘难医之疾。四年阽席。一日医人来言虎骨膏最为良剂。乃入山中设陷阱。日夜沐浴。号泣祝天。果获作膏以进。厥疾乃瘳。乡党亲戚咸称曰。孝哉文镇。若非至诚。焉有是异哉。遭内外艰。哀毁踰制。庐墓啜粥。不脱衰绖以终三年。凡居家处事。无非孝之推也。生于 正庙癸卯。殁于 宪宗己酉。乡评久而未泯。屡呈营邑。又呼龥 阊门跸路。今 上癸巳。特蒙 旌褒之典。呜呼盛哉。存而尽性分之所当然。则没而不朽于 恩褒之下。顾无馀憾矣。孰不钦颂哉。眄彼带田。有侐佳城。即其寿藏也。寿藏之前。煌煌绰楔。巍然相对。尤可荣耀之无穷。路于是者。必为之式焉而有所劝励。则亦岂不为风教之一助也哉。其胤进士洛龟。以其事迹颠末。请记于不佞。不佞虽无文。窃乐道人之善。略识之如此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