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明: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.org,kanripo.org, db.itkc.or.kr 和 zh.wikisource.org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x 页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
书
书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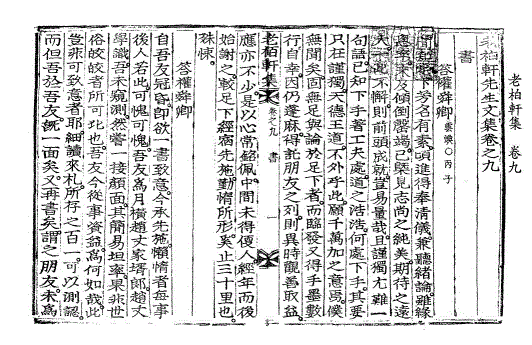 答权舜卿(云焕○丙子)
答权舜卿(云焕○丙子)闻知足下芳名有素。顷进得奉清仪。兼听绪论。虽缘悤卒。未及倾倒罄竭。已槩见志尚之纯美。期待之远大。一此不懈。则前头成就。岂易量哉。且谨独尤难一句语。已知下手著工夫处。道之浩浩。何处下手。其要只在谨独。天德王道。不外乎此。愿千万加之意焉。仆无闻矣。固无足与论于足下者。而临发又得手墨数行。自幸。因仍蓬麻。得托朋友之列。则异时观善取益。应亦不少。是以心常铭佩。中间未得便人。经年而后始谢之。较足下经宿先施。勤惰所形。奚止三十里也。殊悚。
答权舜卿
自吾友冠昏。即欲一书致意。今承先施。懒惰者每事后人若此。可愧可愧。吾友为月横赵丈家婿郎。赵丈学识。吾未窥测。然尝一接颜面。其𥳑易坦率。果非世俗皎皎者所可比也。吾友今从事资益。为何如哉。此岂非可致意者耶。细读来札。所存之百一。可以测认。而但吾于吾友。既一面矣。又再书矣。谓之朋友。未为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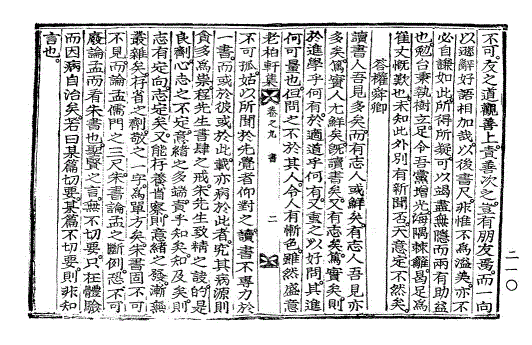 不可。友之道观善上。责善次之。岂有朋友焉。而一向以逊辞好语相加哉。以后书尺。非惟不为溢美。亦不必自谦如此。所得所疑。可以竭尽无隐而两有助益也。勉台秉执树立。足令吾党增光。海隅棘篱。曷足为崔丈慨叹也。未知此外别有新闻否。天意定不然矣。
不可。友之道观善上。责善次之。岂有朋友焉。而一向以逊辞好语相加哉。以后书尺。非惟不为溢美。亦不必自谦如此。所得所疑。可以竭尽无隐而两有助益也。勉台秉执树立。足令吾党增光。海隅棘篱。曷足为崔丈慨叹也。未知此外别有新闻否。天意定不然矣。答权舜卿
读书人吾见多矣。而有志人或鲜矣。有志人吾见亦多矣。笃实人尤鲜矣。既读书矣。又有志矣。笃实矣。则于进学乎何有。于适道乎何有。又重之以好问。其进何可量也。但问之不于其人。令人有惭色。虽然盛意不可孤。姑以所闻于先觉者仰对之。读书不专力于一书。而或于彼或于此。载亦病于此者。究其病源则贪多为祟。程先生书肆之戒。朱先生致精之诀。的是良剂。心志之不定。意绪之多端。责乎知矣。知及矣。则志有定向。志定矣。又能存养省察。则意绪之发。渐无丛杂矣。存省之剂。敬之一字。为单方矣。朱书固不可不见。而论孟儒门之三尺。朱书论孟之断例。恐不可废论孟而看朱书也。圣贤之言。无不切要。只在体验而因病自治矣。若曰某篇切要。某篇不切要。则非知言也。
答权舜卿别纸(戊寅)
工夫大抵贵刻苦。而刻苦太过。则少优游自得之味。有强探力索之病。陈茂卿兴寐箴。间以游泳。发舒精神二句深有味。吾兄不可不知也。退陶先生少时读易。以思索太过。生羸瘠之病。敢举似于吾兄。愿兄勿忘勿助。如春草之日长而人不见其长也。此事是终身事业。非一蹴可到者也。愚于兄望之远爱之深。故其言之不得不切。想谅悉矣。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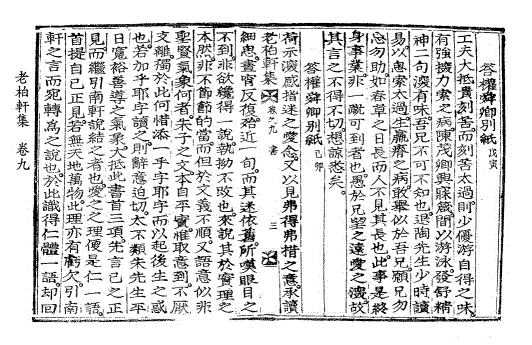 答权舜卿别纸(己卯)
答权舜卿别纸(己卯)荷示深感指迷之爱念。又以见弗得弗措之意。承读细思。昼宵反复。殆近一旬。而其迷依旧。所叹眼目之不到。非欲才得一说。执拗不改也。来说其于实理之本然。非不节节的当。而但于文义不顺。又语意似非圣贤气象何者。朱子之文。本自平实。惟取意到。不厌支离。独于此何惜添一乎字耶字而以起后生之惑也。若加乎耶字读之。则辞意迫切。太不类朱先生平日宽裕善导之气象。大抵此书首三项。先言己之正见。而继引南轩说结之者也。爱之之理便是仁一语。首提自己正见。若无天地万物。此理亦有亏欠。引南轩之言而宛转为之说也。于此识得仁体一语。却回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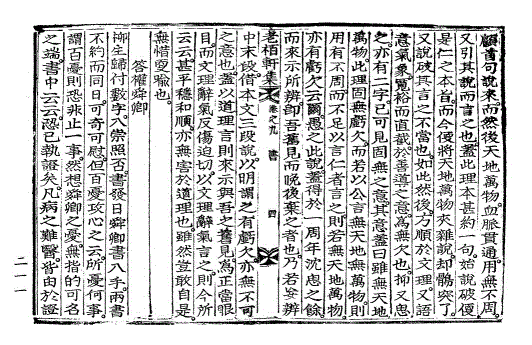 顾首句说来。而然后天地万物。血脉贯通。用无不周。又引其说而言之也。盖此理本甚约一句。始说破便是仁之本旨。而今便将天地万物夹杂说。却鹘突了。又说破其言之不当也。如此然后。方顺于文理。又语意气象。宽裕而直截。于善导之意。为无欠也。抑又思之。亦有二字。已可见固无之意。其意盖曰虽无天地万物。此理固无亏欠。而若以公言无天地无万物。则用有不周。而不足以言仁者言之。则若无天地万物。亦有亏欠云尔。愚之此说。盖得于一周年沈思之馀。而来示所辨。即吾旧见而晚后弃之者也。乃若妄辨中末段。借本文三段说。以明谓之有亏欠。亦无不可之意也。盖以道理言则来示与吾之旧见。为正当眼目。而文理辞气反伤迫切。以文理辞气言之。则今所云云。甚平稳和顺。亦无害于道理也。虽然岂敢自是。无惜更喻也。
顾首句说来。而然后天地万物。血脉贯通。用无不周。又引其说而言之也。盖此理本甚约一句。始说破便是仁之本旨。而今便将天地万物夹杂说。却鹘突了。又说破其言之不当也。如此然后。方顺于文理。又语意气象。宽裕而直截。于善导之意。为无欠也。抑又思之。亦有二字。已可见固无之意。其意盖曰虽无天地万物。此理固无亏欠。而若以公言无天地无万物。则用有不周。而不足以言仁者言之。则若无天地万物。亦有亏欠云尔。愚之此说。盖得于一周年沈思之馀。而来示所辨。即吾旧见而晚后弃之者也。乃若妄辨中末段。借本文三段说。以明谓之有亏欠。亦无不可之意也。盖以道理言则来示与吾之旧见。为正当眼目。而文理辞气反伤迫切。以文理辞气言之。则今所云云。甚平稳和顺。亦无害于道理也。虽然岂敢自是。无惜更喻也。答权舜卿
柳生归付数字。入崇照否。书发日舜卿书入手。两书不约而同日。可奇可慰。但百忧攻心之云。所忧何事。谓百忧则恐非止一事。然想舜卿之忧。无指的可名之端。书中云云。恐已执證矣。凡病之难医。皆由于證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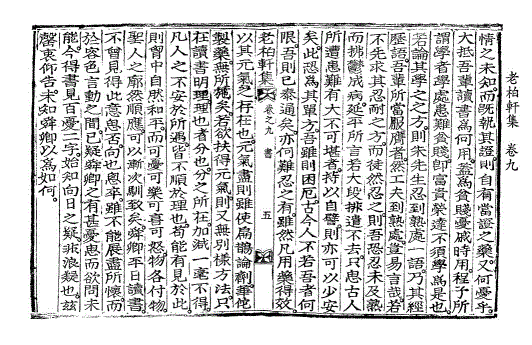 情之未知。而既执其證。则自有当證之药。又何忧乎。大抵吾辈读书为何用。盖为贫贱忧戚时用。程子所谓学者学处患难贫贱。即富贵荣达不须学为是也。若论其学之之方。则朱先生忍到熟处一语。乃其经历语。吾辈所当服膺者。然工夫到熟处。岂易言哉。若不先求其忍耐之方。而徒然忍之。则吾恐忍未及熟而拂郁成病。延平所言若大段排遣不去。只思古人所遭患难有大不可堪者。持以自譬。则亦可以少安矣。此恐为其单方。吾虽则困厄。古今人不若吾者何限。吾则已泰通矣。亦何难忍之有。虽然凡用药得效。以其元气之存在也。元气尽则虽使扁鹊论剂。华佗制药。无所施矣。若欲扶得元气。则又无别样方法。只在读书明理。理也者分也。分之所在。加减一毫不得。凡人之不安于所遇。皆不顺于理也。苟能有见于此。则胸中自然和平。而可忧可乐可喜可怒。物各付物。圣人之廓然顺应。可以渐次驯致矣。舜卿平日读书。不曾见得此意思否。向也悤卒。虽不能展尽所怀。而于容色言动之间。已疑舜卿之有甚忧思而欲问未能。今得书见百忧二字。始知向日之疑。非浪疑也。玆罄衷仰告。未知舜卿以为如何。
情之未知。而既执其證。则自有当證之药。又何忧乎。大抵吾辈读书为何用。盖为贫贱忧戚时用。程子所谓学者学处患难贫贱。即富贵荣达不须学为是也。若论其学之之方。则朱先生忍到熟处一语。乃其经历语。吾辈所当服膺者。然工夫到熟处。岂易言哉。若不先求其忍耐之方。而徒然忍之。则吾恐忍未及熟而拂郁成病。延平所言若大段排遣不去。只思古人所遭患难有大不可堪者。持以自譬。则亦可以少安矣。此恐为其单方。吾虽则困厄。古今人不若吾者何限。吾则已泰通矣。亦何难忍之有。虽然凡用药得效。以其元气之存在也。元气尽则虽使扁鹊论剂。华佗制药。无所施矣。若欲扶得元气。则又无别样方法。只在读书明理。理也者分也。分之所在。加减一毫不得。凡人之不安于所遇。皆不顺于理也。苟能有见于此。则胸中自然和平。而可忧可乐可喜可怒。物各付物。圣人之廓然顺应。可以渐次驯致矣。舜卿平日读书。不曾见得此意思否。向也悤卒。虽不能展尽所怀。而于容色言动之间。已疑舜卿之有甚忧思而欲问未能。今得书见百忧二字。始知向日之疑。非浪疑也。玆罄衷仰告。未知舜卿以为如何。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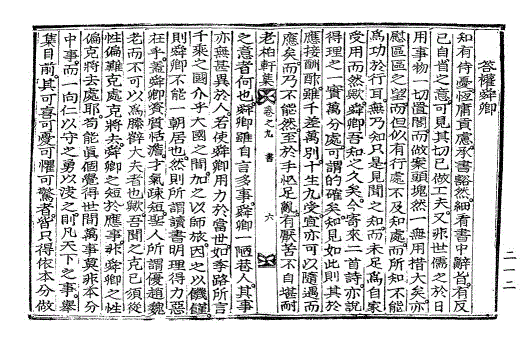 答权舜卿
答权舜卿知有侍忧。恒庸贡虑。承书豁然。细看书中辞旨。有反己自省之意。可见其切己做工夫。又非世儒之于日用事物一切置阁。而做案头块然一无用措大矣。亦慰区区之望。而但似有行处不及知处。而所知不能为功于行耳。无乃知只是见闻之知。而未足为自家受用而然欤。舜卿吾知之久矣。今寄来二首诗。亦说得理之一实万分处。可谓的确矣。知见如此则其于应接酬酢。虽千差万别。十生九受。宜亦可以随遇而应矣。而乃不能然。至于手忙足乱。有厌苦不自堪耐之意者何也。舜卿虽自言多事。舜卿一陋巷人。其事亦无甚异于人。若使舜卿用力于当世。如季路所言千乘之国介乎大国之间。加之以师旅。因之以饥馑。则舜卿不能一朝居也。然则所谓读书明理得力恶在乎。盖舜卿资质恬澹。才气疏短。圣人所谓优赵魏老而不可以为滕辥大夫者也欤。吾闻之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。舜卿之短于应事。非舜卿之性偏克将去处耶。苟能真个觉得世间万事莫非本分中事。而一向仁以守之勇以决之。则凡天下之事。举集目前。其可喜可忧可惧可惊者。皆只得依本分做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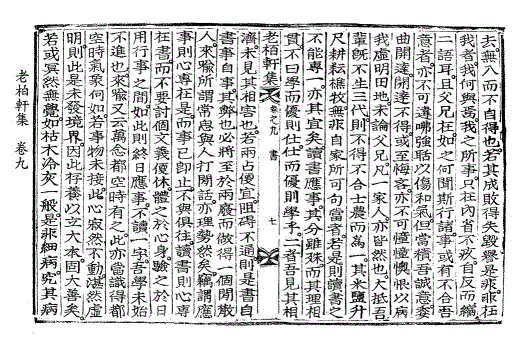 去。无入而不自得也。若其成败得失毁誉是非。非在我者。我何与焉。我之所事。只在内省不疚。自反而缩二语耳。且父兄在。如之何闻斯行诸。事或有不合吾意者。亦不可违咈强聒以伤和气。但当积吾诚意。委曲开达。开达不得。或至悔吝。亦不可憧憧懊恨以病我虚明田地。未论父兄。凡一家人。亦皆然也。大抵吾辈既不生三代。则不得不合士农而为一。其米盐升尺耕耘樵牧。无非自家所可句当者。若是则读书之不能专一。亦其宜矣。读书应事。其分虽殊。而其理相贯。不曰学而优则仕。仕而优则学乎。二者吾见其相济。未见其相害也。若两占便宜。阻碍不通。则是书自书事自事。其弊也必将至于两废而做得一个閒散人。来喻所谓常思与人打閒话。亦理势然矣。窃谓应事则心专在是。而事已即止。不与俱往。读书则心专在书。而不要讨个文义便休。体之于心身。验之于日用行事之间。如此则终日应事。不读一字。吾学未始不进也。来喻又云万念都空时有之。此亦当识得都空时气象何如。若事物未接。此心寂然不动。湛然虚明。则此是未发境界。因此存养以立大本。固大善矣。若或冥然无觉。如枯木冷灰一般。是非细病。究其病
去。无入而不自得也。若其成败得失毁誉是非。非在我者。我何与焉。我之所事。只在内省不疚。自反而缩二语耳。且父兄在。如之何闻斯行诸。事或有不合吾意者。亦不可违咈强聒以伤和气。但当积吾诚意。委曲开达。开达不得。或至悔吝。亦不可憧憧懊恨以病我虚明田地。未论父兄。凡一家人。亦皆然也。大抵吾辈既不生三代。则不得不合士农而为一。其米盐升尺耕耘樵牧。无非自家所可句当者。若是则读书之不能专一。亦其宜矣。读书应事。其分虽殊。而其理相贯。不曰学而优则仕。仕而优则学乎。二者吾见其相济。未见其相害也。若两占便宜。阻碍不通。则是书自书事自事。其弊也必将至于两废而做得一个閒散人。来喻所谓常思与人打閒话。亦理势然矣。窃谓应事则心专在是。而事已即止。不与俱往。读书则心专在书。而不要讨个文义便休。体之于心身。验之于日用行事之间。如此则终日应事。不读一字。吾学未始不进也。来喻又云万念都空时有之。此亦当识得都空时气象何如。若事物未接。此心寂然不动。湛然虚明。则此是未发境界。因此存养以立大本。固大善矣。若或冥然无觉。如枯木冷灰一般。是非细病。究其病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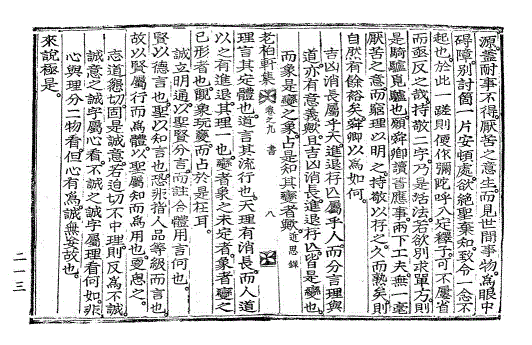 源。盖耐事不得。厌苦之意生。而见世间事物。为眼中碍障。别讨个一片安顿处。欲绝圣弃知。致令一念不起也。于此一蹉则便作弥陀呼入定释子。可不屡省而亟反之哉。持敬二字。乃是活法。若欲别求单方。则是骑驴觅驴也。愿舜卿读书应事。两下工夫。无一毫厌苦之意。而穷理以明之。持敬以存之。久而熟矣。则自然有馀裕矣。舜卿以为如何。
源。盖耐事不得。厌苦之意生。而见世间事物。为眼中碍障。别讨个一片安顿处。欲绝圣弃知。致令一念不起也。于此一蹉则便作弥陀呼入定释子。可不屡省而亟反之哉。持敬二字。乃是活法。若欲别求单方。则是骑驴觅驴也。愿舜卿读书应事。两下工夫。无一毫厌苦之意。而穷理以明之。持敬以存之。久而熟矣。则自然有馀裕矣。舜卿以为如何。吉凶消长属乎天。进退存亡属乎人。而分言理与道。亦有意义欤。且吉凶消长。进退存亡。皆是变也。而象是变之象。占是知其变者欤。(近思录。)
理言其定体也。道言其流行也。天理有消长。而人道以之有进退。其理一也。变者象之未定者。象者变之已形者也。观象玩变。而占于是在耳。
诚立明通。以圣贤分言。而注合体用言何也。
贤以德言也。圣以知言也。恐非指人品等级而言也。故以贤属行而为体。以圣属知而为用也。更思之。
志道恳切。固是诚意。若迫切不中理。则反为不诚。诚意之诚字属心看。不诚之诚字属理看何如。非心与理分二物看。但心有为。诚无妄故也。
来说极是。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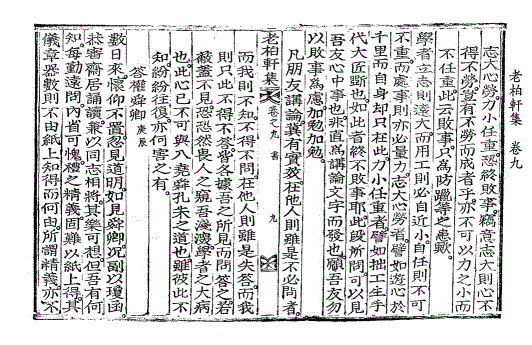 志大心劳。力小任重。恐终败事。窃意志大则心不得不劳。岂有不劳而成者乎。亦不可以力之小而不任重。此云败事。只为防躐等之患欤。
志大心劳。力小任重。恐终败事。窃意志大则心不得不劳。岂有不劳而成者乎。亦不可以力之小而不任重。此云败事。只为防躐等之患欤。学者立志则远大。而用工则必自近小。自任则不可不重。而处事则亦必量力。志大心劳者。譬如游心于千里而自身却只在此。力小任重者。譬如拙工生手代大匠斲也。如此者终不败事耶。此段所问。可以见吾友心中事也。非直为讲论文字而发也。愿吾友勿以败事为虑。加勉加勉。
凡朋友讲论。冀有实效。在他人则虽是不必问者。而我则不知。不得不问。在他人则虽是失答。而我则只此不得不答。皆各据吾之所见而问答之。若蔽盖不见。恐恐然畏人之窥吾浅深。学者之大病也。此心已不可与入尧舜孔朱之道也。虽彼此不知。纷纷往复。亦何害之有。
答权舜卿(庚辰)
数日来。怀仰不置。忽见道明。如见舜卿。况副以琼函。恭审斋居诵读。兼以同志相将。其乐可想。但吾有何知。每勤远问。内省可愧。礼之精义。固难以纸上得。其仪章器数则不由纸上知得而何由。所谓精义。亦不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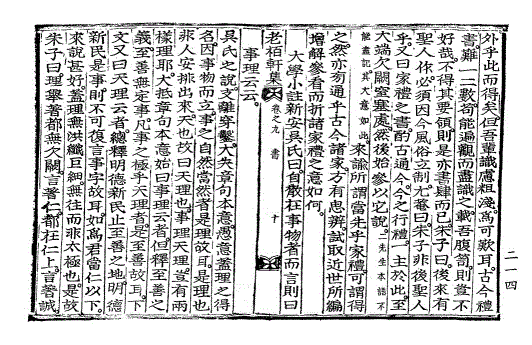 外乎此而得矣。但吾辈识虑粗浅。为可叹耳。古今礼书。难一二数。苟能遍观而尽识之。载吾腹笥。则岂不好哉。不得其要领。则是亦书肆而已。朱子曰。后来有圣人作。必须因今风俗立制。尤庵曰。朱子非后圣人乎。又曰家礼之书。酌古通今。今之行礼。一主于此。至大端欠阙窒塞处。然后始参以它说。(二先生本语不能尽记。其大意如此。)来谕所谓当先乎家礼。可谓得之。然亦旁通乎古今诸家。方有思辨。试取近世所编增解参看而折诸家礼之意如何。
外乎此而得矣。但吾辈识虑粗浅。为可叹耳。古今礼书。难一二数。苟能遍观而尽识之。载吾腹笥。则岂不好哉。不得其要领。则是亦书肆而已。朱子曰。后来有圣人作。必须因今风俗立制。尤庵曰。朱子非后圣人乎。又曰家礼之书。酌古通今。今之行礼。一主于此。至大端欠阙窒塞处。然后始参以它说。(二先生本语不能尽记。其大意如此。)来谕所谓当先乎家礼。可谓得之。然亦旁通乎古今诸家。方有思辨。试取近世所编增解参看而折诸家礼之意如何。大学小注新安吴氏曰。自散在事物者而言则曰事理云云。
吴氏之说。支离穿凿。大失章句本意。愚意盖理之得名。因事物而立。事之自然当然者是理故耳。是理也非人安排出来。天也故曰天理也。事理天理。岂有两样理耶。大抵章句本意始曰事理云者。但释至善之义。至善无定事。凡事之极乎天理者。是至善故耳。下文又曰天理云者。总释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地。明德新民是事。则不可复言事字故耳。如为君当仁以下。来说甚好。盖理无洪纤巨细。无往而非太极也。是故朱子曰。理举著都无欠阙。言著仁。都在仁上。言著诚。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5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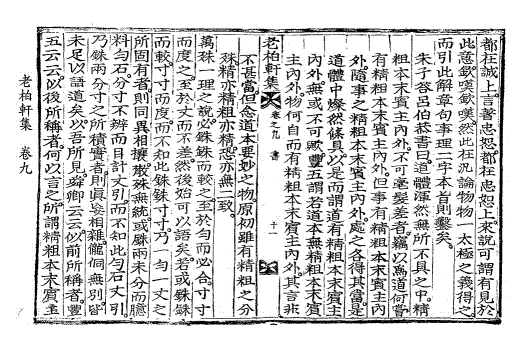 都在诚上。言著忠恕。都在忠恕上。来说可谓有见于此意。钦叹钦叹。然此在汎论物物一太极之义得之。而引此解章句事理二字本旨则凿矣。
都在诚上。言著忠恕。都在忠恕上。来说可谓有见于此意。钦叹钦叹。然此在汎论物物一太极之义得之。而引此解章句事理二字本旨则凿矣。朱子答吕伯恭书曰。道体浑然无所不具之中。精粗本末宾主内外。不可毫发差者。窃以为道何尝有精粗本末宾主内外。但事有精粗本末宾主内外。随事之精粗本末宾主内外。处之各得其当。是道体中灿然条具。以是而谓道有精粗本末宾主内外。无或不可欤。丰五谓若道本无精粗本末宾主内外。物何自而有精粗本末宾主内外。其言非不甚当。但念道本要妙之物。原初虽有精粗之分殊。精亦精粗亦精。恐亦无二致。
万殊一理之说。必铢铢而较之。至于匀而必合。寸寸而度之。至于丈而不差。然后始可以语矣。若或铢铢而较。寸寸而度。而不知此铢铢寸寸。乃一匀一丈之所固有者。则同异相攘。散殊无统。或铢两未分而臆料匀石。分寸不辨而目计丈引。而不知此匀石丈引。乃铢两分寸之所积实者。则真妄相杂。儱侗无别。皆未足以语道矣。以吾所见。舜卿云云。似前所称者。丰五云云。似后所称者。何以言之。所谓精粗本末宾主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5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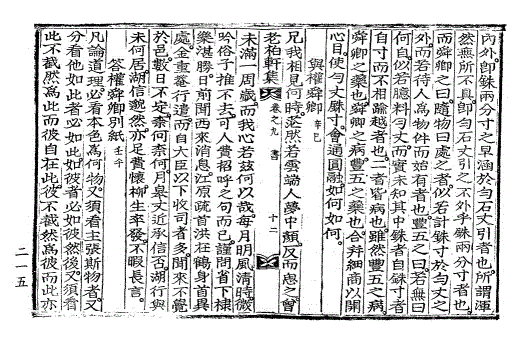 内外。即铢两分寸之早涵于匀石丈引者也。所谓浑然无所不具。即匀石丈引之不外乎铢两分寸者也。而舜卿之曰。随物曰处之者。似若计铢寸于匀丈之外。而若待人为物件而始有者也。丰五之曰。若无曰何自。似若臆料匀丈。而实未知其中铢者自铢寸者自寸而不相踰越者也。二者皆病也。虽然丰五之病。舜卿之药也。舜卿之病。丰五之药也。合并细商以开心目。使匀丈铢寸。会通圆融。如何如何。
内外。即铢两分寸之早涵于匀石丈引者也。所谓浑然无所不具。即匀石丈引之不外乎铢两分寸者也。而舜卿之曰。随物曰处之者。似若计铢寸于匀丈之外。而若待人为物件而始有者也。丰五之曰。若无曰何自。似若臆料匀丈。而实未知其中铢者自铢寸者自寸而不相踰越者也。二者皆病也。虽然丰五之病。舜卿之药也。舜卿之病。丰五之药也。合并细商以开心目。使匀丈铢寸。会通圆融。如何如何。与权舜卿(辛巳)
兄我相见何时。茫然若云端人梦中颜。反而思之。曾未满一周岁。而我心若玆何以哉。每月明风清时。微吟俗子推不去。可人费招呼之句而已。谨问省下棣乐湛胜。日前闻西来消息。江原疏首洪在鹤身首异处。金重庵行遣。而自大臣以下收司者多。闻来不觉于邑。数日不定。柰何柰何。月皋丈近承信否。湖行与未何居。湖信邈然。亦足费怀。柳生卒发。不暇长言。
答权舜卿别纸(壬午)
凡论道理。必看本色为何物。又须看主张斯物者。又分看他如此者必如此。如彼者必如彼然后。又须看此不截然为此而彼自在此。彼不截然为彼而此亦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6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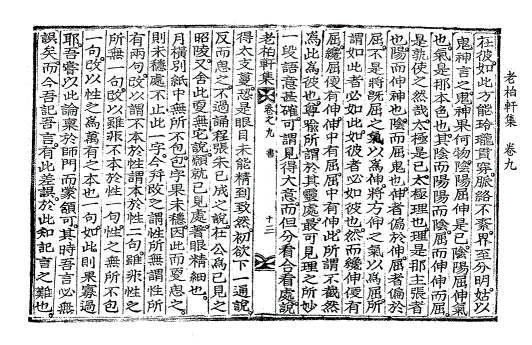 在彼。如此方能玲珑贯穿。脉络不紊。界至分明。姑以鬼神言之。鬼神果何物。阴阳屈伸是已。阴阳屈伸气也。气是那本色也。其阴而阳阳而阴。屈而伸伸而屈。是孰使之然哉。太极是已。太极理也。理是那主张者也。阳而伸神也。阴而屈鬼也。伸者偏于伸。屈者偏于屈。不是将既屈之气以为伸。将方伸之气以为屈。所谓如此者必如此。如彼者必如彼也。然而才伸便有屈。才屈便有伸。伸中有屈。屈中有伸。此所谓不截然为此为彼也。尊喻所谓于其灵处。最可见理之所妙一段语意甚确。可谓见得大意。而但分看合看处。说得太支蔓。恐是眼目未能精到致然。初欲下一通说。反而思之。不过诵程张朱已成之说。在公为已见之昭陵。又舍此更无它说。愿就已见处。著眼精细也。
在彼。如此方能玲珑贯穿。脉络不紊。界至分明。姑以鬼神言之。鬼神果何物。阴阳屈伸是已。阴阳屈伸气也。气是那本色也。其阴而阳阳而阴。屈而伸伸而屈。是孰使之然哉。太极是已。太极理也。理是那主张者也。阳而伸神也。阴而屈鬼也。伸者偏于伸。屈者偏于屈。不是将既屈之气以为伸。将方伸之气以为屈。所谓如此者必如此。如彼者必如彼也。然而才伸便有屈。才屈便有伸。伸中有屈。屈中有伸。此所谓不截然为此为彼也。尊喻所谓于其灵处。最可见理之所妙一段语意甚确。可谓见得大意。而但分看合看处。说得太支蔓。恐是眼目未能精到致然。初欲下一通说。反而思之。不过诵程张朱已成之说。在公为已见之昭陵。又舍此更无它说。愿就已见处。著眼精细也。月横别纸中无所不包。包字果未稳。因此而更思之。则未稳处不止此一字。今并改之谓性所无谓性所有两句。改以谓不本于性谓本于性二句。虽非性之所无一句。改以虽非不本于性一句。性之无所不包一句。改以性之为万有之本也一句。如此则果寡过耶。吾尝以此论禀于师门而蒙颔可。其时吾言必无误矣。而今吾记吾言。有此差误。于此知记言之难也。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6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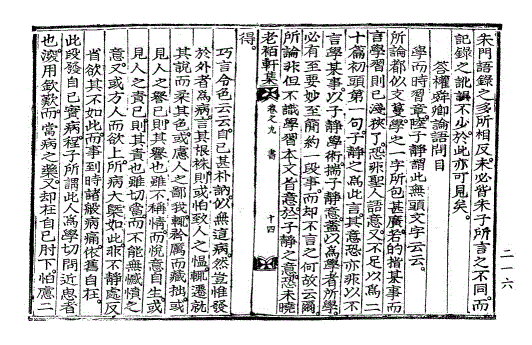 朱门语录之多所相反。未必皆朱子所言之不同。而记录之讹误不少。于此亦可见矣。
朱门语录之多所相反。未必皆朱子所言之不同。而记录之讹误不少。于此亦可见矣。答权舜卿论语问目
学而时习章。陆子静谓此无头文字云云。
所论都似支蔓。学之一字所包甚广。若的指某事而言学习则已浅狭了。恐非圣人语意。又不足以为二十篇初头第一句。子静之为此言。其意恐亦非以不言学某事。以子静学术。揣子静意。盖以为学者所学。必有至要妙至𥳑约一段事。而却不言之何故云尔。所论非但不识学习本文旨意。于子静之意。恐未晓得。
巧言令色云云。自己甚朴讷。似无这病。然岂惟发于外者为病。言其根株。则或怕致人之愠。辄迁就其说而柔其色。或虑人之鄙我。辄矜厉而藏拙。或见人之誉己。则其誉也虽不称情。而悦意自生。或见人之责己。则其责也虽切当。而不能无憾愤之意。又或方人而欲上。所病大槩如此。非不静处反省欲其不如此。而事到时诸般病痛。依旧自在。
此段发自己实病。程子所谓此人为学切问近思者也。深用钦叹。而当病之药。又却在自己肘下。怕虑二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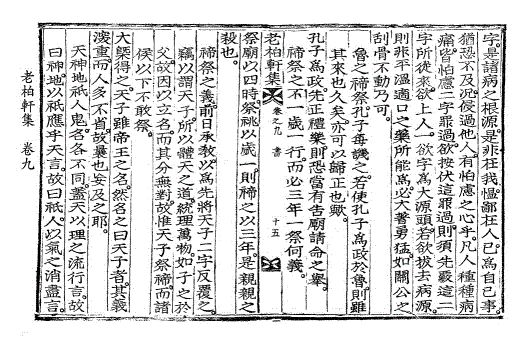 字。是诸病之根源。是非在我。愠鄙在人。已为自己事。犹恐不及。况侵过他人。有怕虑之心乎。凡人种种病痛。皆怕虑二字罪过。欲按伏这罪过。则须先覈这二字所从来。欲上人。一欲字为大源头。若欲拔去病源。则非平温适口之药所能为。必大著勇猛。如关公之刮骨不动乃可。
字。是诸病之根源。是非在我。愠鄙在人。已为自己事。犹恐不及。况侵过他人。有怕虑之心乎。凡人种种病痛。皆怕虑二字罪过。欲按伏这罪过。则须先覈这二字所从来。欲上人。一欲字为大源头。若欲拔去病源。则非平温适口之药所能为。必大著勇猛。如关公之刮骨不动乃可。鲁之禘祭。孔子每讥之。若使孔子为政于鲁。则虽其来也久矣。亦可以归正也欤。
孔子为政。先正礼乐。则恐当有告庙请命之举。
禘祭之不一岁一行。而必三年一祭何义。
祭庙以四时。祭祧以岁一。则禘之以三年。是亲亲之杀也。
禘祭之义。前日承教。以为先将天子二字反覆之。窃以谓天子。所以体天之道。统理万物。如子之于父。故因以立名。而其分无对。故惟天子祭禘。而诸侯以下不敢祭。
大槩得之。天子虽帝王之名。然名之曰天子者。其义深重。而人多不省。故曩也妄及之耶。
天神地祇人鬼。名各不同。盖天以理之流行言。故曰神。地以祇应乎天言。故曰祇。人以气之消尽言。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7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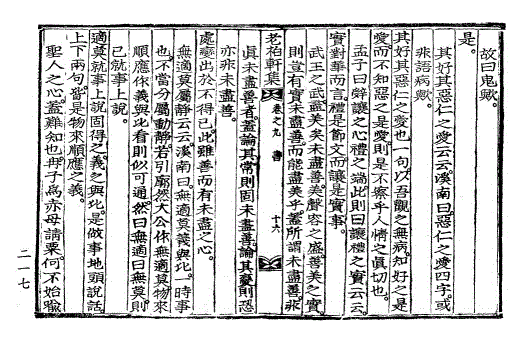 故曰鬼欤。
故曰鬼欤。是。
其好其恶仁之爱云云。溪南曰。恶仁之爱四字。或非语病欤。
其好其恶仁之爱也一句。以吾观之无病。知好之是爱。而不知恶之是爱。则是不察乎人情之真切也。
孟子曰辞让之心礼之端。此则曰让礼之实云云。
实对华而言。礼是节文。而让是实事。
武王之武。尽美矣未尽善。美声容之盛。善美之实。则岂有实未尽善。而能尽美乎。盖所谓未尽善。非真未尽善者。盖论其常则固未尽善。论其变则恐亦非未尽善。
处变出于不得已。此虽善而有未尽之心。
无适莫属静云云。溪南曰。无适莫义与比。一时事也。不当分属动静。若引廓然大公作无适莫。物来顺应作义与比看则似可通。然曰无适曰无莫。则已就事上说。
适莫就事上说固得之。义之与比。是做事地头说话。上下两句。皆是物来顺应之义。
圣人之心。盖难知也。冉子为赤母请粟。何不始喻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8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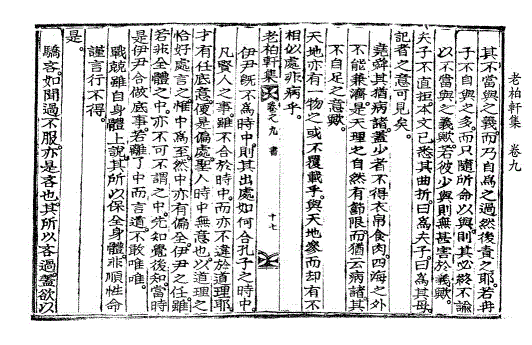 其不当与之义。而乃自为之过然后责之耶。若冉子不自与之多。而只随所命以与。则其必终不谕以不当与之义欤。若彼少与则无甚害于义欤。
其不当与之义。而乃自为之过然后责之耶。若冉子不自与之多。而只随所命以与。则其必终不谕以不当与之义欤。若彼少与则无甚害于义欤。夫子不直拒。本文已悉其曲折。曰为夫子。曰为其母。记者之意可见矣。
尧舜其犹病诸。盖少者不得衣帛食肉。四海之外不能兼济。是天理之自然有节限。而犹云病诸。其不自足之意欤。
天地亦有一物之或不覆载乎。与天地参而却有不相似处非病乎。
伊尹既不为时中。则其出处如何合孔子之时中。凡贤人之事。虽不合于时中。而亦不违于道理耶。
才有任底意。便是偏处。圣人时中无意也。以道理之恰好处言之。惟中为至。然中亦有偏全。伊尹之任。虽若非全体之中。亦不可不谓之中。先知觉后知。当时是伊尹合做底事。若离了中而言道。不敢唯唯。
战兢虽自身体上说。其所以保全身体。非顺性命谨言行不得。
是。
骄吝。如闻过不服。亦是吝也。其所以吝过。盖欲以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8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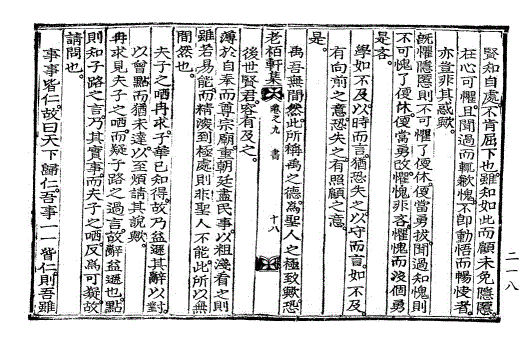 贤知自处。不肯屈下也。虽知如此而顾未免隐慝。在心可惧。且闻过而辄歉愧。不即动悟而畅快者。亦岂非其惑欤。
贤知自处。不肯屈下也。虽知如此而顾未免隐慝。在心可惧。且闻过而辄歉愧。不即动悟而畅快者。亦岂非其惑欤。既惧隐慝则不可惧了便休。便当勇拔。闻过知愧则不可愧了便休。便当勇改。惧愧非吝。惧愧而没个勇是吝。
学如不及。以时而言。犹恐失之。以守而言。如不及。有向前之意。恐失之。有照顾之意。
是。
禹吾无间然。此所称禹之德。为圣人之极致欤。恐后世贤君。容有及之。
薄于自奉而尊宗庙。重朝廷尽民事。以粗浅看之则虽若易能。而精深到极处则非圣人不能。此所以无间然也。
夫子之哂冉求。子华已知得。故乃益逊其辞以对。以曾点而犹未达。以至烦请其说欤。
冉求见夫子之哂。而疑子路之过言。故辞益逊也。点则知子路之言。乃其实事。而夫子之哂。反为可疑。故请问也。
事事皆仁。故曰天下归仁。吾事一一皆仁。则吾虽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9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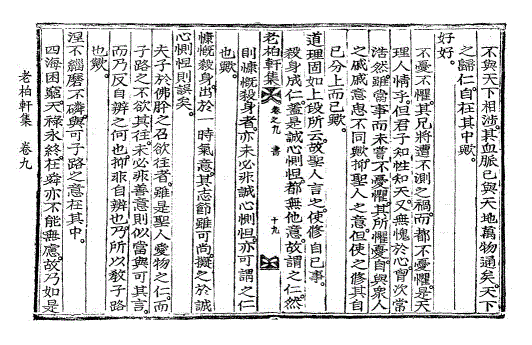 不与天下相涉。其血脉已与天地万物通矣。天下之归仁。自在其中欤。
不与天下相涉。其血脉已与天地万物通矣。天下之归仁。自在其中欤。好好。
不忧不惧。其兄将遭不测之祸。而都不忧惧。是天理人情乎。但君子知性知天。又无愧于心。胸次常浩然。虽当事而未尝不忧惧。其所惧忧。自与众人之戚戚意思不同欤。抑圣人之意。但使之修其自己分上而已欤。
道理固如上段所云。故圣人言之。使修自己事。
杀身成仁。盖是诚心恻怛。都无他意。故谓之仁。然则慷慨杀身者。亦未必非诚心恻怛。亦可谓之仁也欤。
慷慨杀身。出于一时气意。其志节虽可尚。拟之于诚心恻怛则误矣。
夫子于佛肸之召欲往者。虽是圣人爱物之仁。而子路之不欲其往。未必非善意则似当与可其言。而乃反自辨之何也。抑非自辨也。乃所以教子路也欤。
涅不缁磨不磷。与可子路之意在其中。
四海困穷。天禄永终。在舜亦不能无虑。故乃如是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1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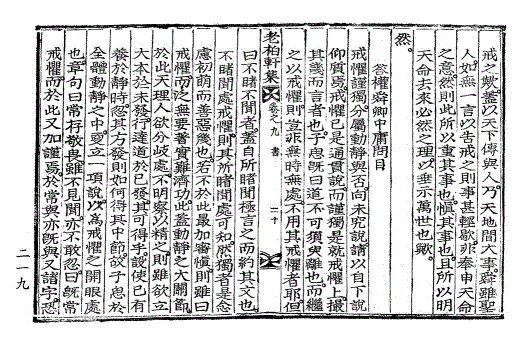 戒之欤。盖以天下传与人。乃天地间大事。舜虽圣人。如无一言以告戒之则事甚轻歇。非奉申天命之意。然则此所以重其事也。慎其事也。且所以明天命去来必然之理。以垂示万世也欤。
戒之欤。盖以天下传与人。乃天地间大事。舜虽圣人。如无一言以告戒之则事甚轻歇。非奉申天命之意。然则此所以重其事也。慎其事也。且所以明天命去来必然之理。以垂示万世也欤。然。
答权舜卿中庸问目
戒惧谨独。分属动静与否。向未究说。请以自下说仰质焉。戒惧已是通贯说。而谨独是就戒惧上。撮其几而言者也。子思既曰道不可须臾离也。而继之以戒惧。则岂非无时无处。不用其戒惧者耶。但曰不睹不闻者。盖自所睹闻极言之而约其文也。不睹闻处戒惧。则其所睹闻处可知。然独者是念虑初萌而善恶几也。若不于此最加审慎。则虽曰戒惧。而泛无要著实难济功。此盖动静之大关节。于此天理人欲分岐处。不明察以精之。则虽欲立大本于未发。行达道于已发。其可得乎。设使已有养于静时。忽其方发则如何得其中节。故子思于全体动静之中。更立一项说。以为戒惧之开眼处也。章句曰常存敬畏。虽不见闻。亦不敢忽。曰既常戒惧。而于此又加谨焉。于常与亦既与又诸字。恐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2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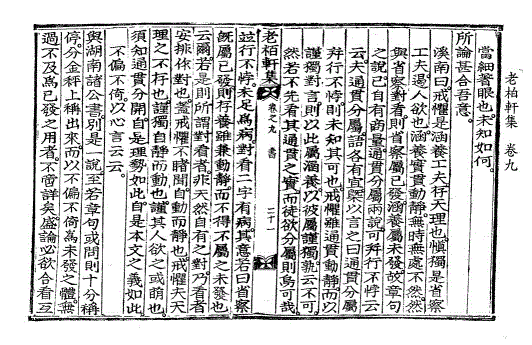 当细著眼也。未知如何。
当细著眼也。未知如何。所论甚合吾意。
溪南曰。戒惧是涵养工夫。存天理也。慎独是省察工夫。遏人欲也。涵养实贯动静。无时无处不然。然与省察对看。则省察属已发。涵养属未发。故章句之说。已自有商量。通贯分属两说。可并行不悖云云。夫通贯分属。语各有宜。槩以言之曰通贯分属并行不悖。则未知其可也。戒惧虽通贯动静。而以谨独对言。则以此属涵养。以彼属谨独。孰云不可。然若不先看其通贯之实。而徒欲分属则乌可哉。
并行不悖。未足为病。对看二字有病。其意若曰省察既属已发。则存养虽兼动静。而不得不属之未发也云尔。若是则所谓对看者。非天然自有之对。乃看者安排作对也。盖戒惧不睹闻。自动而静也。戒惧夫天理之不存也。谨独自静而动也。谨其人欲之或萌也。须知通贯分开。自是理势如此。自是本文之义如此。
不偏不倚。以心言云云。
与湖南诸公书。别是一说。至若章句或问则十分称停。分金秤上称出来。而以不偏不倚为未发之体。无过不及为已发之用者。不啻详矣。盛论必欲合看互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20L 页
 通。恐涉苟且。
通。恐涉苟且。中和是由心气云云。
问者首一句中和由心气之得正而得名。大失本旨。而盛答不明快。恐自家亦未离十字街上。盖中和状此心性情之体用本来如此。至其不中不和处。方说气字可得。然则未发时中而已。气未用事也。不偏倚三字。恐无可言之地。而必以不偏倚释之何也。中是状性之德。不偏不倚状中字。非未发而虑其有中不中。更说中字也。非既中而又虑其有偏倚不偏倚。更说不偏倚也。盍于本文之谓二字。章句而已二字。而著眼看乎。
篇题中庸云云。
惟其有定理而不易。故乃可以随时而在。譬之星秤。其秤之一分一两。是定理之不易也。随物低昂。称一分也平。称一两也平。乃随时而在也。道理本来如此。岂为虑人之泥子莫执中而言此也哉。
以位天地属中云云。
位以定体言。故属中。育以致用言。故属和。于位育二字。咀嚼出味则可见。大抵此一段。句句皆错。曰天地位万物育。则是天地自位万物自育。而今曰位天地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2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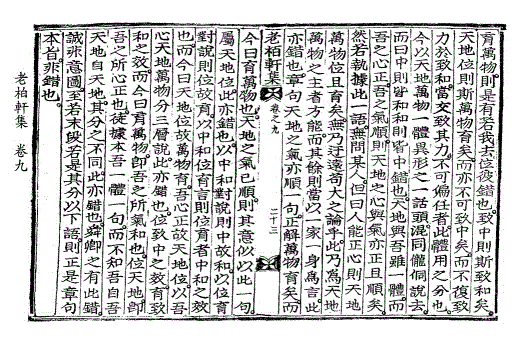 育万物。则是有若我去位彼错也。致中则斯致和矣。天地位则斯万物育矣。而亦不可致中矣。而不复致力于致和。当交致其力。不可偏任者。此体用之分也。今以天地万物一体异形之一话头。混同儱侗说去。而曰中则皆和和则皆中错也。天地与吾虽一体。而吾之心正。吾之气顺。则天地之心与气亦正且顺矣。然若执据此一语。无问某人。但曰人能正心则天地万物位且育矣。无乃迂远苟大之论乎。此乃为天地万物之主者方能。而其馀则当以一家一身为言。此亦错也。章句天地之气亦顺一句。正解万物育矣。而今曰育万物也。天地之气已顺。则其意似以此一句。属天地位。此亦错也。以中和对说则中故和。以位育对说则位故育。以中和位育言则位育者中和之效也。而今曰天地位故万物育。吾心正故天地位。以吾心天地万物分三层说。此亦错也。位致中之效。育致和之效。而今曰育万物。即吾之所气和也。位天地。即吾之所心正也。徒据本吾一体一句。而不知吾自吾天地自天地。其分之不同。此亦错也。舜卿之有此错。诚非意图。至若末段若是其分以下语。则正是章句本旨。非错也。
育万物。则是有若我去位彼错也。致中则斯致和矣。天地位则斯万物育矣。而亦不可致中矣。而不复致力于致和。当交致其力。不可偏任者。此体用之分也。今以天地万物一体异形之一话头。混同儱侗说去。而曰中则皆和和则皆中错也。天地与吾虽一体。而吾之心正。吾之气顺。则天地之心与气亦正且顺矣。然若执据此一语。无问某人。但曰人能正心则天地万物位且育矣。无乃迂远苟大之论乎。此乃为天地万物之主者方能。而其馀则当以一家一身为言。此亦错也。章句天地之气亦顺一句。正解万物育矣。而今曰育万物也。天地之气已顺。则其意似以此一句。属天地位。此亦错也。以中和对说则中故和。以位育对说则位故育。以中和位育言则位育者中和之效也。而今曰天地位故万物育。吾心正故天地位。以吾心天地万物分三层说。此亦错也。位致中之效。育致和之效。而今曰育万物。即吾之所气和也。位天地。即吾之所心正也。徒据本吾一体一句。而不知吾自吾天地自天地。其分之不同。此亦错也。舜卿之有此错。诚非意图。至若末段若是其分以下语。则正是章句本旨。非错也。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21L 页
 鬼神与阴阳何别云云。
鬼神与阴阳何别云云。就阴阳合散上。形容理之流行变化。不得不然底一句语。甚的确。盖阴阳非鬼神。阴阳之灵妙处乃鬼神也。
答权舜卿问目(癸未)
三年之丧。遭师丧则先儒有送葬之说。而于朋友则不吊。师友不同故耳。然师亦有分数。恐未必尽然。
师友虽皆无服。然师丧视父。友丧视缌。亦可同耶。师亦不可以一率论。此在要诀。最下者与朋友最重者同服。虽然同服。礼有以名加之文。亦不可同也。友虽不吊。师则恐不但已也。
居父母之丧。如或有朋友横罹死罪。而若我一书以公诵于执法者。可以得脱。则亦当为之发书否。
朋友有分数。我于执法者。相知亦有分数。若我切友而我又无间于执法者。则虽亲往面折。恐无不可。若于彼于此。俱是凡交则似不可为也。
老少虽不同。而其以友道相待则一也。如或长老多有可规之事。而曾未能随遇规谏。以尽我忠告之义。若因一事追举前失。则在我虽出于相惜之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2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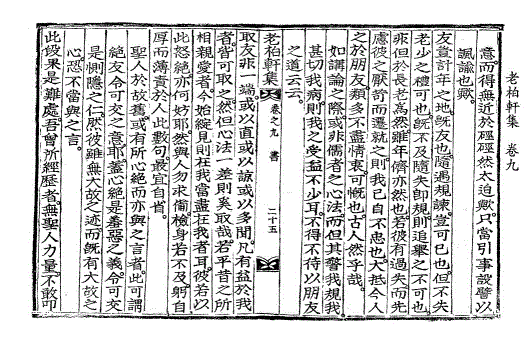 意。而得无近于硁硁然太迫欤。只当引事设譬以讽谕也欤。
意。而得无近于硁硁然太迫欤。只当引事设譬以讽谕也欤。友岂计年之地。既友也。随遇规谏。岂可已也。但不失老少之礼可也。既不及随失即规。则追举之不可也。非但于长老为然。虽年侪亦然也。若彼有过失。而先虑彼之厌苛而迁就之。则我已自不忠也。大抵今人之于朋友。类多不尽情衷。可慨也。古人然乎哉。
如讲论之际。或非儒者之心法。而但其警我规我。甚切我病。则我之受益不少耳。不得不待以朋友之道云云。
取友非一端。或以直或以谅或以多闻。凡有益于我者。皆可取之。然但心法一差则奚取哉。若平昔之所相亲爱者。今始绽见则在我当尽在我者耳。彼若以此怒绝。亦何妨耶。然与人勿求备。检身若不及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此数句。最宜自省。
圣人于故旧。或有所心绝而亦与之言者。此可谓绝友令可交之意耶。盖心绝是羞恶之义。令可交是恻隐之仁。然彼虽无大故之迹。而既有大故之心。恐不当与之言。
此段果是难处。吾曾所经历者。无圣人力量。不敢叩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2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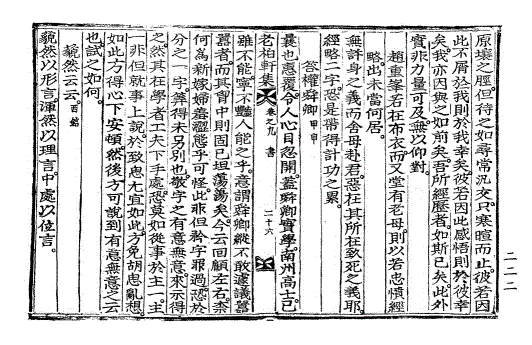 原壤之胫。但待之如寻常汎交。只寒暄而止。彼若因此不屑于我则于我幸矣。彼若因此感悟则于彼幸矣。我亦因与之如前矣。吾所经历者。如斯已矣。此外实非力量可及。无以仰对。
原壤之胫。但待之如寻常汎交。只寒暄而止。彼若因此不屑于我则于我幸矣。彼若因此感悟则于彼幸矣。我亦因与之如前矣。吾所经历者。如斯已矣。此外实非力量可及。无以仰对。赵重峰若在布衣。而又堂有老母。则以若忠愤经略。出未当何居。
无许身之义而舍母赴君。恶在其所在致死之义耶。经略二字。恐是带得计功之累。
答权舜卿(甲申)
曩也惠覆。令人心目忽开。盖舜卿实学。南州高士。己虽不能。宁不艳人能之乎。意谓舜卿纵不敢遽议嚣嚣者。而其胸中则固已坦荡荡矣。今云回顾左右。柰何为新嫁妇羞涩态乎可怪。此非但矜字罪过。恐于分之一字。算得未另别也。敬字之有意无意。来示得之。然其在学者工夫下手处。恐莫如从事于主一。主一非但就事上说。于致思尤宜如此。方免胡思乱想。如此方得心下安顿。然后方可说到有意无意之云也。试之如何。
藐然云云。(西铭。)
藐然以形言。浑然以理言。中处以位言。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2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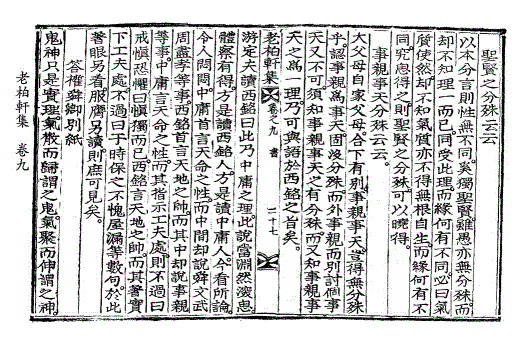 圣贤之分殊云云。
圣贤之分殊云云。以本分言则性无不同。奚独圣贤。虽愚亦无分殊。而却不知理一而已。同受此理。而缘何有不同。必曰气质使然。却不知气质亦不得无根自生。而缘何有不同。究思得之。则圣贤之分殊。可以晓得。
事亲事天分殊云云。
大父母自家父母。合下有别。事亲事天。岂得无分殊乎。认事亲为事天。固没分殊。而外事亲而别讨个事天又不可。须知事亲事天之有分殊。而又知事亲事天之为一理。乃可与语于西铭之旨矣。
游定夫读西铭曰此乃中庸之理。此说当渊然深思。体察有得。方是读西铭人。方是读中庸人。今看所论。令人闷闷。中庸首言天命之性。而中间却说舜文武周尽孝等事。西铭首言天地之帅。而其中却说事亲等事。中庸言天命之性。而其指示工夫处。则不过曰戒慎恐惧曰慎独而已。西铭言天地之帅。而其著实下工夫处。不过曰于时保之不愧屋漏等数句。于此著眼另看。服膺另读。则庶可见矣。
答权舜卿别纸
鬼神只是实理。气散而归谓之鬼。气聚而伸谓之神。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23L 页
 先儒论鬼神。只就一气字说。而今曰只是实理者何也。自其已然而论。则其聚而伸散而归气也。自其本然而论。则其所以聚散屈伸者理也。盖理者妙也。气者迹也。无屈伸之妙则无以屈伸。无聚散之妙则无以聚散。其伸也。非是将既屈之气而复为伸。其聚也。非是翕既散之气而复为聚。以其有本然之理。不以因是气而存。亦不以因是气而亡。故散而复聚。屈而复伸。天地造化。本自如此。若就祖先上说。则魂者气之精也。气存与存。气亡与亡。而人死则气已消灭矣。安有一段不消不灭之气。凝结为魂。常在于冥冥之中。时出而享之耶。惟其有实理也。故能使天下之人。齐明盛服以祭祀之。祭祀之礼。非是安排制作也。因理之自然者而教之耳。若就子孙上说。则祖考子孙。本同一气。故曰祖考精神。便是自家精神。然形既分矣。局于形者。不能无间隔。而惟是理之命于此者无间隔。根于彼者无止息。故生生不穷。而己之精神集。则祖考之神感而应之耳。然则鬼神之洋洋乎如在者。理之昭著也。然无形状影子可以手可摸而目可击者。故圣人虽极其诚敬。而犹止曰如在。曰庶享之而已。其有无聚散著存之妙。于此可以默会矣。
先儒论鬼神。只就一气字说。而今曰只是实理者何也。自其已然而论。则其聚而伸散而归气也。自其本然而论。则其所以聚散屈伸者理也。盖理者妙也。气者迹也。无屈伸之妙则无以屈伸。无聚散之妙则无以聚散。其伸也。非是将既屈之气而复为伸。其聚也。非是翕既散之气而复为聚。以其有本然之理。不以因是气而存。亦不以因是气而亡。故散而复聚。屈而复伸。天地造化。本自如此。若就祖先上说。则魂者气之精也。气存与存。气亡与亡。而人死则气已消灭矣。安有一段不消不灭之气。凝结为魂。常在于冥冥之中。时出而享之耶。惟其有实理也。故能使天下之人。齐明盛服以祭祀之。祭祀之礼。非是安排制作也。因理之自然者而教之耳。若就子孙上说。则祖考子孙。本同一气。故曰祖考精神。便是自家精神。然形既分矣。局于形者。不能无间隔。而惟是理之命于此者无间隔。根于彼者无止息。故生生不穷。而己之精神集。则祖考之神感而应之耳。然则鬼神之洋洋乎如在者。理之昭著也。然无形状影子可以手可摸而目可击者。故圣人虽极其诚敬。而犹止曰如在。曰庶享之而已。其有无聚散著存之妙。于此可以默会矣。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2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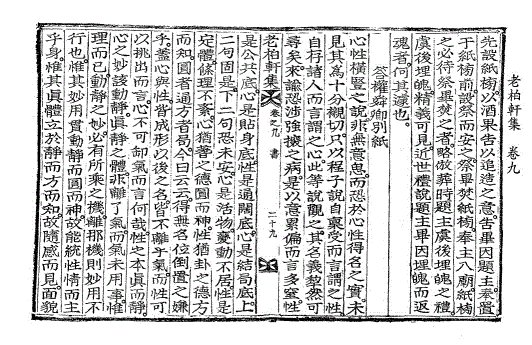 先设纸榜。以酒果告以追造之意。告毕因题主。奉置于纸榜前。设祭而安之。祭毕焚纸榜。奉主入庙。纸榜之必待祭毕焚之者。略仿葬时题主虞后埋魄之礼。虞后埋魄。精义可见。近世礼说题主毕因埋魄而返魂者。何其遽也。
先设纸榜。以酒果告以追造之意。告毕因题主。奉置于纸榜前。设祭而安之。祭毕焚纸榜。奉主入庙。纸榜之必待祭毕焚之者。略仿葬时题主虞后埋魄之礼。虞后埋魄。精义可见。近世礼说题主毕因埋魄而返魂者。何其遽也。答权舜卿别纸
心性横竖之说。非无意思。而恐于心性得名之实。未见其为十分衬切。只以程子说自禀受而言谓之性。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。此等说观之。其名义犁然可寻矣。来谕恐涉强探之病。是以意累偏而言多窒。性是公共底。心是贴身底。性是通阔底。心是结局底。上二句固是。下二句恐未安。心是活物。变动不居。性是定体。条理不紊。心犹蓍之德圆而神。性犹卦之德方而知。圆者通方者局。今曰云云。得无名位倒置之嫌乎。盖心与性。皆成形以后之名。皆不离乎气。而性可以挑出而言。心不可卸气而言何哉。性之本真而静。心之妙该动静。真静之体。非离了气。而气未用事。惟理而已。动静之妙。必有所乘之机。离那机则妙用不行也。惟其妙用贯动静而圆而神。故能统性情而主乎身。惟其真体立于静而方而知。故随感而见。面貌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24L 页
 不同。此心性之一实而二名者也。来谕又谓性自天而出。天一而已。人之性即我之性而无有彼此。心自人而立。人则有万人之心。非我之心。此亦上一截是。而下一截非是。程子曰人心不同如人面。只是私心。先师亦曰心具性。吾之心与圣人之心同。心不能尽性。吾之心与圣人之心异。体段则同而作用则异者。气禀之美恶。用事于其间。然则人各一心者。是果心之本体乎。以气质当心之本体而谓心异者。乃南塘馀论。而不意兄之似之也。心性一物。而必欲分而二之。方寸之间。二者对峙。则末稍之乖离。可胜言哉。此最头胪处。不容泯默。其他各条。与鄙见有同有异。而神眩姑置不道。
不同。此心性之一实而二名者也。来谕又谓性自天而出。天一而已。人之性即我之性而无有彼此。心自人而立。人则有万人之心。非我之心。此亦上一截是。而下一截非是。程子曰人心不同如人面。只是私心。先师亦曰心具性。吾之心与圣人之心同。心不能尽性。吾之心与圣人之心异。体段则同而作用则异者。气禀之美恶。用事于其间。然则人各一心者。是果心之本体乎。以气质当心之本体而谓心异者。乃南塘馀论。而不意兄之似之也。心性一物。而必欲分而二之。方寸之间。二者对峙。则末稍之乖离。可胜言哉。此最头胪处。不容泯默。其他各条。与鄙见有同有异。而神眩姑置不道。答权舜卿问目
若亲病。用蔘朮则可以得差。然力不足以求用。则当此之时。虽颜子恐不无忧贫之心。抑犹不改其乐否。颜子尚矣。不可妄议。以中人以下言。则屈辱吾志而或可以有为于亲。则亦当如何。且养亲者。虽卑贱之事。固无所不可。若亲志不欲。则又当柰何。
此段吾平生经历而欲质于人者也。颜子固不敢遽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25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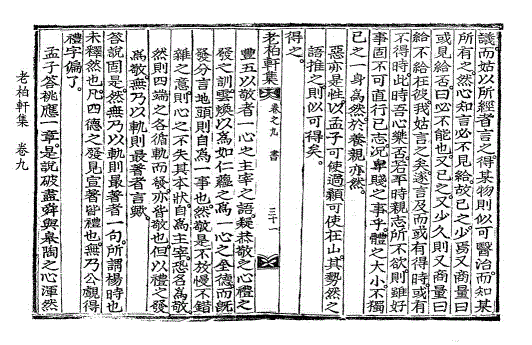 议。而姑以所经者言之。得某物则似可医治。而知某所有之。然心知言必不见给。故已之。少焉又商量曰或见给否。曰必不能也。又已之。又少久则又商量曰给不给在彼。我姑言之矣。遂言及而或有得时。或有不得时。此时吾心乐否。若平时亲志所不欲。则虽好事固不可直行己志。况卑贱之事乎。体之大小。不独己之一身为然。于养亲亦然。
议。而姑以所经者言之。得某物则似可医治。而知某所有之。然心知言必不见给。故已之。少焉又商量曰或见给否。曰必不能也。又已之。又少久则又商量曰给不给在彼。我姑言之矣。遂言及而或有得时。或有不得时。此时吾心乐否。若平时亲志所不欲。则虽好事固不可直行己志。况卑贱之事乎。体之大小。不独己之一身为然。于养亲亦然。恶亦是性。以孟子可使过颡可使在山。其势然之语推之。则似可得矣。
得之。
丰五以敬者一心之主宰之语。疑恭敬之心礼之发之训。云焕以为如仁蕴之为一心之全德。而既发分言地头则自为一事也。然敬是不放慢不错杂之意。则心之不失其本状。自为主宰。恐名为敬。然则四端之各循轨而发。亦皆敬也。但以礼之发为敬。无乃以轨则最著者言欤。
答说固是。然无乃以轨则最著者一句。所谓杨时也未释然也。凡四德之发见宣著皆礼也。无乃公觑得礼字偏了。
孟子答桃应一章。是说破尽舜与皋陶之心浑然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25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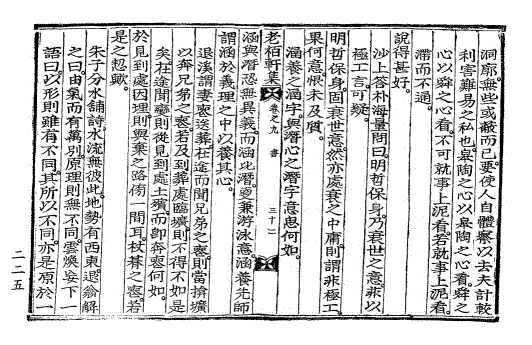 洞廓。无些或蔽而已。要使人自体察以去夫计较利害难易之私也。皋陶之心以皋陶之心看。舜之心以舜之心看。不可就事上泥看。若就事上泥看。滞而不通。
洞廓。无些或蔽而已。要使人自体察以去夫计较利害难易之私也。皋陶之心以皋陶之心看。舜之心以舜之心看。不可就事上泥看。若就事上泥看。滞而不通。说得甚好。
沙上答朴海量问曰。明哲保身。乃衰世之意。非以极工言。可疑。
明哲保身。固衰世意。然亦处衰之中庸。则谓非极工。果何意。恨未及质。
涵养之涵字。与潜心之潜字意思何如。
涵与潜恐无异义。而涵比潜。更兼游泳意。涵养先师谓涵于义理之中以养其心。
退溪谓妻丧送葬。在途而闻兄弟之丧。则当掩圹以奔兄弟之丧。若及到葬处临圹。则不得不如是矣。在途闻变则从见到处土殡。而即奔丧何如。
于见到处因埋。则与弃之路傍一间耳。杖期之丧。若是之恝欤。
朱子分水铺诗水流无彼此。地势有西东。退翁解之曰。由气而有万别。原理则无不同。云焕妄下一语曰。以形则虽有不同。其所以不同。亦是原于一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226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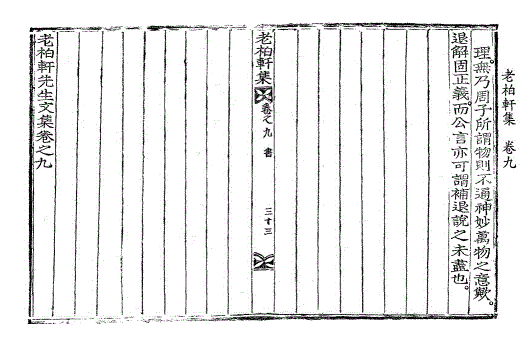 理。无乃周子所谓物则不通神妙万物之意欤。
理。无乃周子所谓物则不通神妙万物之意欤。退解固正义。而公言亦可谓补退说之未尽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