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明: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.org,kanripo.org, db.itkc.or.kr 和 zh.wikisource.org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x 页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
跋
跋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59H 页
 书大学补遗辨后
书大学补遗辨后幽窝公刚毅之气正大之论。载圭尝获私而钦慕之。讲质经学未及也。公既没。得其所著大学补遗辨读之。义精辨明。凿凿有据。于是窃恨当日之不能执经问质也。公于经靡不究。未尝立说。惟此辨以其贰于朱子定本也。其意亦渊矣哉。载圭不揆僭妄。略加刊补。而至于语句重复处。辨之详。不害其层见也。不可刊也。仍念晦斋之为补遗。岂敢多于朱子。公之辨。亦岂少晦斋哉。仁智异见。有不可以苟同者耳。然以朱子而尽一生精力。而著为定本。后朱子而学者贰而超诣。不若信而不逮之为无弊也。盖朱子之道不尊。后人之议论。容易敢到。则非斯文细忧也。然则公之为此辨。其亦有补于世教欤。
答问类编跋
此编始于庚辰。而今始甫就。盖门人金锡龟,郑义林首其议。之孙宇万赞其决。以属载圭。窃伏惟念先生在。道在先生。先生没。道在遗书。梁摧遽矣。微是何述。乃不揆僭妄。编辑为若干卷。而其有疑不敢专辄者。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5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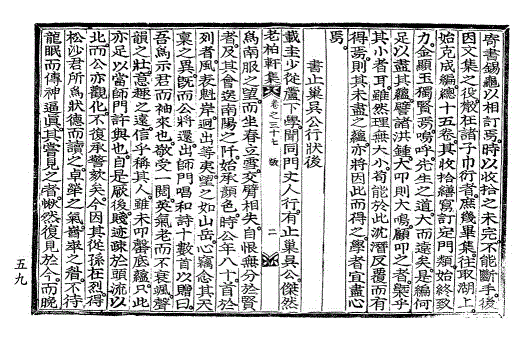 寄书锡龟以相订焉。时以收拾之未完。不能断手。后因文集之役。散在诸子巾衍者。庶几毕集。往取湖上。始克成编。总十五卷。其收拾缮写订定门类。始终致力。金显玉独贤焉。呜呼。先生之道。大而远矣。是编何足以尽其蕴。譬诸洪钟。大叩则大鸣。顾叩之者。槩乎其小者耳。虽然理无大小。苟能于此沈潜反覆而有得焉。则其未尽之蕴。亦将因此而得之。学者宜尽心焉。
寄书锡龟以相订焉。时以收拾之未完。不能断手。后因文集之役。散在诸子巾衍者。庶几毕集。往取湖上。始克成编。总十五卷。其收拾缮写订定门类。始终致力。金显玉独贤焉。呜呼。先生之道。大而远矣。是编何足以尽其蕴。譬诸洪钟。大叩则大鸣。顾叩之者。槩乎其小者耳。虽然理无大小。苟能于此沈潜反覆而有得焉。则其未尽之蕴。亦将因此而得之。学者宜尽心焉。书止巢吴公行状后
载圭少从芦下学。闻同门丈人行。有止巢吴公。杰然为南服之望。而坐春立雪。交臂相失。自恨无分于贤者。及其会送南阳之阡。始承颜色。时公年八十。首于列者。风表魁岸。迥出等夷。望之如山岳。心窃念其天禀之异。既而公将还。出师门唱和诗十数首以赠曰。吾为示君而袖来也。敬受一阅。英气老而不衰飒。声韵之壮。意趣之远。信乎称其人。虽未叩罄底蕴。只此亦足以当师门许与也。自是厥后。贱迹疏于头流以北。而公亦观化。不复承警欬矣。今因其从孙在烈。得松沙君所为状德而读之。卓荦之气。𡺚崒之眉。不待龙眠而传神逼真。其尝见之者。愀然复见于今。而晚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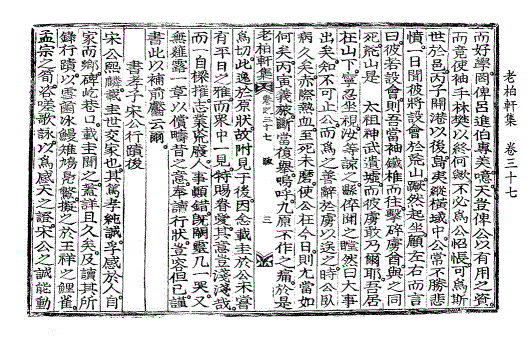 而好学。罔俾吕进伯专美。噫。天岂俾公以有用之资。而竟使袖手林樊以终何欤。不必为公怊怅。可为斯世于邑。丙子开港以后。岛夷纵横域中。公常不胜悲愤。一日闻彼将设会于荒山。蹶然起坐。顾左右而言曰。彼若设会。则吾当袖铁椎而往。击碎虏酋。与之同死。荒山是 太祖神武遗墟。而彼虏敢乃尔耶。吾居在山下。宁忍坐视。汝等谅之。县倅闻之瞠然曰大事出矣。知不可止公。而为之善辞于虏以送之。时公卧病久矣。赤际热血。至死未磨。使公在今日。则尤当如何矣。丙寅义旅。断当复举。呜呼。九原不作之痛。于是为切。此逸于原状。故附见于后。因念载圭于公未尝有平日之雅。而众中一见。特赐眷爱。其意岂浅浅哉。而一自梁摧。志业荒废。人事颠错。既阙灵几一哭。又无薤露一章以偿畴昔之意。奉读行状。岂容但已。谨书此以补前齾云尔。
而好学。罔俾吕进伯专美。噫。天岂俾公以有用之资。而竟使袖手林樊以终何欤。不必为公怊怅。可为斯世于邑。丙子开港以后。岛夷纵横域中。公常不胜悲愤。一日闻彼将设会于荒山。蹶然起坐。顾左右而言曰。彼若设会。则吾当袖铁椎而往。击碎虏酋。与之同死。荒山是 太祖神武遗墟。而彼虏敢乃尔耶。吾居在山下。宁忍坐视。汝等谅之。县倅闻之瞠然曰大事出矣。知不可止公。而为之善辞于虏以送之。时公卧病久矣。赤际热血。至死未磨。使公在今日。则尤当如何矣。丙寅义旅。断当复举。呜呼。九原不作之痛。于是为切。此逸于原状。故附见于后。因念载圭于公未尝有平日之雅。而众中一见。特赐眷爱。其意岂浅浅哉。而一自梁摧。志业荒废。人事颠错。既阙灵几一哭。又无薤露一章以偿畴昔之意。奉读行状。岂容但已。谨书此以补前齾云尔。书孝子宋公行迹后
宋公熙麟。载圭世交家也。其笃孝纯诚。孚感于人。自家而乡。碑屹巷口。载圭闻之。盖详且久矣。及读其所录行迹。以雪菌冰鳗雉鸠凫鳖。拟之于王祥之鲤雀。孟宗之笋。咨嗟歌咏。以为感天之證。宋公之诚能动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0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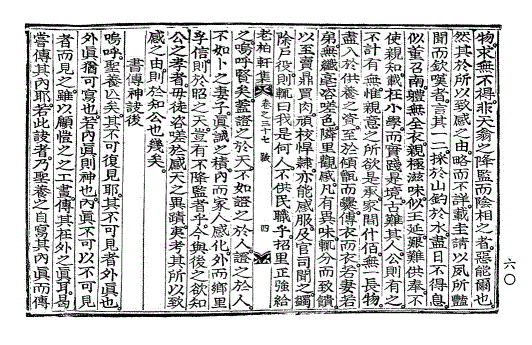 物。求无不得。非天翁之降监而阴相之者。恶能尔也。然其于所以致感之由。略而不详。载圭请以夙所艳闻而钦叹者。言其一二。采于山钓于水。尽日不得息。似董召南。体无全衣。亲极滋味。似王延。艰难供奉。不使亲知。载在小学。而实践是境。古难其人。公则有之。不计有无。惟亲意之所欲是承。家间什佰。无一长物。尽入于供养之资。至于倾甑而爨。传衣而衣。若妻若弟。无纤毫咨嗟色。邻里观感。凡有异味。辄分而致馈。以至卖鼎买肉。顽校悍隶。亦能感服。及官司闻之。蠲除户役。则辄曰我是何人。不供民职乎。招里正强给之。呜呼贤矣。盖證之于天。不如證之于人。證之于人。不如卜之妻子。真诚之积。内而家人感化。外而乡里孚信。则于昭之天。岂有不降监者乎。今与后之欲知公之孝者。毋徒咨嗟于感天之异迹。夷考其所以致感之由。则于知公也几矣。
物。求无不得。非天翁之降监而阴相之者。恶能尔也。然其于所以致感之由。略而不详。载圭请以夙所艳闻而钦叹者。言其一二。采于山钓于水。尽日不得息。似董召南。体无全衣。亲极滋味。似王延。艰难供奉。不使亲知。载在小学。而实践是境。古难其人。公则有之。不计有无。惟亲意之所欲是承。家间什佰。无一长物。尽入于供养之资。至于倾甑而爨。传衣而衣。若妻若弟。无纤毫咨嗟色。邻里观感。凡有异味。辄分而致馈。以至卖鼎买肉。顽校悍隶。亦能感服。及官司闻之。蠲除户役。则辄曰我是何人。不供民职乎。招里正强给之。呜呼贤矣。盖證之于天。不如證之于人。證之于人。不如卜之妻子。真诚之积。内而家人感化。外而乡里孚信。则于昭之天。岂有不降监者乎。今与后之欲知公之孝者。毋徒咨嗟于感天之异迹。夷考其所以致感之由。则于知公也几矣。书传神诀后
呜呼。圣养亡矣。其不可复见耶。其不可见者外真也。外真犹可写也。若内真则神也。内真不可以不可见者而见之。虽以顾恺之之工画。传其在外之真耳。曷尝传其内耶。若此诀者。乃圣养之自写其内真而传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1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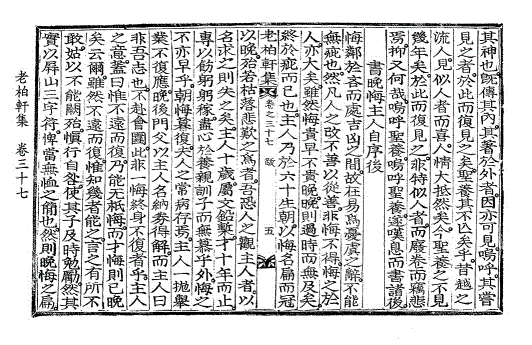 其神也。既传其内。其著于外者。因亦可见。呜呼。其尝见之者。于此而复见之矣。圣养其不亡矣乎。昔越之流人。见似人者而喜。人情大抵然矣。今圣养之不见几年矣。于此而复见之。非特似人者。而废卷而窃悲焉。抑又何哉。呜呼圣养。呜呼圣养。遂叹息而书诸后。
其神也。既传其内。其著于外者。因亦可见。呜呼。其尝见之者。于此而复见之矣。圣养其不亡矣乎。昔越之流人。见似人者而喜。人情大抵然矣。今圣养之不见几年矣。于此而复见之。非特似人者。而废卷而窃悲焉。抑又何哉。呜呼圣养。呜呼圣养。遂叹息而书诸后。书晚悔主人自序后
悔邻于吝而处吉凶之间。故在易为忧虞之辞。不能无疵也。然凡人之改不善以从善。非悔不得。悔之于人。亦大矣。虽然悔贵早不贵晚。晚则过时而无及矣。终于疵而已也。主人乃于六十生朝。以悔名扁而冠以晚。殆若枯落悲叹之为者。吾恐人之观主人者。以名求之则失之矣。主人十岁。属文铅椠。才十年而止。专以饬躬躬稼。尽心于养亲训子而无慕乎外。悔之不亦早乎。朝悔暮复。夫人之常病存焉。主人一抛举业不复应。晚后门父以主人名纳券得解。而主人曰非吾志也。不赴会围。此非一悔终身不复者乎。主人之意。盖曰惟不远而复。乃能无祇悔。而才悔则已晚矣云尔。虽然不远而复。惟知几者能之。言之有所不敢。姑以不能阙殆。慎行自咎。使其子及时勉励。然其实以屏山三字符。俾当无恤之𥳑也。然则晚悔之扁。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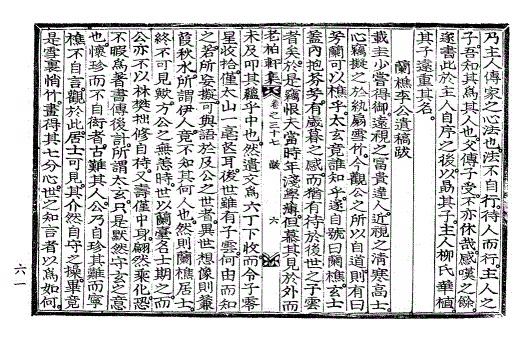 乃主人传家之心法也。法不自行。待人而行。主人之子。吾知其为其人也。父传子受。不亦休哉。感叹之馀。遂书此于主人自序之后。以勖其子。主人柳氏华植。其子远重其名。
乃主人传家之心法也。法不自行。待人而行。主人之子。吾知其为其人也。父传子受。不亦休哉。感叹之馀。遂书此于主人自序之后。以勖其子。主人柳氏华植。其子远重其名。兰樵李公遗稿跋
载圭少尝得御。远视之富贵达人。近视之清寒高士。心窃拟之于纨扇雪竹。今观公之所以自道。则有曰芳兰可以樵乎。太玄竟谁知乎。遂自号曰兰樵。玄士盖内抱芬芳。有岁暮之感。而犹有待于后世之子云者矣。于是窃恨夫当时年浅学薄。但慕其见于外而未及叩其蕴乎中也。然遗文为六丁下收。而令子零星收拾。仅太山一毫芒耳。后世虽有子云。何由而知之。若所妄拟。可与语于及公之世者。异世想像则蒹葭秋水。所谓伊人。竟不知其何人也。然则兰樵居士。终不可见欤。方公之无恙时。世以兰台名士期之。而公亦不以林樊拙修自待。又寿仅中身。翩然乘化。恐不暇为著书传后计。所谓太玄。只是默然守玄之意也。怀珍而不自衒者。古难其人。公乃自珍其难而宁樵不自言。观于此。居士可见。其介然自守之操。毕竟是雪里悄竹。画得其七分心。世之知言者以为如何。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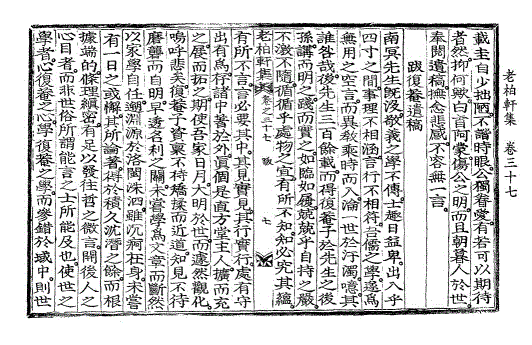 载圭自少拙陋。不谐时眼。公独眷爱。有若可以期待者然。抑何欤。白首阿蒙。伤公之明。而且朝暮人于世。奉阅遗稿。抚念悲感。不容无一言。
载圭自少拙陋。不谐时眼。公独眷爱。有若可以期待者然。抑何欤。白首阿蒙。伤公之明。而且朝暮人于世。奉阅遗稿。抚念悲感。不容无一言。跋复庵遗稿
南冥先生既没。敬义之学不传。士趣日益卑。出入乎四寸之间。事理不相涵。言行不相符。吾儒之学。遂为无用之空言。而异教乘时而入。沦一世于污浊。噫。其谁咎哉。后先生三百馀载。而得复庵子于先生之后孙。讲而明之。践而实之。如临如履。兢兢乎自持之严。不激不随。循循乎处物之宜。有所不知。知必究其蕴。有所不言。言必要其中。其见实见。其行实行。处有守出有为。存诸中著于外。真个是直方堂主人。扩而充之。展而拓之。期使吾家日月。大明于世。而遽然观化。呜呼悲矣。复庵子资禀不待矫揉而近道。知见不待磨砻而自明。早透名利之关。未尝学为文章而断然以家学自任。溯渊源于洛闽洙泗。虽沉痾在身。未尝有一日之或懈。其所论著。得于积久沈潜之馀。而根据端的。条理缜密。有足以发往哲之微言。开后人之心目者。而非世俗所谓能言之士所能及也。使世之学者。心复庵之心。学复庵之学。而参错于域中。则世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2L 页
 道必不至于今日之沦陷。重可悲矣。其孤庸相以其遗稿三册示余。谒玄志。兼嘱丁乙。揆以平素。若不可辞。而顾有拙戒。不敢犯手于琬琰之刻。而丁乙又岂謏寡耄昏者所能。姑书此于卷末。以告后之读者。
道必不至于今日之沦陷。重可悲矣。其孤庸相以其遗稿三册示余。谒玄志。兼嘱丁乙。揆以平素。若不可辞。而顾有拙戒。不敢犯手于琬琰之刻。而丁乙又岂謏寡耄昏者所能。姑书此于卷末。以告后之读者。题权应九切偲帖
凡先人所用。虽簪梳之微。古之人有珍藏而不失者。况师友切偲之言。先人之用以服膺者耶。明狂子既没。其弟舜卿甫作是帖以遗其孤。帖中陋生暨山石公之言最多。其言或讽或直截。非明狂子。固不能受。又不敢言。今已矣。吾两人之言。将亦已矣。林立寰宇。堪此者更有何人。其孤苟能知其先人之心。继其先人之志。则其先人平日所受用以服膺者。岂不是无恤之简。其孤之一生服膺。亦在于是。知也未。揽涕而为之识。识之者后死友艾山郑载圭。书之者山石金显玉。时明狂子入地后四日。癸巳六月也。
书河秀士行录后
右河秀士讳龙辅字义汝之行。而其孤进海为之录者也。进海斤斤述父行。无一字浮辞。亦嘉矣哉。其意盖冀其有一言也。病废泓颖久矣。柰之何。然摩挲数回。愀然如复见二十年前颜面。不觉悲感。余亦少业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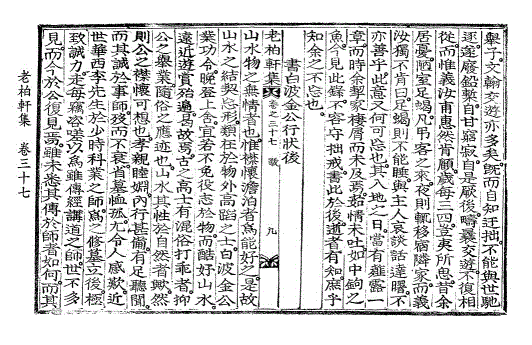 举子。文翰交游亦多矣。既而自知迂拙。不能与世驰逐。遂废铅椠。自甘穷寂。自是厥后。畴曩交游。不复相从。而惟义汝甫惠然肯顾。岁每三四。岂夷所思。昔余居忧。陋室足蝎。凡吊客之来。夜则辄移宿邻家。而义汝独不肯曰。足蝎则不能睡。与主人哀谈话达曙。不亦善乎。此意又何可忘也。其入地之日。当有薤露一章。而时余挈家栖屑而未及焉。茹情未吐。如中钩之鱼。今见此录。不容守拙戒。书此于后。逝者有知。庶乎知余之不忘也。
举子。文翰交游亦多矣。既而自知迂拙。不能与世驰逐。遂废铅椠。自甘穷寂。自是厥后。畴曩交游。不复相从。而惟义汝甫惠然肯顾。岁每三四。岂夷所思。昔余居忧。陋室足蝎。凡吊客之来。夜则辄移宿邻家。而义汝独不肯曰。足蝎则不能睡。与主人哀谈话达曙。不亦善乎。此意又何可忘也。其入地之日。当有薤露一章。而时余挈家栖屑而未及焉。茹情未吐。如中钩之鱼。今见此录。不容守拙戒。书此于后。逝者有知。庶乎知余之不忘也。书白波金公行状后
山水物之无情者也。惟襟怀澹泊者为能好之。是故山水之结契忘形。类在于物外高蹈之士。白波金公业功令。晚登上舍。宜若不免役志于物。而酷好山水。远近游赏殆遍。曷故焉。古之高士有混俗打乖者。抑公之举业。随俗之应迹也。山水其性于自然者欤。然则公之襟怀可想也。孝亲睦姻。内行甚备。有足听闻。而其诚于事师。殁而不衰。省墓恤孤。尤令人感叹。近世华西李先生于少时科业之师。为之修墓立后。极致诚力。走每窃咨嗟以为虽传经讲道之师。世不多见。而今于公复见焉。虽未悉其传于师者如何。而其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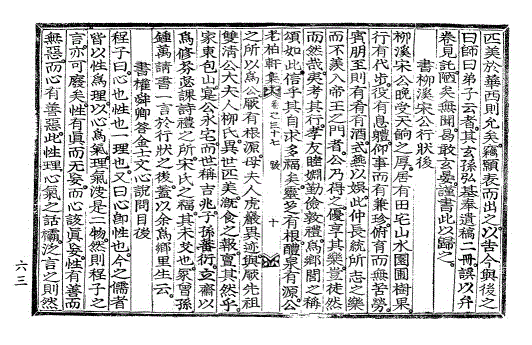 匹美于华西则允矣。窃愿表而出之。以告今与后之曰师曰弟子云者。其玄孙弘基奉遗稿二册。误以弁卷见托。陋矣无闻。曷敢玄晏。谨书此以归之。
匹美于华西则允矣。窃愿表而出之。以告今与后之曰师曰弟子云者。其玄孙弘基奉遗稿二册。误以弁卷见托。陋矣无闻。曷敢玄晏。谨书此以归之。书柳溪宋公行状后
柳溪宋公晚受天饷之厚。居有田宅山水园圃树果。行有代步。役有息体。仰事而有兼珍。俯育而无苦劳。宾朋至则有肴有酒。式燕以娱。此仲长统所志之乐而不羡入帝王之门者。公乃得之。优享其乐。岂徒然而然哉。夷考其行。孝友睦姻勤俭敦礼。为乡闾之称颂如此。信乎其自求多福矣。灵芝有根。醴泉有源。公之所以为公。厥有根源。母夫人虎岩异迹。与厥先祖双清公大夫人柳氏。异世匹美。溉食之报。亶其然乎。家东包山。寔公永宅。而世称吉兆。子孙蕃衍。立斋以为修芬苾课诗礼之所。宋氏之福。其未艾也。冢曾孙钟万请书一言于行状之后。盖以余为乡里生云。
书权舜卿答金士文心说问目后
程子曰。心也性也一理也。又曰心即性也。今之儒者皆以性为理。以心为气。理气决是二物。然则程子之言。亦可废矣。性有真而无妄。而心该真妄。性有善而无恶。而心有善恶。此性理心气之话把。泛言之则然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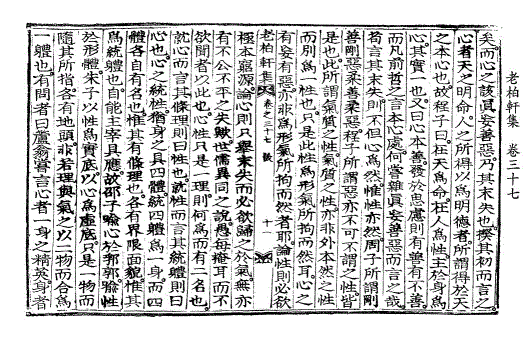 矣。而心之该真妄善恶。乃其末失也。揆其初而言之。心者天之明命。人之所得以为明德者。所谓得于天之本心也。故程子曰。在天为命。在人为性。主于身为心。其实一也。又曰心本善。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。而凡前哲之言本心处。何尝杂真妄善恶而言之哉。苟言其末失。则不但心为然。惟性亦然。周子所谓刚善刚恶柔善柔恶。程子所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。皆是也。此所谓气质之性。气质之性。亦非外本然之性而别为一性也。只是此性为形气所拘而然耳。心之有妄有恶。亦非为形气所拘而然者耶。论性则必欲极本穷源。论心则只举末失而必欲归之于气。无亦有不公不平之失欤。世儒异同之说。愚每掩耳而不欲闻者以此也。心性只是一理。则何为而有二名也。就心而言其条理则曰性也。就性而言其统体则曰心也。心之统性。犹身之具四体。统四体为一身。而四体各自有名也。惟其有条理也。各有界限面貌。惟其为统体也。自能主宰具应。故邵子喻心于郛郭。喻性于形体。朱子以性为实底。以心为虚底。只是一物而随其所指。各有地头。非若理与气之以二物而合为一体也。有问者曰芦翁尝言心者一身之精英。身者
矣。而心之该真妄善恶。乃其末失也。揆其初而言之。心者天之明命。人之所得以为明德者。所谓得于天之本心也。故程子曰。在天为命。在人为性。主于身为心。其实一也。又曰心本善。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。而凡前哲之言本心处。何尝杂真妄善恶而言之哉。苟言其末失。则不但心为然。惟性亦然。周子所谓刚善刚恶柔善柔恶。程子所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。皆是也。此所谓气质之性。气质之性。亦非外本然之性而别为一性也。只是此性为形气所拘而然耳。心之有妄有恶。亦非为形气所拘而然者耶。论性则必欲极本穷源。论心则只举末失而必欲归之于气。无亦有不公不平之失欤。世儒异同之说。愚每掩耳而不欲闻者以此也。心性只是一理。则何为而有二名也。就心而言其条理则曰性也。就性而言其统体则曰心也。心之统性。犹身之具四体。统四体为一身。而四体各自有名也。惟其有条理也。各有界限面貌。惟其为统体也。自能主宰具应。故邵子喻心于郛郭。喻性于形体。朱子以性为实底。以心为虚底。只是一物而随其所指。各有地头。非若理与气之以二物而合为一体也。有问者曰芦翁尝言心者一身之精英。身者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4L 页
 气质之团聚也。子亦尝言性可挑出而言之。心不可卸气而言。今曰云云则不几于左右佩剑乎。曰一身之精英。即理之所在也。朱子曰。气之精英者是神。水火金木土非神。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。在人则仁义礼智信是也。周子图说。言得其秀而最灵。最灵是心。而朱子以人极释之。吾故曰一身之精英。即理之所在也。性是真静之体也。方其静也。气未用事。惟理而已。故可以挑出而言之。太极图第一圈。乃其在阴阳圈里面者。挑出而置之上头。以明造化之枢纽根柢也。若心则众理之总会而主宰众理。所谓心为太极也。然所藉以为地盘。所乘以为运用之机。乃其一身之精神魂魄。朱子所谓气之精爽者也。除却此魂魄精爽之界至。则无说讨个心字处。所以不可卸气而言。朱子所谓比性微有迹者以此。盖性蕴动静而静体为主。心该体用而妙用为主故也。心统性情。仁义礼智性也。爱敬宜知情也。以仁爱。以礼敬。以义宜。以智知者心也。以之者为主。而性情其条理准则也。未发而知觉不昧。心之主乎性者也。已发而品节不差。心之主乎情者也。性情皆以心为主。今乃遗却其主者。但讨个精神魂魄。闪闪烁烁地光景谓心。是
气质之团聚也。子亦尝言性可挑出而言之。心不可卸气而言。今曰云云则不几于左右佩剑乎。曰一身之精英。即理之所在也。朱子曰。气之精英者是神。水火金木土非神。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。在人则仁义礼智信是也。周子图说。言得其秀而最灵。最灵是心。而朱子以人极释之。吾故曰一身之精英。即理之所在也。性是真静之体也。方其静也。气未用事。惟理而已。故可以挑出而言之。太极图第一圈。乃其在阴阳圈里面者。挑出而置之上头。以明造化之枢纽根柢也。若心则众理之总会而主宰众理。所谓心为太极也。然所藉以为地盘。所乘以为运用之机。乃其一身之精神魂魄。朱子所谓气之精爽者也。除却此魂魄精爽之界至。则无说讨个心字处。所以不可卸气而言。朱子所谓比性微有迹者以此。盖性蕴动静而静体为主。心该体用而妙用为主故也。心统性情。仁义礼智性也。爱敬宜知情也。以仁爱。以礼敬。以义宜。以智知者心也。以之者为主。而性情其条理准则也。未发而知觉不昧。心之主乎性者也。已发而品节不差。心之主乎情者也。性情皆以心为主。今乃遗却其主者。但讨个精神魂魄。闪闪烁烁地光景谓心。是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5H 页
 气判心性为二物。而至有尊性而卑心者。气而主理。卑而主尊。亦有是欤。呜呼。天下将何事不有。臣而制君。夷而夺华。亦不足怪者欤。抑又论之。泛谓之心即理则举本而遗末。使学者不察乎危微之几。而弊或至于认贼为子矣。泛谓之心即气则举末而遗本。使学者不知有天命之尊。而势将至于主仆无分矣。何者。理气虽是二物。而吻合一体。混瀜无间。相须为用。理是气之所以生之妙也。气是理之所由乘之机也。理有作用之妙而无作用。作用之任在于气。气若一顺乎理。则气之用即理之用。所谓心即理者。诚得矣。如或所乘之势反重。而未发而不昏则乱。已发而放逸横走。骋其伎俩。自作自用。如曹瞒之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则以其所挟者天子。而认为天子之令。惟令是从。则岂非认贼为子者乎。知气之伎俩如此。而谓心为气。则其于危微之际。固若可以戒谨省察矣。然心也者为一身之主。提万事之纲者也。为主提纲者。果所谓气。则所谓理者。不得不听命于气。而为寄寓可怜之物。如汉献帝之徒拥虚号而慵懦无能。虽十分恐惧。十分戒慎。君如彼何哉。岂非主仆之无分者乎。然则心果是何物。所谓合理气者是耶。人之魂魄。是
气判心性为二物。而至有尊性而卑心者。气而主理。卑而主尊。亦有是欤。呜呼。天下将何事不有。臣而制君。夷而夺华。亦不足怪者欤。抑又论之。泛谓之心即理则举本而遗末。使学者不察乎危微之几。而弊或至于认贼为子矣。泛谓之心即气则举末而遗本。使学者不知有天命之尊。而势将至于主仆无分矣。何者。理气虽是二物。而吻合一体。混瀜无间。相须为用。理是气之所以生之妙也。气是理之所由乘之机也。理有作用之妙而无作用。作用之任在于气。气若一顺乎理。则气之用即理之用。所谓心即理者。诚得矣。如或所乘之势反重。而未发而不昏则乱。已发而放逸横走。骋其伎俩。自作自用。如曹瞒之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则以其所挟者天子。而认为天子之令。惟令是从。则岂非认贼为子者乎。知气之伎俩如此。而谓心为气。则其于危微之际。固若可以戒谨省察矣。然心也者为一身之主。提万事之纲者也。为主提纲者。果所谓气。则所谓理者。不得不听命于气。而为寄寓可怜之物。如汉献帝之徒拥虚号而慵懦无能。虽十分恐惧。十分戒慎。君如彼何哉。岂非主仆之无分者乎。然则心果是何物。所谓合理气者是耶。人之魂魄。是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5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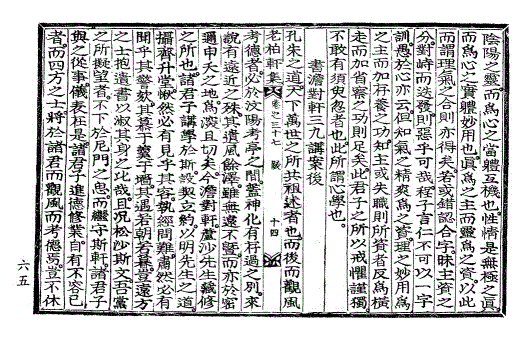 阴阳之灵。而为心之当体互机也。性情是无极之真。而为心之实体妙用也。真为之主而灵为之资。以此而谓理气之合则亦得矣。若或错认合字。昧主资之分。对峙而迭发。则恶乎可哉。程子言仁不可以一字训。愚于心亦云。但知气之精爽为之资。理之妙用为之主而加存养之功。知主或失职则所资者反为横走而加省察之功则足矣。此君子之所以戒惧谨独。不敢有须臾忽者也。此所谓心学也。
阴阳之灵。而为心之当体互机也。性情是无极之真。而为心之实体妙用也。真为之主而灵为之资。以此而谓理气之合则亦得矣。若或错认合字。昧主资之分。对峙而迭发。则恶乎可哉。程子言仁不可以一字训。愚于心亦云。但知气之精爽为之资。理之妙用为之主而加存养之功。知主或失职则所资者反为横走而加省察之功则足矣。此君子之所以戒惧谨独。不敢有须臾忽者也。此所谓心学也。书澹对轩三九讲案后
孔朱之道。天下万世之所共祖述者也。而后而观风考德者。必于汶阳考亭之间。盖神化有存过之别。来说有远近之殊。其遗风馀泽。虽无远不暨。而亦于密迩申夭之地。为深且切矣。今澹对轩。芦沙先生藏修之所也。诸君子讲学于斯。设契立约。以明先生之道。摄齐升堂。愀然必有见乎其容。执经问难。肃然必有闻乎其警欬。其慕于羹于墙。其遇若朝若暮。岂远方之士抱遗书以淑其身之比哉。且况松沙斯文。吾党之所拟望者。不下于尼门之思。而继守斯轩。诸君子与之从事。仪表在是。诸君子进德修业。自有不容已者。而四方之士。将于诸君而观风而考德焉。岂不休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6H 页
 哉。松沙子以载圭亦常猥及于先生之门者。请置一言。忠信进修之方。诸君子已见之昭陵。规警奖励。载圭非其人。且道诸君子薰沐之迩且深者。以致钦艳之意云。
哉。松沙子以载圭亦常猥及于先生之门者。请置一言。忠信进修之方。诸君子已见之昭陵。规警奖励。载圭非其人。且道诸君子薰沐之迩且深者。以致钦艳之意云。书崔孝仲西征记后
梧坡吾晚友也。居一舍地。衰白相识何哉。梧坡早岁蜚英。从都下贤士大夫游。吾迂拙无能。自甘穷蛰。升沈不同。如黄鹄壤虫。其不相及固也。又世之学腾骞者。趋荣赴势。不择所从。曷尝事贤而友仁哉。其中或有自谓稍出头角。而即不过朱先生所谓观其俯仰。亦可怜者也。不惟彼不求我。我亦不愿求也。日有一儒冠叩衡门。伟然之气。见于眉宇容止之间。揖而问之。乃梧坡崔孝仲也。梧坡有声场屋。屡入鼎铛之耳。斯人也何乃尔。心异之。叩其所与游。李承宣宁斋公其主人也。为我道宁公之人与文。且诵其相与唱酬者。其议论文章。有根据有筋骨。而世俗俯仰之态。无一点子著得。吁观远人视其主。观近人视其所为主。于是乎可以知梧坡而宁公又可知也。宁公迩来树立。可谓今世之完人。慨并世而不相见。今得见其所与者。是所谓如见元宾焉。亦足自慰也。其后梧坡向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6L 页
 余道宁公之亡。窃不自胜其痛叹悲伤。非为梧坡吊。实悯斯世。梧坡徒步千里。哭宁公于沁都。往来之所耳目者。一于诗发之。录之为西征记。往往慷慨呜咽。有燕市歌筑遗响。侑文哀辞。调古意真。真得宁公之髓者。穷山壹郁。得此而可以少泻。梧友之惠我亦多矣。梧友今老矣。无复当世之念。盖时然也。此吾之得与梧友游。梧友之不幸。而吾之幸也欤。
余道宁公之亡。窃不自胜其痛叹悲伤。非为梧坡吊。实悯斯世。梧坡徒步千里。哭宁公于沁都。往来之所耳目者。一于诗发之。录之为西征记。往往慷慨呜咽。有燕市歌筑遗响。侑文哀辞。调古意真。真得宁公之髓者。穷山壹郁。得此而可以少泻。梧友之惠我亦多矣。梧友今老矣。无复当世之念。盖时然也。此吾之得与梧友游。梧友之不幸。而吾之幸也欤。书文敬叔系牒叙述后
谱者一家之春秋。疑而传疑。信而传信。书法极其谨严。文友敬叔之先系。稽之于古则各家所藏。信而有證。参之于今则诸公所述。亦无异辞。一家之公论。后先如此。彼一时之惎诬。何足为有无。窃惟孤查公孝义之行。生而满乡党。没而闻邦国。以光先裕后。而敬叔之致力于先系。老而弥勤。所谓孝子不匮。永锡祚胤者非耶。余与敬叔及其子昌锡其孙正浩三世游从。其相与之谊。几乎痛痒相关。玆忘陋一言。以附诸公叙述之后。以贺文氏一门公论之久而不泯也云尔。
龟岩集跋
载圭昔尝侍坐于师门。先生言绫城有文氏子从季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7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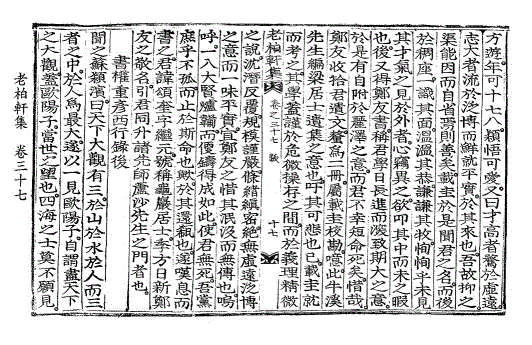 方游。年可十七八。颖悟可爱。又曰才高者骛于虚远。志大者流于泛博而鲜就平实。于其来也。吾故抑之。渠能因而自省焉则善矣。载圭于是闻君之名。而后于稠座。一识其面。温温其恭。谦谦其牧。恂恂乎未见其才气之见于外者。心窃异之。欲叩其中而未之暇也。后又得郑友书。称君学日长进而深致期大之意。于是有自附于丽泽之意。而君不幸短命死矣。惜哉。郑友收拾君遗文。釐为二册。属载圭校勘。噫。此牛溪先生编梁居士遗集之意也。吁其可悲也已。载圭就而考之。其学盖谨于危微操存之间。而于义理精微之说。沈潜反覆。规模谨严。条绪缜密。绝无虚远泛博之意而一味平实。宜郑友之惜其泯没而无传也。呜呼。一入大贤炉韛。而便铸得成如此。使君无死。吾党庶乎不孤。而止于斯命也欤。于其还瓻也。遂叹息而书之。君讳颂奎字继元。号称龟岩居士。季方日新郑友之敬名。引君同升诸先师芦沙先生之门者也。
方游。年可十七八。颖悟可爱。又曰才高者骛于虚远。志大者流于泛博而鲜就平实。于其来也。吾故抑之。渠能因而自省焉则善矣。载圭于是闻君之名。而后于稠座。一识其面。温温其恭。谦谦其牧。恂恂乎未见其才气之见于外者。心窃异之。欲叩其中而未之暇也。后又得郑友书。称君学日长进而深致期大之意。于是有自附于丽泽之意。而君不幸短命死矣。惜哉。郑友收拾君遗文。釐为二册。属载圭校勘。噫。此牛溪先生编梁居士遗集之意也。吁其可悲也已。载圭就而考之。其学盖谨于危微操存之间。而于义理精微之说。沈潜反覆。规模谨严。条绪缜密。绝无虚远泛博之意而一味平实。宜郑友之惜其泯没而无传也。呜呼。一入大贤炉韛。而便铸得成如此。使君无死。吾党庶乎不孤。而止于斯命也欤。于其还瓻也。遂叹息而书之。君讳颂奎字继元。号称龟岩居士。季方日新郑友之敬名。引君同升诸先师芦沙先生之门者也。书权重彦西行录后
闻之苏颍滨。曰天下大观有三。于山于水于人而三者之中。于人为最大。遂以一见欧阳子。自谓尽天下之大观。盖欧阳子。当世之望也。四海之士莫不愿见。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7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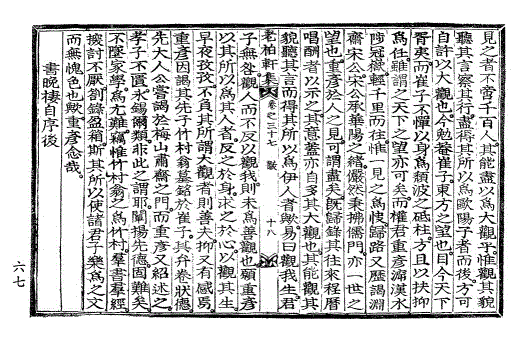 见之者不啻千百人。其能尽以为大观乎。惟观其貌听其言察其行。尽得其所以为欧阳子者而后。方可自许以大观也。今勉庵崔子。东方之望也。目今天下胥夷。而崔子不惮以身为颓波之砥柱。方且以扶抑为任。虽谓之天下之望亦可矣。而权君重彦溯汉水陟冠岳。轻千里而往。惟一见之为快。归路又历谒渊斋宋公。宋公承华阳之绪。俨然秉拂儒门。亦一世之望也。重彦于人之见。可谓尽矣。既归录其往来程历唱酬者以示之。其意盖亦自多其大观也。其能观其貌听其言而得其所以为伊人者欤。易曰观我生。君子无咎。观人而不反以观我。则未为善观也。愿重彦以其所以为其人者。反之于身。求之于心。以观其生。早夜孜孜。不负其所谓大观者则善夫。抑又有感焉。重彦因谒其先子竹村翁墓铭于崔子。其弁卷状德。先大人公尝谒于梅山肃斋之门。而重彦又绍述之。孝子不匮。永锡尔类。非此之谓耶。阐扬先德。固难矣。不坠家学。为尤难。窃惟竹村翁之为竹村。群书群经。探讨不厌。劄录盈箱。斯其所以使诸君子乐为之文而无愧色也欤。重彦念哉。
见之者不啻千百人。其能尽以为大观乎。惟观其貌听其言察其行。尽得其所以为欧阳子者而后。方可自许以大观也。今勉庵崔子。东方之望也。目今天下胥夷。而崔子不惮以身为颓波之砥柱。方且以扶抑为任。虽谓之天下之望亦可矣。而权君重彦溯汉水陟冠岳。轻千里而往。惟一见之为快。归路又历谒渊斋宋公。宋公承华阳之绪。俨然秉拂儒门。亦一世之望也。重彦于人之见。可谓尽矣。既归录其往来程历唱酬者以示之。其意盖亦自多其大观也。其能观其貌听其言而得其所以为伊人者欤。易曰观我生。君子无咎。观人而不反以观我。则未为善观也。愿重彦以其所以为其人者。反之于身。求之于心。以观其生。早夜孜孜。不负其所谓大观者则善夫。抑又有感焉。重彦因谒其先子竹村翁墓铭于崔子。其弁卷状德。先大人公尝谒于梅山肃斋之门。而重彦又绍述之。孝子不匮。永锡尔类。非此之谓耶。阐扬先德。固难矣。不坠家学。为尤难。窃惟竹村翁之为竹村。群书群经。探讨不厌。劄录盈箱。斯其所以使诸君子乐为之文而无愧色也欤。重彦念哉。书晚栖自序后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8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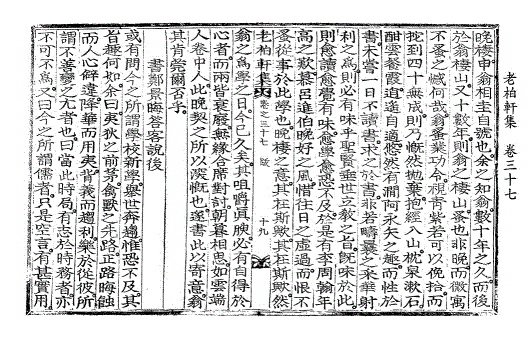 晚栖。申翁相圭自号也。余之知翁。数十年之久。而后于翁栖山。又十数年。则翁之栖山。蚤也非晚。而微寓不蚤之憾何哉。翁蚤业功令。视青紫若可以俛拾。而拖到四十无成。则乃慨然抛弃。抱经入山。枕泉漱石。酣云餐霞。逍遥自适。悠然有涧阿永矢之趣。而性于书。未尝一日不读书。求之于书。非若畴曩之采华射利之为。则必有味乎圣贤垂世立教之旨。既味于此。则愈读愈觉有味。愈学愈恐不及。于是有李周翰年高之叹。慕吕进伯晚好之风。惜往日之虚过。而恨不蚤从事于此学也。晚栖之意。其在斯欤。其在斯欤。然翁之为学之日。今已久矣。其咀嚼真腴。必有自得于心者。而两皆衰废。无缘合席对讨。朝暮相思。如云端人卷中人。此晚契之所以深慨也。遂书此以寄意。翁其肯莞尔否乎。
晚栖。申翁相圭自号也。余之知翁。数十年之久。而后于翁栖山。又十数年。则翁之栖山。蚤也非晚。而微寓不蚤之憾何哉。翁蚤业功令。视青紫若可以俛拾。而拖到四十无成。则乃慨然抛弃。抱经入山。枕泉漱石。酣云餐霞。逍遥自适。悠然有涧阿永矢之趣。而性于书。未尝一日不读书。求之于书。非若畴曩之采华射利之为。则必有味乎圣贤垂世立教之旨。既味于此。则愈读愈觉有味。愈学愈恐不及。于是有李周翰年高之叹。慕吕进伯晚好之风。惜往日之虚过。而恨不蚤从事于此学也。晚栖之意。其在斯欤。其在斯欤。然翁之为学之日。今已久矣。其咀嚼真腴。必有自得于心者。而两皆衰废。无缘合席对讨。朝暮相思。如云端人卷中人。此晚契之所以深慨也。遂书此以寄意。翁其肯莞尔否乎。书郑景晦答客说后
或有问今之所谓学校新学。举世奔趋。惟恐不及。其旨趣何如。余曰。夷狄之前茅。禽兽之先路。正路晦蚀而人心僻违。降华而用夷。背义而趋利。乐于从彼。所谓不善变之尤者也。曰当此时局。有志于时务者。亦不可不为。又曰今之所谓儒者。只是空言。有甚实用。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8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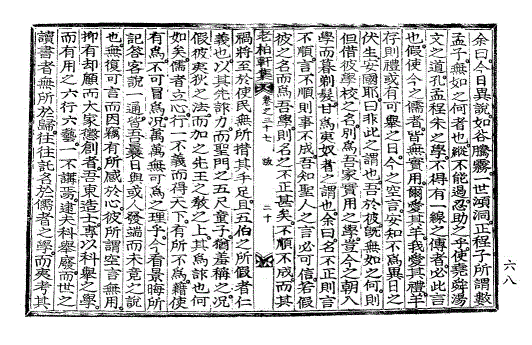 余曰。今日异说。如谷腾雾。一世澒洞。正程子所谓数孟子。无如之何者也。纵不能遏。忍助之乎。使尧舜汤文之道。孔孟程朱之学。不得有一线之传者。必此言也。假使今之儒者。皆无实用。尔爱其羊。我爱其礼。羊存则礼或有可举之日。今之空言。安知不为异日之伏生,安国耶。曰非此之谓也。吾于彼。既无如之何。则但借彼学校之名。别为吾家实用之学。岂今之朝入学而暮剃发。甘为夷奴者之谓也。余曰。名不正则言不顺。言不顺则事不成。吾知圣人之言必可信。若假彼之名而为吾学。则名之不正甚矣。不顺不成。而其祸将至于使民无所措其手足。且五伯之所假者仁义也。以其先诈力。而圣门之五尺童子。犹羞称之。况假彼夷狄之法。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。其为诈也何如矣。儒者立心。行一不义而得天下。有所不为。藉使有为。不可冒为。况万万无可为之理乎。今看景晦所记答客说一通。皆吾曩日与或人发端而未竟之说也。无复可言而因窃有所感于心。彼所谓空言无用。抑有却顾而大家惩创者。吾东造士。专以科举之学。而有用之六行六艺。一不讲焉。逮夫科举废。而世之读书者无所于归。往往托名于儒者之学。而夷考其
余曰。今日异说。如谷腾雾。一世澒洞。正程子所谓数孟子。无如之何者也。纵不能遏。忍助之乎。使尧舜汤文之道。孔孟程朱之学。不得有一线之传者。必此言也。假使今之儒者。皆无实用。尔爱其羊。我爱其礼。羊存则礼或有可举之日。今之空言。安知不为异日之伏生,安国耶。曰非此之谓也。吾于彼。既无如之何。则但借彼学校之名。别为吾家实用之学。岂今之朝入学而暮剃发。甘为夷奴者之谓也。余曰。名不正则言不顺。言不顺则事不成。吾知圣人之言必可信。若假彼之名而为吾学。则名之不正甚矣。不顺不成。而其祸将至于使民无所措其手足。且五伯之所假者仁义也。以其先诈力。而圣门之五尺童子。犹羞称之。况假彼夷狄之法。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。其为诈也何如矣。儒者立心。行一不义而得天下。有所不为。藉使有为。不可冒为。况万万无可为之理乎。今看景晦所记答客说一通。皆吾曩日与或人发端而未竟之说也。无复可言而因窃有所感于心。彼所谓空言无用。抑有却顾而大家惩创者。吾东造士。专以科举之学。而有用之六行六艺。一不讲焉。逮夫科举废。而世之读书者无所于归。往往托名于儒者之学。而夷考其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9H 页
 立心制行。则只学他言语。做他貌样而已。即是楦麟耳。栀蜡耳。有甚实用。请略言之。圣人垂世立言。皆指示吾人当行之路。是以儒者之学。口读底便是身做底。说出底便是心存底。今之所谓学者。口圣而身愚。说舜而心蹠。圣人言古之学者为己。今之学者为人。乃其心之所存。全在为人一边。圣人言君子喻于义。小人喻于利。乃其行之所趋。专向私利一边。圣人言主忠信。乃侈然虚夸。圣人言毋自欺。乃苟然徇外。圣贤千言万语。口诵不错一字。而无一句真切服膺。是以三纲五常。不过为假面妆点之具。天人性命。不过为腾颊争竞之资。五伯之假借。犹为近实。而南朝之清谈。不是过也。儒乎儒乎。若是而谓儒。则果非所谓无用之空言耶。人之元气虚而客邪入。异教之乘时怀襄。亦无足怪者。孟子曰。君子反经而已。经正斯无邪忒。今吾辈之零星收拾。欲强此而艰彼者。盍亦反经矣乎。反经之道无他。以实心行实事。所读圣贤之言。段段句句。必欲心悟而身体之。独善兼善。随遇而行而已。苟或不然而徒斥时学之为夷狄禽兽。则安保其不为解胡之慷慨悲愤乎。可惧可惧。此吾辈之十分反顾。十分内省。不敢斯须忽者也。
立心制行。则只学他言语。做他貌样而已。即是楦麟耳。栀蜡耳。有甚实用。请略言之。圣人垂世立言。皆指示吾人当行之路。是以儒者之学。口读底便是身做底。说出底便是心存底。今之所谓学者。口圣而身愚。说舜而心蹠。圣人言古之学者为己。今之学者为人。乃其心之所存。全在为人一边。圣人言君子喻于义。小人喻于利。乃其行之所趋。专向私利一边。圣人言主忠信。乃侈然虚夸。圣人言毋自欺。乃苟然徇外。圣贤千言万语。口诵不错一字。而无一句真切服膺。是以三纲五常。不过为假面妆点之具。天人性命。不过为腾颊争竞之资。五伯之假借。犹为近实。而南朝之清谈。不是过也。儒乎儒乎。若是而谓儒。则果非所谓无用之空言耶。人之元气虚而客邪入。异教之乘时怀襄。亦无足怪者。孟子曰。君子反经而已。经正斯无邪忒。今吾辈之零星收拾。欲强此而艰彼者。盍亦反经矣乎。反经之道无他。以实心行实事。所读圣贤之言。段段句句。必欲心悟而身体之。独善兼善。随遇而行而已。苟或不然而徒斥时学之为夷狄禽兽。则安保其不为解胡之慷慨悲愤乎。可惧可惧。此吾辈之十分反顾。十分内省。不敢斯须忽者也。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69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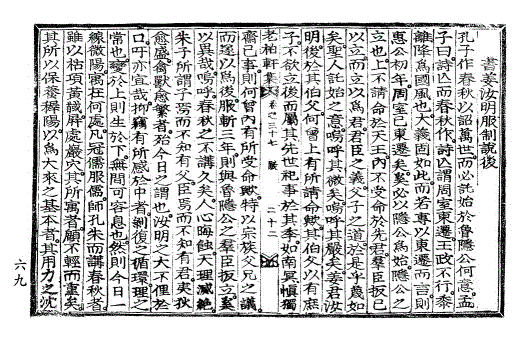 书姜汝明服制说后
书姜汝明服制说后孔子作春秋以诏万世。而必托始于鲁隐公何意。孟子曰。诗亡而春秋作。诗亡谓周室东迁。王政不行。黍离降为国风也。大义固如此。而若专以东迁而言。则惠公初年。周室已东迁矣。奚必以隐公为始。隐公之立也。上不请命于天王。内不受命于先君。群臣扳己以立。而立以为君。君臣之义。父子之道。于是乎蔑如矣。圣人托始之意。呜呼其微矣。呜呼其严矣。姜君汝明。后于其伯父。何曾上有所请命欤。其伯父以有庶子。不欲立后而属其先世祀事于其季。如南冥,慎独斋已事。则何曾内有所受命欤。特以宗族父兄之议。而遂以为后。服斩三年。则与鲁隐公之群臣扳立。奚以异哉。呜呼。春秋之不讲久矣。人心晦蚀。天理灭绝。朱子所谓子焉而不知有父。臣焉而不知有君。夷狄愈盛。禽兽愈繁者。殆今日之谓也。汝明之大不俚于口。吁亦宜哉。抑窃有所感于中者。剥复之循环。理之常也。变于上则生于下。无间可容息也。然则今日一线微阳。寓在何处。凡冠儒服儒。师孔朱而讲春秋者。虽以枯项黄馘。屏处岩穴。其所寓者。顾不轻而重矣。其所以保养稚阳。以为大来之基本者。其用力之沈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70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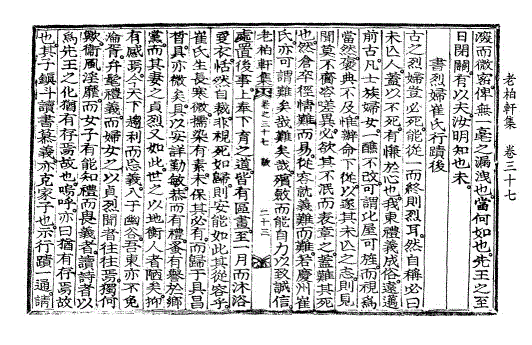 深而微密。俾无一毫之漏泄也。当何如也。先王之至日闭关。有以夫。汝明知也未。
深而微密。俾无一毫之漏泄也。当何如也。先王之至日闭关。有以夫。汝明知也未。书烈妇崔氏行迹后
古之烈妇岂必死。能从一而终则烈耳。然自称必曰未亡人。盖以不死。有慊于心也。我东礼义成俗。远迈前古。凡士族妇女。一醮不改。可谓比屋可旌。而视为当然。褒典不及。惟办命下从。以遂其未亡之志。则见闻莫不赍咨嗟异。必欲其不泯而表章之。盖难其死也。然仓卒径情难而易。从容就义难而难。若庆州崔氏。亦可谓难矣哉难矣哉。殡敛而能自力以致诚信。处置后事。上奉下育之道。皆有区画。至一月而沐浴更衣。恬然自裁。非视死如归。则安能如此其从容乎。崔氏生长寒微。擩染有素。未保其必有。而归于具昌晰。具亦微矣。具以安详勤敏。恭而有礼。蚤有誉于乡党。而其妻之贞烈又如此。世之以地衡人者陋矣。抑有感焉。今天下趋利而忘义。入于幽谷。吾东亦不免沦胥。弁髦礼义。而妇女之以贞烈闻者往往焉。独何欤。卫风淫靡。而女子有能知礼而畏义者。读诗者以为先王之化犹有存焉故也。呜呼。亦曰犹有存焉故也。其子镇斗读书慕义。亦克家子也。示行迹一通。请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70L 页
 下一言。遂叹息而书之。
下一言。遂叹息而书之。书讷窝师友书帖后
余于绫阳尹斯文讷窝处士。窃有三慨焉。讷窝余获知于皓首。其自修之笃。闻见之博。使余望洋焉。因仍蓬麻则庶有扶直之效。而桑榆景短。志气不可以复强矣。敢望收效。此一慨也。入其室。架上储书千卷。比之邺侯之签,公择之房。未知多寡之如何。而亦可谓富有矣。余素贫。敝簏无贮。一生寡陋。非直聪明之不及也。亦半坐是。使得与讷友青少相识。则讷友非厚蠹鱼而薄士友者。庶随其后。掇拾馀香。少充其枵然之腹而未及焉。此一慨也。及考其师友书帖。域中儒门长德。以至一乡善士。无不载焉。何修而交游之富。至于此也。窃欲藉讷友绍介。周流四方。承警欬受箴砭。以为晚暮寡过之地。而柰衰相此甚。非抖擞之所可壮何哉。此又一慨也。噫。虽然炳烛之思。犹耿耿未已。讷友何以相之。又念洛阳渊海。虽非鱼目之所可混球琳琅玕。若彼其积叠。而独以固陋。为子云书中西蜀富人。亦甚可哀。遂书此卷尾。以致私慨云。
书林景三处变录后
记昔先师书金丰五家乘序后曰。不愧于人。不畏于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71H 页
 天。吾知丰五必有后矣。景三此录。大略与丰五序意同。耻崇韬而慕狄青。亦可谓不负所学。吾亦知景三之必有后也。丰五序乘之时。人心之陷溺。犹不至于今日。今则荡然无复愧耻。无复忌惮。景三此录。表章于世。则或可为淑人心之一端。而我非其人。又耄昏。与毛生绝交久矣。柰景三何。遂书此以归之。
天。吾知丰五必有后矣。景三此录。大略与丰五序意同。耻崇韬而慕狄青。亦可谓不负所学。吾亦知景三之必有后也。丰五序乘之时。人心之陷溺。犹不至于今日。今则荡然无复愧耻。无复忌惮。景三此录。表章于世。则或可为淑人心之一端。而我非其人。又耄昏。与毛生绝交久矣。柰景三何。遂书此以归之。书柳公懋矢志说后
古之学者。口读底便是身做底。说出底便是心存底。今之学者。口身心三者不相符。学而为圣为凡。其机在于此。苟知其机之在此。则此心常如过危木桥。自不敢须臾忽也。须日檃栝所言所行所存。勿使有掣肘矛盾而诚心力行。如刘元城之为。则亦可以心口相应而超凡希圣矣。此一幅纸。在君可为千斤担负矣。吾故书此纸尾。以为一臂之助。
晚云马公遗集跋
穷经将以致用也。世之学者。朝暮于经传。而于当世之务。盖昧昧也。昔人所讥束之高阁以待天下太平者。未必非自召也。今晚云马公早从儒贤之门。其于专经之业。闻之宜稔矣。而其所上封事及庙堂方伯之书。皆切切于时务之急。而又皆本之正心修身。若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71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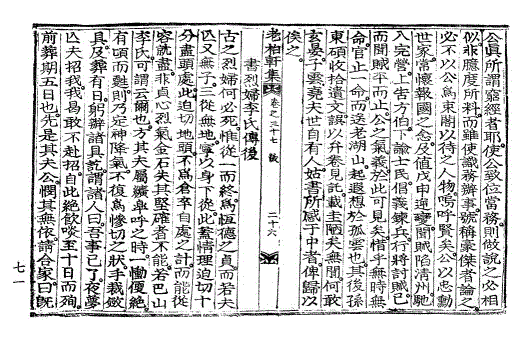 公真所谓穷经者耶。使公致位当务。则做说之必相似。非臆度所料。而虽使识务办事。号称豪杰者论之。必不以公为束阁以待之人物。呜呼贤矣。公以忠勋世家。常怀报国之念。及值戊申逆变。闻贼陷清州。驰入完营。上告方伯。下谕士民。倡义鍊兵。行将讨贼。已而闻贼平而止。公之气义。于此可见矣。惜乎无时无命。官止一命。而送老湖山。起遐想于孤云也。其后孙东硕收拾遗文。误以弁卷见托。载圭陋矣无闻。何敢玄晏。子云,尧夫世自有人。姑书所感于中者。俾归以俟之。
公真所谓穷经者耶。使公致位当务。则做说之必相似。非臆度所料。而虽使识务办事。号称豪杰者论之。必不以公为束阁以待之人物。呜呼贤矣。公以忠勋世家。常怀报国之念。及值戊申逆变。闻贼陷清州。驰入完营。上告方伯。下谕士民。倡义鍊兵。行将讨贼。已而闻贼平而止。公之气义。于此可见矣。惜乎无时无命。官止一命。而送老湖山。起遐想于孤云也。其后孙东硕收拾遗文。误以弁卷见托。载圭陋矣无闻。何敢玄晏。子云,尧夫世自有人。姑书所感于中者。俾归以俟之。书烈妇李氏传后
古之烈妇何必死。惟从一而终。为恒德之贞。而若夫亡又无子。三从无地。宁以身下从。此盖情理迫切十分尽头处。此迫切地头。不为仓卒自处之计。而能从容就尽。非贞心烈气金石失其坚确者不能。若巴山李氏。可谓云尔也。方其夫属纩皋呼之时。一恸便绝。有顷而苏。则乃定神降气。不复为惨切之状。手裁敛具。及葬有日。躬办诸具讫。谓诸人曰。吾事已了。夜梦亡夫招我。我曷敢不赴招。自此绝饮啖至十日而殉。前葬期五日也。先是其夫公。悯其无依。请合家。曰既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72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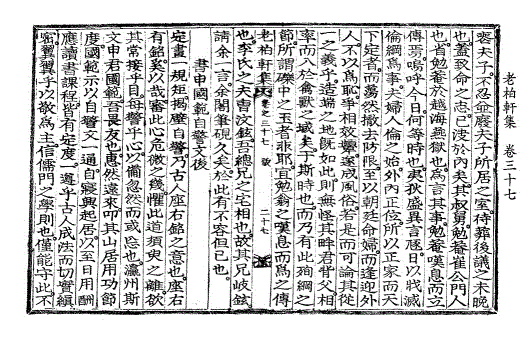 丧夫子。不忍并废夫子所居之室。待葬后议之未晚也。盖致命之志。已决于内矣。其叔舅。勉庵崔公门人也。省勉庵于越海燕狱也。为言其事。勉庵叹息而立传焉。呜呼今日。何等时也。夷狄盛异言豗。日以戕灭伦纲为事。夫妇人伦之始。外内正位。所以正家而天下定者。而荡然撤去防限。至以朝廷命妇。而逢迎外人。不以为耻。争相效颦。遂成风俗。若是而可论其从一之义乎。造端之地既如此。则无怪其畔君背父。相率而入于禽兽之域矣。于斯时也。而乃有此殉纲之节。所谓砾中之玉者非耶。宜勉翁之叹息而为之传也。李氏之夫曹汶铉。吾缌兄之宅相也。故其兄岐铉。请余一言。余阁笔砚久矣。于此有不容但已也。
丧夫子。不忍并废夫子所居之室。待葬后议之未晚也。盖致命之志。已决于内矣。其叔舅。勉庵崔公门人也。省勉庵于越海燕狱也。为言其事。勉庵叹息而立传焉。呜呼今日。何等时也。夷狄盛异言豗。日以戕灭伦纲为事。夫妇人伦之始。外内正位。所以正家而天下定者。而荡然撤去防限。至以朝廷命妇。而逢迎外人。不以为耻。争相效颦。遂成风俗。若是而可论其从一之义乎。造端之地既如此。则无怪其畔君背父。相率而入于禽兽之域矣。于斯时也。而乃有此殉纲之节。所谓砾中之玉者非耶。宜勉翁之叹息而为之传也。李氏之夫曹汶铉。吾缌兄之宅相也。故其兄岐铉。请余一言。余阁笔砚久矣。于此有不容但已也。书申国范自警文后
定画一规矩。揭壁自警。乃古人座右铭之意也。座右有铭。奚以哉。审此心危微之几。惧此道须臾之离。欲其常接乎目。每警乎心。以备忽然而或忘也。瀛州斯文申君国范。吾畏友也。惠然远来。叩其山居用功节度。国范示以自警文一通。自寝兴起居。以至日用酬应读书课程。皆有定度。一遵乎古人成法而切实缜密。翼翼乎以敬为主。信儒门之学则也。仅能守此。不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72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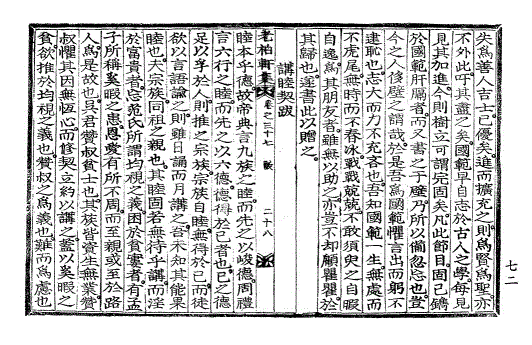 失为善人吉士。已优矣。进而扩充之。则为贤为圣。亦不外此。吁其尽之矣。国范早自志于古人之学。每见见其加进。今则树立可谓完固矣。凡此节目。固已镌于国范肝膈者。而又书之于壁。乃所以备忽忘也。岂今之人侈壁之谓哉。于是吾为国范惧言出而躬不逮耻也。志大而力不充吝也。吾知国范一生。无处而不虎尾。无时而不春冰。战战兢兢。不敢须臾之自暇自逸。为其朋友者。虽无以助之。亦岂不却顾瞿瞿。于其归也。遂书此以赠之。
失为善人吉士。已优矣。进而扩充之。则为贤为圣。亦不外此。吁其尽之矣。国范早自志于古人之学。每见见其加进。今则树立可谓完固矣。凡此节目。固已镌于国范肝膈者。而又书之于壁。乃所以备忽忘也。岂今之人侈壁之谓哉。于是吾为国范惧言出而躬不逮耻也。志大而力不充吝也。吾知国范一生。无处而不虎尾。无时而不春冰。战战兢兢。不敢须臾之自暇自逸。为其朋友者。虽无以助之。亦岂不却顾瞿瞿。于其归也。遂书此以赠之。讲睦契跋
睦本乎德。故帝典言九族之睦。而先之以峻德。周礼言六行之睦。而先之以六德。德得于己者也。己之德足以孚于人。则推之宗族。宗族自睦。无得于己。而徒欲以言语谕之。则虽日诵而月讲之。吾未知其能果睦也。夫宗族。同祖之亲也。其睦固若无待乎讲。而淫于富贵者。忘范氏所谓均视之义。困于贫寠者。有孟子所称奚暇之患。恩爱有所不周。而至亲或至于路人。为是故也。吴君赞叔贫士也。其族皆资生无业。赞叔惧其因无恒心。而修契立约以讲之。盖以奚暇之贫。欲推于均视之义也。赞叔之为义也。难而为虑也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73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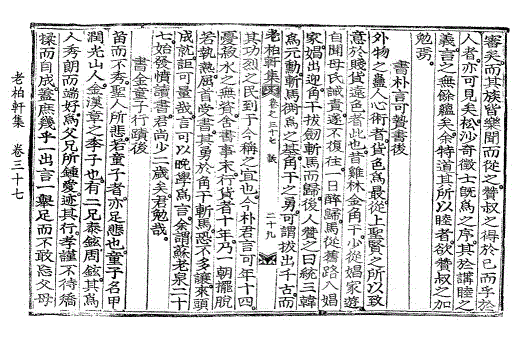 审矣。而其族皆乐闻而从之。赞叔之得于己而孚于人者。亦可见矣。松沙奇徵士既为之序。其于讲睦之义。言之无馀蕴矣。余特道其所以睦者。欲赞叔之加勉焉。
审矣。而其族皆乐闻而从之。赞叔之得于己而孚于人者。亦可见矣。松沙奇徵士既为之序。其于讲睦之义。言之无馀蕴矣。余特道其所以睦者。欲赞叔之加勉焉。书朴言可贽书后
外物之蛊人心术者。货色为最。从上圣贤之所以致意于贱货远色者此也。昔鸡林金角干。少从娼家游。自闻母氏诫责。遂不复往。一日醉归。马从旧路入娼家。娼出迎。角干拔剑斩马而归。后人赞之曰统三韩为元勋。斩马巷为之基。角干之勇。可谓拔出千古。而其功烈之民到于今称之宜也。今朴君言可年十四。忧菽水之无资。舍书事末。行货者十年。乃一朝摆脱若执热。屈首受书。其勇于角干斩马。恐不多让。来头成就。讵可量哉。言可以晚学为言。余谓苏老泉二十七。始发愤读书。君尚少二岁矣。君勉哉。
书金童子行迹后
苗而不秀。圣人所悲。若童子者。亦足悲也。童子名甲润光山人。金汉章之季子也。有二兄泰铉,周铉。其为人秀朗而端好。为父兄所钟爱。迹其行。孝谨不待矫揉而自成。盖庶几乎一出言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73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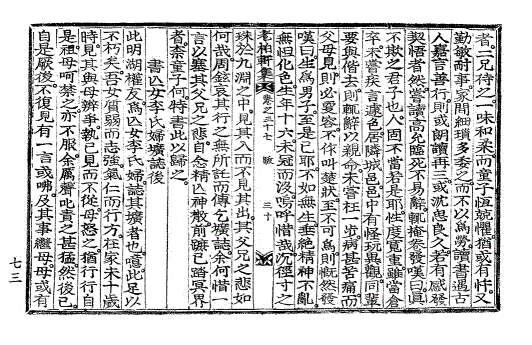 者。二兄待之。一味和柔。而童子恒兢惧。犹或有忤。又勤敏耐事。家间细琐多委之。而不以为劳。读书遇古人嘉言善行。则或朗读再三。或沈思良久。若有感发契悟者然。尝读高允临死不易辞。辄掩卷发叹曰。真不欺之君子也。人固不当若是耶。性度宽重。虽当仓卒。未尝疾言遽色。居邻城邑。邑中有怪玩异观。同辈要与偕去。则辄辞以亲命。未尝枉一步。病甚苦痛。而父母见。则必更容。不作叫楚状。至不可为。则慨然发叹曰。生为男子。至是已耶。不如无生。垂绝精神不乱。无怛化色。生年十六。未冠而没。呜呼惜哉。沉径寸之珠于九渊之中。见其入而不见其出。其父兄之悲如何哉。周铉哀其行之无所托而传乞圹志。余何惜一言以塞其父兄之悲。自念精亡神散。前蹠已踏冥界者。柰童子何。特书此以归之。
者。二兄待之。一味和柔。而童子恒兢惧。犹或有忤。又勤敏耐事。家间细琐多委之。而不以为劳。读书遇古人嘉言善行。则或朗读再三。或沈思良久。若有感发契悟者然。尝读高允临死不易辞。辄掩卷发叹曰。真不欺之君子也。人固不当若是耶。性度宽重。虽当仓卒。未尝疾言遽色。居邻城邑。邑中有怪玩异观。同辈要与偕去。则辄辞以亲命。未尝枉一步。病甚苦痛。而父母见。则必更容。不作叫楚状。至不可为。则慨然发叹曰。生为男子。至是已耶。不如无生。垂绝精神不乱。无怛化色。生年十六。未冠而没。呜呼惜哉。沉径寸之珠于九渊之中。见其入而不见其出。其父兄之悲如何哉。周铉哀其行之无所托而传乞圹志。余何惜一言以塞其父兄之悲。自念精亡神散。前蹠已踏冥界者。柰童子何。特书此以归之。书亡女李氏妇圹志后
此明湖权友。为亡女李氏妇。志其圹者也。噫。此足以不朽矣。吾女质弱而志强。气仁而行方。在家未十岁时。见其与母辨争。执己见而不从。母怒之。犹行行自是。祖母呵禁之。亦不服。余厉声叱责之甚猛。然后已。自是厥后。不复见有一言或咈。及其事继母。母或有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74H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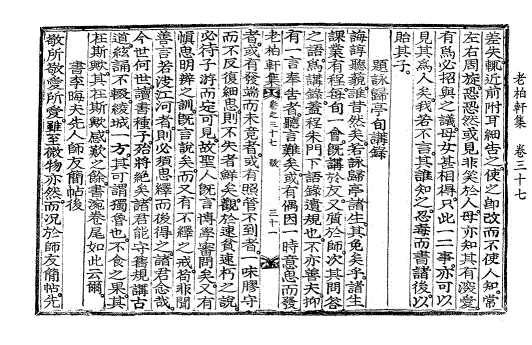 差失。辄近前附耳细告之。使之即改而不使人知。常左右周旋。恐恐然或见非笑于人。母亦知其有深爱。有为必招与之议。母女甚相得。只此一二事。亦可以见其为人矣。我若不言。其谁知之。忍毒而书诸后。以贻其子。
差失。辄近前附耳细告之。使之即改而不使人知。常左右周旋。恐恐然或见非笑于人。母亦知其有深爱。有为必招与之议。母女甚相得。只此一二事。亦可以见其为人矣。我若不言。其谁知之。忍毒而书诸后。以贻其子。题咏归亭旬讲录
诲谆听藐。谁昔然矣。若咏归亭诸生。其免矣乎。诸生课业有程。每旬一会。既讲于友。又质于师。次其问答之语。为讲录。盖程朱门下语录遗规也。不亦善夫。抑有一言奉告者。听言难矣。或有偶因一时意思而发者。或有发端而未竟者。或有照管不到者。一味胶守而不反复细思。则不失者鲜矣。观于速贫速朽之说。必待子游而定可见。故圣人既言博学审问矣。又有慎思明辨之训。既言说矣。而又有不绎之戒。苟非闻善言若决江河者。则必须思绎而后得之。诸君念哉。今世何世。读书种子。殆将绝矣。诸君能守旧规讲古道。弦诵不辍。绫城一方。其可谓独鲁也。不食之果。其在斯欤。其在斯欤。感叹之馀。书涴卷尾如此云尔。
书李晦夫先人师友简帖后
敬所敬爱所爱。虽至微物亦然。而况于师友𥳑帖。先
老柏轩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第 74L 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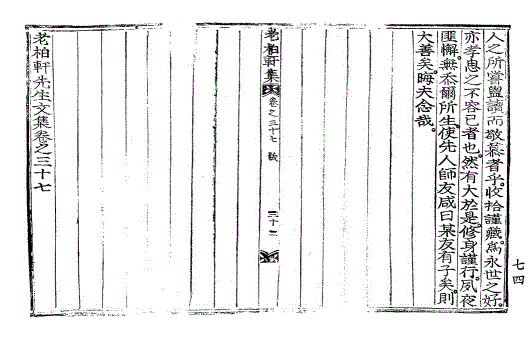 人之所尝盥读而敬慕者乎。收拾谨藏。为永世之好。亦孝思之不容已者也。然有大于是。修身谨行。夙夜匪懈。无忝尔所生。使先人师友咸曰某友有子矣。则大善矣。晦夫念哉。
人之所尝盥读而敬慕者乎。收拾谨藏。为永世之好。亦孝思之不容已者也。然有大于是。修身谨行。夙夜匪懈。无忝尔所生。使先人师友咸曰某友有子矣。则大善矣。晦夫念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