诗文库
楚人谣 先秦 · 无名氏
《史记》曰:楚怀王为张仪所欺。客死于秦。至王负刍遂为秦所灭。百姓哀之。为之语曰:
楚虽三户。亡秦必楚(○《史记》项羽本纪。风俗通王霸篇。《诗纪前集》三。)。
为秦破从连横献书楚王 战国魏国 · 张仪
出处: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一
秦地半天下,兵敌四国,被山带河,四塞以为固。虎贲之士百馀万,车千乘,骑万匹,粟如丘山。法令既明,士卒安难乐死,主严以明,将知以武,虽无出兵甲,席卷常山之险,折天下之脊,天下后服者先亡。且夫为从者,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。夫虎之与羊,不格明矣。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,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。凡天下强国,非秦而楚,非楚而秦,两国敌侔交争,其势不两立。而大王不与秦,秦下甲据宜阳,韩之上地不通;下河东,取成皋,韩必入臣于秦。韩入臣,魏则从风而动,秦攻楚之西,韩、魏攻其北,社稷岂得无危哉?且夫约从者,聚群弱而攻至强也。夫以弱攻强,不料敌而轻战,国贫而骤举兵,此危亡之术也。臣闻之,兵不如者,勿与挑战;粟不如者,勿与持久。夫从人者,饰辩虚辞,高主之节行,言其利而不言其害,卒有楚祸(《史记》作秦祸。)无及为已,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。秦西有巴蜀,方船《史记》作大船积粟,起于汶山,循江而下,至郢三千馀里。舫船载卒,一舫载五十人,与三月之粮,下水而浮,一日行三百馀里,里数虽多,不费马汗之劳,不至十日而拒扡关。扡关惊,则从竟陵已东,尽城守矣。黔中、巫郡,非王之有已。秦举甲出之武关,南面而攻,则北地绝。秦兵之攻楚也,危难在三月之内,而楚恃诸侯之救,在半岁之外,此其势不相及也。夫恃弱国之救,而忘强秦之祸,此臣之所以为大王之患也。且大王尝与吴人五战,三胜而亡之,陈卒尽矣;有偏守新城,而居民苦矣。臣闻之,攻大者易危,而民弊者怨于上。夫守易危之功,而逆强秦之心,臣窃为大王危之。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于函谷关十五年以攻诸侯者,阴谋有吞天下之心也。楚尝与秦构难,战于汉中,楚人不胜,通侯执圭死者七十馀人,遂亡汉中。楚王大怒,兴师袭秦,战于蓝田,又却,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。夫秦、楚相弊,而韩、魏以全制其后,计无过(《史记》作危)于此者矣。是故愿大王熟计之也。秦下兵攻卫阳晋,必开扃天下之匈。大王悉起兵以攻宋,不至数月而宋可举。举宋而东指,则泗上十二诸侯,尽王之有已。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,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,即阴与燕王谋破齐,共分共地,乃佯有罪,出走入齐,齐王因受而相之,居二年而觉,齐王大怒,车裂苏秦于市。夫以诈伪反覆之苏秦,而欲经营天下,混一诸侯,其不可成也,亦明矣。今秦之与楚也,接境壤界,固形亲之国也。大王诚能听臣,臣请秦太子入质于楚,楚太子入质于秦,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,效万家之都以为汤沐之邑,长为昆弟之国,终身无相攻击,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。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之从车,下风须以决事(《战国策》十四,又《史记。张仪传》,少未廿一字。)。
献书韩王 战国魏国 · 张仪
出处: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一
韩地险恶山居,五谷所生,非麦而豆;民之所食,大抵豆饭藿羹。一岁不收,民不餍糟糠。地方不满九百里,无二岁之所食。料大王之卒,悉之不过三十万,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。为除守徼亭鄣塞,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。秦带甲百馀万,车千乘,骑万匹,虎挚之士,跿跔科头,贯颐奋戟者,至不可胜计也。秦马之良,戎兵之众,探前趹后,蹄间三寻者,不可称数也。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,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,左挈人头,右挟生虏。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,犹孟贲之与怯夫也;以重力相压,犹乌获之与婴儿也。夫战孟贲、乌获之士,以攻不服之弱国,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,集于鸟卵之上,必无幸矣。诸侯(《史记》作「夫群臣诸侯。」)不料兵之弱,食之寡,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,比周以相饰也。皆言曰:「听吾计,则可以强,霸天下」夫不顾社稷之长利,而听须臾之说,诖误人主者,无过于此者矣。大王不事秦,秦下甲据宜阳,断绝韩之上地,东取成皋、宜阳(《史记》作荣阳,)则鸿台之宫,桑林之菀,非王之有已。夫塞成皋,绝上地,则王之国分矣。先事秦则安矣,不事秦则危矣。夫造祸而求福,计浅而怨深,逆秦而顺楚,虽欲无亡,不可得也。故为大王计,莫如事秦,秦之所欲,莫如弱楚,而能弱楚者,莫如韩。非以韩能强于楚也,其地势然也。今王西面而事秦,以攻楚为敝邑,秦王必喜。夫攻楚而私其地,转祸而说秦,计无便于此者也。是故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,御史须以决事(《战国策》二十六,又《史记。张仪传》少未十七字。)。
为文檄告楚相 战国魏国 · 张仪
出处: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一
始吾从若饮,我不盗而璧,若笞我。若善守汝国,我顾且盗而城(《史记。张仪传》:尝从楚相饮,楚相亡璧,门下意张仪,共执仪,掠笞数百,不服。仪既相秦,为文檄告楚相。)。
遗书责苏秦张仪 其一 战国齐国 · 鬼谷先生
出处:全上古三代文卷八
若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?仆御折其权,波浪荡其根,上无径尺之阴,身被数千之痕,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?所居然也!子不见嵩、岱之松柏,华霍之檀桐乎?上枝干于青云,下根通于三泉,千秋万岁,不受斧斤之患,此木岂与天地有骨肉哉?盖所居然也(《艺文类聚》三十六引袁淑《真隐传》,又见《御览》五百十)。
遗书责苏秦张仪 其二 战国齐国 · 鬼谷先生
出处:全上古三代文卷八
二君足下,功名赫赫,但春到秋,不得久茂。日既将尽,时既将老,君不见河边之树乎?仆驭折其枝,波浪激其根,此木非天下人有仇怨,所居者然也。子不见嵩、岱松柏,华、霍之树?上叶陵青云,下根通三泉,上有玄狐黑猿,下有豹隐龙潜,千秋万岁,不逢斧斤之患,此木非与天下人有骨血,盖所居然也。今二子好云路之荣,慕长久之功,轻乔松之永延,贵一夕之浮爵,痛焉悲夫二君,痛焉悲夫二君(杜光庭《录异记》。案此校《真隐传》互有删节,而首尾多十馀语,故并录之。)。
离骚 战国楚国 · 屈原
屈原名平,与楚同姓,仕于怀王,为三闾大夫。三闾之职,掌王族三姓,曰昭、屈、景。屈原序其谱属,率其贤良,以厉国士。入则与王图议政事,决定嫌疑;出则监察群下,应对诸侯。谋行职修,王甚珍之。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,妒害其能,共谮毁之,王疏屈原。屈原被谗,忧心烦乱,不知所诉,乃作离骚。(班孟坚曰:「离,犹遭也。」颜师古云:「扰动曰骚。」)上述唐、虞、三后之制,下序桀、纣、羿、浇之败,冀君觉悟,反于正道而还己也。是时,秦使张仪谲诈怀王,令绝齐交,又诱与俱会武关。原谏怀王勿行。不听而往,遂为所胁,与之俱归,拘留不遣,卒客死于秦。而襄王立,复用谗言,迁屈原于江南。屈原复作九歌、天问、九章、远游、卜居、渔父等篇,冀伸己志,以悟君心,而终不见省。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,遂赴汨罗之渊,自沈而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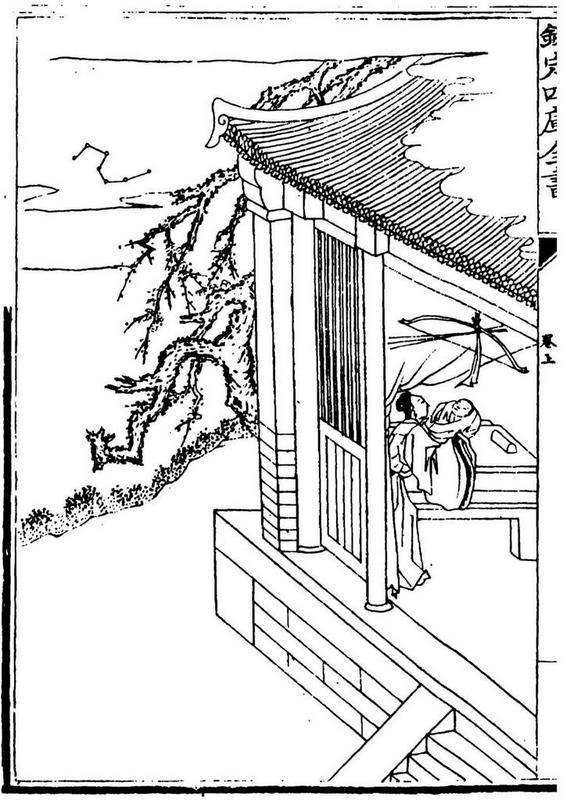
摄提贞于孟陬兮,惟庚寅吾以降。

名余曰正则兮,字余曰灵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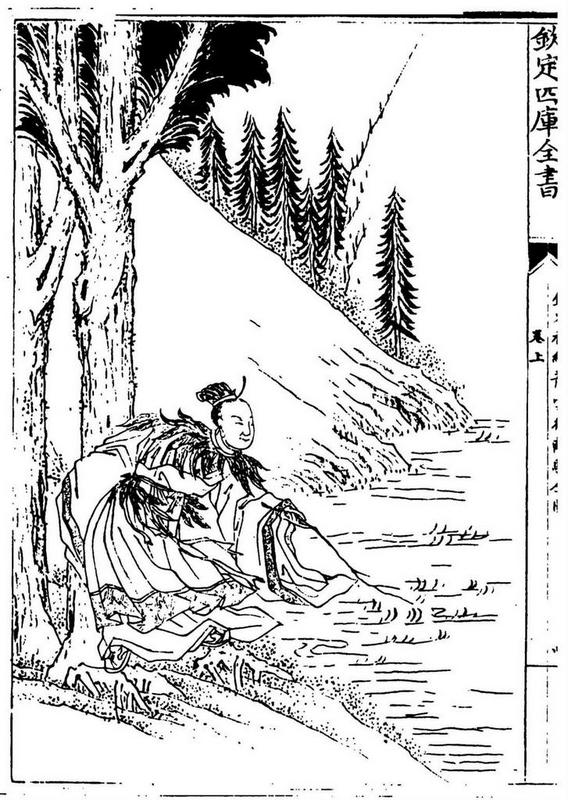
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。
汩余若将不及兮,恐年岁之不吾与。
朝搴阰之木兰兮,夕揽洲之宿莽。
日月忽其不淹兮,春与秋其代序。
惟草木之零落兮,恐美人之迟暮。
不抚壮而弃秽兮,何不改乎此度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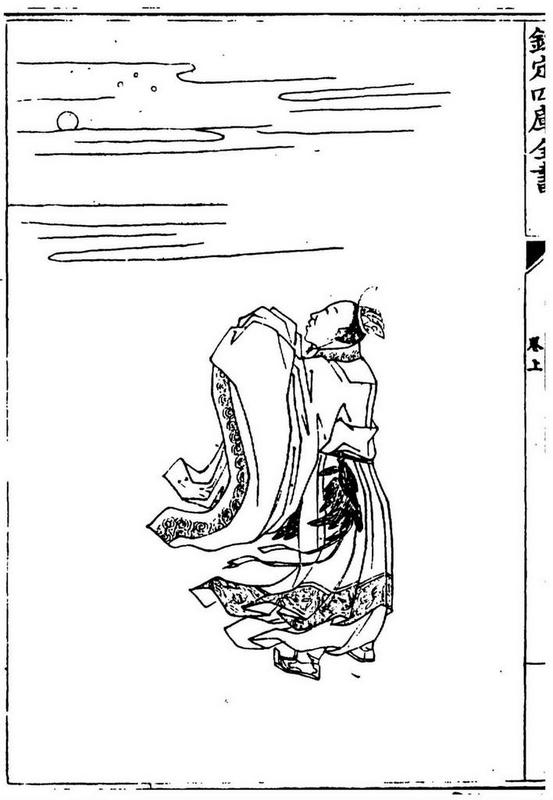
杂申椒与菌桂兮,岂维纫夫蕙茝?
彼尧舜之耿介兮,既遵道而得路。
何桀纣之猖披兮,夫唯捷径以窘步。
惟夫党人之偷乐兮,路幽昧以险隘。
岂余身之惮殃兮,恐皇舆之败绩。
忽奔走以先后兮,及前王之踵武。
荃不察余之中情兮,反信谗而齌怒。
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,忍而不能舍也。
指九天以为正兮,夫唯灵脩之故也。
曰黄昏以为期兮,羌中道而改路。
初既与余成言兮,后悔遁而有他。
余既不难夫离别兮,伤灵脩之数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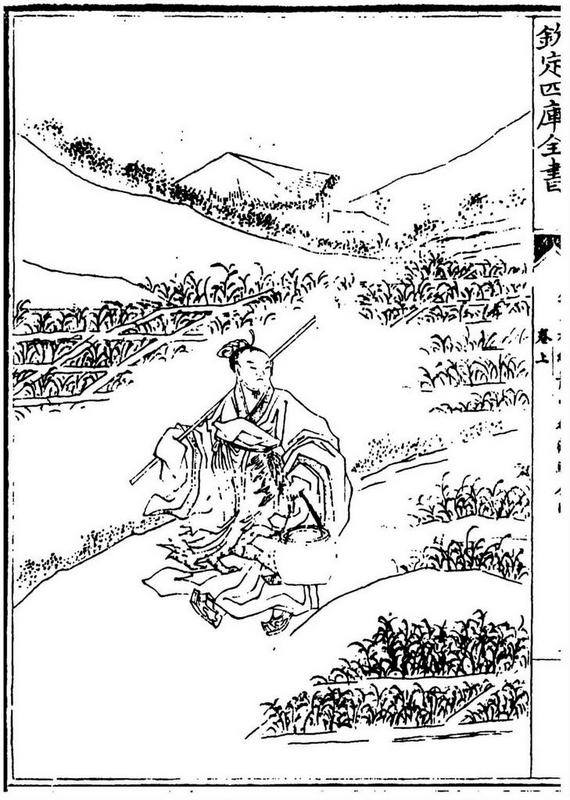
畦留夷与揭车兮,杂杜衡与芳芷。
冀枝叶之峻茂兮,愿俟时乎吾将刈。
虽萎绝其亦何伤兮,哀众芳之芜秽。
众皆竞进以贪婪兮,凭不厌乎求索。
羌内恕己以量人兮,各兴心而嫉妒。
忽驰骛以追逐兮,非余心之所急。
老冉冉其将至兮,恐脩名之不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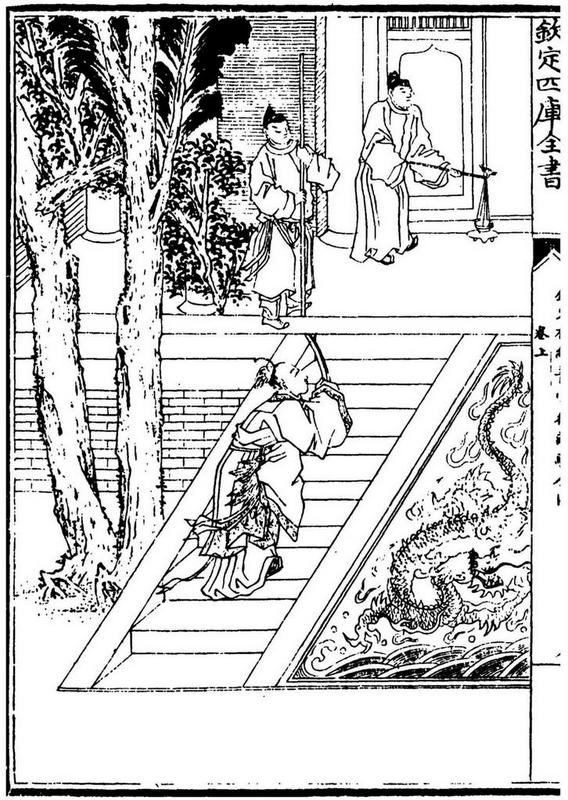
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,长顑颔亦何伤?
揽木根以结茝兮,贯薜荔之落蕊。
矫菌桂以纫蕙兮,索胡绳之纚纚。
謇吾法夫前脩兮,非世俗之所服。
虽不周于今之人兮,愿依彭咸之遗则。
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。
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,謇朝谇而夕替。
既替余以蕙纕兮,又申之以揽茝。
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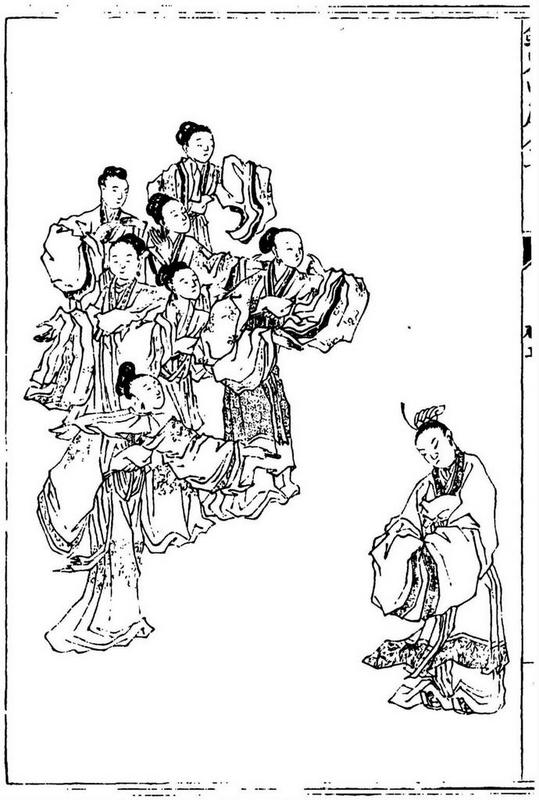
众女嫉余之蛾眉兮,谣诼谓余以善淫。
固时俗之工巧兮,偭规矩而改错。
背绳墨以追曲兮,竞周容以为度。
忳郁邑余侘傺兮,吾独穷困乎此时也。
宁溘死以流亡兮,余不忍为此态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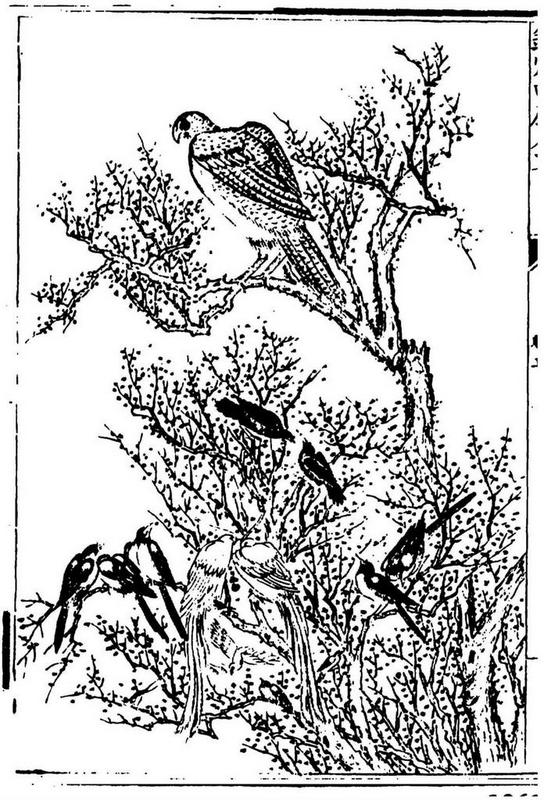
何方圜之能周兮,夫孰异道而相安。

伏清白以死直兮,固前圣之所厚。
悔相道之不察兮,延伫乎吾将反。
回朕车以复路兮,及行迷之未远。
步余马于兰皋兮,驰椒丘且焉止息。
进不入以离尤兮,退将复脩吾初服。

不吾知其亦已兮,苟余情其信芳。
高余冠之岌岌兮,长余佩之陆离。
芳与泽其杂糅兮,唯昭质其犹未亏。
忽反顾以游目兮,将往观乎四荒。
佩缤纷其繁饰兮,芳菲菲其弥章。
民生各有所乐兮,余独好脩以为常。
虽体解吾犹未变兮,岂余心之可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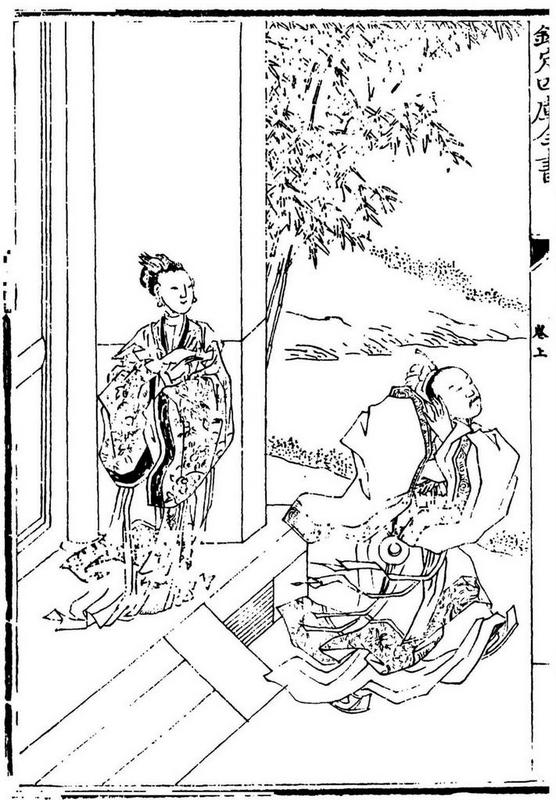
曰:「鲧婞直以亡身兮,终然夭乎羽之野。
汝何博謇而好脩兮,纷独有此姱节」。
薋菉葹以盈室兮,判独离而不服。
众不可户说兮,孰云察余之中情。
世并举而好朋兮,夫何茕独而不予听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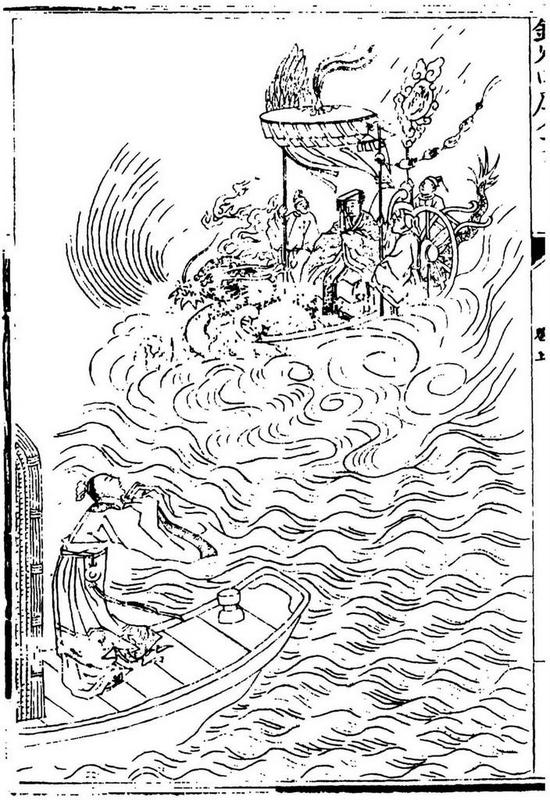
济沅湘以南征兮,就重华而陈词: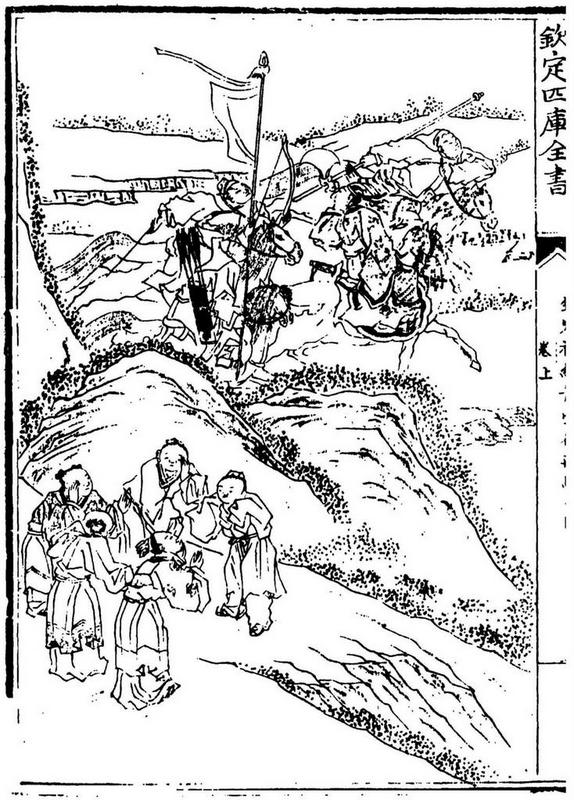 启《九辩》与《九歌》兮,夏康娱以自纵。
启《九辩》与《九歌》兮,夏康娱以自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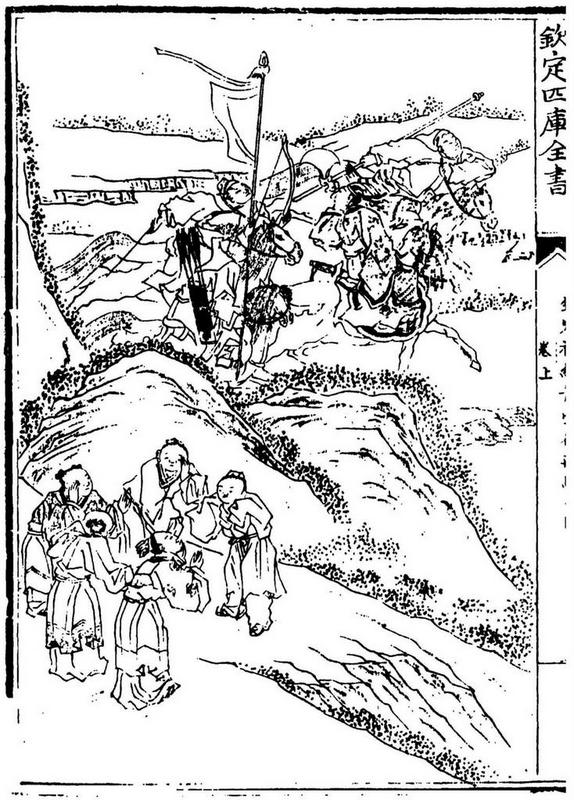
不顾难以图后兮,五子用失乎家巷。

固乱流其鲜终兮,浞又贪夫厥家。
浇身被服强圉兮,纵欲而不忍。
日康娱而自忘兮,厥首用夫颠陨。
夏桀之常违兮,乃遂焉而逢殃。
后辛之菹醢兮,殷宗用而不长。
汤禹俨而祗敬兮,周论道而莫差。
举贤而授能兮,循绳墨而不颇。
皇天无私阿兮,览民德焉错辅。
夫维圣哲以茂行兮,苟得用此下土。
瞻前而顾后兮,相观民之计极。
夫孰非义而可用兮,孰非善而可服。
阽余身而危死兮,览余初其犹未悔。
不量凿而正枘兮,固前脩以菹醢。
曾歔欷余郁邑兮,哀朕时之不当。
揽茹蕙以掩涕兮,沾余襟之浪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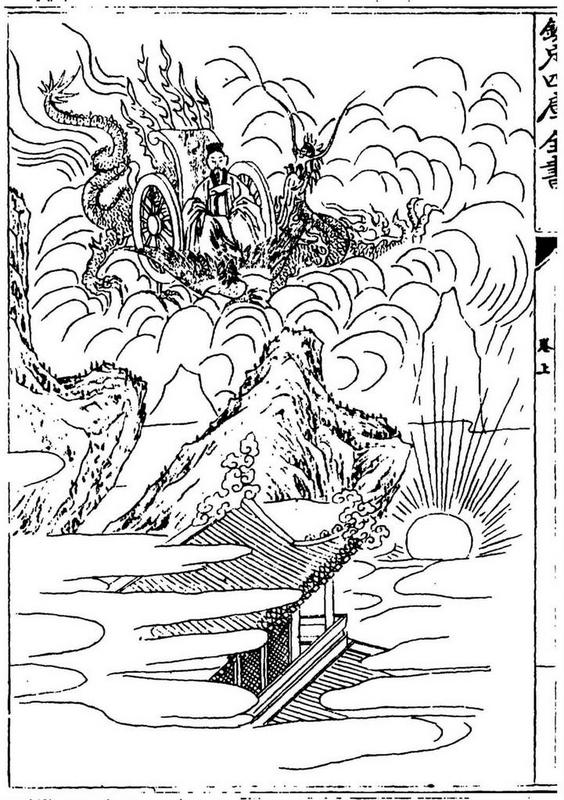
驷玉虬以乘鹥兮,溘埃风余上征。
朝发轫于苍梧兮,夕余至乎县圃;
欲少留此灵琐兮,日忽忽其将暮。
吾令羲和弭节兮,望崦嵫而勿迫。
路曼曼其脩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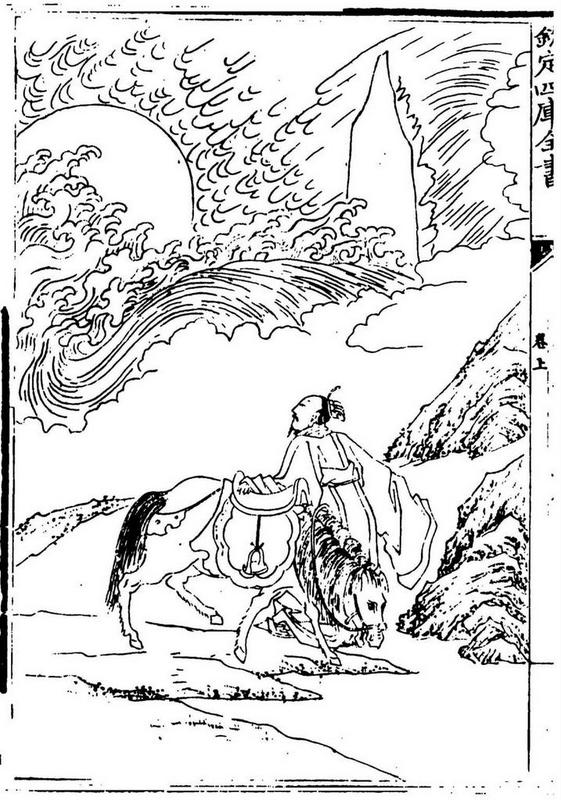
折若木以拂日兮,聊逍遥以相羊。

鸾皇为余先戒兮,雷师告余以未具。
吾令凤鸟飞腾兮,继之以日夜。
飘风屯其相离兮,帅云霓而来御。
纷总总其离合兮,斑陆离其上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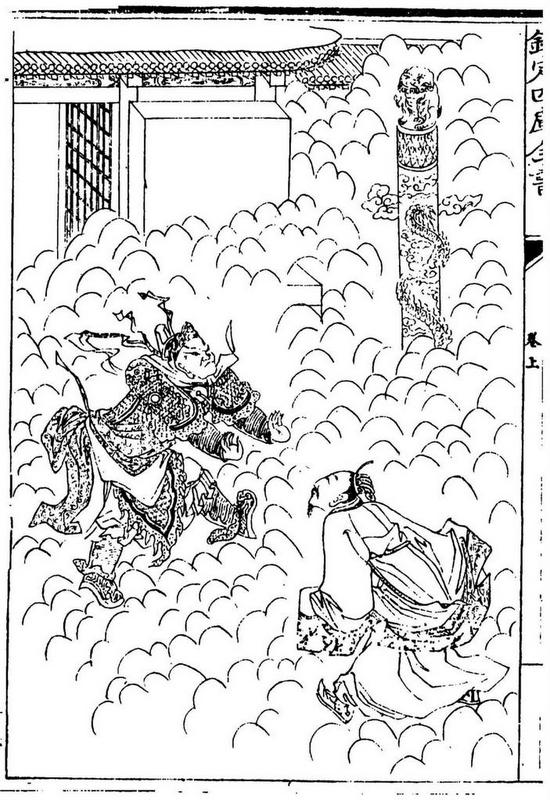
时暧暧其将罢兮,结幽兰而延伫。
世溷浊而不分兮,好蔽美而嫉妒。

忽反顾以流涕兮,哀高丘之无女。

及荣华之未落兮,相下女之可诒。

解佩纕以结言兮,吾令蹇脩以为理。
纷总总其离合兮,忽纬繣其难迁。
夕归次于穷石兮,朝濯发乎洧盘。
保厥美以骄傲兮,日康娱以淫游。
虽信美而无礼兮,来违弃而改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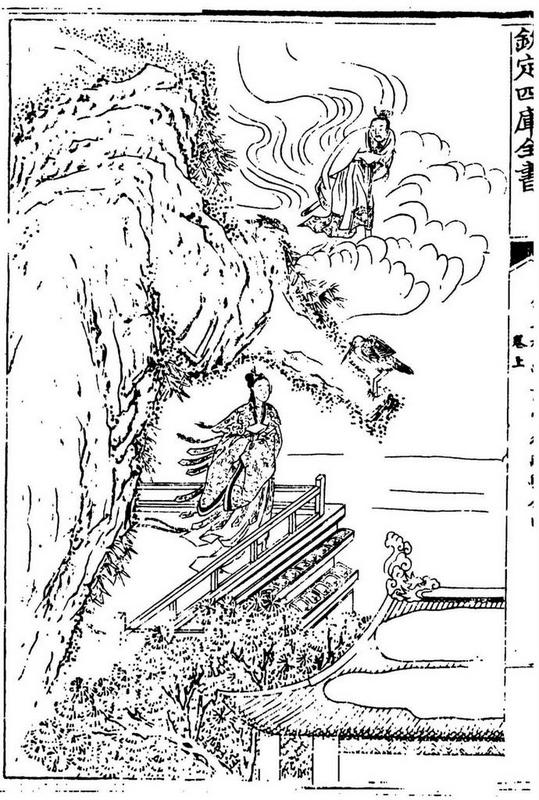
望瑶台之偃蹇兮,见有娀之佚女。
吾令鸩为媒兮,鸩告余以不好。
雄鸠之鸣逝兮,余犹恶其佻巧。
心犹豫而狐疑兮,欲自适而不可。
凤皇既受诒兮,恐高辛之先我。
欲远集而无所止兮,聊浮游以逍遥。
及少康之未家兮,留有虞之二姚。
理弱而媒拙兮,恐导言之不固。
世溷浊而嫉贤兮,好蔽美而称恶。
闺中既以邃远兮,哲王又不寤。
怀朕情而不发兮,余焉能忍与此终古。

曰:「两美其必合兮,孰信脩而慕之?
思九州之博大兮,岂唯是其有女」?
曰:「勉远逝而无狐疑兮,孰求美而释女?
何所独无芳草兮,尔何怀乎故宇」?
世幽昧以昡曜兮,孰云察余之善恶。
民好恶其不同兮,惟此党人其独异。
户服艾以盈要兮,谓幽兰其不可佩。
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,岂珵美之能当?
苏粪壤以充帏兮,谓申椒其不芳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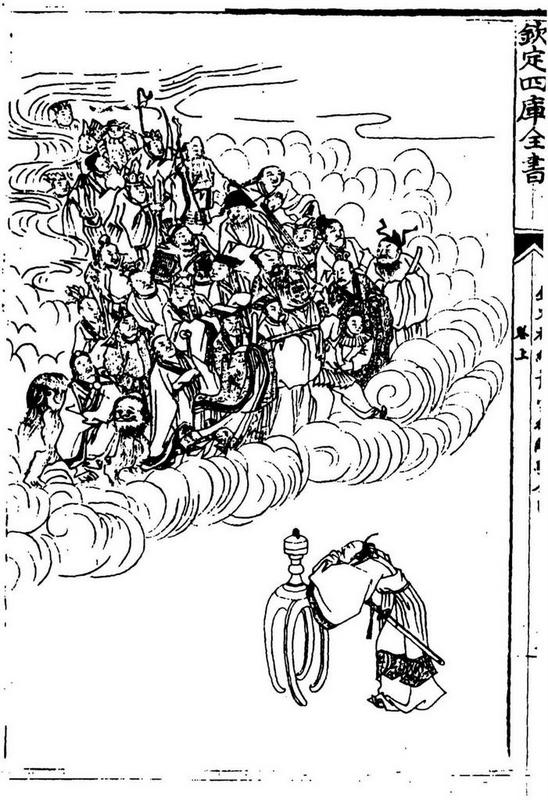
巫咸将夕降兮,怀椒糈而要之。
百神翳其备降兮,九疑缤其并迎。
皇剡剡其扬灵兮,告余以吉故。

汤禹严而求合兮,挚咎繇而能调。
苟中情其好脩兮,又何必用夫行媒。
说操筑于傅岩兮,武丁用而不疑。

宁戚之讴歌兮,齐桓闻以该辅。

恐鹈鴂之先鸣兮,使夫百草为之不芳」!
何琼佩之偃蹇兮,众薆然而蔽之。
惟此党人之不谅兮,恐嫉妒而折之。
时缤纷其变易兮,又何可以淹留。
兰芷变而不芳兮,荃蕙化而为茅。
何昔日之芳草兮,今直为此萧艾也。
岂其有他故兮,莫好脩之害也。
余以兰为可恃兮,羌无实而容长。
委厥美以从俗兮,苟得列乎众芳。
椒专佞以慢慆兮,榝又欲充夫佩帏。
既干进而务入兮,又何芳之能祗。
固时俗之流从兮,又孰能无变化。
览椒兰其若玆兮,又况揭车与江离。
惟玆佩之可贵兮,委厥美而历玆。
芳菲菲而难亏兮,芬至今犹未沬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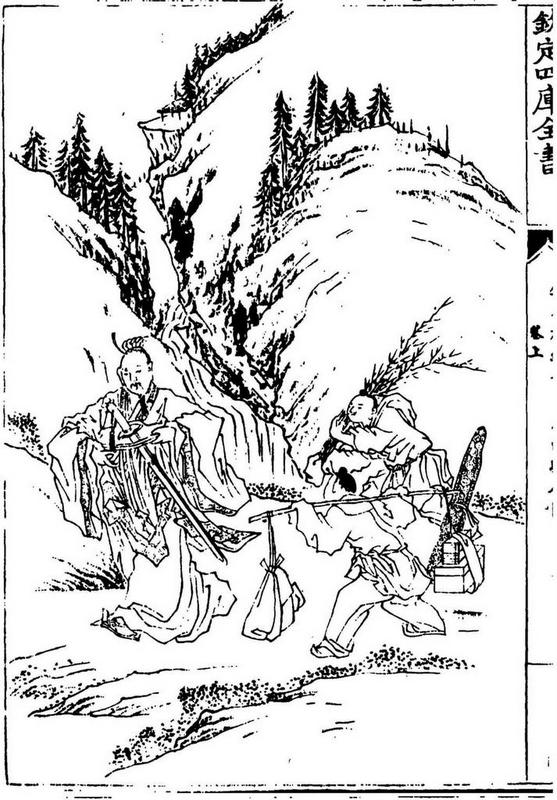
及余饰之方壮兮,周流观乎上下。
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,历吉日乎吾将行。
折琼枝以为羞兮,精琼爢以为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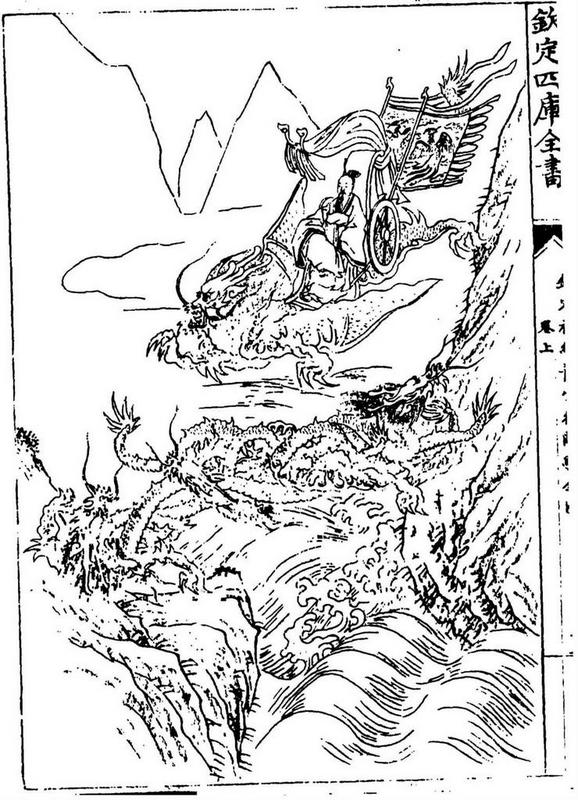
何离心之可同兮,吾将远逝以自疏。
邅吾道夫昆崙兮,路脩远以周流。
扬云霓之晻蔼兮,鸣玉鸾之啾啾。
朝发轫于天津兮,夕余至乎西极。
凤皇翼其承旂兮,高翱翔之翼翼。
忽吾行此流沙兮,遵赤水而容与。
麾蛟龙使梁津兮,诏西皇使涉予。
路脩远以多艰兮,腾众车使径待。
路不周以左转兮,指西海以为期。

驾八龙之婉婉兮,载云旗之委蛇。
抑志而弭节兮,神高驰之邈邈。
奏九歌而舞韶兮,聊假日以媮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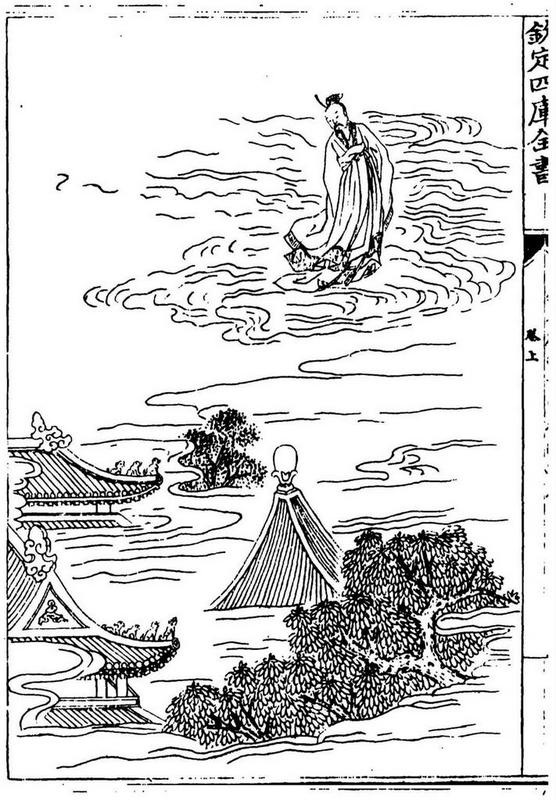
仆夫悲余马怀兮,蜷局顾而不行。
乱曰:已矣哉,国无人莫我知兮,又何怀乎故都?
既莫足与为美政兮,吾将从彭咸之所居。
遗楚王书 战国齐国 · 齐湣王
出处:全上古三代文卷八
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。今秦惠王死,武王立,张仪走魏,樗里疾、公孙衍用,而楚事秦。夫樗里疾善乎韩,而公孙衍善乎魏,楚必事秦。韩、魏恐,必因二人求合于秦,则燕赵亦宜事秦。四国争事秦,则楚为郡县矣。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、魏、燕、赵,与为从而尊周室,以案兵息民,令于天下,莫敢不乐听,则王名成矣。王率诸侯并伐,破秦必矣。王取武关、蜀、汉之地,私吴、越之富,而擅江海之利,韩、魏割上党,西薄函谷,则楚之强百万也。且王欺于张仪,亡地汉中,兵锉蓝田,天下莫不代王怀怒,今乃欲先事秦,愿大王熟计之(《史记。楚世家》)。
上书秦始皇 秦 · 李斯
出处:全秦文、文选卷三十九
臣闻吏议逐客,窃以为过矣。昔穆公求士,西取由余于戎,东得百里奚于宛,迎蹇叔于宋,来邳豹公孙支于晋。此五子者,不产于秦,穆公用之,并国三十,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,移风易俗,民以殷盛,国以富彊,百姓乐用,诸侯亲服,获楚魏之师,举地千里,至今治彊。惠王用张仪之计,拔三川之地,西并巴蜀,北收上郡,南取汉中,包九夷,制鄢郢,东据成皋之险,割膏腴之壤,遂散六国之从,使之西面事秦,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,废穰侯,逐华阳,彊公室,杜私门,蚕食诸侯,使秦成帝业。此四君者,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观之,客何负于秦哉!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纳,疏士而弗用,是使国无富利之实,而秦无彊大之名也。今陛下致昆山之玉,有和随之宝,垂明月之珠,服太阿之剑,乘纤离之马,建翠凤之旗,树灵鳝之鼓。此数宝者,秦不生一焉,而陛下悦之,何也?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,则夜光之璧不饰朝廷,犀象之器不为玩好,而赵卫之女不充后庭,骏良駃騠不实外厩,江南金锡不为用,西蜀丹青不为采。所以饰后宫,充下陈,娱心意,悦耳目者,必出于秦然后可,则是宛珠之簪,傅玑之珥,阿缟之衣,锦绣之饰,不进于前;而随俗雅化,佳冶窈窕,赵女不立于侧也。夫击瓮叩缶,弹筝搏髀,而歌呼呜呜快耳者,真秦之声也;郑卫桑间,韶虞武象者,异国之乐也。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卫,退弹筝而取韶虞,若是者何也?快意当前,适观而已矣。今取人则不然,不问可否,不论曲直,非秦者去,为客者逐。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,而所轻者在乎民人也。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。臣闻地广者粟多,国大者人众,兵彊者则士勇。是以太山不让土壤,故能成其大;河海不择细流,故能就其深;王者不却众庶,故能明其德。是以地无四方,民无异国,四时充美,鬼神降福,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。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,却宾客以业诸侯,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,裹足不入秦。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。夫物不产于秦,可宝者多;士不产于秦,愿忠者众。今逐客以资敌国,损民以益雠,内自虚而外树怨诸侯,求国无危,不可得也。
荅客难 西汉 · 东方朔
出处:全汉文 卷二十五、文选卷四十五
客难东方朔曰:「苏秦张仪壹当万乘之主,而身都卿相之位,泽及后世。今子大夫脩先王之术,慕圣人之义,讽诵诗书百家之言,不可胜记,著于竹帛,唇腐齿落,服膺而不可释,好学乐道之效,明白甚矣,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,则可谓博闻辩智矣。然悉力尽忠,以事圣帝,旷日持久,积数十年,官不过侍郎,位不过执戟,意者尚有遗行邪?同胞之徒,无所容居,其故何也」?东方先生喟然长息,仰而应之曰:「是故非子之所能备。彼一时也,此一时也,岂可同哉?夫苏秦张仪之时,周室大坏,诸侯不朝,力政争权,相擒以兵,并为十二国,未有雌雄,得士者强,失士者亡,故说得行焉。身处尊位,珍宝充内,外有仓廪,泽及后世,子孙长享。今则不然。圣帝德流,天下震慑,诸侯宾服,连四海之外以为带,安于覆盂,天下平均,合为一家,动发举事,犹运之掌,贤与不肖,何以异哉?遵天之道,顺地之理,物无不得其所。故绥之则安,动之则苦;尊之则为将,卑之则为虏;抗之则在青云之上,抑之则在深渊之下;用之则为虎,不用则为鼠;虽欲尽节效情,安知前后?夫天地之大,士民之众,竭精驰说,并进辐凑者,不可胜数,悉力慕之,困于衣食,或失门户。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,曾不得掌故,安敢望侍郎乎!传曰:『天下无害,虽有圣人,无所施才;上下和同,虽有贤者无所立功』。故曰时异事异。
虽然,安可以不务脩身乎哉?诗曰:『鼓钟于宫,声闻于外』。『鹤鸣九皋,声闻于天』。苟能脩身,何患不荣?太公体行仁义,七十有二,乃设用于文武,得信厥说,封于齐,七百岁而不绝。此士所以日夜孳孳,脩学敏行而不敢怠也。譬若鹡鸰,飞且鸣矣。传曰:『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,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,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』。『天有常度,地有常形,君子有常行;君子道其常,小人计其功』。诗云:『礼义之不愆,何恤人之言』?『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,冕而前旒,所以蔽明;黈纩充耳,所以塞聪』。明有所不见,聪有所不闻,举大德,赦小过,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。枉而直之,使自得之;优而柔之,使自求之;揆而度之,使自索之。盖圣人之教化如此,欲其自得之;自得之,则敏且广矣。
今世之处士,时虽不用,块然无徒,廓然独居,上观许由,下察接舆,计同范蠡,忠合子胥,天下和平,与义相扶,寡偶少徒,固其宜也,子何疑于予哉?若夫燕之用乐毅,秦之任李斯,郦食其之下齐,说行如流,曲从如环,所欲必得,功若丘山,海内定,国家安,是遇其时者也,子又何怪之邪?语曰:『以筦窥天,以蠡测海,以筳撞钟』,岂能通其条贯,考其文理,发其音声哉!犹是观之,譬由鼱鼩之袭狗,孤豚之咋虎,至则靡耳,何功之有?今以下愚而非处士,虽欲勿困,固不得已。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,而终惑于大道也」。
战国策书录 西汉 · 刘向
出处:全汉文 卷三十七
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,所校中《战国策》书,中书馀卷,错乱相糅莒。又有国别者八篇,少不足,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,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,除复重,得三十三篇。本字多误脱为半字,以「赵」为「肖」,以「齐」为「立」,如此字者多。中书本号,或曰《国策》,或曰《国事》,或曰《短长》,或曰《事语》,或曰《长书》,或曰《修书》。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,宜为《战国策》。其事继《春秋》以后,讫楚汉之起,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,皆定,以杀青,书可缮写,叙曰:
周室自文武始兴,崇道德,隆礼义,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,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,叙人伦,正夫妇,天下莫不晓然。论孝弟之义,惇笃之行,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,卒致之刑错四十馀年,远方慕义,莫不宾服,雅颂歌咏,以思其备。下及康昭之后,虽有衰德,其纲纪尚明,及《春秋》时巳四五百载矣。然其馀业遗烈,流而未灭,五伯之起,尊事周室,五伯之后,时君虽无德,人臣辅其君者,若郑之子产,晋之叔向,齐之晏婴,挟君辅政,以并立于中国,犹以义相支持,歌说以相感,聘觐以相交,斯会以相一,盟誓以相救,天子之命,犹有所行,会享之国,犹有所耻,小国得有所依,百姓得有所息,故孔子曰:「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」?周之流化,岂不大哉。及春秋之后,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,孔子虽论《诗》《书》,定礼乐,王道粲然分明,以匹夫无势,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,皆天下之俊也,时君莫尚之。是以王道遂用不兴,故曰「非威不立,非势不行」。仲尼既没之后,田氏取齐,六卿分晋,道德大废,上下失序。至秦孝公,捐礼让而贵战争,弃仁义而用诈谲,苟以取强而巳矣。夫篡盗之人,列为侯王,诈谲之国,兴立为强,是以传相放效,后生师之,遂相吞灭,并大兼小,暴师经岁,流血满野,父子不相亲,兄弟不相安,夫妇离散,莫保其命,涽然道德绝矣。晚世益甚,万乘之国七,千乘之国五,敌侔争权,盖为战国,贪饕无耻,竞进无厌,国异政教,各自制断。上无天子,下无方伯,力功争强,胜者为右,兵革不休,诈伪并起。当此之时,虽有道德,不得施谋,有设之强,负阻而恃固,连与交质,重约结誓,以守其国,故孟子、孙卿儒术之士,弃捐于世,而游说权谋之徒,见贵于俗。是以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、陈轸、代厉之属,生纵横短长之说,左右倾侧。苏秦为纵,张仪为横,横则秦帝,纵则楚王,所在国重,所去国轻。然当此之时,秦国最雄,诸侯方弱,苏秦结之,时六国为一,以傧背秦,秦人恐惧,不敢窥兵于关中,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。然秦国势便形利,权谋之土,事先驰之,苏秦初欲横,秦弗用,故东合纵,及苏秦死后,张仪连横,诸侯听之,西向事秦。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,据崤函之阻,跨陇蜀之饶,听众人之策,乘六世之烈,以蚕食六国,兼诸侯,并有天下,杖于谋诈之弊,终于信笃之诚,无道德之教,仁义之化,以缀天下之心,任刑罚以为治,信小术以为道,遂燔烧《诗》《书》,坑杀儒士,上小尧舜,下邈三王,二世愈甚,惠不下施,情不上达,君臣相疑,骨肉相疏,化道浅薄,纲纪坏败,民不见义,而悬于不宁,抚天下十四岁,天下大溃,诈伪之弊也。其比王德,岂不远哉!孔子曰:「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」。夫使天下有所耻,故化可致也,苟以诈伪偷活取容,自上为之,何以率下,秦之败也,不亦宜乎。战国之时,君德浅薄,为之谋策者,不得不因势而为资,据时而为□,故其谋扶急持倾,为一切之权。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,救急之势也。皆高才秀士,度时君之所能行,出奇策异智,转危为安,运亡为存,亦可喜,皆可观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《战国策书录(《战国策》剡川姚氏宋刻本)》。
孙卿书录 西汉 · 刘向
出处:全汉文 卷三十七
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,所校雠中《孙卿书》凡三百二十二篇,以相校,除复重二百九十篇,定著三十二篇,皆以定杀青,简书可缮写。
孙卿,赵人,名况。方齐宣王威王之时,聚天下贤士于稷下,尊宠之,若邹衍、田骈、淳于髡之属甚众,号曰列大夫,皆世所称,咸作书刺世。是时孙卿有秀才,年五十,始来游学,诸子之事,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。孙卿善为《诗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,至齐襄王时,孙卿最为老师,齐向修列大夫之缺,而孙卿三为祭酒焉。齐人或谗孙卿,乃适楚,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。人或谓春申君曰:「汤以七十里,文王以百里,孙卿贤者也,今与之百里地,楚其危乎」?春申君谢之。孙卿去之赵,后客或谓春申君曰:「伊尹去夏入殷,殷王而夏亡,管仲去鲁入齐,鲁弱而齐强。故贤者所在,君尊国安。今孙卿天下贤人,所去之国,其不安乎」?春申君使人聘孙卿。孙卿遗春申君书。刺楚国,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,春申君恨,复固谢孙卿,孙卿乃行,复为兰陵令。春申君死而孙卿废,因家兰陵。李斯尝为弟子,已而相秦,及韩非号韩子,又浮丘伯,皆受业为名儒。
孙卿之应聘于诸侯,见秦昭王,昭王方喜战伐,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,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。至赵,与孙膑议兵赵孝成王前,孙膑为变诈之兵,孙卿以王兵能之,不能对也,卒不能用。孙卿道守礼义,行应绳墨,安贫贱。孟子者,亦大儒,以人之性善,孙卿后孟子百馀年,以为人性恶,故作《性恶》一篇以非《孟子》。苏秦、张仪以邪道说诸侯,以大贵显,孙卿退而笑之曰:「夫不以其道进者,必不以其道亡」。
至汉兴,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,作书美孙卿。孙卿卒不用于世,老于兰陵,疾浊世之政,亡国乱君相属,不遂大道,而营乎巫祝,信示几祥,鄙儒小拘如庄周等,又滑稽乱俗,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,序列著数万言而卒,葬兰陵。而赵亦有公孙龙,为坚白异同之辨,处子之言。魏有李悝,尽地力之教。楚有尸子、长庐子、芋子,皆著书,然非先王之法也,皆不循孔氏之术,唯孟轲、孙卿为能尊仲尼,兰陵多善为学,盖以孙卿也。长老至今称之曰:「兰陵人喜字为卿」。盖以法孙卿也(案,上文至「汉兴江都」以下十七字,当在此句下。)。孟子、孙卿、董先生皆小五伯,以为仲尼之门,五尺童子,皆羞称五伯,如人君能用孙卿,庶几于王,然世终莫能用,而六国之君残灭。秦国大乱,卒以亡。观孙卿之书,其陈王道甚易行,疾世莫能用,其言凄怆,甚可痛也。呜呼,使斯人卒终于闾巷,而功业不得见于世。哀哉,可为陨涕。其书比于记传,可以为法,谨第录。臣向昧死上言,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《孙卿书录(《荀子》宋刻本)》。
蜀王本纪 其八 西汉 · 扬雄
出处:全汉文 卷五十三
蜀王据有巴蜀之地,本治广都樊乡,徙居成都。秦惠王遣张仪、司马错定蜀,因筑成都而县之。成都在赤里街,张若徙置少城内,始造府县寺舍。今与长安同制(《御览》八百八十八、《寰宇记》七十二。)。
蜀王本纪 其十 西汉 · 扬雄
出处:全汉文 卷五十三
《秦惠王本纪》曰:秦惠王欲伐蜀,乃刻五石牛(案:《御览》八百八十八引作「秦王恐无相见处,乃刻五石牛。」)。置金其后。蜀人见之,以为牛能大,便金牛下。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,能便金。蜀王以为然,即发卒千人,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,致三枚于成都。秦道得通,石牛之力也。后遣丞相张仪等,随石牛道伐蜀焉(《北堂书钞》一百十六,《艺文类聚》九十四、《白帖》九十六、《御览》三百五、又八百八十八。)。
蜀王本纪 其十四 西汉 · 扬雄
出处:全汉文 卷五十三
秦惠王遣张仪、司马错伐蜀,王开明拒战不利,退走武阳,获之(《寰宇记》七十二)。
蜀王本纪 其十五 西汉 · 扬雄
出处:全汉文 卷五十三
张仪伐蜀,蜀王开明战不胜,为仪所灭(《史记·秦本纪·索隐》)。
西岳华山庙碑(延熹八年) 汉 · 阙名
出处:全后汉文 卷一百
《周礼·职方氏》:「河南山镇曰华」,谓之西狱。《春秋传》曰:「山岳则配天」。乾坤定位,山泽通气,云行雨施,既成万物,《易》之义也。《祀典》曰:「日月星辰,所昭卬也。地理山种,所生殖也。功加于民,祀以报之。《礼记》曰:「天子祭天地及山种,岁遍焉」。自三五迭兴,其奉山川,或在天子,或在诸侯,是以唐虞畴咨四岳,五岁一巡狩,皆以四时之中月,各省其方,亲至其山,柴祭燔燎。夏、商则未闻所损益。周鉴于二代,十有二岁,王巡狩殷国,亦有事于方岳,祀以圭璧,乐奏六歌。高祖初兴,改秦淫祀,大宗承循,各诏有司,其山川在诸侯者,以时祠之。孝武皇帝修封禅之礼,思登假之道,巡省五岳,禋祀丰备,故立宫其下,宫曰集灵宫,殿曰存仙殿,门曰望仙门。仲宗示之世,重使使持节者祀焉,岁一祷而三祠。后不承前,至于亡新,浸用丘虚,讫今垣趾营兆犹存。建武之元,事举其中,礼从其省,但使二千石以岁时往祠。其有风旱,祷请祈求,靡不报应。自是以来,百有馀年,有事四巡,辄过享祭,然其所立碑石,刻纪时事,文字摩灭,莫能存识。延熹四年七月甲子,弘农太守安国亭侯,汝南袁逢,掌华岳之主,位应古制,修废起顿,闵其若兹,深达和民事神之义,精通诚至,示勺祭之福,乃案经传所载,原本所由,铭勒斯石,垂之于后。其辞曰:
岩岩西,峻极穹苍。奄有河朔,遂荒华阳。触石兴云,雨我农桑。资粮品物,亦相瑶光。崇冠二州,古曰雍梁。冯于豳岐,文武克昌。天子展义,巡狩省方。玉帛之贽,礼与岱亢。六乐之变,舞以致康。在汉中叶,建设宇堂。山岳之守,是秩是望。侯惟安国,兼命斯章。尊修灵基。肃共坛场。明德惟馨,神歆韵其芳。遏穰凶札,揪敛吉祥。岁其有年,民说无疆。
袁府君肃恭明神,易碑饰阙,会迁京兆尹。孙府君到,钦若嘉业,遵而成之。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甲子就。
按:袁府君讳逢,字周阳,汝南女阳人。孙府君讳璆,宇山陵,安乎信都人。时令朱颉。字宣得,甘陵鄃人,丞张昉,字少游,河南京人。左尉唐佑,字君惠,河南密人。主者掾华阴王苌,字德长。京兆尹敕监都水掾霸陵杜迁市石,遗书佐新丰郭香察书。刻者颍川邯郸公修苏张工阙君(阙)。(旧拓碑本《隶释》二)
显志赋(又自论) 东汉 · 冯衍
出处:全后汉文 卷二十
冯子以为大人之德,不碌碌如玉,落落如石。风兴云蒸,一龙一蛇,与道翱翔,与时变化,夫岂守一节哉!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,进退无主,屈伸无常。故曰:「有法无法,因时为业,有度无度,与物趣舍。」常务道德之实,而不求当世之名,阔略杪小之礼,荡佚人间之事。正身直行,恬然肆志。顾尝好俶傥之策,时莫能听用其谋,喟然长叹,自伤不遭。久栖迟于小官,不得舒其所怀。抑心折节,意凄情悲。夫伐冰之家,不利鸡豚之息;委积之臣,不操市井之利。况历位食禄二十余年,而财产益狭,居处益贫。惟夫君子之仕,行其道也。虑时务者不能兴其德,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。去而归家,复羁旅于州郡,身愈据职,家弥穷困,卒离饥寒之灾,有丧元子之祸。先将军葬渭陵,哀帝之崩也,营之以园。于是以新丰之东,鸿门之上,寿安之中,地势高敞,四通广大,南望郦山,北属泾、渭,东瞰河华、龙门之阳,三晋之路,西顾酆、鄗周、秦之丘,宫观之,通视千里,览见旧都,遂定茔焉。退而幽居。盖忠臣过故墟而歔欷,孝子入旧室而哀叹。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,垂鸿烈于后,遭时之祸,坟墓芜秽,春秋烝尝,昭穆无列。年衰岁暮,悼无成功,将西田牧肥饶之野,殖生产,修孝道,营宗庙,广祭祀。然后阖门讲习道德,观览乎孔、老之论,庶几乎松、乔之福。上陇阪,陟高冈,游精宇宙,流目八纮。历观九州山川之体,追览上古得失之风,悯道陵迟,伤德分崩。夫睹其终必原其始,故存其人而咏其道。疆里九野,经营五山,眇然有思陵云之意。乃作赋自厉,命其篇曰《显志》。显志者,言光明风化之情,昭章玄妙之思也。其辞曰:
开岁发春兮,百卉含英。甲子之朝兮,汨吾西征。发轫新丰兮,裴回镐京。陵飞廉而太息兮,登平阳而怀伤。悲时俗之险厄兮,哀好恶之无常。弃衡石而意量兮,随风波而飞扬。纷纶流于权利兮,亲雷同而妒异;独耿介而慕古兮,岂时人之所喜?沮先圣之成论兮,邈名贤之高风;忽道德之珍丽兮,务富贵之乐耽。遵大路而裴回兮,履孔德之窈冥;固众夫之所眩兮,孰能观于无形?行劲直以离尤兮,羌前人之所有;内自省而不惭兮,遂定志而弗改。欣吾党之唐、虞兮,悯吾生之愁勤;聊发愤而扬情兮,将以荡夫忧心。往者不可攀援兮,来者不可与期;病没世之不称兮,愿横逝而无由。陟雍畤而消摇兮,超略阳而不反。念生人之不再兮,悲六亲之日远。陟九嵏而临㟞薛兮,听泾、渭之波声。顾鸿门而歔欷兮,哀吾孤之早零。何天命之不纯兮,信吾罪之所生;伤诚善之无辜兮,赍此恨而入冥。嗟我思之不远兮,岂败事之可悔?虽九死而不瞑兮,恐余殃之有再。泪泛澜而雨集兮,气滂浡而云披;心怫郁而纡结兮,意沈抑而内悲。瞰太行之嵯峨兮,观壶口之峥嵘;悼丘墓之芜秽兮,恨昭穆之不荣。岁忽忽而日迈兮,寿冉冉其不与;耻功业之无成兮,赴原野而穷处。昔伊尹之干汤兮,七十说而乃信;皋陶钓于雷泽兮,赖虞舜而后亲。无二士之遭遇兮,抱忠贞而莫达;率妻子而耕耘兮,委厥美而不伐。韩卢抑而不纵兮,骐骥绊而不试;独慷慨而远览兮,非庸庸之所识。卑卫赐之阜货兮,高颜回之所慕;重祖考之洪烈兮,故收功于此路。循四时之代谢兮,分五土之刑德;相林麓之所产兮,尝水泉之所殖。修神农之本业兮,采轩辕之奇策;追周度之遗教兮,轶范蠡之绝迹。陟陇山以隃望兮,眇然览于八荒;风波飘其并兴兮,情惆怅而增伤。览河、华之泱漭兮,望秦、晋之故国。愤冯亭之不遂兮,愠知之遭惑。流山岳而周览兮,徇碣石与洞庭;浮江、河而入海兮,溯淮、济而上征。瞻燕、齐之旧居兮,历宋、楚之名都;哀群后之不祀兮,痛列国这为墟。驰中夏而升降兮,路纡轸而多艰;讲圣哲之通论兮,心愊忆而纷纭。惟天路之同轨兮,或帝王之异政;尧、舜焕其荡荡兮,禹承平而革命。并日夜而幽思兮,终悇憛而洞疑;高阳邈其超远兮,世孰可以论兹?讯夏启于甘泽兮,伤帝典之始倾;颂成、康之载德兮,咏《南风》之高声。思唐、虞之晏晏兮,揖稷、契以为朋;昔裔纷其条畅兮,至汤、武而勃兴。昔三后之纯粹兮,每季世而穷祸;吊夏桀于南巢兮,哭殷纣于牧野。诏伊尹于亳郊兮,享吕望于酆州;功与日月齐光兮,名与三王争流。杨朱号乎衢路兮,墨子泣乎白丝;知渐染之易性兮,怨造作之弗思。美《关雎》之识微兮,悯王道之将崩;拔周、唐之盛德兮,捃桓、文之谲功。忿战国之遘祸兮,憎权臣之擅强;黜楚子于南郢兮,执赵武于溴梁。善忠信之救时兮,恶诈谋之妄作;聘申叔于陈蔡兮,禽荀息于虞、虢。诛犁锄之介圣兮,讨臧仓之愬知;𡢀子反于彭城兮,爵管仲于夷仪。疾兵革之浸滋兮,苦攻伐之萌生;沈孙武于五湖兮,斩白起于长平。恶丛巧之乱世兮,毒纵横之败俗;流苏秦于洹水兮,幽张仪于鬼谷。澄德化之陵迟兮,烈列罚之峭峻;燔商鞅之法术兮,烧韩非之说论。诮始皇之跋扈兮,投李斯于四裔;灭先王之法则兮,祸浸淫而弘大。援前圣以制中兮,矫二主之骄奢;馌女齐于绛台兮,飨椒举于章华。摛道德之光耀兮,匡衰世之眇风;褒宋襄于泓谷兮,表季札于延陵。摭仁智之英华兮,激乱国之末流;观郑侨于溱、洧兮,访晏婴于营丘。日曀曀其将暮兮,独于邑而烦惑;夫何九州之博大兮,迷不知路之南北。驷素虬而驰骋兮,乘翠云上佯;就伯夷而折中兮,得务光而愈明。款子高于中野兮,遇伯成而定虑;钦真人之德美兮,淹踌躇而弗去。意斟愖而不澹兮,俟回风而容与;求善卷之所存兮,遇许由于负黍。轫吾车于箕阳兮,秣吾马于颍浒;闻至言而晓领兮,还吾反乎故宇。览天地之幽奥兮,统万物之维纲;究阴阳之变化兮,昭五德之精光。跃青龙于沧海兮,豢白虎于金山;凿岩石而为室兮,托高阳以养仙。神雀翔于鸿崖兮,玄武潜于婴冥;伏朱楼而四望兮,采三秀之华英(《文选·登楼赋》注,谢朓《鼓吹曲》注)。纂前修之夸节兮,曜往昔之光勋;披绮季之丽服兮,扬屈原之灵芬。高吾冠之,岌岌兮,长吾佩之洋洋;饮六醴之清液兮,食五芝之茂英。揵六枳而为篱兮(《文选·天台赋》注、《闲居赋》注),筑蕙若而为室;播兰芷于中庭兮,列杜衡于外术。攒射干杂蘼芜兮,构木兰与新夷;光扈扈而断耀兮,纷郁郁而畅美;华芳晔其发越兮,时恍惚而莫贵;莫惜身之坎轲兮,怜众美之憔悴。游精神于长兮,抗玄妙之常操;处清静以养志兮,实吾心之所乐。山峨峨而造天兮,林冥冥而畅茂;鸾回翔索其群兮,鹿哀鸣而求其友。诵古今以散思兮,览圣贤以自镇;嘉孔丘之知命兮,大老聃之贵玄;德与道其孰宝兮?名与身其孰亲?陂山谷而闲处兮,守寂寞而存神夫庄周之钓鱼兮,辞卿相之显位;于陵子之灌园兮,似至人之仿佛。盖除约而得道兮,羌穷悟而入术;离尘垢之窈冥兮,配乔、松之妙节。惟吾志之所庶兮,固与俗之不同;既俶傥而高引兮,愿观其从容(《后汉·冯衍传》,又略见《艺文类聚》二十六)。
荅宾戏 东汉 · 班固
出处:全后汉文 卷二十五、文选卷四十五
永平中为郎,典校秘书,专笃志于儒学,以著述为业。或讥以无功,又感东方朔杨雄自喻,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,曾不折之以正道,明君子之所守,故聊复应焉。其辞曰:宾戏主人曰:「盖闻圣人有一定之论,烈士有不易之分,亦云名而已矣。故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。夫德不得后身而特盛,功不得背时而独彰。是以圣哲之治,栖栖遑遑,孔席不暖,墨突不黔。由此言之,取舍者昔人之上务,著作者前列之馀事耳。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,躬带绂冕之服,浮英华,湛道德,矕龙虎之文,旧矣。卒不能摅首尾,奋翼鳞,振拔洿涂,跨腾风云,使见之者影骇,闻之者响震。徒乐枕经籍书,纡体衡门,上无所蒂,下无所根。独摅意乎宇宙之外,锐思于毫芒之内,潜神默记,縆以年岁。然而器不贾于当己,用不效于一世,虽驰辩如涛波,摛藻如春华,犹无益于殿最也。意者,且运朝夕之策,定合会之计,使存有显号,亡有美谥,不亦优乎」?主人逌尔而笑曰:「若宾之言,所谓见世利之华,闇道德之实,守窔奥之荧烛,未仰天庭而睹白日也。曩者王涂芜秽,周失其驭,侯伯方轨,战国横骛,于是七雄虓阚,分裂诸夏,龙战虎争。游说之徒,风飑电激,并起而救之,其馀猋飞景附,霅煜其閒者,盖不可胜载。当此之时,搦朽摩钝,铅刀皆能一断,是故鲁连飞一矢而蹶千金,虞卿以顾眄而捐相印。夫啾发投曲,感耳之声,合之律度,淫䵷而不可听者,非韶夏之乐也。因势合变,遇时之容,风移俗易,乖迕而不可通者,非君子之法也。及至从人合之,衡人散之,亡命漂说,羁旅骋辞,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,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,彼皆蹑风尘之会,履颠沛之势,掳徼乘邪,以求一日之富贵,朝为荣华,夕为憔悴,福不盈眦,祸溢于世,凶人且以自悔,况吉士而是赖乎?且功不可以虚成,名不可以伪立,韩设辨以激君,吕行诈以贾国。说难既遒,其身乃囚;秦货既贵,厥宗亦坠。是以仲尼抗浮云之志,孟轲养浩然之气,彼岂乐为迂阔哉?道不可以贰也。方今大汉洒埽群秽,夷险芟荒,廓帝纮,恢皇纲,基隆于羲农,规广于黄唐;其君天下也,炎之如日,威之如神,函之如海,养之如春。是以六合之内,莫不同源共流,沐浴玄德,禀仰太和,枝附叶著,譬犹草木之植山林,鸟鱼之毓川泽,得气者蕃滋,失时者零落,参天地而施化,岂云人事之厚薄哉?今吾子处皇代而论战国,曜所闻而疑所觌,欲从堥敦而度高乎泰山,怀氿滥而测深乎重渊,亦未至也」。宾曰:「若夫鞅斯之伦,衰周之凶人,既闻命矣。敢问上古之士,处身行道,辅世成名,可述于后者,默而已乎」?主人曰:「何为其然也!昔者咎繇谟虞,箕子访周,言通帝王,谋合神圣;殷说梦发于傅岩,周望兆动于渭滨,齐宁激声于康衢,汉良受书于邳垠,皆俟命而神交,匪词言之所信,故能建必然之策,展无穷之勋也。近者陆子优游,新语以兴;董生下帷,发藻儒林;刘向司籍,辨章旧闻;扬雄谭思,法言太玄。皆及时君之门闱,究先圣之壶奥,婆娑乎术艺之场,休息乎篇籍之囿,以全其质而发其文,用纳乎圣德,烈炳乎后人,斯非亚与!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阳,柳惠降志于辱仕,颜潜乐于箪瓢,孔终篇于西狩,声盈塞于天渊,真吾徒之师表也。且吾闻之:一阴一阳,天地之方;乃文乃质,王道之纲;有同有异,圣哲之常。故曰:慎脩所志,守尔天符,委命供己,味道之腴,神之听之,名其舍诸!宾又不闻和氏之璧,韫于荆石,隋侯之珠,藏于蚌蛤乎?历世莫视,不知其将含景曜,吐英精,旷千载而流光也。应龙潜于潢污,鱼鼋媟之,不睹其能奋灵德,合风云,超忽荒而躆昊苍也。故夫泥蟠而天飞者,应龙之神也;先贱而后贵者,和隋之珍也;时暗而久章者,君子之真也。若乃牙旷清耳于管弦,离娄眇目于毫分;逢蒙绝技于弧矢,般输搉巧于斧斤;良乐轶能于相驭,乌获抗力于千钧;和鹊发精于针石,研桑心计于无垠。走亦不任厕技于彼列,故密尔自娱于斯文」。
离骚经 东汉 · 王逸
出处:全后汉文 卷五十七
《离骚经》者,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与楚同姓,仕于怀王,为三闾大夫。三闾之职,掌王族三姓,曰昭、屈、景。屈原序其谱属,率其贤良,以厉国士。入则与王图议政事,决定嫌疑。出则监察群下,应对诸侯。谋行职修,王甚珍之。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,共谮毁之,王乃疏屈原。屈原执履忠贞,而被谗邪,忧心烦乱,不知所诉,乃作《离骚经》。离,别也。骚,愁也。经径也。言己放逐离别,中心愁思,犹依道径,以风谏君也。故上述唐、虞、三后之制,下序桀、纣、羿、浇之败,冀君觉悟,反于正道而还己也。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,令绝齐交。又使诱楚,请与俱会武关,遂胁与俱归,拘留不遣,卒客死于秦。其子襄王,复用谗言,迁屈原于江南。屈原放在草野,复作《九章》,援天引圣,以自证明。终不见省,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,遂赴汨渊,自沈而死。《离骚》之文,依《诗》取兴,引类譬谕,故善鸟香草,以配忠贞;恶禽臭物,以比谗佞;灵修美人,以媲于君,宓妃佚女,以譬贤臣;虬龙鸾凤,以托君子;飘风云霓,以为小人。其词温而雅,其义皎而朗。凡百君子,莫不慕其清高,嘉其文采,哀其不遇,而悯其志焉。